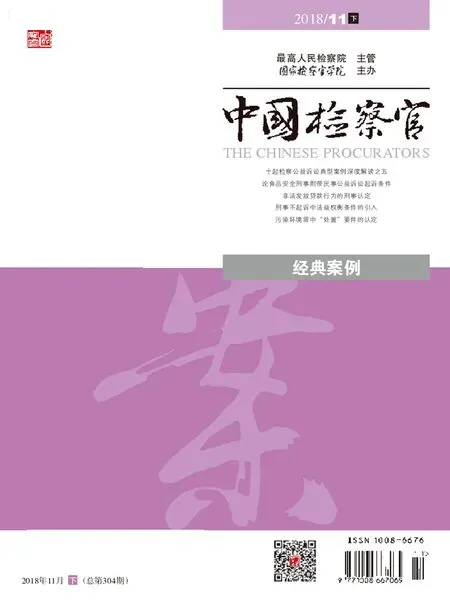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体与程序问题实证分析*
——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S分院为样本
文◎李毅磊** 赵 锐*** 江 威****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具有犯罪智能科技化、犯罪集团职业化、犯罪跨境跨国化以及犯罪高度隐匿化等特征,致使该类案件在办理时缺乏统一认定标准。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通过总结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的犯罪特征,深度剖析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程序法和实体法上面临的困难,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S分院办理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特征
(一)以公司作为诈骗集团载体,犯罪嫌疑人职业化程度高
以重庆市F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康某某等22人诈骗案为例。2016年年底,犯罪嫌疑人康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贸大厦等地租赁写字楼,购买电脑、电话等作案工具,注册大量的微信、支付宝等网络账号,租用网络服务器、建立涉案网站,非法成立名为北京ZR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R公司”)的网络诈骗集团。该集团分为北京总部及省市级代理,其中北京总部下属三个部门,由两个招商部和一个制卡部构成。省市级代理,分属全国各地各省市,共发展100余个代理点。其中,招商部又下设业务部、车贷部及财务部。该公司的具体诈骗行为方式是,公司业务员通过微信、百度等社交软件,向被害人发送推广事先编辑好的诈骗讯息,向被害人宣称年龄在18-65周岁,不论征信是否良好,只要是中国公民都可以办理ZR卡,并承诺办卡之后,可申请30万的额度在网上商城消费、零首付购车、循环积分套现等,待被害人信以为真后,便会联系业务员办理,业务员会假借收取制卡费、激活费为由骗取被害人4500元至1万元不等的费用,事后在被害人要求履行事先承诺事项时,犯罪嫌疑人以征信不好、商城缺货等理由,给被害人设置重重障碍,使其放弃网上购物和贷款,从而达到诈骗目的。2017年3月至12月,ZR诈骗集团多次通过前述方式诈骗他人钱财,共计诈骗5631人次,涉案金额1156.40万元。不难看出,康某某等人的诈骗方式先是通过成立ZR公司作为该犯罪集团的载体,继而细化公司分工推广下级代理等手段掩盖犯罪目的,最后用所谓“套路贷”的方式,[1]即假借无征信办理贷款为名实为骗取被害人制卡费、激活费等费用。该犯罪集团人员构成,从职业经理人、部门主管到车贷业务员、办卡业务员、制卡员,俨然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职业化程度高的网络诈骗集团。
(二)以假乱真、上下游犯罪联动,犯罪嫌疑人科技化程度高
以重庆市F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廖某某等16人涉嫌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廖某某等人预谋电话诈骗后,通过QQ通讯工具,以30-35元/条的价格从犯罪嫌疑人付某某等人处购买包括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住址、意向发卡行名称、额度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嫌疑人廖某某等人以某担保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向被害人拨打电话,询问被害人是否需要办理信用卡,待被害人同意后,犯罪嫌疑人廖某某等人将被害人个人信息发送给专门制作假信用卡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王某某等人使用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处购买的空白信用卡,按照被害人个人信息制作好相应银行信用卡,通过快递送达给被害人,并将快递单号发送给廖某某等人。廖某某等人确认被害人收到假信用卡后,再次联系被害人,以收取开卡费、作银行流水等方式,让被害人向指定账户汇入数百至上万元不等。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廖某某等人亲自或者通过制卡人王某某等人操作一个从犯罪嫌疑人浦某某处购买的假二维码后台,通过更改数据,使被害人在通过该二维码进入信用卡办理进度查询网站后,发现自己信用卡内增加了可用金额,误以为自己办的信用卡是真的。最终,犯罪嫌疑人廖某某等人收到赃款后,自己或者通过专门取款的人将赃款取出,完成诈骗。现已查明廖某某共计诈骗308人次,遍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诈骗金额120余万元。由此可见,此类“以假乱真”的诈骗方式之所以能够得逞,与信息泄露、提供空白信用卡、制作假信用卡、更改二维码数据等行为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而本案涉嫌的上下游犯罪有四种之多,即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上下联动关系不可谓不强、科技化程度不可谓不高。
(三)以发放社会扶贫款为诱饵,犯罪嫌疑人隐蔽化程度强
以重庆市F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饶某某等27人涉嫌诈骗罪案件为例。自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犯罪嫌疑人饶某某提供场地、办公设备和被害人个人信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多名话务员冒充上海市中医院主任、医生、中国人民银行财务总监、医保局工作人员等身份,使用上海021号码网络电话、无线固话座机、手机拨打被害人的电话,虚构为被害人办理6万、36万等金额的社会扶贫款,以收取检测费、个人所得税、转账拨款费、公证费、担保费等为由多次诈骗他人财物。至案发时,饶某某等人诈骗人数共计472人次,犯罪金额300余万元。此类“扶贫诈骗”虽然系传统的电信诈骗方式,但其针对的对象基本上属于农村贫困户,被害人群体受教育程度低、信息获取渠道窄,加之犯罪嫌疑人相互配合,分演医生、银行工作人员、医保局工作人员等多种角色,又使用难以寻找踪迹的网络电话,犯罪既遂后也难以被查获,隐蔽性极强。
(四)以异性引诱实施“仙人跳”,犯罪嫌疑人跨区域作案范围大
以重庆市W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44人涉嫌诈骗罪案件为例。2015年9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等人负责建立和管理在辽宁省鞍山市的多个诈骗窝点,并招募多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该诈骗集团的诈骗方法包括以找工作或以交男女朋友为名,邀约其同学、朋友或网友到辽宁省鞍山市加入该诈骗组织;或者在相亲、交友网站上以女性身份注册账号,与男性网友通过QQ、微信加为好友,和对方以男女朋友交往后,以愿意到男方生活的城市和男方一起生活为由,编造需要路费、途中生活费、住宿费及途中生病的医疗费、手术费,或是以住宿时损害宾馆电脑赔偿费、见面保证费等为借口,诈骗男性网友钱财。各个诈骗窝点均有女性成员,以帮助该窝点内男性成员实施诈骗时与对方打接电话、冒充护士身份等;窝点内男性成员则相互帮助冒充医生、列车长、宾馆老板等身份,并制作假的火车票、检查单等。至案发时,张某某等人采取上述诈骗方式共计诈骗全国各地被害人61人次,诈骗金额34万余元。此类诈骗方式是女性通过相亲交友平台网上结识男性,继而以谈恋爱、共同生活为名继续引诱男性上当,最后为其支付见面所需的路费等费用,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可以归类为升级版“仙人跳”。
二、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实体法方面的疑难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完成形态的标准
根据刑法通说观点,诈骗罪作为典型的结果犯,要求以一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既遂条件。如何判断诈骗损害结果的发生,学界存着“占有说”“控制说”“失控说”“损失说”和“失控加控制说”等观点的争论。[2]以重庆市D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罗某某诈骗案为例。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被告人罗某某通过多个QQ账户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低价销售品牌手机等物品的信息,在成功吸引其他QQ用户后,再通过让被害人支付手机购买费、手机激活费、退款保证金等名义骗取被害人钱财。期间,被告人罗某某除通过自己使用的支付宝账户用于直接收取诈骗款外,还通过他人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以及其他商家提供的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收取诈骗款,再通过向商家支付手续费的方式获取诈骗款。被告人罗某某先后26次实施诈骗,诈骗金额共计6.5万余元,其中通过王某某提供的QQ号获取诈骗金额2.9万余元;某平台商家收款7次,涉案金额7332元。本案中,对罗某某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获取诈骗款认定为既遂没有争议,难点在于某平台商家收取的7332元诈骗款犯罪形态的问题。如果坚持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一样的“失控加控制说”,财产所有人虽然暂时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但其拥有一定的救济条件,如向该平台运营商申诉等,故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完全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应坚持“控制说”,行为人对财产拥有了实际控制权即可。理由在于:一是“控制说”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严打击、惩处的立场,与我国严惩电信诈骗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符合;二是在电信网络诈骗中,采取“控制说”更符合电信诈骗的行为特点,例如,对于盗窃信用卡、抢劫信用卡的行为,一般以行为人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认定犯罪数额,而盗窃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对于记名、可挂失和无记名、无法挂失的情形,在数额认定上也作了相应的区分。虽然诈骗犯罪为交付类犯罪,但电信网络诈骗有拟制交付的情形。一般诈骗行为中,唯有在行为人实际取得被害人自愿交付的财物的情况下,其行为才能构成既遂。对于网络诈骗,特别是存在第三方运营商的时候,交付存在延时性,采取“失控说”难以对网络财产行为进行综合评价,采取 “失控加控制说”则标准过严,不利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
(二)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变现行为的认定
对帮助取款、变现行为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一是罪名认定存在争议。从现有资料来看,各地法院的定性不一,争议焦点在于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及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几个罪名的适用,不仅体现于不同案件中的帮助取款人之定性,而且还体现于同一类案件中帮助取款人既实施了电信诈骗行为又实施了取款行为之情形定性特别是网络诈骗中明知行为人诈骗的情况下,帮助行为人网上转账的行为的认定。二是主从犯认定存在一定分歧。一般情况下,帮助取款人均认定为从犯。而在实践当中,帮助取款人没有参与诈骗的实行行为,虽然其对赃款的提取和变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仍将其认定为从犯不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3]三是罪数也存在一定争议。为了逃避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往往将诈骗所得钱款快速分散至事先准备好的各地银行卡中,并指使取款人实现“异地取款”。从现有情况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助取款人涉及的银行卡或信用卡少则数张,多则数十张数百张,其中不乏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伪造变造信用卡的情形,是典型的牵连犯,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存在争议。
(三)如何理解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这一条属于明显的法律拟制,当无法查清犯罪数额的时候才能够适用,那么如何明确界定“诈骗信息”无疑是重中之重。有观点认为,将含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信息统一认定为诈骗信息。[4]也有意见认为,只能将含有明确的诈骗数额且对象明确的虚假信息认定为诈骗信息。[5]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明显有失偏颇,前者失之于宽,有滥用打击之嫌,后者则标准太严,不利于遏制诈骗信息的泛滥。因此,有必要进行折中适用,即指向性明确、含有一定诈骗数额的信息,均可视为诈骗信息。
(四)共犯参与诈骗期间及作用地位的认定
《意见》规定:“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犯罪集团中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依法从严惩处。”故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因涉案人数较多,且各被告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属于复杂的共同犯罪或团伙犯罪。因此,根据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以及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正确区分主、从犯,从而更准确地量刑,是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按照传统观点,认定主从犯以行为人是否系实行犯为标准,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考察行为人是否系犯意的发起者、犯罪的纠集者、指挥者、主要责任者,是否参与了犯罪的全过程或关键环节等,综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就团伙性较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说,虽然各层面人员所实施的行为都可以说是诈骗活动成功的关键环节,但组织、策划、安排、管理各层面人员的团伙核心成员,才是犯意的发起者、整个诈骗犯罪行为的预谋者和主要责任人。对于电信网络诈骗而言,情形有所不同,特别是有的行为人虽然未在一开始就参与诈骗活动,但其参与的期间却起了关键的、主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其参与的期间进行有效界定。另外,一些共犯的作用地位难以界定,特别是在主犯未到案的情况下,如何划分其他共犯责任是疑难问题。
三、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程序法方面的疑难问题
(一)如何理解管辖异议时的有利于诉讼原则
《意见》规定:“对因网络交易、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关系形成多层级链条、跨区域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案件,可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电信网络诈骗中,往往会存在管辖异议,正确理解有利于诉讼原则可以准确界定管辖权。有意见认为,有利于诉讼原则应当采用便宜主义原则,即由首先介入侦查的侦查机关所在地审判机关认定为有利于诉讼。还有意见认为,有利于诉讼应当赋予公诉方有管辖选择权,即检察机关有决定起诉管辖的权力。上述意见均难以体现“有利于诉讼原则”,均不能有力解决管辖异议这一难题。
(二)电信诈骗技术侦查证据的转化与采信
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技术侦查手段是近年来重要侦查手段之一,然而技术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有:一是启动技术侦查手段审批程序;二是如果技术侦查在前而刑事立案在后,那么此阶段收集到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如何确定;三是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所获取证据的证据资格,其中涉及到转化的主体、转化的形式、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的审查等;四是如何确定技术侦查的对象系犯罪嫌疑人,当犯罪嫌疑人提出异议的,是否必须经声纹鉴定;五是怎样实现技侦证据运用与技侦手段保密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诈骗中被害人身份的认定及其陈述的充分程度
《意见》规定:“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该条规定对被害人身份的证明责任进行了降低,更有利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然而,一方面,一些被害人使用没有实名认证的网络账号,其身份的核实和调查存在较大困难;另一方面,虽然欠缺被害人陈述可以由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予以替代,但其充分的程度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明标准
主观明知作为主观性目的,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在动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主观性目的的证明难度非常大。既要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又要综合考察一些品格证据,诸如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实践中认定标准不一,有必要进行厘清。
四、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疑难问题的有限路径
(一)畅通电信网络防范机制,强调预防机制的有效建立
由于一旦发生电信网络诈骗,常常难以在第一时间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因此,强调预防机制非常有必要。一方面,建立公安机关与银行系统深度协作机制,重点或者说关键点是银行系统要为公安机关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实现联动反应,提供先行冻结、深度查询等业务;另一方面,要强化网络运营商抵制和杜绝诈骗信息的义务,网络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运营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宣传和监管,做到预防和打击并重。
(二)进一步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构成,准确打击犯罪
检察机关要切实学习和钻研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手段、新形势,改变机械套用传统诈骗的惯性思维,进一步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的理解和适用。如,诈骗犯罪形态的认定标准、共同犯罪作用的界分、承继型诈骗罪名的区分等问题。
(三)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罪认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体系
从《意见》的精神来看,电信网络诈骗有跨区域性强、被害人多的基本特点,造成一些证据取证非常困难,因此很有必要降低其证明标准,如被害人陈述可来用客观性证据代替的原则。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同时,实行差异化的证明标准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对于被害人众多的网络诈骗犯罪,单笔事实证据充分标准应有所降低,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或者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诈骗事实和诈骗金额的即可,不必苛求证据种类的多样性和全面性。
注释:
[1]姚勇胜:《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探析》,载《福建法学》2017年第4期。
[2]宋可、白文静:《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题剖析》,载《行政与法》2017年第11期。
[3]孟强:《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帮助犯定罪量刑研究》,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4]赵学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与司法适用》,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
[5]陈晓娟:《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犯罪学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