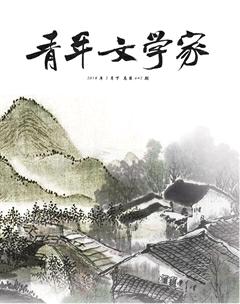盖梯尔问题与认识论的转向及其意义
张天阳+黄飞瑜+王诗静
摘 要:埃德蒙德-盖梯尔于1963年发表了《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知识吗?》一文,这篇短小的文章彻底改变了认识论的研究框架。自那以后,英美哲学界对“epistemology”的讨论变为了对于所谓“盖梯尔问题”的各种回应。依于其研究问题之指称的根本性转变,“epistemology”一词也被中文世界更多地翻译为“知识论”。如今有些学者认为,对此的研究成果固然汗牛充栋,但是“知识论”已经失去了“认识论”的宏大主题,研究视野似乎过于狭隘。然而,这种对于知识论的诘难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在自然科学的参与之下,传统的认识论问题被新兴的认知科学所讨论。知识论自身的研究成果也能够通过与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焕发生机。
关键词:知识论;辩护;盖梯尔;自然主义;认知科学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张天阳,男,汉族,山西文水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第二作者黄飞瑜,女,汉族,福建泉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第三作者王诗静,女,汉族,江苏省淮安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2
一、盖梯尔问题与“epistemology”的概念辨析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的定义,即知识是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一观点认为,首先,知识必定是认知主体的信念;其次,这一信念所表达的不能是假命题;最后,为了确保认知主体的这一信念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和巧合而为真,认知主体必须给出相信这一信念的理由,即为之辩护。这一观点简称JTB(Justified True Belief)原则。JTB原则自诞生伊始,长期没有受到系统的反驳。直到1963年,盖梯尔在《分析》上发表了《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知识吗?》一文,才撼动了这一理论,关于知识本质的问题开始正式被广泛研究。
盖梯尔教授在论文的开头给出了JTB原则的形式化表达:
S知道命题P当且仅当(1)P是真的;(2)S相信P是真的;(3)S有理由地相信P是真的。[1]
在下文中,他指出上述条件并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又构造了一个传递原则:如果S有理由相信真命题P,P又蕴含命题Q,那么S同样有理由相信Q,这一构造也明显符合形式推演规则。基于这一设定,他给出了两个反驳JTB原则的有力案例,因为两者具有较大的同构性,下面仅阐述其中之一。
A和B同时申请一份工作,A有着有力的证据相信,B将会得到这份工作并且B的兜里有十元硬币,根据传递原则,A也有理由相信兜里有十元硬币的人将会获得这份工作。最后,公司恰恰录用了A,而A自己的兜里也有一枚十元硬币,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那么,携带十元硬币的人会被录用这一命题是真的,它满足了JTB原则,但是很明显不能说A知道这一命题,亦即,它并非A的知识。另一个案例与此基本同构,就不再赘述。盖梯尔给出的案例在反驳JTB上无懈可击,英美世界权威的斯坦福哲学百科这样总结到:
为了规定知识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在JTB上添加什么要素呢?这个问题被称为盖梯尔问题。[2]
现在来看,这篇论文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发表以后,带来了巨大的反响。众多学者为解决所谓的“盖梯尔问题”殚精竭虑,留下了非常多的学术成果。其中大多集中于辩护问题,意图在承认JTB原则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的前提之下给出知识的第四个条件;也有的另寻僻径,否认JTB原则的必要性,对知识的条件进行重新刻画。总而言之,从那以后作为一门学科的“epistemology”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包括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乃至怀疑主义等,都试图对知识下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文世界也将“epistemology”更多地翻译为“知识论”而非“认识论”,徐英瑾对此有过如下总结:
知识论的核心关涉是:我们应当按照如何的步骤来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使得信念得到辩护),而不是我们在事实上是如何获取知识的。[3]
二、传统认识论问题向认知科学的让渡
对专注于回答辩护问题的知识论研究,從来都不缺乏批评的声音,即“epistemology”这一传统的哲学分支变成了与哲学内部其他各个门类相关性极低的小众方向,作为知识论的认识论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哲学语境中的宏大主题与研究问题。
然而,对知识论研究的这种指责未免有失偏颇,主要体现在两点:(1)从外部来看,固然知识论不再专门探讨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认知科学的兴起,接过了认识论问题的大旗;(2)从内部看,即使讨论的问题相对窄化,专注于研究知识本身的知识论也并非不能有所作为,知识论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学科内部开展深入研究,并以独立学科的身份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对话,发挥独特的作用。
认知科学是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兴起的,涉及哲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可以看到,认知科学可以广泛地吸收科学前沿的成果,试图以一种自然主义的视角研究认识问题,自然主义也是英美哲学界自蒯因以后最具生命力的“元哲学”[4]。那么,将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即我们事实上是如何获取知识的这一问题——让渡给这种与自然科学似乎过度“亲密”的学科,是否代表了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势与堕落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首先,从哲学史上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本就是非常密切的,哲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在其时代背景之下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科学家,在这个层次认知科学可以看作是哲学与科学之间良性互动的回归。其次,即使是传统认识论问题的哲学式解答,也不能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相抵触,譬如康德的时空观就因为非欧几何理论的出现而破产,直接引发整个哲学体系产生崩塌。最后,身心问题是传统认识论所关涉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出该问题的笛卡尔对其方案也持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endprint
虽然灵魂和整个身体相结合,然而它是特定地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发挥功能而不是全部。[5]
笛卡尔趋向于将心灵的来源归结于大脑而非所谓灵魂,《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对此总结道:“……笛卡尔本人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方法论启示,心身问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的主要希望在于科学……”[6]今天研究身心问题的主力军——心灵哲学的研究就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话中开展的。另外,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对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无疑大有裨益,而在这中间,哲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位不可还原。
三、知识论的现实意义
那么某种程度上确实成为“小众学科”的知识论,是否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呢?这种指责可以用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区分来回应,苗力田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重现世,尚世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然而,实际情况是:以西方思想为内核的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迅速发展,人类生产力也随之飞跃,放下很多哲学家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提,显而易见的是学以致知的学说对现世的影响不一定比学以致用的学说小。对知识论研究现实意义的刻画可以从与各个学科的交流来谈起:
(1)与人工智能的交流。在此引用《西方哲学问题研究》中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是进一步探索人类智能的秘密,揭示人类思维的规律,利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来为人类自身服务。[7]
就现状来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产品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代表强AI已经指日可待,比起单一用途的AI,通用AI现在八字尚无一撇。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卷入AI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的争论中去,讨论范围仅限于將其视为研究人类心灵本质的工具。人类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为了使除人类以外的、与人类心智能力相仿的智能体成为现实,必须要关注知识的获取问题,而知识论研究的就是人类应该通过何种步骤获取知识,在预设人类是唯一智能存在的前提下,AI很大程度上需要效仿人类。在这方面,知识论的成果完全可以指导人工智能研究,促使其设计理念进行重构。
(2)与法律诉讼进行交流。法律诉讼过程涉及真相,需要对记忆、证言(testimony)和物证(physical evidence)等重要因素在获取难易程度、可靠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典型的辩护过程,与知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重合。知识论可以为之提供顶层判定标准,从获取难度、可靠程度等方面考察各个辩护因素,以判断一个辩护的有效性。
概而言之,盖梯尔问题是20世纪发现的极有价值的哲学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重新改组了“epistemology”的整个研究框架,在此意义上,中文世界将之翻译为“知识论”而非“认识论”恰如其分,而如今乃至未来的知识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在新的处境之下,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其作用。
注释:
[1]Gettier E L.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J]. analysis, 1963, 23(6): 121-123.
[2]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网页版的“epistemology”词条
[3]徐英瑾.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一种理性的重构和辩护[J]. 学术月刊,2012,44(04):55-64.
[4]参见程炼. 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J].科学文化评论,2012,9(01):29-40.
[5]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Ⅰ[M].pp.340
[6]张志伟等著.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03重印),第88页.
[7]张志伟等著.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03重印),第106页.
参考文献:
[1]Gettier E L.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J]. analysis, 1963, 23(6): 121-123.
[2]Descartes.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Ⅰ[M].trans.by J.Cotting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85.
[3]徐英瑾.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一种理性的重构和辩护[J].学术月刊,2012,44(04):55-64.
[4]程炼. 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J]. 科学文化评论,2012,9(01):29-40.
[5]张志伟等著.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03重印).endprint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