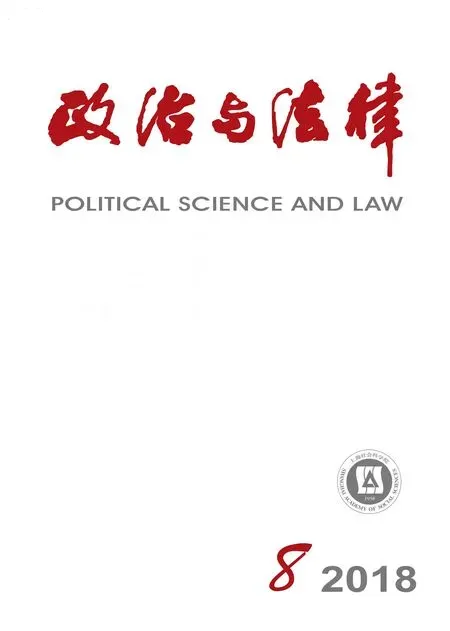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规范解释*
石聚航
(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一、问题的提出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1997年我国《刑法》新设的罪名,当时立法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衔接1993年9月2日通过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诋毁商业信誉的规定。在网络经济时代下,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作为企业无形资产被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实践中,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案件时有发生,从早期的“纸馅包子案”到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的鸿茅药酒案,这一原本在刑事审判中适用频率并不高的罪名,①截止2018年5月29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集到涉及该罪罪名的裁判文书总计为19篇。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该罪为篇名搜索的文献仅为46篇。目前成为了热点罪名。刑法学理论对于该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成要件的理解上,如对于捏造、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界定。然而,在审判实践中,该罪的司法适用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于刑法理论的图景,主要体现为利用网络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几乎成为该罪司法适用中的主要类型,根据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第74条的规定,在没有达到数额标准(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利用互联网或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也可以立案追诉。问题在于,这一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存在过于机械的问题,如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相关信息但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经济损失的,是否也可以构成该罪。倘若过度扩张解释,则可能会由于该罪主要是网络型犯罪,从而导致该罪成为行为犯。进而,该罪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限制处罚过宽的立法旨趣将落空。此外,对于“捏造”“他人”的理解,审判实践也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这种理解是否会导致裁判结论与该罪的法益之间的冲突,抑或是否需要重构该罪的法益等等问题,值得刑法理论与实务的关注。
法益是解释构成要件的基础,对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理解,应当在解释方法上注重规范理解,在罪量标准的设定上应当从体系上予以把握,从而进一步明确该罪司法适用中的相关标准,解决相关问题。
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法益应是个体经营者利益的反射利益
(一)刑法理论基本不涉及该罪法益判断带来的困惑
该罪的刑法条文表述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若进行体系性的理解,刑法将该罪作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首个罪名,其侵犯的法益应当是经济秩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刑法学教材基本上不涉及该罪法益的论述,通常直接阐明该罪的概念,即“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②参见黎宏:《刑法学各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张明楷:《刑法学(下)》(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29页;周光权:《刑法各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只有少量的论文在讨论该罪时,会涉及该罪的法益。例如,李妮:《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6页。理论上对该罪法益的着墨不多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作为该罪的犯罪对象,可以直接反映出该罪的法益,因此,如果侵犯的不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信誉或商品声誉的,自然不可能构成该罪,倘若构成诽谤罪或者其他犯罪的,按照相应犯罪论处即可;第二,该罪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市场经济秩序”的范畴似乎难以把握,从生产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是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用一个准确的法益将之概括。刑法理论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导致该罪在实践中的认定不时陷入困惑。
通常而言,基于报复竞争对手的目的而对竞争对手或者其产品虚构事实,整体或部分诋毁其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的,可以构成该罪。立法权威解读认为,该罪中的捏造,“既包括完全虚构,也包括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上部分虚构、歪曲事实真相”。③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59-360页。例如,甲基于排挤竞争对手的意图而虚构了与其经营同类产品的乙公司商品存在质量缺陷,容易引发爆炸等严重伤害消费者的事实,甲的行为构成该罪没有问题。然而,反向实施此类行为是否可以构成该罪呢?例如,甲在产品说明中声称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是本市唯一的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若认为该罪侵犯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甲的行为变相地损害了当地其他同类产品竞争者的商品信誉,则甲的行为可能就构成该罪。反之,如果认为甲的行为指向不明,因此,尽管造成了其他同类经营者销售金额的重大损失,则可能会认为甲的行为无法以该罪论处。可见,法益指向判断的不同,导致的结论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二)司法实践中该罪法益的模糊化倾向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检索系统进行查询,该罪捏造的对象主要是特定的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尚未看到前述的反向损害。在理解损害对象的特定性时,司法实践存在将该罪法益模糊化的倾向。如在轰动一时的北京“纸馅包子案”中,被告人訾北佳在担任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中心《透明度》栏目临时工作人员期间,通过查访,在未发现有人制作、出售肉馅内掺纸的包子的情况下,为显示工作业绩,化名胡月,纠集该市无业人员张沄江(另行处理),冒充工地负责人,多次到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内,对制作早餐的陕西省来京人员卫全峰等四人谎称需定购大量包子,要求卫全峰等人为其加工制作。后訾北佳伙同张沄江携带密拍设备、纸箱及购买的面粉、肉馅等再次来到13号院,訾北佳以喂狗为由,要求卫全峰等人将浸泡后的纸箱板剁碎掺入肉馅,制作了20余个纸馅包子。与此同时,訾北佳密拍了卫全峰等人制作纸馅包子的过程。在节目后期制作中,訾北佳采用剪辑画面、虚假配音等方法,编辑制作了虚假电视专题片《纸做的包子》录像带,并隐瞒事实真相,使该虚假电视节目于2007年7月8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相关行业商品的声誉,造成恶劣影响,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定罪处罚。④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刑初字第1763号刑事判决书。
对于该案,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并没有指出包子店的经营损失,彼时该罪的追诉标准尚未出台,因此,裁判文书以“恶劣影响”为由,认定被告人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其理由可能在于:第一,由于被告人没有指明特定的经营主体,再加上经营主体的损失难以认定,因此,无法按照损害商业信誉罪论处;第二,由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选择性罪名,尽管行为人没有损害特定商业主体的信誉,但是对于作为商品的“肉馅包子”构成了声誉的侵害,因此,认定为损害商品声誉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的分析意见中,其明显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案。“有时,行为人捏造并散布的是有关特定范围内某一类经营者的虚假事实,也应认定符合特定性要求。例如某市一家生产家用热水器的企业在散发的传单中宣称该厂生产的热水器是全市唯一的合格产品,实际上是变相诋毁本市其他两家热水器企业生产的热水器均为不合格产品,借此打击竞争对手,也属于侵犯他人商誉的行为。如果社会公众无法确认行为人所指向的具体‘他人’,则不符合特定他人的条件。如某洗涤剂厂在所生产和出售的新型洗涤材料的包装说明上标示‘市场上出售的洗衣粉、肥皂均含有铝、磷,会诱发老年痴呆症、非缺铁性贫血等疾病’,并告诫人们以后不要再买其他洗衣粉和肥皂了。很明显,这种诋毁行为所指‘他人’非常宽泛,不具有特定性要求。实践中,对于这种不指名的行为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应依据社会一般大众的普遍认识进行判断。”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
然而上述将捏造散布诋毁行业领域内的产品声誉的情况也认定为该罪,存在问题。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上述散发热水器传单中的反向损害行为以及洗涤厂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对本行业领域中相关商品声誉的侵害,它们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倘若根据被侵害的商品生产厂家的多寡来判断,则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将被虚置。不能因为上述被侵害的热水器的生产厂家少,而被侵害的洗衣粉和肥皂的生产厂家多,就据此判断前者构成犯罪,后者不构成犯罪。第二,将对同行业领域内产品的商业诽谤认定为特定,可能会造成处罚上的不当。对此,可以联系诽谤罪讨论。尽管诽谤罪和损害商业信誉、声誉罪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在行为结构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甲在某单位开会的会场上,跑到主席台,对台下的人说:“只有自己是本单位唯一的真正的男人。”甲的行为显然是对本单位其他男性同事的集体性诋毁,但是恐怕难以将其行为认定为诽谤罪,恰恰相反,人们会认为甲是缺乏理智的表现。同样的道理,在反向诋毁商品的情况下,尽管行为人针对的是特定人,但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恐怕其言论难以令人相信,既然如此,行为人的诋毁行为不可能影响人们的行动决策,在不可能对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的消费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显然不能认定其具有危害性。
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该罪是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但是,其法益并不是笼统的经济秩序,当秩序并不能还原为相关经营主体的利益时,即便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不能以该罪论处。对此,可能有人会反对,他们会认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的法益是集体法益,因此,在界定“他人”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个体经营者。前述“纸馅包子案”反映的就是这种思维逻辑。在统一的法益体系中,的确可以将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等类型,但是在对法益的理解中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能过于泛化地理解诸如社会法益等集体法益。一般认为,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可以认定为集体法益,但是,能否一概地将市场秩序理解为集体法益呢?有学者认为:“社会体系能够为个人所利用,个人可以参与到社会体系中,这种参与互动值得刑法的保护。例如,市场的经济秩序具有公平性,对于任何参与到其中的人而言,这种公平性都是重要的集体法益。”⑥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这种解说对于诋毁商业竞争对手而言,是成立的,但是,对于消费者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而言,消费者并没有参与市场竞争,且主观上并没有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难以认为消费者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公平性。可见,用集体法益来解释,反而可能会造成解释上的漏洞。第二,我国《刑法》中“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一节,其设立在逻辑上本来就存在问题。例如,金融诈骗犯罪,其实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不能认为,金融诈骗犯罪只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但没有达到扰乱的程度。换言之,我国《刑法》在设立该节罪名时,表面上看是保持了刑法分则第三章体系的完整性,但实际上是兜底性的一节,其节的名称也充分显示了这种兜底性。对于其中相关模糊罪量进行认定时,解释论上应当采取严格的限制解释立场。对于兜底的范围,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同质性与结果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仅具有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⑦参见蔡道通:《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退一步而言,即便承认该罪的法益是以“市场秩序”为内容的集体法益,但这种集体法益也只能是通过个体法益反射出来的,这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益是不同的。针对后者,公共安全作为个体法益的集合,其保护的必要性显然要比市场秩序紧迫。因此,对于集体法益的认定,应当从行为特质、危害后果等多个角度综合判断,当行为与危害具有不可控性、瞬间性、不可逆性、涉及公民重大利益,此时,才可以说集体法益能够成为刑法保护的独立型法益,当行为侵犯此类法益时,本身就具有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反之,如集体利益只是个体利益反射的效果,则在判断处罚边界时,必须回归到个体法益的判断,所谓的集体利益并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功能。或者说,此时集体法益的判断是通过个体法益延伸出来的概念,通过个体法益的受损,反衬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倾向。联系到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倘若认为该罪仅仅侵犯的是个体法益,则有关行为恐怕只能认定为毁坏型财产犯罪,但问题在于,毁坏型财产犯罪的核心关键词是财产价值的损失,刑法在评价毁坏型财产犯罪时,只能以财产损失作为基准。可是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与财产相比,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尽管通常被认为是“无形资产”,但是,这种价值并非直接依托于具体的物,尽管商品声誉的客观物理载体是“商品”,但是,商品的声誉却并不是通过商品的价值来体现的。换言之,商品本身价值的大小与商品声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价值很小的商品,也可能在市场上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价值大的商品,反而可能声誉并不怎么样。信誉、声誉是对商家经营活动长时间累积的社会评价。因此,按照传统的财产犯罪类解释就会出现格格不入的局面。反过来,如果对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完全离开具体的经营者和商品,忽略具体经营者和商品的利益,而对其予以泛化理解,可能导致的结局是,将与经营无关的社会秩序也理解为该罪的法益,进而导致该罪滑向口袋罪名的厄运。
三、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不法判断
(一)捏造的虚伪事实需要达到令人相信的程度
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捏造“既包括完全虚构,也包括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上部分虚构,歪曲事实真相”,⑧同前注③,郎胜主编书,第359-360页。对于虚假事实的程度基本不讨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捏造的虚假事实是否需要达到令公众相信的程度。笔者认为,如果只是捏造了虚假事实,但根本不足以令人相信的,不能以该罪论处。
第一,倘若虚假事实根本无法达到令人相信的程度,则并不存在法益侵害的现实性,不值得刑法处罚。例如,甲捏造乙经营的包子店是熊猫肉包子店,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几乎是不难判断其真假的。熊猫是国家保护动物,普通人难以获得熊猫肉,用熊猫肉作为肉馅经营包子,不仅经济成本大,而且违法成本大。因此,尽管行为人散布的是虚假事实,但是这种虚假事实根本不足以令普通公众相信,自然也无法对公众的消费决策产生任何影响。当然,如果构成诬告陷害罪,则可另当别论。只有捏造的事实可能被人相信,如捏造他人经营的包子肉馅是死猪肉,才可能认定为该罪。
第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属于商业诽谤行为,除了在行为对象、罪量标准上的差异外,在行为构造上与诽谤罪的构造并无不同。因此,在解释同类构造的罪名时,不能采取不同行为构造的解释。如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在行为构造上都是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导致他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的行为。只不过前者的发生领域限定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行为人利用的是合同领域中的诈骗方法而已。基于类似原理,在认定诽谤罪时,如果所散布的事实不足以使他人信以为真的,不是诽谤,但有可能构成侮辱罪。⑨参见同前注②,张明楷书,第920页。商业诽谤的行为如果没有达到足以使人信以为真的程度,由于刑法并没有规定侮辱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所以,只能按照一般的诋毁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处理。
(二)价值贬损是否构成捏造需区分不同情形判断
在鸿茅药酒案中,谭秦东医生的行为是否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关键在于如何评价其称鸿茅药酒是毒药的行为。车浩教授认为,将价值贬损行为认定为该罪,违反比例原则,从比例性角度看,如果商家捏造事实虚假宣传,那自然有虚假广告罪可以规制,但是,如果是在效用价值方面夸大虚饰,那么,这种价值浮夸其实也处在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广告含义之内。换句话说,既然允许商家做广告说是“神药”,那就得允许消费者说这个是“毒药”。⑩参见车浩:《车浩评鸿茅药酒案:错在违反罪刑法定与比例原则,而非跨省办案或证据不足》,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25663488&ver=861&signature=kKS5tOJ1-Djq9xqFPQXLnCTS8m626yMPz2B*m5IxBYPucFDp8ns4S-QC1AWCiBvbk4rOqjh7cYIX2a-AIGrmSXDFAbJnk2Q1YY2WvhkRXNKBGafhqMPl1WHpjvMl7SMI&new=1,2018年5月7日访问。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例原则,而是需要规范地理解“捏造”这一行为的概念。就通过损害商品的方法达到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而言,价值贬损是常见的行为方式。尽管单独提出价值贬损概念的目的是为了限定该罪的犯罪圈,但以此与捏造区分,并无实际意义。
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区分言论批评和捏造之间的界限。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几乎没有争议的是,对于商品的批评显然不可能认定为该罪,如对于伪劣商品的曝光和批评等。然而,问题是,在价值贬损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界分上仍然难以泾渭分明。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区分。第一,如果商品本身有瑕疵,贬损商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捏造,即捏造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一致的,不是捏造,此时仅需对捏造的事实和商品的事实进行客观的比较即可,至于行为人是何种动机,属于有责性领域讨论的范畴。按照阶层论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逻辑,当行为不构成捏造时,不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无须进行下一步的判断。第二,基于科学推理的价值贬损,需要具体判断。倘若行为人基于一般的科学,得出商品价值并非厂家所宣扬那样,甚至采取了夸大的语言,也不能认定为捏造行为。然而,如果行为人假借科学推理,并未按照正常的科学实验等程序操作,肆意编造结论贬损商品价值的,应当认定为捏造。
(三)散布虚假信息未必要求不特定的多数人知晓
通常情况下,利用互联网散布捏造的虚假信息,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类型。例如,在“潘某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潘某受人指使录制一段在火锅内吃出老鼠的视频,并将两段视频剪辑合成后发布到网络上。该视频累计播放30135次。法院认为,潘某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①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521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书。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行为人只是针对特定的人散布虚伪信息的,如何定性。倘若认为散布是将信息予以扩散,只有让公众可能知晓的,才构成该罪,则会导致刑法保护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范围过于狭窄。有学者认为:“刑法并不要求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要公然实施。针对他人固定的商业伙伴散布捏造的虚假事实,使他人因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到破坏而无法开展经营活动,也构成该罪。”②同前注②,周光权书,第278页。笔者赞同上述观点,换言之,针对特定的利害关系人散布虚伪信息的,也可能构成该罪。例如,在“方某损害商品声誉案”中,方某捏造并在微信朋友圈散布杨某(生产销售罐车)罐车爆炸的虚假信息,后其又主动删除了该虚假信息,法院认为,被告人方某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免予刑事处罚。③参见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2015)梁刑初字第178号刑事判决书。
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在微信朋友圈内散布捏造虚伪信息的是否构成该罪,仍要具体区分,而不宜一概而论。倘若微信朋友圈内散布的信息能够为相关利益关系人知晓,如行为人的微信朋友均为与被害企业之间具有商贸往来或者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则尽管该信息没有像公众号一样传播范围广泛,仍然会对被害企业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造成现实的侵害,倘若不认定为该罪,会造成刑法处罚的漏洞。如果行为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并无与被害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人,例如,行为人微信朋友圈中的朋友与上述罐车商户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往来的,尤其是在该信息未被他人二次转发的情况下,则不宜认定为该罪。
(四)散布无涉经营活动或商品的虚假信息不宜被评价为该罪
司法实践在认定虚伪信息时,通常过度关注信息的真伪问题,而对于信息内容的性质并不做实质的区分。例如,被告人在互联网上捏造企业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的事实,造成企业产品积压,与他人合同终止,企业经营遭受重大损失。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④参见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2015)文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笔者认为,上述判决书值得反思。该罪所要规制的是市场活动中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虚构了自然人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否可以认定为捏造散布行为呢?笔者认为,其未必一概构成该罪。基本的判断规则是,倘若捏造散布的事实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情况下,尽管捏造的对象是法定代表人,也可能无法按照该罪处理。例如,甲捏造散布某企业法定代表人乙向有关司法机关行贿,并在捏造的事实中说明乙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让司法工作人员丙徇私舞弊,私放其表弟丁。尽管上述信息被公众知晓,导致公众对于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品行产生了怀疑,进而造成企业生产的产品销路阻塞,大量货物积压,但仍然不能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其理由为,甲捏造散布的事实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商品声誉等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甲捏造散布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无法涵括在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之内,不会扰乱市场秩序。进一步而言,甲捏造散布的事实超出了该罪的法益范围,因此,其捏造散布行为不属于该罪中的行为,倘若构成诬告陷害罪或者其他罪名的,另当别论。
然而,如果捏造散布的虚伪事实是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事实,则可以构成该罪。例如,被告人捏造企业法定代表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工商管理部门的抽样检查等正常监管行为,则因被告人捏造他人行贿的事实,对于消费者或与该企业有经济往来的企业而言,依据常识可以判断该企业的商品质量存在问题抑或商业信誉存在不良记录等情况。例如,在“虞某某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虞某某因与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某等工作人员就预付款、退换货等纠纷起怨,为达到泄愤和给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加压力解决纠纷的目的,于2013年8月23日在互联网QQ群上捏造散布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倒闭并涉嫌欺诈、偷税犯罪的虚假事实,号召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停止与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发生业务,随后该信息在互联网上被转发传播,众多客户退单或停止与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业务,造成恶劣影响,致使山东某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620073.61元。①参见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新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其中,被告人虚构的涉嫌欺诈、逃税犯罪事实,属于被害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活动,将被告人的行为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罪并无不当。
需要澄清的是,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倘若捏造散布的虚伪事实是涉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则认定为该罪,倘若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则应当按照其他罪名论处。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标准有问题。第一,尽管法定代表人通常是企业的决策者甚至是企业的外部形象,但是,不能因此说,捏造散布非法定代表人的虚伪事实就一概不构成该罪。例如,甲捏造某食品工厂工人乙肮脏邋遢,经常不洗手揉面,并将上述信息散布到互联网上,造成上述食品工厂停业的,显然不能因为乙不是法定代表人就否定甲的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二,如前所述,即便是捏造散布法定代表人的虚伪事实,倘若和企业经营没有任何关联性,也认定为该罪,则属于明显的法益评价错位。
(五)罪量标准的界定
《追诉标准(二)》第74条的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2.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三)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该罪的罪量标准可以分为三类:直接经济损失型、公开损害型、其他类型。直接经济损失型由于数额较为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没有太大争议。在第二种类型中,如果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也无不当之处。然而,在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情况下,既无数额要求,也无其他损害后果的要求却值得商榷。第一,在现代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的时代,尽管不排除仍然在线下实体场所进行虚假的宣传行为,如在广场上宣扬捏造的虚假事实行为,但是不可否认,该罪的行为类型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或者媒体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当司法解释不对其进行限制时,难以区分该罪与一般商业诋毁行为的界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类型进行限定,易言之,它也包括利用网络或媒体的手段。《追诉标准(二)》的规定,实际上虚化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进而带来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利用了网络或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就一律按照犯罪论处,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底线被放弃了。
从笔者已检索到的相关裁判文书看,司法实践在适用“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时,存在如下几种情形。
1.直接适用
在“刘福胜损害商品声誉案”中,①类似的判决书还有如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2013)蒙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等。被告人刘福胜因故与天津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纠纷,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刘福胜在天涯论坛、新浪博客等网站发布虚假的贬低天津某科技有限公司实木门质量的信息。法院认为,被告人刘福胜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刘福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刘福胜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罚金3000元。②参见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2017)豫0611刑初372号刑事判决书。在此情况下,法院并不具体判断行为人捏造散布的事实对被害企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而是在行为人利用网络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情况下,径直认定为犯罪。然而,由于损失的具体认定没有在裁判文书中得以确认,且行为人有坦白情节,因此,只判处被告人罚金刑。
2.用其他损失予以限定
在“毛某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毛某身为版主,在论坛上发布他人酒吧存在淫秽表演行为,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被害企业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时,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南塘本色酒吧因本案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但本案的虚假信息必然使其无形资产遭受损失,故应当认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造成南塘本色酒吧的经济损失。被告人毛某捏造并通过互联网传播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③参见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刑初字第468号刑事判决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被告人对被害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小难以认定,但仍然认为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至于经济损失的数额,判决书并未交代。善意地理解,法院力图通过对经济损失的强调,避免处罚“没有造成损失”的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体现了裁判者“骑虎难下”的心理。然而,即使如此,裁判仍然存在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方面认定被害企业存在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却并不对损失的具体数额和情形予以认定。尽管从限定“利用互联网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立场上看没有问题,但是,这种限定反而可能会显得裁判文书的说理不充分。
3.虚假信息被点击或传播的范围
在“魏某某、王某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中,被告人魏某某生产加工的“玫瑰纯露”“玫瑰花酱”等产品被辉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被告人魏某某怀疑举报人为辉县市董某商贸有限公司经理董某某。2016年8月20日左右,为诋毁辉县市董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商业信誉及商品声誉,被告人魏某某将其拍摄的位于辉县市薄壁镇孟村一家废弃煤场的照片标注为辉县市董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将该公司的货物周转发货场地照片标注为产品生产车间、编辑“董某化妆品因添加违禁品,新乡和广州有关执法部门正在调查”等虚假信息,后魏某某将上述图片及文字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人王某某,指使王某某将其提供的图片及文字整理后发布在互联网上。后被告人王某某通过淘宝网委托他人将上述虚假信息制作成网址链接,分别于2016年8月21日、2016年8月27日、2016年9月16日、2016年9月17日利用互联网发布在王某某微信朋友圈及其QQ空间,上述网址链接的浏览次数累计为175136次,被转发次数累计为1315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某某、王某某捏造并利用互联网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①参见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7)豫0782刑初209号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判断危害大小的要素主要包括被告人虚假信息被浏览和被转发的次数等。这种思路与诽谤罪的司法解释的思路一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9月6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该司法解释起草者在解读上述规定时指出:“如果一个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信息被众多人所点击、浏览而知晓,足以说明被害人的名誉已经受到损害,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②李少平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刑事卷)》(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533页。依此,在商业诽谤的情况下,虚假信息被浏览、被点击的次数同样可以体现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受到损失的客观现实。尽管该案中的裁判文书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但其内在思路与上述司法解释如出一辙。③类似的裁判如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刑初990号刑事判决书。
然而,对于虚假信息被点击或传播的范围,由于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实践中也存在差异悬殊的判决。在“张某某等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张某某等捏造被害企业景田公司的矿泉水为人工天然矿泉水等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各种回应。浏览人数有约2100人,发表评论7人,转载4人,相关帖子2条。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④参见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法刑二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刑二终字第294号刑事裁定书。在前述“魏某某损害商业信誉案”中并没有采取虚假信息被浏览和转发的次数标准,在浏览、评论和转载的界定上采取的是“人”的标准,在帖子界定上采取的是“条”的标准。因此,难以具体计算浏览和被转发的次数。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界定“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的构罪标准时,应当坚持如下立场。
第一,不能直接适用《追诉标准(二)》中“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标准,理由已如前所述,倘若不要求具体的罪量的限制,则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的商业诽谤行为都可能按照犯罪处理,且会架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从多个角度限制该条款的适用。一是,从行为方法角度加以限制,如要求行为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上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其理由为,此种情况下,行为的方式加大了虚伪信息的扩散程度,对于被害企业而言造成的损害面更广。二是,从被点击次数或传播范围角度加以限制。其原理应当与利用互联网诽谤他人名誉的原理一致,但是被点击数和浏览数应当明显高于诽谤罪的构罪标准。其理由为,刑法对自然人的名誉保护范围和力度,都严于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如仅仅在公众场合砸碎他人商品的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正如有学者所说:“如将有缺陷的某品牌商品当中砸毁、将有缺陷的某种商品的汽车用马拉着游街的行为,只要该产品确实存在所说的缺陷,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⑤参见前注②,黎宏书,第191页。然而在公众场合侮辱自然人的,则可能构成侮辱罪。三是,从被害企业与处理相关虚伪事实付出的代价的角度加以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此种代价究竟应当归属于“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还是作为限定利用互联网或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事由,现行的司法解释并不明确。从前述《追诉标准(二)》的规定上看,“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属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独立的构罪标准,但这种定性存在问题。首先,鉴于此标准的模糊性,在现有检索的样本中,尚未发现根据此标准作出的裁判文书,反而多数的裁判文书是将之作为限定处罚网络商业诽谤的因素。因此,在实践中,该标准的独立性其实已经丧失。其次,如果上述标准具有独立性,则同样会得出利用网络进行商业诽谤并不要求罪量的不合理结论。最后,上述标准本身就是兜底性的条款,这种兜底性条款一旦被泛化理解,将导致笼统的社会秩序危害也被认定为该罪的法益。基于此,笔者认为,这种兜底性条款只能被作为限制利用网络进行商业诽谤的事由。概言之,重大损失,指的是尚未达到直接经济损失标准的情况。它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予以考虑:客观退货损失、滞销压库损失、为正名进行的宣传耗费的损失、预期利益和停产期间的损失。①参见张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中)》(第9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866页。而其他严重情节,也应当限制为客观的违法要素,而不宜将诸如人的主观恶性和反映预防必要性的因素纳入其中,否则将会导致不法与责任、责任刑和预防刑的逻辑混乱。②具体理由参见石聚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法理重述》,《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四、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有责性的判断
几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但在认定听信谣言而散布甚至捏造散布所听信谣言的,是否认定为该罪却存在不同见解。否定构成犯罪的观点认为,听信他人谣言而散布的行为,不具有商业诽谤的故意。“听信他人谣言,而散布虚伪事实乃至对虚伪事实进行某种程度的加工行为,不应认定为本罪。”③参见前注②,张明楷书,第831页。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与之不同的判决。在“孟良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孟良的妻子回家后跟孟良说,刚才在公交车上听两个女的聊天,说额尔古纳市丽丽娅面包房是用工业奶油做的面包。孟良不经核实,就用其手机编写并在朋友圈里发出了一条微信,内容为:“太黑了——额尔古纳丽丽娅面包被质检部门查出用工业奶油冒充食用奶油制作面包出售……以后不要再吃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为了大家的健康……请转起来!!”这条虚假信息极大地损害了丽丽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声誉,给该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未达到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标准)。法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核实,凭空捏造散布虚伪事实,利用互联网或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④参见雷宝印、陈静:《利用互联网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认定》,《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27日,第6版。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值得商榷。
首先,被告人对其妻子从公交车上听信的传言,是否属于虚伪事实,并不清楚。诚然,刑法既处罚捏造又散布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原生行为,也处罚利用谣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加工行为,但其前提都应当是明知是谣言。当虚伪事实是行为人捏造的,认定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后者而言,必须强调只有当行为人知道是谣言而散布甚至加工的行为,才可以构成该罪。在本案中,并无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行为人知晓其妻子告知的信息是谣言。
其次,该法院裁判要旨指出,未经核实是认定行为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关键。之所以法院指出“未经核实”,恐怕在于其认为行为人至少知道其妻子所告知的信息是虚伪的,进而认定行为人在主观上构成故意,但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信息来源是否真实难以判断,而且要求被告人对信息来源进行充分有效的核实,难度较大。反对的观点可能认为,只要被告人到被害企业去了解情况就完全可以判断信息的真假。然而,实践中,在企业未受到有关机关查处之前,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承认自己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企望被告人从企业获取确定的可靠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还存在另外一种质疑声音,既然行为人无法向有关企业核实,则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或质检部门核实,但这同样不现实。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机关对于突发性舆论事件基本上采取类似于“外交辞令”式的“统一口径”的方式予以回复,即便是新闻记者也难以从相关行政机关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信息是否真实的答复。倘若将“未经核实”作为认定行为人故意的根据,即只要行为人没有采取核实的行动,就认定其是故意,这在信息网络时代下导致的结局是,只要未对信息进行充分核实,即便是对商品进行一般的批评,造成相关企业利益受损的行为,也都可能构成该罪。这无疑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