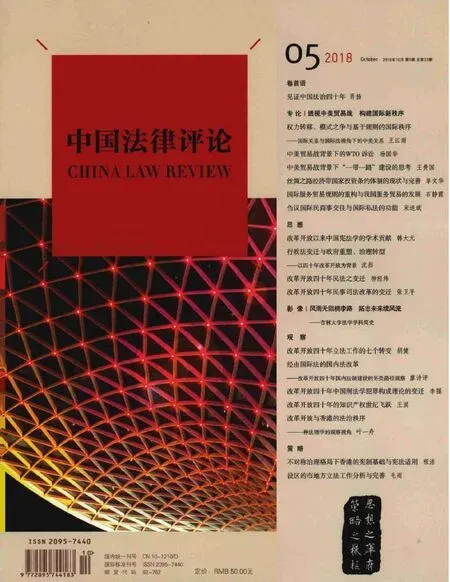不对称治理格局下香港的宪制基础与宪法适用
程 洁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有关香港基本法的各种讨论都绕不开香港的宪制基础问题。而有关香港宪制基础的讨论,又无法回避中国宪法在香港的适用问题。否则,各种讨论总会沦为自说自话、“各自表述”的局面,无法形成对话,也难以达成共识。例如,早期的研究分别形成了分权论和授权论两种主张,分权论倾向于以《中英联合声明》作为香港的宪制基础,1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ition. pp.189-230, also pp.457-492. See also Johannes Chan and Wing Kay Po, "How China's Constitution Ensured that the Basic Law Remains Preeminent in Hong Kong",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08-06, at at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hong-kong/article/2158137/how-chinas-constitution-ensured-basic-law-remains,2018年8月6日访问。而授权论则倾向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作为香港的宪制基础。2国务院新闻办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有关分权论与授权论形成的更多理论和社会基础,参见程洁:《香港新宪制秩序的法理基础:分权还是授权》,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两者虽然观点迥异,但共同点是都承认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的宪制地位。而对于宪法在香港的宪制地位,却有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中英联合声明》与中国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互斥的,从而否定宪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及其在香港的适用。后者则有不同表现。许多持论者原则上承认宪法在香港的最高法地位,但回避宪法在香港的适用问题。他们有的将基本法视为宪法的特别法,3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有的将之视为宪法的附属法,4朱世海:《宪法与基本法关系新论:主体法与附属法》,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也不乏认为香港的宪制基础规范仅源于基本法的理解。而对于“宪法整体上适用于香港”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宪法究竟是否适用于香港,仍然未能给予令人信服的回应。5曹旭东:《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论回顾与实践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结果仍然导致宪法的虚置。
将香港的宪制基础国际法化或简单等同于基本法都会造成“去宪法化”,无助于理解和解决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基本法实施中形成的各种困扰和分歧。就前者而言,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的首要问题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解释和实施机制问题。《中英联合声明》虽然是两国之间的协议,但并没有确立共同的解释规则和实施机构。其中涉及香港的内容最终还是要由主权者中国对其进行解释和实施。就后者而言,基本法虽然规定了香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的政治组织和各种制度,但这一制度存在是有前提的,其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其作为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而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基础则是中国宪法,即使在香港亦是如此。6王振民:《论新宪制秩序于港澳回归后的确立》,载陈弘毅、邹平学主编:《香港基本法面面观》,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35页。由此,强调香港基本法作为特别法而淡化甚至否定宪法的实施结果类似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过,无论国际法论还是其他去宪法化的理论主张,都显示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确实提出了新的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具体来说,就是在既有的宪制框架下,如何理解特别行政区被赋予特别权力、给予特殊待遇的正当性问题。换言之,要解决香港的宪制基础问题带来的困境,就必须直面香港特殊化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这一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在中国宪法上是无法回答的,那么宪法显然无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础;但如果在现行宪法的框架下可以解释,那么就不应当或没有必要寻找其他基础规范。可能还有论者认为,中国政府白皮书已经明确强调香港宪制基础是基于中央对特区之间的授权,7国务院新闻办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似乎争议可以告一段落。其实不然。授权论本身只能回答权力是否派生的问题,但不能完全解决授权的规范来源问题。宪法究竟是否属于香港的宪制基础,以及其与香港基本法的关系如何,是有必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就香港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最近几年开始出现港独团体、本土化主张或城邦论等,都试图从基本法和宪法之外寻求基础规范。8例如,陈云:《香港城邦论》,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刘兆佳:《如何理解香港“本土意识”》,载《大公报》2013年5月30日。与我国台湾地区存在的一些“法理台独”主张类似,这些本土主张通常希望从国际法原则、自然法、国际人权公约、去殖民化理论等视角中寻找理论资源。可见,即使阐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也无法完全排除地方分离主义风险,但如果回避这一讨论,只能让事态向分离主义方向发展。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回答这一棘手的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证及说明宪法作为香港宪制基础的正当性及其如何回应特别行政区制度对现行宪法提出的挑战问题。第一部分从解决地区差异和族群冲突角度,说明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不对称治理的一种形态,并且可以为中国宪法所包容。第二部分从基本法授权的具体特点出发,说明不对称治理在特别行政区制度中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批判性地分析不对称授权带来的悖论与脱离困境的几种可能性。文章最后进行总结,并尝试进行理论和政策上的展望。
一、作为冲突解决机制的不对称治理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解决国家统一和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创新。同时,“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又是历史上中国及其他国家为解决族群冲突与地方差异而采取的一种常见的不对称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虽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在当代各国也各有表现,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却是对现代政治理念的一种挑战。因为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理论建立在普世主义的基本假设上,表现在个人发展方面就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表现在地方发展方面就是地区平等、地方自治。通俗地说,自由平等社会中个人权利和地方自治的基本假设就是“你有,我也有”,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可以有的,我也可以有”。但不对称治理则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就是个别地区或族群可以享受某些排他性的权利或待遇,允许这些特殊权利和待遇的结果就造成了“你有,我没有”或“只能你有,不能我有”的局面。
这种特殊待遇与一般央地关系理论中的地方自治有所区别。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民主成功的原因时,将之归功于普遍的地方自治。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5—76页。托克维尔非常推崇美国的乡镇自治,认为乡镇自由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所特有并为欧洲大陆(尤其法国)所欠缺的,而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也是人民最早实践民主自治的基层单位。美国独有的乡镇精神既强调自由和独立,又带来了归属感和对组织的认同,是美国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但是不对称治理不是普遍的地方自治,而是个别地区的高度自治。政治经济学家将联邦制地区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地方组成单位之间的自由竞争,10Barry Weingast,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of Law, Econ. and Organization, Vol. 11, No. 1, Apr. 1995, pp. 1-31.前提也是各个组成单位都可以同等自由地决定地方政策,从而可以通过居民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敦促地方改进政策。11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 (5) (1956),pp.416-424.而不对称式治理往往是强化某一个地区地方自治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求在人流或物流方面与其他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隔离,否则就无法确保特殊优惠而成为普遍优惠。其结果,在实行不对称治理的情况下,“用脚投票的权利”受到极大的制约。
尽管如此,实行不对称治理又往往是解决地区差异和族群冲突不可或缺的选择。从历史上看,中国唐代以来实行的羁縻州制度,元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禁区制度,都是为了解决边疆地区或不同族群社会、经济问题发展程度不一以及减少族群冲突、怀柔包容之举。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苏东解体之后新的民族国家建国过程中,都出现了为兼容不同族群和地区差异而实现区别对待的问题。12Sujit Choudhry and Nathan Hume, "Federalism, Devolution and Secession: From Classical to Post-Conflict Federalism", in Tom Ginsburg & Rosalind Dixon, eds.,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2011.即使一些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也未能幸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英国苏格兰地区等都属于特事特办、不对称治理的案例。13Susan Henders, Territoriality, Asymmetry, and Autonomy: Catalonia, Corsica, Hong Kong and Tibet, Palgrave Macmillan,2010.
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不对称治理的研究开始得到关注,但有关其正当性及局限性的讨论尚未形成定论。不过从各种研究的一般观察来看,不对称治理的制度设计需要高度的智慧以平衡不同族群和地区之间的关系。若成功,促进融合与兼容;若失败,则导致进一步的分离与冲突。14Sujit Choudhry and Nathan Hume, Federalism, Devolution and Secession: From Classical to Post-Conflict Federalism, in Tom Ginsburg & Rosalind Dixon,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2011.
中国目前有关不对称治理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不过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一定是特殊政策或地区特权造成的,也有可能就是各地方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发挥地方优势形成的结果。15但深圳等经济特区确实存在中央授权地方享有某些超出一般行政区划的立法特权问题。本文对不对称治理的理解包括两方面:地区之间的不对称及中央与地区关系之间的不对称。下面将从基本法规定的四方面权力下放对这两个层面的不对称进行具体说明。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不对称治理表现
不对称治理是中国地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而特别行政区制度所体现的不对称治理则最为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香港基本法是这一不对称治理格局在香港的具体规范表达。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区的内容很多,但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对特区司法权的深度下放,对特区立法权的深度下放,特区政治参与权的国际化以及特区关税和财政权力的深度下放。
第一,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深度下放了司法权,尤其表现在终审权下放和司法互助义务的缺失。司法权的深度下放有多重因素,主要考虑是尊重香港在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中形成的普通法司法独立传统,另外一个现实考虑可能是解决回归之初中国籍法官欠缺的问题。16林峰:《“一国两制”下香港“外籍法官”的角色演变》,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司法独立和普通法司法体制确实有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传统。但是,一方面外籍法官制度延续了香港治理的国际化因素,另一方面缺乏与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司法互助制度容易导致香港与中国法律之间的隔离。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缺乏统一大市场所必要的一致性行为准则。
香港基本法虽然规定香港延续原有的普通法制度,但同时规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中解释自治范围内条款,特区法院如需解释自治范围外条款,并且该解释将影响终审判决,则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158条)。由于普通法地区通常由司法机构负责法律解释,这一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性。香港的司法机构试图广义地理解这一法律解释授权,认为这一授权意味着法院可以认定哪些条款属于自治范围内,并且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范围外条款。在1999年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对该解释条款的理解几乎引发了一场宪法性危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司法机构最终形成了默契与和解,17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 HKCFA 72,简称吴嘉玲案; LAU Kong Yung And Others v.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 HKCFA 4,简称刘港榕案,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2001]HKCFA 48,简称庄丰源案。香港终审法院先是在吴嘉玲案中声称有权审查全国性立法并推翻了特区《入境事务条例》,从而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释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后,终审法院通过刘港榕案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不容质疑的,并且解释权不受限制。不过,在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表示,其所认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仅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做出的有关基本法的解释,而不包括其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解释性文件。但显然这一事件对特别行政区制度下中央和特区的权力边界引发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基本法对特区深度下放了立法权,不但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一般立法权,还规定特区可以就国家安全事项自行立法(基本法第23条)。这一规定一方面是为了延续香港原有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消香港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顾虑。然而,第23条立法后续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分歧。18香港2002年秋季启动立法,2003年9月撤回草案。澳门2007年6月20日公布规划,8月公布草案。《维护国家安全法》共15条,规定了7种维护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及相应处罚。一方面,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不是区域性的,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或者地区能够实现的治理目标,它本来就是国家的一个治理目标,将此权力下放给特区,就很可能出现类似于“公地悲哀”的情况。因为对于特区来说,它其实没有动力去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可能也无法确定到底何谓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秘密,以及哪些组织或活动能够被认定为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该权力一旦下放,中央政府不仅将之视为一般立法事权,而且将之视为地区向中央效忠的宣示性立法表达,拒绝立法就是地区拒绝对国家效忠。
平心而论,无论特区是否制定国家安全立法,最终的执法者只能是国家而非特区。因为根据基本法解释条款,所有涉及中央政府或中央特区关系的条款在做出终审判决时需要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解释。所以,中央和香港特区对国家安全立法的坚持或抵抗,更多是源于过度授权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具体来说,这一矛盾折射的是不对称授权带来的央地关系的不和谐。
第三,基本法对香港的政治参与权扩大到了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根据基本法,除了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公民外,永久居民中的外籍人士也可以在香港参加选举并担任主要官员之外的其他政府职务。香港特区的立法会20%可以是外籍人士,司法机构只有两位法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以及高等法院上诉庭院长)必须是中国籍,其他的法官都可以不是中国籍。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既是考虑到香港本地管理人才的缺乏,也是为了照顾英国人在香港的利益。
不过,这一规定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是香港问题的国际化。例如,通常各国家都不允许参选政团在选举时接受外国的政治献金,但是在香港这种限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允许外籍人士参选的话,他所使用的政治活动经费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境外。香港本来就具有国际化因素,其政治人物的国际化和政治过程的国际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央和特区内不同政治势力间的互相不信任。19王家英:《抗衡多于顺从——选举政治下香港与台湾对中国大陆因素的回应》,载《二十一世纪评论》2004年2月号。对于特区永久居民来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中央政府承诺赋予其的一项政治权利,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做了承诺,那就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但这一认识可能忽略了中央担心外部干预的正当性诉求。毕竟,国际关系还没有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国与国之间对境外贸易和投资都会进行安全审查,对于更加敏感的政治领域,国际化必然带来更高的安全风险。
第四,基本法对香港深度下放了关税和财政权力。根据基本法,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有独立的货币,财政独立,并不需要向中央纳税。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维持香港原有金融和财政体系的稳定性,也是为了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的独立金融体制和财政独立逐渐显示其副作用,形成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在经济和贸易上的一种隔离,尤其是阻碍了金融资本的流通,人为割裂了市场,提高了交易成本。
香港基本法还规定了其他一系列香港可以自行立法或自行进行管理的事项。应该说,这些规定在香港回归谈判和回归之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时过境迁,许多规定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并成为引发特区与中央之间、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矛盾或不满的原因。例如,香港实行独立的边境管治,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入境香港需要专门办理签注并且限制停留时间;同时,港人在内地也无法享受有关教育、工作和社会福利的一些权利或利益。这些隔离性制度的存在各有利弊,但是否有必要长期存在,值得认真考量。
三、不对称治理格局下香港的宪制困境及解困思路
不对称治理的基础是地方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不同需求。为了回应这些需求,给予某些地区特殊政策成为一时之选。然而,不对称治理又会强化“特殊社会”主张,甚至深化地区差异并带来地区分离主义等新的社会风险。从比较宪法的研究来看,不对称治理最重要的外部性可能就是治理的碎片化。因为地区的特殊性主张是可以不断复制的。例如对于国家来说,某一个省是特殊的,但对于省所辖市来说,个别市是特殊的,对于市辖县来说,个别县也可以主张自己的特殊性,所以这种特殊化的主张和要求会有扩张的倾向。“特殊社会”主张的可复制性和扩张性有可能导致社会不断分化,也有可能导致某个地区不断强化其特殊性主张。具体来说,不对称治理格局下的香港就陷入一个三重宪制悖论当中。
第一重悖论是香港的宪法适用悖论,这个悖论具体表现在香港基本法根据宪法制定但又不承认宪法的高级法地位。对香港终审法院涉及基本法和宪法的判决研究表明,判决通常将香港基本法视为香港的“宪法”而回避中国宪法的适用。虽然有些判决也引用了宪法,但并非作为裁判基准或适用性引用,而是作为论证依据。20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法院的做法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例如,香港法院原则上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所以适用宪法有可能带来理解上的歧义。此外,也许法院会认为,如果其适用中国宪法,则需要事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解释,这会给法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工作和麻烦。其结果,虽然法院从来没有否认中国宪法的地位,但由于法院回避适用宪法,就导致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实际上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悖论。
第二重悖论是香港基本法的稳定性悖论。世界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香港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也有必要做出相应的改进。然而,在涉及香港基本法问题时,一方面,各方都认识到,某些具有宪法意义的制度有必要进行改变(如政制发展),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又希望作为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不要改变——不但50年不变, 50年以后也无须改变。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还是需要回归到对香港宪制基础的认识,即宪法究竟是否属于香港宪制的规范基础,及其如何区别于香港基本法。
第三重悖论可以称为香港特区的地方性悖论,具体表现在对香港的认识既强调其权力来源于地方自治,同时又极力主张香港的国际化。甚至有观点认为,香港基本法同时具有国内法、地方法和国际法的属性。21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虽然香港基本法的制定确实存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但是将之理解为国际法规范或者地方规范都有意识地忽略了国家法的真实属性,结果就是导致对基本法宪制基础认识上的混乱。
如何解决不对称治理对香港宪制基础的认识带来的三重困境?一种解决思路是进一步下放司法权力,或者去宪法化,进一步国际化。但这一思路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一理解否定了特区的地方性,将特区地位等同国家甚或凌驾于国家之上。另一方面,有关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的考虑,似乎也是基于国际主体之间而非一国内部的考虑。
另一种思路则认为所有特别安排都是过渡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会走向一体化。黄仁宇教授以中国历史上的元代南北分治为例,说明“分久必合”的趋势。22黄仁宇:《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载《过渡期的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香港浸会学院东西文化经济交流中心1992年版。这一思路有可能导致基本法于2047年废止或香港完全内地化。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其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往往通过同化政策解决族群差异,无论“大熔炉”还是“大一统”,目标都是民族融合。但同化政策在当代政治语境下缺乏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现实可行性。
第三种思路主张是通过包容性治理将少数族群或“异族”纳入正式治理过程中,而非通过特殊政策和设立特区将其边缘化或外部化。这一思路需要修改香港基本法,尤其是2047年之后,考虑收回某些更加适合由中央行使的权力,例如终审权、国家安全审查权、统一货币,撤销区际边境控制,但保留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与独立的关税贸易区地位。同时在国家层面需要解释基本法及审理香港上诉的终审案件时,应当保证一定比例的香港法官或香港代表的参与。换言之,这是一种宪法化的思路。
苏吉特·乔杜里(Sujit Choudhry)的比较研究发现,简单的权力下放会导致族群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独立身份认同和分离主义倾向;而传统的同化政策否定特别族群的身份差异性,很多情况下会导致反弹,进一步激发其对特殊族群身份的认同。他以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表明,承认个别族群的特殊传统不一定非要对其进行不对称权力配置,但是应当考虑在全国性机构中为特殊群体代表预留一定的名额,促使其形成更多的国家身份认同。具体来说,加拿大魁北克虽然是10个省中唯一的大陆法地区,但其立法权和司法权与其他各省无异,魁北克也不拥有终审权。不过,加拿大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法官需要来自魁北克,并且有双语能力。魁北克是加拿大建国之初四省之一,并且属于加拿大人口大省。由于语言和法律传统不同,魁北克一度形成了强大的分离主义势力。但经过1982年宪法改革,加拿大开始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双语法律系统。而魁北克的分离主义倾向在1998年达到高潮之后开始消退,23魁北克省一直主张其“特殊社会”(distinct society)属性并争取在联邦中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一主张未能得到1982年宪法的承认。魁北克省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当选后,于1995年公投脱离加拿大,虽然没有获得多数票,但加拿大政府向最高法院进行咨询,最高法院做出咨询性意见,认定魁北克单方面公投的结果不能作为脱离加拿大的依据,并且国际人权公约有关自决权的规定也不适用于加拿大。按照最高法院的咨询意见,需要加拿大各省共同协商才能最终确定某一省脱离的正当性。1998 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2 S.C.R. 217.更加包容的宪法体制促进了族群团结,并最终促进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
香港的情况固然与魁北克不同,无论从人口、经济地位和文化传统来看,香港与内地的差异性远远低于魁北克与其他九省之间的差异性。国家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确实有其现实原因,不过特区制度最终应当服务于团结与融合而非强化地方性身份认同和刺激区际矛盾。如果出现这样的趋势,即使尚未造成重大后果,也值得认真反思目前的制度安排并考虑适当调整。而进行反思和调整的基础,只能是以整个国家的基础规范作为香港的宪制基础而非推定存在两套甚至多套基础规范。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两套以上的基础规范,只能不断催化矛盾而非解决冲突。
四、总结及展望
如何理解香港的宪制基础及其与中国宪法的关系?不可否认,《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为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法规范依据。但是就香港的宪制基础而言,最高规范只能是宪法而非其他。宪法作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宪制规范,并不影响香港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并获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因为这是中国宪制体系下不对称治理的一种形式,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特区和其他特别行政区划一道,构成了中国不对称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表现在对特区司法权、立法权、外籍人士政治参与权以及财政金融权力的深度下放。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进行不对称治理固然能够解决短期的社会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外部性,尤其是强化地方的特殊社会主张和地区身份认同,削弱国家身份认同。香港社会近期的一些纷争和矛盾就展现出不对称授权带来的三重悖论。
认识到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后,就有必要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强化宪法作为香港宪制基础的的主张和论述。同时,强调宪法作为香港的宪制基础,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对香港实行“大一统”,而是肯定宪法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基础规范。有论者认为,宪法中的很多条款,例如涉及社会主义或地方组织的内容并不适用于香港,所以不能认为宪法适用于香港。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宪法规定了不同方面的事项,不同的事项适用不同的宪法条款。如果认为宪法中有社会主义条款就证明相关内容不适用宪法,那么会推导出非常荒谬的结论:不但香港,中国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用宪法的全部条款。实际上,宪法作为国家的宪法,其有关社会主义的规定是在全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足以否定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理解为中国宪法在香港不适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宪法解释的层面争辩说,中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条款如何理解及适用需要有权机关界定,一般人的直观理解不能作为宪法适用的基础。
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之间差异性有可能会放大也有可能会趋同。但差异性不是主张“特殊社会”的充分条件。未来有必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承认差异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并通过包容性地开放国家议事机构,吸纳香港等特殊地区的政治诉求,同时兼顾特区与国家更加广大的其他地区之间的平等与均衡。承认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并不损害香港基本法的作用,因为香港基本法本来就是国家立法而非地方立法,当然更不是国际法,也不是宪法之外的特别法。真正的挑战也许是,需要从现在开始考虑香港基本法实施50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如何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共同生机勃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