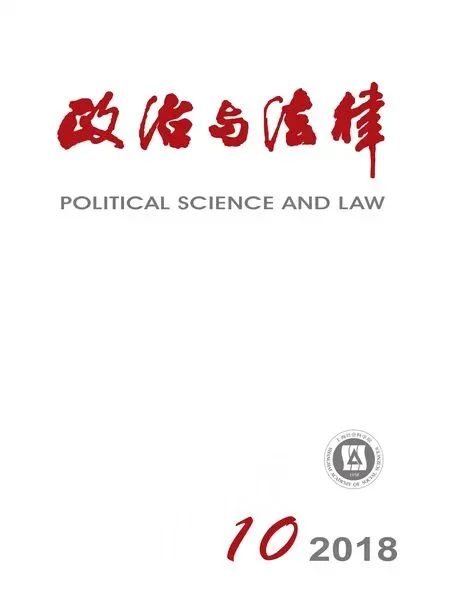法益视角下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
多年来,内幕交易行为虽在证券市场频频发生,但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数量却寥寥无几。不少学者认为,证券内幕交易刑事执法数量偏低的原因在于我国存在大量“以罚代刑”的情形,致使相当一部分行为符合入罪的标准却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①参见毛玲玲:《证券刑法的矛盾样态及反思》,《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冯殿美、杜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若干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姚建龙、郗培植:《内幕交易、泄露 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杨瑷华:《证据法视野下对查办证券内幕交易罪两个问题的探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谢杰:《内幕交易犯罪情节认定疑难问题研究——“两高”最新证券期货司法解释相关条款刑法解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规制存在诸多规范性文件,其不同的理论支撑与文句表述造成了对犯罪主体认定的困难。为此,需要对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体规范进行规范重构。
一、现行法上的规范文句的理论支撑与适用难题
与采用特别刑法规制证券犯罪的国家与地区不同,我国仅在刑法典中对证券内幕交易设置了罪名和罪状。犯罪主体的范围在我国《刑法》中只是一款指引性规范,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第180条第3款)。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对证券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法律文件仅有我国《证券法》。其第73条将该罪的主体限定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并在第74条第1项至第6项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做了详细列举,且设置了第7项的兜底条款,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在我国,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特指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内幕人的认定,证监会于2007年制定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第5条与第6条对“内幕人”做了规定。2012年,为解决我国《刑法》第180条第3款未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具体内容而带来适用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同年出台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第2条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明确。
基于我国上述立法模式,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致使前者在形式上成为了后者的情节加重犯或结果加重犯。②参见张心向:《我国证券内幕交易行为之处罚现状分析》,《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为此,内幕交易罪作为刑事犯罪,其主体适格的判断需倚赖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故我国《刑法》《证券法》《指引》《解释》中关于内幕交易主体的文句及其理论背景,是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识别问题需要剖析和评述的重点。对此,笔者将结合美国在司法实务中形成的诸理论进行探讨。因为美国作为最早规制内幕交易的国家,其所确立的一系列关于主体识别的理论被他国纷纷移植,我国亦不例外。我国法上诸规范的文句,亦体现了这些理论。
(一)理论支撑及在现行法上规范文句中的投射
1.“信息平等理论”与《指引》中“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信息平等理论”是美国对内幕交易规则初期所采取的规则理论,基于这一理论,美国采取了“信息占有标准”作为内幕交易主体的识别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源于1961年的Cady,Roberts&Co.案,③In Re Cady,Robert&Co.,40 SEC.907.911 (1961).针对这一案件,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与公司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在获知了公司内幕信息后,或者公开该信息,或者不得于信息公开前从事与此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公开或戒绝交易规制”(Disclose or Abstain Rule)。至于何为“与公司存在特殊关系”,SEC指出,判断“特殊关系”的有无不应拘泥于行为人是否具有经理、董事、控股股东等身份,而应着眼于行为人是否“接触”了只有公司才有权使用的信息。④In Re Cady,Robert&Co.,40 SEC.912.在Cady,Roberts&Co.案之后,1968年的Texas Gulf Sulphur CO.案判决重申了上述立场,⑤Texas Gulf Sulphur,401 F.2d 833(2d Cir.1968).并将“与公司存在特殊关系”的原因从对信息的“接触”转为强调对信息的“占有”,其后,这种立场被称为“信息占有标准”而固定下来,并被美国多数的联邦法院裁判所采纳⑥[日]並木和夫:《内部者取引の研究》,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1996年,第30页。。
“信息平等理论”旨在通过保护投资者拥有相同的信息占有权而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性。基于这一理论而形成的“信息占有标准”,对内幕交易行为主体范围采取了最广义的解释,将是否占有内幕信息作为判断内幕交易主体适格的核心要素。
在前述我国规制证券内幕交易的规范性文件中,我国证监会《指引》的文句反映出对这种理论的坚持。《指引》第6条在对“内幕人”范围进行列举时,于第5项设置了兜底条款,即“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无论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身份关联,均被列为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对象。可见,《指引》对该罪主体的概念,采用了“信息平等理论”而做最广义的解释,将对信息的占有作为判断主体适格的核心要素。
2.“传统信义关系理论”与我国《证券法》中的“知情人”
“信息占有标准”在忠实服务于规制的目的而广受支持的同时,亦因其语义射程过远、有效适用性低下而受到批判,⑦Edward Herman,Equity Funding Insider Information,and the Regulation,21UCLA L.ReV.1 (1973);W.Kennedy&HerbertWander,Texas GulfSulphur,A Most Unusual Case,20 BUS.LAW.1057,1062 (1965).并最终被1980年的Chiarella案所提出的“信义义务标准”所取代。⑧United State v.Chiarella,445 U.S.222(1980).在Chiarella案中,第一审法院曾判定被告有罪,上诉审中,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亦适用了“信息占有标准”,明确指出:“无论是否属于公司内部人员……通过合法途径入手重要的未公开信息的人在利用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时,通常会产生应当公开信息的义务。”⑨United State v.Chiarella,558 F.2d 1365(2d Cir.1968).在运用“公开或戒绝交易规制”的基础上,上诉审法院支持了一审的判决。该案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以后,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却认为:“当认定一个人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因怠于公开信息而构成欺诈时,应当仅限于此人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而这一义务的产生,应当基于信息的获得缘于交易当事人身为受任者或与之类似的信赖关系。”⑩United State v.Chiarella,445 U.S.228-229(1980).由此,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信息占有标准”,判定Chiarella无罪。
根据Chiarella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内幕交易的成立需要一方构成欺诈,欺诈的成立在于一方未履行内幕信息公开义务,负有内幕信息公开义务的前提在于信赖关系的存在。这一通过信赖关系或者信任关系来判断公开义务的立场,被称为“传统信义关系理论”。[日]萬澤陽子:《アメリカのインサイダー取引と法》,弘文堂2011年版,第68页。根据该理论,内幕交易罪的适格主体为传统内幕人与临时内幕人。关于“传统信义关系理论”下内幕交易主体的范围,有学者认为包括信息受领人(tippee)。参见曾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识别标准的理论基础及逻辑展开》,《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笔者认为,信息受领人的理论依据已超出“传统信义关系理论”而属于“信息传递理论”。前者表现为任职于公司的内部人员,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与公司雇员等。后者表现为因业务关系而与公司存在一定关联的外部人员。
这一理论在我国的《证券法》中有所体现。因为,对比我国《证券法》第74条可知,其所列的六项“知情人”中,第1项至第4项均属“任职”于公司的内部人员,符合上述“传统信义关系理论”中“传统内幕人”的特征;而第5项、第6项则属虽来自公司外部但业务关联而有可能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符合“临时内幕人”的特征。
3.“不正流用理论”与我国《证券法》中部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传统信义关系理论”的一个延伸理论即“不正流用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始于Chiarella案判决书中首席法官Burger的意见(当时其意见并未被判决采纳),也是美国有关内幕交易主体识别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部分。参见前注⑥,並木和夫书,第119页。由于司法界与学界对此各执立场,何为“不正流用理论”至今亦莫衷一是。
这一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以首席法官Burger的主张为代表。他认为:“通过经验、预见力或勤勉以外的……不法手段而入手内幕信息的情况下,掌握内幕信息的人便负有公开义务。”(如不向交易对方公开信息或戒绝交易,则成立欺诈进而构成内幕交易。)另一派则以1997年的O’Hagan案中的裁判观点为代表。在该案中,被告O’Hagan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任职律师事务所被委托担任Grand Metropolitan PLC公司的法律顾问。期间,O’Hagan虽非Grand Metropolitan PLC公司的代理律师,却因职务便利获知了该公司收购的信息,其后进行了证券买卖而获益。依据“传统信义关系理论”,O’Hagan既不属于原告公司的内部人员,亦不属于该公司代理律师,就不属于内幕交易主体,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负有信义义务的一方将义务对象专属的信息私下转为自己谋利并佯装对义务对象表现忠诚的做法构成欺诈”。Untied States v.O’Hagan,521 U.S.654(1997).换言之,O’Hagan作为职员,对其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负有信义义务,其私下使用律师事务所掌握的Grand Metropolitan PLC公司的内幕信息构成了对律师事务所的欺诈而成立内幕交易。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不正流用理论”依旧立足于信义关系,乃是信义关系的细化;而Burger法官的理解因为淡化了“信义”关系,重点更强调对信息的“占有”,所以被批评为是一种“付限信息占有理论”。参见前注⑥,並木和夫书,第120页。
对比1997年O’Hagan案中的“不正流用理论”,笔者认为,我国的《解释》第2条第1项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所囊括的人员与这一理论存在对应,但二者却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不正流用理论”的基础在于“信义义务”的存在,“不正”乃源于对“信义义务”的违反,故未处于信义关系之下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并不在此理论的射程之内。我国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证券法律规范体系中“知情人”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与美国诸理论的内幕交易主体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参见前注,曾洋文。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对于这一部分人员,后来的“信息传递理论”进行了补充规制。
4.“信息传递理论”与《解释》中部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因为“不正流用理论”解决的是处于一定信义关系之下的人员能否成立内幕交易主体的问题,所以这一理论所涉人员的范围无法涵盖原本无信义义务却从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员处受领了内幕信息的人员。为规制信息受领者的内幕交易行为,“信息传递理论”应运而生。虽然美国首次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立“不正流用理论”是在1997年的O’Hagan案中,但自1980年经Chiarella案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后,这一理论已经被下级法院采用并形成判决,例如1981年的Mneman案——Untied Stated v.Mewman,664 F.2d 12(2d Cir.1981)。事实上,“信息传递理论”在美国并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派生于“传统信义关系理论”与“不正流用理论”,因为其规制的主体具有特殊性,所以在此进行单独探讨。
“信息传递理论”来自1983年的Dirk案。Dirks v SEC,463 U.S.646(1983).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信息受领人负有“公开或戒绝交易”义务来自两个前提:信息的传递人负有信义义务;信息受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信息传递人传递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信义义务的违反。基于这两个前提,本不负信义义务的信息受领人才从传递人处“继受”了信义义务,故这种义务又被日本学者称为是一种派生义务。参见前注,萬澤陽子书,第85页。
笔者发现,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罪的法律体系中,《解释》第2条第2项、第3项关于“非法获取内幕交易的人员”的规定正是对“信息传递理论”的折射——这类人员因与具有信义关系的人员存在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抑或在信息敏感期内与信息知情人频繁往来,才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我国现行法上的规范适用难题
通过我国法上的规范文句的理论支撑可以看出,对于何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不同规范性文件采用了不同的识别标准。其中,《指引》基于“信息平等理论”,以对信息的占有与否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内幕交易罪的主体,并不考虑行为人的身份。我国《证券法》与《解释》则立足于“传统信义关系理论”及这一理论衍生出的“不正流用理论”与“信息传递理论”,侧重对行为人身份——信义关系有无的考量,规制的范围远远窄于《指引》。虽然我国《刑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但《指引》作为供证监会使用的指导性文件,并无权划定犯罪主体的范围。这样,当行政犯罪具有了行政违法的情节加重犯或结果加重犯性质,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违法时所依据的《指引》,将无可回避地间接决定入罪与否。如此,必将把现行法上的规范的适用推入到两难的境地:要么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任由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第1项至第6项列举之范围内却占有了内幕信息的人游离于我国《刑法》之外;要么认可《指引》间接规定了犯罪,致我国《刑法》第180条第3款沦为一条具文。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上述“间接决定”无疑有违我国《立法法》第10条,已被多数学者批评参见王新:《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区分视角下的内幕交易——兼评内幕交易司法解释》,《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薛瑞麟:《金融犯罪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笔者于本文中不再赘述。然而,现行法上的规范的另外一个适用难题依然没有解决,司法实践并未严格基于“信义关系”对犯罪主体进行划定。换言之,对行为人能够构成内幕交易罪的“知情人”,并不基于证明其具有特定的身份,而是侧重其对内幕信息的“知悉”。指导案例第735号:“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3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诉刘宝春、陈巧玲内幕交易一审案”,《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期。这两起案件中,被告人均系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明文规定的主体之列,故不具备成立证券内幕交易罪的特定身份。然而,法院认为二人知悉了内幕信息,属于证券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如此做法,使我国《证券法》与《解释》有被空置之尴尬。
二、当前我国的主体识别标准之争:“信义”还是“知悉”
(一)我国学界的理论对立
鉴于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识别标准的不明与实务适用难题,经济刑法学者力图对该罪的主体范围进行修正甚至重塑,并由此分化出两派观点,即信义支持论与知悉支持论。
信义支持论的主张者立足于现有立法,寻求对该罪的主体范围进行保守且谨慎的补正,认为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规制面不宜过度扩张。该论主张者认为,内幕交易罪主体的适格应当基于可识别的信义关系,明确的列举乃必要之举,该罪的主体当为特殊主体。对于该法所未能囊括的人员,如与发行人正在进行缔结契约交涉的人员、参与发行人诉讼过程的公检法人员、因业务关系获知发行人信息的税务人员等,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予以补充,将其明确列举为内幕交易的主体。参见张小宁、刘勇:《中日证券法关于内幕人员范围的比较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由于信义支持论严格坚持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其规制范围被严格限定,故又被称为限定论。参见赵秉志、陈志军:《证券内幕交易犯罪若干问题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针对“限定”所可能带来立法滞后的问题,学者曾从我国《证券法》第74条第7项入手,提出“知情人”的实质特征应当是“基于职务可获取证券内幕信息”,刘宪权:《论内幕交易犯罪最新司法解释及法律适用》,《法学家》2012年第5期。《证券法》第74条第7项所涉及的人员当与前六项的主体类型具有同质性,以期通过对兜底条款进行开放性解释,为“知情人”的判断设置实质性的标准,来弥补明确列举的不足。
与主张信义支持论的论者截然不同,知悉支持论的主张者并不满足于对现行法的修补,而是力求打破特殊主体的限制,对该罪的主体进行颠覆性重塑。该论主张者提出以下观点:其一,“传统信义关系理论”适用于初期证券市场的面对面交易,随着交易模式的转型与交易主体的多元化,致使“传统信义关系理论”的适用显得捉襟见肘,从而不得不派生新的理论以囊括更多主体,“不正流用理论”与“信息传递理论”即为实例。然而,理论的扩张无异于削足适履,以至于类似案情的案件出现迥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带来了适用标准稳定性的动摇。参见前注,曾洋文。这种需要法官所左右的理论射程的收放,在实行成文法制、法官并无“造法”权限的我国并不利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参见傅穹、曹理:《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其二,美国难以摆脱对“信义关系”之依赖的原因在于,其证券法将内幕交易行为置于“欺诈”框架之下,对未将内幕交易行为纳入欺诈框架的我国,在犯罪主体的识别上并无证明“信义关系”存在的必要。参见前注,曾洋文。通过对信义支持论的批判,知悉支持论的主张者认为应当废除内幕交易罪的身份要件,变特殊主体为一般主体,提出成立该罪主体之关键在于知悉了内幕信息,而“知悉”的原因在所不问。参见何青、房睿:《内幕交易监管: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17期。由此即可省去对犯罪主体范围的列举与身份的证明。
(二)对当前争议的评论
1.对移植美国理论的本土条件关注不足
笔者对双方立场均持部分认同的态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知悉支持论还是信义支持论,其立场基础均源于美国的理论,但这些美国理论的产生却有其独特的普通法传统土壤。
纵观美国规制内幕交易诸法,首次明文使用“内幕交易”术语的法律为1984年美国《内幕交易制裁法》,但其未对“内幕交易”进行定义。立法者的理由在于,判例法足以保证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判断,为避免概念设定的不科学而引发不必要的论争,没有在成文法中设置定义的必要。在1984年美国《内幕交易制裁法》出台之前,美国对内幕交易的规制依据为1933年《证券法》与1934年《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中,不仅不存在专门规定规制内幕交易的条款,甚至连认定内幕交易的一般条款亦未予规定。美国对内幕交易的指控基础实为内幕交易行为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以及其下的10b-5规则。第10条b与10b-5规则之性质可以简单概括为“证券交易中的反欺诈条款”。这一条款要求,认定内幕交易需满足两个条件,即欺诈的存在、欺诈与证券交易相关。至于何为“欺诈”,美国不同法院、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立场,由此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主流理论。例如,无论是否负有“信义义务”,单纯地“占有”信息却不向对方披露而交易构成“欺诈”(信息平等理论);负有“信义义务”,同时“占有”信息,但不向对方披露而交易构成“欺诈”(传统信义关系理论);不法流用了内幕信息构成对信息源的“欺诈”(不正流用理论);原无信义义务,却从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员处受领了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构成“欺诈”(信息传递理论)。继1984年美国《内幕交易制裁法》出台之后,美国又陆续出台了有关内幕交易的两部成文法——1988年《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和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因两者皆未对内幕交易进行立法定义,1934年我国《证券交易法》第10条b以及其下的10b-5规则依旧适用。
由此可见,美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规制虽然存在成文法,但对内幕交易的认定却并非建立在成文法基础之上,而是依循普通法传统,以“欺诈”为联结点,通过对个案的阐释形成一整套规则。在“何人”的行为可成立“欺诈”的认定方面,美国历经了复杂的理论演进,以至于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主流理论,并未拘泥唯一标准。无论是以“知悉”抑或“信义”划定内幕交易主体的范围,背后皆有丰富的判例基础与法官论证的空间,确保对规制范围的合理收放。可以说,美国内幕交易规制是以诸理论为枝干、欺诈为根基、普通法传统为土壤孕育出的体系。作为规制证券内幕交易的源起国,美国经验被作为规制内幕交易的蓝本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仿效,我国亦是其中之一。然而,以上诸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致使移植来的理论在我国实务中的适用并不顺畅。由此笔者认为,我国在探索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时,过多侧重于对美国理论的移植,对理论得以适用的法律土壤特别是与我国法律土壤之间的本土适应性关注不足。
2.当前主张存在逻辑误区
除了对他国理论的适用条件这一大前提欠缺关注以外,当前我国学界的“信义”与“知悉”之争还存在具体的逻辑误区。
具体而言,若将“信义”与“知悉”之争具体化,争议焦点莫过于对两类“灰色地带”的群体可否入罪的问题。这两类“灰色地带”群体具体包括:其一,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列举之列,但因职务关系而获知了内幕信息的群体,例如,国家公职人员、并购重组参与方及有关人员、媒体从业人员、上市公司关联公司所委托的专业人员等;其二,被动获知内幕信息的群体,例如,无意间听说内幕信息的人员,或捡拾了内幕信息的人员。
知悉支持论的主张者认为,以上两类群体应一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信义支持论者则主张,应在主体范围上有所节制,对上述人员不予规制。然而,无论哪一立场,实质上仍未走出前述美国的理论。即便当前诸多主张中存在移植欧盟“市场进路”的呼声,参见吴昉昱:《我国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理论之解读与规则构建》,《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前注,傅穹、曹理文。笔者也认为,所谓“市场进路”无非是知悉支持论的换装,对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识别标准很难说是新的突破。
诚然,“信义”与“知悉”不失为解决内幕交易犯罪主体识别的两条路径。然而,如前所述,两者扎根于特定的普通法传统,将内幕交易行为入罪的思路可以清晰表述为“信义违背或不当知悉⇀交易⇀欺诈⇀犯罪”。在我国,既不存在普通法传统,对内幕交易的入罪亦未归结于欺诈,那么,信义违背或不当知悉后所实施的交易,与犯罪之间的连接点又是什么呢?
显然,基于“信义违背或不当知悉”而实施的交易本身,未必当然成立犯罪。在不具备孕育“信义”与“知悉”土壤及以欺诈为入罪根基的我国,移植美国诸理论划定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边界,极易将主体范围推至“信义违背或不当知悉⇀交易⇀界定要素不明⇀犯罪”的逻辑窘境。
从我国有关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不同规定及歧见迭出的学说论争中,不难看出我国立法与学界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摸索。然而,笔者认为,该罪主体识别标准选择的失当,缘于忽视了对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的考量。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素以主客观要件为支撑,在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而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时,先应明确刑法规定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因为法益的严重侵害才是入罪的实质条件。为此,可以说,我国连结行为与犯罪的枢纽并非欺诈,而是法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笔者认为,应当立足我国的当前犯罪论体系,以法益侵害为切入点,对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识别进路进行重新铺设。
三、以法益视角对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识别标准的重新审视
(一)对“秩序说”的批判
关于何为内幕交易罪所保护的法益,我国学界素来存在“单一法益说”与“双重法益说”之争。单一法益说的主张者认为,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为证券市场的管理或交易秩序;参见谢杰:《资本市场刑法——市场滥用犯罪规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8页;张苏:《对内幕交易罪争议要素的评释》,《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4期;双重法益说的主张者则认为,该罪之法益为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双重法益说存在多种表述,如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或制度)与投资者合法权益(参见王作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以及证券市场保密制度与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页)。不言而喻的是,无论单一法益说还是双重法益说,皆认同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为该罪所保护的法益。那么,此处的“秩序”是否当然具有作为法益的适格性?
关于该罪,我国《刑法》第180条没有明确法益所指,因该罪被归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章节,故立足于解释论的立场,将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视为本罪法益看似并无不当。然而,还原“秩序”的本质,所谓“秩序”是指“自然进程中和社会进程中所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作为行政犯色彩鲜明的证券内幕交易罪,其所保护的法益为“证券市场管理秩序”这一主张,亦随着社会发展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然而,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包括证券市场秩序在内的“经济秩序”实际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呈现着流变性与暂时性的特征。过分强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会导致刑法凸显滞后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某些秩序可以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秩序”的内容千差万别,有些秩序对防卫社会具有底线意义,杀人越货的行为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不被容忍;而一些秩序存在的目的,却是出于国家行政管理便利的考量,参见何荣功:《法益、经济秩序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载叶青、顾肖荣主编:《经济刑法》(第15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即为此例。刑法的片断性决定了刑法应当着重选择对前类秩序的保护,过多强调后者,无异于将刑法变为了社会保障法,存在动摇刑法根本属性的危险。
当然,或许有折衷观点认为,刑法保护秩序的目的在于保障规范效力,而规范效力的目的在于保护权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误将手段看作了低位阶的法益,忽略了法益的终极性。追究将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作为内幕交易罪法益的缘由,不难发现,这与充斥我国刑事立法与理论研究的“泛秩序保护”现象不无关联。我国《刑法》第180条虽对法益未予明确,但该法第13条所框定的犯罪概念却明确将“秩序”列为犯罪所侵害的法益(虽然我国《刑法》并未使用“法益”这一表述)。同时,我国《刑法》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则将种类繁多的“秩序”列为法益。此外,理论研究中亦不乏将其他章节中罪名的法益解释为对特定秩序的违反。例如,对非法制造枪支罪,学者认为其侵害的法益除了公共安全,还有国家对枪支的管理秩序。参见贾宇主编:《刑法学》(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
(二)证券内幕交易罪法益的提出
至于如何从实质上把握证券内幕交易罪所保护的法益,笔者认为,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其的解释在宏观上不能偏离市场经济内涵,在微观上需要考虑证券市场的特性,即在市场经济体制语境下,市场主体享有基于个人意志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参见王海明:《论经济自由原则》,《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参与证券发行或交易的主体,应当遵守“三公原则”与“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故内幕交易罪本质上是平等市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严重侵害。此处权益的侵害应当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含有实际内容,因为过于抽象的法益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参见前注,张明楷书,第54页。
具体而言,因为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所以把握信息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把握了财富。同时,证券交易是一种零和交易,即买入价格与卖出价格必然相等。基于此,事先知悉信息者基于信息优势进行预先操作,其获得的经济利益或避免的经济损失,无异于将他人的经济利益据为己有,或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转嫁于他人,是对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经济利益的剥夺。因此,笔者认为,证券内幕交易罪的法益应表现为证券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
(三)主体范围的扩张与限缩:以证券内幕交易罪法益为视角
仅基于证券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这一法益,尚不足以解决前述“灰色地带”的两类群体能否归入犯罪主体的问题,还应对侵犯证券内幕交易罪法益的主体的有关条文进行语义解释,并考虑法益的保护限度。
所谓对条文的语义解释,是指对现有刑法条文进行文义和语用分析,即“在特定语境中考察刑法文本的意义。离开语用的语义是僵死的、教条的、无法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离开语义的语用是虚幻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语义和语用必须结合起来”。王政勋:《刑法解释的语言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1页。
其一,关于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知情人”列举之列,但因职务关系而获知了内幕信息的人员(例如,国家公职人员、并购重组参与方及有关人员、媒体从业人员、上市公司关联公司所委托的专业人员等群体)能否被纳入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体,有学者认为,对此类群体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尚不明确,无疑影响到认定结论的合法性”,曹理:《证券内幕交易构成要件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故其对此类人员的规制合法性持怀疑态度。那么,作为行政犯,既然定性为行政违法尚遭怀疑,那么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考虑,更无将其上升至犯罪的空间。可以说,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是持反对将此类人员纳入该罪主体的学者的主要理由。甚至有学者批判性地认为,2012年《解释》仅是对判断“知情人”所依据法律、法规的简单罗列,因为未涉及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判断难点,所以对于指导反内幕交易实践的意义不大。参见前注,刘宪权文。然而,笔者认为,机械地拘泥于法条文字无益于把握刑法条文的内涵,应当对我国《刑法》第180条及其援引的我国《证券法》第74条进行符合语用的解释。
证券内幕交易罪空白罪状的存在体现了我国《证券法》对我国《刑法》第180条的补充和引导。为此,刑事违法性应结合我国《证券法》文本背后的含义进行整体考量。我国《证券法》第74条虽然只列举了六类“知情人”,之所以如此列举,乃是缘于这类群体存在一个共性,即与内幕信息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身份关联,其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行为通常会侵害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易言之,特殊的身份关联与法益的侵害之间具有惯常性,故法律将这类身份予以了类型化。可以说,我国《刑法》第180条的特定语用含义正是在于,借助证券法规制基于特定身份而对法益侵害存在惯常性的行为。
值得学界与立法者关注的是,随着企业间的合作方式的创新,媒体监督程度的深入、国家公职部门的主动(如税务部门)或被动(如司法机关)地介入,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之列却与内幕信息存在特殊的身份关联和法益侵害惯常性的新群体正在涌现。既然这类群体基于身份关系与我国《证券法》第74条所明文列举的群体存在同质性,那么,“必须把握立法者从形形色色的行为中挑选出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实质的、正义的标准,使根据正义的标准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都纳入犯罪,使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得到相同的至少是相似的处理”。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为此,笔者认为,当前不在我国《证券法》第74条“知情人”列举之列,但因职务关系而与内幕信息存在身份关联的人员应当可以成为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同为“身份关联”,但此处之“身份关联”并非来源美国法中的“信义义务”,其原因笔者之前已有阐述。
其二,关于被动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如无意间听说了内幕信息,或捡拾到了内幕信息的人员)能否成为证券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当前的主流立场是将其归入《解释》第2条第1项所列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得出这一结论的进路在于,对“非法获取”做宽泛理解,将“非法”解释为“不应获得而获得”。参见前注,张苏文;前注,刘宪权文。笔者认为,对此类人员的定性不仅应对条文进行语用解释,还应当偏重从法益保护的限度角度进行考量。首先,关于《解释》第2条第1项之“利用窃取、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私下交易等手段”这一规定,根据语境,其语用含义应为:“非法获取”仅限主动获取内幕交易而侵害法益的情形,若将条文中的“等”解释为包括被动获取在内的一切手段,则是对语境的违反。其次,因刑法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在法益保护的限度角度内,当某类群体对法益的侵害不具有惯常性,则不具备犯罪主体的适格性。笔者并不否认被动获取内幕信息者的内幕交易行为会对证券市场其他主体的经济利益造成侵害,但是,处罚侵害法益的行为人既是为了预防此类人员再次侵害法益,也是为了预防其他人侵害法益,故“对于极为稀罕的行为,即使法益侵害较为严重,也没有必要规定为犯罪”。同前注,张明楷书,第66页。
四、对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引介与评论
以上从法益视角对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之应然范围进行了阐述,但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对此,笔者以下拟引介基于法益视角划定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成功例子即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以期对重塑该罪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提供借鉴。之所以引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理由在于:其一,我国与日本同属成文法国家,在法传统与对法规范的适用上,两国更为接近;其二,日本自“二战“后方开始强化对市场和投资人的保护,且最初亦借鉴了美国理论,然而,历经70余年的本土化摸索,其中部分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三,日本亦立足于法益保护对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进行划定,与笔者于本文中的主张一致。
(一)主体范围的划定
在日本早期规制证券交易的立法中,并无规制内幕交易的单独条款。证券交易的所有行为由依据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条b及10b-5规则所创制的旧日本《证券交易法》(以下简称:旧法)第58条(不正当行为之禁止)一并规制。内幕交易的单独条款始自1987年爆发的“立保化学工业事件”,以此为契机,财务省(旧大藏省)于同年9月开始探讨“谁”利用了“何种信息”可以成立内幕交易。1988年,规制内幕交易的条款自旧法第58条中脱离,改由第190条第3款单独规制。2006年,旧法被更名为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幕交易的条款从旧法第190条移至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166条。虽然日本最初以美国法为蓝本规制证券内幕交易,但其主体范围的识别逻辑与立法已与美国法大相径庭。
其一,在主体的识别逻辑方面,日本未遵循美国将内幕交易的本质归结为“欺诈”的思路,而是注重以围绕法益保护这一核心,研究犯罪主体的外延。关于内幕交易罪的法益,在日本亦有论争,具有代表性的主张者有“证券市场的公正性与健全性及证券市场的运行秩序说”,[日]神崎克郎:《内部者取引の規制に関する各国法の動向》,《ジュリスト》1984年第819号,第79页。“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赖说”,[日]横畠裕介:《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に関する刑罰の概要(1)》,《商事法務》1988年总第1148号,第8页。“证券发行公司的利益说,投资者的财产利益说”等主张。[日]神山敏雄:《経済刑法における保謢法益》,《Law School》1981年总第129号,第52页。这些学说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过理论的主流,也曾因时代的发展渐受批判。在社会发展与学说争议的过程中,有关规制内幕交易的法条几经补充和完善。例如,在制定有关条款之初,处于磋商阶段的合同缔结者未被归入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后因此类人员侵害行为的大量出现而在1998年旧法修订时被新增为犯罪主体。信息受领者亦然,因被指出“一般情况下,与公司关系人具有特别的关联,故其交易行为会有损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公正性与健全性的信赖,基于这点考虑,有将其纳入规制的必要”,[日]横畠裕介:《逐条解説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と罰收》,商事法務研究会1989年版,第121页。而被明文增列为主体之一。
其二,在立法形式方面,日本采用特别刑法,通过高度“形式化、技术化”的列举方式确定主体范围。参见[日]大崎貞和:《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見直しの概要と今後の課題》,《資本市場》2013年第3号,第26页;[日]川崎友巳:《インサイダー取引》,《刑法雑誌》2016年第55巻第3号,第526-527页。根据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166条,日本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可归纳为“内部者”“准内部者”“第一次信息受领者”三大类。所谓“内部者”系指公司关系者,具体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从业人;拥有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持3%以上已发行股票的股东(此类人员又被称为“账簿阅览权人”);优先出资法所规定的普通出资者中的阅览权人或拥有阅览权的母公司的职员。所谓”准内部者”,具体为:基于法令对上市公司享有一定权限的人员(例如,具有侦查权的警察、检察官、与审判相关的法官、可行使调查权的税务局或国税厅职员、仲裁员、行使国政调查权的国会议员与从事国会辅助工作的议员秘书等);与上市公司存在契约关系或正在缔结契约的人员(例如,法律顾问、理税师、便理士、会计师、银行、翻译、购买证券的公司等);所谓便理士,相当于代办人,在日本指代办并鉴定专利、实用创新发明、设计和商标等需要上报专利厅及经济产业大臣的有关手续的业务人员。在“内部者”中有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持有3%以上已发行股票的股东(账簿阅览权人)。“准内部者”中与上市公司具有契约关系或者正在缔结契约的人员为法人的情况下,其董事属于“准内部者”。根据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上述“内部者”与“准内部者”,在其终止特殊身份的一年之内,仍属于内幕交易罪的主体。所谓“第一次信息受领者”,即内部者与准内部者以外的,自内部者与准内部者处直接受领内幕信息的人。“此处的信息受领者若构成内幕交易的主体,需满足三个条件:认识到是从公司关系人处受领信息、此内幕信息为法令所规定的重要信息、信息尚未公开”。[日]神山敏雄:《日本の証券犯罪——証券取引犯罪の実態と対策》,日本評論社1999年版,第56-57页。自立法至今,日本法只规制“第一次信息受领者”。从“第一次信息受领者”处受领信息的“第二次信息受领者”及之后的信息受领人,由于不在前述所列主体中,即便实施了交易行为,也不会被认定为内幕交易。
(二)对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主体模式的评论
1.鲜明的“信义关系理论”色彩
美国法虽为日本规制内幕交易立法的蓝本,但日本法未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定性为欺诈,“公开或者戒绝交易规则”在日本内幕交易的规制体系中并无体现。此外,日本法亦未遵循美国的“信息平等理论”,却借用了“信义关系理论”,并在成文法中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运用。具体而言,旧法与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虽未直接使用“信义关系”或者“信义义务”的表述,但立法者认为,居于特殊地位的人员利用内幕交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会有损法益而应当受到规制,参见[日]資本市場研究会主编:《内部者取引の規制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証券取引審議会報告》,資本市場研究会1988年版,第15页。故其所列举“内部者”“准内部者”,均要求行为人具备与公司存在某种关联为实质性身份特征,具有鲜明的信义关系理论的色彩。不仅如此,日本法围绕法益的保护,在移植“信义关系理论”的路径上较之美国迈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在“内部者”与“准内部者”中,当不具有特殊身份(职务关联性)后,一年之内仍然可以成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这意味着,“信义关系”并未因主体身份的变更而消失。笔者认为,这一设定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不无关联。日本企业高度重视企业员工的“定着性”,长久以来的“雇佣终身制”致无端离职的现象较为罕见。对于企业的“内部者”而言,当“内部者”不再具有特殊身份时,多系达到退休年龄而离任。对于数十年于同一企业工作的人而言,对企业的商业秘密、运行模式与后辈极其熟识,可能成为其进行内幕交易的有利因素。将脱离“内部者”“准内部者”身份一年之内的人依旧划归为规制对象的规制方式,有鲜明的日本企业文化的烙印。
2.“形式犯”特征
无论旧法抑或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日本法对内幕交易罪诸要件的规定一贯回避抽象的概念,尽量客观化、具体化,主体范围亦不例外。同时,有关犯罪主体的条文未予设置兜底条款,严格限制了规制对象范围的扩展。这不同于我国《证券法》对“知情人”的认定(设置了兜底条款)。这种高度形式化、详细化的“形式主义”的识别方式赋予了内幕交易条款鲜明的“形式犯”特征,被日本学者自诩为日本特色。参见前注,横畠裕介书,第16页。虽然多年来对这种“形式主义”不乏批判之声,但是出于法的安定性、刑罚明确性与规制实效性的考虑,这种形式至今未被撼动。参见[日]大崎貞和:《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見直しの概要と今後の課題》,《資本市場》2013年总第331卷第26页;[日]川崎友巳:《インサイダー取引罪》,《刑法雑誌》2011年第51巻1号,第79页。
3.主体范围被严格限定
“信义关系理论”色彩与“形式犯”的特征,使日本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范围呈现出限定性。易言之,日本仅承认基于职务关系而合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此外一律排除。例如,如果上市公司的清洁员在清扫过程中于垃圾箱内发现了内幕信息的材料,那么属于“因职务而知悉”,其利用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可成立内幕交易罪;然而,清洁员于清扫过程中偷看了他人桌上的内幕信息材料,则不属于“因职务而知悉”,因此无法成立内幕交易。>参见[日]西村あさひ法律事務所、聞き管理フループ:《インサダー取引規制の実務》,商事法務2010年版,第44-60页。究其原因,学者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指出,“因职务而知悉”,应仅限于直接行使职务权限而获得内幕信息的情形,若仅是(非基于职权的)与内幕交易的“物理接触”,则不属于对特权的滥用,故未损害法益参见[日]佐伯仁志:《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载西田典之主编《金融業務と刑事法》,有斐閣1997年版,第226页;上注,西村あさひ法律事務所、聞き管理フループ书,第46页。。基于这一立场,日本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范围远远小于我国。因为依据《解释》第2条第1项规定,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属于“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属于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制的对象类型之一,而这类群体因不具备“因职务而知悉”这一要件,在日本均被排除于内幕交易条款之外。同理可以得出,那些在我国尚有争议的、居于“灰色地带”的人员,如无意间听说了内幕信息或捡拾了载有内幕信息资料的人员,在日本不会被规制内幕交易的条款科以刑事处罚。
4.保护法益考虑规制的实效性
关于信息受领者,日本法在美国1997年正式确立“信息流用理论”之前即规定了对“信息受领者”交易的禁止,可以说是具有超前性的。然而,日本法对传递的环节做了严格的限制,仅限于禁止“第一次信息受领人”的交易行为。
关于为何仅强调信息的“第一次”受领者成为规制的主体的理由,日本国会内部产生过论争,在日本第112次国会参议院大藏委员会记录中,当时的和田教美委员提出以下质疑:“条文虽然是针对第一次信息受领者的规定,但是如果信息进而被第二次、第三次传递,法律对第二次、第三次受领者是否可以适用?”针对这一质疑,当时的旧大藏省证券局长藤田恒郎的答复为:“从作为公司关系人的内部者、准内部者处受领信息的人员……基本被限定于第一次的受领人,第二次信息受领者原则上不在规制范围之内。原因在于,如果扩大了信息受领者的范围,……规制对象的范围将无限扩大,这一境况反而将有损法秩序的安全性。参照世界各国例如英国,也仅仅将信息受领者限定为第一次受领者。”[日]平山幹子:《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と共犯の成立範囲》,《甲南法学》2007年第47巻3号,第104页。学说上关于限定信息受领者的范围,亦存在赞成与否定两种立场。批评者认为,基于公平的考虑,第二次及以后的受领者同样应当予以规制,若行政或刑事均不处罚此类行为,如果在行为人与作为信息源的公司关系人之间,即在信息获取渠道间放置一人以上“道具”,则可以为堂而皇之地逃脱法网提供可能;参见[日]中山研一等:《経済刑法入門》,成文堂2001年第3版,第164页。“在何处划定界限固然是一个难题,为此将界限划定在第一次的做法也未免武断”,[日]龍田節:《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ジュリスト》1990年总第948号,第159页。将范围限定于第一次信息受领者的这一规制瑕疵,无异于“规制的巨大漏洞”。[日]龍田節:《インサイダー取引の禁止》《法学教室》1993年总第159号,第67页。此外,有的学者从立足于规制的目的指出:“现行法中将‘信息受领者’的范围限定于第一次信息受领者,从规制目的来看其合理性存在问题。内幕交易规制的重点在于,将规制着眼于消除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平等;或者,如果投资者所持信息不平等,……为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不被侵害,规制对象应当扩展至持有信息的任何人。”[日]神山敏雄:《日本の経済犯罪——その実情と法的対応》,日本評論社1996年版,第240页。针对批评的见解,有赞同者指出:“这类人员(第二次信息受领者与其之后的信息受领者)所实施的信息公开前的交易,在违法性方面虽然(与内部者与准内部者)并无二致,但若处罚此类人员,会将处罚范围置于不明确的境地,有可能损害法的安全性,为此应当加以限定。”[日]芝原邦爾:《インサイダー取引の処罰》,《法学教室》1994年总第166号,第93页。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日本主流学说与立法对于信息受领者范围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态度,在承认信息的传递对交易的侵害同时,对保护法安定性做了让步。
五、法益视角下主体范围的规范重构
(一)活用兜底条款,将“职务关联性”作为“知情人”的实质识别标准
日本对内幕交易规制的经验虽被称为移植内幕交易规制的先驱,参见葛愛軍:《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に関する研究(1)日本·アメリカ·中国の比較を通じて》,《北大法学論集》2008年总第59巻第4号,第99页。但在犯罪主体的划定方面,其缺少兜底条款且高度“具体化”的立法方式,不得不说是当前日本法的缺陷以致日本不得不通过法律修订的方式对主体进行补充。相比之下,我国《证券法》第74条设置了兜底条款(第7项),较之日本法更具有科学性,可用以解决当前列举不足及未来产生的立法滞后问题。然而,我国却未能将其活用。因日本明文列举的主体类型较为全面,有学者主张,从我国《证券法》第74条前六项入手,用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所列诸人员填补我国《证券法》第74条之空白(排除当前我国尚不普及的,如信托业者等)。参见张小宁:《证券内幕交易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08页。笔者不否认日本法对我国的借鉴价值,但对简单移植外国法的主张不敢苟同。因为明文列举仅是当前认知的总结,终会因时代发展而捉襟见肘,何况日本法本身因缺乏兜底条款而存在诸多规制适应性方面的缺陷。
笔者认为,解决“知情人”范围问题,应重视兜底条款的活用。当前有关兜底条款的论述多将焦点集中于《指引》所列人员是否属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继而为数众多的论述认为《指引》间接规定了犯罪,并引出了《立法法》上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现状偏离了完善内幕交易罪主体要件的这一中心。应当基于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将“与内幕交易存在职务关联性”作为“知情人”实质识别标准,明文列入我国《证券法》第74条第7项,以规制不在第74条前六项列举之列,但因职务关系而获知了内幕信息的群体,以此弥补列举的不足,并避免实务中出现对兜底条款的适用争议或不当解释。
(二)缩限“非法”的含义,重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范围
1.关于“信息受领人”
我国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将“信息受领人”单独列为主体,但在条文中却可把握对这类群体行为的限制。例如《解释》第2条中所规定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未对“非法”从主观上细化,致使基于传递者与受领者双方合意才产生的“信息受领者”与单方面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混为一谈。在《解释》第2条中,“利用套取、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者”(第一项中部分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第二项)、“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的人员”(第三项)在性质上与日本法中“信息受领者”并无二致。如前所述,成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信息受领者需满足受领者认识到自己是从公司关系人处受领信息、与受领的内幕信息为法令所规定的内幕信息、信息尚未公开这三项条件。为此,信息受领者的成立需要基于信息传递者的传递意思与受领者的受领意思(双方意思产生的先后在所不问),且双方均明知信息的“内幕”属性。
笔者认为,正是知情人与内幕信息之间的“职务关联性”及其与受领者之间存在的诸多关联,致使两者之间传递意思、受领意思的产生及进一步的交易行为会对法益造成侵害,故信息受领者对法益的侵害未必小于“知情人”。相反,实务中这类群体反而是内幕交易的主力。为此,我国法应当借鉴日本经验,将此类人员规定为与“知情人”并列的主体,以方便法律实施中的识别。对于信息的传递,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与实效性,我国法亦应借鉴日本经验,对传递层级进行限制。
2.关于“信息受领者”以外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对于此类群体,应转变当前将“非法获取”扩大解释为“不应获取而获取”的作法,考虑法益保护的限度及刑法作为一种普遍适用规范的属性,将“非法获取”限定为“主动获取”的情形(如盗窃、抢夺、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譬如,于出租车上捡拾内幕信息材料、公共场所无意间听到内幕信息并交易等不具有普遍性的情形应被排除于犯罪之外。至于不具备普发性的行为将如何规制,笔者主张对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其规制逻辑将在其他论文中探讨,笔者于本文中不再展开。
(三)将犯罪主体扩大至曾具备“职务关联性”的离职人员
鉴于我国近年企业高管离职率的增高,考虑到具备“职务关联性”的“知情人”极可能在获知内幕交易后为实施交易而终止其特定身份;或因其他原因终止身份后再利用职务期间掌握的信息进行交易,与离职前实施该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并无二致。以我国金融市场为例,2016年上半年,沪深两市共计7872位上市公司高管离职,这些高管累计涉及1672家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57%。《上市公司高管离职成风!金融业离职率最高,涉及43公司120名高管》,http://news.cnfol.com/zhengquanyaowen/20160816/23280766.shtml,2018年4月3日访问。针对这类群体,我国法有必要借鉴日本经验,对曾具备“职务关联性”的离职人员,在其终止特殊身份后设定一定期限,在规定期限内仍属于“知情人”,以将其纳入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的范围,为法益提供更周延的保护。2012年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的“周和华—科达机电案”(中国证监会2012年第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为实例。该案当事人提出,2010年1月之前,其已辞去科达机电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去了科达石材董事、科达香港执行董事等职务,故不在法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之内。针对这一抗辩,证监会认为,“2010年3月20日科达机电发布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中,周和华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仍然是被激励对象”,从而否认了周和华的“离职”,将其认定为“知情人”。反之,如果周和华确实离职,其行为依据我国现行法即无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