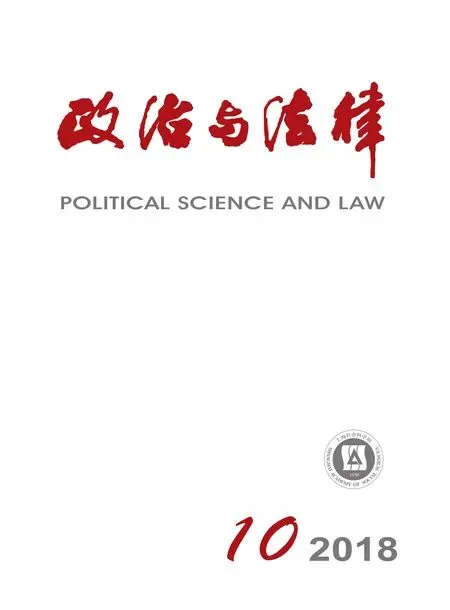象征性刑法概念辨析
郭 玮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一、象征性刑法本体性问题的厘清
近年来,随着刑法对社会领域的规制愈加深入,象征性刑法概念被引入我国并被当成评判刑事立法的工具。一种新理论或概念在被运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本身展开深入的研究,探索其产生的语境与实质内涵。象征性刑法作为舶来品,在传统刑法向现代刑法转型过程中,其能否应用于我国语境以及是否具有较大启示意义,需要立足于本土对其本体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象征性刑法的概念
象征性刑法源于德国,德国刑法学界对此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德国学者Winfried Hasseme将象征性刑法概括为:“为了因应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立法者过度高估刑事立法于实证经验上的成效且实际上根本不期待刑法任务可以实现,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扩张的刑事立法。因立法者原本就无意对立法是否具有成效的问题提出任何解释,故可能衍生的立法不足也就没有调整改进的必要。最终立法者获得政策上的象征性利益,例如回应社会问题的敏捷性、行动能力以及企图让刑法适用范围更具全面性等。”Carl Constantin Lauterwein对象征性刑法的定义为:“刑法对外传达一定讯息而产生的沟通效果,能够让其达到更有效率的法益保护目的,只不过这样的沟通效果欠缺立法行为应当兼具的目的理性。①参见古承宗:《刑法的象征化与规制理性》,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17年版,第121页。Claus Roxin以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否认或粉饰在纳粹统治下所实施的种族灭绝犯罪的,予以刑罚处罚”为例,指出“象征性刑法并非服务于法益保护,而是谋求刑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表达国家自我姿态的法律规定”。②[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刑事法评论》2006年第2期。Eric Hilgendorf如此概括象征性刑法:“社会很多领域存在重大问题,目前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政治发现刑法是一种打击犯罪的廉价和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手段。通过刑法措施,政治可以营造一种积极性的印象,而不必承认它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③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日本学者松原芳博在考察日本刑事立法动向后指出:“与其说这些立法是要保护国民的实际的具体利益,毋宁说是为了回应国民‘体感治安’的降低,试图保护其‘安心感’,作为象征性刑法的色彩要浓一些。”④[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纵观上述对象征性刑法的解释,象征性刑法可以解构为四个层面:立法目的、立法过程、立法结果与立法影响。在立法目的层面,主要出于政治性考虑,借助立法增强执政信心与民众安全感,树立国家消除危险、保护人民的积极形象。在立法过程层面,欠缺理性,利用刑法立法便捷的特点,在未经缜密考察论证之前仓促立法,尽最大可能提升立法效率。在立法结果层面,立法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立法实效,甚至根本不期待取得立法实效。在立法影响层面,以立法者为代表的执政者获得了预期的利益,展现了立法的及时性及对民众的关切,沉湎于自我建构的精致刑法象牙塔中。上述四个层面贯穿了象征性刑法立法的全程,学界对象征性刑法的否定也主要围绕这四个层面展开。虽然上述每种解释侧重点不同,但对象征性刑法的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否定性的。笔者认为,将法律与政治混同,进而对立法科学原则的违反是象征性刑法遭受非议的主要原因。首先,虽然“法律的统治”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法律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法律规范体系源头上的政治缺口,使得法律完全超越政治之上仍然只是一种尚待实现的政治理想。⑤参见胡水君:《法律的政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然而,即便法律无法凌驾于政治之上,其也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与封闭自洽的体系,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治对法律的过度干预与法律作为政治附属物的命运。混淆政治与法律的界限,推动政治主张跨越政治影响力的藩篱,采用具有行为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权威性、普遍约束力等特性的法律形式来统一全体公民的意志,⑥参见卓泽渊:《法政治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6页。进而取得预期的政治效应,是立法工具化的表现,对立法民主造成了极大损害。其次,法律的制定有其基本规律,非理性立法将有损秩序、公正与自由,在立法过程中必须谨慎,对于强调谦抑性质的刑法尤其应如此。哈耶克认为:“立法是以审慎刻意的方式制定法律,已被论者描述为人类所有发明中充满了最严重后果的发明之一,其影响甚至比火的发明还要深远。”⑦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立法科学原则是立法审慎的应有之义,要求在立法活动中遵从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立法规律,掌握立法活动的规律性,善于利用立法技术,提高立法质量。立法科学原则在风险社会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界定风险、确定风险和评估风险,还有助于作出应对风险的科学决策。⑧参见何跃军:《风险社会立法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69页。风险社会要求立法调研与立法规划必须符合风险社会的要求,立法决策在符合风险社会特征之外,还要注重实践,通过扎实的实证调查搜集全面信息,进而提炼出民众对立法的真实需求。
(二)象征性刑法不同于刑法的象征性
象征性刑法不同于刑法的象征性,前者是一种刑法立法模式,而后者是刑法的性质与机能之一。刑法集强制性与象征性于一身,强制性规定主要见于刑法分则及部分刑法总则条款,象征性规定则主要见于刑法总则条款,如我国《刑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与根据的规定,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第13条关于犯罪含义的规定等。这些条款并非典型“三段论”式的刑法规定,没有刑罚后果,但不可或缺。刑法的象征性条款具有较强的宣示功能,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刑法的规定、原则与价值,有利于刑法的稳定及普及。第一,强制性条款具体调整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具有预防犯罪与恢复社会关系的功能,被视为具有“尖牙利齿”,而象征性条款并没有“尖牙利齿”,其作为法规范的“象征”,通过对行为期待的违反进行非难,表达出规范命令的可贯彻性与宣示规范效力应当受到尊重,维持一般社会大众对于法规范的信赖。正是象征性条款的存在,才能在规范的层面上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什么是刑法的目的,等等。因此,象征性条款具有宣示性、引导性及全局性,失去了象征性条款,立法就容易陷入盲目,法律的定位也模糊不清。第二,象征性条款是一种体现公众认知及正义直觉并将其规范内在化的社会整合手段。很多关于正义的判断都是直觉性的,特别是那些涉及人身伤害或者以未经同意的财物占有为核心的不法行为的判断。关于正义直觉,人们具有超越所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高度共识,因此刑法有必要充分体现公众认知及正义直觉,否则不仅不利于公众规范内在化过程的顺利进行,更降低了公众对刑法的尊重与遵从,这时就减少了刑法的道德可信赖性及有效性,人们会倾向于不服从、不合作。⑨参见梁根林主编:《刑事政策与刑法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278页。与刑法的象征性相比,象征性刑法只是对重大社会问题的临时因应,立法者无意去探求立法的实效性,而着力获取政治利益。刑法本身即便发挥出了一定的规制效果,也并不是立法者有意的设定,而是在相当长的适用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潜在的规范宣示功能。总之,象征性刑法与刑法的象征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立法的目的是否为了迎合民众情绪及追求政治效益,是否表达出规范命令的连贯性与规范效力应当受到的尊重。若出于政治考量,以纯粹情绪性的社会不安全感建构出刑法规范,这并不具有刑法的象征性,只是公众情绪宣泄及立法者迎合的产物,且不可避免地偏离了法治国轨道。
(三)象征性立法不同于民主立法
民主立法指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和需求,具体包括立法主体的广泛代表性,立法内容的人民利益性,立法过程的规范性。在风险社会中,民主立法要求人们确保公开且广泛的实质意见交流,即公众能够直接影响立法者,并最终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同时,存在一个确保公众之间、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公开而广泛的实质意见交流机制。⑩参见前注⑧,何跃军书,第157-159页。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公民的实质参与,这样才能保证法律规范体现人民的利益。在风险社会中,价值与利益日趋多元化给民主立法设置了重重障碍,公众的参与范围、参与方式、参与程度、参与机制等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立法的民主与否。风险社会的议题也往往具有高度专业性,如环境问题、转基因问题、医疗问题、网络犯罪问题等。关于上述问题的立法,即便公众积极参与,也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上述问题的叠加使风险社会的民主立法面临挑战,高涨“民意”影响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更是如此。民意一般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其横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与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具有不稳定性、可塑性、模糊性与多元性,这使得其内涵与范围模糊不清,难以把握。美国政治学家凯伊认为,要想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参见何静:《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第32-36页。虽然民意影响下的立法也存在一定比例的民众参与,甚至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参与机制与完善的参与渠道,但绝非民主立法,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立法启动机制不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机构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30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向社会通报。上述机构在提出法律案的同时,还应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事实上,提案的机构往往具有专属的职权和管辖领域,能够在其职务范围内发现需要立法的事项,对社会变迁和犯罪形势变化较为敏感,提案兼具专业性、针对性、科学性与权威性。如大量经济犯罪的提案,很多来自于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的意见。为了确保提案权的民主性、全面性,目前还有扩大提案主体范围的趋势,如有学者建议将提出议案的权利赋予全国性的正当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以及一定数量的选民联合。参见姚龙兵:《刑法立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民意”影响下的象征性立法的根本动因是民众抽象的、诉诸直觉的安全感受。与民主立法程序启动的法定性不同,由于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冲突以及从众的社会心理,“民意”的表达具有自发性与不稳定性,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媒体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信息社会赋予了网络媒体更多的优势,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使得公众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表达其价值观及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参见周道华:《构建和谐社会与网络舆论的引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的优势愈加明显,各类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平台更随意,交互性更强,影响范围更广,任何话题或事件都有可能汇聚成影响立法的汹涌“民意”。然而,媒体固有的“扩声器”作用时常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在这方面,媒体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通过制造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兴趣,并迎合公众的朴素感情和道德意识,激发公众的感性情绪,借以作为向决策者施压的工具。媒体一方面利用倾向性的报道影响公众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利用煽动性报道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其后果是,决策者可以忽略舆论,但无法忽视舆论背后的民意。参见李怀胜:《刑事立法的国家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85页。因此,民意形成的自发特质以及媒体的报道、造势,使得“民意”的成色并不纯粹,具有倾向性、片面性、业余性及非理性,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公众需求,在这种“民意”驱动下的立法质量堪忧。实际上,“所谓的‘民意’具有多样性,任何一种社会都不是由完全单一的个体构成的,任何构成社会的主体都不是由数量不等,但在主体性质上完全等值的‘单向度的人’构成的。”舒国滢:《法哲学沉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具有像自然个人一样的理性器官,它的理性的声音需要极其复杂的制度和机制才能够呈现,而在没有获得这些之前,它的理性可能就仅仅呈现为不同个体之间彼此冲突的意见。参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历史法学(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不同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使得判断真实的社情民意成为一项重大挑战,影响立法的所谓“民意”未必是真实的民意。相比较而言,民主立法程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提案主体多为各个领域的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其人民性、代表性与客观真实性。加之现代大数据的搜集运用,国家机关能够动态地提炼、掌握民众的真实立法需求,并最终按照法定流程向立法机关提出议案。
二、象征性刑法的特征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古承宗将象征性刑法的特征归纳为:预防导向、法益抽象化、归责系统简化、弹性且全面的危险防御。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71-75页。刘艳红教授认为:“象征性刑法以保护弥散性法益为己任,只要有抽象的客体如‘安全’存在就可以动用刑法,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越来越多。”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中国刑事立法总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上述学者均强调了预防刑法观与法益抽象化,它们固然为分辨象征性刑法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并非象征性刑法的全部特征。象征性刑法的核心意义在于立法者为了安抚“民意”,罔顾立法科学性进行非理性立法,故象征性刑法的核心特征在于立法启动的随意性与立法过程的非科学性。象征性刑法的特征包括以下几项。
(一)因风险社会而生
“风险社会是指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高度发展,也同时带来危险或风险事态的社会。现代社会可以说是风险潜在化与一般化,随时都恐惧着料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从复杂社会认知与不确定性而来的恐惧,更加使危险感或不安感增加,从而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安全的希冀与需求。”王正嘉:《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保护机能论》,《法学新论》2009年第6期。民众的这种需要将近代以来被视为有迫害人权之嫌的国家权力由防御者的角色转变为控制风险的角色,人们认为国家对于风险的遏制能够有积极作为,并希望国家权力提前介入,祛除风险。其结果是一方面,预备犯代替了既遂犯,抽象危险犯代替了实害犯,刑法介入时间逐渐提前,惩处力度也逐渐严苛,另一方面,犯罪圈逐渐扩大,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未知的风险,为了安抚民众的不安心理,也基于刑法保护机能及预防机能,企图利用刑法提前消除风险或摆脱危险,进而不断增补刑事立法。在这些增补的刑事立法中,有些立法过程涵盖了谨慎的评估与调研,不盲从于非理性民意,立法效果良好,而有些立法则沦为象征性立法,这些立法借助民众渴望安定的心理,罔顾实际立法效果,积极追求政治性利益,虽然秉持积极的一般预防观,大量适用抽象危险犯,但始终无法更好地保护法益,且罪名适用率低,不仅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还有侵犯人权之虞。
(二)因“民意”而起
象征性刑法的目的并不在于影响现实以促进社会正向及理性的发展,只是国家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形成的价值偏好,期待在大众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法与不法意识,或者只是某个时空背景下社会的集体心理情绪。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66页。这种集体心理情绪一般是非理性的、躁动的,它激起了立法者安抚民众的愿望,也给了立法者扩张权力的灵感。在我国,网络时代的到来及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民众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制造议题与影响立法的能力。然而,公众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反应往往不尽理智,其共性在于将孤立的个案作为某种行为入罪的理由。如在山西“黑砖窑”案中,有人提议设立“奴役罪”,但人们很少去思考,在立法的必要性上,设立该罪的提议是否只是一时冲动,是否现有的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已无法应对该类事件,此类悲剧的发生是否应归咎于刑法等问题。无论一些建议多么不理智,建议是他们的法定权利,应予以保障。然而,对于立法机关,面对舆情民意,能否保持清醒理智的态度,能否对入罪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充分的论证,避免以符合人民期待为由盲目立法就显得至关重要。参见前注,李怀胜书,第74页。这种随意膨胀的集体心理情绪,已经对我国刑事立法形成了较大威胁,应予以警惕。
过度迎合“民意”与社会形势的政策性立法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瑟曼·阿诺德指出,法的功能,与其说是对社会的指导,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安抚。尽管“法治”的观念可能成为反抗的道义背景,但它通常诱导人们安于现状。[美]彼得·德恩里科:《法的门前》,邓子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有时候,刑事立法者关心的不仅是违法之人应受刑事制裁,更是国家可以通过刑法取得全面的社会控制,特别是刑法的行为控制重心将可以在刑事预防与其他法规范系统(如行政规范)两者之间任意游移,刑法最终走向类似秩序管制的危险防御法,形同放弃法治国的刑罚最后手段性原则,变相地转由刑罚前置性取代之。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75-76页。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就体现了这一点,“911事件”之后,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升民众安全感,美国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幅扩张情报与治安机关进行通讯监察与资讯获取搜索权。只要联邦调查局认定相关资料与恐怖主义或外国情报有关,经法院核准后,可强制任何人交出其客户之相关资料。其二,打破传统搜索的“敲门告知”原则,允许秘密搜索。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授权主管机关经法院允许后,等搜索完毕后相当时日,再通知被搜索人。其三,侵害移民人权。即便是已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非美国公民,亦可能因为行使言论、信仰与结社权利而遭拒绝入境、驱逐出境、长期拘禁。其四,恐怖分子正当诉讼权利被剥夺。布什政府不但拒绝适用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文,也排斥司法审查,甚至包括最起码的人身保护令程序,由总统一人决定所有被认定为恐怖分子之人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参见廖元豪:《多少罪恶假“国家安全”之名而行?——简介美国反恐措施对人权之侵蚀》,《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06年第4期。这些举措被评论为以反恐之名,行扩权之实。偏重于“民意”,不讲求立法原则与规律的象征性刑法,在助长权力膨胀之外,可能使公众对法律与政治界限的认识更模糊不清,钝化公众的法感情,甚至颠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法治国原则,走向“敌人刑法”。
(三)法益抽象化
在风险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便捷、科技的广泛运用与重大安全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公众以强烈心理震撼。“与风险的无所不在相伴随的,是人们对诸多影响自己生活际遇的事件的无力控制感的蔓延,风险意识加剧了公众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如何为个人提供制度上的安全保障开始支配政策的走向。”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3页。社会风险的普遍性、多层次性与多变性决定了公众“风险体感”的模糊性与抽象性。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处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刑法改变了原有的严格结果归责结构,尤其是考虑到科技发展后,实务上往往难以证明个案中的因果关联,为了弥补打击漏洞,刑法采用不需要判断结果可归责性的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即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个定型行为,刑法便直接介入予以处罚。”许恒达:《法益保护与行为刑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17年版,第16页。公众“体感风险”的抽象性与抽象危险犯的适用,直接加速了法益抽象化进程,促成了象征性刑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范围。实质上,建立在法益抽象化基础之上的抽象危险犯与象征性刑法的初衷不谋而合,前者也成为后者的最主要表现形式。立法者企图通过象征性刑法获得民意支持以巩固权力地位,抽象危险犯则是象征性刑法的主角。抽象危险犯进一步扩张了立法者的权力,“引起刑法的工具化与象征性倾向,容易成为特定群体或特定利益阶层利用经济、信息、科技能力等优势地位影响刑事立法动向从而设定特定价值观的工具。”黎宏:《结果本位刑法观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学者Tasia E.McIntyre以美国俄亥俄州立法为例,指出,俄亥俄州反恐立法规制了并不具有政治、社会与宗教等恐怖主义特定目的的普通刑事犯罪,且由于其模糊的用语及潜在的擅断与歧视,该法典出现了重大问题。遏制犯罪是刑法的众多目的之一,尽管法院一直着力提升判决质量,但俄亥俄州反恐立法却无法切实地预防恐怖主义。现行州立法典应当被重新评估以便遵从联邦反恐政策,修正过于宽泛的用语,将恐怖主义行为限于特定目的,限制追诉者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恰当地定义、处理和惩罚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Tasia E.McIntyre,PROTECTIMGAGAIMST TERRORISM OR SYMBOLIC POLITICS?:FATAL FLAWS IM OHIO’SCRIM IMAL TERRORISM STATUTE,Case Westren Reserve Law Review,[J].Fall2005.“抽象”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对“危险”概念理解的千差万别,与模糊不清、定位不明的超个人法益立法相契合,可能会扩张刑法的适用,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法益抽象化导致秩序维持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安全与秩序固然是刑法追求的重要价值,但个人自由不应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两者的动态平衡需要谨慎把握。正如庞德所指出的:“一种为了人类的目的对外在自然界和内在本性进行最大限度控制的理想,必须承认两个因素达到那种控制:一方面是自由的个人主动精神、个人的自发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是合作的、有秩序的、组织起来的活动。如果想保持对自然和本性的控制,使之前进并流传下去,那么对这二者就都不应该加以忽视。”[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8-79页。
(四)立法科学性的欠缺
在象征性刑事立法中,立法者受到民意与刑事政策的影响,倾向于仓促跨越“李斯特鸿沟”,实现刑法政策化,这样使民众认为问题已被认真对待且已妥善处置,但其只是一种应急或者安抚公众的举措。“据统计,在英国现有的近8000个罪名中,大多数罪名创制于最近150年之内。对此,菲利评论道:由于对统计学、生物学、人种学、人类学资料印象模糊,并且仍然抱着社会和政治可以人为地创造的旧偏见,今天的立法者一开始就急于成为十足的立法癖,似乎每一个新发现的社会现象都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则或一个刑法条文。这种对刑法不受原则指导的、杂乱的建构,最终引发了刑法是否是一种失败之事业的追问。”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也应警惕此种倾向,一直以来,在灾难性事件爆发后,总有增添新罪名的提议。对于频频爆出的幼儿园虐童案,有学者提议设立“虐待儿童罪”,理由是:“儿童是没有社会化的群体,依赖性非常强,也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避免虐待问题事关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论从家长的期待还是从国家的未来考虑,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都应该优于成人,实行特殊人群特殊保护。法律最大的功能不是打击,而是震慑,就是要让施暴者意识到实施暴力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是一种重罪。”朱琳:《虐童案数量呈上升趋势是否增设“虐待儿童罪”存争议》,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11/14/c_1121950187.htm,2017年11月29日访问。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立的“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是否已无法应对这一局面,是否已无法满足民众的正义观念及朴素的法感情。在现行刑法尚可利用的情况下,为了迎合民众而随意改动刑法,会影响刑法的稳定性、体系性与严肃性。事实上,随着实证法学的兴起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越发需要摆脱象征性立法的阴影,应在对社会形势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基于对各类数据予以分析研判,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并在施行中时刻保持法律的活力。不计实效的重复性立法仅仅是非理性民意的凝结,破坏了现有的法律体系,违反了谦抑性原则,损害了立法的科学精神。
立法科学性的欠缺并不仅仅缘于象征性刑法的非理性民意,更在于立法目的模糊。立法目的是刑事立法的向导,也是立法科学性的重要指征,目的不明会导致刑事立法的失败。“在立法前,立法者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对一个社会内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从中拣选出需要由刑法加以禁止的行为,并设立相应的刑法规范。”赵秉志:《刑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以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为例,由于汽车时代所带来的交通事故频发,对于一些情节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公众反映强烈。于是,从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了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且经过公安部、国务院法制办等多部门研究讨论,才最终决定增设危险驾驶罪。经过对全国交通恶性案件的详细分析与慎重研究,立法机关认为我国醉驾行为高发、多发,有治理必要,而行政治理力度有限,惩治醉驾的刑法规范也存在明显缺陷,完善刑事立法有助于应对这一局面,有助于提升民众规范意识,保护民众人身财产安全。事实证明,该项立法成效显著,实现了预期的立法目的。相比之下,象征性刑法中立法目的的模糊降低了立法科学性。在进行象征性刑法立法时,立法者或许已经意识到,就算动用刑法威吓手段也难以阻止犯罪发生,不过,至少通过一种较不费力的方式来承受社会舆论压力,顺势强化社会大众关于法不可侵害性的信赖与忠诚。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72页。这是一种以刑事立法转嫁社会压力的做法。
(五)刑法泛化
象征性刑法是立法者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更是加强社会控制的手段。“当代的刑法体系在坚守个人的可谴责性作为责任条件之要求的同时,又将一套兼具谴责与惩罚的体系制度化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即实现刑法体系的多重预防目的。权利仍然构成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点,但在整个法律体系向功能性转变的大背景下,挣扎在‘权利’与‘控制’之间的现代法律,注定要屈从于后一种叙述结构。”劳东燕:《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刑法控制力的增强,源于对刑法机能及安抚功能的迷信,不顾行政法、民事法的作用,动用“最后一道防线”提前介入社会争端,短期内会取得平复民众情绪、解决争端的效果。然而,无论民众还是立法者,均会加深对刑法的过度依赖,一旦遇到轰动性事件如造成恶劣影响的见危不救案件、虐童案件、骗婚案件等,民众的感性情绪便会迸发出来。随着类似案件的频发,立法机关也形成了刑法依赖、重刑依赖,倾向于通过象征性立法解决问题,刑法也被视为一种危机处理的手段。长此以往,民众形成了直线、浅层思维,不去从发散、深层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而是反射性地归咎于刑法的缺陷与打击不力。这反映出我国民众理性认识的欠缺,对于国家权力缺乏必要的警惕,没有认识到权力本身的扩张属性。刑法泛滥并不会解决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反而是在掩盖问题,回避关键矛盾,造成公民思维简单化及公民自由范围的逐渐缩小。从实质上讲,刑法泛化现象违背了刑法最小化原则,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刑法虽是为了保护法益而动用的,但保护法益的手段并非只有动用刑罚。能避免的话就应该尽量加以避免。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一个成熟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不应该一切冲突都通过刑事强制手段来解决。在社会转型期,很多犯罪问题是多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运用其他社会控制机制可能比刑法手段更经济有效。随意动用刑法手段代价巨大,且极易阻碍良性解决渠道的生成,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象征性刑法的认定
象征性刑法有着上述弊端,需要批判、警惕与规避。对象征性刑法的认定是展开相关批判的基础,厘清其内涵与外延,有助于人们找准“靶心”,进而开展我国语境下的象征性刑法研究。目前大多数象征性刑法的研究仅局限于对象征性刑法的批判,但并未研究究竟何为象征性刑法。在科学认定象征性刑法的基础上展开批判,进而提出合理规避措施,才能体现其研究价值。
(一)实效性并非认定象征性刑法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象征性立法应当被否定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欠缺实际效果,即“如果使用刑罚来处罚某种行为仍无法达到抑制该行为的目的,那么刑罚法规的设置就不应当被允许”。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在逻辑上,“欠缺实际效果”并不等同于“实际效果考虑的欠缺”。象征性刑法概念的提出,旨在批判刑法沦为政治的工具,即将刑法作为首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在象征性立法中顺势获取绝对的刑事制裁发动基础,甚至对任何一个造成当代社会生存恐惧的行为动辄以刑事制裁对抗之,以期实现毫无恐惧的生存确保。从表面来看,象征性刑法貌似等同于政策性立法或情绪立法,但从深层次来看,象征性刑法概念着力从主观方面对立法举动进行剖析,以批判立法实效性考虑的欠缺论证象征性立法过程本身的不合理性,倾向于立法行为无价值评价。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实效性欠缺问题,不一定是由象征性立法造成的,象征性立法可能被证明为失败,也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虽然象征性立法被批评为法规范的无效率,但仍有可能对社会运作及个人行为发挥规范效果。就算是理性建构的法律也不见得就能有效率地解决社会冲突,但人们也不会因此就将其称之为象征性立法。相反地,部分被视为象征性立法的法律,却有可能非常迅速地影响社会大众的行为取向。所谓的法律有无效率有必要区分为“规范及事实上的效率”及“象征及政治上的效率”,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象征性立法。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119-120页。因此,象征及政治层面的实效与规范及事实的实效并无直接关联,具备象征及政治层面实效的立法,不一定欠缺规范及事实层面的实效。规范与事实层面实效的欠缺,只是特定情况下象征性刑法所带来的副产品,普通的刑事立法也有可能成效不大。如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罪以来收效甚微,网络时代中信息传输的便利导致此类犯罪愈演愈烈。据统计,“目前我国网络非法从业人员已超150万人,已形成一条信息需求、盗取、交易等完整的黑产链条。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近一年时间国内6.88亿网民因垃圾短信、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经济损失约915亿元。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仅2017年,360手机卫士为用户标记各类骚扰电话约2.42亿个,拦截骚扰电话380.9亿次。”康斯坦丁:《个人信息泄露在如今到底有多严重?》,http://www.sohu.com/a/230559694_115224,2018年5月15日访问。刑事手段成效不大的原因并不在于该罪名为象征性立法,而主要在于:第一,网络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犯罪打击提出了巨大挑战,犯罪行为的复杂性、技术性与隐蔽性,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避了打击;第二,非刑事法律的不完善,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我国尚未确立统一完备的行刑衔接体系,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未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缺乏配套的非刑事法律,犯罪认定与刑法适用也会遇到相当的阻碍;第三,刑法规定不完善,如“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等概念争议较多,该罪与其他罪名如诽谤罪、诈骗罪的界限不明,可公开个人信息与不可公开个人信息区分标准不明确,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无法合理协调等。参见胡江:《互联网时代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故与其称之为象征性刑法,不如称之为尚待完善的刑法。
针对德国环境刑法的出台,有学者认为其是典型的象征性刑法,并批评道:德国立法者相信环境刑法的实效性取决于司法实务能够更有效地适用刑法规定,以及将法律适用结果传达给社会大众周知等条件。然而,存在疑问的是,刑法是否真能强化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并降低环境污染的发生率。司法实务上,对于环境污染往往有相当数量的刑事追诉,但最终有罪判决作出甚少,原因可能是行为轻微,或是欠缺环境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最有可能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企业活动,明显少见于环境犯罪的统计资料。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125页。对于我国恐怖犯罪立法,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象征性刑法,主要理由在于:恐怖犯罪立法虽然活跃,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反恐姿态,但实质效果欠佳。恐怖犯罪的九个罪名在实践中司法适用率极低,实际效果有限。另外,各国打击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这些表明了刑事法治手段反恐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参见前注,刘艳红文。
这种以判决率和适用率作为象征性刑法标准的观点值得商榷。对于德国环境刑法而言,德国立法机关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将原本分散的附属规定统合为刑法典的“环境犯罪”一章,并针对原有的内容进行修正或补充。这种立法并不仅仅是对环境污染的应激性反应,而是后工业时代应对环境污染在刑法上的合理反映,也是几乎每个工业国刑法对风险社会的适应方式之一。西方国家由于之前的法律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民事赔偿或罚款的方式,而“多数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仅把赔偿或罚款当成经营管理上的成本和代价,并想办法转嫁给消费者”。吕欣:《环境刑法之立法反思与完善》,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刑法的应对日渐力不从心,纵然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尚存争议,人们对传统刑法概念的坚持亦根深蒂固,但环境法益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代际公平的接受度不断升高,于是环境刑事立法大量出现。正如贝克教授所言:“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薛晓源:《前沿问题前沿思考: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追踪与探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此外,与其他犯罪不同,巨大利益的诱惑、调查取证及因果关系判定的困难、环境污染的常年累积等因素,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一时很难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环境污染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需要统筹规划、多管齐下,而刑法本身具有其局限性,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非易事。因此,环境犯罪惩治的长期性、艰巨性并不等同于环境刑法欠缺实效性,更不等同于立法者在环境刑法的制定过程中欠缺实效性的考虑。对于我国恐怖犯罪立法而言,亦不能以适用率较低为由否认其立法必要性与科学性。一方面,在恐怖犯罪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虽然“行政法上的处罚、民法上的赔偿以及军事打击手段也具有积极效果,但要持续地、稳定地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凭借刑法的严厉制裁特性,这是由民事措施、行政措施的弱制裁性以及军事打击手段的非常态性所决定的。反恐刑法有效弥补了其他法律调整方式的局限性,具有必要性”。杜邈:《反恐刑法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当前反恐立法虽进展迅猛,但仍存在不少漏洞,这是其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反恐立法较为杂乱,欠缺体系性。恐怖犯罪特点突出,与其他犯罪有着鲜明区别,当刑法将其与普通犯罪糅合在一起规定,且相当一部分恐怖犯罪被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炸罪等罪名追责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反恐罪名适用率低的假象。其二,相关概念模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恐怖活动”“宣扬”“煽动”等概念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导致过度入罪与过度出罪状况并存。其三,新型恐怖犯罪缺乏刑法规制。如“毒恐合流”犯罪、网络恐怖犯罪,以及非法邮寄危险物质的行为、入境发展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行为、引诱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接受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等。反恐立法对于上述恐怖活动规制的阙如,造成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普通犯罪予以打击以及恐怖犯罪立法适用率低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恐怖犯罪立法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充分尊重了立法规律,最大可能地实现了立法科学化。我国的反恐立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民意应对之举,而是紧密结合反恐形势,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发展过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一次规定了“恐怖行为罪”,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规定了“恐怖活动罪”,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紧接着,《刑法修正案(三)》及《刑法修正案(九)》又大量补充规定了反恐罪名。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立足国情和反恐局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步推进反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查阅了大量国外立法资料,借鉴吸收了先进立法方式与理念,相关草案经历了三次审议稿,在审议和征求意见过程中,立法机关根据各方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补充完善。“虽然当前反恐立法尚不完善,但这主要是因为恐怖主义还处在发展变化中,只能把较为成熟的认识,以及迫切需要规定的先规定下来,而不强求完备和应有尽有,以免刑法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赵秉志、杜邈:《中国反恐法治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二)象征性刑法的核心特质
象征性刑法的根本标准可以将其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象征性刑法包含了诸多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描绘出象征性刑法的轮廓。纵观国外对于象征性刑法的描述,可以归纳出的结论为,象征性刑法是立法机关为了迎合民众、巩固权力而进行一系列增强民众安全感的立法,其根本特质在于象征性。刘艳红教授也认为,象征性刑法最大的特征在于“立法是一种对犯罪施以威胁的姿态或情绪”。同前注,刘艳红文。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只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象征性刑法描述,这种描述无法区分象征性刑法与其他概念如情绪立法与积极立法,后两者亦包含刑法的象征性,也是对民众立法需求的积极回应,所以这些概念在表面上看起来极其相似。象征性刑法理论提出的根本动因在于对立法机关不负责任立法、滥用立法权以及随意扩张权力的批判,应运用宏观视角,从动态层面对立法全程展开研究,发掘象征性刑法的核心特质。这种核心特质可以作为判断是否为象征性刑法的标准。
“在正常的犯罪化过程中,被规定为犯罪的,应该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中有必要通过刑罚制裁来强调国民遵守的,上升为刑法规范的社会伦理规范的那一部分。”[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某一行为的危害总量随着社会的变迁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被刑法所规制,故社会危害性是犯罪化的基础,也是刑事立法的原动力。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新的矛盾与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但对于尚未危及基础性社会关系的行为,要谨慎把握其社会危害性的度。如有些行为虽然一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危害性会逐渐弱化。有些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尚未达到质变或存在非刑事规制手段时,不足以被视为犯罪。立法机关若误判形势,将上述行为盲目入罪,虽然暂时回应了民意,但实质上与真实民意相悖,不具有普遍的公众认同基础。“当刑法不坚持自己的专业性而判定一个没有明显危害的行为为犯罪时,如果人们后来发现这种行为没有导致他们通常认为确实是犯罪的后果,法律就会失去其信誉。”[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分配原则》,沙丽金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3页。在某一行为被合理地认定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启动刑事立法程序后,立法科学性也应被充分重视。立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力,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与世俗色彩,极易使立法成为政治与世俗的附庸。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科学精神的提倡以及立法技术的锻造为当务之急。刑事立法包含两类技术:一是刑法制定活动的运筹技术,即在刑法制定过程中如何安排、调度、筹划和控制有关事项的方法和操作技巧;二是刑法制定的衡量技术,即在刑法制定过程中,听证、论证、起草、颁行文本皆需借助科学指标体系的衡量;其科学指标体系的建立则需要综合利用医疗学、病理学、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参见张训:《刑法科学化进程中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运筹技术是衡量技术的保障,衡量技术是实现刑事立法科学化的关键一步。这两类技术的充分运用需要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与巨大的投入,是象征性刑法所不具备的。
在社会危害性层面,为了政治性目的,象征性刑法大多将缺乏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学者Amitai Aviram指出,为了展示效率以及提升自己连任的几率,政治家们需要去处理关乎选民的风险,但由于人类的恐慌天性,很多风险是被高估的。当公众高估了某个风险,就会导致消耗资源去降低风险带来的过大政治压力,安抚民众的象征性立法则将这种政治压力降低到了更有成效的水平。象征性立法实为吸引公众注意及便利立法者削减社会福利的烟雾弹,这种立法过于频繁地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去处理社会问题,这反映出立法政策制定机制的崩溃。Amitai Aviram,THEPLACEBO EFFCT OF LAW:LAW’SROLE IMMAMIPULATIMGPERCEPTIOMS,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Movember2006.在立法技术层面,象征性刑法的制定者并不在意立法能否有效影响社会现实,而是出于急切满足非理性民意的初衷,在时间及成本投入上,均秉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因此,立法前的调研与筹划,立法过程中的论证与审读以及立法后的检验与修正等工作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虽然立法者宣称解决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但立法科学化原则被抛弃,这是其立法动机与目的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这里的立法者并不单纯指某种形式意义上的国会或立法成员,而泛指具有影响立法能力的政治力量。作为政治性凝结的象征,立法并不需要被检验是否有能力达到其宣称的目的。单纯通过一部法律可以使焦虑的民众感觉更好,因为“已采取措施”。紧接着,政治利益、连选连任将从被抚慰的选民那里返回立法者手中。这种立法是“夺人眼球的”,但无法应对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即使没有实现可能,但仍承诺解决问题或改善状况的立法。Brian T.FitzPatrick,COMGREEIOMALRE-ELECTIOM THROUGH SYMBOLICPOLITICS:THEEMHAMCED BAMKIMGCRIMEPEMALTIES,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Fall1994.为了准确识别并警惕象征性刑法,应尝试从社会危害性及立法技术层面探索象征性刑法的标准。总体上,象征性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立法环节,判定象征性刑法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具有的政治动机影响下立法实效考虑的忽略。
(三)我国不存在象征性刑法
有学者认为,我国存在着象征性刑法,除恐怖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等类罪外,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具体罪名也属于象征性刑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罪名只具有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参见前注,刘艳红文。还有学者认为不可滥用象征性立法这一批判工具,不可将外国学者对于象征性立法的批判简单地拿来批判我国的立法。只有立法仅具有象征性而欠缺实效性的,才能被归类为象征性立法。我国的象征性立法并非恐怖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而主要存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领域,如虚假广告罪。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上述两种观点均将判定象征性刑法的标准简单化为“象征性+实效性的欠缺”,如前所述,刑法固有的象征性与象征性刑法截然不同,实效性也并非判定象征性刑法的标准。近年来通过的一系列刑法修正案反映出我国正处于适度犯罪化阶段,虽存在情绪立法情形,但积极立法观仍为主导。情绪立法、积极立法与象征性立法较为相似,如均有风险社会背景、扩大了犯罪圈、受民意影响等特征,这使得一些学者极易将情绪立法、积极立法视为象征性立法。其实,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积极立法与象征性立法的区分
传统刑法观中,个人化的、物质性的、静态的法益范畴无法涵盖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新权益类型。传统刑法观还强调现实的物质性侵害结果,但环境污染、核辐射以及转基因等可能引发的危害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导致危害无法认定。参见前注,劳东燕书,第12页。积极立法观旨在克服传统刑法观的缺陷,一方面,顺应社会发展增设了大量新罪,另一方面,广泛运用抽象危险犯,实现了处罚早期化。“从法社会学角度,刑法是被包含于社会大系统的亚系统,社会大系统是刑法的外在构成要素。刑法内部的构造性要素虽然是独立的按照刑法运行法则运行,但刑法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外部社会系统参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刑法要素的变化甚至刑法的演化。”姜敏:《刑法修正案犯罪化及限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积极立法观“立足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考量,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单纯理性化的构想,追求发挥刑事立法的社会功能,注重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因此,积极立法观逐渐为各国所采纳。如德国自1975年以来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方面是经由新犯罪化和刑罚严厉化而进行的刑法扩张,另一方面是通过去除明确和有约束力的规则而出现的刑法灵活化。参见前注③,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书,第35页。我国也有类似趋势,近年来,由于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对刑法提出了挑战。为了防止出现法律真空,我国通过十个刑法修正案增设了众多新罪名,还将原有罪名的触角延伸至预备阶段。从重视法益实害转向重视法益的抽象危险,从注重保护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法益转向重视公共法益和社会秩序,刑法规制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与强度均大幅提升。参见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这种情形下的我国刑法立法是典型的积极立法。
积极立法与象征性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立法动因、立法目的与立法过程。第一,积极立法的动因源自时代发展与变迁,尤其是风险社会的到来,严重削弱了传统刑法功能的发挥。象征性立法的动因在于民意或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更容易引发公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第二,积极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强法律的灵活性与时代性,充分发挥法律功能,防止出现法律真空,有效地保障社会生存。象征性立法的目的并非实现法律进步,而在于带给民众安全感,进而获得政治利益。虽然象征性立法表面上宣称其规范及安全保障目的,但其无意去影响社会现实,背后的真正考量是各种政治、经济等利益。第三,在积极立法观指导下,虽然通过了诸多立法,但每部立法都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调研与公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入罪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研讨,民主性与科学性较强。例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制定过程中,早在2009年下半年,为拟定《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着手对当前刑事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反复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门进行研究,多次听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某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参见袁彬:《刑法中的情绪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页。这些流程保证了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之上的立法,也会客观冷静看待民意,如毒驾问题。虽然毒驾案件逐年增多,群众呼声较为强烈,但由于毒驾认定标准尚不明确,针对毒驾行为的检测技术手段受到限制等,立法机关仍保持了克制。参见喻海松:《刑法的扩张——〈刑法修正案(九)〉及新近刑法立法解释司法适用解读》,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在象征性立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不会明确表示其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何,也不会选择最合乎立法理性的规范手段,只要社会就特定事件表现越来越高涨的情绪能量,立法者就越有可能刻意忽略法规范应有的目的设定与比例性要求,依此制定的法律势必沦为纯粹的技术性规范,不再是基于立法之目的理性的规范。参见前注①,古承宗书,第120页。例如,日本奈良县以杀害女童事件为契机,仓促制定了《保护儿童免受犯罪侵害的条例》(2005年),其第12条、第15条规定,对儿童实施“找茬恐吓”“阻挡去路或者纠缠”行为的,构成犯罪。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找茬”“恐吓”“纠缠”等非规范概念的模糊不定,降低了该条例的科学性与可适用性。
2.我国存在情绪立法
“情绪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在刑事法律修正过程中,因受一定规模的情绪化民意或舆论的影响,而非理性、妥协性地增设、修改或删除刑事法律条文的行为。”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情绪立法的推动力主要为非理性民意,每当重大社会问题暴露出来时,总会出现动用刑法的呼声。从“醉驾”到“恶意欠薪”,从“袭警”到“医闹”,从“虐待幼童”到“精日”,莫不如此。这些舆论呼声更多地属于非理性民意或误导性言论,舆论的复杂性、多变性、易操纵性决定了若欠缺去伪存真的分辨过程,很容易沦为非理性民意,进而对立法带来极大损害。非理性民意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社会层面,转型期众多的违法违规行为与规范性解决渠道的错位与缺位,给人们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这些问题通常较为典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释放的途径,提升了民众社会治理参与感。在文化层面,自古以来的重刑意识及重刑轻民传统,使“刑法工具主义”一直存在。我国普通民众很少会将自己假设为一名罪犯,以致设想自己在触及法网时可能会遭到何种惩罚,因而总会认为刑法更多的是为他人而设的。
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以及立法的不成熟也是情绪立法出现的重要原因。我国各项事业正处于由混乱向规制、由无序向有序的进程中,民众心理也经历了由失范到规范的蜕变,人们对规范、有序、高效的渴求胜过以往任何时代。多发的“失范性事件”及尚不完善的刑法唤醒了民众潜意识中的重刑传统,人们由此将理想图景的实现寄托于刑法完善。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适应时代发展,立法机关有必要认真听取民众的呼声,获取社会意见。正如梅因指出:“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立法机关如何看待并回应所谓的“民意”,直接决定了该项立法的质量,也体现了立法的成熟度。立法者较容易受到民众情绪感染,在未准确甄别真实民意的基础上对“民意”回应过度,渴盼制定出与时俱进且有效调控社会生活的刑法。这样的后果便是刑法立法的科学性、稳定性、谦抑性受损,民众的重刑思维仍得以延续。
情绪立法的主要后果为立法资源的浪费以及立法效果的空泛,在我国,袭警从重处罚条款的增设即为典型的情绪立法。鉴于袭警案件多发,社会上要求加强警察执业保障,设立袭警罪的呼声此起彼伏。一些人大代表及公安部门的同志也提出在刑法中单独规定袭警罪。立法机关一方面认为妨害公务罪能够涵盖袭警行为,另一方面却在妨害公务罪的条文中增设第5款,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从重处罚。虽然没有单独设立袭警罪,此项立法仍是在所谓民意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与让步,情绪色彩鲜明。在司法实务中,袭警情节本就是妨害公务罪量刑的加重因素。如有学者对98例袭警类妨害公务案件作了统计,被判处有期徒刑监禁刑的人数占所有人数的73.02%,被判处拘役的人数占所有人数的25.4%,另有2人分别被免于刑事处罚和判处罚金刑,无人被判处管制。参见段重合:《妨害公务罪量刑情节适用实证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1页。可见,在妨害公务罪四类刑罚中,袭警类妨害公务案件更倾向于判处有期徒刑与拘役,且绝大部分为实刑,相对较重。另外,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暴力袭警行为增加基准刑的10%至30%。这样,已完全可以满足从严从重惩处的目的,基本刑法条文的修改根本没有必要。因此,袭警立法动用珍贵的立法资源去宣示警察执法的不可侵犯性,实现刑法的象征性这一空泛目标,就破坏了刑法本有的稳定性与严肃性,是令人遗憾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立法成本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立法者按照立法程序调研、开会、表决这些形式上的时间和物质成本,刑法被修改就是修改本身最严重的后果。如果刑法可以随意更改,立法者的决策可以轻易推翻,那么社情民意将导致刑法变动不居。参见李翔:《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此外,出于对其他执法机关工作人员一体保护的考虑,袭警重刑并非恰当。其他执法人员如法官、检察官、工商管理、税收管理、城管等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也容易遭遇暴力抗拒甚至被袭击。相比之下,警察的自我防护手段、执法装备保障、对暴力抗法或袭警人的追究能力显然更强。当前袭警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追究袭警人员法律责任的意识不足,有的警察处置能力不足,对警察严格执法的支持力度不足等。参见臧铁伟、李寿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袭警问题的综合应对远比简单的立法宣示重要得多。
与“袭警”相比,“医闹”情节入刑则沦为了更加纯粹的情绪立法。从字面意义及逻辑上,“医疗”完全可以被“工作”“科研”等包含,之所以增加“医疗”二字,主要在于医患矛盾尖锐,存在较多的以医患矛盾为由故意扰乱医疗秩序和侵害医护人员的案例。立法机关为了回应民意,在“工作”“科研”之后增设了“医疗”这样一个明确法律适用的规定。其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4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已强调严惩涉医违法犯罪,对于扰乱公共秩序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可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处罚。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医疗秩序也完全可以被社会秩序涵摄。故司法机关只须按照《意见》的精神惩治“医闹”即可,无需利用宝贵的立法资源完成一项仅具宣示性而无实际功能的任务。或许有人认为,该项立法是刑法的象征性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及医护人员的关爱与重视,强化了公众的规范认知与正义直觉。然而,象征性规定通常为刑法总则条款,主要通过诉诸于感官的具体文字表达抽象的精神意蕴,具有宣示性、引导性与全局性。旨在帮助公众形成刑法印象,理解刑法精神与价值,促进规范的认同。“医闹”条款既非总则条款,亦不具有全局性,民众无法从中领悟刑法的精神。该条款虽具有宣示意义,却不具有象征意义。
3.情绪立法与象征性立法的区分
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立法权是人民意志的有效运用。在立法过程中,人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立法,就法律创制、修改或废除提出意见,与立法机关沟通。因此,立法机关与民意的互动也理所当然。同时,“立法权行使的本质是国家以法定程序和方式分配、协调和确认社会各种利益及冲突的过程,任何立法权都不可能在‘利益真空’中运行,立法结果就是利益分配与均衡的结果。”何荣功:《自由秩序与自由刑法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不恰当的立法参与或非理性民意通常扭曲了利益分配与均衡,掩盖了民众的实质需求,在特定的立法背景下形成情绪立法或象征性立法。因此,情绪立法与象征性立法都以“民意”为引导,不同程度地偏离了立法科学化的轨道,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
由于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情绪立法,且立法效果差强人意,很多学者易将其当成象征性立法予以批判,但两者在立法目的与立法过程层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立法目的层面,情绪性立法的目的虽然包含迎合“民意”的成分,但立法者从民众的呼声以及与域外法治的比较中看到了现行法的缺陷与不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立法机关在面临种种现实困难的同时,也易被民众高昂的情绪所感染与误导。卡多佐指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我们总是面临这一巨大悖论。法律如同人类,要活下去,必须寻觅某些妥协的途径。这两个将法律引向不同方向的趋势应当拧在一起,使其步调一致。这两种趋势的融合,必须依靠某种智慧。”[美]本杰明·M·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在情绪性立法中,非理性民意是动因,真正的立法目的是立法机关在“民意”压力下,对法律落后现状的反思,对法治进步的渴望,甚至是对完善法治一蹴而就的幻想。象征性立法的目的则是在平息民众焦虑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政治利益,立法者并没有将立法进步视为立法工作的应有之义,而是以价值衡量与选择取而代之。学者Willard M.Oliver在梳理1953年至2001年间美国总统发布的总统令后,认为,总统为了象征性的目的,依赖行政命令去应对犯罪,总统们利用犯罪事项作为象征性的功能或姿态去争取民意以及安抚公众的情感。虽然只有53.5%的犯罪相关的行政命令被用于象征性目的,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总统任期惯例的一部分。WILLARD M.OLIVER,EXECTIVEORDERS:Symbolic politics,Criminal Justice Policy,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AMERICAM JOURMAL OFCRIM IMAL JUSTICE.Vol.26 Mo.1,2001.在立法过程层面,情绪立法的立法者虽然有意斟酌并力求立法的科学性,但风险社会的背景以及铺天盖地的“民意”使具有人民属性的立法机关压力重重,进而冲动立法,暴露出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作为人民主权国家,我国的立法民主化一直被有力推进,过去的立法民主化主要体现在立法机关人员产生方式的民主性与代表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让民众直接参与立法,就立法表达自身诉求,更能够让他们建立“主权在民”的心理定势。当然,在立法民主化的机制建设方面,我国目前还处于追赶阶段,参见同前注,李怀胜书,第54页。偏离最初定位的立法民主化反而对立法造成极大损害,若单纯为了应对各种风险而依赖刑法暴力产生并维持秩序,那么立法民主化将沦为“多数人的暴政”,刑法有沦为“敌人刑法”的危险。象征性立法的立法过程虽然遵守既定的立法规则与流程,但更像是一种姿态或仪式,立法机关在所谓民意的牵引下完成了政治利益的权衡、妥协与交换,在实质内容上欠缺立法规范化与实效性考虑。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科学是受到政治支配的,立法者可以并且经常不理睬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逻辑和经验常常成为权力、偏见和贪欲的牺牲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转引自何秉松:《政治对犯罪理论的影响》,《河北法学》2005年第12期。
四、象征性刑法的避免
虽然我国并没有出现象征性刑法,但这种立法态度和方式危害极大,若缺乏警惕并不予积极规避,将不利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刑法。通过梳理与总结避免象征性刑法的方法与路径,也有助于杜绝情绪立法的再度发生。
(一)理性对待民意与舆情
象征性刑法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对民众模糊抽象的寻求安全感心理的无条件满足,正是这种即时的无条件迎合使刑法面临着民粹主义的危险。传统上,精英主义的立法观一直占据着支配性地位,鉴于各类精英在学识、能力、素质与远见等方面超出常人,故这种立法模式一般被人们视为达致法律科学性的必由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刑罚民粹主义在西方出现并迅速发展,刑罚民粹主义表达了对人民的热爱与崇拜,宣称:“现在的刑事司法制度过于偏爱犯罪和囚犯,却牺牲了特定案件中的犯罪被害人和一般守法公众的法感情,它反映了犯罪被害人及其代言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觉醒力量,并从公众对现在的刑事司法体系感到愤怒和不抱幻想的情绪中吸取力量。刑罚民粹主义导致刑事政策的目的只在于在选举中获胜而不是降低犯罪率或者促进公正。”同前注,李怀胜书,第117-118页。刑罚民粹主义的典型为美国的“三振出局法案”与“梅根法案”,这两部法案虽在短时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均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阻碍了犯罪人再度融入社会的努力,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可见,象征性刑法与刑罚民粹主义实质相同,若放任刑事立法中的民粹主义泛滥,刑法难免会被民意所“绑架”,而民意绝非民主,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国民。若要妥善处理刑事立法与民意的关系,需从两方面的疏导入手。第一,在“疏”的层面,刑事立法在抽象层面应紧跟时代发展,仔细倾听民意,但在具体层面不可以以民意为由冲动立法,而应保证立法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与西方国家非犯罪化趋势相反,我国刑法犯罪化进程仍应继续进行,我国刑法总体仍保持着“厉而不严”的风格和“小而重”的体态,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诸多值得由刑法保护的法益仍处在随时被侵犯的危险境地,若视而不见,则导致刑法作用的矮化,不利于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也不利于强化国民的规范意识。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山西“黑砖窑”案,河南天价过路费案,还是上海携程幼儿园虐童案,都反映了民众要求发挥刑法机能,严惩反社会行为的强烈呼声,立法机关应在仔细甄别真实民意的基础上给予充分的尊重。然而在具体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不可被“民意”左右,应充分评估现行刑法体系的有效性、科学性,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做出客观理智的决定。必要时可举行专家论证会或开展重大课题调研,充分发挥法学专家等精英群体在立法中的积极作用,警惕立法民粹化。第二,在“导”的层面,刑事立法应有制度化的民意通道,立法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保障立法民主。民意宜疏不宜堵,非理性民意形成的原因大多在于正常沟通渠道的不畅,立法机关除了保持清醒外,还要给予民众更多参与立法的机会,要构建常态化的立法参与机制,让民众平日能够充分、理性发声,而不是在突发性事件之后进行非理性情绪宣泄。为此,在立法准备阶段,可举办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听取民众意见,也可在网上举行全民大讨论。立法听证会是一项具有实效的措施,我国《立法法》也确认了这一制度。美国学者基夫和奥古尔认为,立法听证会的主要功能有四项:了解事实;听取各方面意见;宣传法案及其可能的结果;把人民的意愿告知立法者。W illiam J.Keefe,Morris S.Ogul,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Process,Prentice-Hall,Inc.1985,p.207.转引自汪全胜:《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在法律制定阶段,可以将法律草案向全民公布,听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正式立法的参考。2016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公布《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告知民众可通过网站、信函、电邮等方式提出意见,在全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法学界人士针对该草案提出了众多意见和建议,也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保证了日后正式出台的我国《社区矫正法》的科学性、民主性。
(二)立法必要性的研判
1.对前置法规制效果的考察
刑法作为保障法,只有当其他法律部门对某行为的调整与制裁措施均无效的情况下,才能由刑法出面调整和保护。对于动辄提议动用刑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呼声,立法者在保持足够的清醒与中立之外,还要强化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认知,即穷尽一切手段均无法解决问题时才考虑刑法的介入。梁根林教授将民事法与行政法视为犯罪化的第一次制约,认为犯罪首先是对民商法、经济法及行政法的违反,如果行为对民商法、经济法及行政法的违反没有造成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国家只需通过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手段进行第一次调控,只有那些民事制裁、行政制裁无效的严重违法行为,才需要刑法进行第二次干预。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因此,对行政法、民事法等前置法规制效果的考察则是判断刑法干预是否必要的前提和事实基础,为此需要对行政法、民事法立法成本与效益展开评估。立法成本与效益评估的基本原理是对法案所需的社会成本(直接与间接)与可得到的收益用货币来计量,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上来计算利益得失。立法的直接成本包括调研成本、立法程序成本、立法监督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立法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收益与环境收益。立法收益与立法成本的差额就是立法效益,较为通行的立法效益测量方法为前后对比评估法,即将两个时段的情境进行比较,一种是方案实施前的情景,一种是方案实施后的情境,通过简单前后对比分析等方式,得出最终的立法效益。参见汪全胜:《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219页。通过立法成本与效益评估,能够保障法律资源配置的正当性,有助于衡量法律规制的绩效,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与透明度。
2.对犯罪化标准的把握
1997年我国《刑法》实施以来,虽然废除了一些零星罪名,但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行犯罪化,迄今已通过十个刑法修正案。象征性刑法虽然也是犯罪化,但与正常立法程序相比,其规范层面的缺陷在于没有准确把握犯罪化标准。犯罪概念是犯罪化的根据,即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惩罚性的行为,夏勇教授认为,“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产生了刑事违法性,犯罪本质特征不是单一的社会危害性,而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并与应受惩罚性相对立统一的矛盾结构。其中应受惩罚性包括了成本因素、预防因素、权利因素、责任因素、公平因素、手段因素、人道因素。”夏勇:《和谐社会目标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标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这些因素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相互作用,犯罪圈最终得以形成。其具体可描述为,社会危害性倾向于扩大犯罪圈,同时,对应受惩罚性各因素的考量,可以对社会危害性的扩张趋势形成反作用力,限制犯罪圈无限扩展,在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科学合理的犯罪圈得以形成。然而,象征性刑法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应受惩罚性的各种因素,民众及立法者只看到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一面,片面地认为应加强刑法规制社会的功能,在非理性的鼓动下,仓促动用刑法手段应对突发事件,造成了刑法的泛化。
(三)客观认识刑法功能
在风险社会,人们对刑法充满了期望,在目睹杀人、抢劫、贪污、受贿等现象后,总是期望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一旦刑法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如刑法缺位或刑罚较轻,便会对刑法感到失望,然而,刑法的机能主要不是预防犯罪与打击犯罪,而是证明实在法规范整体的有效性。参见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面对突发事件及修正刑法的呼吁,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现行刑法是否面对此种情形无可奈何以及现行刑法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只有在即使穷尽刑法解释方法,仍无法证明实在法规范整体的有效性,无法维持刑法的规范效力及民众的基本安全时,才能考虑修改刑法。象征性刑法则没有充分考虑现行刑法的实效性与合理性,对刑法实效性与合理性的评估应建立在理性、客观地认识刑法功能与价值的基础之上。象征性刑法迷信刑法万能,带有刑法国家主义倾向,着重保护国家、集体等普遍性、抽象性法益,为了惩治犯罪不惜限制个人自由。然而,现代社会的国家早已不是无所不能的“利维坦”,而是一个以个人权利为依归的“弱者”。参见前注,张训书,第138页。社会共同体将凝聚公意的刑法规范托付给国家实施,国家以“受人之托”的心态通过渐进缓和的方式适用刑法,力图避免侵犯到每一个托付者。庞德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化和系统化,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所以,现代社会中刑法的功能应当被理解为以权利保障为核心,而不是一味地镇压与惩治,理念的滞后使得象征性刑法与现代刑法潮流格格不入。何荣功教授提出的“法治刑法功能观”不啻为避免象征性刑法的一剂良药,“法治刑法功能观”强调刑法存在范围和刑罚处罚的正当性,正视刑法适用范围和社会作用有限的事实,警惕过分强调刑法适用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等。总之,客观认识刑法的功能十分必要,刑法不同于会带来社会福利的社会管理法,更不同于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刑法的适用伴随着限制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是对法益的二次侵害,因此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参见前注,何荣功书,第150-153页。正因为刑法具有权利保障的核心功能,人们不能单纯依靠刑法实现社会治理,也正因为刑法最后手段性的定位以及应用不当的危险,人们不能轻易动用刑法,一旦深刻认识到这两点,象征性刑法出现的可能性也许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