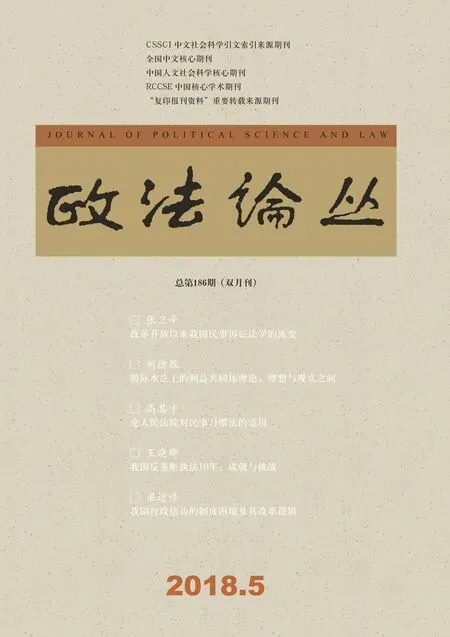跨国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全球法律框架下的原则和基石
[荷]汉斯·范鲁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荷兰 海牙)
王祥修 赵永鹏 译 陈振云 校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上海 201701)
一、引言
1.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编制的出版物《我们共同的未来》①首次将环境问题坚定地列入政治议程。该报告引入了“可持续发展”一词,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前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②报告强调,经济和生态在本地、地区、国家和全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警告称,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③它为一系列全球倡议奠定了基础,从1992年地球峰会开始,该峰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并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继续执行。[1]
2.《我们共同的未来》突出了包括工业在内的公民社会的作用: “工业处于人与环境之间的领先地位。这也许是影响环境资源基础发展变化的重要助力。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2]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商业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已成为企业日益增长的挑战:一方面,创新和开发更适应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另一方面,要面对义务、问责制甚至责任的新形式。这种双重挑战来自于《布兰特报告》发起的更广泛的、正在进行的范式转变,这导致全球经济不再主要依赖化石能源,这种转变是由对自然环境状况(包括全球变暖)日益增长的全球共同关注所推动的。
3. 这种影响的范式转移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现有主流(政治和商业)文化的阻力。因此,这种转变不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发生,争议可能有以下不同形式:第一,社会抗议。例如,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抗议活动,让许多人想到了一种思考全球化的新方式,以及企业经营模式对人们和全球化经济下的环境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运动;第二,政治激进主义。例如,现在存在于大多数民主制度国家的绿党,在环境平台上开展竞选活动;第三,通过司法系统进行的诉讼,往往是以公益诉讼的形式进行的。理想情况下,这种论争应通过现有的制度渠道以非暴力方式进行。因此,启动包括诉讼在内的非暴力方式是公法和私法法律固有的基本功能。[3]
4.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跨国法院诉讼尤其重要。其重要性不仅针对正常的商业过程,尤其是在跨国工业和商业活动对人们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形。解决这些不利的跨境和全球外部性的政治和法律救济,主要仍然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因为国际法律秩序提供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非常有限。通过国家法院的跨国私人诉讼,原告,包括公共利益集团,设法防止或制止有害行为和(或)为已造成的损害获得赔偿。这种诉讼往往还有一个战略组成部分,即它反对私人行为主体的一般行为,例如跨国公司的商业政策以及国家行为。事实上,跨国诉讼在一国法院的可诉性可以为谈判和监管提供基础。
5.这一贡献将首先重新利用一些在未来几年可能被视为世界上新兴的商业规范秩序的因素(第二节)。接下来将讨论基于人权和民事责任(侵权)法的跨国私人环境诉讼的近期发展;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节)。最后,以所确定的原则和跨国私人诉讼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将为可能的环境事务民事诉讼的全球法律框架提供“基石”(第四节)。[4]9-108
二、与环境有关的新兴商业规范秩序
6.关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全球原则和规则并不缺乏。但现有的国际文件通常为国家而非私人行为者确立责任——通常是长期责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私营部门的集体努力,就无法实现全球目标。因此,2030年联合国的名为《改变我们的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制定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试图力求将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团结在一起,以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气候变化”
7.关于企业的作用,必须提到《联合国指导原则》④或“鲁杰原则”。《指导原则》是为了专门解决企业在人权方面的社会责任。虽然保护人权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但无论大小,境内任何公司都有责任尊重人权——避免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在负面影响发生时进行解决——当出现错误时,企业也有责任提供补救措施。
8.根据“鲁杰原则”,企业社会责任适用于公司自身的运营以及所有业务关系,包括整个价值链中的业务关系。在全球生产链和世界市场里,人权的责任不止于公司自己的经营、员工以及他们直接控制的活动。它也不仅仅是关于一级或战略供应商。它包括的影响在他们的价值链中可能远得多,而且还包含由影响力有限的第三方造成的影响。
9.约翰·鲁杰认为,目前全球层面上有:基本制度错位……一方面是经济力量和行为主体的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管理其不利后果的能力。这种错位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没有受到适当的制裁也没有进行应有的赔偿。为了被虐待的受害者,为了使全球化成为一股积极力量,这一点必须得到解决。⑤当(跨国)公司活动的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时,该国往往缺乏对跨国公司的保护以及强制执行权力的严格规定。在极端情况下,“制度错位”可能会失控,导致工业环境灾难,有时,外国公司会因为东道国政府在其领土内实施了侵犯其本国国民以及外国人的人权的行为被指控为共犯(协助以及教唆)。⑥
10.“鲁杰原则”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也没有专门解决自然环境问题。尽管如此,鲁杰原则已经成为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范例。此外,人权的侵犯经常伴随着对环境的漠不关心。的确如此,鲁杰调查过的人权案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是涉嫌影响人权的环境侵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得到承认,意味着对人权和环境的综合和相互依存的保护。⑦
11.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鲁杰原则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新兴的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责任,适用于企业自身的运营和所有业务关系,包括整个价值链的业务关系。
12.这类环境企业责任的更详细指标可在各种软法和自我监管工具中找到,包括:第一,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跨国企业的准则,其中包含关于环境的第六章;⑧第二,《联合国全球契约》倡议[5],得到了近10000家公司和4000家非企业的支持,其中包括了与经合组织指导方针一致的环境原则;与此同时,《全球契约》也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社会责任的26000份指导方针[6],以14001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适用于希望对环境责任进行管理的公司和组织。[7]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些文本和其他文本的法律地位。[8]显然,它们仍然是软法,是调节自我规范的工具。但是,它们共同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提供了广泛的支持,为环境问题上的跨国私人诉讼的持续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⑨
三、跨国私人环境诉讼的最新发展
13.如前所述,环境法条约通常为国家确立(长期)行动方针,而不是公民权利和义务所依据的具体约束性义务。在这方面,它们与全球和区域人权文书以及统一的私法和国际私法文书有所不同,这些文书一般都是用文字编写的,以便国家法院和其他当局可以直接援引和适用这些文书。因此,人权法和私法(国际私法)往往结合在一起,在推动和执行环境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人权诉讼
14.最近的一些人权文书,如《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明确规定了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在SERAP诉尼日利亚公共利益案件中认定,尼日利亚违反了“宪章”第24条规定⑩的对尼日利亚非政府组织的义务,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保护尼日尔三角洲免受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DS)的石油污染。鉴于英国和荷兰正在进行针对RDS的诉讼程序,这一判决也很有趣,因为它突出了东道国自己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责任。
15.此外,在人权机构和法院支持有关环境损害的程序和实质性国家义务之前,已经成功地援引了全球和区域人权条约中不专门处理环境问题的条款:已经确定的程序性义务包括向人们提供环境信息的责任,并使他们能够预先评估任何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参与有关环境问题的决定,并有权获得法律救济;实质性义务包括国家有责任制定和实施一个法律框架,以在保护环境,保护其他利益,保护包括妇女、儿童或当地居民在内的弱势群体之间达到公正的平衡,免受私人行为主体的环境损害,包括跨境案件。[9]
16.《欧洲人权公约》(ECHR),欧洲人权法院(ECtHR)已经从第2条(生命权)和第8条(私人和家庭生活权)中衍生出了这类义务。美洲人权法院进一步以加强环境问题的公共利益的方式解释了《美洲人权公约》。反过来,人权准则也可以为民法准则提供依据,并形成针对政府的私益诉讼的基础 - 例如气候变化。
(二)跨国民事诉讼
17.民事诉讼中的公民寻求救济以获得损害赔偿金,或者禁止或减少环境损害的命令,可以超越国界,因为环境损害及其引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也就是说,由于损害的跨国影响,或者在其母国或在其营业的第三国(典型的是美国)法院对跨国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所在国公司、子公司或承包商对环境造成了损害。在后一种情况下,损害的效果不是跨境的因素,而是公司的法人结构或经济组织。[10]P270
18.国际私法在此类诉讼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法律选择规则将指定适用的法律,该法律将决定经济行为者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其在国内或国外的活动承担责任。关于审判管辖的规则将决定它们是否可以起诉跨国公司以及在哪里提起诉讼,并决定在跨国公司的情况下,这些行为是否包括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及承包商在东道国的活动。
19.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是跨国民事诉讼(包括环境诉讼在内)的首选国家。但是美国和欧盟(EU)最近的发展表明,美国已经不再是提起诉讼的首要选择。事实上我们早已见识到了诉讼策略上的变化——尤其是注册于欧盟的母公司主要活跃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的环境责任。
20.审判管辖权是重要判例法发展的核心问题。管辖权是一个门槛问题; 如果法院缺乏管辖权,受害者便没有寻求救济的平台。此外,法院管辖权具有重要的程序性意义,例如是否可以在诉讼中加入其他被告,集体诉讼和公益诉讼的适用性与适用方式,证据的可采性与获取方法包括发现规则,临时措施的有效性,惩罚性或唯一的赔偿金,花费以及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当然,管辖权也可能对适用的法律产生影响,适用的法律决定了责任的基础和范围,赔偿的种类,举证责任等等。
A.美国
21.在大西洋两岸,环境诉讼被定性为对民事侵权的索赔。但是,在美国,十多年来,来自国外的索赔者可以依靠一项旧的法规,《外国人侵权法》(ATS),对美国和外国公司提出索赔主张。并且索赔者通常都会胜诉,并且得到了大量的赔偿。但是,2013年,在“Kiobel v Shell“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彻底地限制了该法案的使用。该案涉及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DS)与尼日利亚政府共谋、协助以及教唆政府侵犯尼日利亚奥戈尼人民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法案受限是因为其不具有域外效力。对总部设在美国以外的公司进行指控,没有“对美国领土产生足够的影响和联系”。RDS在美国“仅仅以公司身份存在”被认为不能够适用《外国人侵权法》。
Kiobel案很有可能已经取消了大多数基于ATS的人权和环境法案,这些法案是针对在美国境内非常活跃,但总部在美国以外的外国公司的。自Kiobel案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时进一步缩小了属人管辖权。
22.kiobel案发生后的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戴姆勒诉鲍曼案中仔细研究了美国法院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般管辖权,即属人管辖权的问题——据说这一商业活动是由戴姆勒在阿根廷的子公司,通过在美国加州的子公司做出的行为(但是该加州子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其主要营业地点在新泽西),该行为在美国被起诉。法院否认这种一般管辖权,因为戴姆勒及其附属公司均未在加利福尼亚成立或主营业务。
美国经常因为其利用最小限度的联系,就将一般管辖权扩张到单纯的被告住所地之外的地方,包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框架内就全球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全球公约的谈判,戴姆勒可能被视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戴姆勒案降低了对非美国被告的不可预见的一般管辖权的风险。因此,该案的判决是受欢迎的,它有助于在世界各国之间更平衡地分配管辖权。但是,当案件的诉讼程序不可能或者不能在合理情况下被允许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审理的时候,不能排除对司法的适用。因为如此一来,国外受害者受到了包括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后,就会得不到救济。而在欧洲,一般管辖权的限制由特别管辖权的规则补充,包括对于可能反映社会价值并可能保护原告的侵权事件和多重被告案件,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法却相反,往往使受害者无法得到保护,特别是针对外国公司的活动。
23.在戴姆勒案一个月后的瓦尔登诉费奥里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强调,即便是具体的、与案件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例如,与司法管辖权遭受的损害有关),从根本来说,也是以被告为导向的:“适当的问题是被告的行为是否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其与法庭联系起来。只有在表明被告已与法庭具有联系的情况下,对伤害案件才具有司法管辖权。这一决定是在2011年麦金泰尔诉尼克斯塔罗案作出的一项有分歧的裁决之后作出的。一家英国公司在新泽西州出售机器,对新泽西州的一名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但不能将其作为美国具备一般管辖权的事项提起诉讼的理由。
24.正如Symeon Symeonides所指出的[11],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这些案件的结果如下:(i)虽然对一般管辖权的改革是必要的,而从事商业交易的基础就是以正确的所在地为基础以确定一般管辖权,但是法院似乎有些“矫枉过正”;(ii)一般管辖权的改革应该使法院“采取另一种更宽容的方式来看待特殊管辖权”,因为“比如McIntyre这样的案件……非常渴望改革”,假定在美国制度的背景下,“从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的角度看待管辖权的话,客观可预见性是一种必要的保障。”。然而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似乎钟摆已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宽泛的管辖范围转向过于狭窄的管辖范围。
25.根据这些限制性规定,美国法院对于诸如RDS或英国石油公司等外国公司在环境诉讼中享有管辖权,除了必须克服的实体法障碍,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城市的大量气候变化诉讼都以世界领先的石油公司为被告(的现象)似乎值得怀疑。
26.最近的另一个美国最高法院案件,Goodyear诉Brown案,可以得出结论:在侵权主张(的提出)与美国子公司的任何活动无关的情况下,为了对美国母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确立一般管辖权,外国子公司与法院所在国的联系必须具有持续性和体系性,使[它]完全受到法院国的管辖。因此,与母公司的公司联系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对子公司的管辖权。很明显,这一判决降低了在美国找到一家法院起诉该子公司在国外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可能性。
27.但即使法院认定了其确实可以在母公司和/或子公司所在地法院正常行使管辖权,然而,如果它被证明是不方便法院,并且另一个法院被证明比他更合适,那么管辖权的大门仍旧有可能对其关闭,即失去了对这起案件的管辖权。不方便法院原则被频繁用于跨国公司在环境损害方面的集体侵权行为和在国外犯下的有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样以来的后果是,在美国,跨国公司通常不承担其在海外行为的责任,外国原告也被禁止向其索赔。
28.关于不方便法院原则案例,最典型的、被应用并被广泛批评的案例之一是博帕尔案。1984年博帕尔悲剧造成数千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该悲剧是由印度博帕尔一家化工厂发生的气体泄漏引起的。这家化工厂由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旗下的nowDow chemical公司运营。印度方面的原告起诉联合碳化物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印度子公司,但美国法院拒绝审理这个案子,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法院审理这个案子更方便、更合适。尽管一致的事实证明印度政府最初是支持在美国进行诉讼的,并且认为当时印度的法院系统没有能力审理这个案子。可以从该案中抽象出不方便法院一个主要问题,即美国法院是否对母公司拥有个人管辖权(因此也包括适用法律的问题)。在该案被美国法院驳回后,双方达成了和解,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不够的。
29.不方便法院原则在雪佛龙案件的运用中导致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结果。在这里,来自厄瓜多尔和秘鲁土著社区的55,000名原告在美国法院以德士古公司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石油业务而造成了环境损害为由起诉了美国雪佛龙公司(德士古公司的继承人)以及其在厄瓜多尔的子公司。雪佛龙公司提出了不方便法院的抗辩,法院同意,并裁定该案件应该在厄瓜多尔审判。通常,厄瓜多尔法院的最终判决对原告来说是可以在美国执行的。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不可以,雪佛龙成功地辩称厄瓜多尔的程序就像它一开始认为的那样,充满了腐败。雪佛龙甚至向美国法院申请并最终获得了关于执行判决的禁止令,并且该禁止令的效力不仅及于美国,而是在全世界。这个结果显然令人不满意。毕竟,雪佛龙最初是在其注册地——一个全球公认的管辖权地——的法庭上被起诉的;如果雪佛龙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很可能只是在自己心中的法庭上赢了,而且这种法律上的“乒乓球游戏”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B.欧盟
30.与美国不同,在《布鲁塞尔条例I》(修正案)中,公司的住所地提供了管辖权的一般依据(第4条第1款,结合第63条第1款),因此(该依据)可能适用于该公司的侵权行为,包括在国外造成的环境损害。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欧盟,那么与美国不同,将会适用第7条第2款的特殊管辖依据,“要么是在损害发生地的法院,要么是在事由发生地或者危害起源地的法院。”但是,如果上述地方都不在欧盟范围内,那么住所地法院原则上是该条例下唯一可适用的法院。尽管如此,该法院已经确定了,因为在Owusu诉Jackson的案件中已经有了决定,不方便法院原则不包括在在本条例中。因此,原则上有可能起诉一家位于欧盟本土的欧洲公司,即使原告并非来自欧盟,最终裁决也很有可能会在该国家做出。这同样适用于英国,英国的法院都倾向于宣布自己为不方便法院。这也使得欧洲与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区别。
31.关于法律适用的选择,根据罗马条例II第四条第1款对于非契约性义务的可适用性,在关于跨国侵权法律的问题中可适用的法律,“适用该法律的国家通常不考虑危害发生地国”。不过,有关于环境侵权的第7条规定:“法律适用于非契约性义务引起的环境损害持续的环境破坏或持续损害个人或财产等导致其造成的损害可以诉求第四条第1款的规定,除非这个人试图以导致损害事实发生地国家的法律为基础寻求损害赔偿。原告不管是否来自于欧盟,也无论该环境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欧盟境内,都有这样的选择权。
32.布鲁塞尔条例I和罗马条例II的这些规定也可能对跨国气候变化案件产生影响。最近的一个案例是Lliuya诉 RWE AG公司[12]。目前是位于哈姆的上诉法院(Oberlandesgericht:州高级法院)中的一个未决案件,在秘鲁,农民起诉德国RWE公司,指控RWE公司有故意排放大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应该对Lliuya Huaraz镇附近高山冰川的融化负责,这引发了严重的洪水的威胁。根据布鲁塞尔条例I,德国法院毫无疑问具有管辖权。根据罗马条例II的规定,原告可以选择损害行为国家的法律(秘鲁),也可以选择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国家(德国)的法律。
33.如果该子公司或承包商对环境损害负有直接责任,那么是否有可能与母公司联合起诉位于欧盟以外的子公司,或者承包商?本文之前提到,美国的古德伊尔诉布朗案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欧洲,布鲁塞尔条例I(修正案)第8条涉及相关索赔问题,但仅针对在成员国注册的被告。其母公司的注册地在欧盟,但是子公司却在欧盟外注册,是否也可以由欧盟的法院审理,这是一个国内法的问题
34.最近英国和荷兰的判例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接受布鲁塞尔条例I(修正案)第4条第1款建立的强制性规则,英国法院已经制定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测试,这个标准取决于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问题”和“主诉被告”,即母公司——为了避免子公司在案件进入英国法院前将对母公司的索赔诉求非法利用。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在法院的最初决定阶段确定其对母公司和子公司都有管辖权后,对索赔的实质内容,尤其是对母公司的指控进行全面审查是不可能的,法院欣然承认这一点。
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对各种实质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审查,以确定他们对主诉被告是否具有管辖权。有关于此的典型案例是 Chandler诉Cape案,上诉法院仔细区分了其论证与“刺穿公司面纱”的不同,认为母公司基于可预见性的标准、接近度以及由Caparo上议院定义的合理性,有单独的注意义务,(这个义务)由于案件情况的影响,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35.在韦丹塔案中,上诉法院假设适用的赞比亚法律遵循的是英国法律,并得出结论:“在不确定主张是强是弱的情况下,”韦丹塔可能对受其子公司经营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这一考验似乎仍与布鲁塞尔条例I的制度相一致,因为毫无疑问,根据该条例,对权利的明显滥用是不被接受的。另一方面,在另一个最近发生的Okpabi案中,Fraserdelved法官对“真正的问题”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不仅认为,“(布鲁塞尔条例)的修正案以及Owusu诉Jackson一案,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都具有必要性,而且他还认为,只有在真正的问题出现时,才有可能出现滥用欧盟法律的问题。”这一推理似乎暗示了被滥用的测试与“真实问题”是不同的——”法官详细审查“真实问题“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其并不存在。这似乎表明,什么属于管辖范围的领域和什么属于实质性问题的界线已经被逾越了。
36.荷兰法律的立场不同,其更侧重于对程序的适当规定。荷兰民事诉讼法在其第7条第1款中对与索赔有关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该条款与布鲁塞尔条例I第8条第1款是一致的。在Akpan et al诉Shell案中,目前正在海牙上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现正在审案),法院接受了对在尼日利亚的母公司壳牌和其在尼日利亚的子公司的管辖权,因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法院并没有排除在适用布鲁塞尔条例I下滥用程序的可能性,但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发生这种滥用。法院还认为,在诉讼开始时原告和母公司之间存在真正的争议是充分的,即使一审法院最终裁定母公司不负责任。
37.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荷兰上诉法院的判决与地区法院的规定相反,母公司应该向最初的原告披露一些文件,但这可能与母公司是否知道渗漏的问题以及管道泄露的情况有关。
38.这些案件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上诉法院是否会一直享有对韦丹塔和阿克潘的管辖权。但是,根据’外商直接责任”趋势,阿克潘的上诉法院指出,对于总部位于欧盟的跨国公司和其海外子公司来说,在子公司在海外的活动导致的严重环境损害问题时,说服母公司住所地法院,其不能和母公司被一并起诉似乎越来越难。这是本着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的精神而做出的行为。在阿克潘,上诉法院微妙地指出,壳牌在包括环境问题上,都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并制定了团队政策,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和信念。
39.欧盟可能是一个更有潜力的场所,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对于总部位于欧盟或者美国的海外子公司导致的非法的环境损害寻求环境侵权方面救济的诉讼。在美国,针对总部位于外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审判管辖权已大大缩小。
四、建立环境问题民事诉讼的全球法律框架
40.鉴于正在发生的典型的范式转变,最近在环境问题上的跨境民事诉讼的发展,很可能只是在局部损害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此类诉讼的开始。虽然尊重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但正如《联合国2030年议程》所表述的那样,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对于推动此事件的向前发展至关重要,最好是通过法律渠道以有序的方式推进。
41.公民社会在提醒政府当局的职责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例如,1993年的《北美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于1994年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生效,为宣传环保法律法规,政府执法行动,获得民事和行政补救措施和程序保障,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规定(提前)以及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关于在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司法机会的公约》(奥胡斯公约),该公约目前已对47个国家有效。
42.致力于在跨国环境案件中建立的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民事诉讼的法律渠道,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关于裁决管辖权、适用法律、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全球性文书的技术可行性,受到了一个机构合作制度的支持,(技术可行性)是一个广泛研究和讨论的主题,被包括在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中海牙会议的范围内。但这并没有导致在该框架内就一项全球性文书进行谈判的结果。在地区层面上,欧洲议会1993年通过了一项公约,到目前为止,(该公约)规定了实质性的民事责任,规定了获取信息、程序问题,结合法院的管辖规定和对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2003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的类似文件,规定:仅限于跨界水域上的工业事故造成的损害。但这两项措施都没有生效。
43.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目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框架中的关于全球性公约在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方面,在对环境诉讼特别关注之后,在这方面可能会有进步。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对某些其他事项(例如,消费者案件)的确定。2017年11月提供的最新草案第五条(认可和执行的基础)第一段(j)项规定,当外国判决满足“裁决因死亡、人身伤害、有形财产损害或损失而产生的非合同义务,以及直接造成这种损害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论该损害发生在何处。”的条件时,该外国判决就可能获得承认和执行[13]。因此,本条款草案,以它目前的形式来看,没有规定承认和执行在有害事件地点作出的判决,即使只限于局部损害。
44.根据目前的草案,为了从《公约》关于承认和执行的规定中获益,原告基本上只能选择在被告的住所地(第5条第1款(a)项)或在“直接造成损害的不作为行为”(第5条第1款(j)项)地提起原始索赔。而且,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法院根据其国家管辖规则,也可能拒绝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基础上行使管辖权,这将进一步限制未来(相关)文件在跨境环境案件中的效力。这一规则与欧盟法院解释的《布鲁塞尔条例I》第7条第2款有所不同,更符合麦金太尔和沃尔登美国最高法院面向被告的狭义判例法。但是,即使在瓦尔登测试中,如果被告的行为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他与问题联系起来,那么该损害事件发生地的法院也可能拥有管辖权。海牙公约的最终文本应至少为来自损害事件发生地法院的判决的认可和执行腾出空间。正如Symeonides提出的,被告有理由合理预见到其行为在那种情况下会产生危害。
45.然而,即便如此,未来的公约也将只涉及民事诉讼的一个方面,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来的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有多么至关重要。适用法律的问题也是如此。此外,一个跨国界的司法和行政合作制度将大大有助于民事诉讼。
46.鉴于前几部分的概述以及以现有的全球和区域文书中出现的“模式”为基础,应当能够就全球法律框架的若干基本结构组成部分达成协议,包括:
47.管辖范围。对任何实体或个人以外的实体的住所或(惯常)住所的广义定义(《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就是一个例子)。
排除不方便法院对被告住所地国家法院的管辖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这是《布鲁塞尔条例Ⅰ》体系的标准做法,但在包括美国的英美法系国家,不方便法院依然存在。然而,在这方面,《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它将不方便法院排除在该专属法院选择协定之外。为解决环境问题的跨境诉讼,排除不方便法院还是很有可能的;当诉求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时,多个被告案件的管辖权取决于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布鲁塞尔条例一号》(修正案)第8条第1款为例);原告可以在损害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国家的法庭上对被告的违约行为起诉,并且应该给原告提供被告应该合理预见的损害,或者这个事件已经产生损害的地方。该模式遵循1999年《关于民事和商业事项的管辖和承认及执行判决公约》的初步草案的模式。
48.适用的法律。适用发生损害地国家的法律,寻求救济的人可以根据发生损害事件国家的法律提出索赔,但条件为损害是被告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一部分没有什么争议。这一选择是受到欧盟《罗马公约II》针对适用于非合同义务的法律的第7条的启发,但只有在具备了其他同类的管辖理由时才有权选择。
49.承认和执行。基于(i)项的管辖理由,对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可以遵循《海牙关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章的模式,包括第11条(惩罚性损害赔偿)。不应当要求任何互惠。
50.司法和行政的沟通与合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在法庭之间建立直接的跨国交流机制,尊重、倾听各方的权利,避免有关管辖权和证据问题的诉讼程序出现重复;此外,为国家行政协调中心(“中央主管部门”)之间的直接跨国合作提供基本的机制,以促进文件的跨境服务、取证以及法律援助申请的传输为目的确保法律援助可以被申请;验证组织或原告在集体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向居民和外籍人士提供他们关心的有关于环境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并允许他们参与;以及在一般情况下,与其他国家行政协调中心在环境案件方面交换情报。
51.这些只是起点,目的是刺激各方重新努力,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领域建立跨境民事诉讼的全球框架。民事侵权诉讼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执行环境标准的方式,对自上而下的政府执法,特别是跨国执法构成了必要的、有效的补充。各国及其公民将会对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公民获得信息和正义的权利以及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参与决策产生兴趣,1998年《奥胡斯公约》为这种权利提供了典范。至少应该将促进跨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全球框架作为一项紧迫的事情。在这一领域,统一的国际私法规则将对适应新出现的与环境有关的商业规范秩序(包括气候变化)的全球法律架构做出重大贡献。
注释:
① 《我们共同的未来》,被称为“布伦特兰报告”,以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命名;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其中包含两个关键概念:“需要”的概念,特别是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要,应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以及技术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能力所施加的限制的观点(n 1) 43..在Kate Raworth的donought Economics(牛津,2017)中。“社会基础”和“生态上限”这两个关键的概念再一次出现在了“donought”的图像中。
③ 我们共同的未来(n 1)特别是第七章化石燃料:持续的困境。
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1年通过了《关于2008年商业及人权的尊重、保护和救济框架的实行的指导原则》。
⑤ 约翰·鲁杰,秘书长特别代表关于人权、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问题的报告(2007;联大文件. A/HRC/ 4/35) 3.
⑥ 见下文第14、21、35-39号。
⑦ 参见Katinka Jesse和Erik Koppe,《商业企业与环境》,4期(2013年12月),《The Dovenschmidt Quarterly》,176-89,认为“鲁杰原则”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解决国家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以保护环境。
⑧ http://www.oecd.org/daf/inv/mne/48004323.pdf(2018年2月14日访问).注释第71条鼓励企业努力提高其所有业务部门的环境绩效水平,即使在其运营所在国家现有做法可能没有正式要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企业应适当考虑到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该准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不具有约束力,但它们要求加入国家建立国家联系点,还具有向经合组织投资委员会报告的义务,以进一步提高它们的有效性。
⑨ 根据“巴黎协定”的目标,进一步来讲,公司有关气候变化的义务是“使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摄氏度,并努力将温度上升限制在 1.5 C′,最近由企业气候义务专家组出版了“阿姆斯特丹企业气候义务原则”。https://climateprinciplesforenterprises.files.wordpress.com/2017/12/enterprisesprincipleswebpdf.pdf (2018年2月14日访问),以及Jaap Spier对本书的贡献。
⑩ 第24条:“各国民都应有权获得对其发展有利的普遍令人满意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