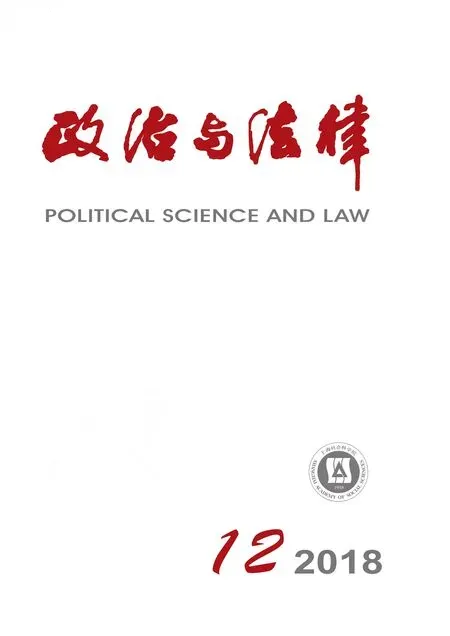科技与刑事司法互动的系统论观察*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现代社会呈现功能分化的特点。功能是对现代社会各种子系统运作结果的事实描述,在价值层面,则呈现为各种子系统话语的价值差异。分化的功能与多元的价值使得各子系统运作难免发生张力,各种价值观念之间难免产生冲突。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事实与价值多元的规范性构成当然对人的自由扩张具有助益,但系统间的功能差异和价值冲突也会给人们的行为预期造成困惑。现代社会要处理自身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复杂性,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不是回到前现代社会功能单一与价值一元的状态,而是需要在多种社会系统功能与价值之间找到平衡与共享的媒介,从而实现整体社会中不同功能与价值的共生。
在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中,现代(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认知的快速增长对传统刑事司法的规范结构与价值预设提出了挑战。①King, Michael, and Christopher J. Thornhill.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0.刑事司法需要回应这种挑战,正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所带来的复杂性。同样,如果科学技术想通过刑事司法的管道实现对人类文明的促进,科技领域必须以理解的态度看待刑事司法的运作。在社会功能演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刑法还是科技都无法拒斥对方的理性和逻辑,两者处于共生的状态。②Teubner, Gunther. “After legal instrumentalism.”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3 (1986): 302. Luhmann, Niklas.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Chapter 11.在宏观层面上研究刑事司法与科技领域中的功能整合与价值共享问题必须在方法论上寻找一种超越个体主义的整体主体。因此,笔者于本文中试图以卢曼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系统论为框架,阐明两者间的这种共生状态及其演化趋势,理解其生成机制,寻找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与规范框架。
一、概念与认知的自我生成:法律与科技结构耦合的前提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并不是定义社会实在的唯一权威。科技系统依赖的是对科学研究“真/非真”的判断,是对预设进行检验的系统运作过程。科技系统的构建以科学假设为基础,并且建立在其系统内部证成这种假设的能力之上。科学假设的基础是科学系统的概念,科学观察以自身的概念体系展开。这并不是说科技系统的沟通仅仅以概念构成,而是表明,科技从一般性的社会沟通中分化出来,依靠的是其特有的概念体系。[注]Luhmann, Niklas. “On the scientific context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5.2 (1996): 258.基于概念的自我指涉,科学沟通也无法避免一种悖论,从而科学系统也就无法声称具有超越的价值和意义。科技系统不能成为现代社会宗教的替代品。[注]Rasch, William. Niklas Luhmann's Modernity: The paradoxes of differenti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 82.
进一步而言,同为封闭的社会沟通系统,科技沟通并不能够直接“介入”刑法体系的运作。[注]Schiff, David, and Richard Nobles, eds. Law, Society and Community: Socio-legal Essays in Honour of Roger Cotterrell.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231.托依布纳认为,应当将法律系统对真实的构建与科技系统对真实的构建看成是具有竞争性的社会语义。[注]Teubner, Gunther. “After legal instrumentalism.”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3 (1986): 302-303.刑法在确认某项法律运作(立法或司法)时,其无法像自然科学一般,基于实验数据进行客观的验证。刑法运作在方法上需要借助抽象价值与规范目的的辩证过程。[注]参见古承宗:《风险社会与现代刑法的象征性》,《科技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刑法学以及刑事实践的方法论是诠释学,即新康德主义和狄尔泰等人倡导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说明相比,诠释学是“体验”和“理解”的科学。诠释学不是单纯去阐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和有什么规律,而是还负有教育人的使命。[注]参见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5页。两者之间需要解决的是兼容问题。
然而,社会诸领域的互相理解和认知并不建立在一种实体性的规范认同上,也就是说,在科技系统与刑法体系之上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规范或价值引导。现代社会的系统间的协同机制通过“程序的制度化”达成。[注]参见[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79页。这种制度化的合法性并不在各个系统中达成价值共识,程序只要求最低限度的运作条件。[注]Scheffer, Thomas, Kati Hannken-Illjes, and Alexander Kozin. Criminal defence and procedure: Comparative ethnograph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pringer, 2010.p. 15.刑事司法裁判的最终结论在程序化制度的搭建过程中将不可能于事前得到明确的预测。不过,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参与诉讼各方对程序性制度的认可。同时,程序化下的合法性认同,则可以减少互为环境的科技与法律的互相“敌视”。
不过,即使有了程序性的制度构建,刑法系统与科技系统间耦合所具有的高度选择性、偶在性依然无法消除。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在事前明确,在何种具体的情况下,科技会影响包括刑法正当性与刑法理性的构建。[注]Teubner, Gunther. “After legal instrumentalism.”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3 (1986): 303.科学知识有可能在法律职业者看来对解决刑事司法问题并无助益,但也有可能对刑法体系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甚至,正如卢曼所言,在常规司法案件中,科技的介入不是有助于减少审判的不确定性,而是增加了审判的不确定性。[注]Luhmann, Niklas. “Legal argumentation: an analysis of its form.” The Modern Law Review 58.3 (1995): 294.并且,事实认知的媒介作用很容易导致科学主义的专业性概念,从而促成一种司法上导入和强化纠问制的因素。[注]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增补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与科技的冲突在当下越来越凸显,而其症结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脚步已经大大领先法律规范理论的更新速度。这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冲击。[注]Posner, Richard A. Divergent Paths: The Academy and the Judici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8. 波斯纳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监视”(surveillance)规则来说明法教义学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满足快速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技术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的有关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使得现有的刑事法律规则无法解决实践中的急迫问题。Posner, Richard A. Divergent Paths: The Academy and the Judici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74.笔者将结合刑法运作中存在的与科技系统进行互动的例证对波斯纳提出的疑问和担忧作出系统理论的解读,从而分析和判断刑法教义理论是否如其所言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能满足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需求,并且,如果这种状态得到证实,是否需要通过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改造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刑事司法是否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结构进行改造。
二、刑事程序中的专家证言与司法鉴定:科学标准与司法标准的辨析
(一)曲解与质疑:专家证言的司法适用
首先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刑事司法中的专家运用。信息收集在法律过程中的不完整性以及案件事实的多样性决定了法律执业者在工作中需要求助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帮助其在有限的时间和证据条件下,建立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在一些案件中,尽管作证专家的意见无法得到所属研究领域的一致认同,且专家并不是利益中立的裁判者,相反却是有着鲜明个体、集体(所服务的机构)或行业利益倾向的职业人,[注]参见黄韬:《公共政策法院:中国金融法制变迁的司法维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但作为法律工作的辅助者,如同其他证据规则的践行者,专家运用也是一种保证司法过程稳步向前推进中“无奈的妥协”。不过,这种“无奈的妥协”在实践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妥协下的失败”。
以科学证据在刑事实践中的应用为例,其中较为著名的例证是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道伯特规则(Daubert Rule)。这一规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采纳专家证据的司法认定规则。在此规则下,法官有权决定是否将“科技证据”呈献给陪审团。“科技证据”必须满足相关性与信度(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条件。此规则要求法官必须判断专家证词与待证事项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是否建立在信度基础之上。专家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作证。科学的方法被认定为建立假设,并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验证。运用科学方式作证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非决定性的、非排他性的、有弹性的有关一般性问题和事实的观察。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可证伪的、可以被推翻的,并且是经过同行检验的(peer-reviewed)。[注]See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 (1993). 参见[美]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这一规则遵循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即最好的科学验证方法是提取那些大胆且具有大量信息的理论,然后通过批判地讨论并严格检验这些大胆的理论来让它们相互竞争。[注]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不过,有关的研究表明,这一司法规则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严格遵循。即使是在那些被视为简单和常规的案件中,道伯特规则也经常被弃而不用。法官对专家证言的接纳在实践中并非以科技领域的标准为导向,反之,却经常接受那些在专业领域看来充满疑问的专家证言证词。[注]See Saks, Michael J., and David L. Faigman. “Expert evidence after Daubert.” Annu. Rev. Law Soc. Sci. 1 (2005): 105-130. See aslo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 592-597 (1993).有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在挑选专家作证的过程中都存在偏向,而这种偏向无疑也会影响相关证词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呈现方式和信度。[注]Scheffer, Thomas. Adversarial case-making: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Crown Court procedure. Brill, 2010.p. 75.
道伯特规则的流变乃至弃用说明了在刑事司法中呈现“科技真相”的困境。在系统理论之下,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刑事司法程序的运作的时间、事实与社会维度与科技系统存在明显区分。
相对于日常科研环境中所允许的时间而言,刑事司法对证据的认定时间显然要短一些,作证的专家面对的是对所证事项没有太多基础知识的人(法官和陪审团)。从事实维度上来看,如果法官基于既有证据做出了判决,那么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往往不能再就同一问题提出诉讼,事实的最终面目就变得不重要了。[注]参见舒国滢、宋旭光:《以证据为根据还是以事实为根据?——与陈波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专家在法庭的作证方式也和科研方法与进程很不相同,即使是书面证言证词,刑事司法程序也提出了与一般科研相比更多的限制。[注]See Shuy, Roger W. “Forensic linguistics.”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2000): 683-691.一方面,作为定案依据的裁判事实会遭到实体法规范的“裁剪”: 作为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并不是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根据相关实体法规范“量体裁衣”的事实。在司法裁判中,作为推理小前提的裁判事实,不仅应当是认定为真的,而且应当是有用的(即与实体法律规范中的事实范式相符合)和能用的(即不违反证据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没有被排除)。另一方面,事实的认定受到了法律程序的制约: 事实的认定必然是建立在相关证据以及法定的证明标准之上的,这些证据标准通常并不要求事实认定是“绝对确实”的。也正因为这样,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根据法律规范所认定的事实,其未必与客观事实相同。[注]同上注,舒国滢、宋旭光文。
相比较而言,科学研究的历程与制度条件与刑事司法相去甚远。以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归纳方法作为例证,具体而言,在使用归纳方法时,一般有三种条件应当具备:第一,通过观察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必须基于足够的样本数量;第二,在不同的条件下,观察结论必须能够被重复验证;第三,观察结论不能与其前提法则相异。因此,在严格的归纳方法下,科学结论也必然是一种概率性的结论,而这与刑事司法对专家证言效度(或在法学理论中被称之为效力的东西)的要求迥异。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司法实践中关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可能性的计算方法并不能用概率论来解释。[注]参见易延友:《通过计算实现正义》,《数学文化》2013年第5期。刑事司法与科学研究在上述话语呈现上的不同,使得任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作证的专家必须根据司法的维度对所要陈述的待证事项进行必要的浓缩,并遵守法律的程序规则。[注]See Scheffer, Thomas. Adversarial case-making: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Crown Court procedure. Brill, 2010.p. 76; Scheffer, Thomas. Adversarial case-making: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Crown Court procedure. Brill, 2010.p. 81.
基于刑事司法与科技系统在时间、事实与社会维度上的差异,应当谨慎对待专家证言。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的立场。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87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证词也受到严格审查。如有关“被害妇女综合症”的研究,即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的科学证据,只能作为说明特定妇女在受到长期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严重暴力的假设下,可能存在的心理状态。这种专家证据不能作为判定正当防卫等出罪事由的法定根据,换言之,不能从这些证据中直接推论,妇女在新的家庭暴力出现之前就对其丈夫采取反击,是一种“法律上”合理的举动。从“法律角度”来看,被害妇女的行为应当满足正当防卫的时间与主观要素条件。[注]State v. McClain, 591 A.2d 653, 657 (N.J.Super. App. Div. 1991); State v. Johnson, 399 A.2d 469, 471 (R.I. 1979).科学(犯罪学)上的被害人学,是从犯罪现象的互动性入手的,而刑事司法的逻辑是对惩罚的对象作出评价。从中可以看到,专家证人证言只具有补充法定证据的效力,不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使用。另外,美国普通法、《联邦证据规则》以及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也对不属专业领域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使这些领域从科学研究的范式来看,并非不能被界定为“科学”。[注]参见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 规则 判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242页、第250页。
法院可以依职权聘请专家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官审理中面临的技术难题。然而,专家证人证言也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可能成为司法过程的决策前提。法学虽然会涉及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背景,但不能以自然科学作为基础,而应以法解释学作为支柱。[注]参见上注,易延友书,第263页。并且,根据相关法院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况来看,专家证人不能对超出鉴定意见或与案件处理无关的问题进行解答。[注]参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若干问题的纪要》,http://www.pkulaw.com/lar/0cac1435377e9cb13afe3fbc44746f93bdfb.html?TKey=byPVBWUfYNQrHvYt3672N%2fP7RcbxSmsWAphIlUdVHiiC4T79kfqgCMFiPSqOaPGibbE5WR4%2bckwOeqOE3El3a0Xr88LVYuaneGsYv29VLzCuCuH7aItMsOQ4qUVDMW7xfHH6ocHezXSw9NAVgYUZZQbJSuqKcM55lA99haUaGGHcNzvk%2b69gCqBbS3fH8lUl,2018年9月27日访问。我国司法系统对专家证言较为保守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保护诉讼参与人不受经过裁剪的专业知识的误导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司法鉴定:事实的法律重构
科技系统与刑事司法更为日常的互动体现在司法鉴定中。在案件立案、侦查、起诉乃至最终的审判与执行中,都有司法鉴定的参与。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司法鉴定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容易引发诉讼主体的困惑。例如,“上访事件”可以看成是科技系统与刑事司法系统耦合过程中产生的“失败”例证。一方面,当前我国司法鉴定中确实存在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从而破坏了司法鉴定中运用科技话语和手段进行证据鉴定的效力,更使得当事人(包括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被告人)对鉴定过程和结论产生怀疑,进而引发对司法过程的信任危机。这种“不信任”一旦形成,想要通过司法的救济予以弥补将非常困难,并且还会带来系统性的影响,产生殃及效果。例如,有的案件中,死者由于自身心脏病死亡,家属甚至也认同鉴定结论,不过由于上访思维“惯性”,为了得到大笔赔偿,当事人家属不断上访、暴力上访乃至牟利性上访。[注]参见陈如超:《中国刑事案件中的涉鉴上访及其治理》,《北方法学》2014年第1期。进而,司法系统也会对上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产生怀疑(甚至质疑其精神状态),并产生恶劣的“截访”等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不存在腐败问题,司法鉴定由于内嵌于刑事司法体系中,也会产生和专家证言相似的对科学事实的“简化”以及“异化”(alienation)问题。也就是说,法律系统中的“鉴定”已经不再以科学系统的运作逻辑呈现。
正如相关判例所述,没有相关专业医学知识,任何法官或者陪审团都无法建立起合理的标准以判断医事事实。[注]Melville v. Southward, 791 P.2d 383, 387 (Colo. 1990).然而,医学研究无法直接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是否启动鉴定以及是否将鉴定人纳入刑事司法程序,均以刑事司法的纲要为准。[注]参见周翠:《破案后:德国刑事司法档案》,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4页。以谋杀案件为例,行为人的行为在刑法上被一系列的法律系统流程、程序和关系包裹,医学话语不可能成为主导司法活动的话语。杀人案件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与在医学沟通中不同。法律将杀人行为构建为一种非法行为,使用侦查起诉审判沟通去完成对案件事实的构建与规范的价值判断。医学上对杀人案件的分析则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刑法规范上的“归责”问题,而是将杀人行为看成医学事件(杀伤的程度、解剖学意义上的砍杀部位等)。[注]Horton, David Paul. “Looking Through the Reeds: System-Theorising the Independent Homicide Inquiry.” (2014). p.48.这些医学话语在传统刑法理论中通常被看做是“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即被认为是不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的。不过,在系统理论看来,有关行为人伤害的“事实”判断,已经是刑事司法系统的沟通,而不是一种医学话语的沟通。由于人类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真正有意义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认识论上的事实常常表达的是主体的一种确信或信赖,[注]同前注,舒国滢、宋旭光文。因此,也可以认为,刑事司法中的概念,即使与医学上的概念在语义学上吻合,但在语用学上,其已是一种“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构建。刑法学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回避价值判断,不过是将价值问题转换为事实认知问题。
规范的价值判断与客观性的呈现是两个问题。正如卢曼所言,信息相关性的最终确定由系统自身的逻辑决定。[注]参见前注⑧,张庆熊书,第163页。法律的认知运作由法律的自我指涉实施,而不是由其对环境的指涉展开。甚至法律案件的事实也是由法律系统自身内部构建的:“没有疑问的是(案件的)事实也是法律系统(法律运作)的构建,而不是法律系统环境的物质化,这从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任意的外部科学观察以及其对证据的处理上都可以看出来。同样,对环境的观察,也就是案件的事实是法律系统内部的系统运作。”[注]Ziegert, Klaus. “The thick description of law: an introduction to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operatively closed systems.” (2002).如果将法律系统视为一个“观察者”,那么这个观察者并不处在世界之外,当观察者通过观察介入到自身关联的过程中的时候(这些过程在结构和功能上创造并保持了被观察的系统),观察者完全有可能改变、保持或创造了他所观察的东西。[注]参见[德]弗里茨·B. 西蒙:《我的精神病、我的自行车和我——疯狂的自我组织》,于雪梅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0页。正如卡多佐所言,司法是科学的,因为它能在唯独科学才能揭示的那些客观因素之中发现自己的坚实基础。[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5页。卡多佐所说的司法科学性与客观性,与实证科学等其他认知模式所展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存在差异。[注]即使是实证统计的结果,也并非不受司法过程与法律规范目的的检验,这一点在运用统计工具进行鉴定的司法过程中有较为鲜明的体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0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当律师和法官在法律系统的沟通中讨论有关政治、家庭、性与暴力等社会现象的时候,这些探讨并不是事实的存在,而是法律系统的构建物。在一种构建主义的社会知识论之下,法律的事实并不能与所谓的系统外部的社会事实进行对照。法律作为一种自治的认识主体,创造了系统自身的社会事实。[注]See Teubner, Gunther. “How the Law Thinks: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of Law,” (1989) 23.” Law & Society Review 5: 727.同样的事件可以与两种社会系统话语相联系,但是两者之间对相同事件的沟通不会融合成一种多维度的超级话语,它们之间也不会产生信息的“交换”。信息在不同的社会语义下被重新组织和构建,这些不同系统和不同语义之间的互相激扰只是形成了信息被不同系统沟通处理的“共时性”。托依布纳认为,对事实产生的不同社会构建需要进行所谓的“社会一致性”的检验,从而替代所谓对法律事实与真实世界对照的检验。在非法律的沟通世界中,法律构建不可避免地在这场知识竞争中败下阵来。在这里,科学在纯粹认知运作的过程中具有更专业的优势地位,而在法律系统的沟通中,认知运作仅仅具有次要的地位。在这些情境中,法律话语掌控了认识运作的过程,使之与法律的规范性特点和制度目标相吻合。法律沟通的“实证模式”牢牢掌控在法律“策略性的”和“系统性的”模式中。不过,正是法律系统的这种制度情境创造了一种内部对科学系统事实构建重新塑造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系统自身塑造过程,使得法律运作能够在自身沟通维度下引入科学知识对认知问题进行权威性的判断。科学系统创造的系统“事实”、它们的社会适当性和可行性,也不再通过“科学”检验方法来判别,而是通过法律沟通的过程来检验。法律系统定义了诸项基本的、有关系统认知方法的条件。[注]See Teubner, Gunther. How the law thinks: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of law.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0. p. 751.
例如,刑法责任中的“精神病抗辩理由”受到医学(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概念的影响,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所指出的,之所以存在这两种有关精神病的概念,正是由于刑法运作和医学运作对个体责任与个体能力的评判标准“存在本质区别”。[注]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359 (1997).美国刑事法实践中,精神病抗辩事由在上世纪的剧烈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医学标准的演进并不能直接促动罪责阻却的发展。在我国,即使在医学上被认定为精神病,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近年来时常发生的吸毒致精神障碍后行为人刑事责任判断的案件中,行为人依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7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此外,近年来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也和科学的鉴定结论存在一定的张力。比如,在面对利用含有淋巴的花油、含有伤肉的膘肉碎等肉制品加工生产的“食用油”,即使科学检测报告显示这样制成的“食用油”各项理化指标均合格,没有检测出有毒、有害成分,但在司法机关看来,检测报告不应是认定“有毒、有害食品”的唯一根据,甚至司法机关明确提出,“应当结合技术标准和法学标准”对“有毒、有害食品”进行判定,有的地方性司法规范性文件也明确指出,“对于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行为人在食品中掺入国家行业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质的,对涉案食品不需由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注]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http://www.chinatrial.net.cn/news/17332.html,2018年9月27日访问。
再如,在一起追打小偷进而造成其死亡的案件的裁判文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谭某的行为与许某某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法医鉴定,许某某的死因是自身疾病引发脑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许某某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是主因,其他外界因素是诱因,即许某某的死亡是主因与多种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定人认为外伤作用导致许某某头部剧烈摇摆从而使血管受到一定程度的牵拉,是许某某脑血管破裂的诱因之一。从案发的情况来看,许某某原本在正常行走,遭到谭某殴打后倒地不起直至死亡,正因为谭某的暴力行为导致许某某的身体产生应急反应,诱发许某某病情骤变而死亡。因此,谭某的行为与许某某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章程:《追贼追出人命 水果摊主坐监》,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7566,2018年4月11日访问。
这段“科学鉴定”,其实并非科学研究意义上对死亡结果的认定,其目的在于为行为人判断刑事责任确定前提。对于物理性的“牵拉”行为,法院的认定并非将其看作一种身体动作的“描述”,而是赋予其价值判断。在事实的认定中,并非不存在规范的语言,例如在该案中,法院就认为许某某的行为,也就是偷水果并逃跑的行为,是“正常行走”,而不是“逃跑”,因此也就在规范上否定了谭某追击的合法性。虽然在对“法律问题”的阐释中,法院对正当防卫的限度做出了说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事实的认定,也就是司法对医学鉴定的重述,决定了行为人责任的认定。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所论证的,在人们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如“这个人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或“这个人盗窃”之类的句子既包含事实判断,又包含着价值判断。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涉及遵循语言用法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受到生活形式中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注]参见前注⑧,张庆熊书,第24-25页。张明楷教授也曾指出,在法律论证的过程中,对事实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舍弃细微的具体事实),但也不能过于抽象,至于抽象的程度,从张明楷教授所举的例证来看,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刑法教义学规范判断的需要。[注]参见张明楷:《实行行为的意义》,载于改之、周长军主编:《刑法与道德的视界交融——西原春夫刑法理论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在“因果关系异常介入”的刑法教义学中,医学鉴定仅仅是判断行为人责任的一种信息,医学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医学的科学话语和逻辑在此“服务”于刑事审判。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将这些医学伤情鉴定称为“司法”鉴定,而非临床诊断。正如我国学者所言,对于法律系统而言,必须发展出一套法律概念和话语用以描述客观事实,并且提炼其法律意义,这样,事实发生的客观的历史才能被转化成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律事件。如果不加分辨的直接使用科学结论,无论如何都会导致歪曲对法律审判行为所追求和表达的社会意义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注]参见前注,易延友文。法律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法律概念作为一个意义甄别体系而存在,根据人类社会的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了分类和排序,从而得以确保一种意义秩序的产生;另一方面,法律概念也使事实和价值、行为和规范得以区分开来,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构建出一套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较为简单的一般性规则。[注]参见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思·韦伯法律思想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就此而言,法律系统内部的事实,与客观发生的事实有所出入,互相矛盾甚至抵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差异往往可能是系统维持运作所需要的。[注]泮伟江:《一个普通法的故事:英格兰政体的奥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三、刑事司法与科技系统视域融合的必要性:生活世界的维度
通过上述的例证可以发现,波斯纳所认为的司法面对科学技术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刑法体系自我指涉效果的体现,两者并不需要在系统沟通的事实、社会以及时间维度上保持一致。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产生并容纳这些系统间的差异。法律事实是被法律框架型构的事实,法律事实必须能够促进法律规范演绎推理的展开。法律事实必须支持法律有效性的展现。法律事实必须给外部观察者传达这样的印象:在规则给定的情况下,法律决定通过事实被顺理成章的给出,但必须是“被认证的事实”。[注]See Scheffer, Thomas. Adversarial case-making: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Crown Court procedure. Brill, 2010.p. 80.事实构建,是观察者对世界的看法。社会理论的考察发现,科学事实和服务于法律或政治决定的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知识在法律系统的内外具有不同的“信度”。[注]See Luhmann, Niklas.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ardozo L. Rev. 13 (1991): 1429-1430; Paterson, John, and Gunther Teubner. “Changing maps: Empirical legal autopoiesis.” Social & Legal Studies 7.4 (1998): 451-486.法律对事实构建中的动机和价值前提与科学构建中的上述前提并不一样(例如科学理性、经验研究以及科学论证过程等)。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接受不同系统的认知条件、检验方法、对确定性的不同标准以及运作成果的不同衡量方式,[注]See Teubner, Gunther. “After legal instrumentalism.”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3 (1986): 302.同时,又不能忽视前述波斯纳所提到的司法困境。这就必须思考刑事司法与科技系统视域融合的必要性问题。
如果刑事司法在运作的过程中,面对高度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在认知上保持封闭,那么司法活动的社会认同就会成为问题。因为即使将现代社会视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各种社会系统在沟通的时间、事实与社会维度上均存在差异,人们依然需要确定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生活世界,不同的社会系统功能以及价值取向依然会在一种共时性的意义上对现代社会的公民及其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通过法律的评价还是通过科技系统的改造产生的。[注]徐冰:《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诠释学进路》,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页。
生活世界总是作为不成问题的、非对象化和前理论的整体性和常识的领域让人们直觉地感知到。[注]参见高鸿均等:《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是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生活世界与分析世界是有距离的。一个是概念化的、简略的、静态式的关系描述,另一个是实践性的、复杂的、动态的生活过程。它们是不同的,但不是矛盾的,任何分析世界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注]参见张静:《“格雷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不论是作为诠释工作的刑事司法,还是作为事实认知系统的科学技术,在普遍的意义上,在与生活世界相对照的意义上,都是分析的世界观。分析的世界观如果不以生活世界的基本样态作为基础,那么现代社会整合问题也就无法实现,或者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会由于分析世界观中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而肢解。因此,在笔者看来,通过系统论分析刑事司法与科学技术运作逻辑的区隔,并不意味着在规范的意义上肯定两者“分离”状态的正当性,而恰恰是在对两者运作逻辑有了充分辨析的基础上,再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视角,论证两者视域融合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必要。生活世界的基础性构成意义不但说明了科学技术与刑事司法融合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同处于共时性社会背景下的两种社会子系统运作中结构耦合的可能性及其形态特征。
四、关系性纲要:破解司法中科学认知的难题
如前所述,生活世界为刑事司法与科技系统的结构耦合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两者都建立在人们对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理解之上,因此两种系统中确立的客观认知标准也都具有了一定的主观性。科学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与人文、社会科学共享的对社会的理解。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突破现有的证据认定框架和诉讼两造的对抗模式,则是建立系统间结构耦合的可行途径之一。法官不仅应当承担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而且作为认知开放的刑法体系的行动者,法官应当主动学习,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引入法庭的独立证人。[注]Gibbons, John. Forensic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 Wiley-Blackwell, 2003. p.129.在信息时代,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法官也可以自主地对待证事项进行认知和学习。当然,为了保证司法过程的中立性和公开性,上述由法官和法庭独立展开的针对待证事实的调查应当向控辩双方公开,在诉讼对抗中建立双方乃至三方的合作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事人进行主义”“法院消极中立”等理论或原则,应当持谨慎态度。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以及制度耦合上的推进,体现了生活世界的维度对法律分析的影响。
在我国,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关于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相关规范),为这种制度结构上的耦合提供了支撑。在哲学认识论上,我国司法始终贯彻“实事求是”原则,法官认定事实的方法和范围,都不受主体行为和要求的局限。[注]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实践中,完全可以在保证诉讼程序公平性的前提下,扩展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扩大适用的频率。比如,在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依职权调取证据,就和权利实现紧密相连,这正如有文件强调的那样:“发挥专家辅助人员作用,适当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注]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7/content_5269267.htm,2018年9月27日访问。当然,除了依职权取证,“组织”这种社会沟通形式,在构建不同系统之间稳定结构耦合上,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比如在我国,律师协会这一组织及其享有的一定国家政策层面的优待,对于律师获取专业证据而言,是具有益处的。
受到上述实践的启发,笔者认为,系统理论提出的现代司法的关系性纲要构建对解决科技与法律结构耦合问题具有理论意义。[注]See Willke, Helmut. “Three Types of Legal Structure: The Conditional, the Purposive and The Relational Program.”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3 (1986): 281;Teubner, Gunther.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83): 239-285.关系性纲要(或者说法律规范中的这种新模式),是基于如下对现代法律形式与功能的思考而涌现的:法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线的,或者说,在规范设立与社会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律,规范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偶然存在的。现代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为自身系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运作提供一种普遍的背景知识,而不直接涉及系统内部的具体操作。在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与实践的法律系统中,法律结构应当在非线性的模式下重新进行思考。对于法律实践的再生产,结构既不是无关的,也不是决定实践的要素。结构与法律系统运作状态的具体关系将会在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实证科学认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的一种统合的、综合的系统观念应当被重新考虑,法律的实际运作是复杂的、地方化的,并且充斥着各种矛盾。[注]See Teubner, Gunther, ed.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Vol. 3. Walter de Gruyter, 1986. pp.183-184.关系性纲要超越系统设定的框架和结构,与全社会范围的“可理解信息的传递”这样一种日常语言(生活世界的)成就相联系。[注]See Cournand, Andre F., and Harriet Zuckerman. “The code of science. Analysis and some reflections on its future.” Studium generale; Zeitschrift für die Einheit der Wissenschaften im Zusammenhang ihrer Begriffsbildungen und Forschungsmethoden 23.10 (1970): 941. 参见Winch, Peter.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8.当然,任何一种更具反思性的理解,都必须以活动的参与者所具有的非反思性的理解为前提。理解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注]同前注⑧,张庆熊书,第163页。日常语言构成了一种在全社会循环的语言的开放媒介。[注]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本),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31-432页。关系性纲要将法律变成促使各系统自我改变的催化剂,促使系统完成“反思”目标,[注]参见前注,高鸿钧等书,第251页。即一种“会学习的法”。[注]参见前注,季卫东书,第175-176页。
关系性纲要所组建的法律形态被系统论法学研究者称之为“反思型法”。“反思型法”把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的“社会组织原则”联系在一起,并且检验这一关系的“社会充分复杂性”。“反思型法”旨在构建一个“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共同演化的更为全面的模型。就系统内部的运作而言,“反思型法”强调法律实质理性的局限和直接控制手段的谦抑,转而诉诸组织、程序、授权等间接、抽象的规制手段。就外部而言,“反思型法”尊重外在于法律的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在法律治理中引入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有益力量,并试图实现它们的协调与整合。“反思型法”既非寄托于“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社会秩序”,也不主张依赖看得见的法律干预对其他社会子系统直接加以型塑,而是提倡“受规制的自治”。[注]参见谭冰霖:《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社会系统功能分化条件下产生的“反思型法”旨在促进社会子系统积极的自我学习,同时试图以辅助性、后设性的法律规范弥补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功能运作中可能面临的缺陷。“反思型法”存在的正当化理由在于协调由各种社会循环系统决定的社会合作形式。“反思型法”的外在功能并非为社会子系统投射统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规范性整合”,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运作为所有社会子系统构造内部的程序和组织机制,从而为功能分化社会的系统整合创造法的结构性前提。
关系性纲要意味着法律不直接进入对各种证据和事件的判断,而是将其交给其他社会系统完成。关系性纲要试图通过建立一般性的程序规范来弥合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理性的差异。这被托依布纳称之为社会的“补偿系统”。作为社会补偿系统的法律及其纲要构建能够为其他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运作提供补偿机制。在这种模式下,法律系统的运作承受双重限制:整合法律系统外部环境需求,但不破坏法律系统自身以及其所“补偿”的社会领域,即其他社会系统(也就是法律系统的环境)的自我再生产。[注]See Teubner, Gunther, ed.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Walter de Gruyter, 1986. p.316.关系性纲要所展现的法律规范不再是禁止和激励,而是“程序性的规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参与关系性纲要的构建。法院对关系性纲要的构建与决策都要全程参与,以弥补当事人之间信息和经济资源的差异。[注]See Teubner, Gunther. “Autopoiesis in law and society: a rejoinder to Blankenburg.”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84): 291-301.对于事实的构建在关系性纲要中采取系统间“合作”的混合沟通模式。[注]See Capps, Patrick, and Henrik Palmer Olsen. “Legal autonomy and reflexive rationality in complex societies.” Social & Legal Studies 11.4 (2002): 547-567.不过,上述改造是法律系统内部的构建,因此最终的判断结构依然通过法律的符码(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呈现。
关系性纲要对于简化当下刑事司法中面临的技术事实的复杂性具有益处。人们通常认为在控辩双方之间,特别是在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双方的合作是对双方利益的减损。然而,在系统理论看来,刑事司法的过程并无预先设定的模式,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变化(增加),竞争性与对抗性的刑事司法过程就发现案件事实而言并无益处。将“事实”问题理解为各种系统参与进来的合作,而非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对于司法正义的实现具有助益。关系性纲要可以化解或者缓解对刑事司法各个阶段进行监督的成本,而将如何分配参与者的角色与功能作为核心问题对待。关系性纲要的构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刑事司法中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查证事实中的权力分配,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对各种社会系统认知的尊重,并且分配事实认定责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刑事司法各方的合作,同时尊重生活世界中的各类“地方性知识”。因为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常常表现为“去地方性”的, 但科学知识其实是把一种地方性扩展(加以改造)到其他地方而已, 是一种地方性征服另一种地方性的过程。[注]参见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1期。这种将科学知识视为确定的、普世的知识的立场,并非现代科学精神(反思与批判)的本质。
在刑事司法中,制度构建者与实践者对此已有所反思。例如,美国通过大陪审团进行的案件与证据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作性”的司法模式,打破了专业人员对司法决策的垄断,使得司法与地方性的个体情感与交往方式相联系。[注]Washburn, Kevin K. “Restoring the Grand Jury.” Fordham L. Rev. 76 (2007): 2333.“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团享有法外开恩的特权,可以置既有法律不顾而径直宣告被告人无罪。这种制度能够使社会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同时,避免对不具有可谴责性的被告人进行实际惩罚,成为普通法体系内特殊的救济渠道。”[注]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1页。基于系统结构耦合形成的关系性纲要,包括法律与科技系统的互动,可以借鉴现有制度进行扩展和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社会”,面对网络时代的责任认定难题,关系性纲要提出的思路和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