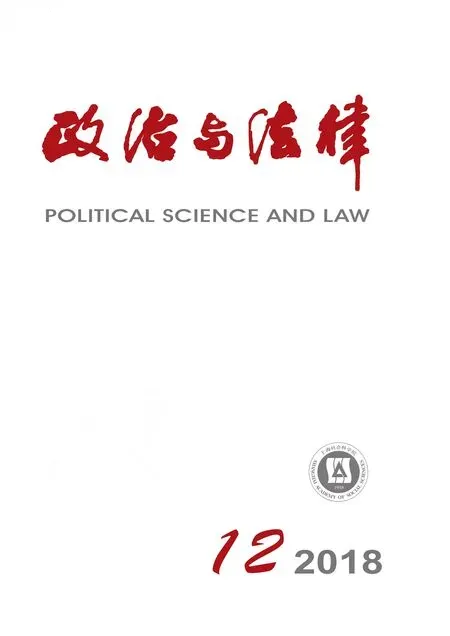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91)
法律是一套由规则组成的体系,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公认的常识。这不仅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的直观印象,而且得到了经典法理学家的肯定。例如,凯尔森在纯粹法理论中,将法律科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规则”,因此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法律规则的体系”。①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哈特虽然注意到了众所公认的权威法学家之间关于法律定义的不一致,因此认为界定法律的概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仍然认为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是确定无疑的事情。②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德沃金虽然质疑法律是仅仅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并提出了原则命题来挑战“规则模式”,但在他的“规则+原则”的理论法体系模式中,规则仍然是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基础性架构。③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0页。应该说,法律是一套主要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几乎已经成为了法理学界公认的、具有类似于“公理”地位的教条。
笔者于本文中试图挑战这个法理学领域众所公认的教条。追问与回答“法律是不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这一问题,本质上就是追问和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规则体系论不过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法律观。该命题包含了两个关键词,即“规则”(Rule)和“体系”(System),[注]传统的法理学倾向于将“system”翻译成体系,这恰好对应于其将“规则”(rule)看作是法律的基本单位。如果在法社会学的语境中将“法律事件”看作是法律的基本单位,则似乎将system翻译成“系统”更为合适。笔者于本文中,在规则系统论语境下,一律将System表述为“体系”,而在“自创生系统”语境下,一律将System表述为“系统”。其各自代表了组成此种法律观的两个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分命题:(1)规则是法律的基本单位,人们通常是通过“规则”的概念与意象来理解“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2)由于法律的基本单位是“规则”,而法律又是众多法律规则所构成的整体,因此法律就被理解成由众多法律规则集合而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就是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或者无矛盾性。为了维护法律体系的此种无矛盾性,人们甚至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冲突规则”和法律解释的技术来消除实践中出现的规则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通常,此种规则的一致性与无矛盾性要由隐藏在规则背后的少数几个基本原理或者公理所支撑与保障。
笔者于本文中将分别从“法律的基本单位”(规则论)与“法律的体系”(体系论)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对“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这个命题进行严格的社会科学意义的分析,从而促使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做出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反思。通过分析与论证,笔者在两个层次上都得出了与规则体系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法律基本单位的层次上,笔者认为组成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法律事件”而非“法律规则”;在法律体系的层次上,笔者认为从社会科学的眼光看,Legal system的基本含义并非是诸法律规则之间的无矛盾的一致(融贯)的体系,而是以诸法律事件之间所构成的条件化的具有自我指涉性质的系统。
需要预先交待的是,笔者对“法律规则体系论”的质疑与挑战,并不意味笔者认为规则不重要,或者法律体系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这个看法完全错了,笔者主张的真正观点是,从更为严格的社会科学分析来看,存在着一种比规则体系论更好的观察和理解法律的视角。将法律界定为规则的体系,虽然有其便利之处,但其本身乃是一种“前科学”阶段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因此有可能在人们对法律进行更深入观察时成为某种“认识论上的障碍”(obstacles epistemologiques)。[注]关于“认识论上的障碍”概念,参见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1995, S223。与此相反,如果人们将法律系统看作是一种由法律事件之间根据某种条件化限制而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甚至是某种具有自我指涉性质的复杂系统,则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律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以规则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单位:利与弊
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应该是最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由直觉形成的法律形象的。所谓规则,就是规定什么事情是人们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人们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人们不可以做的,并分别为它们赋予法律上后果的一般性的规范陈述。[注]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来看待和理解法律的:法律告诉人们什么事情他们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他们是不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做的。通常,这些规则被写在纸面上,由某个权威的机关通过特定的程序制定和颁布。一旦人们不遵守规则,就会被国家强制要求服从。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并非是挑战人们的常识,指出人们日常的观念是错误的。笔者于本文中讨论语境是科学的语境,而不是常识的语境。一个概念在科学语境中的准确含义,与该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语境中不一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正如大卫·莱昂斯曾经指出的:“我们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观念,只是作为这个世界真实组织方式的第一近似(first approximations)。它们易受其他观念的修正或取代,而这些观念取决于科学理论的成功发展。”[注][美]大卫·莱昂斯:《伦理学与法治》,葛四友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5页。例如,水这个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通常指的是“无色无味的液体”,但是在科学语境中,并非所有无色无味的液体都是“水”,水也并非总是呈现为“液体”的状态。
当然,将法律看是一种规则体系,其优势并不仅是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而且有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分析的实用价值。例如,许多规则体系论者认为,法律规则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法律规则承担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规范、指引与评价。[注]See Andrei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法律据此可以规范人们的行动,尤其是划清彼此行动的界限,促进社会秩序,增进各种公共的福利。又如,法律通过禁止性的规则,阻止人们去从事那些对其他人或者公共福利有害的行动,通过授权性规则,鼓励人们从事那些对他人或者公共利益有益的行动。这样一种关于法律规则功能的分析,就很符合社会科学分析的思路。[注]对此,可以参考拉兹对法律功能的分析。参见[美]约瑟夫·拉兹:《法律的功能》,载[美]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性》,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56页。
然而,如果我们用更严格的社会科学分析的眼光来观察,往往又觉得此种规则论很难满足社会科学分析的需要。大卫·莱昂斯就指出,社会科学的功能分析往往会突破法律概念理论家所划定的“界限”,从而提出规则论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如果法律的社会功能是“指引社会行动”,则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宗教,甚至语法的规则,都能够指引人们的行动,那么,规则指引的功能又何以能够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区别开来呢?[注]参见前注⑦,大卫·莱昂斯书,第64 页。
将法律看作是一种规则体系,还存在着更大的困难。例如,许多人都发现,作为一套规则体系,法律未必总是会被人遵守。不被人们实际遵守的规则,尽管被清楚明确地写在纸上,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实际的效果。早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特别地指出这一点。为了弥补法律概念的这个缺陷,早期法律社会学家(如艾利希)提出了“活法”的概念。[注]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方法——关于活法的研究》,张菁译,《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他看来,只有被真正遵守,并体现在人们行动中的法律规则,才是真正的法律规则。庞德也区分了“写在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行动中的法律规则”,强调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体现在行动中的法律规则。[注]Roscoe Pound.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American Law Review(44),1910, pp12-36.
规则体系论并非没有对这个难题做出回应。为此,凯尔森就做了很重要的努力,通过区分“规范有效性”(Validity)与“事实有效性”(efficacy),他指出,个别规范在事实上是否被遵循,并不影响法律规范的效力,因为刑法中规定盗窃罪规则的效力,并不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盗窃分子都被正式抓捕和判刑为前提。只要法律体系整体是有实效的,那么个别规范的有效性就不受影响。也就是说,法体系中个别规范在具体时空中的暂时失效,并不意味着该规范是无效的。[注]参见前注①,凯尔森书,第44页。
凯尔森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它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凯尔森的工作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当人们判断认为一个法律命题是真实的,其条件是什么。[注]Andrei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法理学,都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关。凯尔森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基础规范理论”,哈特则通过“承认规则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凯尔森还是哈特,都预设了某个法律命题的真实性条件,都承认了某种法体系整体的实效性,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判断,从整体上讲,法体系是被人们遵守的。
然而,这个预设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在凯尔森那里,这一点是含糊的。这导致在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中,凯尔森很难将真实世界运行的法律与他所凝练总结出来的纯粹法学的知识体系区别出来。相对而言,哈特试图通过承认规则来进一步澄清法体系整体有效性的含义。在哈特的承认规则的理论中,法体系的整体有效性意味着,法体系中执行规则的官员们,在何谓有效规则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惯习性的共识。[注]参见前注②,哈特书,第110页。这意味着,法体系的整体有效性,与法体系规范的主要对象,即守法者而言,关系不大,主要是执行者是否接受了法体系。因此,哈特可以设想一种类似于羊群治理的法体系:守法者类似于羊群一样被动遵守,而执法者对法体系则是主动接受的。[注]参见前注②,哈特书,第111页。这样一种法律体系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审判规则论”,而哈特在分析“法体系的多样性”时,批判了凯尔森的此种审判规则论,而提倡一种“行为规则论”,[注]参见前注②,哈特书,第89页。就像哈特曾经列举的体育比赛的例子:体育比赛中可以没有裁判,人们仍然可能按照规则进行游戏。[注]参见前注②,哈特书,第40页。
总之,当人们谈论法律体系时,人们不是在谈论一套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动与生活无关的抽象规则体系,人们谈论的是一整套能够体现与贯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发生作用的法体系。如果将法律体系仅仅看作是一套规则的体系,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法体系的此种含义。恰恰是由于规则体系论的此种缺陷,随后人们发展出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法治”的概念。在法治的概念中,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再限于一种纯粹的“法律规则体系”,同时该概念也包含了这套规则体系事实上被遵守和贯彻,也就是说,法治意味着作为规则体系的内在价值的实现。[注]参见陈景辉:《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事实上,当人们说法律的内在价值时,其实并非是在“单纯规范体系”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法治的意义上说的。如此一来,一种纯粹“规则体系”意义的法律概念,就是不够的。因为一种包含内在价值的法律观,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规则的体系”,而且包含着这种规则体系以一种特定的程序与方法被法律官员们解释与适用,同时也意味着这样一套规则体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注]参见前注⑨,约瑟夫·拉兹书,第183-199页。
然而,即便人们可以通过法治的概念来弥补法律规则论的缺陷,将法律看作是一个实际上被遵守和执行的规则体系,仍然无法回避一个严重的不利后果,就是在方法论和概念上,法律科学无法实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将自己研究的对象设定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事实,但作为一种规则体系的法律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待适用与遵守的规范的体系,因此是“反事实”的。整个法律教义学乃至整个法律人的作业体系基本上是在此种规范性预设下发展起来的。法治似乎强调了法律的实效性,但实际上往往被看成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这造成了法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范畴对立与隔阂。如果法律科学要实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两者就必须在一个同样的范畴中,这就意味着,法律的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法律人工作前提的,有待解释与适用的规则体系”,而是同时包括了法律人解释与适用法律规则的实践,人们日常生活遵守并将规则适用于自身的生活实践等现象。因此,如果仅仅将法律的概念局限于“一套规则体系”,那么就很难用一种严格科学的方法去探讨诸如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一系列对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特别重要和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将法律看作一种规则系统,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将法律仅仅局限于当下有效的法律,而无法将过去有效的法律也包括在法律的概念中。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将法律仅仅局限于当下有效的法律规则,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从一种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过去的法律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并且此种“事实性的存在”毫无疑问也具有法律的属性,否则法律史这门学科就应该取消。那么,一种能够同时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法律概念装置,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事件”作为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
笔者挑战“法律是一套规则体系”命题,乃是因为笔者认为,规则也许是法律必要而不可替代的要素,但它并非法律唯一和充分的要素。要定义法律的概念,就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层面,而是要进一步看到,法律同时意味着某种“社会事实”的存在。无论是艾利希的“活法”概念,还是庞德的“行动中的法”概念,都包含着对法律的此种理解。然而,如何捕捉法律所包含的“社会事实”的因素,并将其概念化,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例如,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法律与人们的行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对人们的行动的研究,将法律对象化为某种研究对象。这样一种研究进路的优势是,克服了法律的规范有效性与事实有效性的二元分裂,从而将对法律的研究建立在“事实有效的法”基础之上。同时,由于主流的社会学研究建立在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将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法律与人们的行动结合起来研究便可以参考借鉴大量的社会学的成熟研究方法与手段。艾利希的“活法”理论以及庞德的“行动中的法”理论,就是此种理论研究的出色代表。近年来国内兴起的“社科法学”,几乎也都是在行动理论的框架下对法律展开各种研究。
相对于规则理论,行动理论虽然有其天然的优势,但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天然缺陷。其中一个缺陷是,行动理论及其所运用的社会学方法论工具箱,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社会行动的因果关系解释的基础上的。对行动理论来说,通过行动所显示出的某种行动之“前因”与“后果”稳定关系,就构成了某种对行动进行说明和解释的“法则性”。此种实证研究的因果关系的“法则性”,与法学研究中的法律的规范性,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行动理论虽然能够克服规则理论的实效性难题,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遗失了法律体系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即法律规则的规范性。[注]参见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如果无法以行动为基本单元对法律系统进行观察,则剩下的一个选择,似乎就是以“人”为单位对法律系统进行观察。比较法或者法史学的研究往往采用这种进路。例如,不少比较法研究往往以法律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的实践的描述与研究,来比较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差异。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法律的自主性被看作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主性。[注]Richard Lempert, the Autonomy of Law: Two Visions Compared, in: Gunther Teubner (ed.), Autopoietic Law: 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Berlin 1988, p. 1 52-190.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则被看作是法治的发展。[注]Richard Abel,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Dispute Institutions in Society”,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8, No. 2 (Winter, 1974), pp. 217-347.同样是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法治被看作是法律人之治。[注]参见程燎原:《“法律人”之治:“法治政府”的主体性诠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2期;孙笑侠:《法治乃法律人之治》,《法治日报》2005年11月16日,第10版。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的差异,则被进一步归纳为法律人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差异。[注]参见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由此产生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究竟是法律人由法律体系所定义,还是法体系是法律人这个身份带来的结果?例如,一个法官在钓鱼,虽然这个活动是一个法律人从事的活动,但这并不是一个法律事件。甚至,一个法官在上班路上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也未必是一个法律事件,因为法官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会选择私了。与此相反,当事故发生后,法官停下车,与事故的另一方讨论该交通事故的过错与责任等问题时,这才是一个法律事件。[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66.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官还是法院,都不可能是法律系统的某种基本要素。因为如果没有法律事件发生,法院不过是一座建筑设施,法官则不过是在这座建筑设施中工作的人而已。
上述讨论给我们的启发是,也许可以将“法律事件”当作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通过对法律事件的观察,来观察法律体系的运作、结构与特征。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例如,与法律规则相比,法律事件并不是一堆废纸,而是切切实实的、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因此,将法律事件当作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就不会存在“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分离的问题。同时,与法律行动和法律主体一样,法律事件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因此也可以用社会科学的工具与方法予以观察、测量与评估。
将法律事件作为法律的基本单位,这样一种理论策略选择与社会学理论相对应,超越“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行动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等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陈规陋见,将“事件”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进行的重新定位与选择。将“事件”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并非笔者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以在20世纪后半叶广泛发展的社会学为内在理由和根据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就曾经提出了以“事件”作为世界的基本单位,将事件之叠合形成的过程当作世界的“实体”进行研究和观察的想法。[注]参见[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海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随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多部重要的哲学文本中都专门对“事件”(Ereignis)做出分析和阐明,由此使得“事件”的概念成为受海德格尔哲学深刻影响的法国哲学的关键词汇,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德里达、马利翁、巴迪欧等人都对“事件”的概念做出了深刻的阐述,随后,“事件”这个概念又渗透进了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文艺理论等诸领域。[注]参见[法]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盛宁译,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邓刚:《论马里墉和巴迪欧的事件概念》,《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限于篇幅与主题,笔者不准备对“事件”的概念做一个详尽的概念史的分析与梳理,就本文论证的主题而言,大致可以从“事件”哲学那里,了解到事件的一些基本的性质与特性。首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给人们的启示是,人们未必只能在“实体”的意义上来观察“事实”,而是也可以在“事件”的意义上观察事实。如果从事件的意义上来观察事实,事实其实就是由无数的事件所组成的过程。[注]卢曼系统论法学对“事件”的理解,就深受怀特海的影响。参见Armin Nassehi, Die Zeit der Gesellschaft: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Zeit,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1993, S185。其次,法国哲学家对“事件”的分析,着重强调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关系。结构主义的思潮,最早出现在人类学领域,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也继承了结构主义的思想。结构主义强调静态性结构的稳定性,个体与事件的逻辑和命运是结构所规定的。例如,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原始人婚姻制度和图腾现象的研究,试图发现原始人社会普遍而隐蔽的结构性法则。[注]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2),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8页。结构主义是共时性的,强调的是结构对时间的抵抗与超越。德里达等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赋予“事件”以历时性的结构,强调事件的突发性、自我生成的性质,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关系的偶联性。例如,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事件。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从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的既存社会状况中,很难分析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因此,作为一个事件,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很难预测的。[注]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44页。
如果用这样一种概念与分析的框架来观察法律,那么,法律就既不是法律人所组成的整体,也不是法律人的行动所构成的整体,而是由无数法律事件构成的关系整体。由于整个世界的基本单元就是事件,而非各种静止的“实体”,对世界的观察,本质上就是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及其绵延集合的观察。
这样一种事件视角的观察,也是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例如,当人们试图去了解某个人时,人们往往会从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的经历与过程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与特质。同样地,当人们要了解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时,对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往往能够提供很多帮助。甚至当人们试图去解决某个问题时,也会尝试去了解问题发生的背景与过程,以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些实践,都可以看作是事件世界观的体现。
将法律看作是一种事件,而非一种行动或者行动的主体,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事件的概念本身是突破因果关系范式的,因为事件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自我生成”的含义。正如马利翁曾经指出的,事件是时间化存在,与“空间实体”意义的“对象”不同。对象是在空间里存在的,哪怕我没有看见,它也占据着某种空间的点,因此是可以被事先预见的。然而,作为一种在空间中的存在,事件在发生的同时就旋即消失。事件是一种瞬间的存在,它并不永恒地占据某个空间的点。[注]参见前注,邓刚文。也就是说,人们并无法通过物理实体所占有的空间的“广延性”来理解和把握事件的概念,而是应该通过时间上的“绵延不断”来理解和把握事件的概念。因此,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发生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具有无穷的可能性。事件最独特的性质,往往是它超出预先估计,“满溢出来的”那种全新的视野与可能性,既给人们带来惊讶(这种惊讶可能是惊喜),也可能带来风险。[注]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87, S47.由事件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将事件作为法体系的基本单位,则法体系就已经为未来的变化预留了无数的可能性,这样,法体系的开放性与适应性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同时,由绵延的法律事件组成的法体系并没有如同行动理论范式的法律理论那样,失去规则体系的诸多优点。例如,如果将法体系的基本单位看作是法律事件,那么法律事件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对何谓合法、何谓非法问题的沟通。例如,在前述法官遇到交通事故的例子中,事故双方围绕着事故中法律责任的归属的沟通,仍然坚持了法律的规范性内涵。
将法律体系看作是由无数法律事件组成的一套体系,基本上可以克服将法律看作是由规则所组成的一套体系的观点所存在的三个基本缺陷。首先,由于法律事件是一个事实,它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基本上不存在着规则体系必然存在的实效性问题。其次,由于社会世界是由无数的社会事件组成的,法律事件与其他社会事件之间,在性质上是同一层次的实体,因此相互之间是可比较的。例如,经济事件、政治事件、教育事件等,都属于事件,因此相互之间在观察工具与手段方面,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就像桌子、椅子、石头、金属等这些不同实体,可以用一套相同的概念与工具进行描述与比较一样。最后,对事件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可以作为事件而存在,而不同事件的属性当然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重新理解法律的系统性与统一性
在分析了规则体系说的利与弊之后,就可以在新的视角下,使得将法律看做其他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一套规则体系,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规则体系说基于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性而带来的那种“自然正确性”的错觉,在一种更为客观和严格的科学语境下被破除了。这就为进一步考察“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语境。
1.10.1 线性范围 按 1.8 和 1.9 项的方法制备标准曲线,平行操作 5 份,同时平行处理 5 份空白脑脊液样品作为测定本底值,按 1.6 和 1.7 项的 UPLCMS/MS 条件连续进样分析,以对照品浓度(X)为横坐标,5-羟色胺和 5-HIAA 扣除本底后的峰面积与内标的峰面积比值(Y)为纵坐标拟合回归方程。
然而,尽管将观察的目光从“法律规则”移向“法律事件”,使得对法律的社会学观察成为可能,但如果观察法律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层次,而无法从“基本单位”的层次上升到“系统”的层次,则对法律的观察就仍然停留在“还原论”的层次,从而错失了认识作为“复杂巨系统”存在的现代法律系统。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曾经深刻地受到了法国“事件哲学”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结构学派”与“事件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并且在“事件哲学”的刺激下,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但“过程-事件”式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仍无疾而终。在中国的“关系-事件”范式社会学研究鼎盛时期,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深受其启发,同样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学术品质的研究成果,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理学的研究。然而,此种研究进路本身似乎仍然受制于某种根本的局限性,难以持续和深入的拓展下去,因此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经历了研究方法与进路的激烈转型,其后期的许多研究基本上全盘放弃了此种“过程-事件”式的法社会学研究的进路。中国法社会学研究最近十多年的沉寂,与此种“过程-事件”式的研究的溃散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当初轰轰烈烈的中国法社会学“过程-事件”研究学派的悄无声息地自我终止,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与反思的学术事件。
如果借鉴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作为中国过程-事件学派研究的参照系,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事件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之所在:中国的事件社会学研究虽然敏锐地认识到将“事件”作为社会学研究之基本单位的重要性,但过于沉迷于“事件”本身的“偶联性”与“自我生成”的性质,因此大量的研究精力被投入对各种“单一事件”的挖掘、描述与阐释之中,其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是借此对结构社会学的批判与否定。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事件与事件之间不发生任何联系,或者说,无法对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过程与结构的性质做出说明,则无数的单一事件的罗列与累积,并不能带来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启发与发现。通过“参与式的观察+讲故事”这把“手术刀”所进行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呈现出来的无数的法律事件的个案,对于人们认识“现代法律”这个“复杂巨系统”并无多大实质性的帮助。举个简单的例子,尽管现代心理分析已经揭示出,人类的单个意识具有“事件”的性质,复杂多变且相互冲突,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很难用“因果关系”予以确定,但这些意识的绵延却仍然可以构成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形成相对清晰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从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因此,如果人们无法有效地揭示出诸多单一的法律事件之绵延过程所形成的“意义结构”的整体,就很难将“法律事件”与“经济事件”“政治事件”“伦理事件”“教育事件”等其他类型的“事件”区分开来。并且,正如卢曼通过分析一再揭示出来的那样,如果人们从“单一事件”的角度看,很多具体而单一的事件,往往同时包含着“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伦理的”“教育的”等不同的意涵。因此,判断一个事件究竟是“法律事件”还是“经济事件”,往往不能从“事件”本身的“内在限度”中观察,而只能从事件所处的不同“事件过程”或“事件序列”的脉络中才能够看得清楚。[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41.
就此而言,仅仅在基本单位的层次中观察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根本不能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个法理学的根本问题,还必须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绵延不断的过程中,来发现法律的性质,从而认识法律与其他社会事物之间的区别与界限。现代复杂性科学研究早已经表明,虽然还原论是“对这个世界最自然的理解方式”,但还原论在许多复杂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面前,却完全无能为力。例如,天气和气候现象,生物以及威胁它们的疾病的复杂性与适应性,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就都是如此。[注]参见[美]梅拉尼·米歇尔:《复杂》,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在对简单要素的大规模组合中涌现出的复杂现象进行解释方面,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交叉学科研究远远胜过还原论。
此种对复杂系统的交叉学科研究启示人们,对诸如法律、经济、政治、宗教等“复杂巨系统”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对组成系统的诸元素自身内在的复杂性的揭示而实现。恰恰相反,系统的元素的性质本身是通过系统内诸元素之间的关系而被界定。简单地说,系统的性质并不是由组成系统之最小单位的诸元素决定的,而元素之所以成为系统的最小单位,恰恰是由系统决定的。元素作为系统无可再分解的最小单位,其实是指“系统只能通过诸元素的关系化,而不是透过元素的分解与再组织,以构成并改变自己”。[注]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87, S47.
就此而言,一个事件是法律事件而不是经济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事件从属于法律系统,而并非是由于该事件本身内在的法律属性。也就是说,恰恰是该法律事件与其他法律事件之间构成的法律系统的内在关系,使得该事件成为了一件法律事件。中国的事件法社会学研究学派的内在困境,恰恰就在于其虽然发现了每一个法律事件的独立性,但缺乏合适的概念与工具,用来发现与描述法律事件与法律事件之间的关系性。这些研究虽然也强调“关系”问题,但他们所强调的是“事件”内部所蕴含的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并非是指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事件哲学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误解为单一事件中人际关系,此种方法论的误解与置换,大概只能用接受美学来解释了。
然而,恰恰由于事件本身的独一无二性,作为“复杂巨系统”基本单位的“事件”,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是复杂且多样的。因此,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中,就存在着一个“选择”甚至是“强制选择”的问题,因为法律要有效地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就必须在其内部形成“结构化的复杂性”,而不是无限复杂性。[注]关于从复杂性视野对现代法律系统的分析,参见泮伟江:《法律的二值代码性与复杂性化约》,《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因此,法律事件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互为条件化的”,如“对特别元素的包含/排除的规则以及可计数性的条件等”。[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5.为此,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类早期的社会中,各种纠纷往往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如经济的、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手段等等。这个阶段,也是法律、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彼此浑然不分的阶段。[注]参见高鸿钧:《关于传统法研究的几点思考》,《法学家》2007年第5期。只有当纠纷解决超越了“安抚阿克琉斯的愤怒”,而是努力就事件中诸行动之合法性做出裁决时,[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262.人们才可以说,法律系统分化出来了。为了实现这一点,法律系统内部对诸事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限制。例如,对纠纷解决过程做出一系列的“程序性限制”,从而使得纠纷解决能够脱离各种各样的“身份地位”以及“人身关系”的影响。[注]参见[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192页。又如,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在裁判的过程中“压制针对个案和个人进行论证的做法”。[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262.再如,法律系统发展出一整套的概念、原则和技术,用来区分事件中的哪些事实是与法律相关的,哪些事实又是与法律无关的。[注]Niklas Luhmann, Kontingenz und Recht, Suhrkamp Verlag, 2013, S246-248.这些都是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各种限制条件。通过这些复杂的限制条件,法律系统在内部形成了诸事件之间相当稳定的“选择性关系”,从而使得法律系统得以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形成法律系统的“自我同一性”。
最终,这些限制条件都围绕着一件事情组织起来,即法律系统所有的事件都是根据“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码而相互连接起来:如果某事件是作为“合法/非法”的问题出现,则该事件就属于法律系统,如果无此问题,则该事件就不属于法律系统。[注]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ardozo Law Review,Vol(13), 1992, p1428.经由“合法/非法”这个二值代码,所有的法律事件递归性地连接成一个网络,一种具有自创生性质的递归性网络。[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2-54.
如果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由规则所组成的体系,则legal system的概念只能从诸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中进行理解。由此system只能在新康德主义的意义上被假设成是以某种原则为基础的某种建构,即某种“根据一种统一的视角形成的知识的秩序”。[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29.在很大程度上,此种系统观使得法理学将“法教义学知识体系”与“法律系统的系统性”混为一谈,因为此种系统观将“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一致性”看作作为其研究对象之“法律系统内在一致性”的某种映射。隐含在此种观念背后的是这样的想法:“有待认识的事实必须被预设为是无矛盾的。”[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29.因为“加入对象世界本身充满着逻辑上的矛盾,那么关于该世界的任何陈述都是任意的,即,认识变得不可能”。[注]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89.然而,正如批判法学所一再指出的,在真实世界的法律系统中,往往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断裂。[注]参见[美]邓肯·肯尼迪:《判决的批判》,王家国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真实的法律实践并没有按照这些法理学剧本所规定的内容展开。[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29.
与此相反,将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理解成“法律事件”,就使得一种全新的法律系统的观念成为可能,此种观念就将法律系统理解成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质的系统。具体而言,此处所谓的自我指涉系统,就是指“其自身作为统一体生产它们用作统一体的任何东西”。[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31.这意味着,法律系统的“系统统一性”,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则之间的无矛盾性,而是指组成法律系统基本单位(即法律事件)的统一性,同时也指此种基本单位的再生产机制的统一性,因为一个“事件”之所以为“法律事件”,恰恰是由于该事件从属于法律系统,而不是相反。换言之,法律系统之所以为法律系统,恰恰是由于它是由法律事件集合而成的。
此种法律系统观带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后果就是,它揭示出了现代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有时候也称作是法律系统的规范封闭性,即只有法律系统对其内部发生之事件赋予“法律规范性的品质”,并将它们建构为某种统一性,“没有任何法律相关的事件能够从系统的环境中导出其规范性”。[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31.此种法律系统规范的封闭性,通常被法律实证主义理解成以“分离命题”为基础的法律实证性。然而,如果将法律当作以“事件”为基本单位的“法律系统”,则不但能够将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也能够有效地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
关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其实暗含一个更大的主题,即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也可以说,此种将法律当作以“事件”为单位的“法律系统”的观念,为人们进一步观察与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出发点与理论前景。例如,如果将法律看作是一种自创生系统,那么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孟德斯鸠和萨维尼等学者所主张的“镜像关系”,即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并不象征着社会系统的统一性。不过,法律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如沃森等法律移植论者所主张的相互“隔绝”,由此可以随意予以“切割”与“移植”的关系。[注]参见泮伟江:《从规范移植到体系建构:再论中国法律的本土化困境及其出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5期。因为法律系统虽然是运作上封闭的,但在认知上仍然是开放的。法律系统本身也仍然是以社会系统这个大环境为前提而演化出来的,甚至法律系统本身就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本身就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注]Niklas Luhmann,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tem, Rechtstheorie(14)1983, S136-138.也许,相对于“法律镜像论”与“法律移植论”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更有意义的问题其实是以下几个。从演化的角度看,法律系统又是如何从人类社会早期法律、道德、政治、经济、宗教不分的状态中演化并最终分化出来的(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在演化的历史上,此种法律系统的析出,又需要何种特殊而具体的条件?在漫长的人类法律与社会的演化历史中,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与偶然机遇下,形成了这些演化上的条件与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了法律的演化?此种根据“合法/非法”二值代码运作,具有运作封闭性与认知开放性的现代法律系统,在现代社会中又承担了何种特殊化的功能?
四、法律事件体系论的前景展望
“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这是一个既被经典法律理论著作默认,又高度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用语的命题。笔者则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下,尤其是在作为交叉学科研究的“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下,从“基本单位”与“系统”两个层次对这个命题进行了严格的分析与审视。此种理论决断与策略至少为人们分析现代法律提供了优势。尽管如此,此种理论进路并不天然对“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系统”的命题持敌对立场。它承认法律规则论有其适用和展现优势的场所,并构成了人类认识法律的基本角度之一。不过,它同时也指出了法律规则论在对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方面的局限性与劣势。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两者的区别是两种不同观察角度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同,但未必互相排斥,法律系统论可以被看作是对法律规则论的适当补充。这有点类似于科学层面的“日心说”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地心说”之间的关系:虽然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直觉是太阳绕着地球走,并且人们日常生活的安排与作息的规律,也是根据“地心说”的意象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但这并不妨碍“日心说”这样一种违反日常生活直觉的科学理论的成立,且在推动科学理论的进步以及在航空航天、地图导航、气象与地质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同时,即便采用了以事件为基本单位的法律系统论的立场,仍然有许多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完成。例如,事件本身仅仅强调了法律系统基本单位的性质,但本身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因此人们无法对法律事件的内部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突破法律规则论这个认识论障碍,认识到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很可能是一个事件,这仅仅为人们进一步的法律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使得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更为精细和更实用的概念与理论的创新成为可能。例如,卢曼进一步提出了将“沟通”作为社会系统研究的基本单位,并且将沟通界定为“信息-通知-理解”三种选择的统一体,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系统基本单位的认识与理解。[注]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87, S191-241.如此一来,“事件”变成用来描述沟通性质的一个概念,沟通则成了能够被进一步进行分析的概念,这有助于人们理解诸“沟通事件”相互之间的“条件化关系”的具体构造及其理论后果。又如,在将事件作为社会学分析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卢曼进一步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意识流的分析,尤其是借鉴了其将意识运作性(Operativität)的分析,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社会的沟通性事件的分析之中,从而提出了“意义”的概念,将“意义”的概念界定为一种形式和媒介,即实在性与潜在性的统一,从而揭示了诸社会基本单位之诸沟通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意义结构”的关系,开创了20世纪末社会理论分析的新局面。[注]卢曼将意义作为诸社会事件之间关系的基本结构,这样一种理论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以及就此问题与哈贝马斯展开的争论,对二战后德国社会理论研究复兴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与深远的影响,成为二战后德国社会理论复兴的标志性事件。Niklas Luhmann, Sinn als Grundbegriff der Soziologie, in Jürgen Habermas/Niklas Lhu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Suhrkamp Verlag, 1971, S25-100.显然,这些进一步的理论成果,都必须将事件而不是“人”或者“人的行动”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才能够获得。这一点对分析作为现代社会功能子系统的现代法律系统,也是很有帮助的。它使得人们在规则体系论与预测论之外,走出法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总而言之,将法律理解成是由无数法律事件,在某些特定限制条件下构成的关系整体,这就使得一种超越法官与律师等法律人的、社会学的、将法律系统作为一种“复杂巨系统”予以研究的全新的概念与理论工具的发展与演化成为可能。这将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作为现代社会中关键与核心部分的现代法律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以及更进一步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自奥斯汀所著《论法理学的范围》出版以来,现代法理学一直致力于澄清法律与其他社会事实之间的界限问题。[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陈景辉在《法律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所做的细致梳理与分析。多数的法律理论家都希望通过“概念分析”的方法来“阐明与法律系统观念相关联的特定观念,恰当地区分法律观念和可能与之混淆起来的那些密切相关的观念”。[注][美]大卫·莱昂斯:《伦理学与法治》,葛四友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4页。不过,正如大卫·莱昂斯所指出的,以往的这些尝试都不怎么成功。[注]参见上注,大卫·莱昂斯书,第66页。因为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积淀,规则体系观为人们提供的不过是某种常见的观察法律的角度与认识工具,其本身仍然不是人们理解作为现代社会分化语境下“复杂巨系统”的现代法律系统的最佳角度。作为一个前科学的观念,它甚至构成了人们观察现代法律的某种“认识论上的障碍”,也许“对社会实体的科学研究”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更多的东西。
笔者于本文中通过借鉴20世纪影响深远的“事件哲学”资源,将“事件”的概念引入法社会学研究中,并进一步借助包括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内的“复杂性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诸多研究成果,提出应该突破规则体系论、法律行动预测论等理论的视角,将“法律事件”作为法律的基本单位,通过观察法律事件之间的“条件化关系”来观察法律系统。一旦将法律系统理解为无数的“事件”之间通过各种“条件化的限制”连接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就可以通过引入进一步与概念资源与方法论工具,例如“自我指涉系统理论”“象征性普遍化沟通媒介理论”“社会演化理论”、马图拉纳(H. Maturana)和瓦瑞纳(F. Varela)的“自创生理论”、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理论、冯·福斯特(Von Foerster)的控制论意义的“观察理论”等诸多理论资源,进一步地阐明法律系统的特性。事实上,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就是采用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倡的这种理论策略,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诸如“沟通”“意义”“合法/非法二值代码”“代码化与纲要化”“运作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正义作为法律系统的偶联性公式”“法律演化理论”“功能分化”等富有创造力与启发性的概念与理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法律与现代社会的认识。卢曼显然是此种理论进路的先行者,已经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既鼓励研究者继续沿着这个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前进,又为研究者结合中国法律与社会转型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前期研究成果与理论工具准备。当代中国学者当然可以以中国问题意识为中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吸收借鉴卢曼等先贤的研究成果,开拓创新,从而作出中国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