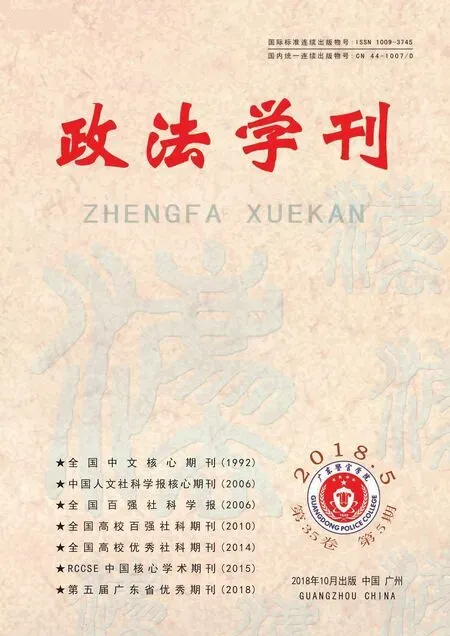强奸罪立法完善之思考
——以2017年日本刑法之修改为切入点
谢 斐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2017年6月23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修改刑法部分条文的法律方案》①日文原名为《刑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平成29年6月23日法律第72号)(下称《修正案》),对日本刑法典进行了修正,其中主要涉及对侵害性自由犯罪方面的修改。日本法务省指出,此次修改是以近些年日本性犯罪发展的具体情况为根据,从案件处理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强奸罪的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八个方面:1)修改罪名名称,改“强奸罪”为“强制性交等罪”;2)由“女子”到“者”,将男性也作为性犯罪的保护对象;3)增加“性行为”的内容,将口交、肛交等也纳入“性交”的范围;4)刑罚幅度变化,将强奸罪的最低法定刑由3年提高到5年;5)增设监护者猥亵罪与监护者强制性交罪;6)废除集团强奸罪;7)废除侵犯性自由犯罪的亲告罪规定;8)完善抢劫强奸罪的规定,将抢劫过程中实施强制性交与强制性交过程中实施抢劫都作为结合犯处罚。本文主要围绕其中三点展开,即强奸罪保护对象的扩大、“性行为”内容的多样化、以及监护者猥亵罪与监护者强制性交罪的增设。
一、强奸罪保护对象的扩大
日本最早颁布的近代刑法是于明治十三年(1880年)颁布的“旧刑法”,其中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强奸十二岁以上妇女者,处轻惩役。其以药酒等物,令人昏睡或迷乱其精神而奸淫之者,以强奸论。”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奸淫未满十二岁幼女者,处轻惩役;若强奸者,处重惩役。”[1]511从其对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的规定来看,“旧刑法”将强奸罪的被害人范围限定为女性。明治四十年(1907年)颁布的“新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行或者胁迫手段奸淫十三岁以上女子的,是强奸罪,处三年以上有期惩役;奸淫未满十三岁的女子的,亦同。”[2]67该条款基本继承了“旧刑法”有关强奸罪的规定,将“旧刑法”有关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的条款合二为一,并且将强奸的手段明确为“暴行或者胁迫”,唯在幼女的判定年龄上有所不同,被害人的范围依旧限定为女性。2017年《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原强奸罪条款修改为:“以暴行或者胁迫手段对十三岁以上的人实施性交、肛交或者口交等行为(以下统称为“性交等”)的,处五年以上有期惩役。对未满十三岁的人实施性交等的,亦同。”本次刑法修正案将强奸罪的被害人范围由传统的女性扩大到“人”,从而将男性也作为强奸罪的保护对象。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强奸罪的保护法益都不是妇女的性权利。在古代中国,强奸罪主要是为了保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在古代西方社会,强奸罪还被视为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唐律疏议》记载:“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诸和奸,本条无妇女罪名者,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通,减奸者罪一等。”[3]421-423对比放在“贼盗”篇中的故意杀人罪(谋杀人)与放在“斗讼”篇中的故意伤害罪(斗殴手足他物伤)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我国古代将强奸罪放在“杂律”一篇之中,而该篇中多为破坏封建纲常伦理、扰乱社会秩序等侵犯社会法益的犯罪。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男女社会地位的严重不平等有关。在古代中国,女性更多的是作为男性的从属和附庸存在,而非独立的社会个体,强奸未婚女子是对父权的侵犯,强奸已婚女子则是对夫权的侵犯。中国古代法律更看重的并非在强奸过程中直接受害的妇女,而是由强奸行为导致的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强奸罪并非为了保护“失贞”的女子,而是为了保护“失贞”女子背后那尊严受损的男子以及整个社会所强调的纲常伦理。强奸只是因为附加了暴力情节而与“和奸”相区别,作为对女子免责、对行为人加重处罚的条件。在西方,强奸罪兼具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男性“财产”的作用。与古代中国相似,希伯来的强奸罪同样是通奸罪的从轻情节,《申命记》规定,对于通奸的男女都要处于死刑,因为双方都给以色列带来了“恶”,而对于强奸已婚女子,则只需处死男子,因为女子在这过程中没有获得救援。可见,希伯来刑法认为通奸会给社会带来“邪恶”,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而在强奸已婚女子的案件中,女子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带来这种“恶”,是因无人援救而不得已为之,因此只需处死男子即可。而强奸未婚女子则从处理财产犯罪的角度加以解决,《申命记》规定,强奸未婚女子的处罚是赔偿其父50谢克尔(古希伯来货币单位)并强制娶该女子为妻,且终生不可休妻。这是基于未婚女子被视为其父的贵重待售商品所作出的判断。[4]570-571尽管强奸在古罗马被视为一种犯罪,但是强奸在古罗马神话传说中是一个普遍而又常见的主题,由此导致古罗马学者对强奸的关注并不在法益本身,而在于如何协调神话中倡导的强奸与法律中禁止的强奸。例如,提图斯·李维指出,将强奸作为犯罪是一种尴尬的选择,对于神话传说的相关内容应当重视其政治层面的救赎意义,他将罗马神话中的“掳奸萨宾妇女”解释为罗马是一个通过合意和条约解决暴力与共存问题的混合民族国家。[5]1-10直到公元前50年,才由伊比鸠鲁派哲学家卢克莱修对强奸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谴责,他将强奸形容为超越先进文明界限的原始行为,本质上是男性的暴力与强加的性冲动。但即使逐渐受到重视,古罗马的强奸罪仍然只适用于那些有良好声誉的女性罗马公民,对于女奴隶的强奸则视为是对奴隶主财产的侵犯。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为了彰显男女平等,女性权利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无论东方、西方,强奸罪都已经成为一项侵犯妇女人身权益的犯罪。现代刑法将女性的性自决权和幼女的身心健康作为强奸罪所保护的客体,但是性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男性的性自决权和男童的身心健康难道就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吗?日本学者指出:“强行实施性行为所造成的身体与精神痛苦在男女之间是共通的,强奸罪的受害人理应包含男性。”[6]1022004年,美军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众,其中就包括林迪·英格兰等三位女兵对男囚性虐待的照片,这一事实更加证明,不仅女性的身体易受侵害,男性也同样如此,而且针对男性的性侵害现象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普遍得多。“一项针对2474名英国男性所作的调查显示,有3%的男性在他们16岁以后有过非自愿性性行为,其中近半是与女性发生的。另外一项针对到伦敦生殖泌尿科就诊的244名男性的调查显示,有18%在成年后受到过性骚扰,而其中48%是受到女性骚扰。他们通常是被迫舔阴(占38%)或性交(44%)。”[7]228我国也同样存在大量男性受到性侵害的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了《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其中第一分册《流氓罪》中就记载了多起性侵男性的案例,例如“吴某鸡奸、玩弄59名学生流氓案①案情如下:被告人吴某辉,男,38岁,小学教师。吴某辉从1971年至1980年10月,在X露小学、X塘小学、X岗小学、X桂小学和X露中学任教期间,利用师生关系,以帮助补课、给学习用品、深夜不便回家留下住宿等手段,将男学生叫至其房间,向他们讲淫秽故事,灌输“性”的知识,进行性的挑逗,继而摸弄男学生的生殖器,吸食精液,鸡奸男学生,还教唆男学生相互鸡奸。10年来,吴先后对59名男学生进行了上述流氓犯罪活动,不少学生被吴玩弄和鸡奸后,精神萎靡不振,有的染上了手淫恶习,有的生殖器和肛门染上了疾病。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作了有罪判决。”。[8]178既然男性的性自决权同样容易受到侵害,为何强奸罪对此不予以保护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与法律皆为男子主导,其区别无非是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质的改变,在男人看来,女人才是值得保护的利益,而强奸罪则为保护这种“利益”制定规则,男人既是这种“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这一“利益”的拥有者,正是男人自己将男性的性自决权排除在了强奸罪的保护范围之外。[9]
时至今日,伴随女权运动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和同性恋逐渐公开而带来的性革命,以及传统强奸罪片面客体保护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这种男强女弱的父权体系对强奸罪立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正在不断减弱。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模范刑法典》的制定,美国各州开始对普通法强奸罪进行改革,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犯罪性别属性的中立”。强奸罪不再对被害人和行为人有性别身份的限制,男对女、女对男、男对男、女对女都可以构成强奸罪,强奸罪成为性别中立的犯罪。[10]92加拿大在1983年强奸、性犯罪法律改革时,同样淡化了强奸罪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性别要求。[11]德国1975年刑法典对强奸罪还有“强迫妇女”的要求,而1998年刑法典对强奸罪的定义则已经变成了“强迫他人”。法国刑法典对强奸的定义同样也去除了性别的要求,根据2005年更新的法国刑法典英文版,对强奸罪被害人的称呼为“person”,而非“female”。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1条规定:“对于男女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它违反其意愿之方法而为性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同样是将强奸罪的保护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了男女。由此可见,日本2017年的修法,对于强奸罪保护对象的扩大化并非突然的“革命性修改”,而是立足于社会变化,在借鉴他国立法修改的基础上做出的稳健尝试,有效地填补了传统强奸罪在保护对象上存在的立法漏洞。
正如上文所列举的案例,我国对此类侵犯男性性自决权的案件,在1997年以前多以流氓罪定罪处罚。1979年刑法规定,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流氓罪的构成要件比较模糊、笼统,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是极易被滥用的“口袋罪”。对于侵犯男性性自决权这种刑法并没有明确保护、但确实存在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以流氓罪定罪处罚是既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又顺应社会民意的下策。1997年刑法将原来的流氓罪拆分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而强奸罪仅保护女性的性自决权,这使得侵犯男性性自决权的行为难以得到法律保护。2010年,北京发生一起强奸男性案件,一名42岁的保安在宿舍内对18岁的男同事实施了强奸,在强奸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轻伤。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提起公诉,法院以同罪作了有罪判决。该起案件为97年刑法修订后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其强奸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轻伤,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只保护了被害人的健康权,而其身为男性所具有的性自决权在被侵犯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救济。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这一系列关于强奸罪“中性化”的改革,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对于男性性自决权的保护确实存在法律漏洞,在法律并无修改的情况下,贸然以强奸罪保护男性性自决权不免有类推解释的嫌疑,只能根据强奸行为造成的其他后果追究刑事责任。例如,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侵犯被害人人格尊严以侮辱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修改使得男性也成为了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保护对象。但这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起点,而非终点,在未来的修法中,男性同样也应该成为强奸罪的保护对象。
二、“性行为”内容的多样化
《修正案》将肛交、口交等行为纳入到强奸罪规制的“性行为”范围之中,而之前的立法只将传统意义上的“性交”作为强奸罪规制的“性行为”。欲厘清“性行为”与强奸罪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性交”一词进行解析。
法医学上认为,性交是指男女生殖器的结合,性交是性行为的一种。从理论上来说,性行为可以分为狭义的性行为与广义的性行为,狭义的性行为就是指性交。广义的性行为包括目的性行为、过程性行为、边缘性行为三类。目的性行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正常的目的性行为与异常的目的性行为,正常的目的性行为就是狭义的性交,即男女两人的阴道——阴茎性交,异常的目的性行为指很多性交变异形式,例如肛交、口交等。过程性行为是性交前后的调情行为,包括接吻、爱抚等唤起性欲的动作和拥抱等减退性欲的动作。边缘性行为,是指界于性行为和其他行为两者之间模棱两可的行为表现。只要行为动机或多或少带有性吸引的驱动力,就至少属于边缘性行为,如眉目传情等为了表示爱慕,或者仅仅是爱慕之心自然流露的动作。边缘性行为有性意识参与或驱动,但暂时不指期待性爱动作升级而朝向性高潮并获得极大性满足,故而具体行动与日常生活的非性行为广泛混杂。[12]595-597社会对于性方式有着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也有一些规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西方社会早期曾将某些性行为规定为非法,认为它们是“正常”性本能的变态,其中就包括口交与肛交。虽然有法律将实施这种行为视为犯罪,但鲜有被审判的案例。同时,据社会调查显示,有过口交行为的人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美国80年代的调研结果表明,80%-90%的人有过口交行为,因此,口交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人口中多数人有过的实践,很难再继续被认定为是违反社会性规范的行为。与此相比,肛交的比重相对较低(约25%),尤其在艾滋病被发现以后,其比重大幅下降,但是资料显示以其他方式刺激肛门来获取快感比肛交的比重高出很多。[13]125-127由此可见,口交与肛交这类“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在社会中并不罕见,而且逐渐摆脱了违反社会性规范的印记,对于这类行为,存在以法律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从刑法理论来看,强奸罪的既遂标准同样立足于“正常的目的性行为”,要求至少存在男女双方生殖器的接触。接触说要求男女双方生殖器存在表皮接触,插入说要求男女双方生殖器有实质的结合,射精说除了要求男女双方生殖器的结合,更进一步要求行为人性欲得到满足后射精。[14]546那对于“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应该如何界定?“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侵害程度不比“正常的目的性行为”要低,两者都具有实质的“插入”行为,不能仅仅因为该“插入”行为并非完全由性器官实施就否定其对被害人性自决权的侵犯。康德曾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5]24犯罪分子也是出于一定的犯罪目的才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性学家李银河将性的意义归纳为七种:“第一,为了繁衍后代;第二,为了表达感情;第三,为了肉体快乐;第四,为了延年益寿;第五,为了维持生计;第六,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第七,为了表达权力关系。”[16]10-11上述七种意义,除了“繁衍后代”以外,“异常的目的性行为”与“正常的目的性行为”并无不同,而强奸犯更多的是为了肉体快乐,为了宣泄变态心理,或是为了表达某种支配欲,很少有将“繁衍后代”作为实施强奸行为的主要目的。更有部分犯罪分子,因身体原因无法实施性交,为了满足自身的变态心理,转而使用其他器具对被害人的口、阴道、肛门实施类似的“插入”行为。若刑法只禁止强行实施“正常的目的性行为”,忽略对强行实施“异常的目的性行为”这种情况的规制,无异于是在放纵犯罪。
在日本今年修法之前,已经有国家和地区注意到了刑法对“异常的目的性行为”的规制空白。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对强奸罪进行实体法方面的改革。《模范刑法典》第213.0条对“性交”和“变态性交”的定义,除了正常的性交以外,还包括口交、肛交以及与动物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性交。基于此,一些州的刑事立法也开始发生转变,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等州的刑法都扩大了“性交”的范围。加拿大刑法典抛弃了传统的“阳具中心论”,转而以性侵的暴力程度划分不同等级,同时将强奸罪更名为性侵犯罪。根据加拿大刑法典,性侵犯罪分为三级:第一级性侵犯罪;第二级性侵犯罪,指的是牵涉武器威吓的性侵犯;第三级性侵犯罪,指的是导致被害人严重受伤的性侵犯。[17]只要满足了罪名中对武器或是受伤程度的要求,无论何种性交形式,都会构成相应的性侵犯罪。法国刑法典规定:“以暴力、胁迫、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质的性侵入行为,构成强奸罪”。[18]95“任何性质”表明法国刑法典对于强奸罪的行为方式同样不再限定为传统的性交,对于“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只要是以暴力、强制、胁迫、突袭等方式对他人实施的,都应受到强奸罪的制裁。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十条增加“性交”的定义:“称性交者,谓非基于正当目的所为之下列性侵入行为:一、以性器进入他人之性器、肛门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它身体部位或器物进入他人之性器、肛门,或使之接合之行为。”直接在刑法总则中将“异常的目的性行为”纳入到性交的概念之中。
日本此次修法,顺应时代形势,与国际刑法发展的潮流接轨,对“性行为”的内容进行了扩大,从传统的性交扩大到了口交、肛交等“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填补了日本刑法的法律漏洞,更加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性自决权。我国刑法对于强奸罪的行为方式仍然限定在“正常的目的性行为”,对于上述“异常的目的性行为”,有学者主张可以通过强制猥亵罪进行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强制猥亵罪的客体是人的性羞耻心,所谓人的性羞耻心是指普通人对于不正当暴露性器官和不正当性行为的羞耻感。正如上文所述,口交、肛交等“异常的目的性行为”随时代发展已经不再是违反社会性规范的行为,逐渐成为两性之间一种正常的性行为。那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对他人实施这类行为就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性羞耻心,更是对被害人性自决权的侵犯。其次,与普通的猥亵行为相比,“异常的目的性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程度显然更高,这种伤害并不比传统强奸罪中的性交要低,以强制猥亵罪规制某些对被害人实施的严重“异常的目的性行为”会出现罪刑失衡的问题。最后,我国刑法的发展,既要考虑本国的国情,又要借鉴域外刑法发展的先进成果。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将“异常的目的性行为”纳入强奸罪规制的“性行为”已经成为新的变革趋势,结合日本2017年对刑法强奸罪的修改,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异常的目的性行为”,而非简单的将其归入猥亵行为。
三、加强对“特殊关系型强奸”的立法规制
《修正案》新设监护者猥亵罪与监护者强制性交罪,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利用自己作为现实的监护人或拥有的影响力实施猥亵行为的,按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者,利用自己作为现实的监护人或拥有的影响力实施强制性交行为的,按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处罚。”该条为注意规定,体现了日本立法机关对于利用监护关系实施性侵行为的这类案件的重视。监护制度设立之目的在于保护行为能力有所欠缺者(包括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的利益。监护人以其对被监护人所享有的监督、教育、保护等职责,往往对被监护人具有较强的人身控制力,相对应的,被监护人往往对监护人具有较强的人身依赖。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性侵行为常常具有的隐秘性,使得利用监护关系实施的性侵案件往往具有更大的侦查难度,从而给被害人造成更长期、更痛苦的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
这类利用监护关系等特殊人身支配关系实施的强奸,与传统意义上的强奸存在一定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熟人强奸”相似。熟人强奸(Acquaintance Rape)是指非陌生人实施的强奸。1982年,《Ms.》杂志就将约会强奸(Date Rape)作为一种新型强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与我们以往对强奸罪的认识不同,并非是那种在深夜或偏僻处突遇陌生人杀出的“陌生人强奸”。拉娜·桑普森将“熟人强奸”分为五种类型:1)派对强奸(Party Rape),也包括轮奸;2)约会强奸(Date Rape),通常发生在受害人或行为人的住所,以及轿车等封闭空间;3)非派对或约会强奸(Rapeinanon-partyandnon-datesituation),例如一起学习、工作时发生的强奸;4)被曾经有亲密关系者强奸(Rape by a former intimate);5)被现在有亲密关系者强奸(Rape by a current intimate)。[19]6“熟人强奸”中,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关系、恋爱关系、同学关系或同事关系,行为人熟识被害人的特点降低了行为人的犯罪成本,也提高了被害人保护自身安全的难度。利用监护关系实施的“特殊关系型强奸”类似于“熟人强奸”的第五种类型“被现在有亲密关系者强奸”。
“特殊关系型强奸”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证明强制手段的困难性。强奸罪以违背女性意志为前提,这就要求行为人为达目的必须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使妇女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而“特殊关系型强奸”主要是利用监护关系、工作上的从属关系等人身支配关系压制女性反抗,这主要是一种非暴力威胁。一方面,并非所有这类非暴力威胁会对女性构成精神强制,也就是说利用人身支配关系不一定构成胁迫;另一方面,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多指采用与暴力、胁迫相当的强制手段,一般包括麻醉或灌醉妇女实施强奸,利用妇女患病、熟睡实施强奸,冒充丈夫或情人实施强奸,利用邪教组织或封建迷信实施强奸等,没有明显胁迫地利用人身支配关系,也没有达到“其他手段”的程度。现有理论很难给这类没有明显胁迫地利用人身支配关系进行定性。
我国刑法理论中,胁迫的实质在于使被害人陷于恐惧的精神压制,从而不敢反抗,至于威胁的形式则不作要求。英美法系则进一步细化了这个问题,将陷于恐惧的精神压制分为暴力威胁(threat of force)和非暴力威胁形式的胁迫(coercion),这种细化处理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殊关系型强奸”的证明难题。利用人身支配关系的暴力威胁当然构成刑法要求的“胁迫”,利用人身支配关系的非暴力威胁是否构成刑法要求的“胁迫”,取决于两个要素:威胁内容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大小和威胁内容本身是否合法。两个要素所占权重的不同,会让同一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以宾夕法尼亚州诉穆利纳里奇①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v. Joseph Mlinarich一案为例,被害人14岁,曾经因盗窃嫂子的钻戒而受到其兄长控告,被法院送进少年犯教养所。被告人与被害人一家为邻居,彼此熟识,被告人妻子建议让被害人住在自己家,由她和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临时家庭监管。通过听证会,被告人夫妇成为被害人的临时监护人。在此期间,被告人多次猥亵被害人,并以将被害人送回教养所相威胁,迫使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如果主要考虑威胁内容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大小,那么在这种利用监护关系的威胁中,被害人只要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作出选择,就不构成胁迫。本案中,被害人虽然遭到了要被送回教养所的威胁,但她完全可以选择回教养所而不接受强奸,这种利用监护关系实施的威胁尚未构成胁迫。如果主要考虑威胁内容本身是否合法,当这种利用监护关系作出的威胁内容没有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就不构成胁迫。本案中,被告人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在被害人并无过错时威胁将其送回教养所,这种威胁已经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而构成胁迫。如果对这两种要素采取折衷态度,即违法的威胁如果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小,也不构成胁迫。本案中,威胁的内容确实违法,但是被害人仍然有足够的意志自由进行选择,因而不构成胁迫。但即使以这两种要素作为标准,被害人面临的压力是否会影响其选择,依然取决于法官与陪审团的主观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特殊关系型强奸”里是否存在压制妇女反抗的情节存在一定的认定困难,由此导致了对这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困难。如果将“特殊关系型强奸”以注意规定的形式加以确认,则使证明的关键从有无胁迫转移到是否利用这种人身支配关系影响被监护人的自主意识,大大降低取证难度,更有利于追究这类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特殊关系型强奸”比起一般的强奸也有着更强的危害性。其一,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特殊关系型强奸”在性侵儿童案件中格外突出。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超过七成的是熟人作案,案件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27.33%、邻里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12%、家庭成员10%。[20]其二,“特殊关系型强奸”会给被害人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更容易诱发恶性刑事犯罪。“特殊关系型强奸”中,因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特殊人身支配关系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案件被曝光的难度,还使被害人更难进行反抗。而且这种特殊关系还会使被害人在案发后陷入控告与否的两难境地,更进一步加大了被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难度。一旦被害人选择沉默,常诱发行为人再次作案,对被害人造成重复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借助特殊人身支配关系实施强奸,会使被害人对亲情、爱情、友情等人类良好情感的期待逐渐破灭,从而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像枥木杀害亲父事件a那样的恶性案件。
“特殊关系型强奸”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部分国家的重视。德国刑法典在第十三章“妨害性自决权”中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对被保护人的性滥用”,该条规定将三类人列入到“被保护人”中,包括:受自己教育、培训或监护的未满16岁的人;受自己教育、培训或监护的未满18岁的人,或在职业或工作上与自己有从属关系的不满18岁的人;自己未满18岁的亲生子女或养子女。惩罚范围包括与被保护人发生性行为和对被保护人进行明示的性挑逗与性变态行为。可见德国对于这种基于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实施的特殊关系型强奸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态度,不仅禁止与被保护人发生性关系,更禁止为了获得性刺激而在被保护人面前实施性行为或让被保护人在自己面前实施性行为。法国刑法典将“特殊关系型强奸”的相关情节作为强奸罪与其他性侵犯罪的加重情节,包括两种情形:由合法直系尊亲、非婚尊亲或养父母或其他对受害人拥有权力的任何人实施;由滥用自身职务赋予之权势的人实施。美国格外重视对“特殊关系型强奸”的预防,主要体现在预防性骚扰与预防家庭暴力方面。例如,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指挥官负有指挥海岸警卫学院负责人制定适用于学员的防范性骚扰与性暴力政策,其中包括提高学员对强奸、熟人强奸和其他性犯罪的认识。除此之外,一般的大学也负有提高学生对强奸、熟人强奸、家庭暴力、约会暴力的认识之义务,并有责任对上述危害行为采取初步的预防措施。如果违反该义务,疏于对学生在这方面的保护,受侵害的学生有权利对学校发起诉讼,并要求赔偿。美国也将“熟人强奸”纳入家庭内部与熟人之间的人际暴力之中,并授权疾控中心采取措施预防并减少这类暴力。
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立法缺陷。以利用监护关系实施的“特殊关系型强奸”为例,一般而言,只有未成年人与成年精神病人存在法定监护人,其中对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实施强奸,不管是否存在监护关系,都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对于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成年精神病人,并没有相关的特殊保护,“特殊关系型强奸”并不在强奸罪的五种法定加重情节之列。只有《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将“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作为从严惩处的情节。此外,我国在青少年性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划分不清,基础的性教育尚未完善,对“特殊关系型强奸”的预防教育更无从谈起。近些年,每当有涉及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曝光,尤其是其中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身支配关系时,都会引起巨大的舆论风波。例如2017年发生在南京的女童猥亵案,受害人被其养兄段某某在南京南站公然猥亵,同行的养父母也并未加以阻止。该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段某某批准逮捕。这种情况表明,一方面,从相关调查得出的数据来看,利用特殊人身支配关系性侵他人的案件已经不再是偶然,这类案件绝非少数;另一方面,从舆论反应来看,公众对于这类案件持更强的否定态度,并希望有更完善的处理对策。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护法益的需要,我国应当加强对“特殊关系型强奸”的预防与惩处。首先,将“特殊关系型强奸”通过刑法典的规定加以体现,新设监护者强奸罪并处以更高的法定刑,或者将“特殊关系型强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加强对特殊人身支配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的性权利之保护。其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在立法上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完善相应的问责机制,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结语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凡是 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21]因此,对于一个罪名的成立范围、刑罚轻重的修改应当慎之又慎。《修改刑法部分条文的法律方案》对于强奸罪的大幅度修改看似激进,实则如其修改理由所言,是基于社会变化,为了更好打击犯罪而深思熟虑的结果。面对性犯罪出现的新问题,为了保护法益与维护公民权利,各国纷纷对强奸罪作出了相似的修改,这体现了针对强奸罪的新兴立法趋势,包括保护男性的性自决权、扩大“性行为”内容、重视“特殊关系型强奸”。面对这一新趋势,我国无法置身事外,因为上述问题在我国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无论是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还是1997年刑法施行至今,我国都存在着大量性侵男性的案件。在流氓罪存在之时尚能定罪处罚,在流氓罪废止以后,强奸男性却成为了无法可罚的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填补这一法律漏洞,促进强奸罪性别属性的中性化,将男性也作为强奸罪的保护对象,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随着社会发展,“性行为”的内容被赋予了更多含义,如果不重视这种变化,无异于在放纵那些涉及新型“性行为”的性犯罪。《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理。”基于此,将口交、肛交等纳入刑法强奸罪的“性行为”范围,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更有利于维护我国法秩序的统一。在特殊人身支配关系中,弱势一方受到强势一方保护,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强势一方的侵犯,这种“特殊关系型强奸”存在更模糊的取证难题和更大的社会危害,有必要在刑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或将其作为注意规定,或将其列入强奸罪的加重情节,以此切实保障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