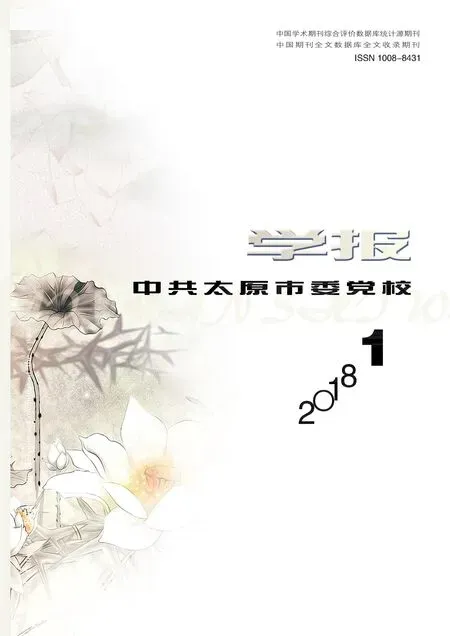弱排名激励视域下的环境政策执行分析
周 佳
(华侨大学,福建 泉州 362021)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央政府既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同时,地方政府作为执行机构,也获得更大的主动权。但根据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部分地区的环境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可是环境污染的趋势依然很严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激励可分为弱激励和强激励。关于强激励的研究最核心的有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他强调相对绩效决定了官员晋升。而关于弱激励的研究则比较少见,练宏对于弱激励的逻辑和作用研究则是从政府内部政治过程的角度展开。本文试图基于练宏提出的弱激励排名的社会学分析,从完成任务逻辑、激励逻辑和政治联盟逻辑分析环境政策的执行力问题。
一、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
练宏(2016)从政府内部政治过程的角度研究弱排名激励,并指出弱排名激励的形成过程就是激励逻辑、完成任务逻辑、政治联盟逻辑三者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过程。由于环保领域处于条块双重关系中,面临外在科层考核和内在权威支配,而弱排名激励兼具适应性和自主性,所以得以在环境政策过程中长期存在。
完成任务逻辑即保证所有下级完成任务,其背后存在着合作机制、责任连带机制、激励强度机制。由于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委托代理链条,在目标责任制中,委托代理方被纳入到同一责任共同体中,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规避风险,会采取措施保护下级,责任连带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环保部门上下级之间利益共存,如果上级部门否决下级部门的努力,则下级部门也拥有“准退出”的权利,这种方式会导致两败俱伤,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表现在如果负向激励过重,则会降低激励强度,代理方则会寻找替代目标,从而放弃委托方为其设立的目标。这三种机制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成任务逻辑。
激励逻辑则强调在考核过程中,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体现差距。这背后的机制是相对绩效考核,周黎安在晋升锦标赛中提到,相对绩效影响晋升概率。可见,相对绩效对于政府官员的重要性。晋升锦标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上级政府有人事任命权;第二,锦标赛标准是明确的;第三,绩效可以衡量;第四,官员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五,参与人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是不易形成合谋;第六,中央政府给出的承诺是可信的。因此,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官员受到一定的激励,就会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目标。
政治联盟逻辑使得上下级环保部门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不对与其相互依赖的部门进行妥协,其核心机制是互惠机制。因为政治联盟逻辑的存在,组织的决策便掺入了非理性的因素,国家环保部与地方环保局在执行环境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牵连,便出现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情况。
(一)从完成任务逻辑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离
环保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遵循一个“高位推动+层级治理+多属性治理”的模式和路径。国家环保部门的高位推动,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巡视、监督和检查是环境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所在。为了提高政策执行力度,上级环保部门开始采用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分配任务,并且对政策的执行程度进行量化。与此对应的是“一票否决”制度,即如果有关项目中的一项没有完成,地方领导干部其他所有的成绩都将被否定。因此,地方领导干部为了能够成功通过考核,必须要达到这些指标。
在完成任务逻辑的主导下,地方环保部门负责人为了自身的晋升发展,这就导致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机械式执行的问题。国家环保部当时在制定目标责任书时,是希望降低政策的模糊性,与此同时,政策的执行也更具激励效果。但是,当国家环保部在向地方环保部门以目标责任书的形式传达环境政策时,事实上,环境政策的执行并不如国家环保部门所预料的那样。如果中央所下达的政策对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都很低时,地方环保部门则会采取观望的策略。一方面,在环境政策颁布之初,地方环保部门并不是采取积极执行的策略,而是先观察上级环保部门以及同级环保部门是如何行动,再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导致政策执行滞后现象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有些地方的环境政策虽未能得到执行,导致环保规划目标难以实现,这一部分的环保局并未被追究责任,这就助长了地方环保部门的拖延心理。但是,由于环保部门之间存在着责任连带机制,上级环保部门为了让下级按规定完成任务,往往会在后期的任务检查阶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下级部门与其讨价还价,降低任务标准,最后使其能够避免因为环保任务不达标而对晋升造成影响。
(二)从激励逻辑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离
激励逻辑是在完成任务逻辑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环保部门的相对绩效考核影响着官员的晋升,因此,地方环保局会有强烈的动力去完成上级环保部门的任务。根据中国政策执行的经验,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偏向于将重要的政策执行目标进行量化,这就导致环境政策的执行与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数字密切相关,伴随而来的是“数字造假”现象。例如,一些地方将环境政策当成一场“数字游戏”,只关注统计数字是否完成得漂亮,而对环境政策是否真实的执行则置若罔闻,这就形成所谓的“中国式”环保。与执行相关的便是合理有效的监督,环境政策的监控一直是一个难题,由于中央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在与经济、政治等相关的方面,而对于环境政策的监控力度则十分有限,这就导致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目标时便采取了十分简单的政策目标和绩效指标。在激励逻辑的引导下,这就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不计成本的来达到绩效指标。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的奖励或惩罚都是根据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绩效考核,在利益的驱逐下,就导致统计的数字越来越好看,而实际的环境问题却依然严重,环境政策的执行形势也依旧严峻。
(三)从政治联盟逻辑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离
政治联盟的核心机制是互惠机制,这意味着互动过程不能仅考虑组织内部利益,还需要顾及其他相关组织的诉求。地方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人事和财政方面的集权,以及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和调配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中央的控制权以及地方的自主权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在环境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地方环保部门同时兼备“检查者”和“被检查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要检查下级环保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他又要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监督和考核。在这种拥有双重身份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双重身份也为上下级之间的政治联盟和合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各级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也由最开始的行政关系慢慢转换为非正式运作关系,由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向合谋关系转变。由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存在争夺决策者注意力的行为,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自然会忽视环境政策的执行。
二、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中的矫正措施
如前文所述,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降低任务标准;地方政府会优先发展更具激励效果的经济政策;在环保任务的查收阶段,上下级政府之间容易为了达到自身要求,而形成上下合谋。如何优化环境政策的执行,进一步缩小政策目标和政策现实的差距,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以问题为导向,提升环境政策的可操作性
在环境政策目标的设定过程中,目标的设置要清晰明了,如果目标的设置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就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提升环境质量。同时,下级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绩效”也将转化为环境问题治理的绩效。环境政策的可操作性越强,政策执行主体就越容易把握上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精神实质,就越能领会政策执行的意图,这样才能使环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挥最大程度的实效;相反,如果环境政策过于严苛,下级政府无法完成任务,就会歪曲政策的真实意图。同时,如果环境政策的制定过于宽松,下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对其进行扭曲,使得政策执行过程的弹性太大,无法达到政策目标,这样必然导致最终的结果各行其是。
(二)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
环境政策执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为居民提供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因此,为了有效的执行环境政策,需要重视环境政策的激励手段,如果上级政府仅仅采取强迫手段使下级政府服从命令,而忽略政策执行的有酬机制,则会导致地方政府将发展重心放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问责机制,主要是依据环境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绿色GDP核算制度,然而难点却在于真实的环境治理绩效有时是无法被测量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在传达的过程中,经过地方的层层过滤,被简化为GDP主导,地方会为了显示自己已经达到考核目标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这个层面上,量化的管理方式反而削弱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激励机制的建立不应该是GDP主导,而更多的是应该以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为考核指标,将环保的政绩纳入考察标准中,当然这个标准的设计也要尽量清晰,操作性要强,可以将自然资源纳入经济的量化之中,通过估价的手段转为货币量化,从而得出自然资源的流失成本,最终从整体上得出环境是改善还是恶化的结论。
(三)拓宽地方政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渠道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委托方和代理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样,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因为中央是利益的最后归属地,要调节两者之间不均衡的关系,就需要拓宽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用地方的利益表达替代上下级之间的“合谋”。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不仅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与政策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也会对最后的输出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部门需要支持吸纳其他主体为政策执行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环境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样也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三、结论
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决定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好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重视。首先,从完成任务的逻辑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发现在环境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拖延执行、机械式执行的情况;而从激励逻辑的角度看待环境政策执行问题,“数字漂亮、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的现象突出;政治联盟逻辑则揭示了地方环保部门以合谋的方式应对国家环保部门的各项检查。最终,本文提出从以问题为导向、提升环境政策的可操作性,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拓宽地方政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三个方面来矫正环境政策执行偏差。
[1]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02).
[2]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05).
[3]殷华方,潘振,鲁明泓.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以外资产业政策为例[J].管理世界,2007(07).
[4]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03).
[5]魏姝.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2(05).
[6]练宏.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以环保部门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