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坏更需要爱吗
文/街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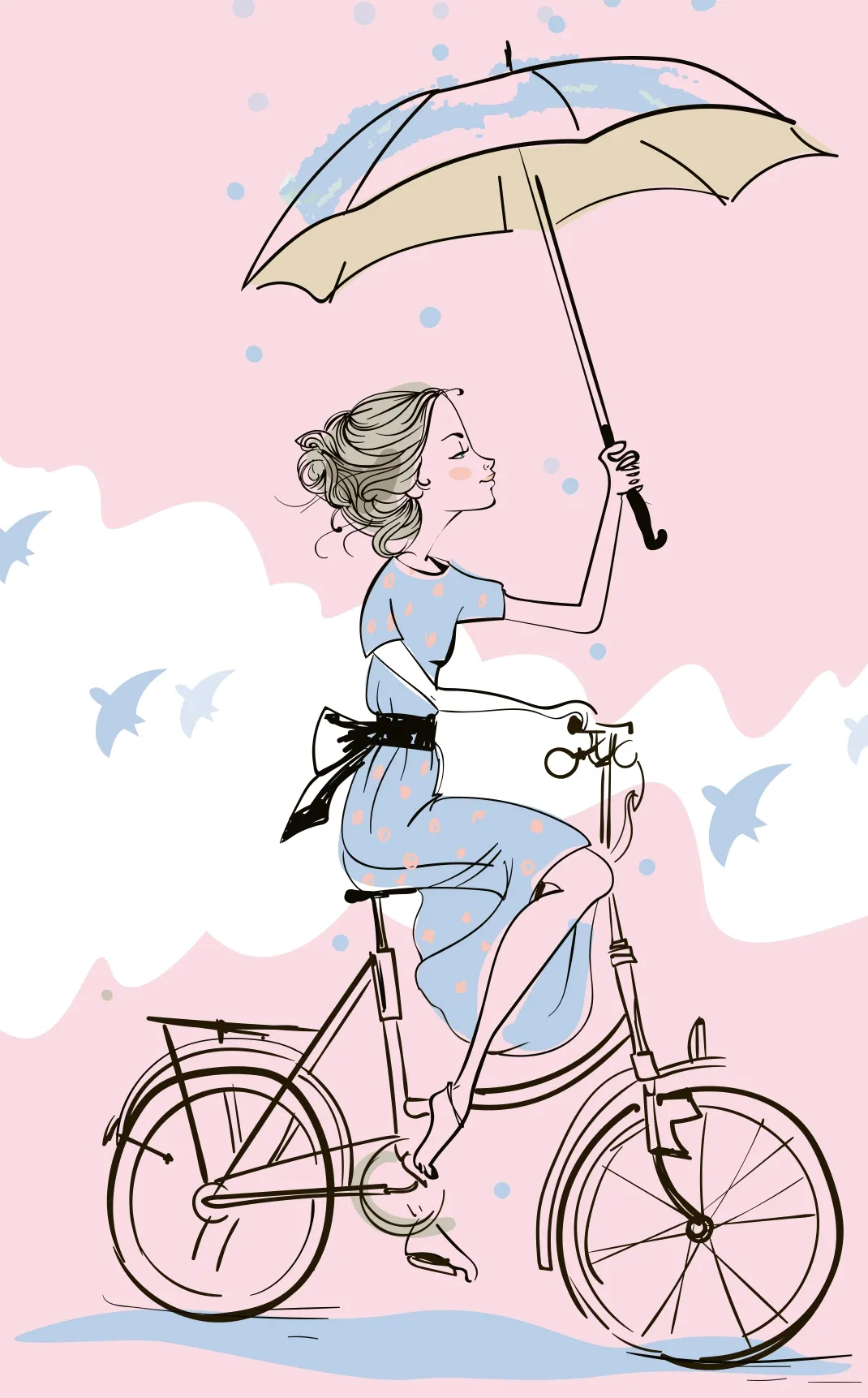
阴郁的冬天摧毁了我生存的意志。我辞掉了工作,从旅途中归来,钻进被窝里拒绝再出来,终日挂着两行鼻涕。大家都说,今年的上海比往年更加冷,因此我也比往年更加扑街。常常一觉睡醒天已经黑了,我坐在漫长的黑夜里,重温那些气质阴郁的老电影,一个人的房间越来越空。当我把自己从床里拽起来,想重新触碰纸质的温暖,书桌上的圆框眼镜却起雾了。我越来越难过,马上就不行了,打开手机刻不容缓跟50个人say hi,然而其实我对谁都无话可说。是我吃得不够饱吗?是我穿得不够暖吗?南方的冬天就是这副德性,无论你吃什么穿什么,都觉得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强烈要求政府给每个公民分配10个情人以度过寒冬。
我人生中最惨烈的一次分手发生在去年冬天,不是我跟对方爱得多么刻骨铭心,而是在冬天分手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我建议国家出台新法律严禁所有情侣在冬天提出分手,否则提分手者要向被分手者提供足够的酒精和安眠药。寒冷还失宠,太惨了真的。本来冬天唯一让人有点盼头的就是在那几个洋节日变着花样折磨男朋友,突然男朋友没了,圣诞节没了,情人节没了,巧克力没了,玫瑰花没了,什么都没了。没有人牵你的手,没有人拥你入怀,没有人吻你的脸。只剩下手脚冰凉的日复一日,我记得自己在床上昏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晚上突发奇想,跑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食材和一瓶红酒,房间里我只开了一盏小台灯,一个人涮火锅到零点,酱是用老干妈油辣椒和老抽调的,我觉得特别美味,撑得几乎反胃,最后抱着瓶红酒躺在沙发上,肚子快要爆炸了,却有种奇异的快感,生活是由我自己一手毁掉的,而不是因为谁的缺席。
消沉过后我开始亢奋,年末天后王菲在上海开演唱会。我每天都在打电话订了一大堆货,在跨年那个晚上跑到王菲的演唱会卖荧光棒和棒棒糖。这是一件漫无目的的事情:有人爱我,我就撒娇。没人爱我,我就吹风。荧光棒没卖出几根,卖到最后,街上只剩下买不到演唱会票的粉丝,垂着头往外走。我把荧光棒和棒棒糖送给那些和我一样有点失落的人。从里面传出来的歌声,刚好我们都会唱,最后汇成一个有点伤心又有点温情的跨年夜。
一年过去了,我好像还是无法抵抗这寒冬。前几天收到前任的信息,他突然跟我说:喂,我最近认识个人跟你好像。要说我们之间还剩什么默契,就是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是这个混蛋又要开始发情了。我心想,哼,似我者死。当然表面上还是得好好端着:哦。像我啥?
像你一样喜欢冬天啊,喜欢大半夜出来溜达吃烧烤。怕冷又穿得少,然后耸着肩膀一直抖,有够蠢的。
我才发现,他对我的认识在一年前就停止更新了。他不知道,我现在怕冬天怕得要死,一阵风就能把我撂倒。我吓得恨不得把自己锁在衣柜里,哪里还敢大半夜出去吃烧烤。再说我现在比较喜欢吃牛排,有什么好烤的?
“你离开我之后,我就不喜欢冬天了”这种酸不拉几的话是无论如何我也说不出口的,我能说出口的是:“那过两天圣诞你把她约出来,脱下你的大外套给她披上,把气氛搞暧昧点,趁她抬头看你的时候迅速吻住她的嘴。”
“好主意。”他说。
夜幕降临了,我从箱子把去年的荧光棒全部翻出来挂在房间里的各个角落。
然后发了同一条信息给所有朋友:带一瓶酒来我家找我,不然我就去跳楼。
圣诞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