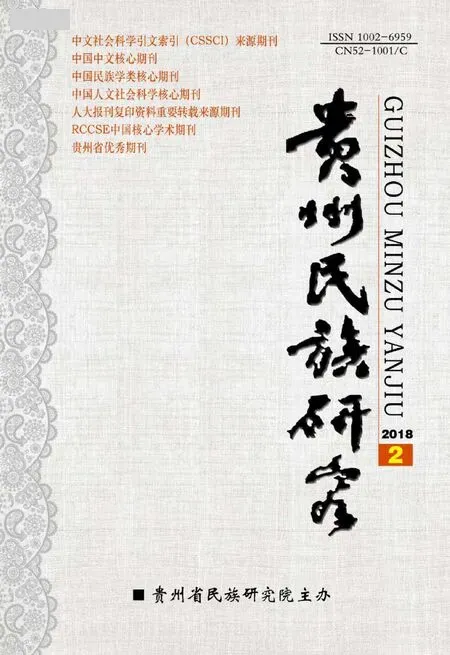云南彝族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的比较研究
邓宏烈 高彩虹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一、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起源与猴崇拜之异
他留民间故事《人变猴与人学猴》讲述:“很久以前,山中有一只老猴子死了,所有山中的猴子都在那里搭青棚大办丧事。人看见了就从猴子那里学来了,是猴子教的,连铎系唱的经也是猴子教给的。猴子不教人是不会的,所以说,猴子是人的老师。”[2]
由此可知,公猴头是铎系的老师。“‘阿爸木纳’(羌族音译),为羌族端公所供的祖师神。阿爸木纳本是天神阿爸木比塔家里专管驱邪、治病、送鬼、占卜的人。”[3]羌族释比的祖师爷是天神家的神职人员,而他留铎系的祖师爷则是公猴头。对比可知,两者的来源相差甚远。但根据民间传说,猴子与羌族释比和他留铎系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留民间故事《人变猴与人学猴》有这样的记叙:“他留人死人的时候要大办丧事,要在院子里搭青棚,举行追悼会,要请吹将来吹唢呐,要请‘铎系’来唱古老的经文、写古老的字符,要跳丧跳神,还要请汉族先生来记账,做‘签点’……这是从猴子那里学来的。”[2]从神话传说和铎系唱经的结构上看,铎系跟猴子是二元结构。该二元结构揭示了公猴头与人的师徒关系。同时,猴子又可划分为公猴头、母猴及其余猴子的三元结构。公猴头是铎系,母猴负责唱女人的调子,其余猴子负责打杂,此三元结构实为他留葬礼在神话故事中的真实反映。“图腾是一种分类手段,图腾的分类能够确定一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同时,图腾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还是一种标记,一种名副其实的纹章。”[4]猴图腾是铎系区别于常人的标记。在他留坟林里,凡是镌刻有猴子图案的墓碑,都是铎系墓,就是说只有铎系死后才享有这一特权,其他人没有资格。[1]
再就羌族释比起源与猴崇拜而论,笔者2016年10月在岷江上游地区调查时,报告人告诉笔者,羌族经书最初写于桦树皮上。因释比在山上睡着了,经书被羊吃了。猴子告诉释比把羊杀了吃掉,把羊皮做成鼓,做法事时击鼓就能记起经书的内容。此传说为多元结构的神话传说,这与铎系唱经的二元结构相异。较之铎系唱经结构,没有划分猴子类别的三元结构。有学者指出:“羌族端公奉祀的祖师阿爸木纳没有偶像,而在家中神龛上供猴头神,做法事时须先敬猴头神。据说,羌族端公跳神的步伐——两脚紧并上下左右跳跃,便是象征着猴子的动作。”[5]而在羌族民间,汶川绵虒、龙溪,理县蒲溪、桃坪,茂县黑虎、沟口等地的端公普遍认为,“羌族本无文字,亦无经书,端公经典中没有猴头神一说,端公供猴头神是以它作法器辟邪,视猴头为灵物,猴头神非真正的神灵,端公是借它的头来供奉端公祖师。”[3]由此可见,羌族释比没有明显的猴图腾之象征符号。
二、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法器经书比较
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在文化传统方面有着共同之处,即二者均没有经书。传说“他留人原来是有文字的,文字是刻在猪皮上的,因携带这张猪皮的人,长途跋涉去办事,途中又累又饿,找不到食物,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把这张猪皮煮吃充饥了。从此他留人就丢失了文字,只保留下来语言,所以他留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1]民间还有羊皮被猪吃掉的说法,《他留文化》创刊号这样记载道:
他留先民没有文字,头人叫几个智者到深山老林里潜心创造文字……他们身边没有可记录文字的纸张,就决定把文字写在羊皮上……他们把羊皮书交给头人的随从。随从跋山涉水往城里赶,半道上,他实在太累了,就把羊皮书放到一边,倒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就在这时,附近的一头老母猪闻到了羊皮的气味拱了过来,几大口就把羊皮书吃掉了。从此,他留人也就没有了文字。[6]
笔者认为“煮”与“猪”的发音相似,在口传过程中可能因为音调问题衍生出“被煮吃了”跟“被猪吃了”这两种说法。对比两者的经书传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书在迁徙途中丢失可能与彝族和羌族祖先从北方迁徙而来有关,是两个民族迁徙史的反映。第二,经书都是由于人或动物饥饿被吃掉,饥饿是两者共同的故事背景。第三,经书被吃掉的传说有极高的相似性。均是由于持有者太累,一时疏忽而被吃掉。第四,至于与文字丢失有关的动物,他留人忌讳猪,因为文字的丧失与猪有关系。所以,墓碑图案中以鹿取代猪。而羌族则因羊偷吃经书,故用羊皮制成法器,羊同时也成为羌族重大祭祀活动的献祭之物。
由上述分析可知,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都没有经书,仅有一些图符或图经。相比之下,铎系图符与释比图经出现的形式、用途和适用范围各有差异。铎系图符的用途较为单一,适用范围较小,仅限于铎系自身参与的丧葬礼仪文化。而释比图经则有较广阔的适用范围,包括丧葬、婚庆、驱邪、请神、占卜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而,两种图符背后都有其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均可以根据图符所指,咏诵相应的经文。可见两种图符都不是表音的图符,而是表意的,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在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师承传统观微
论及羌族释比的师承传统,则有一套相对比较严密的规则制度。“徒弟需要拜师,送给师父一定的拜师礼,如猪肉、大米、白酒等。师父收下徒弟之后,口传心授,带着徒弟做法事,待徒弟精通所有法事,并请释比解卦之后方能出师。出师的时候,师父传给徒弟一套法器,徒弟则给师父准备一些衣服、谢师钱等作为谢师礼。”[7]徒弟在出师前需要掌握唱经,精通与法器的配合技巧、祭祀仪式相关技能、祭祀和法事活动所需法器的制作方法、占卜方法等。至于传承方式,中央民族大学的阮宝娣指出:“释比传承的方式有三种:师徒相传,祖辈家传,家传与师徒传承的复合传承。”[8]笔者在岷江上游地区调查时发现释比多为祖辈家传,师徒相传、家传与师徒传承的比较少。其一,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始学年龄集中分布在10-20岁,最小年龄为6岁,最大年龄为42岁。其二,释比从始学至解卦出师的学习较短,最短的为1年,最长的是20年。而铎系的学习集中分布在30-40年,学习时间较长。这与两者的传承制度有关。释比掌握相关释比文化之后,经释比解卦方可出师;铎系则是等师父年事已高隐退,或者生病不能做法事的时候,经师父授权才可出门帮人做法事或独立。其三,报告人告诉笔者得结婚有后人才能学,婚前学释比者对生育有影响。肖永庆释比则告诉笔者,幼儿学更好,年纪小记得更清楚。年纪小也没有媳妇,也没有家务事,可以专心学习。反观铎系,则无此类说法。
观上述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师承传统,我们明白二者的传承制度多为祖辈相传和师徒相传,且传男不传女,传承方式为口传心授。两者的始学年龄相仿,但学习时长不同,铎系学习时间较释比长。释比有一套系统的拜师、学习、出师制度,铎系则无较系统或明显的制度约束。然其共同之处是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且学习内容较为广泛、深奥。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的地位和职能在不断发生变化,并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其发展现状令人担忧。
四、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职能现状探究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成长足迹的诗意写照,是民族心性、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真实反映,而民族文化得以延续至今,则得益于民族文化传承者的一丝不苟的记录、回忆、描述、教导等方面的倾心奉献。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他们的地位和职能也在历史的烟波里升降变化,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然而却始终难能可贵地追寻和保持着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根与魂。可以这样认为,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作为各自社会的神职人员,即“那些精通宗教仪式的知识与技术,从事沟通人神关系的特殊人物。”[9]“他们的主要职能与宗教仪式、沟通人神关系有关。同时,他们以宗教经验的特别才能为获得社会上高等地位的基础。”[10]
在古代,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由铎系唱经可知,铎系的师父是公猴头,古时候的身份极有可能是部落酋长。而在古羌部落社会时期,“羌族释比的职司是由部落酋长一人兼任。部落酋长一方面执掌部落行政、军事、生产等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又主持着部落中一切祭祀礼仪婚丧嫁娶等社会习俗活动,在社会生活与思想领域里起着部落首领和精神领袖的作用。”[11]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 eorge F ra z er)认为:“在世界很多地区,国王是古代巫师或巫医一脉相承的继承人。”“国王往往被认为是精通巫术,能沟通人神,并以此获得财富和权势,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国王。”[12]就此而论,他留铎系与羌族释比最初为部落首领,并担任祭司一职。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认识能力提升,加之社会分工的出现,祭司一职渐渐从国王的角色中淡出,最终形成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他留铎系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担任红白喜事、粑粑节等大型集体祭祀活动的祭司,也是他留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简良开的《神秘的他留人》[1]和汪宁生的《他鲁人的羊骨卜》[13]等著述论及,他留铎系还会帮人占卜。据兰金荣铎系所述,铎系主要帮人操持红白喜事、祭祖仪式、做法事等。羌族释比的主要职能是帮人测算日子、占卜、驱邪等。释比也主持或参与祭山会、羌历年等传统庆祝活动。至于报酬,以前均是无偿的,现在主人家会根据自家的家庭情况适当给一些报酬。
仪式是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仪式不仅属于一种历史形貌的展现仪式,也是一种人们参与和认知的内容。它既集结了某种人们对宗教生活的“信仰”,同时,又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活动。[14]就此方面的意义而言,主持各类仪式,是他留铎系和羌族释比重要职能的具体体现,他们在仪式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他留人粑粑节祭祖仪式、羌族的祭山会、羌历年等重大节日的纪念仪式,需要通过铎系和释比与神灵或者祖先进行交流,两者的重要性在仪式中得以体现。祭司之所以非常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祭祀大都属于世俗社会的领袖和头人,同时他们有事“通神”、“通灵”之媒,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跟超自然的神灵进行交流。二是仪式本身又加剧了他们的“权力化身”和“神奇符号”。三是这些人的存在又使仪式变得“非凡”和“神秘”。[14]此外,各类仪式深化了铎系和释比的神圣性,同时也加深了参与者对民族、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及族群认同的理解,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现实生活中的铎系和释比并不是全职的宗教神职人员,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身后的事业——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却面临着濒临失传的境地。笔者于2017年7月、8月调查时了解到,他留铎系传承人兰新发、王云德、兰绍章已过世。精通法事,参与主持祭祖仪式的铎系有兰金荣、兰绍增、兰云生、海发清等人。加上有些年事已高,不做法事的老铎系,以及还未出师的徒弟,他留铎系总人数在10人左右。虽然地方政府从中选出非遗传承人,给予资金支持,并在当地开办学习班,鼓励传承铎系传统文化,但他留铎系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再观羌族释比,其现状也不容乐观,释比不仅总人数少,而且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又遭到沉重的破坏和惨重的损失,释比的传承蒙受巨大冲击。
参考文献:
[1]简良开.神秘的他留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97-198、67-68、50.
[2]白庚胜.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永胜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300、231-233.
[3]王康,李鉴踪,汪清玉.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的信仰和礼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50-52.
[4](法)爱弥儿·涂尔干 (m i le D u r k he i m)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41.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43.
[6]陈汝生.他留羊皮文——他留文化创刊号[Z].2017.
[7]赵曦,赵洋.神圣与秩序——羌族艺术文化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293-294.
[8]阮宝娣.羌族释比口述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前言3-4.
[9]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5.
[10]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7.
[11]邓宏烈.羌族宗教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257-258.
[12](英)弗雷泽 (Ja mes G eo r ge Fraz e r) .金枝[M]. 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38.
[13]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247-251.
[14]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7-18、8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