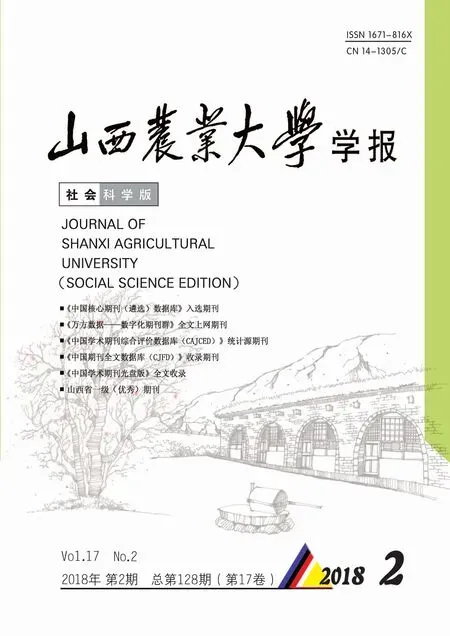农业产业法与竞争法关系的审视与重构
——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分析背景
邱隽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之凸显:供给侧改革的时代命题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面对经济“新常态”所提出的新的深化经济改革规划,它着力于“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纠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在此背景下,我国各产业、各领域都将面临深入变革,而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基础性功能的农业亦不能脱离该趋势。
供给侧改革主张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进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竞争政策的地位将凸显,产业政策中的若干规制措施和扶持标准都需要在遵循竞争政策基本原则的前提上,才应当发挥作用。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对市场实施的一种国家干预手段。产业政策偏重于国家对某类产业直接实施的干预,如推行价格管制、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等,以激活该产业的优势,促进其跨越式发展;而竞争政策则偏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间接调整,政府并不直接影响经营者的行为,而是着力于维护竞争秩序本身,寄望于让竞争机制发挥对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由于产业政策中的某些措施会直接作用于企业本身,以对其施加竞争优势的形式推动产业发展,亦即某些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反竞争”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生了矛盾,这便产生了如何对二者进行协调的问题[2]。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竞争政策理应处于优先于产业政策的地位。即以反垄断法为主的竞争立法、执法应当在更广阔的产业范围内发挥作用,进而建立一个竞争秩序充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产业政策虽然应当发挥作用,但不能僭越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的实施应当以不违背竞争政策为基本前提[3]。这在本轮经济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调结构、降低企业负担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整体背景下,显得更加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竞争法实施的现实困境:来自农业产业政策的僭越力量
(一)中国农业竞争政策先天弱势于产业政策
在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处理一直是一个疑难问题,产业政策很容易僭越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甚至一些反竞争的产业政策会直接影响竞争执法的实际效果。这是因为,中国竞争文化的培育和竞争立法活动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反垄断法》直至2008年才开始在中国实施。这就决定了中国竞争政策的实施是十分弱势的。与之相反,中国却有着实施产业政策的肥沃土壤——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体制基础。“我国目前的行业管制机构体系艰深且繁杂,从而构成了一个根叶茂盛且难以深度改革的复杂结构[4]。”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又急需激励这些行业主管部门,通过产业政策的形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这便进一步强化了产业政策的优势地位。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长期积蓄过程中,这些产业政策的发展已经根深叶茂,其中的反竞争倾向已经难以撼动。本轮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去除这些不正当的政府干预,激活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具体到农业领域来看,竞争政策的实施更是面临受产业政策僭越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在经济政策实施的一般惯例上,农业容易被视为更加脆弱和更需要政府管制的行业。诸如粮食安全、价格稳定、农产品供应等事关公共安全的问题,农业产业政策被视为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而竞争政策则会被视为过于柔性,手段不够“简单粗暴”。其二,中国农业领域的竞争执法常年受到忽视,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竞争立法更是在第56条直接将农业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产业政策立法在农业发展中显然更受到重视,农业竞争法及农业的反垄断执法问题渐趋边缘化。
(二)农业领域竞争执法的停滞
农业竞争环境的现实状况却显露出片面强调农业产业政策,忽视农业竞争秩序的维护,并不利于我国农业整体的产业发展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基于第56条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规则的影响,我国农业领域的竞争执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农民的资本能力、协作能力较低,农业的脆弱性较强、抗风险能力差,如果在这一领域再遵循反垄断执法的逻辑,将会加剧“三农”问题和农业的产业不稳定性。但我国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现实并未如期实现上述目的,恰恰相反,自2010年以来,我国却呈现出关键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却未见改善的奇葩情境:一方面是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涨幅逐年低于食品价格涨幅,与此同时,食品价格涨幅又逐年低于初级农产品价格涨幅,关键农产品如粮、蛋、肉等更是动辄涨幅超过20%[5];但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状况在近几年来却并未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又显著变化,这表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利益并非是由农民所获得,而很可能是被农产品生产经营链条中的其他参与者攫取了[6]。
农业是脆弱性行业,农产品鲜活易腐,季节性、地域性色彩极强,农民对市场供求变化、自然灾害等风险的抵御力极差。即农业生产者极度依赖于下游经销商所提供的批发、零售、仓储、运输渠道。在一般竞争环境中,这种下游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查处纵向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垄断执法的形式弥补,而在农业领域,《反垄断法》第56条对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的规定又令这种反垄断执法的力量极度空缺。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农产品批发、零售、仓储、运输渠道的非农民经营者利用了第56条造就的法外空间,攫取了农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垄断利润;与这些渠道的强势经营者相比,弱势的农产品生产者议价能力低,难以分享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增量收益[7]。
近年来的一些市场调研状况表明,农产品批发、零售、仓储、运输渠道经营者通过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横向拒绝交易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低价收购、高价销售等明显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形式,对农产品供应者进行高价盘剥。这方面最典型的便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通过“手续费”、“上架费”、“管理费”、“摊位费”等名义进行的侵害农产品生产者利益的行为,这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会摊平到最终的农产品价格上,推高其价格水平,但由此换来的利益却完全不会由农民获取,而是由批发商攫取。正是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才导致近年来诸如“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等的农产品暴涨现象[5]。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竞争法与产业法关系的重构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应当对农业竞争法与产业法的关系进行重构,明确农业竞争政策应当在产业政策之上优先发挥效力,这样才能激活农业领域的竞争活力,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更加开放有序的竞争秩序得以主张和保护,并能改变农业发展利益由下游链条经营者攫取的现状。在立法层面,要开展对《反垄断法》第56条农业适用除外条款的再解释,改变由于该条规定导致农业反垄断被长期忽视的现状;在执法层面,我们要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查处农业经销链条的垄断行为,同时还要要开展农业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
(一)对《反垄断法》第56条进行再解释
《反垄断法》第56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该条为农业产业政策优于竞争政策确立了法律基础,因为它将农业领域明确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在反垄断立法中,为了有效地衡平公共利益和社会竞争效率,对于某些具有自然垄断或涉及公共服务属性和维护国民经济安全的领域,竞争政策不应当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优先注重产业政策的功能,[8]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能将这些特殊领域与竞争性领域进行分野,确保反垄断法调整范围的适度性,它“既是对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合理背离,又是对反垄断法局限的克服”[9]。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适用除外的规定有利于推动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积极干预,“政府必须鼓励或强制建立集中化的市场组织,实施特殊的农业政策,实践中,有些国家已经通过不同形式的强制性管制来操作”[10]。
从农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事关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角度来看,上述定位并无问题。但《反垄断法》第56条并未明晰地限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它的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在现实中发生了理解偏差,进而导致农业整体领域都被视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从而不合理地扩大了农业产业规制和财政优待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了农业竞争秩序的维护在促进农业整体发展上本应发挥的作用。该条使用的词语“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极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农业生产经营链条的全部渠道都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范围之内,农业下游经销商实施垄断行为未遭受查处的现实,是这一误解的明显印证。事实上,在对《反垄断法》第56条的解释运用中,我们忽视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一个主体前提,即“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换言之,并非所有主体参与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享有不适用《反垄断法》的特权,而仅局限于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前者是指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处于农产品生产经营链条上游的农民;后者在中国仅指以农村为地缘概念组织的所谓“经济组织”,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等。两类主体均不包含单方面参与农产品下游经销环节的经营者。
由此可见,我国《反垄断法》对农业适用除外条款的态度是:既鼓励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或组织从事生产、加工层面的横向联合,又鼓励其将生产经营链条向下游扩展的纵向联合,这两类行为均属于适用除外的范围。竞争法在这方面的态度是,通过减少其反垄断执法压力的形式,促进其加强协作能力,从而提高在农业生产经营整个链条上的协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非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的,本身即处于生产经营链条下游的批发商、零售商、仓储商、运输商等,它们不是适用除外制度的适格主体,其行为应当纳入到反垄断执法的审查范围当中。
美国、欧盟、日本的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经验均表明笔者的上述分析具有合理性:在美国,1914年《克莱顿法》第6条将适用除外的主体严格限定为“以互助为目的,无资本、非营利”的农业组织*15 U.S.C. §17.,1922年的《凯普沃斯蒂德法》更是将适用除外的主体限定为“农民、植物园主、牧场主、坚果或水果种植业者或乳品场主等参与农产品生产的人”*7 U.S.C. §291.。在欧盟,欧盟委员会1962年《关于处理农业领域协议的26号法规》明确了农业适用除外的范围,仅包含“农业生产者及其协会的生产、销售、贮藏、处理或加工行为”,不包含非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流通环节经营者*Arie Reich. The Agricultural Exemption in Antitrust Law: A Comparative Look 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 Regulation[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2.。在日本,只有合作社才属于《禁止私人垄断与确保公平交易法》适用除外的主体范围,农民基于自助合作达成的“民主地满足其成员共同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11]方属于适用除外的范围。
(二)开展农业反垄断执法和农业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
在对《反垄断法》上的农业适用除外条款进行审慎解释的基础上,只有农业生产者和农村经济组织达成的联合或协同行为才属于适用除外的范围,除此之外的其他农业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均有必要进入到反垄断执法的视野,与此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产业立法也应当以不与竞争政策相违背为实施前提。
首先,应当开展农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上文已述,我国农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问题一直欠缺必要关注,由此造成了生产经营渠道下游链条的批发商、零售商、运输商等对农民进行高价盘剥、攫取垄断利润的情形。具体来说,从《反垄断法》的规范体系来看,应当针对以下几类违法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其一,开展横向垄断协议的执法,如同一区域农产品供销渠道中的经营者达成协议,共同压低农产品供应价格,否则将抵制与其进行交易;其二,开展纵向垄断协议的执法,如经销商强制性地向农产品供货者收取不正当的“管理费”、“上架费”等;其三,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执法,如批发商利用其在相关区域所处的经销渠道地位,强制性地对农产品供货者压低收购价格,对农产品购买者抬高销售价格等;其四,开展针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执法,如当地农产品销售市场上的管理者与经销商相互串通实施上述限制价格或抵制交易的行为。为了确保相关执法措施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建议制定“农业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进一步推动农业竞争秩序维护的法治化。
其次,应当对农业产业政策开展一次以竞争政策为标准进行的系统审查。我国的农业产业政策及其相关立法相当杂乱冗繁,这当中既存在很多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但也不可否认地存在很多限制竞争的管制措施,有必要按照竞争法的标准对其开展审查,实现对限制竞争的农业产业政策的清理和修改,重塑竞争友好型的农业产业环境。2016年6月14日,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国发[2016]34号《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关)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应当开启公平竞争审查。其实质便是针对这些相关产业政策或政府管制行为开展评估,衡量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会不正当的限制竞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要对相关管制措施进行修正,或者索性废除[12]。我国农业领域中杂乱且效果各异的产业政策,亟待按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上述安排开展一次系统的清理。具体来说,应当按照《意见》的相关规则设计,对我国的各具体农业产业政策开展一次有关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的相关审查。农业部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应当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促进我国农业产业政策的系统清理和改进,推动构建农业的良好竞争秩序。
通过针对农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和针对农业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我国方能实现农业领域竞争法与产业发关系的重构,将产业法的有关政策和措施纳入到竞争法建立的竞争秩序的轨道上来,拓展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助推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四、结语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意图于促进经济供给结构优化、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开启的改革规划。在这当中,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理应也深入参与到这场体制机制变革当中。农业竞争法和产业法关系的处理将有利于重塑我国农业发展的市场体制和竞争环境,构建起一个“竞争友好型”的农业产业环境。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不应成为农业竞争政策发挥作用的屏障。希望本文的若干研究成果能够切实有效地推动我国农业竞争环境的优化和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1]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8):12-21.
[2]王先林,丁国峰.反垄断法实施中对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J].法学,2010(9):28-35.
[3]孙晋.国际金融危机之应对与欧盟竞争政策——兼论后危机时代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J].法学评论,2011(1):90-99.
[4]段宏磊.国家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6:178.
[5]于左.中国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垄断因素与公共政策[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4(5):16-19.
[6]战英杰,申秋红.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子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4):144.
[7]李亮国.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农产品经营活动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6):107-109,115.
[8]刘桂清.反垄断法中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0.
[9]种明钊主编.竞争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6.
[10]时建中,钟刚.试析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J].财贸研究,2008(2):141-146.
[11]陈岷,赵新龙,李勇军.经济法视野中的合作社[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17.
[12]朱凯.对我国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框架性思考[J].中国物价,2015(8):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