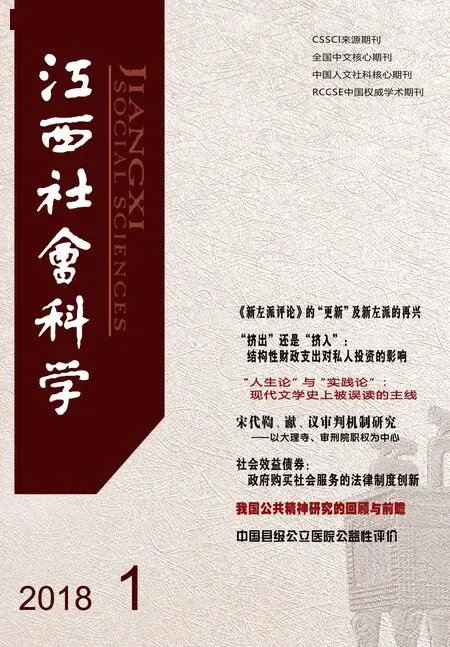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
——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叙事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工业文明的急速发展,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焦虑体验。“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忧虑。”[1](《序言》,P1)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受生存条件的限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面对重重压力。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文学有许多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生活之作。这类作品饱含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便让此种底层叙事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在21世纪被明确提出的文学概念,底层叙事属于一种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其聚焦点在底层社会,生灵活现地展示了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宿命性的生存之道。
方方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从初登文坛时起,就表现出对生活在底层社会人群的关注。她的小说《风景》《黑洞》《落日》《万箭穿心》《声音的低回》《奔跑的火光》《出门寻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把视点聚焦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悲欢离合上,以贴近现实生活的书写,直击生存现状,剖析人物灵魂,述说社会底层生存的尴尬和困惑,对人物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精神挣扎进行把握,展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她创作的小说在坚持底层叙事的同时,将叙事对象转向女性,对女主人公作为妻子、母亲、儿媳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灵魂拷问。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坎坷、跌宕的生存轨迹让读者为之震惊。《奔跑的火光》(2001年)中的农村姑娘英芝,只为想过幸福的生活,不得不忍辱负重,操持家业,结果在封建宗法观念、金钱、情欲等多重压力下走投无路,点燃了复仇的火焰;《出门寻死》(2004年)里的下岗女工何汉晴,尽管她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公婆和丈夫等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导致她要出门寻死;《万箭穿心》(2007年)中的李宝莉泼辣、坚韧,在经历中年下岗、出轨的丈夫为逃避责任自杀后,留下她一人抚养儿子、侍候公婆,却换不来公婆、儿子的同情和理解。从这些女性身上,人生粗粝、严酷的真实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反映出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及人性的思考,也显示出作家对这些女性坚忍顽强、吃苦耐劳、永不放弃品质的赞赏,凸显了女性面对生存困境时不屈不挠、不甘宿命的追求,寄寓了对底层女性的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这些小说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荣登“年度最佳”“年度排行榜”小说之列,“是能代表其写作特点的也较出色的一部”[2],也是“作家本人最愿意向读者推荐的作品”[3]。本文通过分析此类小说中关于社会底层女性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的叙事,探讨她们悲剧生活的成因,梳理借助底层女性视角叙事的独特表达方式。
一、底层女性生存体验的书写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家通过社会观察和生活实践之后,经过加工、提炼、创造出文学作品。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是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命题。不可否认的是,特殊的社会生活经历会对文学创作和作家心态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塑造出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作家方方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动荡的历史环境中,“或多或少的亲身经历了国家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同时“又经过了民间底层生活的淘洗”。[4](P42-43)方方年轻时曾有过长达4年之久在武汉码头干搬运工的经历,对于底层生活非常熟悉。据方方自己说,对底层生活“不是一种皮毛式的了解,而是成天在一起。这就长了见识,有了阅历,使我看得更透彻一点”[5]。对于一名女性作家来说,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让方方感触颇深,因而她的小说多以民间底层叙事为焦点,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贴近社会真实和人物灵魂。作为女性主体叙述者,她的小说在文本叙事特征上又有别于其他底层文学叙事,更是以女性的眼光去观照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女性,把思想和笔触深入女性的性别主题范畴,具有新的女性意识倾向。
方方在塑造底层女性形象时,以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依托,展现她们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角色,进而凸现底层女性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李宝莉、英芝、何汉晴等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她们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但都希望过幸福、安稳的日子。李宝莉美丽漂亮、直爽泼辣、勤快能干、争强好胜,她对生活和婚姻的追求就是找一个自己看得上的知识分子成家生子、过平淡充实的日子,却因性格差异导致她的悲剧生活。农村姑娘英芝未婚先孕,婚后遭受公婆的白眼和丈夫的毒打,她想过上有钱的幸福日子,甚至出卖尊严和肉体,但最终都化为泡影。何汉晴尽心侍候公婆,为家庭琐事付出,过着经济拮据、亲情冷漠的日子,偶尔的一次争吵让她“尊严”意识觉醒,所以出门寻死。方方在书写底层女性生活时,以贴近现实生活的态度,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段,将主人公置于爱情、亲情缺失的多重困境之中,对底层女性人生悲剧的成因持一种反思的态度进行探讨,体现出作品的独特个性以及蕴含的深刻思想,使之对底层女性的审视更具有丰富和深远的意味。
作者在展现主人公的悲剧生活时,为了让悲剧的发展合乎情理,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叙事编码。
首先,在这些底层女性的身份辨识上采取“去知识化”的表达方式。英芝高中毕业后放弃了考大学,知识对她没有吸引力,她甚至认为读书是傻、是白费力,所以后来对爱情、婚姻、生活的抉择以及对金钱、情欲的妥协,都与她的文化水平有关。何汉晴因文化程度不高,在当知青时与推荐工农兵学员失之交臂,在与做过小学老师的婆婆交锋中一直占下风,在儿子的学校丢尽了脸,成为全家看轻的对象。这种知识的缺失成为女性爱情和婚姻生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李宝莉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李宝莉虽然是城市姑娘,但却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便想寻找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为伴侣。当初漂亮的李宝莉肯跟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就因为“马学武是大专毕业,他的文化水平,李宝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6]。马学武来自乡下,但有文化,通过知识从农村进入城市,在知识层面上的一有一无显示了这场婚姻中的不对等关系。正是文化层次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思想境界的不同,双方在婚姻生活中便有了许多龃龉。李宝莉虽无文化,但自恃貌美,便有一种居高临下、处处想占上风的思想,对马学武呼来喝去、口不择言,无视丈夫的情感需求和人格尊严,致使她最终将婚姻经营得支离破碎,走向悲剧的结局。叔本华曾说:“使一种存在高于另一种存在,使一类人高于另一类人的东西,是知识。”[7](P36)在方方的底层叙事中,女主人公的知识缺失被放在重点位置书写,被无限放大。如,由于文化缺失,李宝莉举止粗俗,虽然她深爱自己的丈夫马学武,但嘴里总是离不开“马学武这个狗日的”口头禅,将女性的温柔、娴静、体贴抛弃得无影无踪。“当年轻貌美的天然资本逐渐流逝之后,贫弱的文化知识构成便成为她们校正自我意识与行为方式以逾越突破的阻碍。”[8]李宝莉因容貌在家庭中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使其文化知识的缺乏更加彰显,更重要的是,当她某些时候反思自己行为、言语过激时,无法与丈夫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唯一采取的方式是性。当好友万小景劝她好好待马学武时,她反问小景:“你晓不晓得,在哪里招呼他,他才会叫好?”“被窝里!这个王八蛋喜欢什么我清楚得很。”[6]这种自以为了解和懂得男人的思想让李宝莉沾沾自喜,完全没有认识到两性关系中的平等和自由。在这种缺乏同等精神境界的爱情生活中,李宝莉只有用“身体”来挽回尊严和感情,无法找到与丈夫的精神共鸣。最终使她在家庭生活中由主导者走向被抛弃者,她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
其次,是“去父化”特征的表达。在我国传统的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当她们产生生存的焦虑和失望时,开始梦想“有一个具有父亲特征的人物”在生活中重建秩序。而在英芝、何汉晴、李宝莉等人的身上,这种男女秩序是倒置的。英芝的老公吃喝嫖赌,整天游手好闲,靠她来挣钱养家;何汉晴的老公下岗后,外出工作不顺,只待在家里捯饬模型,她不得不挣钱养家。同时,她们的父亲在生活中都提供不了帮助,甚至儿子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母亲。在她们的人生中,似乎连想要依附于男性的意愿都无法实现,少年时的父亲,青年时的丈夫,中年时的儿子,或者在其生命中没有角色承担,或者突然消失,或者给其带来深深的伤害,她们不得不在一种“无父化”的环境中生存。李宝莉的父亲“原本在码头当起重工,有一天出了工伤,砸断了腿,就被内退回家”,后来摆个修车摊,挣不了几个钱。而母亲“成分硬,早先在针织厂还当过革委会的主任。每有大事,就登台讲话,声音硬硬朗朗,很给人提气”。宝莉对曾经当过“干部”的母亲崇拜有加,母亲对宝莉影响很大,父亲这一角色承担被弱化。她选择马学武是看上了他的有才,事实也正是如此,来自农村的马学武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并分得了可心意的大房子,这对李宝莉来说是“找了个好男将”。[6]但好景不长,刚搬到新房子老公就提出离婚,进而因为生活中的转折老公自杀了,宝莉失去了可以“庇护”的“男性”支撑,家庭中只留下儿子这一未成年的男性存在,直接撇清了宝莉对男性靠山的希望,她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不过,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把希望寄托在学习成绩优异的儿子身上,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她可以跟着享福,但随着儿子考上大学和对她的抛弃,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从父亲—丈夫—儿子这个传统的男性象征关系链中,可以看出,男性符号在底层女性的生活中或者被弱化,或者被消失,或者被忽略和成为消解其欲望的符号。尤其是李宝莉丈夫马学武的突然自杀,在叙事美学上呈现出人物发展的不对称性,马学武平时斯斯文文,性格软弱,即使在男女关系上出了问题、被下岗也不至于抛弃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轻生。作者安排马学武自杀,从这个方面来说,是为了强调李宝莉生活中的“无父化”书写,通过她生命中的“男性缺失”来衬托其底层生活的困境。
在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表达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出身底层,性格直率,换句话说是眼光不高,除了精神上不受重视、生活在不愉悦的环境中,在物质上也是捉襟见肘,为了生活疲于奔波。英芝为了赚钱,在恶俗的民间戏班里唱歌,甚至跳脱衣舞,迷失在物质世界中。何汉晴和李宝莉因为没有文化,早早下岗,而李宝莉则是“没读什么书,小学毕业就出来帮家里卖菜挣钱”[6]。她们或在别人家里帮佣,或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接触的是最底层的人们,这影响了她们在生活中的言行,环境造就了她们的性格,也形成了女性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双重缺失。西蒙·波娃说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9](P17)由于物质和精神的缺失,导致她们人生的悲剧。以李宝莉为例,她行为粗鲁,对待别人很不客气、小肚鸡肠。搬家时对工人的态度就能体现出她在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因为几块钱而争执不下,因为家具被磕碰而破口大骂,活脱一个尖酸小气的市民形象,就连搬家工人都看不惯了。方方曾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10]宝莉妈妈下岗后在市场卖鱼,养活家庭,而宝莉在马学武去世后在汉口街头当了个出苦力的“扁担”,宝莉秉承母亲的吃苦耐劳,还受母亲人生观的影响,在生活中时常记起母亲告诉她的一个“忍”字。与此相同的是,英芝受尽婆家虐待、丈夫毒打,但母亲依然让她“忍耐”。这种人生观深深影响了女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底层生活经验中母女间的生命意识代代相传,在精神领域也不会有太大突破,预示着她们命运的悲剧性。
二、挣扎于日常生活的女性生存焦虑
焦虑作为一种心理学范围内疾病的症候,在文学中表达为身份的焦虑,是指个体对自己个人价值、个人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评价体系的一种担忧。在小说中,为了表达女性的身份焦虑,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出发,选取日常生活作为叙事表达对象。一方面,表达出一种生活中极为平常的悲哀。日常生活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场景,从平常事中提取出的焦虑表达,悲剧性更强。如鲁迅所说:“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11](P293)诚然,底层女性根本算不上英雄,但其生活确实与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家庭一样,也正是通过“近乎于无事的”悲剧书写,体现作者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焦虑的深思。另一方面,通过对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异质书写,强化了主体焦虑的程度。本该属于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相敬如宾的家庭成员关系,却成了轻蔑、背叛、仇视的对象。通过女主人公生活中各个转折点的描写,把这个“消磨于极平常的”大众悲剧主题表达出来,让读者真灼地体会到这种悲剧的深沉,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泪的悲剧。
在底层女性的人生中,与其密切的几个重要关系:为人媳中的婆媳关系、为人妻中的夫妻关系和为人母中的母子关系。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的日常生活都不正常,偏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让女性的人生充满更多坎坷和曲折。首先,在婆媳关系上,自古以来就是女性关系之间的一个另类表达,本来互不相识的两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而有了交集,这就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新关系的诞生,这种复杂微妙的婆媳关系暗含了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英芝嫁给贵清时,因为未婚先孕,在彩礼上就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这让公公婆婆有买廉价货的感觉,更由于英芝抛头露面去唱歌挣钱,公婆认为她下贱,在生活中处处刁难。李宝莉的公公婆婆是教师,都是知识分子,本来对小学未毕业的宝莉就心存不满、看不上,在从老家投奔宝莉夫妻之后,并没有得到好脸色,更对宝莉霸道、暴烈的性格不满。学武死后,婆婆更是把儿子自杀归罪于宝莉的性格上,“成天吵来吵去,是头猪也得去跳江,莫说是个人了”[6],形象地说明了婆婆对宝莉的怨恨。最重要的是她在抚养小宝的过程中,不断灌输是宝莉害学武跳江的思想,为后来宝莉母子关系的破裂埋下伏笔,有力地推动了宝莉悲剧的人生走向。何汉晴也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而下岗后,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做牛做马地侍候一家人,即使在她上厕所时水开了,也没有人替她关一下火。
如果说婆媳关系不合有一定的普遍性,那夫妻关系不和更是女性作为人妻主体焦虑形成的重要原因。英芝和贵清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有了孩子不得不成婚,婚后贵清不但没有对她疼爱有加,反而时常拳打脚踢。李宝莉夫妻二人的结合并非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让这对夫妻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悲剧的走向。李宝莉看中的是马学武的大专文凭,认为这个文凭会给她带来生活保障,尤其是在下一代的进化上,“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6],而马学武看中的是李宝莉的美貌。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婚姻让他们的夫妻生活充满了矛盾,李宝莉个性强,对马学武非骂即打,“马学武在车间当技术员时,脸上常常挂着彩去上班。这就是李宝莉的绝活”[6],长此以往导致了马学武的出轨,直接结果是李宝莉悲惨人生的转折。以李宝莉要强的个性来看,马学武要离婚她是绝对不同意的,为了把他拴在身边,她铤而走险,举报了丈夫嫖娼,让马学武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也成为马学武自杀的导火索。何汉晴和丈夫虽然还有一些夫妻温情存在,但丈夫同样不理解她。在她痛苦不堪要离家寻死时,不但没有安慰,反而招来一顿嘲讽。在夫妻关系上,不知道如何与丈夫沟通、不知道如何管理好婚姻的女性,可以说绝对是失败者。像李宝莉,虽有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想到的只有用性来弥补,真是可悲可叹。
在母子关系上的失败对女性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从血缘上来讲人类最亲密的母子关系上,何汉晴和李宝莉同样收获了失败。何汉晴出门自杀,舍不得儿子,却被他一句“姆妈,你莫没得事找事。我忙得很,你硬要去死,我未必拦得住”[12]的话凉透了心。母子关系的失败在李宝莉这里体现到了极致。马学武不负责任地自杀之后,儿子小宝尚小,为了抚养小宝成才,李宝莉把儿子交给公婆带着,自己去给人当“扁担”挣钱,她每天早出晚归,拼命挣钱,甚至不惜卖血挣钱供小宝上学。但她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母子之间的天伦之乐。因为小宝从小目睹母亲的飞扬跋扈,认为父亲的死是母亲害的,对母亲充满仇恨,小宝在上完大学工作之后,买了房子却把宝莉赶出家门。原本,李宝莉当初与马学武结婚就是图他有文化,将来孩子也有文化、有能力,能保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可小宝是有本事、有出息了,但宝莉却没有达成最初的梦想,她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这种想通过他者进行自我救赎的愿望彻底破灭。戴锦华曾对方方作品中母亲角色的焦虑做过这样的阐释:“她永远在奉献、永远在牺牲,她因作为母亲并超越母亲角色而获得荣耀。而这沸沸扬扬的一幕,在终场处显现为剥夺:即是母亲权力对儿女自由选择命运可能的剥夺,又是社会对一位母亲的剥夺。”[13](P330-331)在母子关系上的失败是李宝莉悲剧生活的最终归宿。
小说在剖析人性灵魂方面,不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关系来表达女性主体的焦虑,更是通过这种“近乎于无事的悲哀”的书写,以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为依托,直击人性灵魂深处,将这种生活在底层女性的焦虑表达得淋漓尽致。通过她们在家庭关系中失败的焦虑表达,颠覆了读者对平常人生的理解,更是通过婆媳、夫妻、母子之间亲情的消解,描写了社会底层女性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万箭穿心”和“无家可归”,以至于要“出门寻死”。“作为个体的人,她们无权也无瑕考虑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个人选择的可能,在此女性的生存和女性的自我意识完全被‘革命’或‘工作’所淹没和替代。”[14](P52)李宝莉虽然性格粗鲁,但她刀子嘴豆腐心,在内心深处,她还是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正因为这无私的爱,她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价值,“没有也不可能具有女性的自我意识”[14](P52),无法正视自己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女性既没有认清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找到女性缓解焦虑的生存之路。方方从女性底层世俗生活的一面出发,以女性生命中至亲至爱的伦理关系为关注对象,对底层女性的人生经验进行开掘,对生活在底层状态中的女性个体命运进行反思,展示了底层叙事中女性视角的丰富内涵。
三、底层女性个体的自我救赎
作为生命个体中的女性,不仅是自然中的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她存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在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女性个体因其生命历程中的角色转变,即从女儿、妻子到母亲的角色更替,打破了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单一化需求。在这种角色更替的过程中,女性不仅需要个体存在价值的体现,更需要精神世界的满足和包容。而生活在底层社会中的女性,虽也有独立思考其个体命运的愿望和能力,但由于其自身性格的不足和在社会存在中价值体现的能力有限,以及传统观念上对男人世界的依附性,注定了其悲剧的人生结局。作家从日常生活中打捞出底层女性角色这个独特的存在,开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反思。何汉晴在家中做牛做马,却得不到亲情的温暖。李宝莉生活在武汉社会的底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婚姻生活中失败,在母子关系上更是让人寒心,这一切的产生,其实和住房风水上的“万箭穿心”无关,而是与她的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底层社会中的女性身份,自然本性的知识缺乏和生活中的男性角色缺失,使她们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的生存焦虑,注定了她在时代变迁和人性社会中的尴尬处境。
方方在对这种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体验进行书写时,将重点指向了她们在生存和精神方面的焦虑状态。虽然英芝在男权的压制下不得不反抗,而导致一声枪响结束了她“美丽而又含辛茹苦的一生”,结局“灼痛着读者的心”。[15]在后来的角色何汉晴、李宝莉身上,作家却安排她们乐观面对困境,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这体现了作家对作为“第二性”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里处境的担忧,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反思,焦虑的表达并不是作品的最终归宿,而是通过这种焦虑书写努力寻求突破口,肯定了在这种焦虑状态下积极追求个性价值的努力。何汉晴在出门寻死的路上为邻居朱婆婆掏耳朵,帮助文三花照顾孩子,并救下了要寻死的文三花。虽然最终何汉晴没有死成,还要过如此这般的日子,但她看到了丈夫对待自己的真心,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而李宝莉经历了生命中“万箭穿心”的悲凉境遇之后,在家庭角色中失败的女主人公虽然还无法把握未来,但仍看到了曙光,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救赎之路的叩问。尤其是李宝莉要如何在丈夫缺席、儿子仇恨的精神世界中立足,找到体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让主体生命得到尊重,是作家书写的一个重要意图。
李宝莉在丈夫去世后,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这个责任无疑是沉重的。本来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挑起的重担压在了李宝莉一个人的身上,但她没有退缩,没有怨言,勇敢地承担下来。她曾说:“我要这个狗日的马学武在地底下看清楚,我也是下了岗的,我一个人,照样能把一家老小养活,让他们出门,照样不失体面。”[6]虽有赌气的成分,却也体现了她的决心。即使干最累最苦的"扁担"也要撑起这个家,供小宝上大学,风里来雨里去,受伤了也不肯休息,实在拿不出钱时还去卖血,体现出她像男人一样的担当。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讨论妇女解放时曾说:“我要讨论的妇女解放,指的不是女人与男人表面上的平等,而是妇女问题中那种真正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深植于女人心中的那种获得男人特性的渴望,即渴望获得男人那种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由,渴望获得男人那种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创造力。”[16](P77)李宝莉代替马学武养家的行为,正是体现了她作为女性为实现个性生命价值所做的努力,她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凸显了自己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抗压韧性,也实现了她努力自我救赎的愿望。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作为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存在,让她们找不到实现自我救赎的出口。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一批作家把目光聚焦在女性身上,对她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描摹,不仅是对这一群体本身的关注,也是通过创作进行女性言说和女性主体寻找的努力,是女性作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主体位置的探寻与实现。[17](P11)方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不但挖掘底层女性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对女性如何在一个现代伦理价值嬗变的社会中站稳脚跟,保持独立的姿态,是作家希冀小说表达的命题。“李宝莉的悲剧让我们对当代社会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不寒而栗。诚然,她的悲剧既有自身的性格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当代社会文化对女性自我身份确认提出的诘难。”[18]李宝莉生活在武汉底层的市民世界,从属于这个社会文化群体,环境不仅影响了她的穿衣打扮和性格,也影响了她的情感倾向,甚至影响了她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她的行为举止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群体保持一致,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小说中多次提到李宝莉对性的看法,她能认识的性就是解决夫妻问题、表达情感的一个手段,高兴时施舍给马学武,惹丈夫生气时也以此化解夫妻矛盾。这种特殊的身体暗示,并没得到马学武的认同。英芝把身体和性当作换取金钱的手段,在这些女性身上,“性哲学”远远脱离了灵肉合一的价值,只成为其生存的一种手段,这也是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所在。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埃莱娜·西苏曾在论述底层叙事中的女性成长时说道:“人必须在自我之外发展自己。在我看来,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人必须逐渐熟悉这个自己,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深谙它内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的栖居地,以便届时从我挣脱,走向他人。”[19](P85)李宝莉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一直在为别人而活,为父母、为丈夫、为儿子,但经历过那段痛苦的岁月后,她逐渐认识到自我的成长,不再拘囿于别人的目光。当儿子向她摊牌家中不会再有她一席之地时,她虽然伤心,但仍没有绝望。“李宝莉想,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的要走完它。”[6]她带着简单的行李,凌晨独自出门来到了汉正街一块五的旅馆,这个地方又响起了李宝莉的笑声,她勇敢地直面人生的态度,反映了现代女性主体从“他者”到“自我”的成长。
四、结 语
在这些以底层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方方大量采用了武汉特色方言,逼真地描写武汉市民的生活场景,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有效地展示了其底层书写的魅力。运用细腻的日常生活描写,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底层社会现实生活的画面。通过底层叙事,作家从千头万绪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出女性这一主体,从女性视角对底层生活女性的悲剧性格进行发掘,她们在教育上的缺失和“男性想象”的缺席,让她们的生活更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在日常生活关系中充满了焦虑体验。小说在对女主人公展开力透纸背的灵魂挖掘中,也表达了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人生感悟和勇敢面对,表达出作家对生活于社会底层女性的深切关怀,一种对世俗人生的悲悯情怀洋溢其中。
这些小说以女性的视角书写底层社会中的现代女性,呈现了她们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双重困境,挖掘和表达了对底层社会的感悟,又以直击人物灵魂的创作姿态,对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焦虑成因进行批判与反思,抨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以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此类小说立意高远,别具特色,为底层叙事和女性视角两个文学叙述学的书写进行挖掘与整合,达到了独特的美学效果。
[1](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吴雁琴.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叙述策略[J].名作欣赏,2012,(21).
[3]金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N].文学报,2007-08-03.
[4]温伟.“世纪之交的湖北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A].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北作家研究室.湖北作家论丛(第七辑)[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5]方方,王尧.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3,(4).
[6]方方.万箭穿心[J].北京文学,2007,(5).
[7](德)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M].金玲,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
[8]高侠.当代女性意识的回填与沉实——论近期女性作家“底层叙事”的三重视角[J].当代文坛,2009,(6).
[9](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10]丁勇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
[11]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方方.出门寻死[J].人民文学,2004,(12).
[1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5]方方.奔跑的火光[J].收获,2001,(5).
[16](奥地利)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M].肖聿,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17]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18]赖洪波.双面镜中的女性镜像:一曲当代女性的命运悲歌——读方方新作《万箭穿心》[J].北京文学,2007,(10).
[19]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