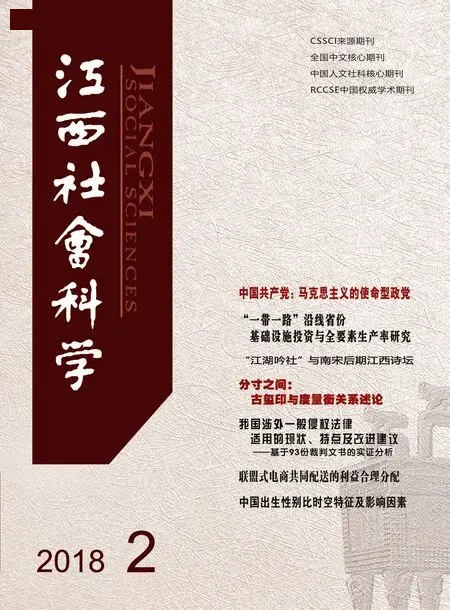北宋士人的文学本原论
——从“文学的形上概念”说起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基于中国传统宇宙论,阐发“文”及其本原问题的相关文学理论皆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形上概念”,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从形而上的宇宙视野思考文学本原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文学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具有构建世界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这种探讨文学的方式出现在汉魏之际,刘勰《原道》篇在“天文—地文—人文”的宇宙框架下探讨文学的起源问题,是最为典型的“文学的形上概念”。他还指出唐代文学实用论中也包含着形上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刘若愚在论及宋人的文学理论时着重分析了苏轼、黄庭坚、苏辙文学理论中的形上因素,而将欧阳修、二程等人的文学理论归入实用理论一派。[1](P27-68)
问题是从柳开、田锡到范仲淹、欧阳修再到石介、二程等人都曾像刘勰那样,在天地框架中探讨“文”及其起源问题,刘若愚对此并未详述。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已经注意到宋人经由宇宙论思考诗歌本原这一现象。如周裕锴指出宋人对诗歌的认识有四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宋人“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诗是天地元气的体现”[2](P3)。然而这种问题意识并未扩展到包括北宋士人古文观在内的北宋文学理论批评史之中。如果说“文学的形上概念”是中国文学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那么辨析“文学的形上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与思想基础,对于彰显“文学的形上概念”之特殊贡献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本文的写作目的即是循着“文学的形上概念”这一理论视野,重新梳理北宋士人的“文学的形上概念”。
一、“文学的形上概念”与“文学本原论”
刘若愚的研究初衷,一方面是朝向构建世界性文学理论体系而努力,另一方面则试图厘清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诸多概念、范畴。在此过程中既需要保持、彰显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特色,又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系,在现代意义上阐释中国文学理论,以发掘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相通之处,令中国文学理论与其他国别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相比,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因为,唯有“同中有异”才能引起百年来占据着学术制高点的西方学界的好奇与兴趣,唯有“异中有同”才能不因其过大的差异而遭受排斥,从而融入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提出“文学的形上概念”。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含义,“形上”取自《易传》,是中国传统宇宙论的说法,对应的是英文的“metaphysics”,即“形而上学”。自古希腊开始,“形而上学”长期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主流位置,19世纪下半叶“形而上学”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20世纪走向终结。在中国,“形而上”代表的是先秦以来悠久的宇宙论传统。可以说,“形上”是中西哲学的汇合,“文学的形上概念”则是中西哲学、文学理论的汇合。
本文用“文学本原论”替换“文学的形上概念”这一术语,是因为中西方“形而上学”探讨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方东美所言,西方是超自然的形而上学,中国是超越性的形而上学。[3](P15)西方“形而上学”主要探讨的是现象之外的本体存在问题,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探讨事物的本质,涉及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真与假等问题,故而是超自然的。中国“形而上学”对应的是本原或者说本根的问题,探讨的是本末、源流、根枝的关系,因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原则,不具有超自然的特点,故而是超越性的。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都是宇宙论,中西方哲学正是经由宇宙论而走向不同的方向。中西方的宇宙论都来自于对宇宙万物的沉思,对事物“本原”的思考,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哲人对“形而上学”以及相关的“本体论”范畴的界定不一而足,中西方哲学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又在追寻“本原”的层面上有着共同的兴趣,故而“本原”较之于“形而上学”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上,“本原”指事物的起点、源头,也可称之为“本根”。《左传·昭公九年》云:“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4](P1309)《左传·文公七年》云:“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4](P557)分别使用“本原”、“本根”代指事物的源头,而无论“本原”还是“本根”皆以植物为喻,表达对事物源头、根本的重视。张岱年认为,中国最早的本根论是道论,此后的太极阴阳论(五行说)、气论、理气论、心论等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宇宙本原的探索都属于“本根论”的范围,这也是“本原论”的研究范围。他还指出中国的“本根”有三层内涵:第一,始义,即一切事物之初,事物的起点;第二,究竟所待义,即万物之依据;第三,统摄义,即统摄一切。[5](P41-43)此外,“本原”或者说“本根”又不仅是事物的起点,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理想终点。中国古人以“道”、“太极”、“理”等为宇宙之初始的同时,也在“天人合一”原则的影响下,以合于“道”、“太极”、“理”等本原为个体修养的最高境界。在现代学术视野的映照之下,中国古人对“本原”的认识常被称为中国的“形而上学”。正如张世英所言,中国也有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是,中国的形而上学主张“天人合一”,“主要地讲本与末、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6](P115)本末、源流、根叶关系来自于古人对宇宙本原、宇宙大化的思考,同样是“本根论”的范围。至此可以说,古代文论领域的“文学的形上概念”与“文学本原论”在研究内容与范围上是相通的。
古希腊哲学始于对世界“本原”(arche)的探究,泰利斯以“水”为世界本原,阿那克西米尼提以“气”为世界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原论,毕达哥拉斯以“数”为世界本原,柏拉图以“理念”为世界本原。亚里士多德认为“原”的含义有六:第一,“事物之从所发始”,即事物起点;第二,“事物之从所开头”,即事物最好的出发点;第三,“事物内在的基本部分”;第四,“不是内在的部分,而是事物最初的生成以及所从动变的来源”;第五,“事物动变的缘由”;第六,“事物所由明示其初义的”。[7](P94-95)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美是许多事物的“本原”,他对“本原”的定义,包含起点、开始、统摄事物变化之意,与中国古人对于“本原”的认识近似。只不过西方哲学中对“本原”的思考最终发展为对“本体”的探究,“本原”渐与现象对举,成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东西。中国哲学则在“天人合一”原则的指导下,认为“本原”与事物的关系不是实在与假象、彼岸与此岸的关系,而是源流、本末的关系,“本原”在事物之中,事物的变化发展离不开“本原”,“本原”既是起点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最高的理想。
“本原”、“本根”虽然是中国固有的概念,但所谓的“本原论”、“文学本原论”仍然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概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本原”常与“本质”、“本体”等概念混用,文学本质论、文学本体论、文学本原论也相继成为文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围。从王国维《文学小言》、鲁迅《摩罗诗力说》、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再到20世纪80、90年代学界对“文学本体论”的研究热忱,对于文学起点、本原或者说本体的研究已然成为文学领域的“第一问题”。
那么,究竟何谓“文学本原论”呢?我们认为,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本原”最初探讨的都是宇宙本原问题,故而基于中国传统宇宙论探讨文学本原及其相关问题的文学理论,均可称之为文学本原论。以刘勰的“文学本原论”为例:“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俯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种,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8](P1)刘勰将《易》的宇宙创生模式引入文论中,认为“天文”或者说“道”既是“文”的本原,赋予了“文”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是“文”的旨归,是文学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刘勰对文学本原的认识与古人探究宇宙“本原”的思维方式同出一辙,这是最为典型的文学本原论。
二、北宋士人的文学本原论
(一)“天文”:古文家的“本原”视野
自宋初开始,经由古人的宇宙论将文学导向“宇宙”的本原论思路已初见端倪。如柳开云:
观乎天,文章可见也。观乎圣人,文章可见也……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圣人之文章,《诗》《书》《礼》《乐》也。(《上王学士第三书》)[9](P582)
又如王禹偁《送孙何序》云: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舍是而称文者,吾未知其可也。[10](P47)
柳开、王禹偁都在溯源流,阐明文章统绪。在“天文”、“人文”相对应的宇宙框架中审视传世经典的意义认为“人文”之前,还有一个更为本原的依据“天文”。不单要明儒家的仁义之道,更要与宇宙万物相通。
不同于柳开、王禹偁简单的比附,古文家田锡将“天文”的本原意义进一步具体化,认为“天文”、“水文”之变是“人文”之功用与“人文”风格多样化的本原与依据:
霹雳一飞,动植咸恐,此则天之变也。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贻陈季和书》)[10](P1-2)
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贻宋小著书》)[10](P4)
天理与诗文之理是相通的,天有“常”有“变”,诗文亦如是。天之常理恢廓广大,“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靡骇其恢廓”,天之变化流动不居,如天之“云与风会,雷与雨交”,水之“激为惊涛,勃为高浪”。“常理”乃寂然之本体,“变化”乃大化流行之用,二者构成了本末、源流关系。在田锡看来,天之常理体现在“人文”中便是“文道合一”,“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天文之变则表现为诗文风格的多样化,李白、李贺的诗歌皆属于变文的序列,虽与儒家正典的修辞风格迥异,仍是天理之用。因为“天文”的创生“了无定形”,“莫有常态”,故而只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令万物之性自然呈现,便是符合“天文”之作。
范仲淹也认为,诗之为诗,正在于它导源于天地,映照着宇宙精神。“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铿如乐府,羽翰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11](P185)这里,范仲淹从诗与天地、诗与社会、诗与君民的关系等角度界定诗,将文学的宇宙属性、社会属性融于一体。以上观点虽然大体出自儒家诗学传统,然而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范仲淹的言说仍然代表着时代的整体趋向。
欧阳修把这种现象称为“天地之和”,在他看来,诗歌是乐之余绪,“盖诗者,乐之苗裔欤”,“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遂独钟于人。故其人之得者,虽不可以和于乐,尚能歌之为诗。”[9](P182-183)原始宗教中,“乐”被认为是天人感应的桥梁。欧阳修从“乐”合于天人的角度论及诗歌的产生契机,可谓返本归源。这里的意思是说乐所承载的天地人相接的和气,也转移到诗歌这种形式之中,表现为“英华雅正,变态百出”的风格。
(二)石介的文学本原论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提出了一个足以与刘勰文学本原论相媲美的“天文—人文”体系:
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之所由见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书,言大道也,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谓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义存乎《诗》,典、谟、诏、誓存乎《书》,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10](P158-159)
石介仿照《易》的宇宙体系构建了一个“天文—人文”相通的“两仪三纲五常九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天文”被置于儒家道德体系之前,既是“六经”的形而上依据,也是“文”的本原。基于“天文”,石介从“文”之体、象、质、数、本、饰、美等层面对“文统”提出新的要求,触及创作主体、创作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文学问题,较之刘勰的“天文”、“地文”、“人文”系统更为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石介追溯了“文”的起源,但其用意不在“文统”而在“道统”。换言之,“天文”为儒家道统、文统提供形而上依据的同时,也将“文”限制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之中。如石介还曾这样界定“天文”的范围,“大者驱引帝、皇、王之道,施于国家,敷于人民,以佐神灵,以浸虫鱼;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阴阳,平四时,以舒畅元化,缉安四方”[10](P150)。若以此为标准,古文家田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推崇的文人之“文”显然被排除在“天文”之外。故而,在某种意义上,石介所谓“天之文”是“人之文”的本原只是为了隆重“六经”的地位,特别是为“圣人之文”提供本体依据以便有的放矢地批判今“文”的浮华背道,对于诗文艺术的发展并无裨益。
(三)“天人合一”:作为终点的“本原”
正如上文所言,“本原”既是起点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最高理想。“文”之本原指向“天文”的同时,“天人合一”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在北宋诗学中被凸显出来,诗人能否把握宇宙韵律成为时人考察诗歌的重要标准之一。以诗著称的梅尧臣讲“且诗之道虽小,然用意之深,可与天地参功,鬼神争奥”[10](P139)。欧阳修评诗也以此为风尚。他说:“‘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贻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洽,读之便觉欣然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12](P173-174)这是欧阳修读唐诗的感发,有两层含义:其一,诗可营造天人相与融洽的意境,可与造化争巧;其二,“天人合一”是一种诗学境界,可以令读者感同身受。到了苏轼,“天人合一”的审美标准中“天”的一面被导向极致,会通于诗、书、画论之中。
这种思路在道学家那里更为清晰。邵雍曾言:“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论物生新句,评文起雅言。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13](P243)与欧阳修等人一样,邵雍赋予诗歌与天地同大的价值,肯定诗歌所展现的天人境界。即便主张“作文害道”的程颐也不得不承认诗歌上达天地之理的美学境界:“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P284)这是说害道之文专注于一隅,无法与天地同参,圣人之文则具有与天地之理同一的气质,观之可以化成天下。唯有上达天地境界的“至文”,才能让这位理学大家折服。
综上所述,文学本原论流行于古文家、道学家的文论、诗论之中,其差异在于:在何种意义上认知、运用“文”的“天文”基础。如果说田锡、欧阳修、范仲淹致力于从宇宙之本原的角度扩充诗歌的多样性与合法性,致力于赋予诗歌与天地同在的价值,以回应诗文为小道的观念。那么在道学家石介、邵雍、程颐这里,“天文”对诗文的指导则成为共识,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文”也成为“道”的附庸。
三、北宋士人的本原论与文学本原论
文学本原论的提出对于北宋诗文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在宋初的七十余年间,文坛弥漫的仍是晚唐五代的浮华卑若。柳开、王禹偁、欧阳修等人接续韩愈“道统”、“文统”并重的思路,别开一种平易自然的风格,才渐与晚唐五代划清界限。对于韩愈的“道统”与“文统”说,宋人有继承也有新的阐发。仅就“文统”而论,韩愈穷究百家之学,构建的是以“六经”为尊,庄骚、史赋为辅的“文统”。北宋士人则视“天文”为文章特别是儒家经典的依据,舍弃庄骚、史赋而独尊儒家。因此,文学本原论不仅在宇宙本体层面发展“文统”说,更以“卷疏变化”、“了无定形”的“天文”为依据形塑北宋诗文刚柔相济而又趋于平易自然的美学风格,为宋人在唐文、唐诗之外另辟一个“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提供理论依据。
文学本原论的提出与“本原论”之演进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是“本原论”取得突出贡献的两个时代,特别是在程朱理学那里,中国的“本原论”走向巅峰。具体而言,魏晋士人结合道家思想与周易宇宙观创建玄学体系,宋人为回应释老“空”、“无”哲学之挑战,基于易庸之学特别是周易宇宙观将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整合为道德形而上学。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学之影响下及南北朝,其诗学影响之一正是刘勰文学本原论的提出。[15](P217-230)北宋士人文学本原论的提出,亦受时人清醒、自觉的本末、源流意识之影响。
“本原论”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人所推尊的儒家道德体系之起点,正如蔡仁厚所言,宋人“由《中庸》《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于《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以讲格物穷理”[16](P1)。所谓“天道诚体”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内在规律,是“本原论”、“本根论”的别名。“天道诚体”向来不是传统儒学关注的重心,宋学之新正在于宋人基于易庸之学阐发儒家的宇宙论与心性论体系,从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功夫”两个层面重新阐释儒家的道德伦理之可能这一问题。《易》之“太极”、“阴阳”、“三才”说,《中庸》之“性命”、“诚”说等是宋人认识宇宙之本,贯通天人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周敦颐以“太极”、“阴阳”为宇宙之本、邵雍以“太极”、“阴阳”、象数之变为宇宙之本到张载以“气”、“太和”、“太虚”、“性”为宇宙之本,再到二程以“理”、“生”为宇宙之本等都是基于易学宇宙观而发。这种探究宇宙之本以贯通天人的思路是文学本原论提出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北宋诗人试图站在宇宙的高度论证儒家经典的意义,“天文”才得以成为“文”之本。
即使在范仲淹、欧阳修所生活的前道学时代,“本原”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也已经形成,特别是作为宇宙之本原的“理”已初现端倪。如土田健次郎认为在欧阳修所生活的时代,“理”为万事万象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秩序感。以欧阳修为例,除了以日常性的“理”为基础,在“人情”的层面探究六经,他还认为万物的消长盛衰、阴阳变化是人所依据的宇宙法则。[17](P45-68)更为重要的是,在前道学时代研习易庸之学以贯通天人的知识格局已经形成。如田锡《贻宋小著书》表明,他论“文”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易》《庸》。史载范仲淹长于《易》,他曾撰《易兼三材赋》表明人道的依据在天地之道,这种上溯天地之道的思路也延续到他的文论之中。某种意义上,前道学时代田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将诗文纳入天人构架之中所提出的文学本原论,即是对《易》之宇宙本原论的发扬。
构建“天道诚体”,探究宇宙“本原”以贯通天人是北宋士人认知世界的普遍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不仅在文论、诗论领域,在画论、琴论领域也产生极大的影响。年龄略长于石介的崔遵度也曾站在“天文”的立场,探究“琴”的本原。他讲:“是则万物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极,太极之外以至于万物,圣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乐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声也。”[18](P10173-10174)《琴笺》是对唐人琴论的反思,唐人认为琴音象征夏至之音,崔遵度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琴乃是天地自然之节的象征,唯有从天人之际论“琴”,方有正本清源之效。他以《易》为基础考察琴之十三徽,认为琴之十三徽的出现是顺应宇宙秩序而来,如同《易》一样是对宇宙秩序的呈现。故而,呈现天地之声便是琴的本质。这种思路也引起好琴者的共鸣,如苏轼、黄庭坚二人曾在“九霄环佩”琴龙池左右分别留有手迹。苏轼言:“蔼蔼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黄庭坚言:“超迹苍霄,逍遥太极。”仔细咀嚼,皆以崔遵度所言“天地自然之节”为尚,紧扣琴之本质品评琴音。
又如,宋代画家也深受《易》学宇宙观的影响[19](P84-90),热衷探究本原问题。以华光老人的画论为例,《华光梅谱·取象》借用太极、阴阳等概念专门讨论梅花的本质:“梅之有象,由制气也,花属阳而象天,木属阴而象地……蒂者,花之所出也,象以太极,故有一丁。房者,花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点。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叶……蓓蕾者有天地未分之象体须未形,其理已着,故有一丁二点者,天地未分而人极未立也。花萼者天地始定之象,故有所自而取象莫非自然而然也。”[20](P36-37)华光老人乃是一僧人,擅画梅花。他论“梅”颇有一花一太极的味道,认为梅之花、木、蒂等凡花之所出皆象太极、三才、五行等天地之数而来,契合阴阳相合之理。依据他的理论,观梅即是观天地秩序,取象画梅即对天地秩序的效法、诠释。这位高僧以《易》为思想基础,引入天地之理以论梅,与石介论“文”、崔遵度论琴的思路异曲同工。
综上所论,如果把石介的“文”之本原说以及北宋士人所提出的文学本原论与崔遵度的“琴”本原说、华光老人的“梅”本原说联系起来看,则经由易庸之学所发扬的宇宙论引起了时人对本原、天人问题的广泛关注,这种问题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不论是文学本原论还是画论、琴论领域的本原论都共享着同一表述方式与认知逻辑,那就是基于传统宇宙论以及古人“天人合一”的理想,认为“人文”源于“宇宙”,作“文”当以奉天法古、融通天人为旨归。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林国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2]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M].匡钊,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4](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注[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6]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李春青.中华古文论释林·北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12](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
[13](宋)邵雍.伊川击壤集[M].陈明,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6]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7](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M].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9]李开林.宋代易学对墨梅艺术的影响[J].周易研究,2015,(1).
[20]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