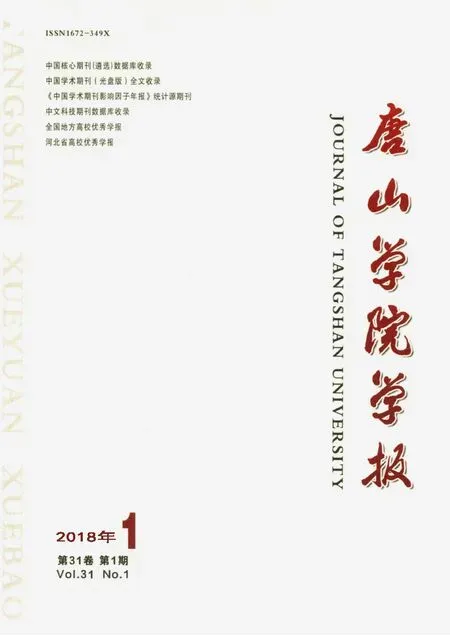国内汉语语义范畴研究述评(1942-2012)
梁吉平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阳 550025)
一、引言
语义范畴研究是当前汉语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中的语义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语言映现,语义范畴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认知客体之间的本质属性及普遍联系,还可以通过跨语言比较揭示出人类认知范畴化中的发展共性。正如邵敬敏所言:“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语法将会有重大突破,那么,首先就会表现在对语义范畴、语义关系和语义选择的研究上。”[1]当然,此处的语义范畴其实是句法语义范畴,但在汉语语言学中一般简称为语义范畴。词语往往是句法语义的互动联系点,所以本文述评即从词语个案或义类开始,其中部分义类词语处于句法语义关联节点,例如递进范畴、条件范畴等。近年来,随着当代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的引入、吸收和运用,汉语语义范畴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话题,目前已经有很多论著围绕汉语语义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整体而言,汉语语义范畴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时及历时两种研究脉络,本文亦从共时及历时研究两种角度,对涉及语义范畴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及总结,同时,为方便读者参阅,整理学界汉语语义范畴研究成果及时间进程,本文将其范畴研究名称及时间列入正文中,而未列入参考文献。此外,通过全面梳理及评述已有成果,进一步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汉语语义范畴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新的突破点。
二、汉语语义范畴的共时研究
最早建立汉语语义范畴系统的是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他以语义为纲构建了一个重在范畴表达和关系表达的“范畴论”,建立了“数量”“指称”“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信”“传疑”“行动·感情”等11种句法语义范畴。随着语义范畴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细化,已经有很多论著围绕汉语语义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2]。如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指称范畴,1985)、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空间范畴,1998)、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语气范畴,1996)、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时体范畴,1997)等。新世纪则有更多以范畴为名的论著产生。如戴耀晶《试论现代汉语的否定范畴》(2000)、徐默凡《现代汉语工具范畴的认知研究》(2003)、周静《现代汉语递进范畴研究》(2003)、刘晋利《现代汉语领属范畴研究》(2003)、周红《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2004)、王珏《汉语生命范畴初论》(2004)、许国萍《现代汉语差比范畴研究》(2005)、罗晓英《现代汉语假设性虚拟范畴研究》(2006)、王天佑《汉语取舍范畴的认知研究》(2007)、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研究》(2007)、汤敬安《情态范畴的认知研究》(2007)、樊青杰《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2008)、刘春卉《现代汉语属性范畴研究》(2008)、张喜洪《现代汉语情态范畴初论》(2008)、王凤兰《现代汉语目的范畴研究》(2008)、程葆贞《现代汉语强调范畴》(2010)、刘承峰《现代汉语“语用数”范畴初探》(2010)、陈光《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2010)等。
从共时研究的成果脉络可以看出,1942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语义表达的范畴系统,但我国的《语言学概论》及《现代汉语》这类教材中所使用的教学概念,仍然将范畴限定为语法范畴,使得范畴研究导向至时、体、态、级及人称等语法概念。新世纪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的引入,范畴研究逐渐从语法性延伸至句法语义(即本文所言“语义范畴”),如上文所列研究成果中的取舍、传信、强调、目的等语义范畴即为典型。从语法范畴到语义范畴的延伸中,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融合新的语用视角。此外,还有很多从范畴角度研究汉语或跨语言比较的论著,此类范畴的系统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这些语义范畴研究大多是从认知或功能角度对现代汉语进行共时探讨的成果,侧重揭示现代汉语中某一语义范畴的类型及功能差异。
三、汉语语义范畴的历时研究
汉语语义范畴的历时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义类或语义场的历史演变,总体上还少有对语义范畴次类的历时形成及发展作出系统研究的论著,研究成果分布较散,主要集中在词语个案、词类、义类等方面。
(一)词语个案语义范畴转化的历时研究
在某个词语个案的语义范畴研究中,很多论著是通过隐喻、原型等认知机制对某个词语的共时态多义范畴进行探讨,如张建理《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2005)。也有论著通过跨语言对比揭示不同语言类型中语义范畴差异,如朱凤梅《中文“花”和英文“flower”相关隐喻的语义范畴转移对比分析》(2010)。但此类词语个案的内部语义范畴研究只是对共时语义层的隐喻解读,或进一步联系外语进行类型学比较,还未能揭示个中语义范畴的历时形成过程。围绕单个词语语义变化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其词性虚化的语法化探讨中,主要有:王雯等《从情态范畴到将来范畴——试论汉译佛经中将来时标志“当”的语法化》(2006)、姚占龙《方位词“里、内”的方位表达及其范畴化》(2009)、李双梅《多义动词“上、下”的范畴化分析》(2010)、程书秋等《语言中两大基本语义语法范畴:动态与静态——从“了”谈起》(2010)、何瑛《从方所范畴到语气范畴:句末助词“在里”的由来》(2010)等,这类单个词语语义范畴历时研究也为汉语语义范畴历时系统及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视角。
(二)词类范畴的历时研究
人类语言中大致有事物、事件、性状等几类基本范畴,根据这些范畴在意义和句法功能上的差异,人们将其划分为不同的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早期的名物化、词类活用或兼类均揭示了不同词类的历时转化或联系。在认知原型范畴理论的应用下,不少论著都在将范畴理论结合到汉语词类研究中,研究内容涵盖名词化及副名结构等多种语言现象。如胡培安《名词和动词的范畴转换》(2003)、胡方芳《由范畴转换看“形容词+着”》(2006)、刘露营等《词类范畴典型概念与动词名词化现象》(2008)、齐红霞等《名词的功能游移是名词非范畴化的结果》(2010)、檀栋《从范畴转换观看汉语名词化问题——从朱德熙〈语法答问〉说起》(2009)、皇甫素飞《范畴转换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解释》(2010)、侯博等《汉语量词的认知范畴化过程初探》(2010)、宗守云《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2010)等。
可以看出,语言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大词类与事物、过程、性质、情态四大基本范畴相对应,通过词类的转化发展也可以看到语义范畴的历时演化过程,无论是动词化还是名词化都体现了基本词类的联系,词类转化的背后蕴藏着深层语义范畴的转移,而语义范畴中的典型特征的转化对词类发展的最终方向起着重要作用。
(三)义类范畴的历时研究
一种语言的词汇可以看作一个组合系统,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项均属于某一词汇(子)系统,词项集结成的较大集合团,称为词义场,小词义场又是大词义场的子系统,从而构成整个词汇系统。通过观察某些语义场可以对场中词语词义在历时演进中的变化情况作出描写[3]。以词义为纲进行的义类范畴考察也是汉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义类范畴的历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某义类范畴的功能或语用考察
如王希杰《“想”类动词的句法多义性》(1992)、吴英慧《“移”类动词句法语义分析》(2004)、张言军《“同意”类动词初探》(2005)、彭利贞《“对待”类动词的粘着现象考察》(2005)、祝东平《“取得”、“消耗”类动词带双宾语的语用分析》(2007)、蒋绍愚《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2007)、朱莹莹《手部动作常用词的语义场研究》(2007)、朱礼金《现代汉语碰撞类动词的句法语义考察》(2008)、韩婷婷《“获取”类动词带双宾语句研究(2008)》、朱坤林《“猜测”类动词句法分布考察》(2009)、王枫《先秦“叙说”类动词语义场基本特征》(2009)等。
2.专书义类范畴研究
如殷国光《〈庄子〉“转让”类动词及其相关句式的考察》(2005)、傅义春《〈敦煌变文〉中的“采拾”义动词》(2005)、毕秀洁《〈诗经〉“到达”义动词研究》(2007)、徐春红《〈左传〉“告谕”类动词词义特点和结构功能研究》(2007)、黎楠《〈论衡〉中的比类动词的用法分类》(2007)、刘义婧《〈齐民要术〉农业生产类动词研究》(2008)、韩松岭等《〈齐民要术〉“种植”类动词的用法探析》(2009)、刘芬《〈论语〉单音节情绪类心理动词的同义关系研究》(2011)等。
3.跨语言义类范畴认知考察
如潘玉华《汉语目视类词群的语义范畴与隐喻认知研究》(2007)、赵海亮《汉语“风”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分析》(2008)、闵娜《汉语“足”词群的语义范畴与隐喻认知研究》(2008)、马春媛《汉语“手”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2010)等。此外,也有大量汉语与其他语言某义类范畴的跨语言比较。如张珍华《汉韩思考类动词及其对应关系》(2004)、马宏宇《英汉“予取”类动词结构认知对比研究》(2009)、曾岚《汉日关闭义动词对比研究》(2009)、王银平《英汉味觉范畴隐喻的对比研究》(2010)等。
4.义类范畴成员历史演变研究
义类范畴成员历史演变研究常常是以语义场为线索进行的,主要集中于同义类成员在历史发展中的分化、更替和延续。如:解海江等《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1993)、崔宰荣《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997)、孔丽华《“捆卷”类动词衍生量词的历时过程和现时表现》(2000)、杜翔《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2002)、刘新春《睡觉类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2003)、汪维辉《汉语“说”类词的历史演变与共时分布》(2003)、王建喜《“陆地水”语义场的演变及其同义语素的叠置》(2003)、马丽《论未成年人语义场的演变》(2004)、李云云《汉语下肢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4)、程云峰《“忏悔”、“礼拜”等佛教修行动作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6)、邵丹《汉语情绪心理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2006)、张庆庆《近代汉语“寻找”义动词更替考》(2007)、萧红《汉语“捕捉”义动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2007)、吕文平《汉语“买卖”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2007)、王枫《“问答”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7)及《“语告”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8)、高龙《汉语“切割”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2008)、蒋绍愚《五味之名及其引申义》(2008)、张荆萍《试论古汉语“出售”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8)、张玉代《“肩负”类动词历时更替浅析》(2008)、闫春慧《汉语“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6)、双丹丹《“种植”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2009)、贾萍《聚集义动态量词衍生机制考察》(2009)、刘恩萍《汉语“行进”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2009)、黄晓雪《“持拿”义动词的演变模式及认知解释》(2010)、张黎《汉语“燃烧”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2010)、唐智燕《汉语商贸类常用词的历史演变》(2011)、代珍《汉语“死亡”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2011)、常荣《汉语“建筑”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2011)等。
对于汉语庞大的词汇系统来说,按照语义场进行义类划分,可以借助义类聚合关系来考察句法语义关联。从这一点来看,对某一义类范畴的功能或语用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共时态词语义项分布并进行系统性描写总结。汉语及跨语言义类范畴的认知考察是对此类语义群的共时性解释,即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将这些次类语义场中的共时性成员词义隐喻关系加以解释。通过跨语言考察,不仅可以揭示其中的民族文化差异,而且可以凸显其中多语言共性认知机制。汉语词汇数量庞大、演变复杂,将词汇范围缩小至义类进行历史考察,有助于厘清义类成员词义发展及历史更替分化,建立汉语词汇史的同时发现词义历史演变规律。目前也有论著在汉语词汇历时研究中尝试将语法化及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引入,探讨词汇与句法结合的问题。如《像义动词到测度类语气副词的语法化》《“持拿”义动词的演变模式及认知解释》等,在论述中不仅有对义类成员语法化的探讨,还有对义类范畴演化进行的规律性总结。某个词义场实则代表了某个概念,所属词义场不同,搭配力也不同;有些词可以同其他很多词组合,而有些词却不能。对基本词类的内部次类范畴成员进行历史演变研究后,可以发现某些共时差异往往需要从义类范畴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演变痕迹。只是目前运用语法化及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范畴研究的论著整体上还不多,而将词汇与语法结合进行考察,研究其中语义范畴演化则可以为语言中词汇与句法接口问题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四、语义范畴间的关系及转化研究
正如词类之间的兼类或历史转化关系一样,词类背后的语义范畴也存在明显的转化关系,但很多论著的探讨还集中在某个语义范畴与其他范畴的比较中。如刘焱《比较范畴与邻近范畴的区别》(2003)、王伟《汉语方所和比较范畴的认知及表达策略》(2008)、王凤兰《谈语言中目的范畴与因果范畴的联系与区别》(2008)、邹海清《从语义范畴的角度看量化体与体貌系统》(2010)等。这些论著也间接表明了汉语中多种语义范畴存在关联关系,而这种关联是何时形成、怎样形成的,是否具有跨语言认知共性等问题还较少涉及。如董正存《时间范畴到条件范畴的映射》(2008)一文,从英汉语言事实指出时间范畴到条件范畴的映射是人类语言演变的共性之一,其中隐喻是范畴转化的重要机制。另外,修辞学也在以范畴关联转化为视角进行探讨。如赵升奎《“比喻”跨范畴的语义映射过程》(2003)、李艳《汉语移就范畴的认知阐释》(2010)等,均为从认知范畴角度对修辞原型范畴或范畴转化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目前对语义范畴之间的转化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比较少见,从我们对前期范畴研究的检视也可以看出,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建立了各类语义范畴,并且对某些语义范畴进行比较,却很少从语言历时发展角度对语义范畴的形成进行研究,各种语义范畴之间是否存在临近演化关系,其间的句法与语义如何互动,不同范畴间如何历时转化是目前语义范畴研究亟需突破之处。
五、汉语范畴研究中的两种范式:语法范畴与语义范畴
通常所说的语言范畴主要是语法范畴和语义范畴。语法范畴(狭义)是词的时、体等形态变化所概括的语法意义,很大程度上隶属于西方语言学中的形态学领域。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陆续出版语言学范畴研究系列丛书,其中就包括体范畴、性范畴、格范畴、人称范畴、时态范畴、限定范畴、数量范畴等主要语法范畴,多是以印欧语系词形形态变化为模本进行讨论的,这些语法范畴往往会体现为语言中的词形变化。而语义范畴是认知范畴的语言化,即人类认知通过对不同事物对象的特征进行归类或概念化,进而付诸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结果。虽然语义范畴本质上也是从语法意义角度归纳出来的范畴,但这种语法意义还包含了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一是从词类次范畴小类中概括出来的具有范畴性的语义特征;二是从词语或句式的组合中概括出的范畴化的语义关系”[1]。也就是说语义范畴范式不仅在研究中能够结合词语或句式的语义特征,而且可以呈现出语义与句法之间互动关系的更多信息。以数量范畴为例,在语法范畴角度中“数量”一般被视为“数”,常被概括为具有二元对立性的单数和复数。然而,对于所有人类的语言而言,单数与复数仅仅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实际上,三种、四种、五种数的区分也并不少见;而且孤立的数词(number)概念并无实际意义,所谓的“数”其实是从属于量的相关范畴,所以在语义范畴中更多地使用“数量”或“量”来代替语法范畴中的“数”。柯伯特就曾收集250种语言的相关材料,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来分析数量范畴的可能系统,揭示了数量范畴表达的多样性[4]。即便是在我们熟悉的汉语中,数量范畴也不仅包括词汇结构上显现出的单数复数性,还可以涵盖微量、常量、极量或主观量、客观量等不同的语义特征或关系,这类量度语义在容纳范围上显然要比传统的语法范畴“数”更广,在词汇和语法层面也具有更强的体现,而且语义范畴更加注重不同语义类别在语用表达中的多样性,对说明跨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相关语义范畴的类型学探索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从语言本体研究来看,认知语言学派常常将范畴研究局限于静态化探讨中。例如Lakoff,Taylor等人虽然运用隐喻、转喻等视角,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词汇语义范畴或句式结构的共时多义性,并形成了隐喻映射、转喻映射、意象图式结构等解释模型,但研究触角在整体上还缺乏一个动态的历时探讨,没有将语言发展纳入一个更长阶段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以此去寻求语言发展中更多的可能性致变因素,如句法语义互动、构式转化等。目前的汉语语义范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导向,也存在类似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语义范畴的深入系统研究。语义范畴并非一成不变,同一个范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或不同的时代中即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语言中不同语义范畴的交叉属性或边缘效应的隐显也可能会导致范畴间的转化演进。因此,探讨不同语义范畴的历时转化关系也应当成为语言范畴研究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我们需要把这些前期诸多共时研究中形成的优秀成果纳入更广阔的历时语言研究中。
六、汉语语义范畴研究的未来趋势及突破点
范畴具有动态性,语义范畴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统,人类对某一认知对象选择的观察角度并非凝固不变的,这样就使语言中的同一认知对象可能转入不同的认知范畴识解。随着人们认知视角或语用目的的凸显,范畴成员也可能会逐渐地从原范畴跨入另一相关范畴。当代词汇的语义范畴转化以及语言中业已固化的范畴转移现象,都揭示了语言中的语义范畴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且考察语言的历时跨度越长,范畴演化即可能越明显、越复杂。
我们还要考虑到,即便在一种语言的基本语义范畴中,各种范畴的界线也并非如此明确清晰,很多词语存在语义共性的同时,还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性,差异性越凸显,越可能偏离以某一个语义共性而形成的范畴。如汉语“来”在趋向动作语义特征上属于行为范畴,但在表示完成态和约量时,又与时间、数量等范畴处于同一集合中。这些语义特征常常被置于语法范畴内进行探讨,因此很多范畴转化在语言学研究中都是围绕词类进行的。Ramat指出,范畴并非一成不变的,相关范畴会存在交集,即可能会具有相同的特征,范畴成员极有可能跨越自己的范畴而导致重新范畴化。如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能够转化为方位词,名词转化为量词等[5]。Hopper和Thompson指出,就语法范畴而言,词的地位不是绝对的,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它们的语义特征、所指内容的确定程度在语境的作用下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语境下,范畴A的成员可能变成范畴B的成员,高范畴属性的成员在一定语境下,可能会变成低范畴属性的成员[6]。在共时语言中,一些范畴的成员在语篇中的典型属性特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完全丧失原有范畴所有特征发生范畴转移的结果,这一过程即为“去范畴化”。刘正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范畴会逐渐失去范畴中典型特征,范畴在原有范畴和即将产生的新范畴之间存在模糊的中间范畴,这类中间范畴丧失了原有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同时也获得新范畴的某些特征。”[7]由于这种中间范畴演化只是原范畴部分特征的丧失或者转化,所以刘文释为“非范畴化”。本文用“范畴化”概指整个范畴的发展变化,沿用“非范畴化”来指代范畴未完全演化时的过渡状态,而用“重新范畴化”来指代完全丧失原有范畴所有特征发生范畴转移的结果。当然,此处的重新范畴化指代已经固化后的范畴转移结果,转移后的范畴仍然可能在共时语言中有原范畴的语义或语用功能。当代汉语中“很明星”“很男人”等类似副名结构,其中的名词处于范畴演化的中间状态,即名词“非范畴化”现象;汉语历史中空间范畴转化为时间范畴的稳定且差异较大的过程,即为重新范畴化,如果将语言历时共时视角考虑在内,那么语义范畴演化的动态模型当如图1所示。

A1:重新范畴化;A2:稳定范畴;A3:非范畴化图1 语义范畴演化的动态模型
可见,在语言中,不同词类之间也可通过范畴化形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范型网络,各种类别的词又与其他类型的语言单位之间发生范畴化(如递进与条件语义范畴之间),因而整个语言范畴是一个巨型范畴化关系网络[8]。从历时及共时两种角度不仅能够研究语义范畴的历时演化,而且能够在历时演化中解释共时功能的差异成因,将不同范畴之间的亲疏远近及句法语义互动转化的关系呈现出来,这对汉语语义范畴研究是一个难点,同时也必将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1] 邵敬敏,赵春利.关于语义范畴的理论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2006(1):29-40.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131-211.
[3] 张建理.词义场·语义场·语义框架[J].浙江大学学报,2000(3):6.
[4] 柯伯特.数量范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177.
[5] RAMAT.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linguists categorization[J]. Linguistics,1999(37):157-180.
[6] HOPPER P J,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67-209.
[7] 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78.
[8] 吴新民,顾超美,杨战.词类范畴研究述评[J].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08(6):9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