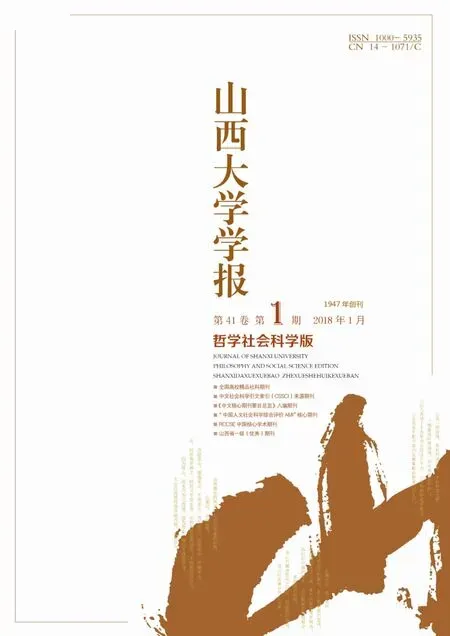“量化法治”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
朱景文,杨 欣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2)
一 环境司法专门化成为国际发展趋势
近年来,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无疑已成为现代环境法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里程碑。[1]专门解决环境纠纷的“环境法庭”在各国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极大地拓展了世界环境正义的版图,成为人类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制度创新成果。[2]环境司法专门化主要是指在司法系统内部建立专门的机构,根据专门的程序,由专业人员来处理环境纠纷。[3]据统计显示,到2016年底,全世界范围有44个国家建立了1200个(国家级、省/州级)专门环境审判机构,还有15个国家正在完成建立专门审判机构的程序。①需要说明的是,各国学者研究在提及“环境法庭”的时候是一种广义的指称,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是环境司法意义上的专门审判机构,还包括了在政府机构等非司法系统专门处理环境纠纷的机制,可以说更加全面。参见: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UNEP2016),PP.12-13.环境法庭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要产物正在改变着传统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早在1992年的《里约宣言》中,就提出了“用有效的司法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倡议,经过1998年《奥尔胡思公约》和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巴厘战略计划》,提出了实现国际环境法治的三个基本权利:获取环境信息的民主权利、公共参与环境决策的民主权利、接近司法的民主权利。[4]2012年联合国“里约 +20”会议、“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5]以及2016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6]都进一步重申了环境司法变革对于保障人权、实现环境法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各国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民众要求治理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各国现有司法体系无法有效地应对环境公共问题,促成了环境法庭的诞生。公众要求环境司法能够“公正、及时、可负担”,环境司法改革也以此三者为主要目标。然而,目标与现实的背离、救济不及时、审判不独立、人员不专业、程序不公正等问题均困扰着环境司法的发展。[1]
二 “量化法治”在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应用:域外视角
各种类型的法治指数、法治评估的出现促成了“量化法治”的发展趋势,为比较法的研究拓展了新视角,提供了有力工具,也成为各国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实现环境法治的工具。目前,“法治评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世界银行对全球治理的量化评估和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关于各国法治指数的报告,从法治的各个方面对主要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6年发布的《环境法庭:政策制定者指导》报告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将“量化法治”方法作为决策工具应用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改革中,从环境法庭筹备、设置,到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改进司法政策和实施方案,“量化法治”工具为司法决策者提供了决策依据,检验专门环境司法机构是否有效地解决环境纠纷,是否实现了“公平、及时、可负担”和一系列环境法治的原则。[2]如果把环境司法专门化看作一种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那么“量化法治”方式将有效地保证这种转变的科学性、有效性。
环境法庭在数量上激增,说明了司法决策存在着“非理性”:是否有些环境法庭仅为解决某个具体环境事件而匆忙设置,事后又由于缺少案源而被迫关闭,类似情况屡见不鲜。UNEP统计,有七个国家的环境法庭都出现了先设置、后关闭的情况。①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哈马、中国(江苏省)、芬兰、匈牙利、荷兰和南非。那么,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就需要回答一些基本诘问:采取什么方式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立法先行还是地方实验?是否需要设立环境法庭,是全国统一管理还是地方自主决定?设立什么级别的环境法庭,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基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独立的审判庭还是非独立的合议庭抑或是委任环境法官?配给什么样的司法裁判人员,是普通法官还是增加环境技术专家?单纯依靠政治决断和定性分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具有定量研究传统的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开发了一系列“量化法治”的工具,为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一)内部量化评估
司法机关的“内部测评”(Internal Assessment),是由司法体系内部的专家主导,邀请当地政府环保机构、非政府机构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内部考评。UNEP认为这样的测评需要着重关注以下问题:环境法庭的设置是否符合法治原则;是否具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利益受损者是否具有诉讼资格;司法审判是否独立;法官是否能够准确合理地适用环境法律;案件是否能及时审判等。已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1.卓越法院国际框架标准(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Court Excellence)
卓越法院国际标准框架(IFCE)的主导者是一个由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司法组织和法院组成的联合财团法人。他们致力于开发一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世意义的衡量司法体系、司法质量的评估框架。[8]2008年,参与该财团的各国法院适用该框架对各自司法体系进行评估,现更新的2013年版本是在2008年评估反馈基础上的改进版。该框架为“卓越法院”提出了十个核心价值:法律平等、公平、司法正义、审判独立、胜任职责、廉洁、司法透明、便捷、及时、司法确定性。这十个核心价值的强调体现了IFCE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其目的不仅在于评估法院表现,更在于评估之后的“改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IFCE提供了一个用来评估法院具体表现的自测表格,自测表格包含三个方面七项问题:一是司法职责,包括法院领导和管理;二是司法体系,包括法院规划和政策、法院的人财物资源、法院的程序;三是司法效果,包括公众需求和满意度、可负担的便民司法、司法公信力。每个问题都从方法策略与实施效果两个方面来测评,满分5分,按每个得分加总结果。这套框架邀请的评估主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了法院内部的人员,还包括参与司法活动的律师、检察官以及普通人;评估主体的多样性增强了内部评估的民主性和客观性,为后续改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打下了基础。
2.“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评估实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LEC)自1980年建立以后,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环境法庭实践。独立的法院、充足的资金和人员配置、国际化合作等因素使LEC成为世界环境法庭的典范。自2008年以来,LEC每年都使用IFCE对法院当年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估,并且制定相应的行动策略;每年具体评估情况和改进措施都体现在当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
LEC评估小组根据IFCE进行内部评估,首先根据自测表格的各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结合法院当年的内部数据,征求各方意见,进行打分评价。在LEC的年度报告中,除了自我评估得出的改进计划之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当年法院各个审判庭各类案件的统计数据分析。LEC共有8个审判庭,除了每个审判庭单独的案件数据统计和具体分析,还有按照立案数、审理中、已审结、审前处理等分类统计的案件数据。此外,通过ADR各个方式解决的案件数目有详细的统计和评价。[9]LEC把案件的管理和统计当成是IFCE评估中司法核心价值的关键方法,也是体现司法是否便民、高效、及时裁判的核心。如果司法是一种公共服务,那么案件就是司法服务的“产品”,对案件各方面的评估其实质就是对司法服务的评价。LEC的法官在一份报告中也表示,通过IFCE的评估,法院认识到虽然其在审判上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法院还是需要政府财政拨款的支持,促使法院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得不加强与各机构的广泛合作和交流以保证继续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10]
(二)外部综合测评
内部测评是环境法庭运行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工具。外部测评①除正文所述的两个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System)开发的世界法治指数,无疑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法治评估较为权威的报告。2016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已经是这个系列报告的第六年,基本采取了原有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数据更新和比较,为全世界113个国家进行了法治指数的评分(0到1分)和排名。虽然法治指数并非直接测量环境立法和司法的状况,但是能够从它具体的各项指标的分析中看出每个国家的司法状况,从而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其中的民事司法、刑事司法以及非正式司法这三个指标能够为环境司法反映一国司法体系的基本情况,为环境司法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民事司法指标中的第七项小指标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这是各国在专门性的环境司法机构中常常使用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个小的指标也可以反映一国设立环境司法机构的制度基础。则是司法决策的制度背景,也是重要依据。
1.环境民主指数(Environmental Democracy Index)
环境民主指数(EDI)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WRI)在2015年发布的,它测量了70个国家的有关环境的民主权利发展程度,给出评分和相应的排名。[11]EDI的最大特点是,它所测量的75个法律指标是从1992年《里约宣言》的23个原则发展而来。《里约宣言》认为,实现环境善治有三个基础:获取环境信息的民主权利,公共参与环境决策的民主权利,接近司法的民主权利;相应地,EDI的法律指标也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给予相同权重。EDI的评分主要是基于一国的法律体系本身,侧重于法律规范,75个指标都是“法律指标”;为了弥补这一缺陷,24个用于测量实践是否和法律规定相符合的“实践指标”,被相应地补充到了每个部分以保证测量的客观全面。各国的资深环境专家、律师为每项指标打分。各国都有一个熟悉环境法的资深律师担任国别研究员负责收集和分析各项指标评分;另外有一个环境专家担任国别评论员负责补充和检查初步评估成果;这些指标最后由WRI的工作人员汇总和评分。
2.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环境绩效指数(EPI)是目前测量国家环境绩效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指数,它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长时间地收集整理关键领域的数据,形成具有时间跨度和可比性的国家环境绩效排名。[12]这个指数由耶鲁大学的环境法与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信息中心联合开发。2016年报告集中测量的是环境绩效对人类健康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共测量了9个问题,形成了20多个主要测量指标。比如在“空气质量”这个大指标中又分成了4个小的指标,分别是:室内空气质量、PM2.5平均指数、细颗粒物质超过数、二氧化氮平均值,每个指标以表现最优异的国家为高分区域,根据数据状况对国家表现打分。EPI的一手数据来源于卫星监测和分析,二手数据主要来自各国官方机构。
目前,许多国家都借鉴了EPI的指标体系,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并取得一定成果。②笔者抽取UNEP中列举的在环境司法方面具有成功实践的几个主要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智利、日本、瑞典和英国),将其2016年EDI(数据1)与WJP之中的“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两项加总(民事和刑事各占50%,作为数据2)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两组数据的相关性高达0.85,这些国家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是以司法系统的成熟和完善为基础;而这些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方面发展突出的国家,其司法指数与其环境绩效指数有非常高的相关性。2016年的EPI报告中特别强调,国家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形成通常缺少科学和量化依据,这使得环境政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发生背离;没有量化的依据,环境决策就会迷失方向,同时造成对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影响缺乏认识,导致本来就稀缺的环境治理资源被错误配置。不可否认,采用数据测量的方法指导环境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实现决策的“有的放矢”,这被证明是实施科学治理的较好方式。
三 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现状分析和研究路径
近年,我国学术界在“量化法治”发展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了环境法治评估的研究。
(一)环境司法的量化研究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主持发布的《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中,通过公众的满意度,评价中国环境法治的总体状况。[13]数据显示: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环境立法和环境治理的力度,但是在法律实施层面,还远没有达到公众满意的程度。在各项社会治理的指标中,环境依法治理的差评率是最高的,高达55.1%,超过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的依法治理差评率。在各项行政效率的指标中,处理污染事件的效率的差评率也是最高的,达到48.7%。就问责而言,由于政府疏于监管,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被问责的差评率高达64.5%,高于立法越权、审判不公、对犯罪分子不起诉和超期羁押的问责的差评率。这项评估表明,我国环境治理在依法治理程度、治理效率和问责上与公众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所面对的严峻现实。
在此背景下,我国司法机构越来越重视采用这种“量化法治”的评估模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发布的第一部环境司法白皮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虽然该白皮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估报告,但是在环境司法白皮书中,提供的法院内部多年来搜集的有关环境司法发展情况的数据,并有说明、总结和反思,其实就是一种“内部测评”的形式。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浙江省三级103个法院独立开展测评,并公布了首个“阳光司法指数”报告。这次测评包括审务公开、立案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和保障机制等5个板块,虽然是委托科研机构专业人员测评,但是法院内部事先“不通知、不动员、不布置”,[14]并开放了所有内部数据,积极配合测评,有效地保证了评估的客观性。
(二)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研究路径
截至2016年7月,我国已经成立了558个环境法庭,相关法律法规也得到完善,但也应该看到,很多“环境法庭”的设置决策缺乏定量依据,导致很多“环境法庭”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囧境。例如:贵阳环保法庭为了解决案件不足的问题,法官们打破“不告不理、司法中立”的原则,主动“上门揽案”“提前介入”来解决环境纠纷。[15]还有一些“环境法庭”的建立,是为了和当地的环境行政部门配合来解决环境污染事件,比如贵阳“两湖一区”的污染以及江苏太湖“蓝藻”污染都是当地成立环境法庭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法庭”的设置决策仓促,具有强烈的行政目的性,[16]并没有进行科学评估,也未考虑环境法庭的长远发展。这些实际情况说明了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受到强烈的行政驱动,其建立和运行都有着“运动式”治理的特征。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研究路径,宜放下理论制度的争执,着重于现实,尤其是案件统计研究,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开展内部评估;利用外部综合评估的数据,优化司法决策,促进环境司法的改革。
每一种路径和模式背后都代表着特定的价值观,每一种方法的背后还有一个“元方法”。“量化法治”作为认识和评价法律实际运行状况的有效方法,根源于实证主义之下的定量研究范式[17],通过可测量的数据展现法律的属性。从“量化法治”方法的发展和历史来看,有着定量研究传统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开发各种“法治指数”的先锋,例如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持续开发一套评价州初审判法院绩效标准,并不断地在各地试点和完善,30多年来得到有效的推广,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8]环境司法专门化问题,在司法改革和环境法治的大背景之下,已是持续升温的学术热点。而关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研究路径,究竟是制度梳理、理论反思,还是用实证方法检验现实状况。有学者指出: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为司法改革实验,其方案是否可行,不宜先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或者建构,而应首先“尊重客体”,慎谈“立法”和“改革”;重在“理解”和“阐释”。[16]那么“量化法治”的定量方法,可以发现大量行为和事实背后的客观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一些学者也已经开始认识到“量化法治”的方法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研究的意义,进行以环境案件数目和类型统计为主的研究,以阐释改革的规律和趋势。
四 “量化法治”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中国借鉴
“量化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IFCE评估框架,学习LEC在内部评估方面的优秀实践,应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环境案件统计分析数据库,参照IFCE的核心价值进行法院系统内部的评估。外部的综合性环境法治指数、司法指数,则是司法决策和制定发展计划的重要参照数据。“量化法治”不应该是为了评估而评估,为了“打分”而“打分”,而应是面向现实,解决问题。
(一)量化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决策依据
具体的国情决定了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方式,各国现有的“环境法庭”都采取了十分不同的形式。①比如在加拿大,有一种用行政机制来处理环境土地纠纷的习惯,民众遇到这样的环境纠纷,一般不诉诸法院,所以他们就设置了许多非司法的环境纠纷解决机构;而智利、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却与加拿大截然相反,法院等司法机构在解决环境纠纷的事宜上受到民众的信任。需要澄清的是:court和tribunal在很多国家是混用并不加以区别;但是也有一些国家court专指司法机构中的法庭,而tribunal则是非司法系统的纠纷解决机构,比如行政性的纠纷解决机构;而因此“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司法”也被广义地理解:就是具有纠纷解决和调处功能的机构。即使是在司法系统内建立所谓的环境法庭,每个国家也采取了不同形式②完全独立的环境法庭,比如前述的LEC、新西兰环境法庭;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置半独立的环境审判庭,又如美国佛蒙特州最高法院中的环境审判庭;法院中有法律专业的法官和非法律技术类专家法官,比如瑞典和智利的环境法庭。。虽然各国成功的尝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脱离具体社会背景分析司法形态是偏颇的。在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浪潮里,短时间涌现出了很多环境法庭,但有些环境法庭却最终被关闭,没有在决策前审慎地考察具体法治国情,是这些法庭失败的重要原因。
采取何种形式发展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由一国的政治体制、社会背景、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共同决定的。每个国家发展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共同追求是建立最有效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根据各国经验,我国环境司法机构的设置需要考虑以下关键问题:如由哪个机构来主导?公众对现在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是什么?现有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哪些问题?预算和人员问题如何调配?环境司法结构的设置是否会遇到阻碍?是否有解决环境司法问题的专业人才?是否有相应的环境司法专业人员?培训的机制?新的举措?如何加强公众参与环境司法,等等。外部评估决定了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方向、形式和措施。故外部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治理现状、法律发展现状,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民众的环境司法需求,对以上问题可以进行专门测量,用数据客观真实地描绘环境司法发展的基础,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决策的重要依据。如上文提及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就可以作为环境司法决策的量化依据。
(二)量化环境司法专门化面临的问题
司法决策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环境案件的数量。可以通过统计以往的法院中环境案件的数量,考虑地方现实情况来预测未来可能的环境案件数量。UNEP的报告中指出,很多国家在设计环境法庭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而导致环境法庭的规模和设置与现实的案件量不相符。如果通过合理的评估和预测,发现该地区的未来环境案件的数目不多,那么自然要对法庭的规模、人员、设置和经费予以合理的控制,不应该片面追求效果设置豪华型的环境法庭(UNEP报告中称之为“劳斯莱斯”式的法庭),避免发生“大炮打蚊子”的现象。而相反的情况:规模过小和人员经费过少的环境法庭不足以处理数目庞大的环境案件,从而使得环境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需要用定量方法事先对于环境案件数量做出合理的预测,能够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前叙的“环境法庭”因为没有足够的案源被迫关闭,如辽宁省先后在沈阳、丹东、大连等地设立了十余个环保法庭作为派出机构,但此后由于无案可审,除铁西和东陵两区外,其余试点均被撤销,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鉴于此,在决定是否设置环境法庭,在什么级别设置环境法庭以及设置什么规模的环境法庭都需要事先预测该地区每年可能产生的环境案件的数量,这个数量就决定了是否设置环境法庭及其规模。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正当性依据是环境案件的增多和环境案件的复杂,那么就需有具体的数据客观反映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从而指导环境司法决策;与其对环境司法专门化进行理论分析,不如放眼实践,用“量化法治”的方法对其展开客观精准的认识。
除了环境案件数目的预测对环境司法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外,在“环境法庭”的运行中,对其所处理的案件类型进行数据化梳理和分析,借鉴LEC的成功经验,引入“量化”方法对“环境法庭”的运行进行评估,客观评价“环境法庭”是否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发挥了作用①比如贵阳清镇法庭在2007年到2013年之间一共受理案件763件,其中刑事案件445件,占到了58%;说明该法庭主要是集中解决了环境刑事纠纷。有学者调查,在2010年清镇法庭公布的103件环境刑事案件中失火罪有58件,56%;非法伐木罪占37%;清镇法庭建立是为了解决当地的水污染问题,而成立之后解决的环境纠纷以刑事案件为主,且判决所施加的经济赔偿不足,这些案件的被诉人并不是那些污染企业,而是受教育程度低且相对贫困的当地农民。参见:Rachel Stern,The Political Logic of China’s New Environmental Courts,China Journal,2014(72):63.,是否在处理环境案件中实现了司法公开和公众参与,为环境法庭进一步的发展指出方向。通过这样的案件的评估分析,环境法庭发挥的功能和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
(三)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科学治理工具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环境行政部门执法监管乏力,环境法立法不完善,这些因素迫使国家采取了“动员型”环境治理模式[19],同时也将环境治理重任赋予了司法机关,希望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如火如荼发展背后,有着强烈的行政化目标导向和司法能动的影响,这使其目前的发展备受质疑,加之现实中地方的环境法庭的发展确实面临着合法性质疑,缺乏专门人才,缺乏专门的程序等问题,所以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伴随着诸多理论争论。从地方环境法庭的设置到最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建立,行政导向的背后是一种治理方式变革的疑问:司法机关在公共问题的治理上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能,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究竟有哪些不同的职责划分以及如何协调配合?在有关环境司法专门化和“环境法庭”争论背后,其实质是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科学治理,并且在法治的框架之下建构科学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治理能力。
“量化法治”方法在提高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工具作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治理核心在于过程的精准化、追求资源的有效配置已达到效率的提高。以量化手段对决策、管控、诊断、调整等过程进行精准描述是目前我国迫切需要的科学治理方法。[20]目前,我国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探讨,还主要是反思性、建议性的论点,对未来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理论的构建,并没有量化的、科学的检验体系来印证论点。而国外关于“环境法庭”的研究非常注重实践,用量化评估的方法来指导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科学发展。更可贵的是,“量化法治”的过程是不断地检验司法实践是否满足了公共的“法治需求”的过程,什么司法体制才能构建起环境法治?在精准化具体化的“法治评估”这把标尺之下,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任务,越来越符合公众对于公正司法的期待。“量化法治”方法,在环境法庭设置之前,为其提供决策依据;在发展过程中,对现状采用的评估手段加以描述又可以清晰地突显现有的问题;在整个动态过程中,为环境司法专门化阶段发展提供一个精细化的评价,把理想化的环境法治状态拆分为具体的指标,指出现实的状况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为未来的改革指明方向。对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科学测量,是司法改革和实现科学治理的有力工具。
(四)公众参与环境司法建设的新模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积极促使公众参与环境司法是一种共识和趋势,也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必由之路。量化方法一般参照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的双重结果,评估操作一般采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种方式。因此“量化法治”拓展了公众参与司法的方式,加强了公众参与司法的范围和程度,具有重大现实的意义。公民社会的强大,是西方许多国家出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原因之一。公众对于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涉及切身利益的水、土地的环境决策具有平等的知情权和实质参与权,这也是西方“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内容。环境决策涉及公共利益,本来就需要加强公众参与;而理想的环境司法治理的实现更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环境司法是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特点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司法白皮书中特别强调了树立现代的环境司法理念,其中的重点就是“公众参与”环境司法。我国目前的“余杭法治指数”、浙江省“阳光司法指数”都采取了公众参与评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的客观感受,起到了公众监督的作用。2014年余杭垃圾焚烧的环境事件引起很大争议,当年的法治指数为71.85,比2012年的73.66有明显跌幅。而这样的评估结果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倒逼政府用法治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20]所以“量化评估”是民众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司法的一个新的方式,也是十分有效能够直接导致决策改变的方式,应该充分认识到“法治评估”对于加强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中公众参与的作用。
五 结论
综上所述,在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过程中,相关国家把“量化法治”方法当作治理工具,在环境法庭的筹划、设置、运行和发展中,把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当做决策的依据,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环境治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相关国家的实践和指标体系值得借鉴,而指标体系反映出当今世界对于良好的环境司法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及时、可负担以及公众参与。
中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一开始主要是为了配合行政机关执法而建立专门机构,到在司法能动的影响下大力建设环境法庭,再到依法治国背景下为了实现环境法治从而引出了环境司法模式的变革,高级别法院出现了环境资源审判庭。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始终受到行政驱动的影响,许多司法实验需要得到上级司法机关的“认可”,这使许多司法决策难免偏离实际,这是导致环境法庭备受质疑同时也是一些“环境法庭”被迫关闭的主要原因。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取得一定成绩,但仍要看到其存在的诸多问题:80%的环境专门审判机构在基层法院;审判程序和管辖问题还没有在制度上理顺;缺乏环境法律专业人才;环境法庭中还没有引进专门技术人才作为审判人员参与案件审理。这些问题需要环境司法模式的变革,通过开发“环境法治指数”等测量工具,使环境司法决策、制度反思以及发展规划都建立在量化标准和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科学化治理;同时在评估的过程中强化公众参与,实现阳光司法。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目的是实现环境法治,实现环境法治就需要变革环境治理的模式,“量化法治”促进实现环境治理的科学化,为环境法治的建设贡献力量。
[1]George Pring,Catherine Pring.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M]∥Paddock L,Glicksman R,Bryner N.Decision Making in Environmental Law:VolumeⅡ.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2.
[2]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R].UNEP2016:1 -2.
[3]张 宝.环境司法专门化建构的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0.
[4]Pring G,Pring C.Greening Justice:Creating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R].Access Initiative 2009:6-9.
[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个目标改变世界[OL].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2017 -05 -29.
[6]巴黎协定[OL].http:∥www.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r01.pdf,2017 -05 -29.
[7]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7):109.
[8]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Court Excellence[OL].http:∥www.courtexcellence.com/~/media/Microstites/Files/ICCE/The%20lnternational%20Framework%202E%202014%20V3.ashx,2017 -08 -31.
[9]LEC’s Annual Reviews[OL].http:∥www.lec.justice.nsw.gov.au/Documents/Annual%20Reviews/2015%20Annual%20Review.pdf,2017 -08 -31.
[10]The Hon.Justice Brian J Preston,Chief Judge and Ms Joanne Gray,Achieving Court Excellence:The need for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R].Judiciary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urt Excellence,28 January 2016,Singapore.
[11]环境民主指数[OL].http:∥www.environmental democracy index.org,2017 -05 -29.
[12]2016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R/OL].http:∥epi.yale.edu/reports/2016-report 2017-05-29.
[13]朱景文.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中国法治评估指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9-112.
[14]最高法.全国首部阳光司法指数测评报告发布[R/OL].http:∥www.gov.cn/jrzg/2013 - 12/09/content_2545228.htm,2017-05-29.
[15]汪志球.贵阳环保法庭频频“亮剑”[N].人民法院报,2013-05-18.
[16]Wang Canfa.Specialized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J].China Legal Science,2013(28):35.
[17]孟 涛.论法治评估的三种类型——法治评估的一个比较视角[J].法学家,2015(3):21.
[18]Ingo Keilitz.Standards and Measures of Courts Performance[J].Criminal Justice,2000,4(1):559 -593.
[19]王树义,蔡文灿.论我国环境治理的权力结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3):155-166.
[20]钱弘道,王朝霞.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5(5):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