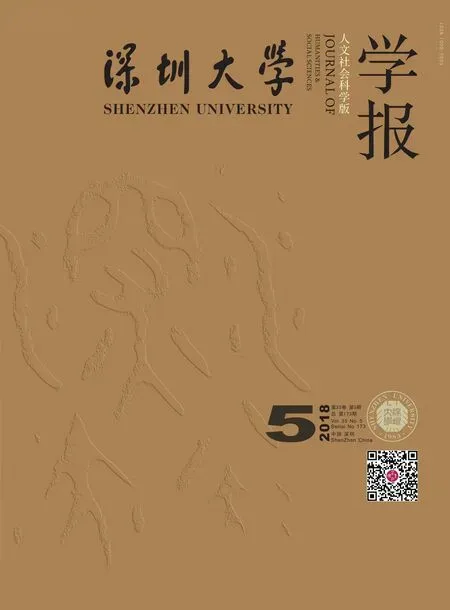新时期“人文精神”的传播与文艺理论的使命
张 弓 ,张玉能
(1.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993年6月号 《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谈话录[1],针对当时的“痞子文学”和商业化电影,提出了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3年之久广泛深入的讨论。在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再次回顾和反思这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目的和使命,持续不断地发展和繁荣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
一、新时期“人文精神”的传播
“人文精神”就是一种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诉求。所谓“人文主义”主要是一种来源于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理论,狭义指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反对基督教神学的,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广义的“人文主义”,泛指中西方历史上所有的肯定人、歌颂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原,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从词源上来看,人文主义是拉丁文humanism的译文,不过,humanism一词,还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汉译。我们认为,为了比较明确地划分不同的humanism,可以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以人为本”的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等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译为“人本主义”;把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对基督教神学的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译为“人文主义”;而把启蒙主义运动以后的提倡“人性”“人道”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译为“人道主义”。因此,简而言之,所谓“人文精神”就应该是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的思想追求和理论旨归。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文主义”之类的词,却很早就有“人文”一词。 《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这里是把“人文”与“天文”对举,天文是指自然界阴阳刚柔交替出现,人文是指社会中人伦文明令行禁止。观察天文就可以了解自然的时序变化,观察人文就可以教化社会的人伦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很早就讲究 “人文精神”,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人伦教化,也就是要教会每一个人如何做人,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因此,中国古代的“人文”或“人文精神”就是“教化”,教会每一个人的“为人之道”,因此,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在“立人”这一点上应该是相通的,不过,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主要强调人的个性独立,要求按照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做人,从神权和君权中解放人;而中国古代的“人文”和“人文精神”主要强调人的“教化”“化成天下”,按照社会(天下)的人伦秩序做人。因此,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所突出倡导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主要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诉求,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的“立人”和“成人”的思想。
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具体来说,就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浪涛从南到北席卷整个中国,社会上世俗化形成滚滚红尘,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日益浓盛,国民素质呈现“急功近利”趋势,道德风尚出现一定滑坡,社会上流行一种“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烘烘铜臭的市侩口号。这种风气也浸染到了文化艺术界,文化艺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也形成了商业化、商品化的潮流,作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作品日益变得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有些人公然声称自己就是“码字儿”赚钱吃饭的主儿,并不是什么“灵魂工程师”,要弃绝那些“虚假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鼓吹“我是痞子我怕谁”,并且申言就是要“游戏人生”“玩文学”,打起了“痞子文学”的旗号。与此同时,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的“商业化电影”也逐渐兴盛起来,以“票房价值”为主要追求目标,以“娱乐至上”“娱乐至死”为标榜。这些文化艺术现象形成了一股“躲避崇高”、不要理想和信仰、只要金钱和“票房”的潮流。与此同时,所谓“纯文学”逐渐萎缩,而“俗文学”以娱乐和广告而大行其道。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一批年青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聚集在一起,忧心忡忡,焦虑丛生,商量对策,做了一个谈话录,以《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实际上,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商品化及其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首先,这种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商品化是对“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致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逆反或反其道而行之。众所周知,从残酷的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方针政策,曾经为人民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仍然一直在以“政治运动”模式管理和发展文学艺术,一直走到“文化大革命”,把文艺园地折腾得百花凋零,杂草丛生,文艺成为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充斥着“假大空”“高大上”之类的虚假理想、伪装道德、矫情崇高,物资匮乏而精神疲惫的人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之下,也只能敢怒不敢言。等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紧接着“四五诗歌运动”的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然而,人民不可能总在抚摸伤口和反思过去中讨生活,也不能尽日里谈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倒是邓小平南方讲话给人民点燃了一点希望,尤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早已穷怕了的人民一些盼头,于是“向钱看”就使得不少人暂时忘记了改革开放的宏大目标,而寻求一点点实惠,市场经济卷起的“下海潮”也使得一些人只注意了在“商海”里捞钱,而忘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正是这样的现实让一些“文学痞子”“电影商家”顺市场经济大潮而干起了 “痞子文学”“商业电影”,让人们在他们的“调侃”和“娱乐”中排泄淤积很久的“阶级斗争恐惧症”“政治运动迫害症”。因此,只要能博得一笑、揶揄调侃生活、让人出口恶气、发出牢骚、活得轻松的东西,不管它有多庸俗、低俗、媚俗,都一时间受到了欢迎喝彩,而“码字儿的”就可以得到稿费,“扛摄影机的”也就可以坐收票房了。于是,这些现象引起了王晓明等年青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注意,发出了“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这些年青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确实具有很强的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其次,这种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商品化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的伴生产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是学习苏联的经验,搞市场经济,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遇到了严峻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新时期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本的本性是 “唯利是图”“追求最大的利润,可以不择手段”,而商品的本性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和“价值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和“商品”的本性的制约和影响。一时间市场经济的性质难以判定,因此邓小平和党中央告诫大家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先搞起来再说。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和商品的一些“唯利是图”“价值规律”等本性也就必然伴生出来。同样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展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作为特殊的生产和消费,文学作品作为特殊商品,当然也应该遵循资本和商品的基本规律,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和商品的规律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也必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这些对于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也会引起某些不适应和震惊感。于是王晓明们,包括当时的我们,都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反思起来,王晓明们的反应是十分自然的,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有许多真正值得深思、研究和改进的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艺术的“生产劳动性”和“非生产劳动”的二重性,文艺作品的商品的多重价值的特殊性,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文学艺术的这类“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也正在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方针政策[3]。第三,这种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商品化是文化艺术探索改革之路的记录。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40周年。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美学和文艺理论,在这40年中正在伴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早就研究过文学艺术生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 “生产劳动性”和“非生产劳动性”的二重性,文艺作品作为商品的多重价值性(审美价值、交换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这些论述,新时期“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重振“人文精神”的呼声,不仅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也有不可掉以轻心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今天仍然势在必行,那么文艺生产和文艺作品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也就必不可免,因此,关于“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诫声音也应该不绝于耳,警钟长鸣,让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此可见,今天回顾20多年前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仍然是具有不可漠视的现实意义的。
二、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与“人文精神”
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昭示我们,社会大变革必然促成文学艺术的巨大变化,美学和文艺理论首先应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正视“纯文学”的萎缩和“俗文学”的兴旺,清醒面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
新时期社会变革的最根本表现就是,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确立了由从前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市场的需求和供求关系来决定。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的商业化,文艺作品的商品化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而出现了,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以知识精英和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严肃文学艺术或者“纯文学”“纯艺术”的刊物,订数迅速下滑,而一些以广大市民、白领阶层、有闲阶层为对象的文学艺术报刊,却借助于电影、电视和当时迅速普及的网络而兴旺起来,加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营造的相对宽松的氛围,通俗文艺、大众文学、大众文化不断流行,形成了一部分人丢弃“人文精神”而“一切向钱看”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从而激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担忧和震惊,发出了召唤“人文精神”的呼喊。不过,在这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也有一部分人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商品化、商业化对于文学艺术的冲击,并非只有负面影响,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回到“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本义之中。
实质上,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高扬的人文精神来看,人文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基督教的神学和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力,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就以倡导“人的文学”的口号,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形式,在呼唤着大众文学、大众文艺、通俗文艺,西方小说的翻译和通俗小说的流行正是这种“人的文学”的具体表现。这种对“人的文学”的呼唤,还在1950年代钱谷融先生的 “文学是人学”的论述中再一次表现了出来。因此,“人文精神”大讨论肇始于钱谷融先生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似乎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精神”大讨论应该也与新时期19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息息相通,一脉相连。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摧残人性、侮辱人的尊严、禁锢人的解放的揭露和反叛,是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呼唤大众文艺、通俗文学和文艺世俗化的担忧和焦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实质来看,应该说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非人性、非人道主义、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异化”现象的揭露和表现。因此,从表面现象上来看,似乎“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从反对“痞子文学”和“商业电影”的“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而引发的,但是,从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本质和本质特征来看,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的“人的文学”到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呼唤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的“人的文学”。因此,“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于大众文学、大众文艺、通俗文学、通俗文艺的“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和震惊,实际上也是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商业化、商品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的一种思考和探索。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文学艺术,认真对待和研究的。
三、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坚持和弘扬“人文主义精神”
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昭示我们,美学和文艺理论同时也应该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弘扬 “人文主义精神”,从理论上澄清“游戏人生”“玩文学”“躲避崇高”等等论调的是非曲直、美丑真伪,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使命。
第一,“游戏人生”是与文艺的人文精神相悖的,“游戏人生”与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 “游戏说”实质上是南辕北辙的。新时期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讨论对于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提出了质疑。本来,一些作家艺术家提出 “游戏人生”的口号是一种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性、反人性、非人道、反人道的“异化”现象和“四人帮”的阴谋文艺而发出的逆反心理和反叛行为,在宣泄“阶级斗争恐惧症”和“政治权力迫害症”的“集体无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的“人文精神”的意味,但是,一旦把“游戏人生”当做了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那就与“人文精神”渐行渐远了。有人当时就指出了,“游戏人生”的关键就是“调侃人生”,把人生当做一种没有价值,不值得珍惜的东西来玩弄于股掌之间,视人生和世界为虚空和伪善,却并不是揭露和讽刺人生和世界的虚假和丑恶,反倒是嘲笑和戏弄人生和世界的真实和美好,戏弄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使人是非不分,真假难辨,美丑混淆。因此,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的最大危害就在于,使人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最终感到人生的无聊、空虚、伪善、无价值,也就是一种“痞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痞子们自己过的觉得百无聊赖,心安理得,却让人哭笑不得,前途迷茫。这种“游戏人生”的文艺观,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实质上也就是人性的扭曲,人的尊严的丧失,人的价值的泯灭,人的解放的无望。也许有人会把新时期 “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这种“游戏人生”与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游戏说”相提并论。实际上大错特错了,二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游戏说”的正式成立是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家康德。康德在论述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时候,提出了“文艺是自由的游戏”的学说。他所说的“自由的游戏”就是一种“无功利目的”的、无概念的、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也就是“自由的游戏”。这个“自由的游戏”突出了艺术的无功利性(区别于手工艺)、无概念性(区别于科学)、人类创造性(区别于自然)。实际上也就是把美和艺术视为同一的,为18世纪欧洲“美的艺术”的概念奠定了基础。席勒进一步发展了“游戏说”,把“游戏”当作艺术的起源活动来论证。他认为,人类的艺术是起源于人类实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的“精力过剩”而引起的“游戏”活动,同样也是指明了人类艺术的无功利性、自由性、创造性。同时,他还把人类的原始的“冲动”(本能)划分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两大类,这两种冲动是对立的,促使人类的人性分裂,而只有在人类产生了一种把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结合起来的“游戏冲动”时,才能够使人的人性完整起来,而这种 “游戏冲动”的对象也就是“美”。所以,美可以使人性的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的人性完整。因此,美与游戏冲动是不可分的,由此也可以看到美的特性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无功利性”、“自由性”。 因此,来源于“游戏冲动”和“游戏”的美和艺术就具有“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性”、“无功利性”、“自由性”。由此可见,美和艺术就可以使人恢复到“人性完整”的状态。在这里,“游戏”就是一种极其高尚的、重要的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着人的“人性完整”“人类自由”的活动。以后所有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比如,斯宾塞、谷鲁斯、伽达默尔都是从美和艺术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性”、“无功利性”、“自由性”,来把美和艺术与“游戏”联系起来,并且把“游戏”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性、人生的健全活动。因此,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反对的“游戏人生”与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游戏说”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
第二,“玩文学”是文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一种表现,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美学和文艺理论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玩文学”就是把文学当作玩具,也就是把文学当作闲着没有事情干时才做的,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玩物,因此,这里的关键是一个“玩”字,也就是“消遣”“消磨时间”,用“痞子文学”的说法就是“码字儿”。这可是完全违背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种文学艺术功能论。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是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的,也就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使人成为人”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文学)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唐代的古文运动说“文以载道”,宋代的理学家说“文以明道”,梁启超说小说可以通过“熏”“浸”“刺”“提”达到“移人”的功能,这些无疑都是在强调和突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功能。而“玩文学”的论调,却有意抹煞这些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实际上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戏耍”文学,不过,一般人“戏耍”文学是一种“消费”,是要花钱的,而“玩文学”的“码字儿”的主儿,确实要通过“玩文学”来赚钱的,也就是生财之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文学艺术的“生产劳动性”,也就是把文学艺术当作“谋生”“赚钱”的手段,当作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如果诗人像春蚕吐丝似的表现自己的天性那样来写诗,就不是一种“生产劳动”,而是“非生产劳动”;如果一个作曲家为了换取一顿午餐而写一支曲子,一个歌女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唱歌,那就是“生产劳动”。因此,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批评的“玩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生财之道”,是一种创造特殊商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玩文学”的论调是把“非生产劳动性”的文学艺术“异化”为“生产劳动性”的“稻粱谋”,消解了文学艺术的“非生产劳动性”的本性,而把文学艺术“异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化和商品化的 “娱乐”和 “玩具”,也就是在鼓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欲主义。那么,这样势必也就会把文学艺术由“与资本主义相敌对”的东西变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东西。这当然要引起当时倡导“人文精神”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反对和批评,因为“玩文学”论调已经让文学艺术及其作品 “沾满了铜臭”,成为了“市场的奴隶”。因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反对这种“玩文学”的论调。
第三,“躲避崇高”是文艺的“人文精神危机”的一种来源,实质上也就是一种丧失理想和信仰的危机。“躲避崇高”的论调,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其本意是要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艺术的“假大空”“虚假英雄主义”和“虚伪的崇高精神”,似乎还有一点反思批判的精神,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命题,却是极其有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没有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文艺倾向的一种遁词。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和信仰的表达,没有了理想和信仰,文艺也就失去了灵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和“自我实现说”等学说的观点,人类的需要是一个由低到高的不断发展的序列,一共可以分为7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或相属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7层需要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前面4个层次的需要可以叫做物质需要,因为它们是人类存在必需的不可或缺的需要,因而也叫做生存需要或者缺失需要;而后面3个层次的需要可以叫做精神需要,因为它们是人类在生存基础之上发展的需要,因此又叫做发展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最终都指向人类的“自我实现”,最终可以达到一种“高峰体验”的自由境界。我们可以看到,审美需要是一种在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发展需要,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的主要基础之一,而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的美和艺术则是人类“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的主要表现之一,它们直接指向人类的理想和信仰。因为人类的理想和信仰是人类在自己的“自我实现”过程中所追求的和为之奋斗的目的,因此它们就必然具有了崇高性质。所谓崇高,是在矛盾和冲突中表现人类实践自由的价值的美学范畴。崇高所感性显现的人类的实践自由,并不是一种已然实现的自由,而是一种克服困难和险阻而必然会达到的自由,或者叫做“未来必达的自由”,因而就表现出一种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在人类实践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艰难和险阻,人类却是应该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去克服矛盾和冲突,排除艰难和险阻,去实现自由的理想和信仰,因此,就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审美特征,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品格,而具有这种崇高特征的人物也就显示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躲避崇高”就是一种懦弱和胆小的表现,它必然消解了英雄主义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是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一种变相表现。在新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躲避崇高”论调必然遭到了批评和质疑,因为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充满着风险、布满荆棘的征程,如果没有崇高精神的鼓舞,势必不可能夺取改革开放事业的最终胜利。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国古往今来的神话传说和文艺作品就已经以神话传说和浪漫想象的方式,记录和抒写了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品德,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的追求理想和信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人们耳熟能详的 “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未悔”的屈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怒发冲冠”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等无数先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焦裕禄、王进喜、雷锋、邓稼先等等先进人物,都是中华民族崇高精神和品德的形象显现。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各族人民正在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英勇奋斗,我们绝对不应该“躲避崇高”,我们更加需要用文学艺术作品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和品德。
总之,新时期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但是,它所提出的“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新时代美学和文艺理论认真反思、研究,当时讨论中大力反思批判的“游戏人生”“玩文学”“躲避崇高”等等有害论调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不良倾向,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对,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进行现实的考量和审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发扬“人文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