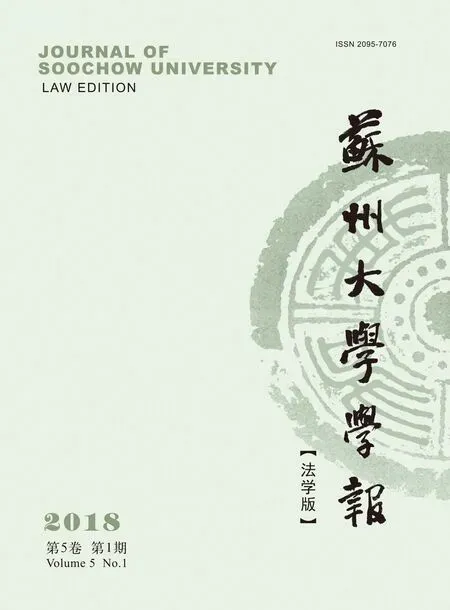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教义学认定—引入防卫过当条款的尝试
尹 子 文
一、引言
近年来,涉及正当防卫相关问题的案件往往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邓玉娇案到最近的于欢案,在为反抗不法侵害而致人伤亡的场合,行为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抑或是普通的犯罪,司法机关、理论界与民众的立场往往不尽相同。但比较没有疑问的一点是,防卫行为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因为从防卫效果来说,不法侵害由不法侵害人实施,只有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才能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210页。从权利限制的面向来看,行为人只能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防卫权,而不能滥用权利,殃及无辜。②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207页。而在一些案件中,由于各种原因,防卫行为虽然一开始指向的是不法侵害人,但最终却伤到了无关的第三人:
案例1:2013年2月10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秦某甲与同村村民李某、张某、刘某等人在秦某乙家喝酒,在喝酒过程中,刘某与秦某甲争吵,被在场的李某、张某等人劝解。之后,秦某甲与李某在回家途中被任某、刘某、张某追至李某家门口,任某和刘某殴打秦某甲和李某,秦某甲持酸刺棒进行防卫时将一旁的张某眼睛误伤。经法医鉴定:张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伤残等级评定为七级。法院认定秦某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①(2014)岷刑初字第162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2:1993年2月9日,黄某与本厂工人刘某在上班时因铲沙子发生纠纷,后经车间工人劝解平息。2月15日下午,刘某纠集多名同厂工人到车间找黄某,对其进行殴打。黄某脱身跑到本厂办公室躲避,但刘某等人继续追赶,后被车间主任制止。黄某回到车间上班,刘某等人再次对其进行拳打脚踢,黄某则一直躲避退让。当退至本车间侧门一工具箱边时,随手操起放在工具箱上的一铝合金浇口模具,向刘某砸去,刘某头一偏,结果砸中前来劝架的同车间工人马某,致其当即倒地,头破血流,经医院抢救无效,于3月23日死亡。法院认定黄某构成过失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②(1993)祁刑初字第49号判决书。该案发生于新刑法(97刑法)之前,适用的是旧刑法(79刑法)第133条。该条规定:“过失杀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在上述案例中,秦某甲在防卫的过程中误将并未实施不法侵害的张某刺伤,而黄某本来是将模具砸向不法侵害人刘某,却误将前来劝架的马某砸伤致死:二人的防卫行为本来都是指向不法侵害人,却因为打击失误而伤害到无辜的第三人。对于如何评价这种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刑法理论上存在激烈争论,比如正当防卫说、紧急避险说、假想防卫说、假想避险说、事实错误说、完全的犯罪说,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学说争论进行梳理,挖掘此类案件中所潜藏的深层次问题,并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即将上述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情形归入防卫过当,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以期全面评价防卫行为的不法与责任,使行为人获得法定的减免处罚待遇。
二、学说梳理与问题发掘
对于如何处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问题,不同学说的关注点各有侧重:正当防卫说与紧急避险说试图从违法性层面来论证行为人的行为为阻却违法;假想防卫说、假想避险说与事实错误说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行为人的责任形式上,认为在误伤第三人的场合,阻却故意犯罪的成立;而完全的犯罪说则提出了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甚至丧失的问题。下面分类阐释。
(一)正当防卫说、紧急避险说
1.正当防卫说
该说认为,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在反击不法侵害时,虽然附带产生了第三人损害的后果,但行为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并不丧失,行为人的行为仍然在整体上成立正当防卫。③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208页。也有修正的观点认为,行为人在对不法侵害人实施反击时,即使偶尔对第三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仍然可以认定为具有正当防卫的相当性;只不过在防卫行为可能危及第三人生命的场合,防卫人可以而且能够安全退避时,应对其科以适当的退避义务;此外,第三人也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④参见李齐广:《涉及第三者的防卫行为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5期。
但正当防卫说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如果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属于正当防卫,那么《刑法》第20条第1款所要求的正当防卫的对象限度,即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就变得不重要,甚至被消解掉了。后果就是,行为人在制止不法侵害时,可以不用考虑其防卫行为是否会对周围的无辜人员造成伤害;而对于无辜的第三人来说,就必须忍受该防卫行为,而不能就此对行为人实施正当防卫。具体到案例2,前来劝架的马某就只能忍受被模具砸伤致死的后果,而不能针对黄某实施正当防卫。即使按照上述修正后的正当防卫说,第三人也只能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能对行为人的防卫行为采取避险措施。即在案例1中,当秦某甲挥棒而来时,张某首先应该躲避,在无法躲避而且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但问题在于,张某和马某并未参与针对行为人的不法侵害,⑤在案例2中,从事前来看,甚至可以说马某帮助了行为人,因为马某来劝架也是为了制止刘某等人对行为人的殴打。却被剥夺了正当防卫权,事实上也遭受到了比不法侵害人更为严重的伤害,而正当防卫说却对此视而不见,这难言公平。简言之,将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效果扩展至第三人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成立正当防卫所需要的对象条件,不符合《刑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而且也不适当地扩张了行为人的防卫权限,这对于无辜第三人来说是极其危险和不公平的。①类似的结论性观点参见陈璇:《侵害人视角下的正当防卫论》,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
2.紧急避险说
该说认为,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在对不法侵害人的关系上,可以说行为人是受到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对第三人的关系上,可以认为行为人遭受着现实的危险;所以行为人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在对不法侵害人的关系上是正当防卫,而针对第三人则可以说是避险行为,只要没有损害法益的权衡,就可以成立紧急避险。②参见[日]大塚仁:《刑罚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类似的观点参见:陈家林:《防卫行为与第三者法益侵害》,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具体到案例1,秦某甲挥酸刺棒进行反击的行为,在针对任某、刘某的意义上构成正当防卫,而在对张某的关系上则可以说是避险行为,只要符合法益权衡,就构成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成立紧急避险不仅要求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还要求行为人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躲避危险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损害第三人的方式来避免危险,即避险行为必须是“不得已”的。但是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不得已”要件很难满足:其一,行为人可以通过逃跑来躲避危险,而不必将危险转嫁给第三人;其二,即便行为人来不及逃跑,也可以通过直接向不法侵害人反击来制止危险,而没有必要伤害第三人。具体到案例1,秦某甲至少可以通过逃跑来避免危险,即便是其不愿意或者说可以不逃跑,也可以通过直接反击任某、刘某来避免危险的发生,而不必伤害无辜的张某。事实上,秦某甲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反击的过程中误伤了张某。同样,在案例2中,黄某也明显是可以通过对刘某等人的反击来避免危险的发生。另外,从事前的角度来看,在案例1及案例2中,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伤害后果明显是偶然的、意外的,这一点多少也可以辅证在这种场合不符合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因为如果对第三人的伤害是“不得已”的,那么该结果的出现应该是必然的,至少是大概率事件,而不是偶然所致。其次,从避险效果来看,在案例1及案例2中,如果连直接反击侵害人都不能避免危险,那就更不可能通过将危险转嫁给第三人来躲避危险;而如果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反击来避免危险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伤及第三人了。换言之,在上述场合,从事前的角度来看,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往往并不能转嫁或避免自己可能遭受的危险,因而不存在避险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上述场合绝对不可能构成紧急避险。比如乙绑架小孩丙作为人肉盾牌,准备炸毁大楼,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乙,但同时也造成丙重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制止乙即将实施的炸毁大楼的危险行为,就必须击毙乙;但因为乙将丙作为挡箭牌,要想击毙乙,就难免伤及丙;因此,甲伤及丙的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可以构成紧急避险。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将丙作为乙实施犯罪的工具,将三角关系简化为两方关系,进而将甲的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说认为此处存在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竞合。换言之,在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不能躲避且实施反击行为的同时必定会伤及第三人时,才有成立紧急避险的余地;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设定,因而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
综上所述,正当防卫说与紧急避险说都试图论证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阻却违法,但上述情形要么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要么不符合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被正当化。但是透过对正当防卫说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普通的因方法失误而伤及第三人的情况相比,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虽然不构成正当防卫,但是从事前来看,该防卫行为指向不法侵害人,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存在一定的防卫性。④这可能也是正当防卫说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归入正当防卫的主要原因。
(二)假想防卫说、假想避险说及事实错误说
1.假想防卫说
假想防卫说是日本司法判例的观点。日本曾发生与案例1、2相类似的案例,基本案情如下:在年轻人团伙间的斗殴中,被告人想要对与自己的亲哥哥乙互相争夺木刀的对方团伙中的甲施以暴行,在急速倒车时,撞到了甲的右手(但是并未导致甲受伤),还撞到了乙,导致乙被碾压致死。另外,被告人急速倒车的原因是为了赶走对方团伙成员救出乙与其一起逃走。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除成立对甲的暴行罪之外,还成立对乙的伤害致死罪。而二审的大阪高等裁判所则认为:其一,被告人对甲实施的暴行,虽然该当于暴行罪的构成要件,但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其二,甲和乙在构成要件的评价上不是等价的,不能根据法定符合说,认为被告人对乙的侵害也有故意;其三,乙并不是不法侵害人,被告人主观上是为了实施正当防卫而实施暴行的,其对乙的侵害属于广义的假想防卫的一种,阻却故意;其四,在本案中,被告人受到激烈的攻击,产生了剧烈的心理波动,因此认定被告人对乙的侵害存在过失也是困难的。①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以下。简言之,假想防卫说的基本观点是,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第三人并未实施不法侵害,但防卫行为却导致了第三人的损害,这属于假想防卫,阻却故意。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211页。
但是假想防卫说也不是没有疑问。就第三人而言,其没有实施不法侵害,不是不法侵害人,行为人要想对第三人构成假想防卫,其必须针对第三人存在防卫意识。可不管是在案例1、2还是日本的司法案例中,行为人压根没有认为第三人实施了不法侵害,也没有据此对第三人产生过防卫意识;换言之,行为人所具有的防卫意识是针对不法侵害人的,而不是针对第三人,因此也就谈不上针对第三人的假想防卫。③类似的立场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周光权:《刑法总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或许,假想防卫说的逻辑在于,将行为人对不法侵害人的防卫意识转用至第三人,据此来肯定行为人对第三人具有防卫意识,或者认为就假想防卫的成立而言,行为人只要具有防卫意识即可,至于行为人的防卫意识到底是针对谁并不重要。可是,这与假想防卫说的立场存在矛盾,其一方面认为,不法侵害人和第三人在法律评价上是不一样的,在故意的认定上不能将二者同等对待;但另一方面,却恰恰在阻却故意的防卫意识的认定上,将不法侵害人与第三人同等对待,而忽略了二者的差异。
2.假想避险说
如前所述,在案例1及案例2中,行为人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误伤了无辜的第三人,似乎符合紧急避险的形式外观,但是其并不满足紧急避险所要求的“不得已”条件,不构成紧急避险。对于这种情形,有学者将其归入假想避险,从而否定行为人构成故意犯罪。④参见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39页。有德国学者也倾向于将这种情形归入假想避险(Vgl.,Schönke/Schröder/Perron,StGB,29.Aufl.,2014,§ 33 Rn. 10.;Kindhäuser/Neumann/ Paeffgen,StGB,4. Aufl.,2013,§ 33 Rn. 13.)。
与假想防卫类似,要成立假想避险,行为人就必须具有避险意识。但问题在于,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如何来肯定行为人具有避险意识?持假想避险说的学者指出,在行为人所具有的反击意图中实际上也包含着避免现实发生的危险的意思,即紧急避险的意思。⑤参见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39页。换言之,该说是想通过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针对不法侵害人的防卫意识中分解出“避免现实发生的危险”的意识,即紧急避险的意识,以此来论证假想避险的成立。的确,不管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险,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自己遭受损害,因此当然可以从行为人的防卫意识中分解出避免现实发生的危险的意识,这个意义上的避险意识是一个公约数性质的基础性存在。但是正当防卫与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区别在于: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而攻击性紧急避险则是通过向第三人转嫁风险的方式来避免自己受损;在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场合,存在危险源、行为人、第三人这三方关系,行为人要想构成假想避险,其具有的避险意识应该是“通过将风险转嫁给第三人或者损害第三人法益的方式来避免危险”的意识,而不是笼统地避免危险的意思。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就很难将假想避险与假想防卫区别开。而在案例1及案例2中,可以说行为人仅有避免危险的意思,但没有“通过转嫁风险”来避免自己受损的意识,不能构成攻击性紧急避险意义上的假想避险。①与攻击性紧急避险相对应,防御性紧急避险是直接针对危险源的避险行为,在上述案例1、2中,可以从行为人的防卫意识中分解出防御性紧急避险意义上的避险意识。但是,这里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行为人也具有紧急避险的意识,其构成真正的防御性紧急避险(或者说对行为人更有利的正当防卫)而不是假想避险。退一步讲,即使将此处的真正的防御性紧急避险评价为对应的假想避险,其也与第三人无关,不能解决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问题。换言之,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客观上出现的是类似于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外观,而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的是(从防卫意识中分解出的)防御性紧急避险意义上的避险意识,二者发生错位,不存在成立假想避险的对应关系。从亲缘关系上来看,防御性紧急避险更接近于正当防卫,而不是攻击性紧急避险,将上述情况认定为攻击性紧急避险意义上的假想避险也不妥当。
3.事实错误说
事实错误说认为,案例1与案例2不属于假想防卫,而应该按照事实错误的一般原则进行处理,即行为人不构成故意犯罪,主观上有过失且法律处罚相应过失犯罪的,构成过失犯;主观上没有过失的,构成意外事件。②参见陈兴良:《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57页;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郭泽强、张艺娇:《正当防卫的第三者效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7期。
总结来看,以上三种学说都认为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不构成故意犯罪,但论证思路各不相同。事实错误说认为,行为人是对一般的构成要件事实没有认识,因而不构成故意犯罪;而假想防卫说与假想避险说则认为,行为人对作为正当化事由前提的事实存在误认,阻却故意。但假想防卫说与假想避险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说明行为人具有“误以为存在正当化前提”的意识,即对第三人存在防卫意识或者避险意识?相比较而言,事实错误说的观点较为可取。因为在案例1及案例2中,行为人虽然对不法侵害人存在“伤害的未遂”,或者像日本的司法案例那样对不法侵害人存在暴行,但是这里所谓的“伤害的未遂”或者“暴行”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因而属于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也即,就对不法侵害人而言,行为人构成正当防卫,不存在不法;而责任是对不法的责任,既然(就对不法侵害人而言)不存在不法,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作为责任形式的故意的问题,③如果把正当化事由作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进行看待的话,也可以说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对不法侵害人的“伤害的未遂”或者“暴行”不满足消极的构成要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探讨所谓的针对构成要件的故意。进而也无需探讨所谓的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故意能否转用至第三人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只需要判断行为人对给第三人造成的伤害是否有认识,进而确定是否存在故意。在案例1及案例2中,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对不法侵害人的反击)行为会伤到第三人,因而阻却故意犯罪。
(三)完全的犯罪说
该说认为,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对第三人法益的损害没有起到保全法益的作用,也不符合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更没有带来避险的效果,因而行为人的行为不属于紧急行为,原则上应该成立犯罪。但是,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期待行为人不侵害第三人的法益,因而欠缺期待可能性。因此,根据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行为人的防卫行为虽然违法,但一般能够阻却责任的成立。④参见陈家林:《防卫行为与第三者法益侵害》,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李齐广:《涉及第三者的防卫行为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5期。
完全的犯罪说主要面临两方面批评:其一,因为事后不存在避险效果或防卫效果便肯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做法并不恰当,即其选择的事后判断标准存在疑问,同时其所要求的避险效果也是一种过剩的要求;⑤参见陈家林:《防卫行为与第三者法益侵害》,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李齐广:《涉及第三者的防卫行为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5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是不能从事后来考察避险效果,但如果从事前来看,行为本身也不包含任何避险效果,那就没有实施紧急避险的必要了。其二,根据期待可能性进行出罪的做法也存在疑问。期待可能性毕竟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误用或者滥用期待可能性会损害法秩序。①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207页。
的确,完全的犯罪说在归罪思路上存在严重的方法缺陷,但是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可能存在期待可能性丧失的情形。比如在前述的日本司法判例中,虽然被告人在防卫过程中误伤其亲哥哥乙,但是法院同时指出,“被告人受到激烈的攻击,导致剧烈的心理波动,所以认定被告人的确存在(成为过失责任之根据)的注意义务也是困难的”,即在本案中,因为面临严重激烈的不法侵害,被告人存在剧烈的心理波动,难以期待行为人注意到其倒车行为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乙。
而“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有无的问题(是否阻却责任),还存在程度问题(是否减轻责任)”②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326页。,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虽然存在过失但期待可能性大幅下降的现象更为普遍。比如,在案例2中,法院认定黄某对给马某造成的伤害存在过失,但是当时黄某面临着刘某等众人长时间持续的拳打脚踢,难免产生恐惧、慌乱等高度紧张的状态,期待其在反击的过程中避免伤害到无辜第三人的可能性明显比较小。换言之,虽然可以认定黄某存在过失,但是其期待可能性已严重降低。同样,在案例1中,秦某甲受到任某等人的不法侵害,也难免会产生害怕等紧张情绪,从而较难期待秦某甲在挥动酸刺棒自卫时准确地拿捏行为的精准度,进而避免伤害到无辜的第三人。因此,在该案中,秦某甲也存在期待可能性下降的情况。
其实,不管是从经验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可以认定,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因为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慌乱、害怕、惊恐等紧张情绪,导致期待可能性降低,从而导致责任程度下降。③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388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235页;钱叶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及限定性适用》,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前述日本的司法判例也佐证了这一点。此外,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案例,《九朝律考》“汉律考”中记载:“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除了“原心论罪”的思路外,本案也表明,在面临父亲被殴打时,子女“莫不有怵怅之心”,即在至亲被殴打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害怕担心等心理动摇。这其中包含两重含义:其一,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期待可能性的降低是一个普遍情形;其二,行为人是因为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即防卫情状)而产生慌乱、惊恐、害怕等紧张情绪,进而导致期待可能性降低。换言之,在这里,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具有发生概率上的普遍性和产生原因上的与防卫情状的关联性。前者决定了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期待可能性降低的认定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后者则表明,此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有其特殊性。此外,结合前面关于正当防卫说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最后伤到的是无辜的第三人,但是从事前来看,防卫行为是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的,具有防卫性,也即,从发生环境上看,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发生在一个包含防卫性的行为过程中,这补强了此处期待可能性判断的特殊性。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如何来评价普遍存在的期待可能性的降低甚至丧失的问题?基于法治的理念,期待可能性的适用应该尽量明文化,否则可能与法律适用的平等性、权利分配原则、法律的明确性及法安定性等存在龃龉。④Vgl.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 22 Rn. 142f;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327页;张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刘艳红:《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定位》,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换言之,对期待可能性的评价来说,法定的评价事由明显优于超法规的评价事由。因此,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可以全面评价上述期待可能性降低程度的法定事由。但显然,现有理论并未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四)小结
对于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来说,通过对现有理论学说的梳理可以确认以下结论:其一,除了极少数符合紧急避险的情况外,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并不阻却违法;其二,对于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行为人不构成故意犯罪,存在过失(且需要刑法处罚)的构成过失犯罪,不存在过失的属于意外事件;其三,从经验上讲,因为行为人面临不法侵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期待可能性降低甚至丧失的情况。简言之,在现有理论学说的框架内,除了不构成犯罪的情形,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构成过失犯。
但是,这对于解决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问题来说,还不够理想:其一,与普通的因打击失误而伤及第三人相比,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有其特殊性。具体来说,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防卫行为并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但是从事前的角度来看,防卫行为本身是指向不法侵害人的,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即从效果上来看,行为具有防卫性。但是,现有理论学说并未重视其对于处理误伤第三人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中普遍存在的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问题,现有理论并未给出完善的解决办法,更不用说从与防卫情状相关联的角度来评价此处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特殊性。
三、防卫过当条款的引入
如前所述,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因防卫情状而起,发生于防卫行为中。对于如何评价此处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情况,从法治的理念出发,法定的评价事由肯定优于超法规的评价;从评价效果来看,能够全面反映案件特殊事实的具体的评价事由明显优于抽象的评价。而与防卫情状相关联,涉及行为的防卫性以及期待可能性内容的评价事由只有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条款,即《刑法》第20条第2款。本文认为,将《刑法》第20条第2款引入对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完整、全面评价行为人的不法与责任程度,尤其是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程度,而且能与前述各种理论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兼容。
(一)形式理由
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该条规定,防卫过当的成立有两个关键性的要求:其一,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其二,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首先,如何来理解该款规定中的“正当防卫”?没有疑问的是,防卫过当是违法行为,而正当防卫阻却违法,①或者可以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及第2款的规定说,认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根据同一律的要求,一个行为不可能既构成正当防卫又构成防卫过当,因此,当我们说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时,就意味着其不是正当防卫。所以,《刑法》第20条第2款表述的“正当防卫”并不是说作为防卫过当的该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应该是指作为防卫过当的该行为具有防卫性。②在此意义上,司法判决中常常出现的“该行为不是正当防卫,更不可能构成防卫过当”的表述也值得反思。具体来说,就是在面临不法侵害时,从事前来看,该行为指向不法侵害,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③此外,如果认为防卫意识是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的话,则还应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该过当行为时同时具有防卫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行为要想构成防卫过当,(从事前来看)必须具有防卫性。而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虽然防卫行为最后误伤第三人,但是从事前来看,其指向不法侵害人,明显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满足防卫性的要求。比如在案例2中,在面临刘某等人的殴打时,黄某随手将身边的浇口模具砸向刘某,却最终伤到了前来劝架的马某;但从事前来看,黄某的行为明显是出于制止刘某等人殴打的目的,针对不法侵害人刘某,而且也明显具有制止刘某等人不法侵害的可能。
对此,黎宏教授质疑道:“或许有人会说,上述情况(即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引者注)本质上还是正当防卫,只不过超出了防卫的必要限度,造成了无辜的第三者的损害而已,因此可以将其看作防卫过当。但是,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防卫过当虽然不是‘不负刑事责任’的正当防卫,但基本上还是具备正当防卫的主要特征。即行为人出于防卫目的,指向不法侵害人,实施了反击行为,其在本质上还是紧急行为,只是在防卫限度上有误差而已。但是,在上述案例中,损害结果发生在和引起紧急不法局面的加害人完全无关的人身上,对于该无辜第三者而言,该反击行为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反击性质。因此,这种行为怎么能说是防卫过当呢?”①黎宏:《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界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6期(上)。从黎宏教授的表述来看,其也认为,要想构成防卫过当,行为本身必须包含防卫性(其所谓的“主要特征”),即“出于防卫目的,指向不法侵害人,实施了反击行为,其在本质上还是紧急行为”,那么按照黎宏教授的这种逻辑,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当然应该构成防卫过当,因为虽然最后伤到了第三人,但也是“行为人出于防卫目的,指向不法侵害人,实施了反击行为,其在本质上还是紧急行为”。换言之,对于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上述观点仅看到了防卫行为对第三人的伤害,但没有认识到防卫行为所具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性,而且从事前来看,防卫行为更多地包含了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而不是对第三人的伤害。总之,在行为的防卫性上,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与传统的防卫过当不存在差别。
其次,如何解释该款规定中的“必要限度”?传统刑法理论认为,防卫过当仅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防卫强度的情形。②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版,第136页。而对于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时间限度,刑法理论上称为防卫不适时,对于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刑法理论上称为防卫第三人,二者都不属于防卫过当。换言之,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刑法》第20条第2款中的“必要限度”就是指正当防卫所要求的必要的防卫强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就是明显超过必要的防卫强度。但问题是,将“必要限度”仅仅解释为必要的防卫强度的规范或法理依据何在?或许是因为,传统刑法理论一般将正当防卫所要求的强度条件描述为“正当防卫未超过‘必要限度’”,因此就将《刑法》第20条第2款所规定的“必要限度”等同于防卫强度意义上的“必要限度”。如果是这样的学术惯性导致了上述结论,那只能说传统刑法理论下意识地用理论术语代替了法律术语,从而限制了对法律文本可能含义的发掘。
而回到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可以发现,正当防卫的成立不仅有防卫强度的限制,还有时间限度(即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对象限度(即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要求。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逾越正当防卫的时间限度和对象限度的都应该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都有构成防卫过当、进而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可能。而像案例1及案例2所展现的情况,就属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由于方法不当而伤及第三人,逾越了正当防卫的对象限度,并造成了第三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损害,明显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所描述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防卫人的防卫行为虽未造成不法侵害人任何损害,但却造成围观的他人丙重伤,造成他人重大损害。显然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在客观上造成重大损害,如果防卫人主观上具有罪过的话,应承担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③陈正云:《论准确认定和把握防卫过当的标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1期。
综上所述,从行为的防卫性来讲,与传统的防卫过当一样,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从事前的角度来看,行为本身指向不法侵害者,包含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同样具有防卫性。从行为的过当性来讲,二者都逾越了正当防卫的限度,只不过一个是强度限制,一个是对象限度。按照黎宏教授的描述,也可以说二者都是“行为人出于防卫目的,指向不法侵害人,实施了反击行为,其在本质上还是紧急行为”,只不过一个是“在防卫限度上有误差”,一个是“在对象限度上有误差”。而不管是强度限制,还是对象限度,抑或是时间限度,在规范评价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成立正当防卫所必须的条件,逾越这些限度条件的,都有成立防卫过当、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可能。因此,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归入防卫过当的范畴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的文义内涵,也从反面证成了成立正当防卫所需要的诸种限度条件。
(二)实质根据
除了外观上的类似,要想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归入防卫过当,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进而获得减免处罚的待遇,还必须说明其与传统的防卫过当在减免处罚的原因方面存在实质的相似。关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德、日等国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通过了解德日刑法中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原因,可以更准确地确定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行为人因慌乱、恐惧或惊吓而超越正当防卫的界限的,不处罚。对于防卫过当免除处罚的原因,“责任的双重减轻理论”认为,在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行为的不法程度在其所保护的法益范围内得到了减轻,相应地也带来责任的减轻;此外,行为人在虚弱时的情绪冲动(即慌乱、恐惧及惊吓)下,其正常的自我决定能力被大大削弱,这使得行为人适法意识的形成变得更加困难,进而导致责任的减轻;这种双重的责任减轻导致过当行为达不到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而被免除处罚。①Vgl. Jescheck/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5.Aufl.,1996,S.478 u. 491.;Stratenwerth/Kuhle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6.Aufl.,2011,§ 9 Rn. 99.;Rengi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3.Aufl.,2011,§ 27 Rn.1.;Kühl,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7.Aufl.,2012,§ 12 Rn. 129.以刑罚目的为导向的观点认为,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虽然行为人是有罪责的,但是在虚弱时的情绪冲动下,即便行为人实施了过当的防卫行为,其仍然是一名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公民,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另外,即使对这种因虚弱时的情绪冲动而过当的行为不进行处罚,也不会引起一般人的模仿,不会动摇法和平,因而也没有一般预防的必要;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必要性的丧失使法律放弃对行为人的处罚。②Vgl.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 22 Rn. 69.
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超过防卫限度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对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原因,日本刑法理论主要有四种观点:责任减少说认为,行为人在面对对方攻击这种紧急状态时,因恐惧、惊愕等心理动摇而减少了期待可能性,因而具有减免刑罚的可能。③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违法减少说认为,防卫行为虽然过当,但毕竟是针对紧迫的不法侵害,也保全了正当利益,因而在此限度内能够肯定违法性的减少。④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以下;[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违法责任减少说认为,较之单纯的法益侵害行为,在防卫过当也属于针对急迫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其违法性的减少;但是如果要解决防卫过当可以免除处罚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心理的压迫状态所导致的责任的减少。⑤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以下。违法或责任减少说认为,应当从违法或者责任的减少中寻求防卫过当减免刑罚的根据,即便只有其中某一方(违法或者责任)的减少,也应该根据减少的程度,至少肯定减轻刑罚的可能性。⑥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不法的减轻、责任的减少、预防必要性的降低等方面进行分析:
1.不法的减轻。就不法的减轻而言,理论上一般有两种说明路径:一种观点从攻击者的要保护性减少的角度来肯定过当行为不法的减轻;⑦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利益不同于单纯的法益侵害行为,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保护了面临侵害的法益,并实现了法确证,存在不法的减轻。⑧Vgl. Kühl,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7.Aufl.,2012,§ 12 Rn. 129.
可以确定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行为人在损害某一法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另一法益就肯定其行为存在不法的减轻。比如,医生甲为了急救失明患者,便强制取下一名路人的眼角膜给患者移植。在这里,不能因为甲在损害路人的同时也救了病人,便认为甲的行为包含不法的减轻。但是,在法益冲突的场合,法益之间的比较与取舍要么不可避免,要么为法律所允许。比如,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行为人通过损害他人较小法益的方式来避免自己的重大法益受损;又如,在义务冲突的场合,一法益必定会成为保护另一法益的手段,该法益的牺牲不仅在事实上不可避免,而且也为法律所允许。而在防卫过当的场合,因为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法益冲突的局面同样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允许行为人在必要限度内予以反击,其在此限度内给攻击者所造成的法益损害为法律所允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结果非价。换言之,过当行为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违法的,但其违法的确证经过了正当防卫阶段的判断,又因为在正当防卫限度内给攻击者所造成的损害为法律所允许,所以其不法程度应在此范围内予以扣减。①类似的观点参见许恒达:《屋主的逆袭——再论延展型防卫过当》,载《月旦裁判时报》2015年第41期。具体来说,应该以假定的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行为为参照,以此来确定过当行为的不法程度。例如,在对于制止不法侵害来说伤害即已足够,但却将攻击者射杀的的场合,如果将单纯的伤害行为的不法标记为N,将单纯的射杀行为的不法标记为N1,那么虽然可以说行为人实施的射杀行为是过当的、违法的,但其不法程度应该标记为N1—N,而不是N1。而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N1—N的值不是极小且N1的值较大时(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才能说行为人的射杀行为是防卫过当。
与单纯的因打击失误而伤及第三人一样,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虽然最后造成第三人受伤,但是从事前来看,防卫行为指向的是不法侵害人,其不仅包含对无辜第三人的伤害(的可能),还包含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伤害的危险,甚至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更大。但与单纯的因打击失误而伤及第三人不同的是,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中,因为行为人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法律允许行为人在必要限度内采取针对不法侵害的反击措施,而防卫行为所包含的指向不法侵害人的伤害的危险正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因此其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果非价,其所代表的不法也应该在对防卫行为进行评价时被扣除。换言之,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防卫行为虽然也同时包含对第三人的伤害和对不法侵害人的伤害危险,但是后者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允许,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在对防卫行为进行不法评价时应该将这部分不法予以扣减。具体到案例2,虽然模具最后砸到无辜的马某,但是从事前来看,其显然是砸向不法侵害人刘某,明显具有造成刘某伤害的危险,但是这是行为人为制止刘某的侵害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因此在对防卫行为进行评价时,应该将其所包含的这部分不法予以扣减。事实上,在处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问题时,现有学说之所以仅考虑防卫行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所涉及的犯罪问题,其实也是默认了防卫行为给不法侵害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属于正当防卫,为法律所允许,其所代表的不法不应计入最后对防卫行为的评价。但是不将这份不法计入评价范畴不代表其不存在,因此仍然可以说,与传统的防卫过当之于普通犯罪一样,相较于单纯的因方法失误而伤及第三人,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中,同样存在正当防卫限度内的不法的减轻。②透过这一点也可以更好地说明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满足成立防卫过当的形式条件。因为如果对《刑法》第20条第2款中的中“正当防卫”作严格的形式理解,或者像实务部门那样,要求防卫过当的成立以正当防卫的存在为前提,那么也可以说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防卫行为中包含(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正当防卫,只不过其进一步逾越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对象限度),造成了过当的结果(即对第三人的伤害)。反而对于传统的防卫过当来说,在只有一个自然意义上的防卫行为时,更多地是在与假定的正当防卫行为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肯定防卫行为构成防卫过当,而不是从防卫行为本身分解出一个“正当防卫”行为,进而认为其在构成正当防卫的基础上进一步构成防卫过当。
2.责任的减少。如前所述,从经验层面可以肯定,在面临不法侵害时,行为人往往会产生恐惧、慌乱、害怕等紧张情绪,而剧烈的心理动摇会使行为人适法意识及行为的形成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很难从规范上期待行为人做出精准的不过当的反击行为。换言之,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的反击行为虽然超过了必要限度,但是其期待可能性大幅减少,导致责任程度降低,甚至降低至微弱状态,从而使行为人获得减免处罚的待遇。其实理论上已广泛认可期待可能性的降低所带来的责任程度的降低是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重要原因,比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对于防卫过当来说,责任减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的反击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行为人对事实状况的判断与决意,因而应当减免其责。”①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388页。其他文献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246页;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217页;张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钱叶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及限定性适用》,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等等。
同样,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也是直面不法侵害,一样会因此产生害怕、慌乱等紧张情绪,从而导致期待可能性降低。此外,行为人是因为面临不法侵害而感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压迫,即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可归责于不法侵害。还有,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发生于其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过程中。简言之,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不法侵害而起,发生于防卫行为中。对比来看,在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发生概率、发生原因及发生环境上,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与传统的防卫过当有着实质的相似。这样一来,借由《刑法》第20条第2款来评价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中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程度就具有实质的根据,而且也不会使《刑法》第20条第2款泛化为一项普通的评价期待可能性降低的责任减轻事由。
3.预防必要性的降低。对于预防必要性的降低来说,理论上认为在恐惧、惊吓或慌乱等心理虚弱时的情绪冲动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过当的防卫行为,其仍然是一名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公民,并未明显偏离法秩序的轨道,因而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小,甚至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②Vgl.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 22 Rn. 69.在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较小或者丧失的场合,即使不判处刑罚,也能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③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63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乃至丧失也能够为部分防卫过当免除处罚提供根据。而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虽然行为人因为方法的失误伤及第三人,但是如果考察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所具有的防卫意识和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同样可以认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过当的行为,伤害到了无辜第三人,但其并未明显偏离法秩序的轨道,因而预防必要性较低。所以,在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这一点上,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与传统的防卫过当并无二致。
但是,在一般预防的问题上,罗克辛教授对于将防卫过当免除处罚(德国刑法第33条)扩展适用于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提出了质疑。罗氏指出,从概念上来讲的确可以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归入防卫过当;④也有学者将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称为“空间的量的过当”(der räumlich-extensive Notwehrexzess),Vgl. Kühl,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7.Aufl.,2012,§ 12 S.424.但是只有在不法侵害人与第三人属于共同侵害人的情况下,对因心理虚弱时的情绪冲动而实施过当防卫的行为人免除处罚才能符合一般预防的要求。⑤Vgl.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 22 Rn. 91;ders,Über den Notwehrexzeß,in FS-Schaffstein,1975,S.124. 除了一般预防的考虑外,罗克辛教授还从与紧急避险条款(德国刑法第34、35条)相协调的角度,否定了将防卫过当免除处罚条款(德国刑法第33条)扩展适用于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场合。但是我国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与德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刑法有避险过当减免处罚的规定,而德国没有,但德国刑法有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条款),故不予展开。对于此,需要明确以下几点:首先,在行为人因为虚弱时的情绪冲动而不存在特殊预防必要性的情况下,能否仅根据一般预防的必要来处罚行为人?这其中是否有将行为人工具化的嫌疑?其次,我国《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的规定与德国的规定并不相同。德国刑法倾向于将刑法第33条规定的防卫过当“不处罚”(……nicht bestraft)理解为阻却责任,即不构成犯罪。我国《刑法》规定防卫过当应该负刑事责任,即使免除处罚,也应该宣告有罪。换言之,在我国,将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归入防卫过当,并不是宣告此时行为人是无罪,不会起到鼓励民众模仿实施相关行为的作用,也不会损害人们对相关规范的理解和确信。最后,我国《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的规定也并不是单纯的免除处罚,还包含减轻处罚的法律后果,这样可以将关于一般预防的忧虑降到最低。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原因在于:防卫行为本身包含不法的减轻;在面临不法侵害时,行为人往往会产生害怕、恐惧等剧烈的心理动摇,导致其期待可能性大幅降低,责任程度进一步下降;同时,上述情形也会使行为人的预防必要性降低。而与传统的防卫过当一样,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同样存在不法的减轻、期待可能性的降低、预防必要性的降低等。因此,将《刑法》第20条第2款扩展适用至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情形具有实质理由。
(三)与现有理论的兼容
如上所述,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与传统的防卫过当在形式外观与具体内涵方面都有实质的相似,因此可以将其归入防卫过当,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在引入《刑法》第20条第2款来评价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时,防卫行为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伤害的危险属于必要限度内的正当防卫,不计入对防卫行为的不法评价;而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伤害就成为过当部分,作为对行为人进行归责的事实基础。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与传统的防卫过当在事实因素上存在实质的相似,但囿于评价方法的局限,在评价传统的防卫过当时,在罪名的确定上难免将必要限度内的不法也包括进来,所以才会将不法的减轻再作为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根据;而在防卫行为误伤第三人的场合,因为过当事实和必要限度内的反击结果存在分离,所以可以在一开始的罪名确定上就将必要限度内的不法予以排除,这样的话,在量刑时似乎就“不存在不法的减轻”。但这种所谓的“不存在不法的减轻”其实更符合处理防卫过当时该有的方法与态度,即仅将过当事实作为评价的基础,甚至说表现得更为彻底。只不过,因为一开始在罪名的确定上就考虑了防卫限度内的不法的减轻,那么随后在进行量刑上的减免处罚时,就只能考虑行为人的责任减轻程度和预防必要性降低的程度,而不能再考虑不法的减轻,否则就构成重复评价。那么现有理论学说(假想防卫说、假想避险说或事实错误说)对误伤第三人的责任形式的探讨,就变成在防卫过当语境下对过当事实的责任形式的认定。在确定了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构成过失的基础上,借助《刑法》第20条第2款可以进一步评价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程度,确定减轻处罚的幅度甚至免除处罚。而且,因为《刑法》第20条第2款本身不解决行为人对过当事实的责任形式问题,所以不会与现有学说在结论上存在冲突。在此意义上,引入《刑法》第20条第2款不仅可以与现有学说兼容,而且为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寻找到法定的评价事由,进而更加全面地评价行为人的不法与责任,使其获得减免处罚的待遇。
具体到案例1、2,引入《刑法》第20条第2款后,秦某甲及黄某的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就属于防卫过当中的过当事实,因为行为人对过当事实不存在认识,阻却故意,所以行为人构成过失犯。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量行为人面临不法侵害时期待可能性的降低程度,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来确定减轻处罚的幅度。尤其对于案例2,虽然法院认定黄某对第三人马某的死亡存在过失,但是从当时情况来看,刘某等多人对黄某进行殴打,在黄某不断退避的情况下,刘某等人仍旧辗转多个场所对黄某进行持续的拳打脚踢,此时黄某内心的害怕、恐惧程度可想而知,期待黄某在近身防卫时做出精准恰当的防卫行为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而且在面临不法侵害时,黄某一直是以躲避为主,最后的反击也是万般无奈,基本上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因此,对于黄某,可以依据《刑法》第20条第2款免除处罚。
四、防卫过当条款适用情形的进一步拓展
如上所述,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语境下,可以在过当事实的意义上评价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就案例1及案例2而言,行为人是因为反击方法上的失误而伤害到第三人,因而对过当事实构成过失。但在实际的防卫过程中,行为人还会因为其他原因而伤及第三人。比如行为人在反抗不法侵害的过程中,将第三人误认成不法侵害人的同伙而伤及第三人。又如,在反击不法侵害的过程中,行为人虽然意识到其反击行为可能会伤及第三人,但仍然实施了反击行为,最终也伤害到了无辜的第三人。在防卫过当的背景下,上述两种情况其实只影响行为人对于过当事实的责任形式,但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是过失还是故意并不是《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评价内容,因此不会影响该条款的适用。下面结合具体案例分别阐述。
(一)因对象认识错误而伤及第三人
案例3:2008年5月23日晚,被告人谢某甲和谢某乙、王某因乘坐出租车与孔某等人发生争执,后孔某等人对被告人谢某甲和谢某乙、王某实施殴打,并把谢某甲、谢某乙带至某中学地道内实施殴打。被告人谢某甲在被殴打过程中从地上捡起一把刀将孔某刺伤后跑到地道出口时,遇到被害人尹某,并误以为尹某与孔某等人系一伙人,便持刀将尹某左、右肩胛部砍伤,致尹某血气胸并呼吸困难的重伤后果。法院认定谢某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免予刑事处罚。①(2016)云0328刑初第35号刑事判决书。
在本案中,谢某甲误以为尹某与不法侵害人孔某等同属一伙,进而持刀将其砍伤。对于这种情况,理论上一般认为对于给尹某造成的伤害,行为人构成假想防卫,按照过失犯进行处罚即可。②参见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80-181页。但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只评价了行为人的责任形态,没有评价谢某甲的反击行为中所包含的防卫性,以及在面临不法侵害时谢某甲因高度恐惧害怕而期待可能性降低的事实。相反,如果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谢某甲所实施的系列行为的连续性、时空的紧密关联性以及防卫意识的持续,则可以将其前后实施的一系列反击行为整体评价为防卫行为,并在过当事实的意义上理解其给尹某造成的伤害,进而在认定谢某甲构成过失犯的基础上,再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对其责任降低程度进行全面评价,作出减免处罚的决定。
首先是谢某甲行为的防卫性。在本案中,谢某甲在刺伤不法侵害人孔某后,误以为站在通道出口的尹某是孔某的同伙,遂对其实施了伤害行为。如果单纯地看谢某甲对尹某的伤害,其的确符合假想防卫的情形,因为此时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第三人尹某并未实施不法侵害,但谢某甲出于防卫目的将其刺伤,这似乎意味着谢某甲的行为并不具有防卫性。但是这种描述方法没有考虑到行为人在面临多人不法侵害时防卫的特殊性。从经验上看,在面临多人不法侵害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往往只能对不法侵害人各个击破,而不是一次搞定,也即行为人的防卫行为往往是一个针对多个不同的不法侵害人的有先后时间顺序的逐个反击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如果行为人对不法侵害的范围出现误认,主观上不当扩大其所面临的不法侵害的范围,比如将其所面临的甲、乙、丙三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扩大为面临甲、乙、丙、丁、戊五人的不法侵害;那么其在防卫的过程难免伤及丁、戊二人,这样的伤害行为可能发生在对甲、乙、丙进行防卫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对这三人进行防卫之前或之后;但是,这不影响可以从整体上将行为人实施的一系列反击行为一体性地评价为防卫行为,进而将因对不法侵害产生错误估计而给丁、戊造成的伤害评价为过当事实。具体到案例3,谢某甲对其所面临的不法侵害的形势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将无关的尹某也纳入了不法侵害人的范围;在此误认基础上,谢某甲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误伤了尹某。在这一过程中,谢某甲存在防卫意识的一贯性与系列行为在时空上的紧密关联,可以将谢某甲前后所实施的伤害行为一体性地评价为防卫行为,并在过当事实的意义上理解其给尹某造成的伤害,认定其整体构成防卫过当。这样既肯定了反击行为中包含的防卫性,也符合行为人在面临多人不法侵害时的防卫实际。
其次,不法与责任的减轻。在将谢某甲所实施的一系列防卫行为一体性地评价为防卫过当的基础上,可以认定谢某甲对孔某的刺伤行为属于防卫所必需,在对防卫行为进行评价时应该将这部分不法予以扣减,进而只将过当部分,即给尹某造成的伤害,作为不法评价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谢某甲所实施的一系列防卫行为中包含正当防卫限度内的不法的减轻。而就责任的减轻来说,当时谢某甲是被孔某等多名不法侵害人带至地道这样相对封闭的场所进行殴打,其必定会产生严重的恐惧、慌乱等紧张状态;而且事前谢某甲与孔某等人并不认识,更难精准判断在场的人哪些是孔某的同伙,哪些不是;再加上当时谢某甲恰好是在地道的出口遇到尹某,在当时剧烈的心理冲动下,很难期待谢某甲准确认定尹某不是孔某的同伙,进而放弃对尹某的伤害。换言之,虽然谢某甲在防卫过程中伤害到了无关的尹某,但是在本案的具体情形下,期待其做出精准防卫的可能性很低,因而可以认定其存在责任程度的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谢某甲所实施的一系列防卫行为整体构成防卫过当,在认定其对过当事实(即给尹某造成的伤害)存在过失的情况下①传统学说从假想防卫的角度来解释谢某甲构成过失,其实,在将防卫行为给尹某的伤害评价为过当事实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借由假想防卫来认定谢某甲构成过失。具体来说,此时从客观上来看,给尹某造成的伤害属于过当事实,但是行为人认为尹某也是不法侵害人,其给尹某的伤害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是正当防卫,因而并不过当。这样的话,谢某甲就属于对防卫行为的“过当性”存在误认的假想防卫。需要注意的是,案例3中行为人构成假想防卫的结论并不与案例1、2中行为人不构成假想防卫的结论矛盾;因为在案例1及案例2中,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本身就没有认识,而在案例3中行为人是在过当事实本身存在认识的基础上,对行为的“过当性”产生了错误认识。,进一步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进而全面评价谢某甲的责任降低程度,给予其减免刑罚的处遇。在判决书中,法院是适用自首条款对谢某甲进行免除处罚,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况下,才可以因自首而免刑,可见法院认为与一般的过失致人重伤犯罪相比,谢某甲的犯罪较为轻微。对此,法院指出:“本案的引发是由于被告人谢某甲的人身权益受到侵犯,在反抗不法侵害的过程中,误将被害人认为是不法侵害人的同伙,遂将其致伤,被告人谢某甲的社会危害性较小”。从这一表述可以明显看出,法院在认定谢某甲的犯罪情节较轻时考虑了行为人当时面临不法侵害、行为本身的防卫性、行为人的防卫意识等因素,并将尹某重伤的事实作为防卫行为的附属结果予以看待,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当然,如果法院能够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话,则可以更加全面评价行为的不法与责任,给免除处罚的决定提供更为全面、充实、法定的理由。
(二)对伤害第三人存在未必的故意
案例4:2014年7月16日11时许,在某工地,因施工材料问题,被告人王某甲的姐姐王某乙与刘某(受害人钟某甲的妻子)等人发生争执,被推到在地。王某甲听到王某乙的喊声后,赶到现场,与钟某乙、钟某丙两人(钟某甲的儿子、侄子)发生撕扯并相互殴打,在双方厮打过程中,王某甲被钟某乙、钟某丙按在地上,王某甲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理石石块扔出,击中钟某甲头部,致钟某甲颅骨开放性、凹陷性、粉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属重伤二级。法院认定王某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②(2014)乌刑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书。
对于王某甲的责任形式,法院指出,被告人王某甲捡起石块扔出是发生在与钟某乙、钟某丙厮打过程中,其主观上对这一行为可能造成他人身体受伤并无反对的意思,而是出于相互厮打、攻击的需要,对伤害结果持放任态度,符合间接故意特征。对此,即使按照法院的判断,认定王某甲对于给钟某甲造成伤害存在未必的故意,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因为王某乙与刘某被钟某乙、钟某丙按倒在地,王某甲扔出石块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主要为了击伤第三人(否则就应该认定其构成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在此基础上,就行为的客观面而言,从事前来看,王某甲扔大理石石块进行反击的行为具有制止钟某乙、钟某丙不法侵害的可能,属于防卫行为,只不过出现了过当结果,给第三人钟某甲造成了伤害。而且从当前的情景来看,王某甲被钟某乙、钟某丙两人按到在地,难免产生慌乱、害怕等紧张状态,再加上身体受控制,也较难期待其做出过于精确的防卫行为,因而可以认定王某甲存在期待可能性大幅降低的情况。
换言之,除了行为人对过当事实(即给第三人造成的伤害)的责任形式不同,在行为的防卫性、不法的减轻、责任程度的降低等方面,案例4都与案例1、2存在实质的类似,因此,结合前面的论述以及对案例1、2的分析,可以将本案中王某甲实施的反击行为评价为防卫行为,并在过当事实的意义上理解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钟某甲造成的伤害;在认定王某甲对过当事实存在间接故意的基础上,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进一步评价王某甲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程度,为其减免处罚提供法定的理由;加上本案王某甲还存在自首情节,至少可以考虑将对王某甲的有期徒刑期限进一步调低,并适用缓刑。
五、结论
回归到《刑法》第20条第2款可以发现,本款只是指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但如何来理解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法条本身保持了开放性。如果先见地认为“必要限度”仅指必要的防卫强度,防卫过当也仅指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防卫强度的情形,可能过早限制了对文本可能含义的发掘。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与传统的防卫过当一样,在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场合同样存在行为的防卫性、不法的减轻、责任的减少以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等情况,二者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将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归入防卫过当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行为的不法与责任,尤其是为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寻找到法定的评价事由。从具体结论上来看,除极少数满足紧急避险条件的情况外,可以将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情形整体理解为防卫过当,并在过当事实的意义上来理解防卫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在此基础上,确定行为人对过当事实的责任形式(过失和间接故意①从理论上说,似乎不应排斥将故意伤及第三人的情形纳入防卫过当的可能,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行为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明知第三人不是不法侵害人还针对第三人实施伤害的,其伤害行为从客观上就很难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即不具有防卫性,因而也就很难将其理解为防卫行为,进而也就丧失了对其适用防卫过当条款的前提。此外,从结论上看,将此处(即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防卫过当的责任形式主要归纳为过失和间接故意,也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的防卫过当主要由过失和间接故意构成相协调。),并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来评价行为人期待可能性降低的情形,给予行为人法定的减免处罚(尤其是免除处罚)的处遇。
但是,防卫过当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便是免除处罚也应该宣告有罪。换言之,借助《刑法》第20条第2款也只能做到对行为人构成犯罪的情形的全面评价。而在防卫行为伤及第三人的场合,还存在行为人没有过失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形,对此,可以考虑援引《刑法》第16条的规定,认为此时“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不是犯罪”。②如果从奠定责任基础的意义上来理解期待可能性的话,也可以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不具有过失的情形。对于期待可能性的不同意义及其与过失认定之间的关系,参见张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