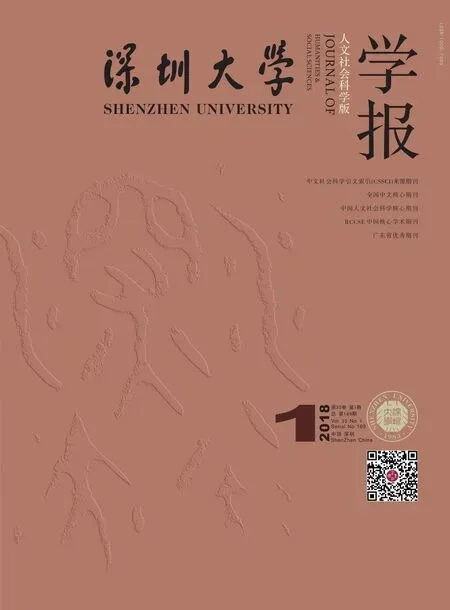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与文学结缘之现象
王力坚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桃园)
一、引 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全面发展的时期,除了士人园林与寺庙园林相继兴起,在秦汉时期已达鼎盛的皇家园林亦得以延续并发展演变。
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计有曹魏6处,孙吴4处,西晋1处,东晋2处,刘宋4处,萧齐7处,萧梁5处,陈3处,北魏1处,北齐3处。主要分布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一带)、建康①及其附近新林等地[1]。著名皇家园林则有魏晋的西园、落星苑、桂林苑、洛阳华林园(芳林园),南朝的建康华林园、乐游苑、芳乐苑、上林苑、新林苑、博望苑、青林苑、江潭苑等,北朝的洛阳华林园、西游园、龙腾苑、仙都苑、玄洲苑、鹿苑、北苑、西苑、东苑、游豫园、清风园等②。这些皇家园林的形制、功能、景观等有多元化的表现,本文所关注者,在于园林与文学的互动关系③。长久以来,学界的讨论基本集中在秦汉或明清的皇家园林,甚少关注到其他时期的皇家园林,更鲜有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几乎无人涉猎。
根据现存文史资料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家园林跟文学有不同程度关系者,计有西园、玄武苑、北园、华林园(芳林园)、上林苑、玄圃、乐游苑、建兴苑、西池、桂林苑、博望苑、鹿苑等。这些皇家园林有大小、先后、同名异地、异时同名、互有交错、交集、包含等形态,择其荦荦大端者论述如下。
二、邺城西园:肇启游娱赋诗传统
两汉的皇家园林是帝王武演校猎的主要场所(详见后文),曹魏邺城西园,仍保留着这个传统:
长铩糺霓,飞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连。跱如丛林,动若崩山。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泽之修旃……消摇后庭,休息闲房。步辇西园,还坐玉堂。(曹丕《校猎赋》)
尽管如此,邺城西园的主要功能已转为游娱。游娱风气在建安时代颇为盛行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云:
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邻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序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是对建安文坛概貌的描述,“邻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序酣宴”便是其时文士生活场景亦是创作内容,曹丕《又与吴质书》已有陈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吴质的《答魏太子笺》亦有云:“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
刘勰等人的陈述,足见游娱风气与文学创作是关系密切的,而二者的交集的场所,便是皇家园林。西园,也就是这样一个游娱而赋诗的场所。
建安十七年春,曹丕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身份,率众“□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所作《登台赋》云:
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其景之清丽,其情之畅逸,与灵帝西园迥然异趣。曹植奉命而作的《登台赋》则多了一层歌功颂德的浓彩: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杨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寍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如此表现,反而更真实地凸显了“皇家园林”的身份与地位。
西园之游,在诗歌创作中亦得到颇为充分的反映: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丕《芙蓉池作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曹植《公讌诗》)
虽然在诗中曹丕曹植二人的主从关系颇为明显,随着“逍遥步西园”“飞盖相追随”,展开对西园景致游观似的描写。曹丕游观的动线是从地面的清渠嘉木上延到天上的云霞星月,曹植的游观动线却是始终盘桓于明月当空下的园中景色。二诗的共同点则是在自然景观中点缀着能显示身份的人文景象,如前诗的“乘辇夜行游”“惊风扶轮毂”,后诗的“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诗的结尾,亦同是抒发酣畅快意的情怀:“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值得注意的是,曹植诗名之“公讌”,却始终聚焦于游园。
不过,王粲《公讌诗》的焦点倒是集中于宴席场景:“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并且在诗末表达不无谀意的祈愿:“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无论如何,西园之游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以上位者为中心,聚集文士,亦宴亦游,最终导向群体性的创作。应玚的 《公讌诗》颇能阐明这一现象: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这个传统得到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继承:“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逸兴咏,并命从游。”(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而“西园”也成为涵括园林、宴游、文学的典事,诸如:“平台盛文雅,西园富群英。”(谢朓《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其二)“复乖双阙之宴,文雅纵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园。”(萧纲《与萧临川书》)“复有西园秋月,岸帻举柸。左海春朝,连章摛翰。”(萧绎《金楼子序》)“南皮朝宴,西园夜游。词峯飙竖,逸气云浮。”(萧绎《太常卿陆倕墓志铭》)“副君西园宴,陈王谒帝归。列位华池侧,文雅纵横飞。”(刘孝绰《侍宴同》)“带才尽壮思,文采发雕英。乐是西园日,欢兹南馆情。”(陈叔宝《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诗》)由此可见,建安文士西园游娱赋诗,并形成君臣群体游娱创作的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逺的影响。
三,玄武苑(湖)与北园:掩映于历史光影的故事
曹魏邺城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还有玄武苑与北园等。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左思《魏都赋》描绘玄武苑风景有曰:
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缭垣开圃,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筱怀风,蒲陶结阴。回渊漼,积水深。兼葭贙,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绿芰泛涛而浸潭……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
如此美景,却甚少见诸诗文,或许是由于当年曹操建玄武苑的军事目的(以肄舟师),宋孝武帝刘骏的《春蒐诏》再次强调这一点:“可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终其历史,惟曹丕《于玄武陂作》有所记述: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讙哗鸣。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后赵时期,石季龙复建邺城华林园,将玄武池涵括进去。北魏宣武帝元恪建洛阳华林园,北齐后主高纬建晋阳仙都苑,也都加设玄武池景区。晋武帝在东吴建康华林园基础上进行扩建,玄武池也是重要的景区。此外,南朝历代在建康玄武池周围营建的皇家园林多达二十多座,如刘宋的乐游苑、上林苑,萧齐的清溪宫(芳林苑)、博望苑,萧梁的江潭苑、建新苑等[2]。可以说,作为完整独立的园苑,玄武苑的表现似乎并不显著,然而,作为园林元素,玄武池的作用在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史上的作用与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与此相关的诗文亦散见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历史阶段,诸如:
暮冬霜朔严,地闭泉不流。玄武藏木阴,丹乌还养羞。劳农泽既周,役车时亦休。高薄符好蒨,藻驾及时游。鹿苑岂淹睇,兔园不足留。升峤眺日軏,临逈望沧洲。云生玉堂里,风靡银台陬。陂石类星悬,屿木似烟浮。形胜信天府,珍宝丽皇州。白日回清景,芳醴洽欢柔。参差出寒吹,飉戾江上讴。王德爱文雅,飞瀚洒鸣球。美哉物会昌,衣道服光猷。(鲍照《蒜山被始兴王命作诗》)
寒云轻重色,秋水去来波。待我戎衣定,然送大风歌。(陈叔宝《幸玄武湖饯吴兴太守任惠诗》)
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宫移渡汉,天驷动行镳。斾转苍龙阙,尘飞饮马桥。翠观迎斜照,丹楼望落潮。鸟声云里出,树影浪中摇。歌吟奉天咏,未必待闻韶。(江总《侍宴玄武观诗》)
玉马芝兰北,金凤鼓山东。旧国千门废,荒垒四郊通。深潭直有菊,涸井半生桐。粉落妆楼毁,尘飞歌殿空。虽临玄武观,不识紫微宫。年代俄成昔,唯余风月同。(段君彦《过故邺诗》)
北园似乎是与建安文士文学创作联系密切的皇家园林,曹丕曾作《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不过,检索现存数据,仅繁钦有《赠梅公明诗》一首,另曹植与杨修各有一篇《节游赋》。
尽管如此,北园赋诗的传统却在后世得以呈现,如有鲍照《学刘公干体诗五首》其五:“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北园有细草,当昼正含霜。乖荣顿如此,何用独芬芳。抽琴为尔歌,弦断不成章。”似乎可替代当年刘桢的应制之作。江总《赋得一日成三赋应令诗》所谓“副君睿赏遒,清夜北园游;下笔成三赋,传觞对九秋”当可重现建安文士北园游园赋诗的景象。萧纲《夜游北园诗》的“星芒侵岭树,月晕隐城楼;暗花舒不觉,明波动见流”,与庾肩吾《奉和太子纳凉梧下应令诗》的“北园凉气早,步辇暂逍遥;避日交长扇,迎风列短箫”俨然邺城君臣唱和风气的翻版。
由南入北的庾信,似乎将北园故事带到了北朝。庾信在长安北园落成应赵王宇文招之命赋诗有云:
虹枌跂鸟翼,山节拱兰枝。画梁云气绕,雕窗玉女窥。月悬唯返照,莲开长倒垂。盘根纽坏石,行雨暴浇池。长藤连格徙,高树带巢移。鸟声唯杂曲,花风直乱吹。白虎题书观,玄熊帖射皮。文弦入舞曲,月扇掩歌儿。玉节调笙管,金船代酒巵。若论曹子建,天人本共知。(《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诗》)
建安文士园林游娱风气,穿越了整个魏晋南北朝,产生了跨时空的影响。及至隋人作诗,仍有“若奉西园夜,浩想北园愁”(陈政《赠窦蔡二记室入蜀诗》)的遐思。
由上可见,在史实记录中,玄武苑(湖)与北园并未留下真切的痕迹;然而,通过文学作品,则呈现了掩映于历史光影的故事。
四、华林园(芳林园):南北不同的文学情缘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北(邺城,洛阳)南(建康)多个不同时空的华林园。
北方的华林园,始于邺城。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开始营建凌云台、灵芝池、天渊池等;至明帝曹叡继位,更开始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建设,包括天渊池等景区在内的芳林园便建于此时:
是年(青龙三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魏略》)
魏明帝增崇宫殿,雕镂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毂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太平御览·地部·石上》引《魏志》)
曹叡史上与曹操、曹丕并称“三祖”,虽然文学成就远不如后二者,但亦为善诗文之人;其游宴园林的作风,显然得自曹丕真传。齐王曹芳继位后,改称芳林园为华林园。入晋以后,华林园更成为王公贵族游宴赋诗的重要场合,干宝《晋纪》载:“泰始四年二月,上(晋武帝)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其实,被誉为“最美”的应贞诗,不外是诸如“天垂其象,地耀其文”、“恢恢皇度,穆穆圣容”、“贻宴好会,不常厥数”、“文武之道,厥猷未坠”(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之类虚美颂扬之辞。其他关涉华林园的诗作,如荀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与《从事华林诗》、潘尼《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等,亦均是如此风貌;惟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稍显清新之气:“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
晋室南迁,南北对峙后,后汉帝王石季龙(石虎)曾于永和三年 “使尚书张羣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晋书·石季龙载记》)。此华林园的功能,仅止于供帝王宴游享受,与文学毫无交集。直至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命茹浩统领重建华林园,“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魏书·恩幸传》)。 宣武灵皇后胡氏与肃宗孝明帝元诩于华林园宴群臣,“令王公已(以)下各赋七言诗”(《魏书·宣武灵皇后传》),仅宣武灵皇后与孝明帝各存诗一句。之后,也只有北齐邢邵《三日华林园公宴诗》一首:
回銮自乐野,弭盖属瑶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树风仪。芳春时欲遽,览物惜将移。新萍已冒沼,余花尚满枝。草滋径芜没,林长山蔽亏。芳筵罗玉俎,激水漾金巵。歌声断以续,舞袖合还离。
北周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并序》倒是留下如此佳句:
千乘雷动,万骑云屯。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石堰水而浇园,花乘风而绕殿。熊耳刻杯,飞云画罍。水衡之钱山积,织室之锦霞开。司筵赏至,酒正杯来。至乐则贤乎秋水,欢笑则胜上春台。
南方的华林园,有不一样的发展。据《至大金陵新志·古迹志·城阙官署》载称,东吴时,建康台城便有宫苑华林园。此后,历经吴后主、晋元帝、宋文帝及孝武帝的治理营建,成为南方历朝涵括天渊池、景阳楼(山)、华光殿,并联接覆舟山、乐游苑等景区在内的著名皇家园林⑤。虽然也用以习武、听讼、讲易、颂经,甚至列肆、射鬼等,但宴游始终为华林园主导性的功能,即如陆云公所云:“华林园者,葢江左以来,后庭游晏之所也。”(《御讲般若经序》)而能与文学交集的也始终只是宴游,如梁普通四年,长沙王萧孝俨从梁武帝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异之”(《南史·萧孝俨传》)。可惜诸作均无传世,不过,其他关涉华林园(含景阳山【楼】、天渊池)的作品却多有所见,诸如宋文帝刘义隆《登景阳楼诗》、颜延之《登景阳楼诗》、江夏王刘义恭《登景阳楼诗》、宋孝武帝刘骏《华林园清暑殿赋》、裴子野《游华林园赋》、沈约《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与《会圃临春风》、丘迟《九日侍宴乐游苑诗》、徐爰《华林北涧诗》、谢朓《落日同何仪曹煦诗》、萧衍《首夏泛天池诗》、萧纲《蒙华林园戒诗》、任昉《奉和登景阳山诗》、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王僧孺《侍宴景阳楼诗》、张率《咏跃鱼应诏诗》、张正见《御幸乐游苑侍宴诗》、褚洊《芳林园甘露颂》、江总《芳林园天渊池铭》等等。
“三月三”诗,是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颇为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据史书载称:“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絜。”(《南齐书·礼志》)这样一个古代禊祭,在魏晋产生了变化:“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羣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宋书·礼志》)其变化有三:其一,出自民间的禊祭仪式,纳入了王朝文化体制,且“官人循之至今”;其二,絜濯祓除的性质,蜕变为宴饮游娱;其三,“于东流水”的场合,转换为皇家园林“天渊池南”“流杯石沟”“流杯曲水”的景区。最后一点也有区别:魏国时是“流杯石沟”,入晋则为“流杯曲水”,也就是“曲水”成为关键的变化。尽管如此,西晋三月三诗,仍无曲水之语,一如《南齐书·礼志》所指出:“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东晋以降者,则多见曲水意象,曲水与禊祭已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亦即如《南齐书·礼志》所言:“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絜之也。”
南朝宋、齐、梁的“三月三”诗,除了少数为野外或难以辨别场合的作品外,均为华林园活动的反映,诸如宋孝武帝刘骏《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栢梁体诗》、颜延之《应诏燕曲水作诗》与《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谢惠连《三月三日曲水集诗》、谢朓《侍宴华光殿曲水奉勑为皇太子作诗》、《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与《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沈约《上巳华光殿诗》、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与《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刘孝威《侍宴乐游林光殿曲水诗》、《褉饮嘉乐殿咏曲水中烛影诗》与《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并序》、《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诗》与《曲水联句诗》、庾肩吾《三日侍宴咏曲水中烛影诗》等。
陈朝的华林园,是侯景乱后所重建,已然为后主及嫔妃居住享乐的场所,与园林游娱的目的有所疏离,故从现存诗文看,陈朝的三月春禊活动,无一在华林园举行,而转移到玄圃及其他皇家园林了(详见后)。
五、上林苑与玄圃:奢华绮艳VS萧散清丽
众所周知,秦汉之际建于长安的上林苑是皇家园林的经典之作,也因此受到后世王朝的仿造。东汉京都洛阳亦有上林苑,规模虽远逊于长安上林苑,但功能亦多为武演校猎。两汉上林苑的校猎场面,在汉赋中得到颇为夸张的描绘:“武帝广开上林……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赡齐民。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举烽烈火,辔者施技。方驰千驷,狡骑万帅。”(扬雄《羽猎赋并序》)“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迄上林,结徒营。次和树表,司铎受钲。坐作进退,节以军声。三令五申,示戮斩牲。 ”(张衡《东京赋》)尽管如此,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描述,亦显见其宴游娱乐功能。
《宋书·孝武帝本纪》载,大明三年九月,宋孝武帝刘骏于建康玄武湖北重建上林苑。从此以后,上林苑便一直是南朝历代重要的皇家园林。与其他皇家园林如华林园不同,上林苑偶有武演校猎,却少有听讼讲经之类的活动记录,更多的是通过诗文记载的游娱宴饮活动,有关诗文名录如下:张率《河南国献舞马赋应诏幷序》、庾肩吾《谢赉菱启》、徐陵《谢赉麕启》、庾信《春赋》、陆厥《左冯翊歌》、萧衍《江南弄》、《登台望秋月》、王训《独不见》、萧统《上林》、刘孝威《行行且游猎篇》、《独不见》、萧子晖《应教使君春游诗》、萧纲《春日想上林诗》、《大同八年秋九月诗》、《倡楼怨节诗》、萧绎《咏晚栖乌诗》、《春别应令诗四首》其一、阴铿《西游咸阳中诗》、顾野王《芳树》、徐陵《咏柑诗》、江总《咏采甘露应诏诗》、苏子卿《朱鹭》等。
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傅晶的《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研究》、余开亮的《六朝园林美学》均不录北朝上林苑。其实,北朝应该有皇家园林上林苑,而且还似乎一如秦汉旧制,包含昆明池、阿房宫,邻近未央殿。《北史·魏太武帝本纪》载称,太平真君元年二月,曾发长安人五千浚昆明池。《北史·魏孝文帝本纪》则记载,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元宏“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北朝的诗,如阳休之的《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王褒的《和张侍中看猎诗》、庾信的《同州还诗》、《见征客始还遇猎诗》、《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与《咏春近余雪应诏诗》、元行恭的《秋游昆明池诗》、卢思道的《后园宴诗》等,便有上林或昆明池的描述。
上述诗文,虽然尚有烘托皇家奢华富丽的表现,如:“祥露晓氛氲,上林朝晃朗。千行珠树出,万叶琼枝长。徐轮动仙驾,清晏留神赏。丹水波涛泛,黄山烟雾上。风亭翠旆开,云殿朱弦响。徒知恩礼洽,自怜名实爽。”(江总《咏采甘露应诏诗》)“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风生拂雕辇,云回浮绮翼”(阳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但其中的唯美倾向已与文坛风尚同步,尤其后者为北朝文士作品,显见南朝的文风已深入影响北国文坛。
以下诗作,更是淡化王朝霸业色彩,重笔渲染后宫脂粉气,其华艳风貌直逼风靡一时的南朝宫体文学:
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苔始绿而藏鱼,麦纔青而覆雉。(庾信《春赋》)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萧衍《江南弄》)
朝日斜来照户,春鸟争飞出林。片光片影皆丽,一声一啭煎心。上林纷纷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驰节流易尽,何为忍忆含羞。(萧纲《倡楼怨节诗》)
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萧绎《春别应令诗四首》其一)
玄圃有洛阳与建康两处。洛阳玄圃或为西晋惠帝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园林⑥,亦当属皇家园林。与此相关的诗作,只有两首应制诗: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与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纯粹为感恩颂德之作。愍怀太子不仅在文学上无建树,在政治上亦无作为,更不堪的就是在游玄圃之日被废太子位 (《晋书·愍怀太子传》)。不知何故,从此后洛阳玄圃在任何文史资料中再难寻踪影。
相反,后来居上的建康玄圃发展却甚为顺畅。建康玄圃亦是太子园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所拓建,“其中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玄圃虽然是文惠太子私开的园林,但却得到其父王世祖齐武帝萧赜的“认证”:“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南齐书·沈文季传》)故可说是一座文士化的皇家园林,王俭《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诗》当可表明这一点:
明明储后,冲默其量。徘徊礼乐,优游风尚。微言外融,几神内王。就日齐晖,仪云等望。本茂条荣,源澄流洁。汉称间平,周云鲁卫。咨我藩华,方轶前轨。秋日在房,鸿鴈来翔。寥寥清景,霭霭微霜。草木摇落,幽兰独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畅旨酒,亦饱徽猷。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从“徘徊礼乐,优游风尚”到“眷言淄苑,尚想濠梁”,俨然其时身在庙堂而心怀山林的文士风范。
入梁后,玄圃仍为太子园,但其皇家园林地位已然牢固:“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梁书·简文帝本纪》)在昭明太子萧统主导下,玄圃的文士化更得到发扬光大。《梁书·昭明太子传》载,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并慨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当可以之为玄圃的园林文化定位。尤其是“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梁书·王筠传》),并作《玄圃讲诗》云:
白藏气已暮,玄英序方及。稍觉螀声凄,转闻鸣雁急。穿池状浩汗,筑峯形嶪岌。旰云缘宇阴,晚景乘轩入。风来幔影转,霜流树条湿。林际素羽翾,漪闲赪尾吸。试欲游宝山,庶使信根立。名利白巾谈,笔札刘王给。兹乐踰笙磬,宁止消悁邑。虽娱惠有三,终寡闻知十。
虽然诗中内容与诗关系不大,但诗题旨意所向、诗中的园林景观描写以及淡薄功名的意识,也为玄圃书写导引了一个方向。梁陈诗人所写玄圃诗,多有如下特征:
首先,所写园林景观,虽然仍不免有传统的皇家气息点染,如:“樵螟动兰室,神飙起桂丛。”(刘缓 《奉和玄圃纳凉诗》)“玄圃栖金碧,灵涧挹琨瑶。”(刘孝威《奉和六月壬午应令诗》)“绮殿三春晚,玉烛四时平。”(陈叔宝《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诗》)但更多是自然野趣展现,诸如:
曛烟生涧曲,暗色起林隈。雪花无有蔕,冰镜不安台。阶杨始倒插,浦桂半新栽。(萧纲《玄圃寒夕诗》)
长洲春水满,临泛广川中。石壁如明镜,飞桥类饮虹。垂杨夹浦绿,新桃缘径红。对楼还泊岸,迎波蹔守风。渔舟钓欲满,莲房采半空。(王褒《玄圃浚池临泛奉和诗》)
同云遥映岭,瑞雪近浮空。拂鹤伊川上,飘花桂苑中。影丽重轮月,飞随团扇风。还取长歌处,带曲舞春风。(张正见《玄圃观春雪诗》)
在这些诗例中,萧散清丽的风貌显然已取代奢华绮艳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侯景之乱,华林园尽毁⑦,陈朝虽然重修,并在园中光昭殿前建临春阁、结绮阁、望僊阁,“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祷、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谟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但其功用主要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即供帝王后妃佞臣宴饮荒淫奢靡享乐,因此也产生了《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之类以艳丽相高的宫体诗作(俱见《陈书·张贵妃传》)。
有意思的是,此时帝王的园林游娱中心似乎已从华林园转移到玄圃,所产生的诗文,与前述宫体诗迥然异趣。这些玄圃诗作,既沉浸“园林多趣赏,祓禊乐还寻”(陈叔宝《祓禊泛舟春日玄圃各赋七韵诗》)的人生意趣,亦不乏“自得欣为乐,忘意若临濠”(陈叔宝 《立春日泛舟玄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的方外之思;字里行间,更流露“带才尽壮思,文采发雕英”(陈叔宝《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诗》)、“既悦弦筒畅,复欢文酒和”(陈叔宝《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赋六韵以次成篇诗》)的文士情怀;景观的描绘,更已是著意渲染清新明丽的山光水色:
石苔侵绿藓,岸草发青袍。回歌逐转檝,浮冰随度刀。遥看柳色嫩,回望鸟飞高。(陈叔宝《立春日泛舟玄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
寒轻条已翠,春初未转禽。野雪明岩曲,山花照逈林。苔色随水溜,树影带风沉。(陈叔宝 《献岁立春光风具美泛舟玄圃各赋六韵诗》)
园开簪带合,亭逈春芳过。莺度游丝断,风驶落花多。峯幽来鸟啭,洲横拥浪波。(陈叔宝 《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赋六韵以次成篇诗》)
春池已渺漫,高枝自嵸森。日里丝光动,水中花色沉。安流浅易榜,峭壁逈难临。野莺添管响,深岫接铙音。山远风烟丽,苔轻激浪侵。(陈叔宝 《祓禊泛舟春日玄圃各赋七韵诗》)
玄圃诗的如此表现,显然疏离了皇家园林文学而趋向文士园林文学的风貌。究其原因,一方面,或是由于玄圃之名与传说中昆仑山顶的神仙居处、黄帝下都有关,张协《游仙诗》“峥嵘玄圃深,嵯峨天岭峭”,葛洪《法婴玄灵之曲》其二“玄圃遏北台,五城焕嵳峨”可见此意;另外,便是玄圃为太子园,而昭明太子又是文士化颇为彻底的皇族;玄圃诗作者,不是文士便是高度文士化的皇族帝王(萧纲与陈叔宝),于是,在文士园林盛行、皇族文士化日盛的南朝,玄圃的文士化,及其文学反映的文士化风貌,当是有迹可循亦自然而然的。
六、结 语
以上皇家园林诸多个案的论析,各具代表性地显示了如下三个现象:
一、纵向的历史进程。西园之游形成以上位者为中心,聚集文士,亦宴亦游,最终导向群体性创作的传统,对魏晋南北朝历代皇家园林的游娱赋诗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玄武苑(湖)与北园虽然在史实记录中未留下真切的痕迹;而是通过文学作品,呈现了掩映于贯穿魏晋南北朝历史光影的故事。
二、横向的南北分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北(邺城,洛阳)南(建康)多个不同时空的华林园。北方华林园的功能,多用于供帝王宴游享受,与文学甚少交集。南方华林园虽然也用以习武、听讼、讲易、颂经,甚至列肆、射鬼等,但宴游始终为华林园主导性的功能,而能与文学交集的也始终只是宴游。尤其是南朝宋、齐、梁的“三月三”诗,大多为华林园活动的反映。
三、文学风格的分野。呈现为上林苑与玄圃的比较,前者的奢华绮艳VS后者的萧散清丽。上林苑诗赋既有皇家奢华富丽的表现,亦表现出与文坛风尚同步的唯美倾向;更有甚者,其重笔渲染后宫脂粉气,华艳风貌直逼风靡一时的南朝宫体文学;北朝上林苑的作品,亦显见南朝的文风已深入影响北国文坛。洛阳玄圃在文史资料中难寻踪影,建康玄圃发展却甚为顺畅,是一座文士化的皇家园林。梁陈诗人所写玄圃诗,萧散清丽的风貌显然已取代奢华绮艳的风格。陈朝帝王的玄圃诗文,则与同期的宫体诗迥然异趣而趋向文士园林文学的风貌。
总的看来,皇家园林与文学结缘的关键因素为文士化。帝王皇族的文士化,促使皇家园林文化及其活动与文士世界交汇,皇家园林与文学更为广泛而紧密的结缘。皇族与文士,君王与臣僚同游共宴已然为皇家园林文化的常态,应制奉和等群体性的文学创作亦日渐蔚为风气。
注:
①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吴起,其治所称秣陵,之后,相继改称建业、建邺,晋愍帝司马邺建兴元年,改名建康,此后,东晋及南朝四朝均定都建康。为叙述方便,本文统称为建康。
② 参吴功正《六朝园林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总第3期),第112页;张纵《从园林起源谈六朝时期的皇家宫苑及其它园林形式》,《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第50页;王贵祥《中国古代园林史札(15世纪以前)》,《美术大观》2015年第3期,第105页;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第289-297页。
③比如,就功能而论,除了宴游之外,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至少还具有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宗教,以及生活等诸种功能。然而,这些功能所产生的活动及其表现跟文学创作关系甚为疏远,本文将采取存而不论的处理方式。
④Robert J.Cutter认为,建安宴游风气及其文学创作,主要产生于建安十三年至黄初元年之间。参Robert J.Cutter, “Cao Zhi’s(192-232)Symposium Poems,”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Sponsoring Institutions:Indiana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an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Vol.6,No.1&2(July 1984),pp.1-33.
⑤参 《六朝事迹类编·真武湖》;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 96-97页。
⑥《文选》载陆士衡《皇太子燕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注引杨佺期《洛阳记》曰:“东宫之北,曰‘玄圃园’。”
⑦ 参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97页;傅晶《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56页。
[1]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52-54.
[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8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