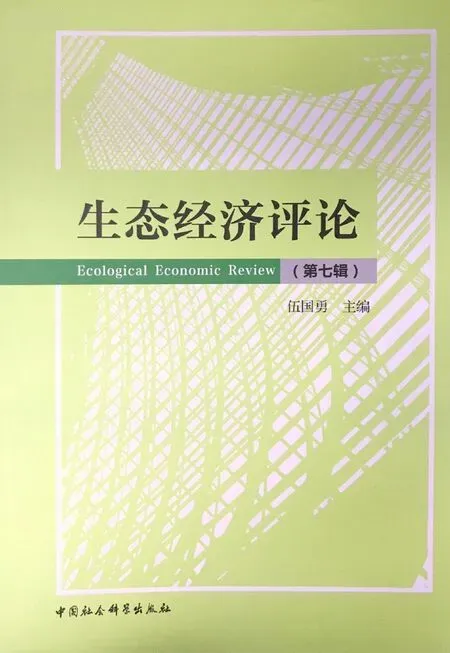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之辩
——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的对比研究
秦 竩
内容提要:同属于贵州省雷山县的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方面的条件基本相似,由于保护和开发的政策不同,导致了两地30年来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西江苗寨在经济发展方面占据优势,在自然和文化生态保护上却牺牲巨大;郎德上寨因为保护禁令得以保持原貌,但经济收入低使得原住民生活贫穷。看上去是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本文就上述状况做情境和理论上的分析,力解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之辩。
一 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乡村旅游对于20世纪80年代才开放的中国来说尚算是个新鲜事物,城市里的人在节假日回归向往的田园风光,最好再有些少数民族风情,以缓和城市发展的快速导致的不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发达的国家逐渐有了乡村旅游休闲产业,中国乡村旅游的开发算是比较晚的,并且还面临着比其他国家复杂的情况。比如,发展中城乡观念的差异、政策的导向、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的特殊情况等。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很难做出开发或者保护的决策,而执行决策时又会被种种因素牵制,走向是不好预计的,显示出来的表象就是各地的旅游开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原生性矛盾。
许多学者都做过相关研究,致力于解决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则更多地关注到了旅游地的文化生态问题。“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居住,这一术语最早由生物学家海克尔 (Ernst-Haeckel)在1870年提出,指生物的聚集。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首先明确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 “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①Julian 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对 “文化生态学”做出相类似的定义:“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但是,它还结合变革的其他过程来分析这些适应。”②[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换言之,既借生物学 “生态”的意义描述文化系统的结构性存在和演变。
文化生态之于某个地方而言是人们自我认同的根本,自我认同是民族自信和幸福的来源,所以保护文化生态的原貌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延存和提升地方原住民的文化自觉,实现文化多样化共存。而旅游带来的开发代表着商品经济和全球化的入侵,从观念上植入了统一的 “幸福观”,即鲍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中陈述的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幸福有了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幸福 “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得出来的福利。”③[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幸福”的物质性迫使开发旅游的乡村地区放弃原有文化中与之相悖的部分,逐渐地被城市化的生活所同化。这种转变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旅游催生的畸变,因为实际的案例证明了这种畸变使得旅游地原住民因文化错位而不适,旅游本身的意义也随之改变。
笔者八年间在贵州省雷山县的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进行了数次的田野调查。两地在20世纪80年代各方面都处于近似水平,西江苗寨进行了旅游开发,而郎德上寨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两地命途悬殊,随着时间的迁移,两地在经济发展、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就两地的对比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旅游开发同文化生态保护的地域性问题,并为类似少数民族地区在旅游业发展上提供参考。
国内学者何景明、杨洋在 《旅游情境下民族村寨管理制度于经济绩效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制度角度就两地进行了比较,认为两地的差异主要是由制度决定的,将西江苗寨归纳为 “公司制”,将郎德上寨归纳为“工分制”。①何景明、杨洋:《旅游情境下民族村寨管理制度于经济绩效的比较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实际上,制度只是一种决策,它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认可方式,“制度”参与但不直接决定一地的发展走向。另有文红和唐德彪 《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文化旅游资源适度开发——从文化生态建设的角度探讨》②文红、唐德彪:《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文化旅游资源适度开发——从文化生态建设的角度探讨》,《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9期。、林美珍和吴建华的 《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③林美珍、吴建华:《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2004年第19期。和肖琼《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旅游社区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④肖琼:《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旅游社区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8期。等文章都从文化生态角度关注了旅游开发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还有部分关注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研究,如覃物的 《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⑤覃物:《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和吴文才的 《贵州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问题研究》⑥吴文才:《贵州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问题研究——以肇兴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等,旨在探索旅游开发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平衡点。
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只是把旅游开发同文化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分析,期望从对立中取得平衡,还未触及两者深层次的联系。在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的对比案例中,可以说明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更复杂的共生关系。
二 两地基本情况
(一)地理概况
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同属贵州省雷山县。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东临台江、榕江县,南接三都水族自治县,西连丹寨县,北临凯里市,距省府贵阳184千米。
雷山县是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下辖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包括中国苗族第一寨 “西江千户苗寨”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郎德上寨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雷公山等。
1.西江苗寨
西江村隶属于西江镇,距雷山县城37千米,因有千余户苗族人家而被称为 “西江千户苗寨”,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村常住人口中99%都是苗族,80%以上都以农业为生。西江千户苗寨1982年被贵州省政府列为贵州民族风情旅游景点、乙类旅游开放区;1987年再次被列为贵州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贵州省政府列为全省八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1999年被列为全省十三个 “古镇保护与建设乡镇”之一;2004年被列入全省首期村镇保护与建设项目五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国务院把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银饰等五项苗族工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9月 贵州省在西江苗寨召开了全省第三次旅游发展大会,之后,“天下西江”蜚声国内外,西江千户苗寨成为与云南丽江齐名的旅游地。
2.郎德上寨
郎德原意是 “住在河流下游的村子”,位于雷山县北部,距离雷山县16千米,距离凯里市27千米。郎德分上下寨,全寨共128户,500多人,全部都是苗族。1987年郎德上寨被列入贵州省民族风情旅游点;1985年,郎德上寨作为黔东南民族风情旅游点率先对外开放;1993年被载入 《中国博物馆志》;1994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乔石至郎德上寨考察;199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1年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至今接待多国政要。
(二)发展方向
由于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发展走向上开始走向两个方向:郎德上寨也开放旅游,但因为被列入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没有进一步扩大开发和经营,基本维持了被列入时的原貌;西江苗寨因为旅游开发而不断改扩建增大游客接待量,今日的西江苗寨已经被摘除了各种 “保护”导向的头衔,成为了著名旅游风景区。
1.西江的旅游发展之路
西江苗寨的旅游发展之路起始于1982年,但真正腾飞的起点确是在2008年的第三届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会上打出了 “天下西江”的旅游品牌。自此,从省到县各级政府都对西江的旅游开发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2008年,西江苗寨获得8000多万元的注资,完成了大型民族歌舞表演场、苗族博物馆、西江供销社、民族精品街及古街、风雨桥、鼓藏头、夜景灯光系统等26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2009年之后,已知的项目建设追加资金额度为5600多万元,旅游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已完成投资2700万元实施了西北服务区建设、西江污水处理管网收集系统工程等20个工程分项,又投资了2900万元建设马鞍山停车场、观景台至1号风雨桥观光栈道等7个分项,以及另外投资70万元完成了苗寨景区的步道维修、山体创面处理等。①根据雷山县旅游局提供资料整理。
2006年西江接待游客量为52217人次;2007年为267340人次;2008年为777269人次;2016年游客接待量就已经突破40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41亿元。②同上。可以说,西江苗寨已经成为了继云南丽江之后的又一个旅游业神话,年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百分比每每突破惊人的数字。西江苗寨对于雷山县甚至黔东南州的旅游业而言是当之无愧的现金牛,它带动了整个巴拉河沿线甚至黔东南州的旅游产业。
2.郎德上寨的保护使命
1985年雷山县公布郎德上寨为 “民族文物村”;1986年郎德上寨被贵州省文化厅列为省级首批重点保护民族文化村寨,并拨款资助村民整理村寨容貌,1987年以 “苗族风情博物馆”之名对外开放。1993年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 “苗族歌舞之乡”;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同年,“上郎德苗族村寨博物馆”收入 《中国博物馆志》。1998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 “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之一,1999年被收入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2001年 “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贵州省政府公布郎德上寨为四三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村);2008年,郎德上寨是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走过的唯一苗寨。
郎德上寨及周边的保护性建设也持续不断:1986年,贵州省文物处拨款2万元,修建村寨巷道,全村80余条村巷全部用鹅卵石铺砌,民族古村落建筑格局得到完整保护;1992年083集团资助修建人畜饮水工程;2008年,为迎接奥运圣火,由上级政府出资,对寨门及欧兑河沿线进行重新包装,进一步强化农耕文化、苗族元素;2014年,作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的郎德获得上级部门300多万元的保护资金,用于解决排污系统建设、消防安全建设、步道维修等系列工程。
郎德上寨几乎是获得荣誉最多的苗寨,作为文化类的博物馆开放旅游与西江作为旅游景点开放旅游的时间几乎同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郎德上寨的面貌几乎没有改变,仅在郎德下寨到郎德上寨村口修建了进寨的道路。这样的保护是基于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法律法规限制,也是一种引导。郎德上寨在2006年的游客接待量为68243人次 (同年高于西江苗寨);2008年郎德上寨游客接待量则为95406人次,可见的是郎德上寨旅游接待人次的增长率基本是趋于稳步小幅增长的水平,与西江苗寨不可同日而语。
(三)开发与保护的决裂
同属一地区的两个苗族村寨,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时各方面的基础水平都是旗鼓相当的,由于开发和保护两种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今日两地的天壤之别,以下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说明对比案例的分歧。
1.经济发展的影响
比邻的两个村寨,在发展上相互观望和比较是两地从管理层到基层群众都非常在意的事。西江苗寨开发旅游是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和支持的,为此,西江苗寨以 “政府+公司”的模式开展旅游业,提出规划、注入资金、兴建旅游设施。在2008年前后,公司与紧邻街面的村民签订协议,或租或买下村民的房屋进行改扩建或修缮再雇用或者出租给村民用以接待游客,这样下来,多数的相对于旅游发展而言位置较好的房屋的归属权或者使用权都属于西江苗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成了最大的获利者。西江苗寨成为著名旅游景区后,门票一路上涨到了100元/人次,每年的门票收入随着游客接待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据西江苗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介绍,每年的门票收入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原住民的分红。
旅游的确给西江苗寨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然而并没有给西江本地的苗族原住民带来多么大的幸福感。在西江的旅游开发中获利的首先是西江苗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其次是外地来西江做生意的人群;再次是西江本地开客栈的家庭,与旅游景点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的或者不临街的原住民家庭则基本上参与不到旅游业当中,仍然靠农业和外出打工为生,他们的收入自然与参与旅游业的家庭差距很大。因此,在西江的田野调查中,并非所有的西江原住民都持积极态度支持旅游业发展。
2.支持西江旅游开发的声音
支持西江旅游开发的原住民多数都参与了旅游相关的经营,如客栈、餐厅和旅游纪念品销售。以采访的个案为例,潘先生,42岁,苗王银庄的老板,曾外出打工数年,在外时平均月收入能够达到五六千元,2008年回到西江开始经营 “苗王银庄”,开业后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万元,店铺租金每月5000元左右,他坦言以前一个月的收入现在一天都能赚回,所以他回到西江,积极支持旅游开发。由于率先从事旅游相关经营活动,他还获得了公费到外地学习、展销等机会,他说:“有一次到成都的非遗展销活动,我3天卖了3万多。”作为因发展旅游而获利的西江原住民,潘先生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①2016年11月采访于西江苗寨。
外地来西江做生意的人也不少,贵州安顺人,胡先生,55岁,2010年到西江租下河边的两间店铺,加工和销售木雕工艺品,铺租3000元左右/每月。他坦言这两间店铺一年的利润额大约为十几万元,比在北京潘家园做生意挣得多,他觉得西江苗寨很适合做生意,游客愿意买工艺品,要是跟导游合作,上万元的工艺品都很容易卖出。①2016年11月采访于西江苗寨。
3.不赞同西江旅游开发的意见
37岁的张女士是西江本地人,开了一间农家乐,位置处于观景台山的中腰位置,既不靠河也不在山顶,对于旅游业而言,这个位置并不理想。她说,西江刚开始搞旅游开发的时候基本上全部的西江人都是支持的,大家都想在家门口挣钱,不用再出去打工了,这样想大家都挺高兴的。后来旅游业发展起来了,靠河的住户都因为地理优势发家致富了,而山坡上的人家,除了鼓藏头和观景台等景点的住户,其他住户很少沾上旅游发展的光。随机走访的几位住在山坡上的原住民说起旅游开发都是怨言颇多,有的说:“旅游没有我们什么事,我家在山坡上没机会。”他们多数只能到步行街去摆摊卖小吃,这样的收入与店铺和位置好的客栈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非常不满。②同上。
4.保护政策的效果
看着近在咫尺的西江苗寨因为旅游开发而富得流油,郎德的原住民不被触动是不可能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往着更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羡慕西江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挣到钱,认为天天与家人在一起才是幸福。
郎德上寨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是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个名号的保护下,哪怕是挪动村寨中的一草一木都需要层层报告直到国家级别相关单位。多年来,郎德上寨因为这个名号而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政府持续的资金投入虽没有一步到位地实现原住民集体搬迁,但是为保存原貌也着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③在国际国内的古代村落保护案例中,较为受到推崇的做法是在原村落比邻的地方兴建新的村落,将原住民集体搬迁,修缮古代村落建筑,实现统一保护。部分地区雇用原住民白天到原古村落工作、经商等,以发展旅游业,而晚上则回到新建的迁出地生活。对于自上而下的保护令,郎德的原住民呈现出矛盾的态度。
(1)坚持保护优先
因为保护工作宣传已久,年轻的郎德原住民们从小就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村寨,而年纪大的村民们尽管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也能够理解保护的重要性。他们为自己的村寨而自豪,争相告诉笔者村寨获得过哪些荣誉,如数家珍。大部分的村民认为尽管保护限制了旅游开发,但是他们的家园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也保存得很好,日常生活不会因为旅游而被影响,所以他们还是很支持保护政策。
郎德的旅游接待经常是国外的旅游团体或者有一定政府背景的参观考察,村民的集体表演全部都是未经专业指导编排的原生态模式,一场演出2—3个小时,一位村民大概能拿到21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七八角钱,但只要村里来了国外旅游团或者各级领导参观团,村民们都会参加表演,包下一场表演仅需几百元人民币。①2016年11月采访于郎德。
寨老 (村寨里年纪大的能主事的人)们一致认为保护得好就是郎德上寨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的坚定使得二次开发迟迟没有展开,采访到的一位寨老认为,部分村里人想要破坏村寨搞旅游是行不通的,他们都不会同意,游客量少才能保护好村寨以持续发展。
(2)期待经济发展
32岁的杨女士住在郎德上寨的村子左边靠出口的位置,她家里有两个小孩和年迈的婆婆,靠种田为生,她的丈夫常年在外做建筑工人,家庭生活就靠务农和丈夫寄回的钱维持,走进杨女士的家,尽管不算家徒四壁,也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笔者把携带的糖果分给杨女士的小孩,杨女士却从小孩手上接过去给了婆婆并连连道谢。她说他们也希望能发展一点旅游,这样她家的生活就能好过一些,她的丈夫就不用出门离家去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但她知道保护村寨是上头的规定,她们穷但是始终都会遵守。②同上。
三 西江模式与郎德态度
(一)西江模式
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随着游客量的逐年增长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标杆,从而发展出 “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天翼认为“西江模式”是一套以旅游带动实现地方全面发展的经验体系,西江苗寨的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典型案例。①林文君:《“西江模式”:民族地区发展的 “样本”——对话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天翼》,《贵州民族报》2017年3月3日第3版。
真正的 “西江模式”包含哪些因素呢?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原生条件和经营模式。
原生条件包括:西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这种独特性不可复制;西江苗寨的地理位置距离州府凯里和雷山县城并不远,交通便利;西江苗寨的地形是两山夹着一条河,民居沿河靠山而建,形成了良好的视觉景观;另外,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非常早,西江的原住民一早就有发展旅游业的概念。
经营模式上:西江采取 “政府+公司”的经营模式,在旅游发展初期通过政府和民间渠道双向获取基础投资;而统一管理经营性的房屋,为旅游业的统一发展扫清了障碍;景区评级使得门票收入名正言顺;顺势加大投入以打造西江的旅游明星效应,同时扩大游客接待量。
第二,政策的一致性支持。
从贵州省省级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到雷山县政府、旅游局,层层领导在2008年旅游发展大会后都对西江苗寨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2011年,西江苗寨获得了4A级风景区的评级。
式中:P为块段中锆英石、或钛铁矿矿物量,t;V为块段体积,m3);C为块段锆英石或钛铁矿的平均品位,kg·m3。
历任雷山县旅游局局长都在西江苗寨的开发上秉承一致。2012年时任局长张局长认为要开发西江旅游不仅仅是一个西江,而是把巴拉河沿线的景点贯穿起来,让游客吃住玩一线,能够停留的天数增多才能进一步加大旅游收益。雷山县旅游局的规划是将西江苗寨、郎德上寨、巴拉河和雷公山以及雷山县城连在一起,形成有自然风光 (巴拉河和雷公山自然保护区)、有民族风情 (西江苗寨、郎德上寨)和高级住宿接待条件 (雷山县城)的旅游线路,这一规划已经上报和通过了省级相关部门的批准。①2011年8月采访于雷山县旅游局。
第三,经济发展优先。
西江从修建商业街开始,到2008年统一规划开发,收取门票,无一不是按照打造著名旅游地的商业模式在发展,一切建设都是围绕着增加游客接待量和增加游客住宿天数来计划的,酒店和民宿不断增加扩建,道路铺设更加方便旅游大巴进入,增设景点和在多个媒体上做广告。这一切都把西江引向了一个旅游发展以大幅提高经济收入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一切与之产生矛盾的因素都被掩盖或者压制了。
第四,文化生态畸变。
西江苗寨自开始开发起,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失去保护。据原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张处长介绍,在申报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西江和郎德都是难以取舍的,再三斟酌把郎德上寨上报了,希望再有机会将西江列入保护。后来有机会把西江苗寨列入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村”时,西江已经开始开发了,没有资格再收入保护名录,而这个开发就是在村寨旁边修了一条商业街,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近年来,还引进了职业歌舞表演团体,在西江每天提供上下午两场演出以及晚上的篝火晚会表演,另外,还加入了故事性的演出,杜撰出与苗王苗后等有关的子虚乌有的内容,扭曲了传统苗族文化,传播了伪苗族文化。②2012年3月采访于贵州省文化厅。
苗族文化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历史传承依靠的是语言和刺绣,在西江苗寨,所有的原住民因为旅游业的发展都学习了普通话,年轻的西江人甚至不会说苗语,语言态度中也表现出对于汉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推崇,西江原住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每隔一代人,越年轻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了解越少,汉化程度越高。年轻的西江人少有学习和从事苗绣的,数年间曾经一个学徒都没有,老一辈懂得苗绣的原住民则年事已高,现在重新开始学习的苗族年轻人多是为了在旅游业中进行展示,对于刺绣背后的苗族历史记载也不甚了了。毫无疑问的是,旅游开发作为特定的技术经济因素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扭曲和改变了西江苗寨原有的主流文化即苗族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江苗寨的文化系统已经成为了旅游的附庸,苗族文化的内核被破坏了。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可以天天过年、时时表演。
在这一切的背后,实实在在的是西江的旅游收入,2016年已经达到了41亿元人民币,收入的提高就是 “补偿”给原住民的 “幸福”,或者是 “购买”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 “价值”。
笔者三次到西江苗寨考察,第一次是2008年,西江开始大规模破土动工,建设新西江来迎接游客,以一种近乎于激动的状态开始大搞旅游开发,不惜拆部分建筑物或者以一种非原貌的形式修缮,以便能够承载旅游功能。第二次到西江是2011年年末,即将要过年的西江苗寨游客比较少,生意好的原住民和很少参与到旅游业中的原住民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差距,这种差距带来的社区结构不平衡使得西江人对旅游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少从旅游业中获利的西江原住民甚至憎恨旅游业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进出自己的村寨都要检查身份证,而仍旧依靠务农为生的这一部分人,谈及旅游便怨声载道,另外,文化资源保护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对于西江的开发也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过度的开发和利用是对西江最大的破坏,而对西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旅游业中获益匪浅的原住民和当地政府、旅游经营公司都对旅游大大称赞。第三次到西江是2016年,人山人海的西江已经和丽江、阳朔无二,走在景区的商业街上,并不清楚自己置身何处,因为这些著名的民族风情旅游点已经趋于同质化了,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使得收入不高的西江原住民们对旅游充满了排斥和厌恶。西江苗寨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苗寨,对于苗族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传承和民族的延续,这样的价值也许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即使每年有专项资金用于西江的资源保护,然而怎样的保护能够抵消掉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的对环境和文化的多重伤害呢?
(二)郎德态度
对于郎德的保护,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从村民到文化保护相关部门,都认为这是贵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得最好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有民族特色,原汁原味,自然淳朴。
至今,郎德上寨依然实行公平分配的工分制度,平均分配保护了村寨原住民的相对收入平衡,弱化了贫富差距的落差,也协调和统一了村民对于保护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自国家级文化相关部门到村寨的民间领袖寨老都一致认同的,对于家园环境的保护就是对于苗族自身的认可。郎德上寨的年轻人固然也向往城市和富足,但是他们对于乡村的生活保留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大多都会说苗语,还在上学的郎德年轻人放假必然要回到郎德上寨,参与到村寨的表演和其他活动中。年轻人结婚必然要回到郎德上寨按照苗族婚礼的习俗一步一步进行。十几岁的姑娘们多少会一点针线活,老一辈的郎德人认为年轻人应该去读书就不学刺绣了,但也觉得还是会一点更好。尽管现代的苗族女性需要本民族的服装都可以在赶集时买到工厂生产的现成品或者半现成品,她们还是认为传统手工制作得更有价值,因此,郎德的原住民多数是把母亲的礼服转赠给女儿或者是由婆婆、母亲和姨母等女性共同为后辈子女制作民族礼服。
郎德上寨的村民们说他们心中寨老的地位很高,寨老都说要保护,他们都会遵守,而这几位寨老要是不在了,有人可能就要动手开发旅游了。2012年重访郎德上寨时途经临近路边的郎德下寨,在2010年原本还是鹅卵铺就的乡间小路改成了可以进出车辆的水泥路,下寨不在保护令的区域内,因此,饭馆和客栈也多了几家,还搭建了新的风雨桥 (风雨桥本不属于苗族文化)直通上寨寨口。2016年再度来到郎德上寨,迎门的已经不是郎德的寨老们了,换成了盛装的年轻姑娘们,大型旅游客车已经开到了上寨寨门口,原本要走过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再穿过小河才到寨门口的诗情画意般的景色已经被旅游汽车呼啸的扬尘和尾气代替。即使郎德上寨的原住民们发自内心热爱和保护着自己的村寨和文化,比邻的西江始终都在演绎着另一种可能。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令纵然严格,但相关部门不可能时时刻刻在郎德上寨监督检查,所以,开发或者不开发,有时就在原住民的一念之间,事后即使惩罚也于事无补。面对着落后的生活条件和低收入水平,郎德上寨的村民也想改善,这无可厚非,随着旅游业的进入,雷山县政府给郎德上寨提供了集体搬迁的计划,搬迁之后的郎德成为专供旅游参观的景点,这个重大的变革又会带给郎德上寨怎样的命运呢?
四 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之辩
(一)“西江模式”的再探讨
国内学者王云才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发展的战略产业,它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为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提供了基础。①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旅游学刊》2002年第4期。事实的确如此,旅游开发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切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业的成功必然引来其他村寨的侧目,正如当年丽江一夜走红一样,“西江模式”带动了经济腾飞一举成名,吸引了大批同类型地区的参观团到西江学习和借鉴 “西江模式”。如今再谈到 “西江模式”,尤其是在西江旅游开发30年之后,应该明确它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一个政策指引或者一种制度的模型,经年累月,“西江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生态和旅游开发共生的方式,它包含着当地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当初开发西江苗寨的政策不过是开启这一模式的引线,后来的 “西江模式”是西江当地政府和经营公司以及原住民和游客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各方面优势和局限在近10年的时间里已经逐步显现出来。
“西江模式”目前看来在旅游开发上显示出了经济成效,它的基础是西江苗寨独特的文化资源:全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几乎全部都是苗族的苗寨。此外还有不错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依山傍水而建的苗族吊脚楼村落。文化资源和人文景观在旅游业发展中转化成了经济效益,这种转化并非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可再生产、可持续并保持原貌不变,而是经过不间断的转化接受了主流价值观的经济优先导向,成为经济发展的傀儡。西江的原住民不断否定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城市文化,不惜篡改自身的文化核心来迎合游客对于少数民族的臆想,然后按照这种 “臆想”将原有的苗族人文景观也改造成跟其他民族文化旅游地风格类似的境况。发展的基础改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编造伪民俗和快速走向城市化,西江苗寨的文化内核完全被更改了,它原有的文化生态不复存在。
“西江模式”是不是一个值得各地少数民族村寨开发旅游全盘借鉴的模式还有待定夺,它并不完善,也不是一个广泛适用的乡村旅游模型,它只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探索实践。
(二)郎德态度的可能性
一直保护着坚守着但时时面临开发的诱惑,郎德上寨的态度也随时可能会动摇。郎德上寨的苗族在30年的时间里忍受着西江苗寨的开发诱惑,坚守着对自己村寨和文化的保护,除了认可之外也应看到,不发展的死保护是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追求衣食富足的现代化生活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发展旅游对于有着国宝称号的郎德上寨势在必行。需要讨论是以保护为基础的相对缓慢且更为科学的旅游发展能不能满足人们想要快速致富的欲望。
在人文民居和自然风貌及文化生态上保护得相对更好的郎德上寨一直以来的定位都是接待外国旅游团和国家地方的政要等,不设住宿、餐饮,来郎德上寨的游客只能参观村落和观看原生态的村民演出。这样初级的旅游发展不会成为郎德上寨的支柱产业,所以郎德上寨的主业一直是农业,但迫于地理条件限制,郎德上寨的农业发展很不乐观。一旦进行二次开发,旅游业必然成为支柱产业。郎德下寨不断新建的民宿和餐馆正在重复着西江的道路,郎德上寨村民的迁出和寨口公路的建设都是在为旅游业做准备。
在二次旅游开发和文化生态保护之间做抉择对于郎德上寨的原住民来说必然是艰难的,大多数原住民都积极支持保护村寨并以此为荣,他们能接受游客来他们村寨参观并赞叹保护得好,不能接受像西江那样因大批量游客入境而破坏村寨。地方政府为提高经济收入已经把路修到了寨门口,下寨的改建也是在为上寨做辅助,可见 “擦边球”已经打到了郎德上寨的边缘线上。
(三)旅游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共生
进行开发或者保护对于地方而言都是一种决策,而决策本身无法强行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态势,原住民、村寨和各个参与决策者,以及潜在的游客等才构成决策的整体。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影响结果的是各种参与因素和人们的态度,各方的态度和立场往往出自于身份地位和观念的差异。政府按部门职能倾向决定要么保护要么开发,地方希望通过卖风景、卖文化产生经济效益,少数民族同胞希望在家门口脱贫致富①秦竩:《旅游开发:“伪民俗”与 “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4日第8版。,游客希望在他乡追寻原始的自然风光和想象中的少数民族风情。政策和规划作为决策不能面面俱到,只是一种倾向性指引,在实践之中必然会遭遇未曾预料的问题,例如西江苗寨的文化资源受到旅游业带来的创伤,而郎德上寨因为保护而相对贫穷,看上去似乎是开发与保护的对立矛盾,也可以理解为物质与精神发展关系的矛盾,这些问题并非完全不可调和,而要解决就必须回到旅游开发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原点——当地原住民。
从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的对比案例中可见,旅游开发并不能独立于原有文化生态环境之外而存在,文化生态的破坏跟旅游开发的经济增长不是正相关的。相反,文化生态的破坏导致旅游开发的基础动摇,进而关系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原住民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也是幸福感的来源。联系各种发展控制因素正是原住民的观念意识。
苗族原住民的文化传承千年经历了朝代更迭延续至今,有着完整的系统,它的内核是苗族对于万物有灵的信仰带来的平和、淳朴的民风,系统化的民俗和对民族迁徙史的荣耀感。现代社会不顾一切强行将金钱和物欲至上的 “幸福”观植入他们的思维中,这种 “幸福观”的结论就是现代化的城市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丰富的物质等于更加幸福。现代 “幸福观”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屈从于主流的价值观,从此失去平和与对万物有灵的平等的信仰,一步步忘却他们悠长的迁徙史,把特殊的节日常态化而毁灭了节日对于本民族文化自身的意义。
如果放弃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全盘接受旅游开发主导的经济优先思想,就能够 “幸福”的话,那么西江苗寨的原住民应该很幸福,可事实并非如此,:西江苗寨并非人人因为经济发展而 “幸福”,反而因为贫富不均产生了以前没有的矛盾和负面情绪。但为了保存固有的文化生态系统不与时代接轨而停滞发展就会出现另一种问题:假设郎德上寨的 “工分制”代表着共产主义性质和公平的幸福,那么,西江经济发展带来的对比就不会形成如此巨大的现实落差。
以原住民的 “幸福感”作为出发点,物质层面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满足似乎并不需要针锋相对。并不是一定要等物质丰富了之后人们才会追求精神幸福,两者的平衡才是真正的幸福。少数民族同胞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并不希望用破坏日常生活来换取旅游开发的一夜暴富,失去自我认同的原住民并不会在另一种文化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游客的钞票也换不来文化创伤的自愈。
城市文化越加成为主流,金钱至上的 “幸福观”越被推崇,少数民族地区别样的文化生态系统就越弥足珍贵,游客向往着欠发达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正是他们对于这些地区文化生态的认可,大可不必为了迎合游客的臆想而将原本的文化逐渐演绎成为不真实的模样,处处都是丽江、西江、阳朔,除了地名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游客到少数民族乡村来旅游的幸福感也会消失。
因此,保护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把他们的文化置于同主流文化平等的地位,尊重他们的文化系统和发展意愿,全然不必把旅游开发和文化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在旅游开发之前,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规划图册,武断地开始投资建设,而是应当深入了解各方决策参与者的态度和相关的影响因素,从一开始就更科学地探究开发与保护的合理范畴,计划旅游开发的合理增速,预测将要面临的文化和发展问题,以一种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更能带给原住民幸福感的道路。
——粤桂手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