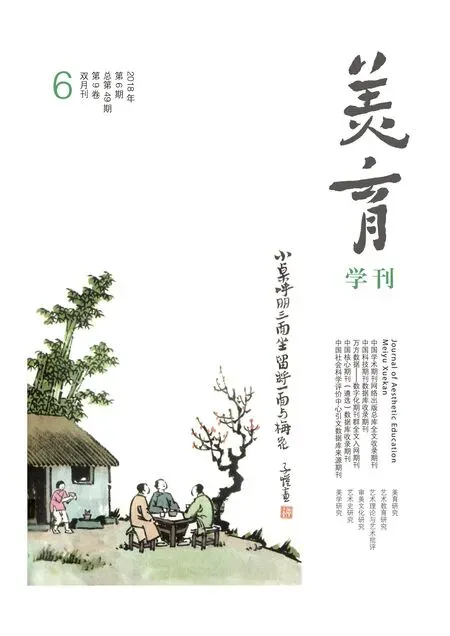儿童幻想小说的经典之美
——论《哈利·波特》的游戏精神
许 巍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
英国女作家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风行全球,曾在图书市场创下奇迹并“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1]。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后在儿童文学文化批评领域引起轰动,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纵观近20年学界对这一系列小说的研究,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倾向于对作品进行文化解码,多数用文化批评的方式解读作品的现实意义而很少挖掘作品的美学维度,有的甚至对其持否定的态度。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评析《哈利·波特》时会充分肯定其审美功能。然而,正如李学斌所述,传统的接受美学过于强调读者在文学场域上的作用而忽视了文本固有的美学特质。其实,儿童作品本身“所蕴涵的审美信息,及其审美空间的深度、广度,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136。它们向儿童读者发出了召唤,要求读者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意识和情感与文本建立联系,激发读者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体验。总之,在儿童文学的审美阅读中,文学文本在先,儿童读者在后。儿童作品之所以产生审美价值是因为它内聚文学性和美学特质。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曾指出,欧美儿童文学倾向于幻想型,不仅“追求奇特、神秘的艺术效果”,而且“侧重于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游戏精神,主要影响于少年儿童的精神性格、审美情趣、想象空间”[3]。这就需要作家将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夸张、变形、荒诞、非物性、时空错位和任意组合等具体生动的艺术表现“转化为文学的审美阅读图像与生命体验”[3]。所以,我们在谈论《哈利·波特》的审美功能时首先要考虑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西方儿童幻想小说的文学经典性和美学特征。有学者指出,主人公哈利直面挑战、无畏权威的品性特征以及不断追寻自我超越的个性气质促使儿童读者进行“审视自我”和“体验环境”、在自我发现或探索中最终获得教益[4];也有学者认为,哈利在应对人生难题时所显现出的悲剧般的崇高美对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重要价值[5]。他们虽然都强调了《哈利·波特》的美学内涵,但还未明确论及这一系列小说的游戏精神。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是其独特的审美心理和情趣的表达,游戏性的突出自然成为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审美精神的重要途径。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艺术精神,甚至指向整个儿童文学精神:“儿童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游戏。”[2]70这种游戏精神不止于展现文本中游戏式的欢闹活泼、好玩有趣的审美效果,而且蕴含着属于儿童生命本体的内容与意义,与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达成默契。如此,才能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经历并释放出对于生活和世界的最为真挚的感受和领悟,帮助他们实现情感的满足、情趣的回归和情智的培育,从而使其个性趋于丰富健全、甚至成为席勒所倡导的“完整的人”:“在人的各种状态下正是游戏,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6]对于儿童读者来说,阅读或欣赏作品就如一场自我形塑、自我实现的游戏,是游戏精神真正实现了儿童作品的审美价值。《哈利·波特》深受小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更多地传递出一种“游戏效应”:主人公从一个弱小无助、懵懂无知的男孩成长为一名破除万难、优秀全能的魔法师,这样的故事情节无疑满足了囿于现实规范的少年儿童读者的愿望,让他们在寻求释放和补偿中达到精神的平衡。除此之外,小说的场景设计、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文学手段更是造就了庄谐并重的游戏精神:“幻想性”和“幽默性”构成小说的两大美学品格,艺术性地再现了游戏般自由、快乐且积极昂扬的儿童生命活动。这种游戏精神的核心就在于“玩闹”等表象背后的“情感的自我调控和超越”,“乐观精神的弘扬和建构”,“以想象力、创造力为核心的童年生命形态的激扬与释放”。[2]70
二
作为当代儿童幻想小说的代表,《哈利·波特》呈现了不为惯常思维所能理解、不被既定法则所操控的“第二世界”,以其虚实交错的魔法文化深深吸引了儿童读者。文本中的魔法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儿童的现实生活,因为那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存在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7],引领他们从成人世界进入属于自己的王国,享受生活的真正自由与快乐。幻想是儿童独特的心理品质,它“既是一种现实性缺乏的补偿,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预测、预演,一种以神秘方式展现在他们(儿童)面前的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8]。而《哈利·波特》正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幻想的诗性描述,让他们在自由想象的游戏中体验生命能量的飞扬、激发出生命的创造力。这是幻想在文学作品中之于儿童天性发展的意义。
哈利的魔法世界可谓眼花缭乱、光怪陆离,除了奇妙诡异的魔法生灵、应接不暇的魔法技艺与咒语,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魔法器具,例如飞路粉、鱼鳃草、冥想盆、复方汤剂、复活石、时间转换器、老魔杖等天马行空的幻想物比比皆是。但如潘冀春所言,小说中“很多令人梦寐以求的魔法道具都有着虚幻与现实紧密融合的特点”,透射出的力量“无限靠近人类想象的终极边缘,”它们背后却是主人公们“思想意识的操控与指挥”。[9]故事人物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会重新唤起儿童读者破除自然法则或现实规范的冲动,让他们更容易地与阅读对象建立认同关系:“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达到情感的移置与分享”,“把他人的经验与感受当作自己的经验与感受。”[10]113思其所思,行其所行,在满足感和愉悦感中忘记故事的虚幻性而实现一种“想象的真实”。儿童对能力的渴望是非常重要的心理需求,他们在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多种力量时往往表现出无奈、无助和无望等消极情绪,转而嫁接于幻想世界中的特殊体验来释放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以上所提及的魔法器物具有强大的法力,都有可能成为儿童读者渴望拥有某种能力的投射对象。作者对它们的精心设想与构思符合儿童“精神扮演”的审美阅读心理,具有浓郁的游戏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源于日常生活的魔幻意象。一类属于日常活动空间的延拓,诸如破釜酒吧后面的对角巷,国王十字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以及移动变幻的楼梯台阶,在此,现实世界中庸常的活动空间超越了固有的形态与功能,其中隐藏着的玄机或孕育着的各种可能性正召唤着儿童读者前去挖掘和探索,从而促使他们的心灵指向无限的想象;另一类属于日常事物的再创造,诸如飞天扫帚、飞行摩托、打人柳、熄灯器、活点地图、交头接耳的画像、穿梭扑闪的钥匙等不胜枚举。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华丽变身为活力四射的魔法物品,有些关键性的魔法器具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小时候与伙伴们玩耍的扫帚成为魁地奇比赛中清除障碍、争强取胜的空中利器;高中时期搭乘兜风的汽车变成罗恩家上天入地、横冲直撞的老爷车。总之,魔法世界到处充溢着类似的游戏情趣:担任信使的动物是猫头鹰,空中的飞行工具是扫帚柄和摩托车,进出穿行的通道不是门窗而是画像后面的墙洞,巫师商店兜售的零食和玩具分别是“果冻鼻涕虫”“冰耗子”“滋滋蜜蜂糖”和“粪蛋”“饱嗝糖”“咬鼻子茶杯”等等。这些奇思妙想打破日常禁锢(如汽车不再受制于交通规则;扫帚不再受限于地面、突破缓慢拖沓的刻板形象),把现实中毫无关联的事物衔接在一起或者把截然相反的概念结合成一体并赋予其崭新的价值和意义(前者如“粪蛋”“果冻鼻涕虫”;后者如“打人柳”“冰耗子”)。它们在改造现实物品的基础上不失真实性,同时让儿童读者在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体味新奇与快乐、收获惊奇的体验与启示,成为他们渴望超越现实生活、释放自身创造力的投射对象。罗琳的艺术创作就如一场想象力的游戏,十分契合儿童读者的心意,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游戏在“成人感到平淡无奇的地方发现无穷乐趣,创造新奇的意义”[10]112。在罗琳创造的魔法世界中,儿童读者能够尽情挥扬被现实压制的想象力,他们经历冒险活动的成就感得以满足、充分表现自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可以说,幻想性赋予《哈利·波特》“一种艺术逻辑的真实”[11]:故事通过艺术形式的展现而成为儿童读者审美享受的对象。它不仅在儿童认知能力的范畴内给予故事丰富的生命情态、让读者感同身受、心领神会,而且能够触发他们想象的兴奋点而去开拓心灵发展的自由空间。小说的审美价值在于其对现实生活的诗性把握,通过幻想赋予现实生活存在的意义。
三
据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学斌所言,儿童幽默作为“一种特殊游戏形态与儿童生命状态息息相关”,它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作家艺术创作的过程而成为文本独特的审美属性[12]71。《哈利·波特》的作家罗琳也不例外,她笔下的情景编排和人物设计既夸张又充满谐趣,让儿童读者流连忘返、在幻想的游戏中体味细节的离奇、错位或相互背离而产生的幽默感。进一步说,小说展现的幽默是“一种在现实基础上悖情、悖理的反常态语言、行为或情景创造”[2]160,作者对不协调关系、矛盾组合的呈现与处理构成儿童读者体验幽默的重心。这里首先包括在夸张、讽刺和对比等艺术手法加工下所显现的冲突和斗争,它们带来奇巧而热闹的幽默效应。故事中至少有两对人物的关系体现了“超常喜剧性矛盾”,即幽默的本质[13]:哈利和德思礼一家的对立、以哈利为首的学生群体和乌姆里奇巫师的交锋。前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弱者或被动群体,从一开始就以“正面形象”出场;而后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强者或主导群体,始终以“反面形象”示人。为了持续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期待,罗琳调动以上这些文学手段来强调、突出正面人物的气质与特点,或者去揭露、嘲讽反面人物的形象,从而造成超越常识、常规和常理的矛盾和冲突。它们足以能让现实世界中的“正常与反常”“正经与荒唐”“现实与理想”“有序与无序”颠倒错位,由此产生的滑稽感或荒谬感就构织出喜剧性意蕴。
小说主要讲述哈利及其朋友在魔法世界的成长历程,作者罗琳显然是维护主人公的立场、从儿童的视角看待其周围的成人与老师。德思礼一家是哈利在现实世界的唯一亲戚,收入可观,生活体面,代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可是,在哈利的眼里,弗农姨夫“膀大腰圆,没有脖子”[14]2,整天想着公司钻机的买卖业务;佩妮姨妈“骨瘦如柴,长着一张马脸”[15]11,总喜欢窥探邻居的私事;达力表哥有“五层下巴”,就像“一头戴假发的猪”[16]13,总是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哇哇大叫。这种对人物形象的变形处理具有鲜明的喜剧性与深刻的用意,让小读者攫取到“情理之外”的阅读快慰感而进行大胆恣意的想象游戏,产生趣味盎然的审美效果。儿童钟情于魔法世界而抵触现实世界的原因之一就是诸如德思礼一家人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商业社会的思维定势所裹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日常生活被电子产品和商业消费品所垄断,由此带来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操控了他们的认知模式,驱使他们抗拒任何与“幻想”有关的东西。小说多次呈现德思礼一家和哈利的矛盾冲突,凸显了他们极力抵制“魔法”而陷入自欺欺人、几近发狂的场景。这家人平时视哈利为异类,忙不迭地嫌弃、排斥他,随后遭遇“魔法”而又紧抓哈利不放,千方百计地阻止他拿到霍格沃茨的入学通知书。为此,弗农姨夫与“魔法”展开一场闹剧式的争夺大战,竟然气得“揪掉了一半胡子”[16]25、“挟持”哈利一路逃窜至荒无人烟的礁石岛上。如上文所示,德思礼一家是典型的“麻瓜”,理应遵循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然而,他们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举动违背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其言行的前后矛盾性或不可理喻性是理性失控所致,促使他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轨道,令儿童读者感到可笑的惊奇而难以相信他们的真实存在。无独有偶,魔法世界有一位与学生唱对台戏的乌姆里奇教授。罗琳以哈利的视角对此人进行详细的描述,特别指出她“像弗农一样看不见脖子”[17]102,这一细节暗示了她与弗农姨夫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颇具反讽意味:乌姆里奇说话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经常遭受学生的嘲讽或反击;她的行动总会遭遇适得其反的下场,例如,她禁止学生阅读《唱唱反调》中采访哈利的文章,结果是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在谈论这篇采访,《唱唱反调》的发行量一路飙升[17]382。与此同时,罗琳多次提及乌姆里奇留给哈利的印象:活像一只“大癞蛤蟆”。可想而知此人的品性特征:平时喜欢哗众取宠,上课却枯燥死板。与学生的第一次交锋中,她极力否认黑巫师卷土重来的事实而无视学生的需求,一味地照本宣科、灌输魔法的理论知识,哈利等人奋起反驳而遭受其严厉的责罚。随着师生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姆里奇以学校最高统治者自居,强行解散学生团队和俱乐部的活动,到处扼杀学生对学习生活的创造想象力。文中出现的“母夜叉”“老妖婆”“丑八怪”“老蝙蝠”等称谓不仅表露学生对乌姆里奇的厌恶憎恨之情,而且让文本外的读者自然而然地把她的品质形象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愚蠢短视”“凶恶专横”等行为特征等同起来,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某段经历、相信有关事件的真实存在。但是,这种揭露或抨击丑恶现象的过程并不沉重,主要通过突兀的对比给读者带来奇妙有趣的阅读体验。罗琳在安排乌姆里奇出场时,特意凸显人物身上的若干“不和谐”的细节。首先,这位女巫的身份地位与其穿戴举止极不协调:作为魔法部的“高级副部长”,霍格沃茨学校的高级调查官和校长,她现身于部级审讯会,学校的开学典礼等重要的官方场所,但总是身穿“毛绒绒的粉红色开襟毛衣”、头戴“黑色天鹅绒小蝴蝶结”或“粉红色大蝴蝶结”,喜欢粗鲁无礼地打断他人的讲话;其二,乌姆里奇的相貌与其声音极不相称:“癞蛤蟆”般的模样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又矮又胖”的个子搭上“又高又尖”的声音,“阴森的笑容”配着“甜腻的声音”。其三,在她管理下的学校阴森郁闷、死气沉沉,而她的办公室却布置得艳丽花俏、俗气腾腾:“挂着一组装饰性的盘子,每只盘子上都有一只色彩鲜艳的大猫咪。”[17]185这两个场景形成极端的对比,产生强烈的感官冲击力,让读者忍俊不禁、体味轻松滑稽的文本氛围。以上细节的设计正好符合幽默感产生的逻辑:“就是从语言、心理、行为、肖像等方面,描写出与人物的时代、身份、场合等‘不和谐’的细节表象所展现出的‘可笑味’……把此举与彼举、此地与彼地当对立,不合常理地交错在一起,让人从矛盾中感受到突梯滑稽。”[18]在此,罗琳对现实生活的素材进行重新编排,融合了写实性与虚幻感,通过不可能的、不协调的组合勾勒出荒诞可笑的阅读对象。罗琳以漫画式的夸张、讽刺和对比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有效地营造出幽默效果、传达作品“外在的幽默”[注]据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学斌所言,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本里蕴含着双重的“幽默效应”,分别是“外在的幽默”和“内隐的幽默”,这两种幽默的具体定义或内涵请参见其著作《论儿童文学幽默效应》的第140页。。
四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具有一层更深意味的“幽默”,它直接指向儿童生命的本真状态、儿童游戏精神的核心。这种幽默主要体现在“顽童”形象的塑造上。具体而言,小说中韦斯莱孪生兄弟的言语举止构成最具幻想性的不协调的场景,他们在家庭、学校等环境中显得奇特兀然,与其他人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又融入其中并积极影响着他人。他们是典型的顽童,是罗琳再现儿童幽默的不可或缺的环节。“顽童”成为“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儿童文学中最主要的形象类别与价值范型”[2]219,代表着儿童读者“心底里被抑制、被框范的那个真正的‘自己’”[2]221,是自由、快乐与力量的代言人。韦斯莱兄弟俩继承了经典“顽童”形象的美学特质,他们身上的“游戏精神”正是作品幽默价值的主要体现。
弗雷德和乔治在韦斯莱大家庭中属于“非典型”的孩子,在学校是有名的捣蛋鬼、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他们以机智风趣的言语质疑甚至否定成人世界的常规常理,以夸张不驯的行为把玩甚至颠覆那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他们身上展现的戏谑精神别开生面,构成魔法校园中奇妙的生活场景,这可能是“大家都觉得他们很有意思”[16]60的原因。兄弟俩看似麻烦制造者,喜欢“违法乱纪”,总想创造一番自由的天地。小说数次提及他们对学校“级长徽章”的反应,例如他们经常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嘲弄哥哥珀西的贪图荣誉和固守陈规:以珀西的名字和“级长”的第一个字母都是“P”为理由吵闹着给后者穿上韦斯莱夫人为其编织的毛衣。兄弟俩对珀西的调侃和戏弄实则是藐视和挑衅既定规章制度的表现。珀西后来叛离家庭、投靠魔法部的举动应验了他俩智趣盎然的对话:
“魔法部明天会提供两辆车的。”
“为什么?”帕西好奇地问,
“那是为了你啊,珀西,”乔治严肃地说,“帽子上插着小旗,小旗上还有缩写字母HB——”
“——就是奇大无比的大脑袋啊。”费雷德说道。[15]38
对于罗恩当上格兰芬多学院的级长这件事情,兄弟俩反话正说,是为母亲的过度关注和特殊对待而愤愤不平;尔后他们正话反说,“是啊!我们违法乱纪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17]115,是为罗恩不能和他们一起冒险而惋惜不已,以至于让罗恩产生循规蹈矩等同于愚蠢无知的念头,“只有傻瓜才会当上级长”[17]115。诸如此类的戏言或者恶作剧式的举动使他们在魔法学校广受欢迎。毋庸置疑,罗琳本人也认可兄弟俩的做法,与他们一起致敬恶作剧的人:“高尚的人啊,不倦地工作,为的是帮助新一代破坏法规的人。”[15]116罗琳似乎想说明,例如“活点地图”这样的宝物只有通过恶作剧的形式才能发挥其神奇的功能,帮助哈利弥补内心的缺憾,实现他在霍格莫德村欢度圣诞节的愿望。的确,弗雷德和乔治把魔法学校当作“玩闹”的舞台,把同学当作“恶作剧”试验的对象,但也因此成为其他学生眼中的“开心果”甚至英雄。他们研制出“鼻血牛轧糖”“昏迷花糖”“速效逃课糖”等各种帮助躲避繁重枯燥的学习的魔法产品,大家遭受他们魔法的“折磨”后反而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产品。他们还利用魔法幻变出多种对抗学校专制管理的手段,例如点燃施过魔法的烟火,把学校的走廊变成沼泽地。高潮部分是他们捉弄乌姆里奇后乘坐扫把扬长而去,后者气急咋呼的狼狈相和学校师生惊奇欣喜的心理活动形成极具冲击力的喜剧效应。这些“恶作剧”为黑暗时期的魔法学习带来亮光与快乐,其他学生从他们身上寻得愉悦与满足,儿童读者也跟随书中人物一起狂欢庆贺。孪生兄弟以“反教育”的面目出现,消解了成人加于孩子身上的主流价值期待和学校加诸学生身上的道德评判,营造了内心消极情绪得以释放的空间与机会,从而让其他孩子窥见真实的自己,传递了“顽童”形象普遍具有的审美情感。
不仅如此,弗雷德和乔治更是儿童追求生命力量的象征。他们的“恶作剧”充满想象力、极具创造性,“嗖嗖—嘭烟火”和“便携式沼泽”堪称大家口口相传的杰作,获得麦格、弗立维等教授的赞赏,被认为是“了不起的魔法”[17]561。他们的新奇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和学校家庭的管制氛围格格不入,两者的交集碰撞产成幽默的效应——这就是一种力量,不仅感染了魔法学校的学生,而且直接作用于儿童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孪生兄弟实现了儿童真实生命状态的外化,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生活格局、满足内心无限渴求的但又无法实现的愿望的自由力量。这点可以从主人公哈利和孪生兄弟的关系中看出:他们彼此欣赏、相互帮助并达成一定的默契,兄弟俩似乎成为背负重大使命的哈利在潜意识里的那个具有自由主体精神的自我。作为小说的配角人物,弗雷德和乔治游离于主要事件之外。然而,罗琳总是安排他们进行事后的参与,例如当哈利被误认为是袭击学生的密室怪物后,兄弟俩并不像哈利的其他朋友那样极力避而不谈,而是高调地宣扬此事:“给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让路,最邪恶的巫师驾到……”;“是啊,他要赶到密室,和他长着獠牙的仆人一起喝茶呢。”[14]123显然,他们脱离了当时众人所关注的话题范畴,以嘲讽、反讥的口吻对事件本身进行否定或超越,由此形成一种具有正能量的幽默效应。儿童读者会感受到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语行为的背后闪烁着他们的纯良天性与智慧热情,随之对此暗自赞叹或拍手称快。兄弟俩是勤与“懒”、公与“私”、正与“邪”的奇妙统一,他们展现的“游戏精神”看似与成人世界的价值判断背道而驰,其实孕育着真诚、善良、正义感与责任心。在伏地魔崛起的一系列事件中也不缺乏孪生兄弟的参与:他们施法让雪球追着奇洛教授跑、“砸在他的缠头巾后面”[16]119——读者到后来才发现他们砸的是伏地魔的脸;在秘密电台“波特瞭望站”上,他们声称伏地魔“正在造成一点点可爱的恐怖气氛”[19]324,通过笑话提醒大家保持冷静,其轻松诙谐的口吻足以逗乐逃亡在外的哈利;在霍格沃兹保卫战中,他们通过反话正说来振奋大家的情绪,鼓励大家的战斗士气:“我们赶紧上楼战斗吧,不然所有像样的食死徒都被抓住了。”[19]445“这个夜晚真过瘾。”[19]457即便弗雷德在牺牲前的一秒钟内也是玩笑不止。兄弟俩自始至终视伏地魔为最大的笑柄,他们的言语举止看似对穷凶极恶、闻名丧胆的伏地魔的调侃作弄,实则在无形中已化为对抗恐怖与专制的重要武器。他们的幽默具有积极的感染力,表现为逆境中保持昂扬乐观、风趣豁达的生活姿态,在最黑暗的时期传递快乐的生命力量,给予他人勇气与希望去面对危险、克服困难,赋予儿童读者一种肯定的美学判断。罗琳笔下的“顽童”形象集自由、快乐、机智、想象力和创造力于一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游戏为核心的儿童精神世界,将文本的儿童幽默效应推至高潮。
五
儿童游戏精神的审美创造离不开作家对儿童生命活动的情感态度,即“以理解之心、欣赏之情、乐观之态”关注儿童的“游戏、玩闹、恶作剧等种种童稚行为”,把它们“当作有价值的生命形式予以充分肯定的态度”[12]72。以此为前提,作品才能保存“作家对儿童独特精神状态的认识和把握”[20],作家才有可能以儿童的眼睛看待周围的人事,以儿童的心性感知所经历的遭遇,实现童年情趣的回归、致力于对童年价值的维护。他们关注并挖掘儿童的情感、意识和行为等方面的审美特征从而复归或重塑童年生活。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丰盈的童年情怀,作家罗琳不仅得到儿童读者的情感共鸣与认同,而且也使得她自己对童年时代的记忆、认识和感受得以释放和弥补,达到“作家自我表现意义上的情感宣泄和精神补偿”[2]202的目的。由此,小说完成了读者和作家双层面的审美游戏创造,帮助我们解释了《哈利·波特》等这些成人作家为自己而写的小说如此深受儿童读者欢迎的真正原因。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赋有以幻想性和幽默性为内容的儿童游戏精神的美学特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能够当之无愧地跻身西方儿童幻想文学的经典之列。
——吐槽之神快来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