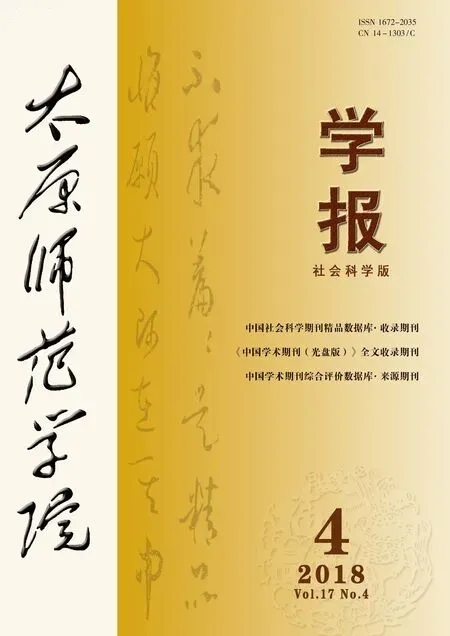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
(1.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2.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安徽 宣城 242000)
一、小引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虽然在马克思生前这部著作只是以“手稿”形式存在,没有发表,但自从它1932年面世以来,这部手稿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特别对该部著作中的“异化”概念作了发挥。当然,我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部著作。笔者认为,这部著作蕴含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类本质”,这个概念是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把钥匙。它表明了马克思从人学方向、从哲学方向——而非经济学方向——推导出共产主义的进路,即,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首先是出于人固有的类本质,或者说,出于人固有的要实现或恢复人的类本质的倾向。
以前的学者虽然也大谈特谈“异化”,但他们大多谈论的是劳动的异化,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或者,一般地谈论“异化”,比如像卢卡奇,将“异化”普遍化为“物化”,揭示了人异化为物的过程;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揭示、对人被功能化被异化为某项理性功能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延续了卢卡奇的思路。但他们都没有考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否免于异化?这里的关键是:以前的学者都没有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没有注意到劳动的异化只是一个表层现象,而更深层的异化其实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或者说,人失去了“类本质”。
二、“类本质”概念辨析
“类生活”、“类本质”等术语费尔巴哈也使用过。费尔巴哈用这些术语表示人的概念、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概念,这种生活以友谊和善良,即以爱为前提,属于类的自我感觉或个人属于人群的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得每个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但费尔巴哈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不懂得要恢复或者说实现人的类本质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创造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笔者认为,“类本质”、“类存在物”等术语确实是费尔巴哈使用的,且费尔巴哈使用的意义与马克思大致相同,但该术语更早的来源则是费希特。在其伦理学中,费希特认为自我不是单个的自我,而是作为群体的“类概念”,单个的自我实际上是由后者建构的而非相反,也就是说单个的自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人的社会性质。费希特说:“人的概念绝不是个人概念,因为个人概念是不可想象的,相反,人的概念是类概念。”[1]297而这也就等于说,“社会意向属于人的基本意向。人是注定过社会生活的”[2]18。
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与费希特、费尔巴哈一脉相承,即是指人的社会性或群体性。类本质就是社会本质,同理,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类存在物就是社会存在物。但此处所说的“社会”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普通的社会,后者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真正的“社会”,而是异化的社会,在异化的社会中人不具有真正的类本质、真正的类生活。真正的类本质或类生活是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不仅想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产品来确证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合理内核,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在对象化的实践和结果中确证自己的方式,是人的需要。,而且一般地,也想要通过他人或者说社会,也即通过人“类”的实践和产品来实现自己、直观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人的类本质就好像是你希望人人都是在为你工作,类生活就好像是人人看起来都是在为你工作。另一方面,类本质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不同于动物的生产“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3]53人的生产是脱离个体肉体需要的生产,是一种类生产,是人作为人“类”、为了人“类”的生产,他通过这种生产所实现和确证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类存在物、作为人“类”的本质。再比方说,好比你是某家族成员之一,你的成功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而且也是家族的成功,也是为了家族。这也是人天生就有的倾向,是人的类本质。当然,上述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3]79。通俗地说,类本质就是,人天生有被别人爱的需要和爱别人的需要。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爱或者无法爱别人,那么这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人失去了类本质。
如何摆脱异化呢?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3]79。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化的现实才能够实现一个人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也就是实现人的类本质。这里的“社会”是指马克思心目中的真正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导致异化呢?因为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处处显得不是自己的,而是某种陌生的、冷漠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异己力量的,使得人不能自由地外化自己的本质力量,不能在世界上确证自己的本质,从而使得人变成了动物性的、肉体的、个体的存在物,失去了类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54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也即类生活对人来说仅有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意义,而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意义,人们结成社会不再是因为出于真正的类生活的需要(在这种类生活中,人能在他人或社会那里直观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存在),而仅仅是出于一种经济需要,维持肉体存在。这就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也即类本质的异化,而这种异化也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54,因为他不再能在他人那里直观自身,他人也不能在他那里直观自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连资本家也逃脱不了异化。资本家虽然不从事直接的异化劳动,但私有制同样束缚了他,使得他的存在也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他的自私自利是一种天性,使得他的存在不是为别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工人虽然受雇于他,但并不是“为了”他而工作。资本家是一个既无法爱别人又不被别人爱的人,他的类本质同样被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这一点却从来就不是人的本性,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人感受不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和尊严。可见,我们并不是为了抽象的经济上的平等或解放生产力之类才要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恢复人的本质和尊严: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人学概念、哲学概念,经济学考虑只是手段。
当然,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异化状况需要通过经济手段,即扬弃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使得对象化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不再是非己的、别人的,而是处处成为自己的,成为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正如马克思所说:
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3]82-83
扬弃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是手段,目的是要使得“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这样的社会才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即,它不再是单个人的对象,不再是私人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即,人成为类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即,在这种情况下,人具有真正的(而非异化的)社会本质,也就是类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化大生产仍然存在,但工人并不会异化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因为甚至连机器和机器化大生产都成为工人本质力量的确证,“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
马克思还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80这一段向来是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难点,在笔者看来,应作如下理解: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使得自然界对人来说到处都成为他自我确证的对象,成为真正的(而非异化的)社会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因而自然界成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那么,为什么还说“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呢?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对象化活动是出于实现人的类本质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界,人不再为了私利而去争夺自然,而是作为人“类”、为了人“类”的生产,从而人就不再会认为自然“反正不是我家的”而去破坏自然,因为自然是每个人作为人“类”的共同的对象化领域,因此人必然不再只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改造自然,而是会按照“类”的尺度来改造自然,会按照美的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进行对象化活动,所以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78。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类本质”概念,还有几个特别的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除了谈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外,还谈论劳动的异化,这是以前的研究者谈得比较多的。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否存在着两种异化或多种异化呢?笔者以为不然。劳动的异化和类本质的异化以及其他异化都是一回事,或者说,都是紧密相连的。在讨论劳动异化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使人的类本质、使人同人相异化。[3]51-54可见,这些异化是内在相连的。劳动的异化是表层现象,而类本质的异化是深层现象,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
2.前面曾说过,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是与费希特、费尔巴哈一脉相承的。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在哲学史上,把人看成是群体动物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往后看的话,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与他人共在”的存在论结构也与马克思的“类本质”有些相像。只是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群体性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群体性语境上有很大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的群体性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生存、分工合作的意义,一个人是无法自足的,城邦才能自足,这种意义上的群体性有点像一般的群居性动物。(当然这种经济生存意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群居性动物,因为后者之所以是群居的乃本能使然或自然选择使然,即,虽然群居性动物的群居性更有利于其生存,但这却并非动物之选择,并非动物“为了”其生存的选择,而人的群体性则是历史地形成的或理性选择的,历史与理性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维度。)而马克思的“类本质”却没有这种经济生存的意义,人们之所以要结成社会并非出于经济生存。
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群体性也没有经济生存意义,他认为此在总已经是“与他人共在”的,这个“与他人共在”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群体性,而所谓存在论意义,在笔者看来实为美学意义,[4]50-55即,人之所以总已经是群体动物乃出于一种语言—意义上的(区别于肉体上的)情感需要,因为语言—意义的有效性总是一种主体间性,一个人是没有语言、没有意义的,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而此在的存在既然有“意义”、既然是一种“意义”性的东西,它当然总已经是“与他人共在”的。而马克思的“类本质”并无这种存在论意义,人之所以是社会动物并非因为人是一种语言性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仍处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人之所以具有“类本质”,或者说,人之所以是一种群体动物、社会动物乃出于人的概念本身,这种人的概念处在某种概念秩序之中,人的本质是其概念的规定性。如果要问这种概念秩序是哪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大都相信,这种概念秩序是先于人而存在的,而且是必然的、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神圣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虽然最终都反对德国古典哲学,但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某些概念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类本质”即是一例。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群体动物并且想要过群体生活,不是因为人是肉体动物或语言动物,而是因为“人”是某种神圣的概念。
3.有的论者注意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批评过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所作的“类”的理解,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没有从现实性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18。
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研究的一个令人困惑之处,因为在这里马克思似乎对于“类本质”这一概念持否定态度,这该如何解释呢?要知道这两份文献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到8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为什么时间上如此接近的两份文献会有着相反的观点呢?难道马克思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可能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就改变对自己不久前还反复讨论的一个概念的态度。笔者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所批评的对人的本质所作的“类”的理解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是两回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5]18
马克思并没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否定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反复提到的“类本质”,而是反对费尔巴哈对于人所作的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虚假抽象,这种抽象由于脱离社会,只能把个体的人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无历史的、处于真空中的人,说这些个体具有某种普遍的本质只能是虚假的抽象、虚假的幻想。如果我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中的“类本质”换成“社会本质”,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中“理解为‘类’的本质”换成“虚假抽象”或“虚假的普遍本质”,那么我们就不会发生理解上的困难。换言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指的是作为“类”的本质,即人具有一种真实的普遍本质,这种本质叫作“类”;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类”可以被理解成虚假的“普遍性”。马克思这里所反对的只是虚假抽象或者说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抽象、反对普遍,因为任何学科都离不开抽象、离不开普遍。
4.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把马克思的类本质和共产主义思想理解成单纯的集体主义或平均主义,理解成一种不允许人的个性存在、发展的政治上的普遍主义。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实际上,马克思明确反对这种理解。在他批评主张实行公妻制的早期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时,他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缺点就是“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3]76。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或者说社会性并不必然要求采取集体的形式,人的社会性也并不与他的个体性相对立,二者实际上互为条件。对此,马克思有明确的论述: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3]80-81
可见,共产主义并不简单的是集体主义或普遍主义之类,共产主义也强调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社会性并不以消灭人的个体性为代价,反而以它为基础。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的类生活或者说社会生活也将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你虽然想要让他人过上好的生活,他人也想要让你过上好的生活,但你和他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好”的生活。
四、小结
综上所述,“类本质”概念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理解该文献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用这个概念表示,人们首先是出于其固有的类本质倾向而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社会”,在那里,个体和类之间已经和解,每个人不再是自私的个人,而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个人、作为具有类本质的个人,他不仅想要而且能够从他人或社会那里实现和确证自己,同时,他不仅想要而且能够使得自己对象化的活动,即,使得自己的工作,成为“类”的工作、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个体和类之间的和解同时也就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和解,同时也就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解……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3]78“类本质”概念显示了马克思从人学进路、从哲学进路推导出共产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思想,该文献中的经济学进路只有与哲学进路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