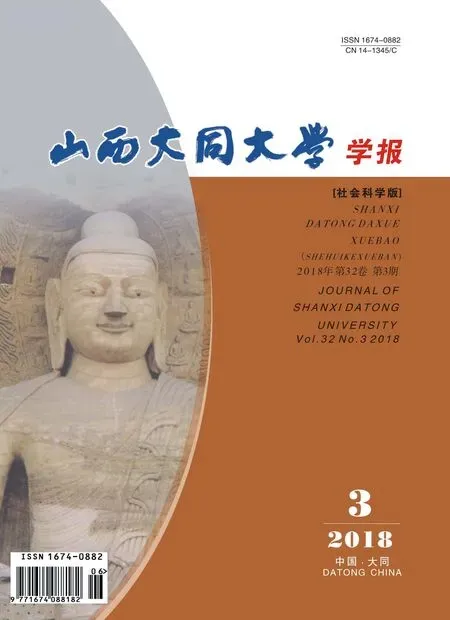明代北方军事防御体系建设探究
——以右玉要塞杀虎口为例
石 陶,刘凤强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军事防御的内涵是指军事上的防守与抵御,即对敌人的军事行动和行为进行有效的抵抗,以达到保护自身实力、维护统治安定的目的。军事防御相关的事物,主要包括军用工事、军事管理、军事思想等,它们共同作用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1]杀虎口作为边关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自然也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如何派遣重兵防守,设关设卡,成为历代统治者需要面临的问题。当前的史学界对于杀虎口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商业经济、民族关系、风土人情等方面,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我们将从工事修筑比较频繁、军事防御更加系统全面的明代展开探究,力求能对杀虎口的军事防御体系的构筑有一个更加直观、全面、系统的把握。最早关于杀虎口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在经历了唐宋的发展和元代的衰落,到了明代,随着蒙古、鞑靼部的频繁南侵,明政府为了统治的长久和边境的安定,多次对杀虎口的城墙、堡垒、屯堡等进行修筑与加固。内外防御之间相互配合,使得军需后勤保障得到了有效保障的同时,也使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构建逐渐走向合理,军事防御性得到大幅的提高,在震慑蒙古外敌的同时,也稳定了边境安全。杀虎口作为内蒙与山西二省三县之间的一个必经之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扮演着军事要塞的重要角色,这与它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一、杀虎口军事防御要塞形成缘由
(一)历史渊源 杀虎口在历史渊源上可谓是深远持久,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虽然朝代在不断地更替,但是它所发挥的军事要塞、贸易要地、交通要冲的作用却从未改变。《旧志辑录》中记载:“归化城为蒙古一大都会,而杀虎口实为中外之襟喉焉。”[2](P336)当时的杀虎口就是沟通归化城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要道。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杀虎口被称为“参合陉”,隋唐又被叫做“白狼关”,宋被称做“牙狼关”,一直到明朝才改名为“杀胡口”,但由于明后期蒙汉互市后为了避讳,被称作“杀虎口”。[3]杀虎口作为连接关内外的要塞,在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战国时期,这里曾是赵国的驻地,赵孝成王派李牧多次到这里击退匈奴的侵犯。汉初,匈奴又企图取道于此,攻入晋阳,当时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至大同征讨,此后又相继派出了大将柴武、周勃、樊哙等人征讨,雁门郡和马邑县相继被收复,叛将刘信也在参合陉被杀死。汉武帝在位时,李广、霍去病和卫青等也在这里抗击过匈奴,为边关的安宁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厚的历史渊源,奠定了杀虎口重要军事要塞地位的同时,也在朝代更迭中留下了许多军事防御的痕迹。让后来人能够在汲取前代军事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使杀虎口军事防御功能不断加强。
(二)自然防御屏障的运用 坐落在山西省右玉县城关(旧城)西北方向10公里处的杀虎口,得天独厚的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它不一样的使命。东边挨着塘子山,西边是大堡山,自西向东一个弧形的山沟被这两座山包围其中。在二山之间,有着一条长达2000多米的险峻山谷贯穿其间,这条山谷也成为唯一的一条连接内蒙与山西的通道。除此以外一条河流由南向北的流淌着,那是苍头河,它属于黄河的一条支流。这样一个月牙形的大山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封闭的山坳,但是两山之间出现的这条河流,有种曲径通幽的意境,河流蜿蜒流向远方。张相文在《塞北纪行》称:“杀虎口内外,实为数水交汇之地,故其地绾彀南北,自古倚为要塞。”《朔平府志》中记载:“当时长城以外,有蒙古众多番邦,部落数百个……而杀虎口位于整个云中之西,是整个右玉县北上之要道,简单概况为‘扼三关而控五原’。”[4](卷4)如此天然的关隘,地势易守难攻,完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真实写照,因此它能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借助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杀虎口拥有了这样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在后来的历朝历代中,借助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的同时,加上人类自身的智慧成果的完善补充,使得杀虎口军事防御日渐完善,体系也日趋完整。
(三)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化差异 杀虎口之所以可以发挥军事防御的作用,必然会有军事防御对象的存在。杀虎口一直是属于汉族管辖区域的最前沿,并且与不同的少数民族接壤。西周时征战猃狁,秦汉时期抗击匈奴,隋唐时期应对突厥的叛乱,宋朝遭到契丹的侵扰,明代应对鞑靼的猖獗,包括清代的噶尔丹南侵[3],这些都成为杀虎口冲突与交融的见证。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民族的交融,文化的碰撞与熏陶也让右玉这个地方独具特色。文化上的差异,带来了关系冲突的不断,对于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来说,中原稳定的农耕经济相对于那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而言,带给他们极大的诱惑。除此之外这种游牧的生活状态也让关外人养成狂野粗犷的性格,他们敢于冒险,为了抢夺金钱、土地、粮食,他们常常铤而走险。当时杀虎口作为大同镇右玉卫下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边关要塞,在应对突发情况,或者矛盾激化的时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抵御外患,固守边关,为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安定,统治者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加强军事防御措施来应对各种矛盾冲突。
二、明代杀虎口军事防御设施的构建与完善
(一)外围线性防御布防
1.周边军事要塞布防
整体往往是在部分的共同作用下起作用。杀虎口在当时整个边关防御中一直处于中心的位置,众多的军事要塞分布其周围。这样的军事部署让这些要塞能够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当时在杀虎口的周边构筑了两道防御战线,杀虎口的第一道军事防御战线,由左向右分别是云石堡、铁山堡、林家堡、残胡堡、马堡、破胡堡等堡垒,而以右卫、玉林卫为中心向左右延伸有黄土堡、威坪堡、牛心堡、云阳堡、红土堡等堡垒,这又形成了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的第二道防御战线。[5]根据《明史》记载,鞑靼贵族仅对雁北地区大规模的侵扰就30多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右玉保卫战。这次战争是“桃松寨事件”引发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之子辛爱的小妾桃松寨,因为行为不检点被辛爱发现,害怕被问罪,私自逃到了大同,时任大同总督杨顺,顺势收留了桃松寨,准备将她送入京廷邀功以求升官发财。当时辛爱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就向明朝要人,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鞑靼以此为借口,挑起了事端,大军从杀虎口北大举南下,包围了右玉城。右玉保卫战,就在兵力极少,又孤立无援,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坚持守城八个月之久,成为一大奇迹。右玉保卫战的胜利离不开当时右玉卫、左云卫的相互声援,以及周边要塞包括两条防御战线上堡寨的相互配合。善于突然袭击的鞑靼骑兵受到了重创,危机在明军到来之前就得到了解除。
2.明长城的加固及修筑
除了周边军事要塞的辅助之外,杀虎口利用自身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历朝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下不断完善自身军事体系。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不断通过加派兵力,修筑防御工事等,来应对边境侵扰隐患。洪武二年(1369)就开始修筑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的长城,在此后为了进一步抵御外患,当时在大将军徐达的指挥下,外长城顺利修筑起来。这段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明长城,在明清两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城的作用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右玉保卫战中得到验证,在形势危急的时刻,明政府兵部尚书杨博,组织大量的兵民利用农闲时节,对因战乱造成残破的外线长城进行了修整,加固城墙,在周围挖掘战壕、土沟,当时总共在沿线挖掘了一千多米,对后来的外来侵略者的进犯起到了抵制作用,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明正统年间,将玉林卫与大同右卫合并成立了右玉林卫。玉林卫的古城呈现长方形,东西墙长均为1400米,南北墙长均为1200米,全部用黄沙土夯筑,该城设有四个城门,当时除了西门,东、南、北门都设有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市防御的主要设施之一,往往是半圆形的或方形的结构,类似防守修筑的护门小城,当时的南门是双联瓮城,其墙高10米多。可见当时明长城中一部分已经成为了杀虎口的又一重保障。这样的一个外围城墙的防御为整个边关上了一重保险。
(二)内部屯堡防御布防及形成
1.军事设施的构建与运作
(1)军需屯田与屯兵指挥 蒙汉的关系看似稳定中往往蕴藏着巨大危机,危机的不确定性,只有以防患于未然的方式解决。为了应对战争,明政府不得不通过在杀虎口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兵力以维持安定。明政府逐渐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屯田、民运和开中盐粮为主的后勤保障体系。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极具刚性的性格,往往通过单一的以战养战的方式来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明在元代的基础上取其精华,选择在边关立屯堡,开垦荒地,军兵在战时出征,平时耕种务农,达到以军养军的目的。屯堡是军屯的最基层组织,当时的明政府为了能够有效的对屯田进行管理,将所有户所分为屯、堡二级组织,一个屯里有一百户,设置正副屯长各一人负责管理,七八个屯或者五六个屯可以设置一个堡,堡内主要有守备、操守等官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堡址会根据距离各屯的远近选择,往往堡离各个屯很近,保证了农业生产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除了军屯之外,当时明代在杀虎口又相继建立民屯、商屯等。明代名臣庞尚鹏在《清理盐法疏》中提出:“盖九边额供之数,以各省民运为主,屯粮次之,此十例也。而盐粮乃补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6](卷22)由此可见,当时的民运在明代九边的军事后勤保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且开中之法也解决了军需紧缺的情况,据万历末年成书的《三云筹俎考》之《军实考·主饷岁额》中记载,当时山西行都司开中两淮、长芦盐价银18 189.5两,屯田粮米20784石3斗2升,豆达到23358石6斗2升,折合白银共26376.94两;民运税粮折合的白银671691.25两。[7]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军需钱粮储备是十分充裕的,证明屯田确实在当时取得很大的成效。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充足的军需物资,有效的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鞑靼蠢蠢欲动,时常活跃在边境,从明太祖开始便逐渐在杀虎口集结重兵,准备随时待命应敌。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后,英宗被俘,明王朝受到了重创,在经历惨痛教训的同时,如何鼓舞士气,让浮动的人心安定下来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明政府从根源出发对边关逐渐加强了防御。当时位于杀虎口以北、和林格尔南的玉林卫,与当时的右玉卫合并,再加上威远卫,当时在杀虎口附近相当于集结了三个卫的兵力,每个卫大概有5600多兵马,当时整个杀虎口就总计有二万多的兵马,占到右境内兵力的大部。《朔平府志》云:“马营河堡、残虎堡……以上九堡,自明嘉靖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4](卷4)当时在杀虎堡中设有营守备、坐堡把总各一人负责防御驻守,旗军777人,而军用马骡有152匹;在平集堡配备团总一人,旗军270多人,而在这些官兵包括马匹的配备,直到清朝才被废除。可见,当时杀虎口内部军事部署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兵种齐全,有守备、把总、团总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屯兵系统在当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烽火及驿传交通系统 在抵御外患的同时,仅仅具备充足的军需保障和合理的屯兵系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城堡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驿站通道、墩台、烽堠等。墩台是每隔二里就修筑一墩,这种墩高宽各二丈,杀虎口的每个屯堡的周围都设置了数量不等的墩,这些墩不但可以及时为堡垒提供后勤补给,而且还可以输送兵力。墩台相当于今天的眺望塔,可以随时观测边境动态变化。此外明政府为了能够及时将敌情反馈给驻守将兵,在城堡上修筑了许多烽火台。如果是夜里的时候,一旦有敌情,会燃烧干柴发出耀眼的火光作为信号传递给后方兵将,叫做“烽”;如果在白天要放炮,并燃烟为信号,这就叫做“燧”,烽燧就在当时起到这样一个传递敌情的作用,此举不仅使得后方的将士及时收到敌人来犯的信号,并能从狼烟和放炮的多少知道较详细的敌情,如兵力等。除了烽火台,明代杀虎口在堡内也设置了专门的驿站、快马,让战报能够及时送回朝廷,保障了军情的时效性,避免延误战机。
2.明中期军事防御的加强
(1)嘉靖年间诸堡的修筑 土木之变直到嘉靖年间,西北地区经常受到鞑靼贵族的侵犯,骑兵到处烧杀抢掠,雁北人民叫苦不迭。嘉靖六年,10余万的骑兵从杀虎口攻入,两年后俺答又相继侵入大同、应州、朔州等地。嘉靖十三年,俺答第一次提出向明政府交纳贡赋,以此示好,通过此举希望将紧张的关系得以缓和。但是当时明政府的统治者并没有给予相应答复。在嘉靖十九年,这次蒙军做了充分的准备,携带了大量的马具、铁浮图、矢锤、铠甲等武器,在俺答的带领下蒙古骑兵一路势不可挡,沿途烧杀抢掠,当时最远到达晋阳、平遥、介休、潞安等地。之后为了缓和双方关系,俺答派遣石天爵去大都谈判,当时明政府将特使石天爵斩首示众,并传令当时北方的九边重镇,高价悬赏购斩俺答项上人头。此举激怒了当时鞑靼贵族,并成为鞑靼大举进攻的借口。根据《明实录》记载,当时鞑靼攻入大同,南侵山西,并连续击破数十个卫所,州县总计38,烧杀20多万人,掠夺马牛羊200余万。[8](P1355)在《明史·兵志》记载,元代蒙古人在退守北方以后,多次谋划想要复兴元朝,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平,当时北平三面都接近北方边塞。当时一开始边关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为了能够全方面的进行管理,在四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其余二镇是由太原总兵负责,主要治理偏头地区,三边制府驻扎在固原,总共是九镇,习惯被称作是九边。从永平、蓟州一直至密云以西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总计设置了关卡隘口多达1129,这里都戍守着军队,当时外寇进犯山西,必然经过杀虎口,这种现象在当时引起当局统治者的重视,认为只有在杀虎口这个地方加大军事防御强度,才会大大提高中原的安全系数。于是请求进一步加强军工建设,当时城墙修了上千米,烽堠363所。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结合杀虎口的重要战略地位,综合各方面因素陆续修筑了11堡。在《山西通志》也记载到:“杀虎口……为宣大以西、宁朔以北,归绥以南之首冲。”[9](P1675)所以在当时的宁朔以北的右玉林卫下陆续修筑堡垒。嘉靖年间右玉林卫下面陆续修建了13城堡,包括左卫、右卫二城,杀虎、破虎、残虎、铁山、牛心、马堡、黄土、云阳、红土、三屯、马营河11堡。这些城堡,在嘉靖年间被相继建立起来。11堡的修筑,再加上之前的长城与烽堠,城、堡、烽堠组合起来并联接成网络体系,杀虎口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
(2)嘉靖年间杀虎堡的修筑 根据《山西通志》记载,“当时开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马市罢。”[9](P1859)这是记载嘉靖年间蒙古人仍对山西以北地区经常性侵扰,可以看出蒙古部落出尔反尔,频繁的军事进攻,面对这一状况明政府继续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工事,此时杀虎口的军事建筑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世宗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在杀虎口的长城内侧建筑了杀虎堡。杀虎堡城周1公里,高三丈五尺,起初堡内还开放了马市,经济往来在断断续续中进行。
(3)万历年间砖包的加固与平集堡增设 万历二年(1574),当时城墙由于黄土修筑,雨水冲刷及连年战火损坏严重,万历皇帝下令对当时的长城进行砖包。修筑的城墙周长约1公里,高大概约有11.7米。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杀虎口堡外修建了一座新堡,叫做平集堡,平集堡的周长约有1公里,高下与旧堡一样,它的规模、大小与旧堡相同,其中堡内设有客栈、商店等,方便内外交易。在杀虎堡和平集堡之间修筑了城墙,东西走向,前后左右各有一门,叫做栅子门,栅子门与长城的城头堡相连,常常设官兵驻守。东西南北相互贯通,周围有五百四十丈,共计约1.5公里,他们之间形成唇齿相依,犄角互援之势。
三、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的作用
(一)保证了北方边关的安全与稳定 对于逐渐完善的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不仅对北方边关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是有效的稳定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一方面兼顾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在军事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百姓的安全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这样的体系更是促使了民族间进一步的和解与交往。少数民族游牧式的生活方式,物资上的贫乏与产品种类的单一,这种状态下的生活,在无法改变它对自身经济产品的转换的同时,某些维持生存必备的产品必须通过农业地区中取得。由此可以看出,从古到今,农耕地区对草原游牧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由式的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草原游牧地区下的人民,往往通过对外交换产品,以此不断壮大部族,繁衍发展。产品的交换中往往是有序中夹杂着无序,有序可能是有秩序有规模的贸易往来,而无序往往伴随着冲突与矛盾,甚至军事对抗与野蛮掠夺。在北方边疆大规模修筑军事工事,修建长城,一方面可以简单的看成是军事防御工程,另一方面这种军事防御工程可以看做是稳定秩序的一种方式,将野蛮的抢劫掠夺变成安定有序的边关贸易。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里的城堡及其他军事建筑、军需、军事指挥系统等,不仅可以看作是军事矛盾激化后,采取的防御措施和方法,在稳定边关经济贸易有序发展的同时,让这种体系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保护规则,在这种管理下进行有效的贸易往来。
(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意义方面上看,正因为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支撑,和谐安定的统一局面得以持续。加上大量的兵力驻守在这里,经济迅速得到发展,文化相互交融,商业水平迅速提高。边境的不安定因素的存在,让明政府在当时不得不投入重兵驻守边关,大量的兵力需要有充裕的军需物资作为保障。数万屯军如何生存,如何在战斗中没有后顾之忧,政府采取了屯垦的方式来应对这一迫切的问题,大量的军屯和民屯在后方建立起来了,有效的保障了粮草的充足。常年的战乱使得边境流民迅速增多,民屯的建立,在让大量边境流民有了避身之所的同时,对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起到了有效的维持作用。民屯的耕种,不仅解决了维持兵将日常生活的问题,更是挖掘出了边关的潜在商机,在极大刺激了边关经济发展的同时,屯民和流民也成为了驻守杀虎口的重要后备力量和兵力来源。
(三)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 杀虎口地处蒙汉边界,双方长期经济往来密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缓和与冲突相互碰撞下走向融合。由于明代蒙汉互市经常出入于杀虎口边关的集市商人,渐渐学会了蒙古语,熟悉了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与礼仪交往,在这种贸易交往中,除了带来贸易方面上的便利,更从侧面反映出民族间文化相互熏陶与融合的过程。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舒适宽松的氛围,而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以及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等都成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思想渊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冲破了民族,推动进一步融合。无论什么时期,经济上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即使是闭关禁边,都是暂时的,在军事防御保障的情况下,为双边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的同时,在贸易往来的互惠、互利的有效机制下,北方边疆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对民族的融合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结语
杀虎口之所以能够在明之前一直保持着军事险塞的地位,不仅是它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环境,更是因为明代统治者能够依据时势,合理布防。军事防御体系的加强,给当时北部边疆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促进边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汉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杀虎口既可以看成是蒙汉双方交战冲突的场所,也可以看成是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场所。杀虎口军事防御体系的完善既有利于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维护了当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更在对抗中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平已经成为各族人民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他们渴望和平,厌恶战争,所以杀虎口在明末之后,特别是清朝以后,逐渐由军事要塞转换为商业重镇也是大势所趋。中华民族的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杀虎口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成为了文化特色中重要组成部分。
[1]张国硕.夏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J].中原文物,2008(04):40-49.
[2]右玉县志办公室.旧志辑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3]张建国,牛建山.百年杀虎口考证[N].山西政协报,2006-01-20.
[4](清)朔平府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5]刘建生,雷承峰.明清西口地区军事建筑群落布局及特点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13(02):98-104.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张金奎.明代山西行都司卫所、军额、军饷考实[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03):41-59.
[8]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国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清)李 侃,胡 谧.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