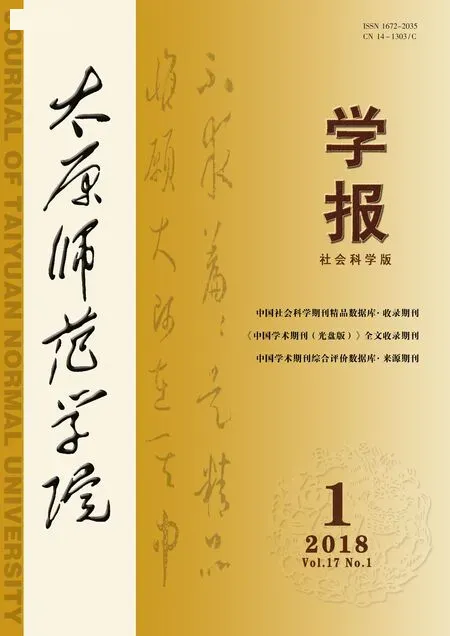从陈年的小说看底层写作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在葛兰西的《狱中杂记》中,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相当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无产阶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解释说,底层的主体构成是工人和农民。底层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身份,而是对各种身份的相似性作出的一种总体把握。
底层文学就是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人民而创作的文学或底层人民自身的文学。它分为两类:知识分子的创作和底层人民的自我表述。知识分子创作的底层文学往往带有俯视、隔膜、臆想或虚妄的同情色彩,属于代言式或启蒙式的创作;底层人民的自我表述又常常陷入低级和粗俗,缺乏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陈年是一位生长在矿区的作者,她的作品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她曾经作为一名小生产劳动者,拥有对底层生活的体验;另一方面她爱好文学,因而在作品中将自身经历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虽摆脱不了一些低俗之处,但已比底层人民的自我表述更具可读性。
一、切身的体验写出细致的生活
陈年的作品大都反映矿区人的生活。她的四部作品《小烟妆》《胭脂杏》《九层塔》和《梅花沟》分别描写了矿区工人艰难的生活、矿工出事后他们妻子的苦难经历、矿区下岗工人的谋生遭遇和矿区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然而在她的眼里,矿区是个好地方,“生活简单,幸福也简单”,“人们是善良的宽容的”。[1]她说“在矿上最幸福的一幕是男人下班回家,手里拎着一块红润而肥腻的猪头肉,女人接过肉在案板上切开,再用刀背把黄瓜大蒜拍扁,黄瓜切成不成形状的块,蒜切成末,放在小盆里,倒上多多的醋,边吃边喝上点酒。女人欢喜地坐在男人的对面看他喝酒吃肉,欢喜地听男人吹牛皮,欢喜地和男人温存”[1]。她熟悉这样的场景,也喜欢这样的场景,所以在《胭脂杏》中她便刻画了这样一幅场景:陈小手用卖废铁刚赚的钱割了一块香喷喷的猪头肉,到胭脂的理发店里一起下酒。这样的生活简单而美好,勾勒出矿区人平凡的幸福。
在矿上,男人如果出了事,“那对女人就是天塌地陷的灾难,她们不光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接受现实的无情”[1],所以“谁都不会去深究这些苦命女人的生活方式”[1],这就是矿区人的善良和宽容。在她的作品里,这些女人有的盼着再嫁,好找个男人,有个依靠;有的为了给孩子赚钱上学而出卖肉体;有的开个小店或是在小店里打工,也不免被那些男人“揩揩油水”。
陈年也是个下岗工人,下岗后她开过小店,当过小老板,所以她熟悉小店里的生活,在她的作品里,有胭脂的理发店,有陈平唱戏的茶座,她把小店每日的熙熙攘攘写得生动真切,以女性独有的视角细腻地剖析人物的内心,因此将人物的心理展现得细致入微。一些俗语的运用如“女人活个俏色,男人活个调对”[2]等使作品具有生活化、乡土化气息。
陈年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矿区工人的谋生手段多了,竞争却激烈了。《小烟妆》里的贫富差距就是新时代所造成的结果:住在高档小区里的人出门花钱不花力,城区改造,道路施工,汽车没法走,才催生了刘军他们的摩的行业。《胭脂杏》里的胭脂也巴望着到城里学点新手艺,开个大发廊好赚钱。《九层塔》里陈平通过微博晒出和老徐的幸福生活,又因为微博上吴小花的出现而悄然离开。这些都具有新时代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陈年的作品还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贫富分化、矿区工人的艰苦生活、矿工出事后的赔偿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底层民众对城市的陌生感,对物欲的追求,已经造成了人性的变异,他们憧憬着未来,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但现实的残酷总让他们从苦难中得到救赎的希望破灭。原有的道德秩序和生存观念被颠覆,他们只渴望安稳的生活和一个精神家园,却往往难以如愿。就像《小烟妆》里的小烟,原本平静、满怀希望的生活却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
二、缺乏深刻的思想性
从陈年作品对矿区的描写来看,似乎是非常真实的。作者切身生活在矿区的环境中,所描写的应该是外人看不到的细节,但这样的细节却总让人想起两个词:肮脏和龌龊。《胭脂杏》里的男人们一听到胭脂杏的招牌,就“嘴里酸溜溜地往外冒水”[3];《小烟妆》里车站外那些拉客的女人和“住店”的男人;《九层塔》里戏女陪客人喝茶时的乱摸乱动和半推半就,还有那些不结婚只搭伙过日子的男男女女……好像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所有的女人都是风尘女子,而矿区就是一个红灯区,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都有那么一点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好像所有的男人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找女人做爱,而女人的身体被作者描写得没有丝毫美感。这样的描写是否就是矿区真实的生活?笔者愿意相信陈年的初衷是想要表现矿区人的质朴和善良:《胭脂杏》里最后胭脂没有离开,怀了陈小手的孩子;《九层塔》里最后陈平默默退出,成全了另一个可怜女人的幸福等等。
从倾向性和价值立场来看,这些作品并没有折射出较深刻的主题思想,也没有揭示出某些本质的东西或让人思索的东西,更没有对生活的趋势或未来矿区的发展有所触及,这些作品充其量就是真实地反映了矿区人的生活——如果这就是矿区人的真实生活的话。
再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并没有展现出一种崇高的审美理想,也不具有陶冶性情、愉悦身心的作用。作者没有表现出普通劳动人民的朴实和美好,反而把他们塑造得有些不堪:“一个大老爷们儿,又不是黄花大姑娘要守个清白身子。守什么守?”[2]“别看不起那些女人,我觉得比那些贪污犯强多了,最起码人家靠身子挣血汗钱,干干净净。”[2]“摸手,摸胸,沿着腰身往下走,陈平没觉得难为情。脸不红,心不跳。女人长着这些东西就是供男人用的,不用,白白放着,倒是可惜了。”[4]
三、底层写作的应有走向
底层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写实性。其价值就在于揭露现实问题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底层写作有其自身的缺陷,常常异化为苦难写作、残酷写作、仇恨写作,再加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有夸张虚拟的成分,很容易将一些矛盾或感情放大。尤其是对于底层女性的描写,虽然迫于生计出卖肉体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陈年的作品中更像是一个群体的自甘堕落。陈年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再加上作为女性的敏感,必然有其童年的阴影和伤痛情结。但是进行文学创作,其真实性既不能令人确信,审美内涵又无法表现出来,小说的价值便大打折扣。
底层文学不应变成“伤痕文学”,应当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而不是千篇一律;应当在表现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反映普通民众的精神诉求。那些忘记崇高,甘于平庸的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百姓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着。作者不应在描写苦难、残酷、仇恨的大潮流中淹没了民众的真实意志,而成为“单向度写作”。
[1] 陈年.《小烟妆》作者自白[J].阳光,2012(8).
[2] 陈年.小烟妆[J].阳光,2012(8).
[3] 陈年.胭脂杏[J].阳光,2009(6).
[4] 陈年.九层塔[J].山花,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