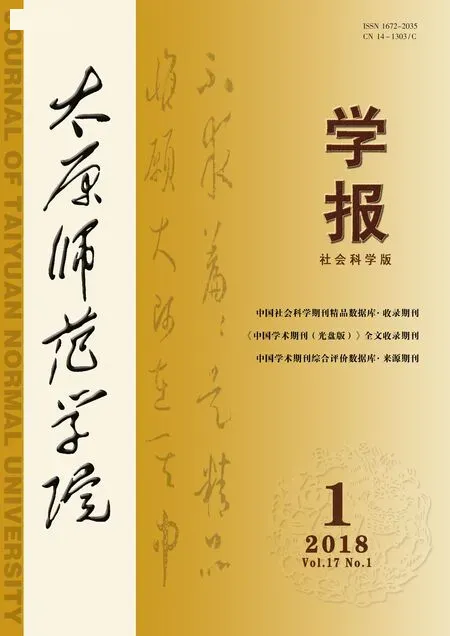道家文化与《棋王》中的王一生形象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一、王一生形象的道家文化色彩
阿城的《棋王》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在其发表之后,苏丁、仲呈祥即撰文指出其与中国传统的道家美学存在一种渊源关系,“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王一生的棋是道家的棋”,王一生身上有着“岸然道风”。[1]20
首先,在王一生的命名上就显现出道家文化色彩。《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233,由“一”而“生”近“道”者也。
其次,在王一生的出场描写上也显现出道家文化色彩。道家思想讲“静”,讲清静无为,但作者却把王一生的出场安排在火车站这样一个纷乱不堪的场所——“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3]15。这不仅是小环境的纷乱,车站里“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这些特定的意象把车站这一小环境与大时代联系起来,车站是这一时代的缩影与隐喻,“乱得不能再乱”可以说是对这一时代的描述,而不仅仅是车站。这也不仅是社会层次的纷乱,“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在一个个人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的时代,时代的纷乱是深入到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与内心世界的。具体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对于身在其中者内心世界所产生的震动,虽《棋王》中言之不详,但是只要读一读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是写车站送别的一首经典诗作《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会有所体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一生一出场就超离于这一由大到小、从外及内的纷乱的时空之外。王一生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是这个样子:“孤坐着,手笼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3]15-16,他似乎进入了庄子所谓的“坐忘”状态,或者如陶渊明所言“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在一个动荡纷乱的语境中出现了王一生这样一个特别的“静”的存在。紧接着写王一生在车上心无旁骛地找人下棋,不但“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力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1]20,而且对到车站为他送行的妹妹都不管不顾,无动于衷。《庄子·至乐篇》中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鼓盆而歌”[4]284,王一生此态与之相似。
其三,王一生的棋道。王一生的棋道源于捡破烂的老头,捡破烂的老头可以说是王一生的精神导师。有人指出王一生与捡破烂的老头的故事,“《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就与之相似”[5]46,而这一故事中的黄石公其实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道家隐逸之士。这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捡破烂老头更像是庄子一流的人物,庄子一生贫困潦倒,却不愿用自己的才干换取功名利禄,据说曾拒绝了楚国请其去做国相的邀请,“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6]444,从庄子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来源来看,“游戏于污渎之中”其实不是种虚拟语气,而是庄子的真实生存状态。捡破烂老头亦是隐身于社会下层谨守“为棋不为生”,不愿以棋艺换取功名利禄者,与庄子其实更为接近。王一生受教于捡破烂老头之后棋风大变。“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的棋道是“道家的棋”,棋道即人道,棋盘如人生,王一生的处世之道及其性格显然是受这样的棋道影响的,或者说受这样的棋道指引的。
其四,王一生拒绝了脚卵用自己家里珍藏的字画与一副明朝的乌木棋为他换来的参赛机会,而是在赛后进行了一场一对九的民间棋赛,这也可以看作是王一生“淡泊名利”的道家风范。在王一生身上,道家文化的影响更多的偏于思想文化观念。当然也有海外学者指出王一生求艺中存在着功利主义心态。比如对于名手和捡破烂老头,当他破解了名手的残局后断然拒绝了“名手”收他为徒的要求,“这就把技术绝对化了,以技术来衡量人性的尊严”[7]55;而对于捡破烂的老头,王一生被他打败后,为了学艺就百般讨好老头,“表现出更深一层的功利主义。为了棋艺上的受益,他可为别人干事,不管这种事,他作为一个学生是否该做或不该做,对他来说,只要能帮助他学到棋艺的事就该做”[7]55。但是,王一生仍然把胜负作为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其道家的棋其实仍然是种取胜的手段,而非棋道本体,他“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钱”,“亦非老子‘无为’的精神”[7]55。因之与港台武侠小说的套路很相似,换句话说,阿城的《棋王》中的道家文化呈现仍难脱“术”的层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功利化色彩,笔者觉得与这两方面的原因有关:其一是受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传统叙事文学中对于道家文化的书写基本止于“术”的层面。其二,在多年来把道家文化当作封建意识大加荡涤之后,国内学人对于道家文化的熟谙与理解程度恐怕远不如海外,即使有通过文学对道家思想文化作思考的追求,但受限于道家文化方面的修养,要做到怕也非易事。
二、道家文化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意义
尽管《棋王》中的道家文化已经超越了“道术”的层次而在哲学思想方面多有呈现,但是《棋王》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对道家哲学思想的思考与探讨,而在于把小说产生与叙述的历史时空相联系,从中去探寻道教文化的价值。
道家的政治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垂拱而治”,老子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果运动过繁,反倒会把国家搞乱。王一生所生存的历史时空中运动不断,不仅为政者“动作”过繁,生存于其间的普通民众也陷入一种狂乱的状态。这种治理模式显然与道家的治国理念相去甚远。生活在这样的时空中,王一生“‘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力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他心如止水,万物自鉴,空心寥廓,复返宁谧。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迷狂时代里,这种不迎不持、无动于衷的呆痴,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消极,这种在‘大而无当’中遨游的超脱,不正是对动乱现实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明智选择吗?不正是不愿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吗?”[1]20王一生沉湎于棋中,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迷狂时代并没有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的反抗行为,似乎是“无为”,但却以疏离主流的方式实现了对这一时代的超越,与这一迷狂时代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这似乎又是一种“无不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包括官方在内都把这段历史称为“十年浩劫”,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对整个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的伤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识,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到个人的精神肉体的伤害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记忆,但是最深最大的伤害恐怕还在于生存于其间的生命个体独立的思想能力的被逐渐销蚀甚至于被泯灭。在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
我说:“假如有一天不让你下棋,也不许你想走棋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他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你净说些不可能的事儿。”[3]23
“不让下棋”“不让想走棋的事儿”,不正是从行为到思想的规约,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空中,对于棋外的世界这不是“假如”,而是现实。“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通过下棋,王一生的独立思想的能力得以保持下来。独立思想的能力的保存必须以全身为前提,而道家哲学正是一种对乱世全身有深入研究的哲学思想,而王一生秉持的道家思想在这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却更具异质性。
联系《棋王》所产生的时代与其所叙述的时代,道家文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积极意义有这样几重:
其一,从历史来看,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或曰统治术的黄老之学往往是在大乱之后休养生息的时代获得施展机会,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被频繁的政治运动搞得伤筋痛骨的国家与民族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主张“无为而治”为政以简的道家政治思想,在国家治理的层面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其二,在个人的层次上展现出一种柔性抗争的可能。王一生对于当时的政治思想有着深度的不认同,但是与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文化大革命英雄的正面反抗不同,他是用一种道家的全身智慧使自己从现实中超离出来,既保全了自我性命,又保持了自己精神世界的独立性,此中亦可见出这样一种东方式智慧的价值需要重新被审视,至少需要正视其中的“抗争”意义,不能简单以“退让”“逃避”目之。
其三,王一生尽管被称作“呆子”,不谙世事,但是王一生在这样一个自由思想空间不断被压缩的时代却保存了自己独立思想的能力,这显然得益于其身上的道家文化影响。而独立的思想能力是五四以后所形成的启蒙主义的核心内涵,所谓的启蒙最关键的问题即是塑造被启蒙者独立思想的能力,以往一般认为启蒙的思想文化资源来源于西方,从王一生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亦有启蒙可资利用的资源,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被看作五四启蒙传统中断后重新被接续的时代。
三、道家文化与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是理论与创作都很完备的文学思潮。从理论角度看,在中国文学自五四起更多的引西方现代文化及同样源自西方文化的俄苏文化为资源之后,寻根文学把视野重新拉回到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了重新的审视,更偏向于挖掘其中积极的因素对其作现代性的转换,其理论主张背后隐含着一种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企图。但是从创作上来看,却出现了两种流向:其一,以文化批判为主要内容与价值取向,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有着更多承继关系。其二,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更多的认同,着力于发掘追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因子与正面的价值。从创作上看,前一种流向是寻根文学的主流,但是后一种流向与寻根派的理论主张更为契合。阿城的《棋王》是后一种流向的代表作品,其中对道家文化的积极正面价值有多方面的思考,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寻根文学倡导者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小说结尾时有这样一段描述,王一生在取得一对九的棋战胜利之后:“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地一声儿吐出一些粘液,眼泪就流了下来,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妈——’”*在最早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棋王》中是这样描述的,上个世纪末的一些书籍中收入的《棋王》也是如此,但后来的一些书籍中收入的《棋王》却不知何故把王一生的话改为“妈,儿今天……妈——”。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人还要有点儿东西”,这点儿“东西”从表层来看,是王一生的棋艺,但是深层上却是棋艺背后的道家文化,或者也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妈”在小说中意指王一生的亡母,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多年来把祖国称为母亲的国度,“妈”可能已超越了这种直接的意指,可以理解为国家民族。“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的岂止是王一生,国家与民族不是更应该如此吗?这似乎不是王一生或作者对个人生存的感悟的言说,而更像是代国家民族面对世界的发言。
[1] 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1985(3).
[2] 老子(著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译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阿城.棋王[J].上海文学,1984(7).
[4] 庄子(著),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邓国均.道家文化与《棋王》中的“隐士”形象——兼论“棋道”的思想文化内涵[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6] 司马迁.史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7] 黄风祝.试论《棋王》[J].文艺理论研究,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