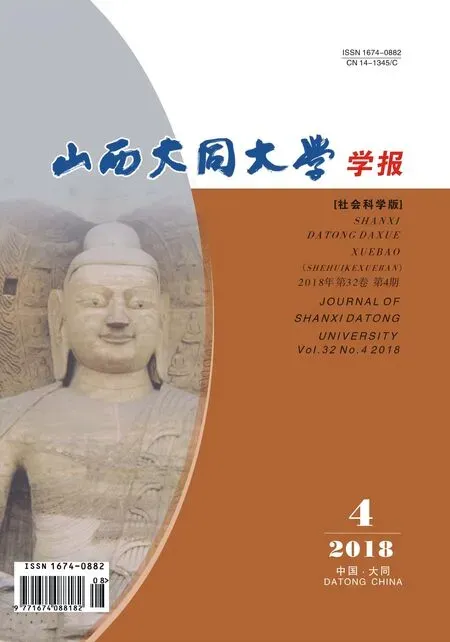特朗普新政与中美关系新走向的研究述评
孟 斌,孟范昆
(1.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7;2.江西泰豪动漫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7)
特朗普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后,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提升就业机会、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并将美国安全利益置于首位。这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在中美经贸、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等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学者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展开讨论。笔者拟就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对美政策三个领域的最新研究作扼要述评。
一
当前关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客观上存在着差异、竞争甚至博弈,但最终中美关系将沿着合作的方向发展。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以婚姻作比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中美关系,他指出:“中美之间可能不是最好的婚姻,但离婚不是选项。”[1]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中美虽然差异巨大,但如果要成功维系全球公域管理、国际安全、稳定繁荣,就必须相互合作。”[2]台湾朱云汉也认为:“中美之间尽管存在战略竞争,但也有合作空间,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3]复旦大学倪世雄指出,“中美关系前景‘复杂多变,但希望犹存’。复杂多变是指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朝鲜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冲突性加强;希望犹存是指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势所趋。只要中美两国努力,中美两国有望在一个新起点上取得进展。”[4]复旦大学吴兴伯表示,“特朗普上台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阶段性的变化,但双方利益持续交融,合作面也不断拓宽。所以,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将沿着稳健方向发展”。[5]外交部曹辛提出“新G2”的概念:“中美双方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6]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尹承德对未来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他表示,“中美关系不可能顺风顺水,像美国对华贸易调查以及南海巡航计划都有可能对中美关系形成冲击,但是促进中美关系的主客观因素不会消减,在特朗普任内中美以合作为主态势不会改变。中美关系总体向前向上发展的势头将继续并可能进一步抬升”。[7]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和专家还很多,比如华侨大学林宏宇、美利坚大学赵全胜、纽黑文大学霍华德·斯托弗(Howard Stoffer)和卡托研究所道格·班多(Doug Bandow)等。
另一批学者则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冲突将多于合作,这一类学者专家人数相对较少。其中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在战略竞争方面,他认为,“中美将不可避免成为‘零和竞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对亚洲盟国有保障安全的义务,一旦中国与其盟国发生争端,中美冲突的风险随即加剧。”[7]在中美经济合作层面,他认为,“两国有合作的空间,但也存在两个方面挑战。一是美国欲领导世界经济体系,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欲摆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发展一套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而面对中国的客观挑战,美国会对这些新兴组织进行各种抵制。二是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倾向,有可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3]美国西北大学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ster)则从经济、安全以及朝核问题分析了中美关系,他指出:“中美经济逐步在疏远,在安全问题上可能出现潜在的对抗,甚至中美在最有可能合作的朝核问题上都难以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8]
国内学者钱文荣则从中美力量对比来分析中美关系。他表示,“未来中美关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美差距在缩小,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忧虑也在加剧。尽管中美两国的经贸依存度较深,但美国为了控制这种战略威胁,势必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这种趋势在特朗普上台后将继续增强,不可能减弱。”[9]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如果中美都不愿意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双方有可能跌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导致全球秩序的动荡,最后引起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其依据是,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目的,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可能推行孤立主义政策,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同时,中国也不愿意为稳定国际经济秩序提供更多帮助。这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连锁反应,从世界经济的失序到政治体系的崩溃,甚至是中美两大国爆发激烈冲突。”[10]
二
鉴于中美关系可能的种种新走向,很多学者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的应对提出了建议、预判和分析。北京大学王栋和孙冰岩从经贸和安全两个方面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贸易方面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在安全议题上更倾向单边主义和军备发展,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力度,中美关系在如台湾、南海等核心热点问题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11]中国现代关系国际研究院达巍、复旦大学吴心伯等人都对中国应采取的具体政策提出了建议。他们一致认为,“在未来短期,中美关系有可能紧张和震荡,中方应在心理和政策上都做好准备。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应采取主动行动或回击,同时要扩大和坚持双边合作与协商,尤其是经济合作领域”。[12]达巍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保持清醒,不能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相反,鉴于美国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的后撤,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引领全球化与全球潮流。”[12]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对中国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一是加强沟通,更好地了解彼此之间的战略意图;二是一旦出现分歧,应通过耐心的谈判和对话解决冲突和矛盾;三是应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的倡议,消除美方的疑虑;四是加强人文交流,这是其它领域取得合作和进展的基础。”[13]
同时,针对中国的崛起,美方专家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联合12位专家,共同撰写报告《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有可能,谋求与中国的稳定互利关系,同时保持在亚太地区的积极存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14]这份报告确定了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处理的六件优先事项:“与中国一道阻止朝鲜的核导计划;重申美国对亚洲的承诺;用有效手段解决美中贸易投资关系中的互惠不足;力求用基于原则与规则的方法处理解决亚太海上争端;对损害美国组织、公司、个人及更广泛关系的中国社会政策进行回应;保持并扩大美中全球气候变化合作。”[14]
也有专家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特朗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尹继武和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寿慧生等。尹继武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分析并预测了特朗普的政策偏好。[15]寿慧生则通过分析特朗普个性特点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具体建议,他认为要尽力寻找渠道和合适的代理人来与特朗普进行个人层面的沟通,以获得好感,进而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发展。[16]
三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在各领域既有合作,也存在冲突。和奥巴马政府相比较,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总体来说呈现出三种趋势:中美经贸领域谈判博弈比较多,合作比较少,但中国会在该领域做适度妥协;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上合作互动频繁,直接摩擦比较少;在国际秩序领域上中国主动性、贡献比较多,美国承担和付出比较少。
造成这三种趋势的原因分别是:第一、中美经贸领域,中国是美方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470亿美元,特朗普则高举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不断抨击中国通过倾销和补贴手段对美出口,甚至污蔑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必然导致美国采取措施解决贸易逆差等经贸问题,如果双方能保持理性的话,理应通过谈判方式来沟通,达到共赢的目的,一旦谈判破裂,不排除双方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当前中美双方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贸易战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的一场双输局面。中美经贸双方的合作更多呈现出的是中美双方企业的相互投资,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存量,而中国对美投资则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增量。中国加大对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刺激了自身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产生了效益创造了机会。但考虑到特朗普要实现美国优先和减少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会通过谈判和博弈逼迫中方在经贸问题上让步来实现其目的,和合作相比,谈判和博弈才是中美经贸领域的主流,但是中国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为达到双赢的局面,在不损害中国重大利益的前提下,会适度做出让步,以避免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在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将会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内事务上,这样特朗普政府就有可能在地缘政治层面实施收缩政策,但是为了在亚太地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会更依赖于盟友的力量来制衡中国,而不是依赖于自己的力量直接和中国对抗制衡,所以摩擦会较少。另一方面中国也无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挑战美国现有地位。所以中美双方摩擦将会相对减少。在安全领域,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力量施压朝鲜,迫使朝方放弃核武,中方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时中美双发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都有遏制恐怖主义蔓延的利益需求。因此中美之间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而且随着恐怖势力的日益猖獗,朝核问题日趋严峻,双方都不愿目睹恐怖势力在全球扩散,朝鲜半岛局面失控甚至爆发战争,这样中美间互动合作就会成为必然。
第三、在国际秩序领域,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回归孤立主义的倾向,认为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不一定有利于美国利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进程中并未推动美国获得巨大实际利益。美国虽然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但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也不愿过多的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反观中国,中国现在不仅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而且有意愿有能力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一方面,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接受服从国际规则,并且是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受益者,因此中国无意挑战也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但中国有改善国际秩序的愿望和期待,使国际秩序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这从侧面反映中国不是一名现有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中国会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发展和稳定做贡献。
四
对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研究,学者既能够从国际大背景的视角分析中美关系,也能从贸易、南海等热点领域探究对外政策。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从文化视角思考和分析中美之间的外交政策。当前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仍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关注不足。事实上,中美两国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体,文化情境、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引起双方的偏见甚至敌对情绪,影响到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和思维。接下来可以从文化情境着手,具体分析决策者的内心世界,预判和推测中美双方的外交政策。第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国内外学者通常从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三个层面分析中美关系,对非国家行为体关注较少。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为政府提供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支持和建议,而且在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重要载体发挥重大作用。如学者以个人身份,担任政府政策咨询顾问,非政府组织通过举行研讨会 、发布研究报告的方式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因此,研究中美关系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还应具备超国家的全球意识,不能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第三、缺乏历史研究与热点研究的有机结合。当前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点问题上,如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学者们针对热点问题纷纷提出对策和建议,但对隐藏在热点问题背后的深厚的社会和制度基础,缺乏历史层面的纵向考量。在探询历史真相,总结热点问题背后的潜在规律上存在不足。如通过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及演变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等,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无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第四、跨学科研究成果不突出。目前学者们能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特朗普及其对外政策,但鲜有研究成果利用语言学研究政策决策者的语篇和话语,国内外学者可利用相关学科理论框架,如系统功能语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等,开展话语和语篇的分析,揭示政策决策者隐含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尽管特朗普新政与中美关系的研究仍有许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但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一批丰富的科研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必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中美关系走向更清晰,相关创新性成果也会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