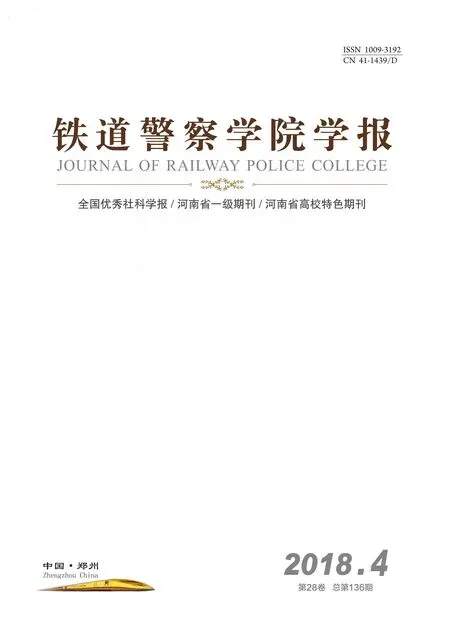我国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审判规律分析
陈 岩,姜丰文
(1.公安海警学院 基础部,浙江 宁波 315801;2.系山边防派出所,山东 烟台 264000)
引言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中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又是正当防卫的核心问题,它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1]。纵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规定,可以发现前者在法律制定方面较为笼统,后者则更为具体、细致,不同类别的案件有着不同的认定标准[2]。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类似大陆法系,相关法律制定抽象,理论发展不完备。这就导致我国的司法审判较为混乱,在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问题上,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对同类案件的态度和标准各不相同,出现大量有争议的判决。研究我国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司法运行状况,分析实践的审判规律,从中正确理解和准确界定必要限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司法审判规律的角度分析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相关问题,从实践出发研究理论,再回归实践,不仅对厘清理论上与实际上存在的模糊概念有很大帮助,还对保障公民的防卫权,完善我国正当防卫立法,推进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审判规律
(一)正当防卫相关判决样本统计
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权威网站及书目中选取了全国各级法院公示的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有关的案件判决117份,这些判决涉及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湖南、河南、安徽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代表,甘肃、海南和青海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代表,选取样本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基于所选取的案件样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关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审判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绝大多数案件都被认定为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在统计的样本中,构成正当防卫的仅有5件,占总样本的4%,其余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防卫行为涉嫌犯罪时最终认定的无罪率极低。其中故意伤害罪61件、故意杀人罪30件、聚众斗殴罪17件、寻衅滋事罪4件,分别占到统计样本总数的52%、26%、15%、3%。
第二,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的最主要原因为防卫结果过当。在这112份有罪判决书中,除了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不构成防卫过当之外,剩下的91份被法院判定为防卫过当的原因如下:一是防卫结果过当(43份);二是防卫手段与防卫结果皆过当(27份);三是防卫手段过当(11份);四是超过有效制止(6份);五是受侵害的法益轻微(4份)。
第三,同样类型的案件在各地、各审级法院之间有着不同的审判思路和标准。例如赵某某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就是同一个案子一审与二审对必要限度审判标准不同的有力证明。1999年12月23日被告人赵某某在舞厅与被害人周某、王某某发生言语不和。事后,王、周等人数次到赵某某家对其进行挑衅恐吓,赵均躲在家中不出。1月4日晚,王、周暴力踹门闯入赵某某家中,赵为阻止二人进门,持凶器进行击打阻拦,致王某某轻伤、周某轻微伤。一审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赵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赵某某是正当防卫,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类似的案例还有湖南省岳阳市的杨某故意伤害罪①2011年11月6日,被害人方某与被告杨某发生纠纷,继而发生打斗,杨某躲回自己家中,并将房门锁上。方某持一根杉木筒子继续追赶,并同其妻吴某甲一道强行进入杨某屋中。在杨某家厨房中,吴某甲揪住杨某头发,方某用杉木筒子对杨某实施了殴打,杨某被打后持菜刀将方某头部砍成轻伤,将吴某甲头部砍成轻微伤。一案,一审判杨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二审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杨某的行为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一审到二审由有罪到无罪的改判尚且如此,一审与二审量刑改变的更是数不胜数。
(二)判决结果原因总结
总体来看,各地、各级法院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审判持十分谨慎保守的态度。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正当防卫必要限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现了1053份判决,其中判决结果为正当防卫的案件仅有5件,占总数的0.5%,剩下的判决中,有大量的案件审判受到学者和民众的质疑,由此可见我国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认定是十分苛刻的。
在遵循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法院审判结果所呈现出的差异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法院以防卫人的防卫行为给侵害人造成严重后果为由,认定防卫人造成的结果明显超过限度,不构成正当防卫;二是法院以案件中防卫人的防卫强度、手段和造成的后果超过侵害人的侵害强度、手段和造成的后果,二者不相当为由,认定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限度,不成立正当防卫。第一个原因在判决样本中占主要部分,尤其是在不法侵害者的伤情超过防卫者的案件中,将轻伤的防卫人判定为故意伤害罪,侵害人无罪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原因,除了对必要限度的认定没有明确的标准之外,法院也普遍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明显”,以及“造成重大损害”的“重大损害”没有具体的审判标准。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中的考察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其公布的案例具有权威的指导意义。笔者研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公布的案例后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考察标准也不尽相同。在朱某红正当防卫案②被害人李某(男)欲与朱某梅(女)谈恋爱,多次纠缠和拦截朱某梅,遭拒后竟威胁恐吓并伺机报复。1993年9月9日晚,李某携刀强行进入朱某家,与朱母口角撕打起来,恰朱某梅进屋。李某将朱某梅踹倒后,拿刀扬言“不跟我谈恋爱就挑断你的脚筋”,就持刀向其刺去。朱母见状便用电筒击打李某头部,李某返身又与朱母撕打,朱某梅方得逃脱,此时朱某红进屋见李某正用力刺其母,便上去制止,被李某持刀扎破右手,在夺刀、撕打中,朱某红刺中李某胸部和腹部多处,造成李某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朱某红行为的性质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属于正当防卫,判决朱某红无罪。裁判理由:防卫的程度适当。中,判决书出现“防卫的程度适当”一词,显然采纳了“基本相适应说”作为判案依据;在叶某某故意杀人案③1997年1月上旬,王某等人在叶某某开设的饭店吃饭后未付款,遭叶某某催讨。王某认为有损其声誉,遂纠集郑某等人又到叶某某店中滋事,威胁要叶请客了事,后见叶不从,遂取刀往叶某某左臂与头部各砍一刀,叶某某拔刀反击刺中王某左胸,又将王某抱住互相扭打砍刺。郑某在旁见状即拿凳砸叶某某,叶某某转身还击刺伤郑某胸部后,继续与王撕打并夺下王某手中凶器,王、郑二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叶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判决叶某某无罪。裁判理由:犯罪分子持刀且已砍在防卫人身上,如不对其进行有力的反击,不能制止其犯罪行为,防卫人放任、甚至不排除希望将对方刺死、刺伤,不应成为认定正当防卫障碍。中,根据判决理由可以判断出法院采用的是“客观需要说”;在李某等故意伤害案①2000年8月13日晚,徐某、王某等人不仅自己不买票欲强行入场观看演出,还强拉他人入场观赏表演,被在门口检票的李甲阻拦。徐某、王某遂分别击打李甲,被闻讯赶来的李乙扯开,继而双方发生撕打。后徐某、王某分别找来木棒、钢筋与李丙、靳某对打。当王某手持菜刀再次冲入现场时,被李丁手持“T”型钢管座腿猛击头部致其倒地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李丁等人行为不克制,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分别判处李丁等人有期徒刑;二审法院认为徐某、王某一方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无论强度、情节都甚为严重,李丁等人在整个发案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改判宣告李丁等人无罪。裁判理由:所谓“必要限度”一般要求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基本相当;防卫行为虽然稍超过必要限度,但并非过于悬殊,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大损害的,也不能认定防卫过当。和赵某某故意伤害案的判决书中,明显有“折中说”的痕迹[3]。
这些相关标准的缺失就造成了法院在审判中的混乱,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及其理论学说的理解不同。
二、审判规律背后的理论问题分析
(一)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相关学说
目前,我国关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学说分为三种:一是“基本相适应说”。该学说主张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要求完全相等,但必须基本相当,要求防卫行为强度、性质以及造成损害的程度应与侵害行为大抵相同,防卫强度不能大于侵害强度[4]。二是“客观需要说”。该学说以有效制止侵害行为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只要能够有效制止不法侵害,防卫的强度可以小于、等于甚至可以大于不法侵害的强度。三是“折中说”。该学说是“客观需要说”与“基本相适应说”的糅合折中,要求防卫行为既要以有效制止为出发点,并且要与侵害强度大抵相当。支持“折中说”的学者认为,防卫者的行为及其给不法侵害者造成的危害必须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且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基本相适应[5]。
笔者认为这三种学说各有利弊,具体体现在:“基本相适应说”要求防卫行为要与侵害行为在强度、性质、手段及后果方面基本相当,为了防止防卫人恶意报复,并适当维护侵害人的基本权利,有其合理之处,但“基本相适应说”并没有从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合法权益的层面来考虑,并且忽视了防卫者的主观目的。当防卫者处于危险境地时,要求防卫者选择与侵害者相似的手段、强度,显然会束缚住防卫者的手脚,使其在防卫中放弃优势手段,将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状况。
“客观需要说”认为防卫的强度不应该被不法侵害的强度所限制,只要是客观需要的,就可以超过侵害强度。这种观点有利于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作斗争,但是可能促使防卫人选择过激行为进行防卫,损害侵害人的利益,也不利于法律法益平衡原则的实现[6]。
“折中说”又称“相当说”,该学说以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基础,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满足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要求;二是防卫行为要与侵害行为基本相当,无论是手段还是结果都不能过限。这种学说集“客观需要说”与“基本相适应说”的精华,既强调了防卫行为的必要性,又强调了防卫手段与结果的相当性,作为一种修正,规定了防卫行为的最低限度为不能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防卫结果的最低限度为不能造成重大损害。吸收融合之后的学说较前两者更为完善,成为主流观点,一直被学者们推崇。但正是由于该学说是两种学说的结合,弊端也有所延承。“基本相适应说”要求防卫行为要与侵害行为相当,“客观需要说”要求防卫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超过侵害行为,两种学说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这就导致“折中说”在司法上往往会无所适从,理论难以指导实践。
(二)“折中说”对我国司法实务的影响
“折中说”的局限性导致法院在审判时会出现罪与非罪的差别。对于同类案件,不同法官的理解可能千差万别,有的认为防卫行为可以超过侵害行为,有的则认为防卫行为必须与侵害行为大抵相当,超过的皆为防卫过当。
“折中说”还间接影响了司法实务对必要限度的认定标准,即容易使我国防卫限度的审判走入唯结果论的误区。司法机关往往将“行为明显超过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当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认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限度必然导致损害结果重大,损害结果重大皆是由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的。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一书中提到了“整体过当理论”,他认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是一个整体,不存在“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的现象,更不存在“结果过当”而“手段不过当”的现象。首先,采用循环论证的方法容易使司法实务中的逻辑推演倒置,从而在演绎的过程中出现错误:以结果过当推出手段过当,或者以手段过当推出结果过当,而不是两者综合考虑;其次,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理论缺失,要认定防卫手段的过限程度,必须经过相当复杂的法律考量,相较而言,司法机关通常会选择更为简单清楚的方法,即通过判断防卫结果的严重程度来推断防卫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7]。
因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这一方面是存在倾向性的,通过认定防卫结果的严重程度来判断防卫行为有无超过必要限度成为司法机关更多使用的法律考量手段,进而导致司法机关容易将正当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简化为防卫结果是否严重的判断,即简单地将防卫人与侵害人之间的法益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比如在赵某某故意伤害案审判过程中,一审法院简单比较防卫人与侵害人各自受到损害的程度,认为后者受到损害的法益高于前者,便判定赵某某防卫过当。
为了避免司法部门简单地以防卫结果作为评判结论,笔者从四个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方面着手,并对“明显超过”的“明显”以及造成“重大损害”的“重大”的标准进行具体细化,以期能够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办法。
三、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认定
(一)适当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从1979年《刑法》第17条①1979年《刑法》第17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可以明显看出,防卫强度要求过于苛刻,防卫限度把握过严。而1997年《刑法》的修改明显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放宽,将“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改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外法律还制定了第20条第3款②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虽然学界对该款是否赋予公民无限防卫权仍存在争论,但将“超过必要限度”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将“不应有的危害”修改为“重大损害”,使用“明显”和“重大”二词,立法者显然意在放宽对必要限度的要求,鼓励公民维护个人与他人的合法权益。此外,由“基本相适应说”到“客观需要说”再到“折中说”,从相应学说的发展顺序中也可以看出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由严转宽的变化趋势。
最高人民法院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相关问题虽然没有一致的审判标准,但仔细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时期公布、整理的案例,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基本由“苛求”到“严格限制”再到“开始放宽”的趋势。对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公布的相关判例,有学者归纳总结如下:若防卫满足客观需要,且强度大于不法侵害的强度,则重点考察“客观需要”;若防卫超出客观需要,但强度近似于不法侵害的强度,则重点考察“强度”[8]。笔者认为,不管学者对判例解读是否全面准确,但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公布的案例所体现的“利益的权衡更多地向防卫人倾斜”的价值导向和所持有的对防卫限度更为宽和的态度对于司法实务中必要限度的整体精神把握无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所以在判断正当防卫必要限度时,首先应当准确把握1997年《刑法》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立法宗旨,沿袭最高人民法院由严至宽的审判态度,适当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使防卫人能够很好地实施正当防卫,充分发挥正当防卫的效能。
(二)判断必要限度的四个方面
笔者认为判断必要限度要从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的强度、现实的缓急、不法侵害的权益以及防卫人本身状况这四个方面分析。
一是不法侵害的强度。不法侵害的强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防卫手段的选择及防卫强度的大小,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当两种力量大抵相当时,很难有一方力量制衡另一方力量,所以,当侵害强度不断增强时,则应当允许防卫强度增大[9]。不法侵害的强度,主要从人数的多少、侵害行为的轻重、工具的选择以及击打部位的要害等因素综合来考虑。防卫行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在于某故意伤害案中,11名侵害人对于某和他的母亲进行殴打,于某拿起水果刀逼退众人后捅伤四人;再如李某蕊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李某甲用一把铁质的簸箕胡乱击打马某乙的头部背部,并手持砖块击打李某蕊后脑勺,李某蕊为了阻止李某的不法侵害,用水果刀在李某甲的左腹部戳了一刀后逃离,这些都是考察防卫手段需要考虑的事实。此外,笔者通过研究判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防卫人使用工具的强度评估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赤手空拳造成的危害就一定弱于使用刀具棍棒,所以在进行防卫者与侵害者强度对比时,不能囿于工具的局限,还要结合工具使用者的强弱进行分析。
二是现实的缓急,即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紧迫程度。除了侵害的强度,现实的紧迫性也是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限时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10]。有的情况下,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不法侵害的强度未能开始表现出来。如在旋某琦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杨某将被告人旋某琦骗至出租屋内逼迫与其发生性关系,此时不法侵害已经开始而侵害强度尚未表现,就应当将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作为衡量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重要标准。相当数量的案件中出现了防卫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随手抓起身边水果刀进行防卫的情况,所以司法机关在判断案件必要限度,尤其是防卫强度超过侵害强度的案件中,考察现实的紧迫性与制止不法侵害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是不法侵害的权益。即防卫行为所维护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可以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制止正在进行的财产侵害不宜使用重伤甚至死亡的暴力防卫[11]。“白玉案”与“龙女士案”皆是女出租车司机在拉载客人时,遭遇暴力抢劫财物,而后女司机选择开车撞击歹徒,这种制止不法侵害造成侵害人死亡和重伤的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正当防卫是授权性规范更是禁止性规范,既不能过分偏向防卫者,也不能偏向侵害者,决不允许为了一般或是较小的财产权益而损害不法侵害者的生命权。
四是防卫人本身状况。诚然,人在作出决定之时会受到很多状况的影响,如年龄、性别、地位、经验、病痛、氛围、劳累感、爱国心甚至气象等等[12]。当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防卫人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没有能力来准确判断侵害的手段和强度大小,也无法准确预料防卫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防卫人所作出的防卫行为往往是本能和潜意识之举,防卫行为受制于防卫人本身的情况。在邓某娇故意杀人案中,在两次被邓某大按倒在沙发上,强奸行为已着手实施的情况下,文化程度不高、身材娇小柔弱的邓某娇随手拿起手边的刀刺向邓某大是一种本能反应,符合防卫人自身的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在受到严重危险时要求防卫人从容判断防卫行为需要相适应的强度、手段及后果,显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三)“明显超过”和“重大损害”的具体标准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理论之所以很难运用到司法实践,屡次出现由结果推向行为手段的逆逻辑思维,关键原因是可操作性弱,缺少具体评判标准。因此,笔者对《刑法》第20条第2款中的“明显”与“重大”提出如下标准:
如果侵害行为只有造成轻微伤的可能,那么防卫人对侵害人造成轻伤以下的伤害,就不能称其为“明显”超过;倘若侵害行为可能使防卫人受到轻伤,而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重伤的,可以认定为“超过”,造成他人死亡的,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例如在甘肃省平凉市张某甲过失致人重伤一案中,被告人张某甲与同事二人遭到喝酒后的郭某乙等多人挑衅殴打,张某甲用拳头击打郭某乙的面部数下,郭某乙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在张某甲背部刺戳四刀,在被告人逃离后,郭某乙等人继续追赶殴打张某甲,直至被正在巡逻的民警制止抓获,后经法医鉴定,张某甲损伤程度构成轻伤,郭某乙由于受伤前左眼存在病理性改变,受到拳击后损伤构成重伤。张某甲在遭到郭某乙等多人的挑衅殴打后,作出自己可能受到轻伤以上侵害的判断是人之常情,在以一敌众的情况下,用拳头击打郭某面部进行自卫,显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关于“重大损害”的标准,笔者认为应当借鉴体系解释的方法,将“重大损害”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理解,通过解释前后法律的条文和目的,来厘清“重大损害”的含义。在我国刑法里,除了第20条第2款中出现“重大损害”的规定,其他条文均未出现相关规定,但有将“重伤”解释为“重大伤害”或者其他“重大损失”的并列规定,如《刑法》第95条①《刑法》第95条规定:“本法所称重伤,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第115条②《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第133条③《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等。因此,笔者根据体系解释认为“重伤”是正当防卫必要限度中规定的“重大损害”的最低限度,必要限度中造成“重大损害”只能是人身侵害的重伤、死亡和财产侵害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轻伤或轻微伤不属于重大损害的范畴[13]。所以在赵某某被控故意伤害案中,赵某某为了防止王、周二人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导致二人轻伤和轻微伤的损害结果不足以认定为重大损害,不构成防卫过当。
结论
为了弥补我国司法实务中单纯以防卫结果作为审判标准的弊端,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首先应当顺应立法从严变宽的发展趋势,适当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其次,在正当防卫的认定方面,还应该考虑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的强度、现实的缓急、不法侵害的权益以及防卫人本身状况这四个方面;最后,笔者认为必须通过比较的方法才能得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结论,“造成重大损害”也只能是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防卫结果。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问题是决定防卫人罪与非罪的关键,然而我国现行的理论学说还处于发展不完善的阶段,笔者只是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进措施,以期能对当前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健全我国正当防卫制度,还需要国家提高立法技术,改正概念模糊宽泛、用语缺乏严谨、举证判断困难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的“期待可能性思想”和“比例原则”[14],出台一系列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真正将正当防卫制度落在实处,解决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如何准确认定的审判难题。
——以美国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