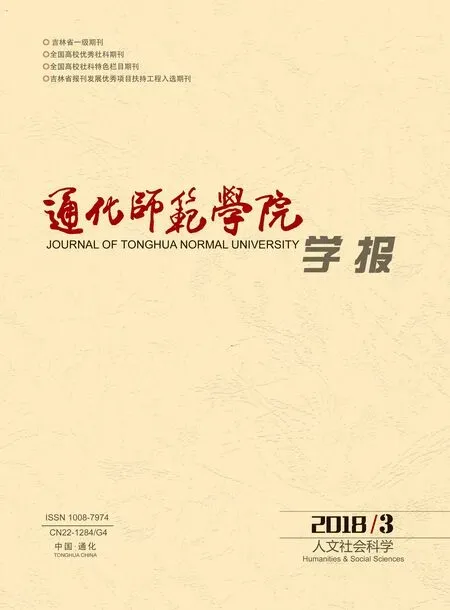论庄子的自我实现之道
翟志娟
在我国传统思想家中,庄子是极有自我意识的一位。面对当时社会普遍的自我迷失与人格异化,庄子深感保持自我人格之可贵与艰难。如何在混乱不堪的现实中找到自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自我?庄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索。
一、自我意识的确立
人要实现自我,首先要觉知自我的存在。这个觉知的过程,就是不断超离外界条件的种种束缚,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庄子的超越精神,集中体现在《逍遥游》中的大鹏身上。当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的时候,它超越了种种依赖与局限性,超越了空间、时间、有限、相对,而进入了广大、绝对、永恒、真实的世界。反观那些蜩与学鸠式的人物,为现实的有限性所束缚,只能生活在渺小、有限的时空之中,还为自己良好的适应性而自鸣得意。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说:“这些人就是那抢上榆枋又投回地面的学鸠,就是那在习惯与惰性之中频频鼓着翅膀的蜩。他们安住在常识层面的价值与规范之世界,将这一角世界当作世界之全,而埋没其中。他们毕竟与自己原系何种存在?人之‘应然,为何?人之根源真实的生涯是何物这等问题全不相及。”(《庄子》第五章〈自由的人〉)
现实世界纷然淆乱,从各个方面对人施以影响,以迷惑人的自我,改造人的本性。个人与外部世界相比是如此的渺小无力,因而丧失自我就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而要觉知自我的存在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个逐渐揭示的过程。人必须要摆脱外在、内在、有形、无形的种种束缚,才能发现自我。《秋水》中引北海若的话说: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477
这三种事物,各自受到空间、时间和观念的局限,因而不能自由,见识有限。在现实中,人的不自由来自太多外来观念与规定性的束缚,我们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清理,才能发现真实的自我。
1.摆脱世俗名利观念的束缚
所谓的名缰利锁对人的束缚和限制是第一位的,要求得精神自由首先要看淡名利得失。《庄子》里边讲了许多淡泊名利的故事。当曹商向庄子夸耀其出使秦国获得的富贵时,庄子尖锐地指出,这种获利是以人格的卑污为代价的。当楚王请庄子为相时,庄子首先想到的是当官后的人格不自由。颜回居陋巷而安贫乐道,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改初心。庄子反对人过分追求名利富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其伤生害性。《至乐》篇中说: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惽惽,久忧不死,何苦也![1]519
二是因其导致本性的扭曲与异化。《骈拇》篇中说: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1]288
庄子指出,三代以下,世人无不为追求外物而丧失自我,迷失本性。“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其不悲哉!”(《让王》)庄子以为用宝贵的生命去追求外在的名利,简直是“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同前)实在是不值。
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些,庄子才能彻底摆脱对功名富贵的依恋而安贫乐道,甘心“曳尾于涂中”。他宁愿像泽雉一样,“五步一啄,十步一饮”,艰苦地谋生,也不愿意被人豢养,过一种衣食无忧,羽毛光鲜的生活。
2.摆脱世俗道德观念的束缚
世俗的道德观念主要表现为仁义礼教。庄子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极力反对仁义礼教对人性的戕害和删改。《大宗师》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1]237
在庄子眼中,标榜仁义道德之人,就像是被天施过肉刑的犯人,人格残缺不全。在儒家道德规范的束缚下,人类的精神便无自由活动的可能。这些道德观念把人切割,使人碎片化。人要找回完整的自己,就必须“涤除玄览”,清理那些进入意识范围的种种观念,这样才能找回完整真实的自我。
庄子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首先是因为它残害人性,“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役其德者也。”(《天运》)“以己为质。使人以为己节,因以死偿节。”(《庚桑楚》)
其次,是因为仁义道德的虚伪。《盗跖》中写道: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怙),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1]894
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
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嫡),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1]907-908
其三,仁义道德是统治者奴役民众的工具。《在宥》篇中借老子之口表明了这种认识。老子对崔瞿讲述了自黄帝以来道德不断衰落,政治不断恶化的过程,最后说道: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1]323
在老子看来,仁义道德只不过是用来加固刑具的木条、榫子,目的是麻痹民众的反抗意识。人们如果真心照办的话,只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危害: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自埋,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盗跖》)[1]908
最后,从庄子的相对主义立场看去,人类的道德认识具有时代性和相对性,而且确立这些观念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马斯洛在《自我实现的人》中说,“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被视为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东西,可能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毫无道理的副产品。”[2]50而世俗之人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只是昏昏然随世俗观念而动:
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也,愚之至也。(《天地》)[1]383
这就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讲到的自我意识普遍丧失后的人性表现:“我们的愿望、思想及感觉并不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外界加于我们的。要认清其程度如何,是尤其困难的……他所思、所感、所愿都是别人期望的样子,而他却自认为是自己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自我。”[3]169-170
3.摆脱礼俗制度对人的束缚
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礼俗制度试图把所有个体的情感与反应都纳入同一种行为模式之中。这种制度对个人身心自由的戕害是极严重的,因而遭到庄子的激烈反对。《庄子》中反对礼制的人物很多,这些人对礼制采取的态度大致有两种:
一种态度是,消极适应,将其工具化。老聃死的时候,秦失去吊丧,三号而出,不屑于再陪演下去。“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大宗师》)孔子说他“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他只是随着大家“人哭亦哭”,迎合大家的观感而已。
他们对待礼制的态度,与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表现如出一辙:“他们对惯例的不遵从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每件小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而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尽可能地通情达理。”“实际上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他们独立于惯性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2]17
他们将礼制工具化。《天运》中师金对孔子说,“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1]434
礼只是一种工具,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用来役使人的。师金批评孔子欲行周礼于当世,是欲“推舟于陆”,“没世不行寻常”;是东施效颦,反增其丑。
另一种态度是,积极反对,按自己的意愿改造礼。
《大宗师》讲子桑户死了,他的朋友为他作词编曲,边弹边唱,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1]227
在《庄子》这里,对世俗礼制的反叛还只是个别的事例。而到魏晋时期,士人反礼教的言行才开始普遍显露,“礼岂为吾辈设邪?”成为当时进步人士反礼制的口号。
二、自我人格的实现
自我意识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揭示过程,自我人格的实现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终身努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大宗师》篇讲到女偊引导卜梁倚实现自我的过程: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1]216-217
在传统社会中,自我人格的丧失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庄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对那些迫于外界的压力与诱惑而丧失了真实自我的迷失者表示了极大的悲悯,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1]58
这些人“役人之所役,适人之所适”,最终沦为达成外在目的的工具。庄子指出丧失真实自我是一件比身体死亡更可悲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他把这种心死而身存的人看作是一种鬼,“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德)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庚桑楚》)
如何才能做得撄宁?在自我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保存自我的完整性与同一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关于自我与外部的社会观念,庄子称其为天与人,或内与外。)对此,庄子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庄子认为,要想遨游尘世而不失自我,人首先要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即心中有“真宰”或“真君”。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齐物论》)[1]57
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表现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自我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内心的判断取舍,即内心有“真宰”。方东美先生说:“就是从事这个生活的人自己要有一个使命,要在自己的生命宇宙里面,自作精神主宰。”
当人有了主宰意识,便可“物物而不物于物,”成为外物的主宰而不是被外物役使的工具。这样的人虽“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虽不断接受外部信息,但其内在的自我是稳定的,一致的。
公示语是社会用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标牌、路标、指南、公告等,即在公共场所张贴的旨在为一般公众或特殊群体提供指示、警告、告示等帮助的服务性语言标识都属于公示语的范畴。(唐红芳,2007:142)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城市公示语采用中英双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逐步形成了由国际化大都市向中小城市普及的趋势。英语公示语不仅影响着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及对外交流形象而且正确得体的公示语也可为外籍人士的观光旅游、工作生活营造一种舒适便利的环境。
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心与之莫多。……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知北游》)[1]677
这里讲的“外化而内不化”,实际上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静态适应,也就是只改变自己外在的行为方式,而内心并未被波及,所以不管怎么变化,内心并不增益改变(心与之莫多)。这样的人能做到“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外化”是为了与世界相交接,“内不化”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理想。但普通人则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接触外界的同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内心也改变了。庄子评价这类人说: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长梧)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故卤莽其性者,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则阳》)[1]785
这些人卤莽地对待自己的性情,轻易随外界而改变自我,以致逐物而不返,成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徐无鬼》篇中讲到社会上自上而下各行各业的“囿于物者”,评价道:
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1]734
这些人易己为物,把自己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因而丧失了自我价值。以丧失自我为代价来谋求世俗的成功,这种成功代价昂贵,却意义不大,不过是把自我变成外界的工具而已,而普通人对此毫无知觉,反为此沾沾自喜,因而造成了当时社会上人格的普遍物化。《人间世》中讲到各种果树因有用而受害,庄子评论道:“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因此,人要保持自我,就不要让自己成为外界的工具,这样才能去掉种种负累。“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有道之人,尊重自我的本性,也尊重他人和物性,自己不做工具,也不把他人作为工具。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1]288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1]290
社会不要把个人当作它的工具,而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
其次,当自我与外部世界(天与人)在观念上发生冲突时,选择坚持自我。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1]495
“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1]945
而对那些既想顺天又想从人的“全人”,庄子是很鄙视的。
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庚桑楚》)[1]715
只有最低级的虫子才能完全没有自我与环境的冲突,才能完全适应环境,“全人”哪里做得到呢?只有人类,才会具有自我与环境的对立,这正是人类的生存优势之所在:正是这种对立与冲突推动了变革,人们尝试通过更高层面的形成,实现矛盾的统合或解决。如果自我与社会完全相同一,那这个社会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因此,自我与外部社会观念的矛盾冲突机制,必须启动。
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敢面对自我与环境的冲突,更不敢在此冲突中坚定地选择自我,因而导致了自我的撕裂。《庚桑楚》里讲到,在外界的纷扰之中迷失了自我的南荣趎,携带干粮,独自一人走了七天七夜,来到老子这里求解疑惑。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
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
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
老子曰:“何谓也?”
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
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性情而无由入,可怜哉!”[1]691-692
老子真是犀利,一眼就看出南荣趎的问题在于与外部观念纠缠不清,于是劈头问道:你为什么跟这么多人一起来呢?南荣趎一下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身边有鬼呢,吓得“惧然顾其后”。确实,我们与自我疏离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病态地与他人搅在一起。针对南荣趎的问题,老子指出:“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惑于外者,将封闭内心;惑于内者,将封闭外界。二者都是人格的病态:前者“逐外物而不返”,导致自我迷失;后者自我封闭,不与外界接触,导致自我的萎缩。
正确的做法是:
“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1]555
既不能拒绝外界,也不能背弃自我,关键是要在自我与外界之间确立一个清醒的守护者,即“真宰”,由他来对内我与外物进行判断取舍,“定乎内外之分”。
“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天运》)[1]439
自我就在这种内外交流中得以形成。杨国荣在《〈庄子〉哲学中的个体与自我》中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个体而言,与他人的这种共在主要呈现消极的意义,它使此在湮没于众人之中,从而失去了自我的个体性品格。在此意义上,共在常常意味着沉沦。”[15]46因而,海德格尔认为,要保存个体性就必须与外在脱离关系。
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人的自我本就是在外界事物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受其浸染,为其迷惑,那么,它又怎么能对外部观念保持清醒的判断呢?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外界保持清醒的态度呢?其二,在强大、牢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外部观念影响下,个体的自我意识显得如此的渺小无力,个体与之交接必然会导致自我的迷失与丧失。因此,要保存自我,就必须与外部世界脱离关系。
然而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其一,个体是有可能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因为自我并不是外部世界的翻版,自我从来就不是对外界被动的、彻底的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甄别地接纳。这便是米德所说的自我中的主我部分(类似于庄子的“真宰”)的功能。其二,人在与外物“相刃相靡”的过程中,固然有可能丧失自我,迷失本性,但也有可能战胜外物,强固自我,这个过程便是“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庄子看出,自我是在外界的干扰、破坏下才得以形成、得以强化的。没有这一过程,自我便无法真正确立,即便存在,也无比虚弱,不堪一击。
事实上,自我与外界一方面表现为对立冲突的关系,另一方面,自我的形成又离不开外部世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没有外部世界,哪来的内在心灵?因此,纯粹的自我是虚无的。自我只是一种对待性的存在,一种反应性的产物,它只有在个体与外界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显现。要实现自我,必须借助外界。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庄子采取一种“外化而内不化”的方式与外界相周旋,目的是实现“内不化”的真实自我,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缮性》)[1]469
不管是为追求外部的事功,还是为了完善内在的自我,个人都离不开外部世界。失去生命,我们无法作为;而离开现实,我们又能做什么呢?饶东原对此评论道:“庄子本身是个现实的人,他有现实的功利观,有现实的意图。这一意图尽管用超现实的烟雾笼罩着,然而却是时露峥嵘的。”“庄子在处世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体现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绝不能说庄子是浑浑噩噩的。”[19]4确实如此,如果真的消极避世,庄子也不需要如此煞费苦心了。
在自我与外界的这种双向交流中,主体一方面深化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他的自我也变得更为真实而强大。真正的自我实现者是高度个人化,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人。他们的自我牢固地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深刻认识之上,他们既能接受世界,也能接受自我,“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则阳》)他们在与外物交往的过程中,“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天地》)这是因为他们有强大而稳定的自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庚桑楚》),他们的内心能发出一种智慧的光芒,照见人世,照见万物。“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天道》),在最深入地了解外物的同时,还能不失自我的本真。正像弗洛姆说的那样:“个人在所有自发活动中拥抱世界,他的个人自我不但完好无损,而且会越来越强大坚固。因为自我活跃到什么程度,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3]175
当自我强大到一定程度,个人便足以对抗一切外在的干扰与破坏,“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缮性》)“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逍遥游》)“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田子方》)“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德充符》)
一切外在的毁誉得失都不足以扰乱其内心的宁静,这种状态就是撄宁。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彻底地完成了真实自我的实现。
庄子的自我实现途径,不是逃避现实的自我封闭,而是在与现实的血脉相通中实现自我的性质与价值。庄子对现实有很深的依恋,“曳尾于涂中”而自得其乐,让泥土从头到脚感动自己,沉溺其中,得其三味,而能自觉抗拒各种诱惑;与物往还,不失本真;“极物之真,能守其本。”由此,庄子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以一种“外化而内不化”的静态适应方式与外部世界相周旋,为自我人格的成长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途径。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7.
[3]弗洛姆.逃避自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涂波.庄子思想的自我主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5]徐强.英美汉学界对《庄子》“自我”观念的研究管窥[J].文化学刊,2014(5).
[6]奚彦辉,高申春.心理学视角的《庄子》自我观探究[J].心理研究,2008(2).
[7]肖捷飞.从《庄子》寓言看庄子自我形象:睿智冷眼热心肠[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3).
[8]何念龙,大鹏:从哲学意象到文学自我——庄子、李白文化符号类型比较[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5).
[9]李清章.论庄子、屈原的自我悲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1).
[10]张文勋.儒、道、佛的自我超越哲学——孔子的“四毋”、庄子的“三无”和佛家的“破二执”之比较[J].中国文化研究,2006(4).
[11]刘康德.“浑沌”三性——庄子“浑沌”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2]马鹏翔.“生态自我”与庄子的物我观[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3]李海萍.米德与庄子自我理论的现时代意义[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14]陈清春.庄子“吾丧我”的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5(4).
[15]杨国荣.《庄子》哲学中的个体与自我[J].哲学研究,2005(12).
[16]颜翔林.庄子怀疑论美学及其当下意义[J].求索,2014(1).
[17]路传颂.自我修养与劳动——论《庄子》的反异化思想[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18]贝京,王攸欣.“至人无己”与“敖倪万物”——庄子人格理想与行迹叙事新诠[J].中国文化研究,2016(2).
[19]饶东原.一个矛盾的理论体系——论庄子超脱中的自我[J].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