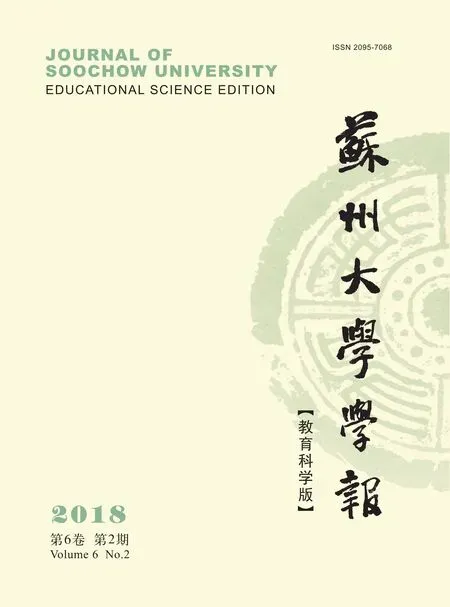跨界的心理科学史研究
王 文 基
(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心理学史研究对了解心理学的过去与现在不可或缺。早年高觉敷先生主编之《中国心理学史》内容着重整理传统中国心理学思想的流变。晚近国际与华文学界就重要心理学家的事迹及贡献,心理学知识与政治、社会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成果丰硕。例如阎书昌教授的《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便利用一手材料,就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整理。然而相较于其他“心理科学”或“精神科学”(psysciences,包含精神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治疗、精神卫生等领域),整体而言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心理学史的形貌与研究者选择的视角密切相关。举例而言,论者迄今多关注前辈心理学家的生平与思想贡献,重要心理学派与机构的发展,以及重要概念的译介过程。相较于学术思想史,学界对实验、量表、仪器在学科建置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具有的社会文化意涵了解有限;就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议题本身,乃至这些对象与议题在历史中的转变,一般亦尚无系统性的掌握。此外,学界对心理知识的少数生产者知之甚详,但知识与技术的操作者(如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及使用者(政府部门、企业乃至社会大众)的样貌依然十分模糊。再者,或因学术分工、研究旨趣之故,迄今心理学史学者多依据重要年代框定其研究范围。也因此,例如民国时期与1950年之后的心理学发展间的关系,两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下延续与断裂一事,学界迄今亦无较细致的考察。
过去数十年间人文社会领域特别强调采取“跨界”(boundary crossing)的视角,借此松动本有熟悉、不证自明的视野及问题意识,进而丰富研究的内涵。就目前研究成果观之,与近现代中国有关的心理学史研究,大多还是在学科史、内史的架构中进行,与其他领域的互动有限。笔者并非心理学训练出身,然因研究兴趣之故,晚近从事心理科学的历史研究。上文列举的几个跨界研究的可能题材与视角,正是来自晚近科学史、医学史的启发。
既然史学研究的特色在于对史实的整理、诠释与分析,本文便以实例简述跨界心理科学史研究一两个可能的方向。众所皆知,丁瓒先生(1910—1968)为著名心理学家,对中国心理学学科的建置贡献卓越,其论著已被选编成集。201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其百年诞辰时也扩大纪念,编有专刊。晚近学者如范庭卫等就其事迹及研究特色专文讨论,并着手编撰年谱。学界迄今对丁瓒的生平与贡献了解甚多,然而与以往较为不同的视角或许可以更为丰富吾人对心理学前辈,乃至中国心理学整体发展的认识。
一、学科上的跨界
就20世纪初以来心理卫生运动的发展观之,心理科学间的合作频繁,甚至被认为理所当然。以丁瓒为例,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工作人员内除精神科医师外,亦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工作员、护理师等。此一分工合作的现象不仅在制度上符合当时国际精神卫生机构的惯例,也凸显此单位对精神疾病及心理健康采取跨领域的认识。史料也显示,包括医师(如许英魁等)、心理学家(如丁瓒、刘瀹慈)在内的工作人员曾接受心理治疗师、社会学家戴秉衡(Bingham Dai)的精神分析,这也充分说明医学心理学对当时心理卫生专业人员训练的重要性。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丁瓒等人带领的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团队与北京医学院精神病学教研组、北京大学卫生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等单位合作,发展神经衰弱的快速综合疗法。此一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疗法的核心为以对疾病的认识、思想教育及个人治疗为基础的心理治疗,再佐以药物、物理及体育疗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此一结合中西医学且跨领域的疗法在北京以外许多城市的医院施用。
丁瓒最常被人称道者,除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奠基者之一外,便是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过程所做的贡献。然而,不论从其毕生推动医学心理学的努力,或20世纪初以来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发展而论,丁瓒的事迹都无法仅从心理学学科的建置一点理解。例如,若从精神卫生或心理科学史的角度观之,或许可进一步思考:心理学家与其他心理科学专家(如精神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师、中小学教师等)得以合作的历史、知识及制度条件为何?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心理科学家们之间是否也存在如在西方常见不同专业间的张力?不同心理科学家们对精神疾病、心理学概念及知识的看法又是否一致?若意见相左时,共识又如何达成?若要就上述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甚至掌握其所具有的历史与文化特殊性,势必同时需要了解心理学及其他心理学科的历史。
二、地理上的跨界
近数十年来全球史、跨国史领域的发展提醒研究者避免将眼光局限于地理及政治上的疆界之内,更多地关注人员、知识、技术、物品及制度实际移动的轨迹。医学史、科学史及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强调,科学知识与技术所具有的形貌,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社会文化高度相关。
若分析丁瓒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论著,可知其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所谓“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模式”的影响甚大。通过莱曼(Richard S. Lyman)及戴秉衡等人的引介,梅耶(Adolf Meyer)心理生理学的概念,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中对于环境影响及社会适应的强调,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成为民国时期精神医学及医学心理学的主流之一。然而,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以来批判传统家庭结构、儒家思想的风潮,及丁瓒本身自青少年以来对中国社会实情的不满,又使得他特别强调病态社会及家庭关系对人格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换言之,丁瓒的许多心理学知识与技术的确来自西方,但其又一再强调必须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心理学概念,正足以说明当时特殊的时空脉络对其心理学的影响。而到了政治与学术环境丕变的20世纪50年代,丁瓒从原本主要从西方学界吸取养分并与之对话,转而在推广巴甫洛夫理论上不遗余力。冷战时期东欧精神医学史的研究指出,虽然在战后巴甫洛夫的理论影响甚大,但东欧各国并非全然以俄为师,其各自有接受及诠释巴甫洛夫理论的方式。也因此,在高度政治与学术动员的环境下,包括丁瓒在内的中国心理科学家如何有机地融汇苏联与西方的心理理论,开创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心理学,而当时的种种又与之后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关连,实需兼顾跨国性与在地性的研究视角。
从以上简介可知,若要了解丁瓒在内的中国心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对20世纪心理学与心理科学在国际上的趋势有更多的掌握。与此同时,丁瓒等前辈的贡献除在引介西方与苏联心理学外,也从事许多“本土化”的工作,让心理学的知识与技术在一个与欧美及苏联迥异的环境中发展。而唯有透过整理这些概念与技术实际移动的轨迹,分析这过程所具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涵,或许方能对这些心理科学家前辈的工作有更细致、精准及脉络化的理解。
三、小结
西方学界近来曾就心理学史的未来有颇多讨论。对心理学家而言,心理学史的任务为协助心理学家认识学科的成就,引导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心理学家藉此可评价心理学的过去及现状,进而形塑学科的认同。相较而言,主要由专业历史学界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由于立场上较为批判,选题多元,关切的焦点不尽然与心理学本身的发展有关,总的来说常引发心理学家侧目。
笔者从跨界的角度思考心理科学史研究的可能性,希望拉近心理学史与包括科学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间的距离。首先,跨界的心理科学史研究,应可促进心理学史与其他历史研究(特别是科学史、医学史、社会文化史)间的交流,丰富心理学史探讨的议题,吸引更多学者甚至社会人士对心理学史产生兴趣。其次,回顾心理学过去的发展,乃至审视当今心理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心理学本身涉及的议题便极为多元,涵盖不同领域。“跨界”的主张与其说尝试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不如说提醒研究者应实际跟随心理学家、心理学理论、概念与技术移动与发展的轨迹,如实地了解其具有的特色,时代意义,以及社会文化意涵。就此意义而言,跨界的视角或许更能帮助心理学家以更开阔的胸襟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合作,进而更清楚自身的特色及贡献。
——博弈论
——“科学史上的今天”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