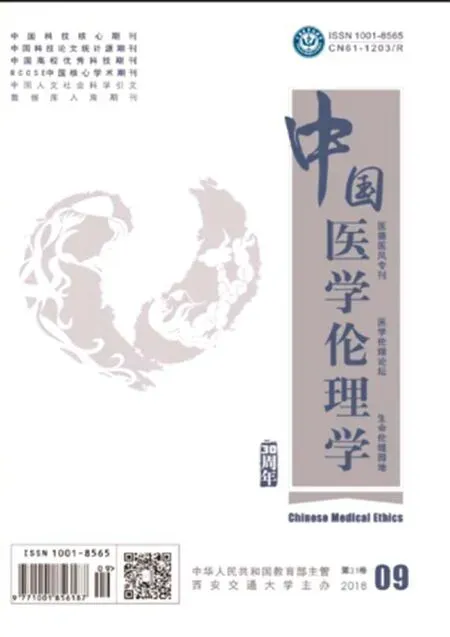论孕妇分娩方式选择的伦理基础
张俊义
(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北京 101300,jyz0819@sina.com)
2007年,一名孕妇因丈夫(存在事实婚姻)拒签剖宫产手术同意书而死亡;2017年,另一名孕妇要求剖宫产手术却不得,因疼痛难忍而跳楼身亡。虽然这两起悲剧皆属极端个案,但这对于孕妇及胎儿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本可挽留却无奈逝去的生命迫使我们凝思分娩方式选择机制上可能存在的模糊之处,并探讨其背后潜藏着的伦理冲突,寻找更全面更具张力的解决方法或途径。
1 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的孕方同意权
孕妇或胎儿出现异常情况,如前置胎盘、产程异常、宫缩乏力、胎儿窘迫、胎膜早破、先兆子宫破裂、羊水过少、产妇合并内科及妇产科疾病等[1],继续自然分娩很可能会难产甚至导致母婴生命危险,因而医生会建议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这就是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根据医学指征的严重程度,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可进一步分为相对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和绝对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2]。
1.1 相对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的孕方同意权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当他人行为涉及一个人的这些权益时,必须经过其知情同意,并以一定的“意思表示”形式体现出来。剖宫产手术属于法律规定的需经孕方以特定形式即书面形式予以确认的民事法律行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存在明显不同。因为《侵权责任法》相较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属于上位法,故医方告知与孕方同意应依《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侵权责任法》更突出了患者在知情同意权上的自主性。因此,“孕方”一词,首先指孕妇,然后才是孕妇的近亲属,他们主要在孕妇意志不清或其他无法表达意见的情形下作出决断。
剖宫产手术的相对医学指征,是指孕妇或胎儿出现前述医学指征,但指征数量少或只有一项,且程度较轻,既存在症状进一步加重的危险,又存在经医患协同努力而成功顺产的可能,属非紧急情形。此时,医方向孕妇提出剖宫产手术的医学意见,合理合法。但如果孕妇不同意,则需遵从其意愿,不得强行实施剖宫产手术。
在非紧急情况下,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是医者实施某种医疗方案的伦理前提,是其必须遵守的基本执业规则。行为过程符合规则是伦理判断的一般性标准。当有相对医学指征的孕妇拒绝剖宫产手术时,医方不仅不能将此视作孕妇的不配合,而应给予积极助产,给予更多鼓励与支持,并密切观察孕妇与胎儿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做好产程中可能的急症剖宫产手术的准备。
1.2 绝对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的孕方同意权
剖宫产手术的绝对医学指征,是指孕妇或胎儿出现了前述医学指征,且程度较重甚至有多项指征并发,如果采用自然分娩方式,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危险性极高,属于紧急情形。此时,医方向孕方充分说明危险情况,并提出剖宫产手术的医学意见,现实中绝大多数孕妇及其近亲属一般会同意医方意见。但在过去的医疗实践中,也出现过孕妇或其近亲属出于种种原因而拒绝签署手术同意书。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医方应怎么办呢?
2007年11月21日下午,一名孕妇情况危急,但因其丈夫拒绝在剖宫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护人员只能实施常规抢救,最终无效死亡[3]。在该案中,医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担心手术无法可依,只能无奈地甚至痛苦地等到抢救的失败。依现有法律法规,医方行为没有违法之处,但其是否已经用尽法律法规赋予医者的处置权了呢?
首先,在医事法层面上,仍留有医者使用处置权的余地,虽然该余地处于某种模糊状态下。这种模糊性是由语言与实践的关系决定的,“语言与思维的清晰化的基础是实践。”[4]语言的模糊处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清晰化,但模糊无法绝对排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在这一条规定中“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就是该案例中医方未能或未敢援用的法律余地。2010年先后施行的《病历书写规范基本规范》(第十条)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都规定,为抢救患者,在患方“无法及时签字”或者“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意见”时,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的负责人签字批准。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的情形作出解释时,在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中规定,“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5]《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有关规定也应得到该第五项的确认。
其次,在基本法律层面上,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才是医者可以援用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在医院里,患者紧急情况相较于他处出现频率肯定要高得多,而且要复杂得多,因此,启动医学紧急避险机制应格外严格与谨慎。在现实中,即使患方拒绝急救手术,但民众仍感觉医方应果断出手的情形一般是:实施常规医学救治,患者凶险度仍极高,而实施急救手术便会相对安全,这时医方突破一般情况下必须遵守的执业规则而强行实施手术抢救,即使最终抢救失败,医方也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在伦理学中,在常态情况下要讲“规则”,在紧急情况下更讲“目的”。当危急患者或其近亲属拒绝可靠性高、预后较好的手术施救时,医方面临的是患者生命权与同意权的较量,而医疗机构以维护生命健康为目的,此时在确保“善良动机”(如前案例中医方承诺免费治疗,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形式)前提下,应被允许实施以生命为“目的”的医学紧急避险。2010年12月3日,广州一孕妇胎盘早剥,情况危急,但仍明确拒签剖宫产手术同意书,医院在得到其近亲属同意后强行剖宫救其性命[6]。虽然胎儿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但这仍不失为一起成功的医学紧急避险案例。
医学紧急避险还有其他伦理理由:患者或孕妇已到医院求助,只是在治疗方法或分娩方式上有异议;拒绝最佳抢救方式或分娩方式的患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就很接近于拒绝医学救治的自杀者,而面对后一种情形,医者显然会不顾其拒绝而予以施救;在人处于生或死的紧急关头时,社会应努力寻求更高层级或更科学的机制来面对,而不应完全攥在另一个人的手中,而且这个人出现不理性甚至不可信任的可能性并非微乎其微。
2 非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的孕方选择权
剖宫产手术是一项快速完成孕妇分娩过程,化解因难产、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可能导致的风险,从而挽救产妇和围生儿生命的有效手段。然而随着该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其稳定性与安全性越来越受到更多孕妇的信赖,甚至有些孕妇主观认为剖宫产是与自然分娩作二选一的正常分娩方式。但医学科学告诉我们,自然分娩才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正常生理过程,剖宫产手术不管发展到多高水平,总是对这一自然过程的人为干预,其产生母婴并发症概率相较于自然分娩要来得更高。在我国剖宫产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提出“逐步降低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7]的目标,医疗机构在实践中也为此进行不懈努力。
2.1 影响孕妇自主选择倾向的经济利益因素
剖宫产由于手术费用以及产妇住院时间延长等原因,其医疗费用必然要高于自然分娩。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孕妇家庭对剖宫产费用承受力不断增强[8]。对很多孕妇来说,剖宫产费用与剧烈产痛相比,费用问题便构不成影响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医方角度看,如果没有政策引导,仅从经济原因[9]考虑,剖宫产手术也会成为较好的选择。一些医疗机构中助产士逐渐被边缘化,产科医生起着主导作用,这其中也存在经济原因,因为助产士看护产程的风险性和劳务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10]。总之,现有经济利益因素并不能引导孕妇偏向选择自然分娩,在这方面作必要调整应是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2.2 左右孕妇自主选择倾向的生命健康因素
剖宫产手术可能给孕妇或围生儿的生命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如剖宫产后子宫复旧、恶露持续时间较长[11],产妇切口子宫内膜异位及瘢痕子宫(降低再次生育自然分娩的可能性)[12],相对于自然分娩发生率较高的胎儿羊水吸入综合症、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13]、败血症、病理性黄疸,较低的视觉记忆和视觉结构能力[14]。自然分娩对孕妇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剧烈的产痛、因产程相对的不确定性而给孕妇带来的恐惧感等[15]。
在量上,前者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后者。但对孕妇来说,负面影响更多是从质上来感受的。当无医学指征的孕妇倾向选择剖宫产手术时,对她来说,自然分娩的剧烈产痛是确定的,而剖宫产中的妊娠并发症却是可能的,虽然其相对概率比较高(相对于自然分娩方式),但其绝对概率却仍然比较低(相较于剖宫产孕妇总数)。因此,应避免任何他者直接代替孕妇本人以其生命健康利益为由而直接排除其对分娩方式特别是剖宫产手术的自主选择权。分娩方式直接关涉孕妇个体的生命感受,这是他人无法代替的,理应得到足够尊重与同情。
2.3 现实中存在的对孕妇自主选择权的限制
2017年8月31日,一名待产孕妇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因伤势过重,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身亡[16]。其直接原因就是孕妇无法忍受剧烈产痛,间接原因就是她多次要求剖宫产而不得。在一些媒体报道中,孕妇家属与医方相互指称是对方不同意剖宫产手术。但作为读者,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孕妇本人做不了主呢?为什么她的意见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意见?如前所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是首先支持患者本人意见的。
无独有偶。2017年12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一名产妇产床试产三天,期间三次要求剖腹产,被医院拒绝,导致新生儿死亡,因医方对孕妇与胎儿状况判断有误,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最终医院被判赔61万元[17]。医院若以孕妇没有出现相应医学指征而绝对拒绝提供剖宫产手术服务,便会出现因判断失误而行为过错导致的执业风险。
“降低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本身内含着降低的方式方法,即通过健康教育、宣传正确分娩观念、提供更好的助产技术服务[18](如陪伴分娩、导乐分娩、非药物性镇痛等)、政策鼓励等途径来引导孕妇更多地自愿选择自然分娩。“严格掌握剖宫产医学指征”是医疗机构应承担职责,要通过积极引导而非简单拒绝来完成。类似“禁止或严禁无医学指征剖宫产手术”的规定不应出现在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之中,因为这样会让“积极引导”成为可以被省略的事。
3 进一步完善孕妇分娩方式选择机制的伦理建议
3.1 细化医学标准,完善运行机制
孕妇分娩方式的选择按孕妇与胎儿所处不同身心状况而有不同规则。从医方应否提出剖宫产手术医学意见,把孕妇的生命状况分为两大类,即有医学指征与无医学指征。对于无医学指征的孕妇,医疗机构要积极引导其自愿选择自然分娩。对于出现医学指征的孕妇,医疗机构会提出剖宫产手术的医学意见;这其中会出现少部分孕妇或其近亲属拒绝的情况,我们应进一步将医学指征剖宫产分为相对的与绝对的两种类型,对于前者,医疗机构应提供密切观察下的助产服务;对于后者,紧急时应动用医生处置权,或启动医学紧急避险机制。探讨医方在不同情形下采取不同处置方法的伦理基础,这属于分娩方式选择机制的价值性规范。而这些价值性规范的实现需要一套清晰的医学标准以及科学的运作机制。特别是医学紧急避险机制,其目的在于以防万一,不为常用,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轻易启动,因此该机制需要技术支撑,要有绝对剖宫产医学指征的医学标准,要有严格的实施机制;在实施机制上,除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的负责人签字的法定程序之外,或可增加“事后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备案”的程序,由其行使监督权。
3.2 增强引导力度,尊重孕妇选择
如果非药物性镇痛技术发展成熟并得以推广,能保证孕妇分娩时免于遭受产痛,且较少甚至无副作用,那将是从根本上解决无医学指征孕妇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的内心纠结。在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教育、引导、人性化助产服务等都是倡导自然分娩的必要努力。除此之外,或可适当调整医保与补贴政策,利用经济杠杆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