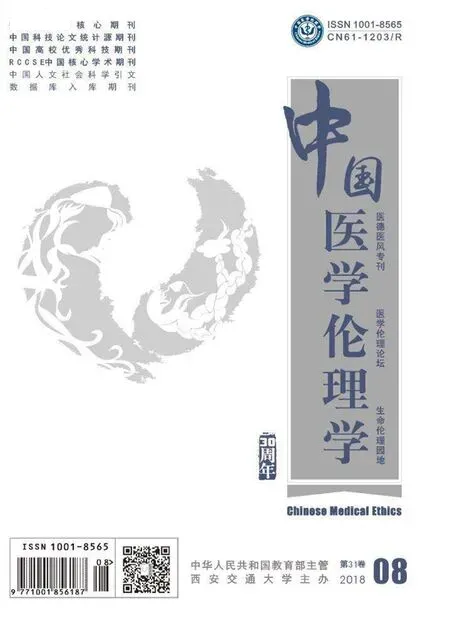信任:医患关系复杂性的简化*
焦 剑
(海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254063512@qq.com)
1 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信任的对立面是不相信、猜忌、怀疑和戒备。……信任产生于人们相互交往的伦理实践中,其基础是共同的事业与利益,以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与支持。”[1]正像尼可拉斯·卢曼所指出的:“在其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2]3。信任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你可以选择是否信任,但不可能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生活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我们可以认同卢曼的这样一个观点,把它看成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容置疑的真命题。正是因为有信任这一事实的存在,它自然就成为正确行为规范产生的根本根据。在对信任的思考历史上对此做过众多的解读,但在卢曼看来“尽管令人头晕目眩的观念有其用处,也可能有教益,但它们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4因此,对如何在医患之间夯实信任基础,通过采取一种较为深入的系统观解读当能为此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路径。
要探讨如何以信任来简化医患关系的复杂性,那就需要对信任进行解读。简单说来,对信任的研究分析通常并不是主要通过从主体之间互动的行为数据和体现出的知识蕴意之间建立的联系来实现的,各主体间的互动通常不是在(如果有的话)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内进行,而是通过将分析对象放在一定的多因素影响之下的可能性框架中来提升主体间将复杂性化简的能力,也就是一种系统观。由此,世界的复杂性与人对此的认识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如何在此两者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以满足个人对世界的调适,就构成了系统间试图在世界中维持自身平衡的问题。因此,复杂性就是世界的一种表象,世界是由众多系统所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且这种复杂的众像正日益增加,人类要想在面对复杂性的同时满足自身的个体需求就必须在不断提高的社会复杂性的条件下,“能够而且也必须发展出比较有效的简化复杂性的方式”[2]10。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信任本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哪里缺乏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行为复杂性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系统复杂性的膨胀,而信任就是能够简化这种复杂性的有效方式之一。
医学的发展是从单纯的天人之间的关系走到如今伴随着科技日益彰显的现代医学,是一种系统的、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个系统的形成过程正随着医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复杂。对于医学的发展来讲,它的目的的实现内含着两个最主要的执行主体:医生与病者,因为他们是“医疗决策活动的核心”[4]。医患关系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各自立场背后诸如专业知识体系、医学健康认知、医疗体制运行等方面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结果预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内含于医学系统当中的小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复杂的医学这个大系统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通常来讲,信任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医患之间一般来说是一种建立在彼此之间互不认识但又利益攸关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通过医患之间在就医过程中的互动,双方存在通过建立彼此之间的熟悉,克服相处过程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从而使得当下变得可控,未来变得可预测的可能性。因此,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信任的关系[5],而信任也正是通过内化于医患双方的互动之中来扮演医患系统的简化角色。通过信任来简化医患关系的复杂性,可以捋顺二者之间的关系,且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正如罗马时代的博物学家大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曾告诫的:“对医生,决不可掉以轻心。医生这种职业,就是以患者的生命为代价,来磨砺自己医术的。正所谓‘一代名医万骨枯’[6]。一旦治疗失误,患者受到伤害,医生总是将责任推给患者。”对这一信任问题的解决,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够将医学大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在医患关系这一小系统之间简化到最大程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2 熟悉的信任
显示信任就是预期未来,通过信任,时间仿佛就被克服,实际上信任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时间的克服,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关于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明确的给出方向性的指示,因此都是不充分的。对于信任来讲,当下是最重要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的可能性远远多于当下的现实性。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复杂不确定给人们增加了过多的思想负担,作为个体,他必须消减未来以适应现在。
但同时,工具性手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未来又带来一定的方向性,即确定性。即便如此,“人们不能期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事件处于控制之下,用对事物的控制取代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信任,因而使后者没有必要。相反,人们应当期望,作为忍受技术生成的未来复杂性的一种手段,对信任的需求与日俱增。”[2]22
医学发展历程中所采用的科技手段日益先进和复杂,这对于医患之间的异化作用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对于复杂性简化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强,而医患间的这种简化需要通过信任来降低。信任需要彼此的熟悉,熟悉进一步推动信任的建立,熟悉与信任是简化医患关系复杂性的一种互补方式。当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医患双方作为其影响下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医患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时刻处于变动中,这种关系的变动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控制这种复杂性的一种更大的需要。医患之间冲突的解决,需要以信任的建立来实现,而信任的获得首先是要建立在彼此间熟悉的基础上。前文提到,信任是一种期望,熟悉就是一种能够使期望产生的途径。医患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不仅取决于沟通的质量,也取决于沟通的时间(包括次数)。沟通的质量和时间会使得医患之间熟悉彼此的行为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熟悉必然会产生信任。就熟悉本身而言,熟悉既会产生有利的期望,也会产生不利的期望,进而可以看出,熟悉既是信任产生的前提,也同样是不信任产生的前提。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不熟悉,如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与应用(医生“红黑榜”)使患者对于医生的社会评价唾手可得,这是一种对于对方情报的搜集过程,过程的结果,不论是否公允地反映实际,都使得患者对于他想要了解的医生产生一种熟悉,但是这种熟悉却既可能产生不信任,也可能产生信任。这也就使得最终的决定取决于过去的表现,这正是卢曼所讲的“在熟悉的世界中,过去胜过现在和未来”[2]26。一般来说,一个令人满意的医生,通常在与患者的多次沟通之间会建立患者对其的一种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通过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而在患者之间形成一种认识,即过去的表现影响了现在的行为。患者通过对一个医生的通常认识所形成的依赖感,使得他会优先考虑某个医生过去的行为指向,以此来达到简化复杂性的目的,从而试图期待能够保证当前与医生相处情景中的安然无恙。
但是,信任的产生不单单是过去的结果,它更应该成为未来的灯塔。当然,在熟悉的情况下,患者才会对医生产生信任,信任绝不仅仅是过去的推断,它要冒险去界定未来。之所以会如此,恰恰是医学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当医学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时,整体上来看,它通常会伴随着发展带来的问题,而问题的出现会使得医学的发展失去原来的品性。患者和医生在面对日益高度发展的医学时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无法通过对于过去经验的传承来解决了,过去现在仅仅变为一种“预先确定的结构”,医患之间必须以信任为基础来形成一种新型的和谐互动关系,这种对信任的新需求的满足并不是指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无需熟悉做基础,而是指这种需要要求医患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能够再将陌生人排斥在建立互动关系之外。过去和未来对于当下的医患双方主体未必是经历者。当下的医患双方迫切需要回顾过去本人或他人的互动经历,并对未来做出预期,从而熟悉当下双方可能和应当采取的行为来避免误会,建立信任。
3 以信任简化复杂性的三种路径
当前在我国各大医院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医患之间总体满意度不高,如长时间的等候、医疗团队的非专业服务态度和恶劣的就医环境等[7],如何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就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讲,他们只有片刻的时间来了解在场时彼此间的言谈与举止,并有意识的据此调整自我以期能够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点。在这种情况中,患者病情的复杂性与医生某种医疗行为背后医学过程的风险性,对于医患双方来说,他们对对方的行为表现只有极为有限的了解,因而只能获得同样极为有限的合理性判断。如果患者愿意给与医生信任,愿意合作,这种合作也“不是马上得到回报的,也不是直接看得到收益的”[8]。
“只有在充满信任的期望对于一个决定事实上产生影响时,信任才算数;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希望而已”[2]31。也就是说,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投放,必须在医生一方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医生应当采取的诊疗措施的选择。反之,则是患者一方的简单希望而已,因为“信任虑及偶然性,而希望则忽视偶然性”[1]31。
因此,患者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行为,在医疗过程结束后回想起来是否正确,就取决于其对医生的信任是受到尊重还是遭到背弃。医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组织体系,但是对于患者来讲,不管这套体系如何完善,患者都不大可能对体系中行为人(即医生)的行动后果做出可靠的预测并使其放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最多可以用来解释赋予医生以信任的原因,而不是解释信任本身。信任仍旧是一种冒险的行动,信任带来的复杂性简化代表的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要求透明和承担责任。如何将医患间的复杂性进行简化,如何化解这一冒险性行为,以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从以下三种路径来分析:
第一,医患之间如前文所述,本身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因素,正因为如此,医患之间的沟通具有一定的内在确定性。而医学这个大系统随着它的发展而带来的不断变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则对医患之间产生一种倒逼压力。这种倒逼压力使得医患之间需要不断地调整彼此行为,但即便如此,医患之间的内在稳定性通常会表现出一种滞后的抗性,在这种抗性当中,医生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沟通医学与患者,医学体系与医患体系之间的唯一桥梁。所以,患者的信任,首先要来自于医患系统内部医生的支持,而不是直接地来自于医学体系的某种保证。无论医学如何发展,作为医生来讲,他需要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素养来合理地降低患者对于医学体系的变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当医生通过对患者进行自为的意思表示(言语、态度、行动等)来降低基于医学复杂性的不确定性时,患者才会将信任赋予医生。
第二,无论是医学系统还是医患系统,作为其中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对医生和患者来说,必须学会如何以信任来简化彼此间的复杂性,这是一种态度,不只是信任本身,还应该包括怎样信任。医患之间不应当通过彼此武装自己来应对各种可能性中蕴含着的复杂性的不可预期性,双方应该戮力同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合适的氛围来促成和维持相互的信任以减少复杂性的产生,这样的行为通常是有意义的行为。当然,医患之间信任的增加过程实际上也有可能包含着双重风险,如医生对于某种病情及诊疗方法或预后注意事项等信息的阐释,是否使得患者对此产生的信任达到了医生自身所设想的程度;患者是否会因为医生的某个言辞或举动而突然失去了对医生善意行为的信任。由此可见,医患个体间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其自身的信息,一般来讲总是大于医患各自所设想的要给与的信息量。因此,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医患之间有效沟通的可能性。医生与患者处于一种近乎难以逾越的信息不对称的境地,如果医患之间不能够进行合理、高效的信息沟通,就会产生类似“囚徒困境”那样的因信息沟通不畅而阻碍彼此信任建立的局面。因此,医患双方必须不断地反思自身行为来消除彼此之间的信任障碍。
第三,医患冲突的一个个事例实际上就是破坏医患信任基础的一记记重拳。在此种情况下,在医患各自内心中会形成一种用现象学意义上的“符号记忆”。对于医患双方,无论是哪一方付出信任,都必须对他自己所采取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时刻保持一种警惕之心。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一定的限度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信任决定。这种信任决定有可能因某种“符号记忆”而做出,也可能因某种“符号记忆”而取消。所以,必须减少医患冲突的发生率,如将医生的个体性审慎提升为整体性审慎以化解医患冲突[9],虽然一例医患冲突的事例都可能会加深“符号记忆”,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要进行“符号控制”,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建立和完善,加强对于医患间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来保障医患双方对于未来好的预期。
4 结语
通过建立信任关系,可以简化相应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任的建立就是问题的解决,信任只是一种复杂性问题的替代的表达方式,信任本身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带有危险性的复杂性问题。医学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医患之间通常不可能取得对方未来会做出的行为信息,为避免对未来信息产生误判,医患之间可以将这一问题转移到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的领域。这一领域通常来讲应当是法律的范围,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安排,它能够为特定的医学期望提供保证,使得这种保证成为任何长期考虑不得不构建的基础,它能够降低付出信任的风险。实际上,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信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种付出,谁想要赢得对方的信任,就必须综合行为、情感、态度、语言等众多因素来将他人的期待体现在他自己的自我表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