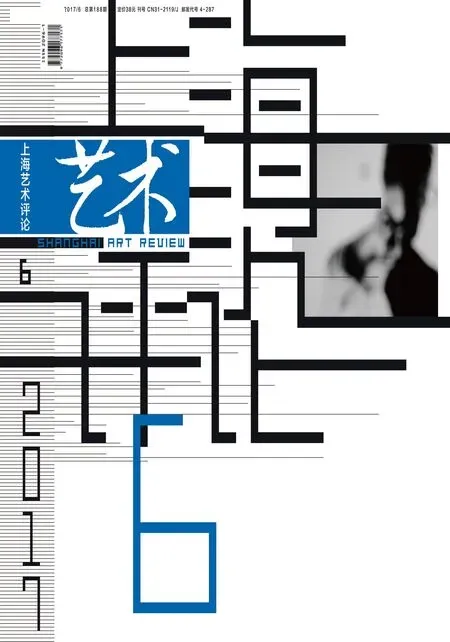文化视阈下的人性反思—评话剧《兰陵王》
刘 丽
剧作家的智慧在于,戏剧创作不只是善/恶、爱/恨、真/假概念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它刻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与人情,并对社会有着健康的引导,在剧场里震撼观众心灵的同时,也引发观众深入思考,传递社会正能量。因此,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定具备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厚的哲理思考,剧作家不仅仅是借助创作这一形式表达观点、启示他者,同时也是生命体验与深刻思想的传达。
2017年7月11日,话剧《兰陵王》首演于国家话剧院剧场,反响热烈,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认为该剧“充分体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当”。这出戏,旨在引发观众对于人性的深层次思考,并冀望于树立文化自信,让中国原创戏剧走向世界。
革新:从神兽大面到人格面具
话剧《兰陵王》里,“面具”在剧中具有双重内涵:既指兰陵王的“神兽大面”(实物“面具”),亦象征着兰陵王、齐后及先王旧臣所戴上的“人格面具”(隐形“面具”)。对于前者(先王留下的神兽大面),既是一种显性存在,也是一种象征。容貌秀美的兰陵王,不着大面是齐主宫中豢养的伶人,是懦弱的羔羊,听任齐主羞辱、欺凌;戴上神兽大面后则统帅将士,征战沙场,是骁勇异常的狼。“大面”把兰陵王分裂成了两个人:“这副大面,甫一戴上,便觉力大无穷,只想厮杀,可是一旦脱落,顿时心慌意乱,斗志全消。”这副大面具有难以言说的神秘魔性:既使他神勇异常,亦令他迷失自我。乃至于刺伤母亲,禁闭先王旧臣,辱骂情人,怀疑好友。在他的灵魂深处,隐忍、孤独、压抑、痛苦。当失势的齐主手持利刃刺杀凯旋的兰陵王,郑儿为他挡去利刃时却被洞穿,临死之前,郑儿提出观其真容(即没有失去正常心智的兰陵王),大面终难卸下(象征异化的兰陵王);齐后为把他“恨的深渊”来“用爱填平”,针簪刺心,用“爱”的血液融化了兰陵王的“恨”,大面自行脱落。母亲的血终于换来了和解,回归本性的兰陵王认回了母亲。这是实物“神兽大面”的威力,当然,剧中还有另外一副面具,是看不见但隐形存在的,即“人格面具”。
剧中,不仅兰陵王戴着“人格面具”踽踽独行,齐主、齐后以至左仆射、右丞相、艺伎郑儿、宫廷伶人们,在尔虞我诈的残酷环境里,都戴着面具小心翼翼地活着。其中,塑造最有力、拷问人性最深的,无疑是主人公兰陵王。十余年前,叔父(齐主)觊觎先王(齐主之兄,兰陵王之父)之位,窥伺良久,在兄长的酒里下了鸩毒,御厨献食,兰陵王母亲不明真情,为丈夫斟酒,先主饮酒暴毙,齐主为封口刺死御厨,遂自立为王,以掐死先王与齐后之幼子(兰陵王)为由,威胁齐后委身自己。为了幼子生命安全,齐后忍辱嫁给齐主。躲在帷幔后的九岁少年兰陵王,将一切看在眼里,为了自保并寻求机会复仇,麻痹齐主的警惕之心,收起善剑尚武的一面,在宫中做了弄戏唱曲、卖乖邀宠的伶人,供齐主取乐,戴上“假面”活着。这一副面具,即荣格所谓的“人格面具”,既具有积极作用,亦存在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在于:兰陵王如若想在暗藏杀机的宫廷里生存、活命,必需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得以保证他与嗜杀成性的齐主和睦相处,从而能够自救,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深藏一颗须眉之心:“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兰陵王,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须眉。须眉,娥眉,为了在宫廷里存身,谁又能真正看透我的心思?我就是存心这么笑着、疯着、忍着、等着,等到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要堂堂正正地做回男人,不,男人中的男人,那是什么,英雄,对了,英雄!”这副人格面具可以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使他成功摆脱齐主的监视,以区区八百骑将击败大周五万兵马,收复洛阳,刺死齐主,报仇雪恨。“人格面具”的消极作用在于,在宫中险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是紧张的、防范的狼与狼关系,狼性远胜于人性,长期的警惕心态使兰陵王迷失了自我,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扮演的伶人角色,逐渐与自己的善良天性疏远。他爱上歌舞伎郑儿,面对齐主的强权却不敢、不能保护她,因而被母亲齐后啐面;他痛恨母亲嫁给鸩杀父王的齐主:“每当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在杀父仇人面前恭恭敬敬温柔小心的样子,我就恨不得冲上去唾你骂你,恨自己竟有你这个母亲!”不仅痛恨母亲的选择,不能理解母亲的权宜之计与救子之心,对先王旧臣尉迟琳、左仆射、右丞相亦难再信任;一旦大权在握,比齐主还要冷酷、嗜血。在狰狞的神兽大面和变形的人格面具之下,藏着一颗被屈辱、孤独、哀伤、怨恨反复侵蚀而压抑、扭曲、异化的灵魂。
历史上的兰陵王形象,貌柔心刚,戴上大面后骁勇异常,被视为完美的“英雄”,无形中被“神化”了,几同于“神”一样的存在;话剧《兰陵王》则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创造了一个负着创伤、怀疑世界、怀疑人生的有诸多瑕疵、复杂的“人”,他身上存在着人性的种种弱点:既懦弱又残忍,质疑爱情、亲情、友情,怀疑人生。这样的兰陵王复杂而真实,这才是真正的“人”,直逼人性,连接时代,通向未来。剧作家并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而是着力于创造艺术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这样的“人”,是有血有肉、真实的人;这样的剧作,是真正的“人的戏剧”。
反思:从人性批判到文化担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是人与权力关系的总和。在专制体制的挤压之下,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因而感到压抑、窒息,自我、个性不复存在,“如何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压力,丧失主体意识在所难免。在荣光/卑鄙、高大/渺小、君主/奴隶之间,人疯狂追逐前者,既被掌权者奴役,又期待自己握有权力,在此意义上,人是权力的奴隶。话剧《兰陵王》里,齐主疯狂追逐权力,丧人伦、灭人性,兰陵王戴上大面之后亦如此。整出戏,刻画了在“权力”面前萎缩的“人”,反映了中国人文化、思想、性格和命运的特质,批判了反常、扭曲的人性,意在建构一种健康、理想的人性。

话剧《兰陵王》(摄影:祖忠人)
剧中,齐主窥伺兄长王位,不仅鸩杀之,占有其王位,掌握权力后,以杀掉侄子兰陵王为条件胁迫、占有兄嫂,宫廷上当众杖杀大臣,以阉割兰陵王为条件威胁皇后收回“后悔做了陛下的皇后”这句话,以维护自己的威权,强调其作为王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皇后护子心切,惶恐地跪地求饶时,齐主则“(扶起她,心满意足地)皇后起来,其实朕就是想看看,有谁胆敢藐视朕,胆敢挑衅朕的威严。”在威权面前,齐主弑兄霸嫂,践踏人伦、道德,蔑视亲情、爱情,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这样的文化,当然是反常的,也正因此,残暴的齐主最终被兰陵王刺杀身亡。这是剧作家着力批判的文化;当然,批判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构:齐后用生命、鲜血重新唤回了兰陵王的真诚、善良与爱,兰陵王的怨恨最终在母亲的自杀里逐渐消解、冰释,爱与善的本性重新回归。人对权力的追逐、觊觎、窥伺,在权力面前丧失正确的判断力、思考力,是人性失去理性的后果,善/恶、爱/恨之间,剧作家诠释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于兰陵王这一形象,悲悯情怀使剧作家从“同情之理解”的创作心理出发,从权力的受害者到孤独的王者,从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到嗜杀成性的豺狼,再到郑儿、母亲的劝诫、离世,使兰陵王幡然醒悟、悔恨、愧疚,承载着中国文化(政治、权力)的兰陵王,与其丰富、复杂的人性融为一体,从舞台上这个未被“神化”的躯体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光辉。
剧作家的智慧在于,戏剧创作不只是善/恶、爱/恨、真/假概念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它刻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与人情,并对社会有着健康的引导,在剧场里震撼观众心灵的同时,也引发观众深入思考,传递社会正能量。因此,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定具备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厚的哲理思考,剧作家不仅仅是借助创作这一形式表达观点、启示他者,同时也是生命体验与深刻思想的传达。
编剧罗怀臻首次涉足话剧领域,意在“溯源中国传统戏剧模式,把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应用到当代文艺创作中……回归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重新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同时将中国戏剧与世界接通是当代戏剧人的使命”。《兰陵王》以合理的历史虚构超越了历史本身,消解了戏剧创作中惯常使用的宏大叙事,弱化政治色彩(仅仅将其作为叙事背景),不局限于探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再执著于人物“忠奸两分明”的武断,而是从人物内心出发,关注人物生存的环境对人物生存、命运的影响,由表入里,探寻人物形象幽微的内心世界,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把握人物复杂的内心。在剧作家笔下,人物形象不再是抽象、模糊的符号,而是有意去除类型化、概念化的标签,关注人性、人情,同时引导观众发现“人”,发掘历史与现实的相通之处,在创作时将传统与现代融合,文辞与情志融合,写实与写意融合,木偶、面具等道具的使用,使这出“历史寓言剧”彰显出典型的“中国风格”:一度创作(思想性)与二度创作(舞台演出)的完美结合,人性真实与现代精神的契合,才是舞台上真正的“文化担当”,即“中国意象的现代表达”——“要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传递哲思的完整过程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传统戏剧的美学意蕴,要充满中国情感和中国文化内涵,更要表达当代观察和当代哲理思考。”
探索:从中国原创到走向世界
6月22日,在《兰陵王》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曾说,剧院秉承“中国原创、世界经典、实验探索”的创作理念,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创排《兰陵王》,是“希望通过艺术家们的表达,让《兰陵王》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戏剧110周年来的成熟与发展。”发挥剧作家创作的主体性,跟上现代都市文明发展的步伐,是中国戏剧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话剧《兰陵王》在同类作品中可谓光彩夺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现代化与都市化实践。2004年,编剧罗怀臻在《重建中的中国戏剧——“传统戏剧现代化”与“地方戏剧都市化”》一文中曾言:“中国传统戏剧或地方戏剧必然地要依附在中国社会的当代背景中,而当代中国正在快速地实施着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国戏剧不可能脱离这个大背景和大趋势而孤芳自赏,它也必然地要被时代负载着前行。”这里所提到的“戏剧现代化”,实指戏剧的发展必然要跟上现代都市文明的步伐,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只有不断地尝试、探索,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现代戏剧生长的土壤。《兰陵王》即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人物,重点在于表现权力对人的扭曲和异化,契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价值观,但它的最终旨趣仍在于追求戏剧的传统意蕴和传统美学价值。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代性,认识其本质追求,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形式的关系。
二是“案头剧”与“场上剧”的综合。《兰陵王》是名副其实的“剧场戏”,早年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使剧作家在创作时将文本与表演紧密结合起来,一度创作时即已考虑到舞台演出的需要,心中有演员、有舞台,从结构、人物到道具安排,每一个环节都为表演提供足够的发挥空间,从而更好地推动舞台演出,烘托舞台效果。该剧导演王晓鹰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寓言”,在舞台上融入傩戏、傩舞,多次使用象征手法,“追求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传递哲思的完整过程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传统戏剧的美学意蕴。”《兰陵王》从舞美、灯光到形体、服装、音乐设计等,进行了革新和实验,力求将中国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如服装设计融入戏曲元素,水袖的运用别有韵味;音乐设计里尝试加入西凉乐龟兹乐元素,侧重表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融合;“面具”在傩戏、傩舞中的使用,本身就是重要的舞台元素,曾参与《伏生》等剧目面具设计的张华翔,为了增加舞台效果,使面具兼具艺术性、历史感与实用性,前往日本实地参观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能剧《兰陵王入阵曲》传统面具,寻找创作灵感,但对于传统面具的借鉴“绝不是照搬,在设计过程中,他还融入了中国戏曲始祖‘傩戏’面具的特点,力求让每一件面具都成为极具古朴美又不失现代感的艺术品。”
但若要其“走向世界”,舞台演出的形式美固然重要,一度创作必须有超越时代或者引领时代的力量。《兰陵王》是一出严肃戏剧,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而转向人物的内心(即“向内转”),对人物所生存的外在环境(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对人的挤压、扭曲,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悲悯,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挖掘,创造了一个丰富的“人的世界”,兰陵王的正邪两赋,齐主的凶狠残暴,齐后的忍辱求全,他们心理上的斗争、激荡,人性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坚守抑或转变,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如兰陵王的犹疑、脆弱、敏感,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但同样设计了复仇情节,兰陵王的行动又与哈姆雷特截然不同。《兰陵王》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在宽广的艺术领域内是相当开放的,由此带来的审美意蕴也是多重的,也因此,这样的剧作是人类的、世界的,而不单单是中国的。
《兰陵王》至少为戏剧界提供了以下思考:如何丰富史剧的思想内涵,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类型化评判,着力于刻画人性与人情,使其“人归人”,而非夸张的神、魔对立,诠释着温和、悲悯的人文关怀;如何彰显创作主体性,解构所谓的“历史真实”,延展剧作家虚构与想象的空间,突破传统戏剧创作的表现形式,尝试多种创作手法,傩戏、木偶戏、曲艺/戏曲等多种传统艺术手法的融入使舞台生动、空灵,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情怀;如何体现戏剧的现代化与都市化理念,紧跟时代,契合当代审美精神,体现出走向世界的宽广襟怀和格局。由上观之,话剧《兰陵王》的路,将会走得更久,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