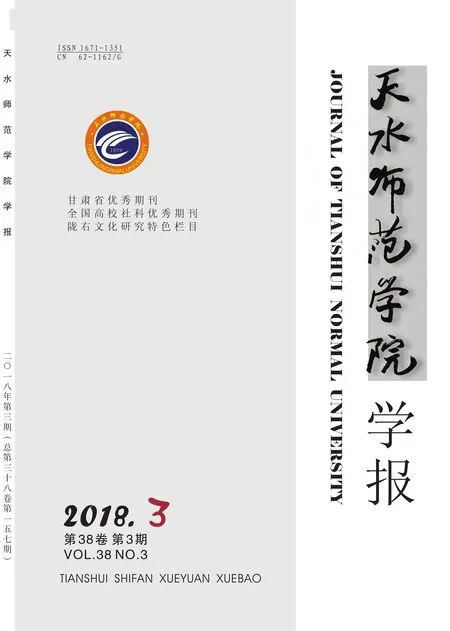论汪泉生态小说的环境想象
吴 哲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环境想象”是劳伦斯·布伊尔探究生态危机问题的起点。布伊尔认为,环境危机包含着一种想象的危机,所以解决环境危机需要找到想象自然以及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最佳方式。[1]2布伊尔探究了地方的情感意义及生态意蕴,将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压缩到地方话语空间中,进一步丰富了环境想象理论的内容。布伊尔指出,环境文本对环境的再想象有利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文学激活人们的地方依附意识,培育人们的家园情怀,引发读者关注和拯救“濒危的地球”。总的来说,布伊尔的批评理论采用文学想象的新视角,引导读者转变环境观念和生态立场,帮助他们培养绿色的生态价值观。
汪泉,1970年出生于甘肃古浪,他的文学创作着力反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汪泉有诗集《父亲的尘土》(1993),长篇小说《白骆驼》(2005)、《沙尘暴中深呼吸》(2006)、《西徙鸟》(2009)、《枯湖》(2013)等。其中,《沙尘暴中深呼吸》获第二届黄河文学奖,《枯湖》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汪泉的生态小说刻画“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反思生态危机时代西部地区民众的迁徙和生存。从《白骆驼》《沙尘暴中深呼吸》《西徙鸟》再到《枯湖》,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恶化逐渐成为汪泉小说环境想象的深刻主题。汪泉通过想象西部的自然环境危机来反思人们的栖居困境,呼吁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实现重建家园的目标。
一、环境想象的景观呈现
从生态文学的发展来看,生态文学并不局限于表现自然,而是侧重于探究“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从环境文本的内容来说,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产物,文本中的环境是现实环境和作家想象中环境的结合。古浪以北是腾格里沙漠,以南是祁连山,这为汪泉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现实的生态空间。汪泉以古浪地理环境为原型,利用朴素的生态景观进行环境想象,直面西北农村现实的生存困境,立足于严肃而现实的立场来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汪泉小说的环境想象表现为:对乡村自然的诗意想象和对荒芜田野的真实描摹。汪泉在想象西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注意虚实结合,所以他的小说既呈现了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区的自然景观又预警了西部的环境危机。
汪泉的生态小说勾勒了诗意的乡村自然景观,暗示西部严峻的环境危机。小说《枯湖》描写了西部的湿地景观:“浩瀚的水面上倒映着瓦蓝的天空,远远看上去像一面凸起的镜子,镜子里有一房子高的芦苇,芦苇丛中有无数的水鸟,……。”[2]3《西徙鸟》中有美丽的雪山、森林、草原景观:“皑皑白雪下面是茂密的森林,森林之下是绿油油的草地,绿油油的草地下面又是金黄的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间或还有翠绿的麦田。”[3]43《西徙鸟》中也有大地景观的描写:“纯纯的黄土啊,就像油拌的炒面一样”。[3]115汪泉笔下的湖泊、草地、雪山、森林等自然景观既是作家焦虑西部环境的情感外化,又是作家想象西部环境的诗意产物。汪泉对昔日猪野泽的环境想象勾勒出风光旖旎的西北乡村,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从生态美学观的角度来说,只有人们主动地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平等地对待自然万物,才有可能重新栖居在大地上。从生态整体观的角度来说,雪山、森林、湖泊、草原等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人们尊重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组成部分,尊重自然生态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汪泉的生态小说在反映西部环境危机的同时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面对乡村社会的转型,作家叙事的疆域由传统的乡村日常生活向乡村生态、城市生态等领域拓展,作家笔下的乡村日常生活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景观。[4]6《沙尘暴中深呼吸》反映了沙尘暴过后的村落和小城敦煌:“正如一幅永远读不懂的抽象风景画,色彩和用笔杂乱无章,但主色调是以苍白的绿色为主。”[5]267《西徙鸟》描写凋敝的雪山、森林景观:“玛雅雪山的华服也在日渐破旧,甚至烂掉,昔日充满鸟语花香的林阔像老人的头发一样。”[3]80同时,汪泉也反思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对草原生态景观造成的破坏:“无尽的草原一片沉黑,被烧焦得草场到处是一点一点的灰黑,就连最为坚韧的芨芨草也只剩下椭圆的黑根了。”[3]170汪泉的生态小说揭示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沙尘肆虐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的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对立、冲突的关系。
汪泉想象西部生态环境危机是为了思考造成“人与环境”紧张关系的原因。首先,从自然生态的维度来看,地处石羊河流域的古浪是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多风与干旱同样影响了自然景观的形成。其次,从社会生态的维度来看,《沙尘暴中深呼吸》和《西徙鸟》集中反映了商业文明带动乡村自然资源的开采,滥砍滥伐加剧西北的环境危机。从精神生态的维度来说,物欲蒙蔽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忽视了土地沙化、水源污染、沙尘肆虐等造成的生态后果。事实上,潴野泽的生态移民不爱惜生养他们的土地,当无知的人们随心所欲地践踏自然时,自然也会给他们以惩罚。汪泉面对社会转型期凋敝的西部乡村表现出了严重的环境焦虑。他想象潴野泽、黑沙窝、饮马湖区的环境危机,就是呼吁人们重新认识西部的生态处境,重新思考环境危机时代西部如何处理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环境想象的地方依附
布伊尔认为从文学出发的环境想象可以唤醒人们的地方依附意识,这种意识既能帮助人们认识地方的局限性,又能塑造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1]253地方依附传递“地方养育我们,我们依附地方”的生态理念。地方依附强调人融入地方,这种融入包括了情感依恋和身份认同,表明“人和地方”关系密切。从情感维度来说,地方依附体现为人对某地的情感依恋。这种依恋可以内化为一种家园意识或者地方意识。从物质生存的维度来说,地方依附强调保护地方的重要性,因为地方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场所和资源。汪泉的生态小说《沙尘暴中深呼吸》《西徙鸟》《枯湖》等深刻地阐明了地方依附意识对于人们实现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汪泉生态小说的深刻主题是:只有人们懂得如何合理地依附地方,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小说《西徙鸟》《枯湖》中,汪泉将居无定所的生态移民想象成一群群的候鸟,迁徙是他们永远的宿命。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水资源短的缺导致人们纷纷逃离地方。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困境,汪泉笔下的生态移民撕裂了人与地方的血肉联系,他们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谋生方式加剧环境危机;再者,生产方式的改变影响了生态移民对环境的认知,从春种秋收到砍树挖草,从爱护环境到破坏环境,地方对人们的意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小说中的生态移民来说,雪山、森林、草原不再被看做家园,仅仅想象为谋生工具。汪泉的生态小说揭示了地方依附的本质就是要认识到地方的局限性。干旱缺水是以猪野泽为代表的西部农村的显著特征,因此水源是人们生存和发展之本。也就是说,生态移民依附地方要以保护水源为前提,人们必须切实地保护雪山、森林、湿地。《西徙鸟》中,汪泉想象了干涸的湖泊、满目疮痍的雪山、千疮百孔的草原,指出生态移民破坏了生存和发展之本,所以无法实现永续发展。汪泉也细腻地刻画了生态移民难以融入地方的生存体验,执著地探寻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区的生态移民来说,雪山、草原、森林和湿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和依附的根本。雪山提供农业、生活用水,森林防止水土流失,草原阻止沙漠蔓延,湿地改善水质。汪泉认为生态移民真正地依附于地方必须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可持续地利用地方的自然资源,身体力行地保护雪山、森林和草地不被污染和破坏。
汪泉的生态小说强调地方依附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人们依附于地方建立一种归属感,这种情感体现为:首先,生态移民必须在情感上认同地方,但又不局限于地方。这就需要人们在理解地方的过程中主动地形成保护环境和家园的意识。同时,对地方的深刻认识意味着在理解自然生态的同时形成对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认知。对于汪泉想象中的生态移民来说,不管他们的年龄、文化、身份,又或是去往玛雅雪山、敖日格勒大草原还是张吴李家湾,他们都应该坚定地守护脚下的一草一木,重视人与大地的亲缘关系。所以,生态移民不仅仅要保护他们生长的那片土地,更需要认同自己实实在在所处的那块地方。汪泉的生态小说倡导人们认同地方的山山水水、草木虫鱼,同时也要认识到:“个体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也是山川河流的‘我’、生态的‘我’、自然万物的‘我’。”[6]91其次,生态移民要将地方依附内化为地方意识。因为地方依附体现为人依赖于地方,而地方意识更加强调人们主动承担起保护、回馈自然的责任。面对《西徙鸟》中被破坏的森林、草原、雪山和湿地,生态移民们必须用自己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取代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必须用符合生态伦理的行为去缓解人与自然岌岌可危的紧张关系。[7]252汪泉的生态小说重视地方依附的生态意义,反思人与地方之间的必要联系,强调依附于地方的前提就是保护地方,呼吁人们树立保护地方环境、可持续利用资源的生态意识。
三、环境想象的家园意识
当代生态审美观照中家园意识的提出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精神危机使人们产生一种普遍的无家感。[8]19面对西部生态环境危机,汪泉倡导从地理、心理和文化上建构家园意识。重新入住家园不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回家。因为家园是人们生存繁衍的重要场所,只有在家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安顿,所以保护家园是人们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存在论美学来看,家园意识最早体现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返乡》的审美阐释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返乡”就是培养家园意识的过程,“返乡就是回到本源近旁”。[9]24家园的本源就是大地,所以家园与自然环境具有天然的联系。具体来说,汪泉生态小说中的家园意识是指在生态危机愈加严重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文学想象思考如何重新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化家园的生态内涵,探索生态移民重新栖居的可能性。
家园意识强调立足地方经验,因为大地上的劳作经验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塑造了人们对家的归属意识。家园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所以人们会在诗意栖居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汪泉笔下风光旖旎的猪野泽是生态移民永远向往的家园,是生命繁衍和诗意栖居的场所。在这个地方,人们保留有朴素的生态意识。在汪泉的生态小说中,家园意识常常表现为对猪野泽、黑沙窝特有的自然景观、四季变化、春种秋收的深刻体验。汪泉想象昔日充满生机的草原、森林、湿地,想象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表明家园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感受。汪泉的生态小说也反映了猪野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因素对生态移民的身体和心灵产生重要的影响。雪山、草地、森林的破坏导致生态移民与猪野泽关系的破裂,造成他们无家的茫然,迁徙路上的孤独和异化。家园意识的淡薄同样表现为生态移民对破坏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无知和轻视。《西徙鸟》中,生态移民破坏了自然环境,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只能走上候鸟式的迁徙之路。汪泉想象西部的生态环境危机,目的就是唤起人们心底的家园意识。家园不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家,它更意味着人们能够在此处获得理解和认可。所以生态移民不仅需要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及人文环境,而且也要树立家园责任感和生态伦理意识。
汪泉将身体和心灵都无处安放的生态移民形象地比作候鸟,反映了家园意识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家园意味着个体进入新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区域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并找到情感归属。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有利于促进身份认同,从而激发人对家的归属感。对现代人来说,寻找栖居之所即寻找可以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家园。汪泉的生态小说反映了环境危机导致生态移民的精神困境。这源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影响人们对家园的认知,因此他们习惯性地陷入家园失落之中。对不断迁徙和寻找家园的生态移民来说,“候鸟式”生存方式的根源在于缺乏认同意识,破坏和迁徙使人们陷入无根感;生态移民盲目地谋生存,以致在任何新的家园都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汪泉想象生态移民即使逃离了潴野泽,迁徙于玛雅雪山、敖日格勒大草原、张吴李家湾,终究不能摆脱身份认同的焦虑。《西徙鸟》生动的隐喻说明不论生态移民迁徙到何处,当身份认同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个人或群体就会永远奔走在迁徙的路上。汪泉想象家园的失守所引发的栖居困境,揭示了生态栖居是重建家园意识的重要前提。
从浅层次上看,汪泉生态小说中的家园意识体现为保护自然环境,爱护生态家园。从深层次上看,家园意识就意味着人本真存在的回归与解放,即人们的身体与精神回归到澄明。[10]6汪泉生态小说中倡导家园意识的现实意义就是呼吁人们有意识地承担起修复家园生态环境的重任。重新入住家园并不仅仅是保护环境,更加要求激活地方的生态智慧。在对自然环境和土地的再认识和修复过程中,人们还必须转变传统观念,提倡一种绿色和谐的生态文化。这就意味着个体的生态栖居须与自我身份认同达到和谐,意味着个体在精神和情感上认同自己所处的大地。家园意识就是深化以家园为中心的情感认同,因为家作为一个情感地理空间,人惟有身心俱在其中方能得到安顿。作家深刻反思“人与家园”的基本关系,强调家园意识引导个体的身体和心灵回归本真。汪泉的小说也暗示了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人们失去了对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处于普遍的无家感和身份焦虑中,所以家园意识对于茫然的现代人来说意义深远,有助于他们重新理解“诗意栖居”的本真意义。
四、环境想象的绿色启示
人们对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的文学想象会改变其思想观念,进而引领其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11]73环境文本想象恶劣的生态环境,想象生态危机时代的家园毁灭,其根本目的是呼吁人们转变环境态度,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维护可持续的绿色家园。因此,环境文本想象环境危机不仅仅是预警生态灾难,想象也是为生态移民寻找修复生态环境的方式。
汪泉生态小说的绿色启示就是敬畏自然,保护环境。《西徙鸟》中,作家想象了丧失敬畏之心的生态移民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过程。潴野泽的生态移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找到赚钱的营生。他们不加节制地砍树伐林、挖草皮卖野菜、过度开采地下水,为自己的利益牺牲了雪山、草原和森林。结合当下,对于失去家园的生态移民来说,“无家可归其在世的基本方式”。[12]316这就是一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存方式。从土地伦理的角度来说,人与自然是互利共生的有机整体,雪山、草原、湖泊、森林与个体生命具有血肉联系。在大地上,人与自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有密切关联,所以敬畏自然就是爱护生态家园。《沙尘暴中深呼吸》中,汪泉塑造了防风固沙的绿色英雄毛老汉,呼吁人们像毛老汉一样坚定地保护家园,担起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绿色使命。但是,更多的生态移民把掠夺自然资源作为谋生手段,所以他们漠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实。《西徙鸟》中的生态移民表面上无所顾忌,实质上忽视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考量,违背了土地伦理和生态法则。因此,重建西部的绿色乡村首先要转变人们的生态观念,敬畏自然方能受惠于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方能实现诗意栖居。其次,重建家园就是要求人们将植树种草、防风固沙、节约用水的绿色理念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汪泉的生态小说反思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异化作用,认识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作家想象环境危机时代生态移民“候鸟式”的生存方式,反思工具理性如何摧毁生态家园。从潴野泽的水源污染到玛雅雪山的滥砍滥伐再到张吴李家湾的地下水枯竭,生态移民破坏自然的谋生方式无法改变其迁徙的命运。同时,汪泉的生态小说也反映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于地方环境的影响。“有了铁锨,土地就活了,活了的同时,却又在死去。”[3]189工业文明复活西部乡村经济的同时也间接破坏了西部的自然环境。《西徙鸟》反映了工业文明造成了人的物质化,生态移民以金钱去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意味着他们与家园纽带关系的断裂。从生态中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说,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并非以消费为基础的“我——它”,而是以亲缘和责任为基础的“你——你”。[14]126《西徙鸟》的生态启示就是发展西部的乡村经济必须走以保护环境为基础的绿色发展道路。汪泉倡导人们“做‘环境卫士’,……自觉自愿地不干扰环境,不随意地、不专断地改变环境,不剥削环境。”[13]222西部人必须深刻反思环境和栖居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认识修复生态环境、重建绿色家园对于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汪泉呼吁人们积极培养家园意识,树立地方责任感,身体力行的践行绿色理念,坚定地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汪泉想象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区的河流、湖泊、雪山、草地,并不是为了诗意地回忆过去,而是试图表达一种对西部深切的环境焦虑。汪泉注意到人们对物质、自然的占有欲会加剧环境危机。作家也认识到工业文明影响了西部人的环境观念,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淡化了人的家园意识。汪泉希望西部人坚守敬畏自然之心,重建生态家园。从表面上来说,重建家园就是修复和保护生态家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深层上来说,重返家园就是精神生态回归本真,建立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稳定的绿色关系。汪泉的生态小说创作自觉致力于抗拒人类中心主义,而试图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汪泉倡导一种绿色的创作观念,西部文学不能局限于沙漠、戈壁书写的窠臼,而要在描述传统的西部经验的过程中重塑生态观,为解决普遍性的生态问题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