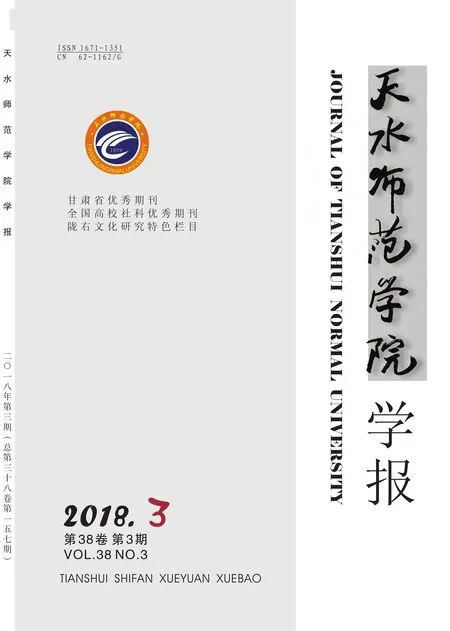当代藏族小说讲述的“中国故事”
白晓霞
(兰州城市学院 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新时期以来,当代藏族小说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小说,更有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尘埃落定》,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放生羊》,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还有大量藏族小说获得了骏马文学奖、全国梁斌小说奖等其他奖项。这样的创作实绩,既展示了藏族小说作家主观的实力与努力,也客观展演了藏族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版图有机组成部分的魅力与特色。小说是文体家族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骨干力量,尤其是长篇小说,以其巨大体量、多元内容、宏大结构与社会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折射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当代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数量已经较多,也初步形成了代际样貌,如降边嘉措(《格桑梅朵》《最后一个女土司》)、益希单增(《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益希卓玛(《清晨》)、才旦(《又一个清晨》)、班觉(《松耳石》)、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阿来(《尘埃落定》《空山》《瞻对》《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祭语风中》)、尕藏才旦(《首席金座活佛》《红色土司》)、央珍(《无性别的神》)、梅卓(《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白玛娜珍(《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尼玛潘多(《紫青稞》)、格绒追美(《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青藏辞典》)、达真(《康巴》)、江洋才让(《康巴方式》)等作家,都有代表性长篇小说问世。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涉及到了革命历史叙事、族群叙事、部落叙事、家族叙事等等),手法多样(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有不少作品生动讲述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体现出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情韵和五彩风度,闪现爱国主义光辉,是卫藏、安多、康巴等地的藏族作家共同谱写的或团结奋进或温暖和谐的中国好声音。
一、中国民族地区新公民形象塑造:社会主义新中国公民的故事
中国小说素有重史的传统,“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藏族小说在80年代就是以革命历史小说走上了中国当代文坛。被视之为“报春燕”式的作品都有关于翻身农奴的中国故事,如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作品分析出人物生活苦难的原因是农奴制度,人物在对共产党的政治归属过程中渐次脱离了旧的束缚,反对旧制度的过程中也与传统的母族信仰文化发生了背离。作品中的人物不再相信“天命”,认识到了保证其幸福生活的是现代新型的政治力量。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以农奴边巴的政治成长为叙事主线之一,农奴边巴孤苦伶仃、一无所有,而且被道貌岸然的农奴主文化借助于民间文化以所谓驱“鬼”进行打击和驱赶。在这样的绝境中,进藏的解放军给予了边巴全新的政治生命,于是,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终于觉醒,参了军,救了自己,也为同胞指出了正确的出路。益希单增《幸存的人》中的女农奴德吉桑姆也是如此,受尽凌辱,反抗无效,被当作“妖”扼杀,结尾处侄子桑节普珠终于觉醒,开始追随解放军的脚步,曙光来临。
这些都是从社会政治时空视角去讲述的“新中国故事”,其上有着饱满的中国力量,故事中的藏族人物也以“社会主义新公民”的全新角色而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鲜活元素。
民族作家热情讲述中国故事的动因有两个,一是自身的政治经历。新中国的成立,贫苦农牧民的解放感动了民族作家,使他们产生了书写新人新事的主动性。降边嘉措12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藏的过程中,看到了老百姓在旧制度下的苦,感受到了党给予藏族同胞的温暖,“这段生活,成为我后来写作《格桑梅朵》的生活基础……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冲动。”[1]1951年,降边嘉措跟随部队进入西藏,是中国共产党重点培养的优秀翻译家,青年时期就为班禅等西藏宗教界领袖担任过翻译,也和周恩来等党的高级领导人有过近距离接触。复合的政治素养为降边嘉措带来了极强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多次真诚表示“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在一起的。”[2]二是个人的文学修养。多数藏族作家是在《红岩》、《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等“十七年时期”的汉语红色经典的启蒙下开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公民的故事”书写,如降边嘉措所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新儿女英雄传》,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大家坐在帐篷里,我请他们给我讲革命故事,讲小说里的故事。……那本书差不多让我磨破了,我也开始爱上了文艺。我觉得可以从文艺作品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慢慢地,我自己也想到要写小说。”[3]红色文学作品构筑了文化空间,浸染了作家的主体性意识,启发作家主动书写民族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
有评论家曾将《格桑梅朵》(降边嘉措)、《幸存的人》(益希单增)、《清晨》(益希卓玛)的三部小说称之为“三部曲”:“三部小说在叙事时段和内容上相互衔接,分别通过抗争、进军、剿匪“三部曲”,形象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进程。”[4]这一藏族革命历史小说三部曲,是藏族群众从被侮辱被损害者走向解放了的新中国公民形象的生动记载。这类“成长小说”意义重大,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人民的新生,讲述着“新中国新人物新故事”,既具有开创崭新历史的意义,也具有指引光明未来的作用,是藏族作家以赤诚的中国之心讲述的生动的中国故事。诚如巴赫金所说:“在(成长)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成长的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的传记中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5]文学史家也曾这样总结过上述藏族小说的意义:“长篇小说创作的崛起和成就,改变了建国以来没有藏族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的状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同时,也使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第一次在建国后的本民族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6]
二、“祛神秘化日常写作”:改革开放的中国藏地村落故事
21世纪以来,在对西藏文化“祛神秘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讲述村落故事的藏族小说作家,他们以藏地的村落为叙事空间,着力于“还原”藏区的世俗与日常,将之视为中国大地上的普通一角,与其他村落中的中国人一样,经受着经济发展、观念改变带来的种种冲击,这样的村落有着藏族文化的形式要素,人们在春耕时要打卦,丰收时要酿酒,可能也会有因为独特的婚姻民俗而带来的略为新奇的爱恨情仇,老一代人还在恪守着“不与铁匠通婚”的老习惯,年轻人却已经开始用能否挣到钱是否疼老婆的新标准来择偶。于是,我们看到,这样“混搭风”的生活故事,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村落一样,是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脉搏基本一致的,藏地的村落故事绝对不再是神秘封闭原始的,而是有着与其他村落相似的变迁轨迹和发展逻辑,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大潮中,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这类小说也因此而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审美魅力,成为中国当代村落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以细腻的民族风情描写、民族心理描写贡献了独特的乡土叙事经验。
如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很有特点,桑吉、达吉、边吉三姐妹,还有两个阿妈曲宗。作品中的两个“阿妈曲宗”,一个是桑吉的亲妈,恪守老礼,善良却也有一点小贪财,但也为新的时代变化所冲击(如儿子罗布为了娶铁匠的女儿而和阿妈曲宗反目),最后在无奈中带着对今世的困惑离去。一个是收留了桑吉的城市“养母”,善良却又带着城市文化所培养的小狡黠,由于生活的苦难而在城市中产生了不安全感,所以有点重利商人的气质,因为手艺赚了一点小钱,也非常重视赚钱的事(有点像《骆驼祥子》中的高妈),但又没有泯灭藏族民间乡土文化所培植的善与忍,所以热忱无私地帮助着怀着身孕流浪的桑吉。作家笔下的老一代藏族女性形象因此而出现了新意,不再只是忍受命运、笃信佛法的形象符号,而是带上了市场经济或城市文化的冲击印痕,是构成当代“中国故事”的鲜活元素。
作品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形象,平凡却有血有肉。普村是离县城最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村庄,像它的名字一样,非常普通,达吉有着经商才能,不甘心于普村的贫穷生活,对物质富裕、男女平等的新生活充满了渴望,由于被叔叔收养,她来到了“有三四个普村大,几乎是和县城连在一起的”森格村,这为实现她的理想提供了一个现实平台。作品以她的成长、离开、发展为线索,深度表现了中国民族地区青年的梦想和理想,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卫藏村落故事进行了新意叙写。同许多地方的青年人一样,达吉追逐着金钱(如热心于做酥油奶渣生意),但同时也坚守着人性(如做生意时对顾客的诚信,分红时对伙伴的公平),她不是一个被宗教道德去框定的完全的“好人”(爱动脑筋去赚钱,也有一点向往城市物质文明的小虚荣心),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同情弱者,不取不义之财),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符合生活逻辑的现代中国人。纵向来看,达吉这一形象不再是藏族小说中传统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性、笃信佛法秉持宿命人生观的劳动妇女,因此,这一人物形象应该说在藏族女性人物画廊中是有新意的,是中国西藏农区小说人物的创新,人物形象充满了烟火气息和人间味道,没有被宗教文化提纯,更没有被民族文化标签化,而是变得更加丰富而真实,就像藏族大年三十吃的“古突”,有甜有辣,有香有苦。而结尾昂扬而充满生机,也预示着改革开放语境中藏族女性将在经济、地位、心理等方面发生巨变的全新生活:“很快,达吉和旺久合作的商店开张了,这是整个嘎东县城最大的批发商店。坐在柜台后的达吉精心装扮了一番,俨然一副女商人的模样,也许因为内心激荡着创业的热情,整个人变得神采飞扬。”[7]
青海的藏族小说作家龙仁青(短篇小说集《〈光荣的草原》)、甘肃的藏族小说作家王小忠(《小镇上的银匠》)、何延华(《嘉禾的夏天》)的一些短篇小说也有类似的表达,对现代化语境中的甘肃青海藏族地区的村落变迁进行了关注,对城市文明给藏族基层群众带来的物质诱惑和心理影响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书写,也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中国故事”。
三、亚文化空间写作:“中国藏彝走廊”故事
藏族历史文献将藏族地区分为三大区域: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智者喜宴》),当代学者将这三大传统区域与现代地理学家划分的西藏高原地貌区域作了联系,划分成今天我们所说的藏地三区:卫藏、康巴、安多。一方面,辽阔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使得作为藏文化原始发源地的“卫藏”和唐吐蕃王朝之后才见于史书的“康巴”和“安多”藏区的文化特点带有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三区的藏族小说作家因为出生成长地、藏语方言区、文学活动地的相异而让藏族小说的描写空间多姿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散布范围渐广,与其他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和深度的交流,“7世纪以后,经过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藏族进一步演化为许多支系,散布于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与汉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白族、蒙古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相互接触,杂居交融,结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今天当我们探索我国西南、西北各民族的关系和民族走廊问题时,处处都涉及藏族。”[8]正因为这样的交融和互渗,在藏地三区之中又形成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多民族亚文化空间,藏族与其他一些民族共生共荣于其间,共同构成了和谐丰富的多元文化,这些空间内发生的故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切片,是有意味的“中国故事”的鲜活缩影。
比如有一部分藏族小说比较集中地书写了“中国藏彝走廊”故事,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前后在研究“平武藏人”的问题时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这个走廊是汉、藏、彝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9]作家阿来正出生、成长在这一走廊地区,由于多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四川西北部的嘉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就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因此,他的小说《尘埃落定》并没有选择藏区主流的“卫藏叙事”,而是深情地专注于自己的出生地。他在这个长廊中形成了自己独具慧眼的历史观,在爱国视野中对地方政权进行了冷静观察,以上层政治人物(民族地区的地方权力人物)为书写对象,独特的区域藏族文化、区域政治史、区域多民族文化交织在一起,切近鲜活地表达着近现代历史时段的亚地域文化形态,作家的人类性视野使得其小说不再以被简单地贴上“藏族小说”的标签为是,转而成为“中国藏彝走廊故事”的深度讲述,在这样的场域中一幅由多民族人民共同充当历史角色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画卷被庄重绘就。他的《空山》里的机村、《瞻对》里的瞻对等这些有意味的文化空间中也发生着各种别具特色的中国故事,亚地域文化形态有自己奇特的植物、动物、物候、民俗,这是表层的文化,它们都被中国大地上共同的革命叙事、历史叙事之风所吹拂,这是深层的文化,这样的杂糅叙事使得文本平中见奇、瑰丽跌宕。
四、关注民间活力的特殊表达方式:中国藏区的长征故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自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长征时期先后经过了云南、四川、青海果洛、甘肃甘南等藏区,最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时经过藏区92天,是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中占用时间最长的行走,其中富含了值得藏族小说认真讲述的中国故事。藏族作家在处理这类红色题材时比较关注民间活力,是讲述中国长征故事的新手法。
比如说安多藏族作家尕藏才旦的《红色土司》对红军在迭部等地的“红色故事”进行了情景还原,在对当事人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文学地还原了杨土司支持红军的历史故事。《红色土司》是以甘肃卓尼的十九代杨土司为人物原型而创作的小说,重点讲述了红军长征经过卓尼时他开仓济粮的历史往事,和康地土司孔萨益多相类似,杨积庆及其家族也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开放的文化眼光,小说中的杨土司精通藏汉双语、熟谙汉族的琴棋书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对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洞若观火,对时势有着清晰准确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土司》虽然是主旋律叙事,但是作者在处理红色题材时对民间文化(文学)及蕴含其中的民间活力进行了格处关注,试图用新手法讲述中国长征故事,应该说贡献了另一种有价值的艺术经验。民间文学孕育了现代叙事学理论,从学术渊源上看,叙事学理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弗拉基尔·普罗普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他是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确立其理论主张的,代表作有《民间故事叙事学》,这也是叙事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他指出,故事中的基本单元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并就此对俄国民间故事的数十种功能作了分析。功能理论把故事从一般时间叙述顺序中抽离出来,从而构成了一种形式结构。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家则从另外的理论高度提出了“民间”这一当代文学关键词,“民间”一词是90年代由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与《民间的还原》两篇文章中系统提出的,按照王光东的理解,“‘民间’在文学史上不是作为一种思潮或者潮流出现的,而是一种创作元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这两层意思虽然相互联系,但又有所不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它是一个自在的存在——自由自在、藏污纳垢是其基本的特点,作为民间的价值取向则是知识分子由民间的这种自在性转化为主观的精神原则,这种精神原则的根本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多元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10]将“来自民间的人物所具备的创造性活力”作为结构全篇的主要力量这一手法,在甘肃的藏族作家尕藏才旦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富有民间活力的人物既发挥了结构全篇的作用,也以自身的鲜明特点彰显了中国民间的多姿多彩情致,作品因此而具有了多民族中国的气韵和风范。主要人物杨土司就整合融汇了藏地民间智慧(以母亲为代表的族群智者给他传授的生产知识、生活经验、宗教哲理、艺术趣味等等),充满了创新意识,理智解决了现实问题和矛盾冲突。其他次要人物也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身上也有着明显的“民间活力”,比如小说中对民间故事原型的运用,在敌我双方对峙的关头,土司的妻子金花急中生智,以柔克刚,用彻夜演唱“花儿”的方式智斗军阀鲁大昌,迷惑了对方,拖延了时间,对红军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典型的藏传佛教文化圈的民间叙事方式——“歌舞除妖”(如藏族的朗达玛故事,土族的“除王蟒”故事)。
其他如降边嘉措的《最后一个女土司》也有类似的表达,支援红军长征的中国故事发生在爱国土司身上,但却以主人公的爱情生活为线索进行表现,面对纯洁的爱情时,土司同百姓一样,有诸多趣味十足的民间婚恋习俗,人物既结构了全篇,又让文本充满民间活力,清新可人,鲜活质朴。这种表达方式,在革命历史的主旋律叙说中夹杂着文化色彩的辅助线,内容新鲜而活泼,既勾勒了一幅幅中华文化地理版图中的藏族民间生活风俗画,也彰显了多民族国家充满生趣的民间活力,是藏族作家为长征红色叙事贡献的一份独特艺术经验。
五、结 语
当代藏族小说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准,值得认真总结和分析。藏族作家小说中的“中国故事”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如上所述,以中国民族地区新公民形象塑造、“祛神秘化日常写作”、亚文化空间写作、关注民间活力等方式贡献了独特的艺术经验。个人的一己之见,笔者认为藏族小说的“中国故事”书写如果能够持续走向成熟和繁荣,不仅能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凝聚国家认同意识,从而实现民族团结、文化自信、中华复兴。而且也将为建构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大文学观”建构提供有益的个案和理论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