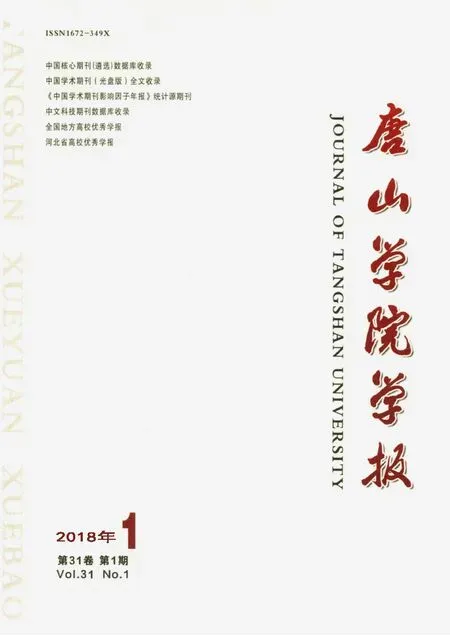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英语非洲工人运动与民族国家认同
杭 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民族国家认同构建是英语非洲现代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工人群体的民族国家认同可被简称作“工人民族主义”。它的产生和变化持续受到西方主导下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非洲的全球化环境有两次突出变化:一次是1950-1960年代殖民帝国体系瓦解,另一次是1980-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无条件市场体系(华盛顿共识)席卷而来。殖民帝国瓦解是由于民族矛盾让非洲各族群、各阶层人群凝聚在一起,工人民族主义初步形成;新自由主义市场体系席卷而来使阶级矛盾削减了民族凝聚力,各族群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工人民族主义重构并得到升华。通过分析工人运动所反映出的民族国家认同变化,可以看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群体特殊利益与民族国家普遍诉求之间的分合关系,及国家制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学界既有的不多的研究与介绍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工人运动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1-2]。笔者的研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殖民制度与工人民族主义的形成
国家因素在工人民族主义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恩格斯对国家的作用曾有过精辟阐述:“这种力量(国家)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3]国家成为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最主要的工具,国家因素渗透到生产过程、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塑造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制度的两个层次来进行分析:一是一般性制度,如政治权力结构、民众权利规定、强制力使用等;二是由一般性制度决定的劳动制度,如国家与工会关系的制度和劳工权利规定等。
秉持种族主义的原则,殖民制度将殖民地人口分为白人和非洲人两个群体,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工人问题被转化作民族问题处理。白人享受各项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政治权力把持在白人殖民者手中,非洲人毫无政治权利,没有任何劳动权利,更没有集会、结社与提要求的权利。殖民主义作为西方主导下全球化的手段,惯用超经济强制力处理经济整合问题。非洲劳动力被强制动员进入商品农业和矿业生产,以及附属的运输业。直到战后,非洲大陆上都广泛存在着强迫劳动体制。在主要的殖民时期,即1885-1945年,非洲工人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的分化不明显,非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也便不存在工会监管制度,自然不存在工人民族主义问题。
1945年后,殖民政府实行“文明劳工”政策,部分非洲工人被赋予准白人的身份,工人民族主义才真正发端。随着白人优越论的破产、工人群体壮大,一部分非洲熟练工人逐渐被官方承认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群体,被承认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其他的权利,这便是所谓的“文明劳工”政策。政策的实质是赋予这些被选出的能获取稳定工资的工人以准白人工人地位。这种承认是半心半意的,因为英国政府在殖民地施行远较本土严厉的工人政策。官方工人政策的核心概念是隔离。一是同非洲传统文化隔离,以将非洲工人同非洲社会其他部分隔绝开来,成为有“效率”的工人。官方认为非洲社会不适应工业时代的要求,这是由“他(非洲工人)在许多工业技术上是无效率的,因为他出生、成长和本土文化的性质”[4]决定的;二是同民族主义政治隔离,或者退而求其次创造一个政治温和的工人群体,作为合作者反对“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危险、落后的非洲大众。这便需要加强对工会的监管,以便“避免不负责任的个人或群体为政治或非工业目的组织工会”*殖民地工人问题顾问委员会会议记录,1949年4月21日,mss.292/932.5.1,转引自Paul Kelemen,Modernising Coloni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Africa,第231页。。英国政府想通过殖民地工会,将工人培育成只专注于经济利益,而不参与政治斗争的“驯服合作者”。具体而言,殖民政府实行以下五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是执行不同于英国本土的单独工会法律,为政府保留更多的权力。殖民地工会立法将不执行英国早已签署的《国际工人公约》(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中的规定。政府保留干预工会组织和运转诸多方面的权限,诸如当选为工会管理层的人选、限制政府雇员自由参加工会、在工会立法中排除特定阶层的工人、还有限制工会的合并与联合*英国殖民部档案:CO859/183/3,no.29,1951年7月26日,[工团主义问题]:殖民大臣格里菲斯(Griffiths)致各总督的通阅急件,见Ronald Hyam,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London: HMSO,1992,第4册,第369号文件。英国殖民部档案:CO859/183/3,no.47,1951年10月,[工人关系]:殖民地工人部门领导人大会报告(殖民部,9月24日~10月5日),见Ronald Hyam,edi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第4册,第370号文件。。种种限制显示出英国政府并没有将非洲人工会接纳入体制的诚意。非洲工人自然同它离心离德。
第二是坚持“有色人种禁令”(Colour Bar),继续将非洲劳工排除于大多数高级岗位和技术性工作之外。这代表了白人雇主和白人工人的利益。白人雇主极力主张非洲人劳动力仅能获得临时工性质的工资,以压低整体工资。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白人工人则希望尽可能多的占据高级和技术性的岗位。于是经济问题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进而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禁令成为许多罢工的导火索,而罢工又成为全体非洲人反抗的引信。
第三是实行工会注册制度。殖民政府对工会选举和工会会费进行监督,限制工会参与政治活动。一是限定工会的领导层必须为工会所属行业从业者,来制约当时的许多工会领导人同时也是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实际情况。二是规定工会基金不能用于政治活动,工会财务状况要处于政府监管之下。实际上,工会运动同民族独立运动的联系并未被切断。
第四是制约罢工权。一方面实行硬的一手,总督有权定义“基本服务”的范围来限定罢工为非法。在1950年代,在坦噶尼喀有15个广泛的基本服务大类被列出,在肯尼亚有13个,在尼亚萨兰有10个。另一方面实行软的一手,引入法定的工资确定体制(Fixing Salary System)和局部罢工权。这种半心半意的让步并未能软化工人们的立场。
第五是为本国工会同殖民地工会的联系牵线搭桥,以培养殖民地工会的亲英情感,搭建影响力渠道,破坏国际工人的团结。在殖民统治时期,许多怀有反欧和反英情绪的殖民地民族领导人,也不得不向英国职工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英国工人运动兴起较早,起初按行业建立了各种工会组织,1868年进一步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会寻求有关工会组织管理问题的帮助*英国殖民部档案:CO859/748,no.24,1954年7月19日,[殖民地劳资关系]:李特尔顿和英国职工大会和海外雇主联合会于7月12日讨论的殖民部记录草稿,见David Goldsworthy,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London: HMSO,1994,第1册,第504号文件。。这就为英国职工大会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英国政府出台专门文件建议英国职工大会,从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形势出发,优先在东非、中非建立联系,同时维系西非已经建立的联系,再兼顾加勒比和东南亚地区*英国殖民部档案:CO859/752,no.8,1956年12月,[英国职工大会和殖民地工团主义]:12月10日英国职工大会代表会议殖民部记录草稿,见David Goldsworthy,edi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1册,第510号文件。。临近统治结束时期,英国公司和雇主要求英国职工大会继续保持和加纳工会的既有联系。因为工会联系渠道是英国方面唯一能直接影响加纳政府工人政策的渠道。当然,通过英国驻加纳高级专员干涉加纳政府的工人政策也是一条渠道,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措施,只能用在对英国的终极利益形成主要威胁之时*英国殖民部档案:CO859/1229,no.6,1958年10月7日,殖民地工人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紧急状态地区事务的关系,见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7-1964,London: HMSO,2000,第2册,第358号文件。。
由于政治权力把持在白人殖民者手中,工人没有政治权利,对工人运动的武力镇压仍非鲜见。1949年东非联合工会建立,但被拒绝注册,因为政府担忧东非联合工会被一个显然是共产主义鼓动者的印度人所领导。1950年,肯尼亚非洲工人联合会和东非联合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奈洛比的总罢工被武装警察、军队和皇家空军冲散。300名工人被逮捕,一些工会领导人被判处惩罚或监禁,理由是组织非法罢工。肯尼亚的事情并非孤例。1949年尼日利亚恩奴古(Enugu)的煤矿业罢工,23名罢工矿工被武装警察射杀,超过100名矿工受伤。恩奴古的屠杀在殖民地工业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却成为民族反抗的最后导火索。
“文明劳工”并没有被真正纳入殖民地政治体制,却由此促进了工人群体的同一性,更促进了民族统一的政治身份的形成和统一诉求对象的出现。享受组织工会权利的“文明劳工”只占工人群体不超过10%的比例,更多的是“流动劳工”。“流动劳工”占多数的状况既是由殖民地原材料出口型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于殖民官员们不愿意完全放弃利用乡村部落组织的管理结构。该群体往往在农村有耕地,迫于生活压力到城镇提供廉价劳动力。有些人在农忙季节要返回农村耕作,有些人长期在城镇居留从事简单劳动但终究还是不得不回到农村,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工资都不足以养活整个家庭,甚至他们个人的生存也只能勉强维持*英国殖民部档案:CO822/657,1952年11月11日,非洲人工资政策,转引自Paul Kelemen,Modernising Coloni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Africa,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4,Issue 2(May 2006),第224页。。这部分劳工占多数的情况导致工人群体的利益往往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混杂,易于彼此联合。于是,“文明劳工”联合了“流动劳工”、“流动劳工”联合起其他社会群体,一致地反对殖民体制。
殖民政府半心半意的措施并未能实现其将工人群体同非洲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同民族主义政治隔离的目标,反而激发了非洲工人的共同体意识,在阶级层面上表现为工会的兴起,在民族层面上表现为“工人民族主义”,他们将自己阶级的命运和民族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抗殖民统治。受过西式教育的精英和西式厂矿中的工人将自己争取权利的行动同争取全民族解放的事业联系起来,形成现代性全民群众运动,使得争取独立的要求具备了现实基础[5]。这便是英国将工人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的结果。
二、新自由主义危害与工人民族主义重构
非洲各国独立后,国家制度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在一般性制度层面,非洲人自己掌握了政治权力,非洲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在政治法律层面获得了权利保障。在劳动制度层面,国家工会纳入体制之内,保障劳工权利。政府通过承认工人权利、保障工人福利来换取工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如埃里·凯杜里所认为的那样,当国家中的统治阶级转而信仰民族主义时,就很容易用这种学术设想来管理和影响国家[6]。总体上,政府处理工人运动的国家制度设计秉持民族团结的思维。同时,工人运动促成国家制度的调整。
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民族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殖民者被赶走,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受到削弱,工人的阶级意识得到增强。这是因为对于普通工人而言,他们仍旧处于权利遭忽视和廉价雇佣劳动力的地位。尼日利亚联合工人大会(United Labour Congress)在1962年5月的一份政策文献中说:“独立日,1960年10月1日,使我们从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不幸地是,它没有让我们自主地从殖民体制中解放出来。特权的大厦仍旧保留,只是它的所有者不同了……联合工人大会将继续战斗以反对阶级对阶级持续的剥削,就如它热诚地战斗反对帝国主义一样。”[7]另一方面,反殖民时期形成的民族共识仍旧存在。如一名赞比亚年轻矿工所讲:“独立给矿业带来很小的变化。即便是有(资产)国有化和(员工)赞比亚化,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因为白人控制每件事情。”[8]继摆脱政治控制之后,摆脱西方经济控制,获取切实的经济福利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共识。
在此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工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西方以债务胁迫非洲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经济改革,导致非洲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1986年非统组织峰会上,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Sankara)指出,“在这些债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新殖民主义’体系”,“当前,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和统摄下,外债成为殖民主义者精心设计的重新占领非洲的工具”[9]。非洲政府被迫削减公共开支,取消基本食物价格补贴和减少公共医疗支出,这对包括工人在内的中下层人群影响很大。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放开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扶持,吸收大量就业人口的制造业和小规模农业不再受到扶持,直接加大了就业困难。国有企业私有化刺激了工人共同体意识。新时期共同反对私有化的经历让工人获得相似的社会身份,维护了工人共同体意识。自然而然,许多社会运动都由工人罢工引发、由工会组织领导人发起。
面对此种局面,各国政府采取不同的措施,试图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代表的外资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维持某种均衡,尽力争取工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为配合新自由主义政策,尼日利亚主要采取的是压制工人要求的解决路径。工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遭遇曲折。受新自由主义影响,1993年尼日利亚工人真实工资只有1983年工资的20%[10]。这种情况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具有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工会如非殖民化时代一样再次成为积极的反体制力量。1993年拉各斯和其他大城市爆发大众抗议,以求结束军事统治和推举民选政权。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金融中心、燃气站和大多数市场和工厂全部停止运转。联邦军队进入拉各斯恢复秩序,大约150人被射杀,同时数百人被政府安全部门(State Security Service)逮捕。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工人都走向街头。到了1994年8月中旬,60%的工厂停工。军人政府制定出限制工会的法律,用指定的领导人替换原来的领导人,但并未彻底取缔工会、否认工人的权益。工会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地位要远好于殖民时期。军人政府提供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秩序,能够压制住工人们的诉求。这是军人政府能够维持到1999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军人政府缺乏工人们的认同也为民选政府登台埋下伏笔。
在津巴布韦,工人运动促使新自由主义政策收缩。工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仅获得暂时的巩固。1996年的津巴布韦,先是公共服务联合会、护士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健康部门,从清洁工到医生罢工,之后全国范围内所有公共部门一天内全部罢工,选举产生统一的罢工委员会。1990年代新一代工人成长起来,他们生长于城区受过教育,不同于他们有乡村背景的父母。他们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只能找到合同工或临时工岗位,工作稳定性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成为罢工的主力军。穆加贝总统不得不部分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撤回到国家干预经济的激进论调。从意识形态上讲,执政党日益采用反白人农场主的种族主义政策论调凝聚国家认同。政府试图以此为基础完成劳动力体制重构。然而不管是穆加贝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明确提出解决生产增长问题的方法。
新自由主义政策激化的社会矛盾,导致南非政权更迭,工会直接参与到政权中。工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感达到新高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和白人政府谈判期间,工会发动了48小时的声援罢工。为纪念索韦托事件12周年,南非工会大会发动了包含制造业70%雇工在内的大罢工。从1986-1990年间,罢工造成的工时损失超过了之前75年的总量[11]。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1992年10月,以非国大为首的三方联盟(包括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接受同白人分享权力的策略,为重组国家、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重塑社会稳定提供了新框架。在这一框架下,1994年南非政权实现和平过渡,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南非工会大会直接参政的结果之一是黑人家庭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头十年里平均收入增加71%[12]。2006年,这一组织代表了65%的有组织工人,占所有工人数量的14%[13]。通过反对私有化、反对黑人内部不平等分配,构筑起工人运动新共同体意识基础,作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基础,确保了南非民族国家的向心力。
工人阶级中诞生出“非传统民族主义”意识,阶级独立意识更为明显。正式部门的工人又一次成为反体制的先锋。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由于生活问题、城市化问题或乡村土地问题同正式部门的工人形成新共同体意识。殖民时期,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以殖民政府为化身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在不发展状态下以压制本土工人权益为基础处理劳资矛盾。工人以融入民族解放运动为斗争形式,民族意识更为明显。在后一时期,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更多以经济手段逼迫当地政府牺牲发展权,放弃对工人权益的保障。工人以对政府化解渠道的疏离为斗争形式,阶级性得以彰显。此时,非洲工人运动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组织性。
另一方面,工人们的“非传统民族主义”仍旧包含着民族国家认同。传统、政治法律承认、社会福利照顾共同筑起工人民族主义的界限不被突破。共同的反殖民经历、数十年居于共同民族国家内的经历和西方压力塑造的压迫感构筑起民族共识的大框架,已形成工人民族主义的传统。不管各政府或采取压制、或采取妥协、或吸收工会进入政权,各政府都承认工人的政治法律权利、提供或多或少的福利。所以工人运动一直保持在体制之内,并且在重塑自身的同时塑造了国家制度。工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在挫折中增强。
三、结语
民族国家认同依靠民族主义来寻求同一性。同一性的获取有两个来源,一是外部民族的压迫,二是民族内部协调。从历史上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反而激发起英语非洲人民反全球化民族主义浪潮。正是西方资本促使不同的工人利益凝聚为一体,创造出工人共同体意识。该意识又同其他社会阶层的诉求相结合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分别表现为反殖民运动和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为民族主义构筑起共识的大框架。以包容性的民族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建设是维系民族主义的支柱。民族主义的维系需要将民族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融入到制度性框架,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利益分享。独立后的非洲人政府保障工人的政治法律地位并给予公共经济福利,使得工人运动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终未突破民族共识的底线。非洲民族国家构建在曲折中前进。
[1] 唐同明.战后英属东非的工人运动[J].西亚非洲,1987(3):39-46.
[2] 利奥·蔡利格,克莱尔·塞鲁蒂.贫民区、反抗与非洲工人阶级[J].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23-28.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4] COOPER F.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40.
[5] BOAHEN A Adu.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Colonialism[M]. New York: Diasporic African Press,2011:63.
[6]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4-105.
[7] MELSON R. Nigerian politics and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64[M]//ROTBERG R I,MAZRUI A A.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776.
[8] BURAWOY M.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belt[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74.
[9] ISMI A. Impoverishing a continen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Africa[R/OL]. 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 Report,2004.[2016-11-11].http://www.halifaxinitiative.org/updir/ImpoverishingAContinent.pdf.
[10] ZEILIG L. Class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in Africa[M]. Chicago, Ill: Haymarket Books,2009:138.
[11] DWYER P, ZEILIG L. African Struggles today: social movements since independence[M].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2012:108.
[12] 潘兴明.南非:非洲大陆的领头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2.
[13] MARAIS H. South Africa pushed to the limi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ange[M]. London: Zed Books,2011:445-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