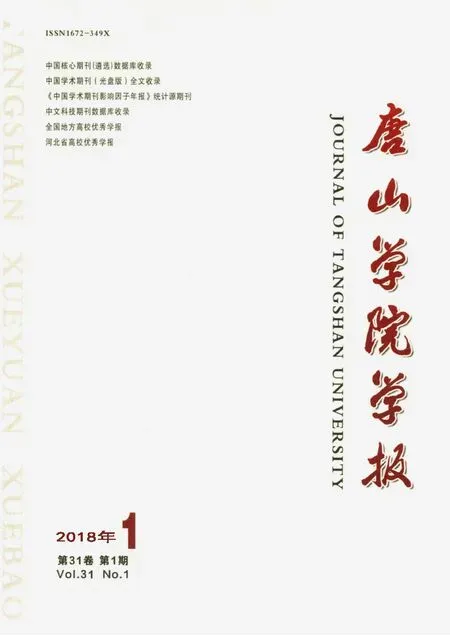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独特贡献与历史价值
谈思嘉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非基督教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首先在上海爆发进而波及全国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对基督宗教的运动,最初只是起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学理讨论,后来随着国内民族主义不断高涨,逐渐升级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立甫半载的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导,在运动组织上和理论宣传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李大钊在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中坚角色。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并出席非宗教大同盟各项活动,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撰写大量文章阐发鲜明的宗教观,为非基督教运动做强舆论宣传。然而,在以往的李大钊研究中很少学者关注到这段历史的进程,故有必要对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言行进行深入考察,进而更全面地了解李大钊的思想和生平。
一
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究竟是一场随机触发的爱国运动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预谋,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其中关于政党组织究竟与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有无关系,政党是否参与并策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等问题的探讨尚无定论。但只有厘清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定位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重要贡献。
目前学界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以鲁珍烯、杨天宏、顾卫民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政党组织在非基督教运动产生之初与之并无太大关系,“如果一个政党的思想政治纲领没有对这场运动产生直接作用,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政党参与了运动”[1]。虽然有不少国、共两党党员参与到运动中,但这仅属于无组织的个人行为而不能代表政党的主张,至多只能代表个别社会精英或某个小团体。而另一派以郭若平、牟德刚等人为代表,他们根据近年陆续披露的史料和档案,认为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生与政党有着直接关联,如果没有政党参与其中并发挥一定作用,非基督教运动不可能以如此的面貌和规模出现。对于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无关说”显然与现已披露的史料相背离,政党确实是发生非基督教运动的直接推动力量。但是“无关说”也不失参考价值,它强调五四以降中国社会发展态势、历史条件和群众基础等背景构成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历史合力。而在承认政党作用的学者中,有的学者仅将共产党或者国民党视作非基督教运动产生的唯一力量*参见田海林、赵秀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牟德刚的《中国共产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及其历史意义》,陈海军的《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1923-1927)》。;有的学者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两个政党组织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趋同促使了运动的持续发展*参见周兴梁的《二十年代初期国共两党成员指导进行的“非基督教运动”》,郭若平的《国共合作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考察》和薛晓建的《论国共两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还有学者通过观照国际政治格局认为共产国际的介入也是不可忽略的力量,它“除了最初直接策划了非基运动外,在以后错综复杂的革命局势中,仍一再表现出对非基运动的关注”[2]。对于上述各方观点,本文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是非基督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导力量。仅从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前夕的情况来看,有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批判基督教有了思想认识。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受过新式教育洗礼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进行了一次深刻变革。在以往人们的观念中,新文化运动只是将矛头直指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孔教。其实,新文化运动在“反孔”的同时也展开“非耶”的批判。基督教信仰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压迫和奴役,以及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精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使其不可规避地遭受批判。特别是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剖析宗教问题的相关理论成为了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一股批判宗教尤其是批判基督教的热潮在思想界涌现。李大钊利用唯物史观辩证地考察了宗教的产生及影响,在肯定宗教“坚人信仰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深刻揭露“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3]98的弊端,更坚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宗教也必将消亡。此外,诸如陈独秀撰写的《基督教与中国人》、恽代英的《我的宗教观》等文章也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立场上对基督宗教进行了深刻剖析,为非基督教运动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其后备组织对运动爆发有了组织准备。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端要追溯到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的一场矛盾,当时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中的《评议部纪事》一文中,在涉及学会会员宗教信仰问题时规定,“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绍为本会会员”,并且“主张已入本会而有宗教信仰者,自请出会”*《评议部纪事》,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第87页。。规定一经刊登,立即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激起波澜,继而引发关于宗教问题大讨论,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前奏。而引发矛盾的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当运动正式爆发,第一个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就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发起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当时在华工作的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中写道,“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4]91,还称“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4]92。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准备。
二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李大钊究竟与非基督教运动有着何种联系,还需通过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李大钊对运动的发展态势所起的重要指引作用。
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一般被认为是1922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第十一次大会。此次会议的召开被认为是基督教组织意识到中国反宗教潮流将限制和挑战教会事业的发展,故在此时选择在中国地区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加以应对[5]。但是,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揆诸历史事实发现这一判断并不能成立,联盟大会早在1913年就决定第十一次大会于1916年在中国召开,只因“欧战”正酣才延期至1922年,而且从谴责战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会议主要议题上也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文化上控制侵略中国的企图[6]。
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和破除偶像的热潮在中国兴起,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当时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尤其是联盟大会中某些不当宣传最终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被引爆。于是在联盟大会召开前夕,社会主义青年团在2月26日就在上海召集起反对基督教的同学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同盟成立后便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非基督教运动立即得到各地积极响应,尤以北京反应最为激烈。据范体仁回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由范鸿劼主持”[7]。李大钊出席大会,并与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15人一起被推举为干事,负责日常事务。期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投入大量精力,作出重大贡献,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动非宗教大同盟的建立。1918年,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除了搜集马克思著作,组织有翻译能力的会员对其进行编译和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外,还积极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联问题,强调在思想领域内不应当回避宗教问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多次在研究会内部商讨组织非宗教同盟的事宜,这在罗章龙的《椿园载记》中的回忆可以得以印证。罗章龙回忆道,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即组织非宗教同盟”[8]90。后来,非宗教大同盟的成立主要就是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成员基础的,再广泛联络北京部分高校的师生参与其中[8]91。
第二,执笔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电坚定非宗教立场。1922年3月20日,李大钊、陈独秀等77位学界名流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同盟宣言并通电全国,宣言就为何要发起非宗教大同盟以及为何将矛头对准基督教的缘由进行了深刻阐释。宣言和通电一经发布,全国各地应声四起,纷纷成立非基督教团体。但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开始出现反对声音,周作人、钱玄同等多名教授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干涉了信仰自由,将会为日后用强力取缔思想自由埋下祸根。对此,李大钊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当天再次主笔起草《非宗教者宣言》,重申了非宗教立场,并对反对派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表示坚决反对“信教自由”,否认宗教和自由并立的可能。
第三,积极参与非宗教大同盟活动,以提升运动宣传力度。非宗教大同盟的常规活动主要是组织公开的学术演讲[8]91,身为同盟主要发起人和常务干事的李大钊积极出席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1922年4月9日下午1时至5时,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开演讲大会,李大钊到会并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就发起非宗教大同盟以及将矛头对准基督教的缘由再次进行阐释。1925年12月25日,非基督教大同盟举行第二次公开名人演讲大会,李大钊再次出席并发表了基督教侵害中国的种种情形及补救办法的演说。李大钊通过发表演说,以自己的社会声望号召更多社会人士加入同盟,扩大同盟的队伍和力量,使非基督教运动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三
除了积极参加非宗教大同盟集会活动外,李大钊还就宗教问题撰写了《非宗教者宣言》和《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多篇文章,阐明了鲜明的、彻底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宗教观。这不仅有力地配合和声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进展,为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更深化了人们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为人们探求科学真理和思想自由扫除了宗教迷信的毒害。
第一,宗教有碍思想自由。非基督教运动兴起后并未形成一边倒的情形,在猛烈批判宗教的同时,一些学者教授和信教人士也针锋相对地发出反对声音。其中,周作人等北京大学5名教授就于3月31日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坚决反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的运动,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必须遵守约法规定,保证宗教信仰应当享有绝对的自由而不受任何人干涉。一场关于宗教信仰与思想自由关系的论争由此引发。次日,李大钊便立即发表通电,批驳周作人等人虽表面上不拥护宗教,但已经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在他看来,宗教信仰是对神的绝对体认,信仰神就必然受到神定的束缚,既然受到神定的束缚,那么“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3]98。所以,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不代表思想自由,反而“宗教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3]98。按照马克思宗教观所认为的,只有当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发展到一定高度,不需要向虚妄的神灵寻求精神寄托,能够摆脱宗教这一异己力量的支配,那么人类才能实现真正解放,获得充分自由。同样,李大钊也主张“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9],只有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3]98,那么才有真正实现和维护思想自由的可能。
第二,宗教教义的虚伪性。但凡宗教总是通过宣扬自身教义以俘获世人之心灵,使之投身该宗教而成为其教徒。表面上各派别宗教教义无比光明正义,如基督教教义颇含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崇尚之意蕴,但李大钊却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宗教只是假借宣扬教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为此,他在《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文中逐一进行批驳,直指宗教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的背离。尤其在论及宗教与平等关系时,李大钊剖析了原始宗教产生的条件,认为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强力而存在着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缺陷,从而产生敬畏和崇拜,“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有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仰”[3]99,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此表现出来。由此,人们将宗教视为精神寄托来谋求实现平等关系从宗教产生的源头就已断然不可能实现。既然宗教的自由、平等是虚伪的说教,缺乏自由、平等作为基础的博爱自然也是经受不住拷问的。
第三,宗教妨碍人类进步。从李大钊早期的宗教观来看,对于宗教历史作用的评判并非是全盘否定的。李大钊对宗教能够“坚人信仰之力”尤为赞赏,还一度号召“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10]。对于宗教内部具有合理部分,李大钊一开始也主张应依据真理的标准辨别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但是,为了配合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宣传,李大钊在评判宗教的作用时,只考虑宗教的消极因素而忽略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他认为“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换言之,这是不懂得进化论为何物”,因而违背科学、逆社会发展进程的宗教在传递“廉价的幻想”的同时也成为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譬如,李大钊以基督教宣扬的无抵抗主义为例,认为所谓“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等语,嫁接到现实生活后,它某种程度上就暗含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无需做出任何反抗,只需安分守己甚至容忍并主动让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自己。而这必然不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所以,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依赖宗教幻想是毫无意义的,必须竭力加以反对。
四
李大钊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都对推进非基督教运动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深化时人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壮大中国革命队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深化了人们对宗教的本质认识。五四运动以前,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对于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基本持有正面肯定的态度。然而,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他们的宗教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都转向痛批基督教的教义,但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李大钊则首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研究宗教问题的先河”,为扫除宗教迷信毒害、正确认识宗教问题和制定科学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李大钊参与和领导非基督教运动壮大了中国革命的队伍和力量。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积极投身运动,对自近代以来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一的基督教信仰予以沉重打击,荡涤了一切宗教迷信,为中国人民探求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作出了独特贡献。反帝反教理论的广泛宣传,吸引了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刚刚建立半年、人数不足百人的小政党团体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了国内政党团体中领导民族独立和反帝斗争的中流砥柱。并且,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使政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都得到了充分历练,尤其是掌握了如何发动学生、工人等群体参与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机制,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最后,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直接证实了在政党组织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无关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同样代表着全党的思想和意志。尽管目前尚没有材料能直接表明李大钊是接受党组织的决定领导和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的,但从实际历史的进程来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前赴后继地参与到非基督教运动中,直接影响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态势。由此,早期中国共产党是非基督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1]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294.
[2] 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J].近代史研究,2003(5):114-136.
[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91.
[5]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444-445.
[6] 杨天宏.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与中国反教运动关系辨析[J].历史研究,2006(4):173-177.
[7] 范体仁.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M]//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74.
[8] 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7.
[10]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