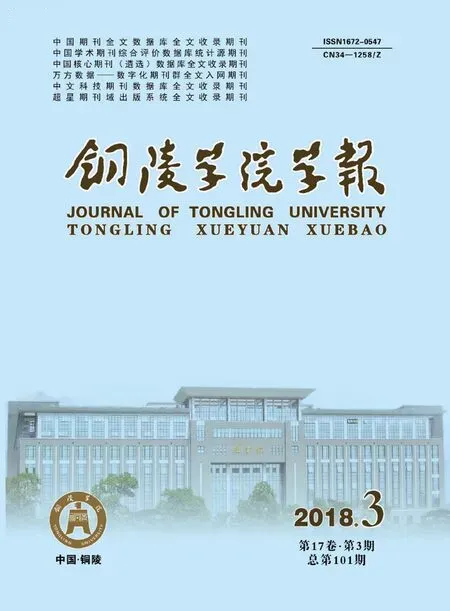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与改革探析
王带平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特别针对性的提出了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对国学经典文化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中国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实现中国梦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精神滋养”,[1]中国画艺术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本土文化美的再现。它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脉络发展了几千年,起起落落,始终与当前环境息息相关,笔墨当随时代,新形势下国民更高的文化需求也为中国画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一、中国画教学的历史文化传承
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的绘画体系就已经相当完整,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在其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了独特的与其相符的哲学观、画学理论以及教学方法。
中国画的教学经历了一个由个别行为到集体行为的发展历程:早期古代传统国画教学以“课徒制”为主,师徒相传或是父子相传,并以诗书画印和传统国学经典文化为重要教学内容和手段;到了宋代形成完整的“画学”模式,诞生了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美术教育机构—国子监,后来发展成翰林图画院,考学、分科建设、课程设置、文化与技艺的精湛提高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准。学生在了解孔孟、老庄哲学思想的同时,注重佛道法意的审美,研习山水、人物、花鸟、虫兽等多种题材的绘画之外,诵读《尔雅》、《方言》等经典书籍,如此,学生的择业还是最终的考核都具备严格的标准。[2]
19世纪末,清政府受西洋文化影响,效仿开办西式学堂,其中便设立了美术科,开启了近代美术教育的先例。1902年,教育家张之洞创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设国画课的学校。20世纪初,近代中国画教学的模式和方法一直处于摸索阶段,一些国学大师意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危机,无不愤慨直言,竭力挽救之前固步自封的状态,有识之士如蔡元培、徐悲鸿等人为中国画教学输入新鲜的血液,尝试将西方绘画艺术与本土国画艺术嫁接,一段时间内确实让老态的艺术教育焕发了青春,提高了中国画教学的发展速度。
二、高校中国画教学的南北分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画教育改革的主要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观点出自地处江南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以“传统出新”的思路为核心,提出中国要与西方拉开差距,南派的早期代表黄宾虹、陆俨少、潘天寿等先生都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另一方面观点集中在地处政治中心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认为“以西润中”,即中西融合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画的发展思路,北派以徐悲鸿、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等先生为代表,在教学内容上提倡将中国画的笔墨融合西式素描形体表现在传统宣纸之上,创新中国画的现实主义表现。两种教学思路是两所美术院校求新、求变的体现,学术见解不统一。事实上,大部分综合院校内部存在着两种教学思路相互交叉影响的情况。
随着20世纪思想开放的浪潮席卷艺术领域,西方的“再现艺术”冲击了东方的“表现艺术”,融合东西文化还是保持本民族文化,这两种诉求彼此消长,南北两派的分歧更为加剧,这使国画教学在 “传统”与“创新”这两条思路上始终裹挟不清。到了21世纪,一个鼓励并接纳艺术多元性的新时代来临,一些人漠视本土文化艺术,盲目崇洋媚外,效仿西方学院派,致使一些艺术院校教学模式的设置背离了传统文化,最后直接将本土“表意”的人文精神和崇高文化信仰支离、解构。为此,学者、艺术教育家们忧心忡忡,对如何正确的引导和鼓励学生们学习中国画,他们各持观点,意见不一。如李小山提出的“中国画穷途末日”、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等等[3],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高校的国画教学。文化开放本是一件好事,但糟粕、精华兼收,未做过滤处理,往往失当。
教育工作者纠结于正视中国画教学的基础与传统的问题,太强调一板一眼的基础与传统,学生不能解放天性,不免限制了他们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若不重视文化基础与传统审美修养的提升,又缺失了文化信仰。于此,国画教育者们尝试各种教育可能性,但仍感到艰难。
三、当今高校中国画的教学面临的基本问题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各类高等院校为适应社会发展,扩张了专业招生人数,相继增设了其他艺术专业,一些推进了中国画教学的繁荣,另一些实则产生了一些弊端,多元文化将本土国画艺术排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很难传承和创新,中国画教学也遭遇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综合能力差,选拔机制有弊端
每年通过美术高考和各大院校招生考试都要选拔一批人才,然而在这种当前教育条件下认为较合理的方式却存在着弊端。招生统考基本以素描、色彩、速写为主,除几大美术学院校考稍有不同科目,或是对招考专业科目稍作区分,大部分高校通常以专业课与文化课乘以不同比例系数相加的方式来计算总分,以得分高低为标准“一刀切”。
这样,选拔的人才看似高分实则低能。有很多学生在高考之前会参加绘画技能课的集训,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为节省时间会不负责任的教学生背头像、水粉,甚至是速写人物动态。学生失去了正确观察方法,绘画上枯燥乏味,更谈不上兴趣可言。如此背离艺术教育规律的做法却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考生在就读大学后对绘画专业也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还有大部分考生选择美术之路通常是迫于文化课薄弱的无奈,为走一条把稳、快速的捷径,可能只会考前集训的头像或是静物水粉,估计连毛笔都拿不稳,更别提书法和国画了。
再加上一些高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原本对学生的文化功底、艺术修养要求甚高的精英国学教育,如此一来只能培养一些国画初学爱好者,缺乏了基本的审美能力,很难把握中国画的灵魂。
(二)中国画教学的基本思路有偏差,培养方案的设置严重西化
课堂上教学内容和形式愈来愈西化,大众化、市场化,教学方式单一、僵硬,传统文化内涵缺失,文化理论教学基础薄弱。近些年来,在高校教学培养方案中多以素描、色彩等与西方艺术课程相像的技法课为主要内容,误导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使中国画教学失去了其自身的本质含义。让学生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带着西方看世界的习惯性思维,往往混淆了中国画的要义,即“表意”与“表物”的关系,重视“表物”而忽略“表意”。表意者,技法与物体形态皆以绘者的主观表达,即人文思考为依托,识中国画者,不在乎技艺和造型的表象,更不屑于山川草木的物态形似,而重在培养个人的文化涵养和内在修为。
(三)教学上“重技法,轻理论”,“技能主义”使学生失去了思想指引
一些基础课教师在造型能力、色彩训练、线描写生、章法布局授课时往往偏重技法,把不符合国画的西方美学理论引用于教学过程,并将几何形体、静物、石膏、人像等素描科目作为教学的关键,过多地把物相的精准训练确定为教学标准,占用了大量的教学时间,耽误了学生笔墨的训练,忽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力的培养。大部分学生只会机械的照搬考前学习的西化素描,完全不知白描是何物,把人像和景物的写生错误理解成照片式写实,等同于西画客观再现事物,完全背离了中国画学习的初衷。
(四)传统精神文化缺失
“品格不高,落墨无法。”这是现在学生学习中国画的普遍状态。究其原因,不光与其自身潜在的文化素质相关,更多在于高校设置教学内容的平庸,教学大纲的浅显所致。一味强调技法,忽略绘画本身的审美与民族文化中儒道、老庄、礼教等哲学思想的联系,便不能透彻的领悟中国画的意趣,理解、表达中国画中用墨、用笔的层次、笔法,如“墨分五色”“浓淡干湿”“如锥画沙”“刚柔并济”“深藏不露”等无不体现了东方绘画的人文哲学观,这种独特的动与静、宾与主、开与合、粗与细、刚与柔、密与疏、藏与露的审美包含了千变万化的笔墨内涵、美学特征、意境营造。学生若不在品格上下功夫,便难于下笔。
“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厂。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无人顾及和关注”。[4]课堂大部分课程的设置都与当下时代紧密联系的专业相关,功利且实用,而一些看似无用的学科如:古诗词欣赏、篆刻、中国哲学史等却鲜有人问津。
(五)教学基本思路与知识结构不明确
中国现今的知识结构体系经历了大的变革,文革时期一些珍贵的古迹、字画、古董和历史文献资料流失,给艺术教学带来不小的影响。近几十年,深受国学传统文化熏陶的老一代艺术家、教育家大多数已退休,或是风烛残年,难以充当教育的生力军。改革开放后期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批高校教师,深受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影响,因缺乏传统认知的土壤,对自身认知浅显,留于其表,并为当今多元的艺术形式弄的不知所措,知识结构混乱。他们也想尝试改变现今的局面,但在教学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
四、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中国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最为独特,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观念的体现,它融合了哲学、佛教、诗歌、历史等多学科的精华。若要发扬、继承传统中国画,必须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从选择人才、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规律的遵守、文化缺失的补救、材料的多元化等方面创新改革,迫在眉睫。
(一)从完善健全合理的入学考试制度入手
确立合理的选拔绘画专业人才的模式,按照画种性质设置考试科目,健全美术招生考试各项环节,增加线描、书法、绘画基础理论等相关考试科目,把文、史、哲等国学经、史、子、集的内容列为文化修养的考查内容,全面考察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客观再现能力 、综合概括能力、传统文化修养等多角度、多侧面的整体素质。选拔一批合格的中国画接班人。
(二)在尊重中国画教学规律的基础上设置其教学内容
1.“借古开今”,临摹为先导
“借古”,才能寻根。教师应站在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推进中国画的教改,在备课时不仅要涉猎广泛的国学文化,熟知古画的背景知识、画家的个人创作意图以及绘画步骤、设色技法等等;授课过程中,对临摹课的讲授也应层层剥茧、渐渐递进,这样,教师与学生在通过赏析、学习、临摹历史上前人经典画作、摹本、真迹的同时,理解、感悟中国历代画学、画论、画史、画评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养分,以亲身示范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感悟中国画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计白当黑等绘画规律,把握其以形写神、似与不似、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味,如此,教学相长,相互促进。
在高校中国画教学中,掌握古人的表现技法、模式和手段也为今后学生们的国画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外师造化”,重视写生
中国画与西画不管是观察方法、绘画技巧,还是绘制材料和载体上都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画视 “写生”为“写心”,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方面,”而非写实,林风眠认为:“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方面,后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因趋于相异,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5]这种东、西艺术相得益彰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画走向衰微。中国画历来重视吸收和借鉴,在传承、变革中求发展,不能割裂与前人的哲学思想联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既要强调画家内心情感的主观世界,又得尊重客观形体的外部世界,以写生外物来寄于情思。
在写生方法运用上,西画多采用焦点透视法,而中国画则采用散点透视法,需目识心记,移步换景,最后胸有成竹的将意象化的形象和场景记录下来。因高校中国画教学多是从西画素描基础训练开始的,许多学生不了解它们在观察方法上的差异。因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先行示范,多加强写生,使学生对自然景物的掌握做到俯察仰观,远近游目。
3.“书画同源”,以书入画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的题诗中便论述了注重书法在中国画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以书入画,重视用笔的轻重缓急、浓淡干湿、起承转合,把握其骨法用笔的内在规律和联系。“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凡工画者多善书”[6],画形即是写形书意。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才数不胜数。并且从线之起源来说,书、画与河图洛书,与传说中伏羲发明的“八卦”,以及与后来的《周易》一书不无关系。这也许是先代圣贤观宇宙之万物而归纳获得的玄妙感受,以意来传神写照,直抒胸臆。
从中国画形式各要素来看,学习“诗书画印”样样都离不开书法的练习基础,离不开对毛笔掌握的熟练程度,从起笔开画到收笔落款,每个环节都要求笔墨的精准到位,学生只有勤加练习,方能得道。
4.工笔与写意结合,加强山水、花鸟与人物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改善教学手段,设置合理的教学板块
按绘画技法,中国画分工笔与写意;按绘画内容,中国画分为山水、花鸟和人物这三大基本科。当前各大高校一般按照时间段来开课,大一一般是基础课程,到大二以后才开始分不同板块教学。两种手段、三个板块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不能割裂其中的联系,只在某一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会影响学生综合知识构架的缺失而沦落到偏执的艺术道路,阻碍国画艺术的综合理解和吸收。
大学四年的学习时间非常短暂,大一做基本练习,大四以毕业创作、论文为主,掐头去尾,只有大二、大三能全面的分科学习,然而就这两年能将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国画精髓全面吸收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便需要教师耐心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需要教学团队科学合理的搭配工笔与写意各门类的课程,实施一种“工”“写”横向平铺,山水、花鸟与人物纵向深入的教学结构;并且加入多种实验、实践、展示课,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
(三)着重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的培养,补救文化缺失
历代经典的“画学”、“画论”是古代名人名家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若想让学生的国画技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必定要在多看、多研究谢赫的《六法论》、宗炳的《画山水序》、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等“画学”范本上下功夫。其中“六法”从品格的深度审视中国画的高低优劣,即神、妙、能、逸四品,历代画家也以此标准来评定其绘画品格的高低。在主观精神表达上,他们的“法以写道,物以写我”,是中国绘画艺术参透宇宙万物的凝练精华,同时也映照出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若想在讲堂上使学生领悟这些上乘的审美标准,具备一些基础的人文涵养,必须调整文化理论课程安排的比例,保证主修课时的同时增加国学选修课的类别;让诗词、曲赋、印章等古学进入高校课堂;请经、史、子、集等一些国学课的名家到国画课堂上讲学;开设现场示范、学习观摩课和参观、考查课,丰富、开阔学生的眼界,汲取各个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
(四)“格古求新”,探索新材料,鼓励多元化的艺术创作
“君子惟借古以开今。”[7]中国画学习者在了解、参透前贤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而后创新,已达到“格古求新”。“我们就不妨像古人之从竹板到纸张,从漆刷到毛锥一样,下一个决心,在各种材料同工具上试一试,或设法研究出一种新的工具来,加以代替,那时中国的绘画就一定可以有新的出路。”[8]中国画改革首先得从材料上探索新思路,继而卸下传统负担,表现更广阔空间。
其一,从颜色的稳定性和大众性考虑,传统中国画的石色颜料越来越稀缺,可以尝试高温结晶材料和相对呈色好的化学材料来替代;其二,在纸张、绢帛的制作上,尝试不同的介质和区别与古人的方法,打破传统技法的束缚;其三,在画面的构成上,打破单一的维度和时空观念,借鉴平面、立体构成中的重叠、拼贴、并置、分割等手法,使中国画保持内在“心源”不变的状态下,形式上得以更新;其四,在绘画技法和内容选择上,可以从“唐卡”等一些少数民族艺术、民间非物质文化、甚至是儿童画中汲取养分,展现一个新的风貌。
增设新材料实验课、表现创新课,或是开设此类别的实验工作室是顺应当前趋势发展的需要。它帮助学生摆脱了固定思维模式,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交叉学习到其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将这种多元、创新意识推广到艺术创作中去。
五、结语
所谓“入古者深,出古者远”,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当下面临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为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让中国画在世界艺术范围内具有更高辨识度,同时保留特色又不失本真,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们的双向努力。“时代变,事物变,艺术家的思想也应该变。但无论如何变,还是从生活和传统基础上来,否则变不出新的东西。”[9]教育者应以朴素的观察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潜心钻研的绘画精神从教学内容、方法上重新改良,架构崭新体系,夯实文化基础、以适应当前变幻的时代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