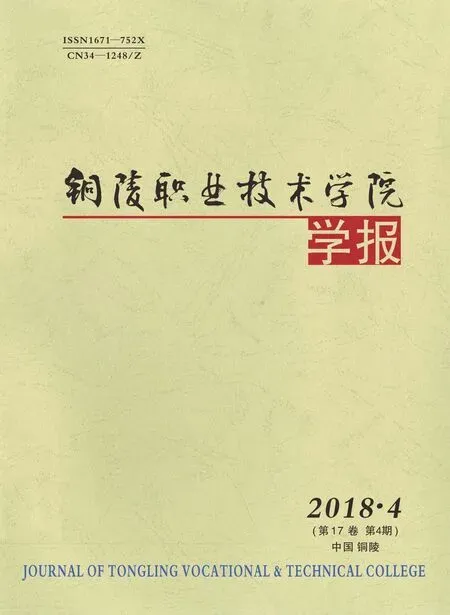海丰文化名人研究:丘东平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陈醒芬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丘东平(1910-1941),海丰梅陇人,七月派小说的中坚作家,“抗战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处女作《通讯员》,代表作《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其他小说作品 《给予者》、《长夏城之战》、《火灾》、《忧郁的梅冷城》等,其中长篇小说《茅山下》未完成。作为海陆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名人,他是中国文艺学的一面鲜亮的旗帜,是建设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宝贵财富。他的创作,以独特的“战争文学”风格揭示了现代作家表现自我存在和实现方式的另类选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花”,其文艺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别具一格。
一、丘东平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海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地
海丰,取义于“南海物丰”,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沿海,东临揭阳市,西连惠州市,北接河源市,南濒南海,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主要有福佬、客家和疍民三大民系,以及少数民族畲族。海丰县历史悠久,人文璀璨,英才辈出,是近代文化名人陈炯明、马思聪、钟敬文、丘东平、柯麟、黄鼎臣等的故乡。1991年2月,海丰县被评为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13块红色根据地之一。海丰县文物古迹资源丰富,境内分布着西汉羊蹄岭古驿道、海丰宋元古城东岳庙、明清古城城隍庙、赤石元明清村寨、明末赤山塔、清初道山塔、明海城黄氏祠堂、吴氏将军府、民国陈炯明将军府等人文遗址。
海丰县有着光荣的抗争与革命传统。早在南宋末年,宋端宗及其大臣文天祥的抗元事迹,在海丰留下五坡岭方饭亭。海丰更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建者彭湃的故乡,红宫红场、澎湃烈士故居、烈士陵园、赤山约农会旧址、中共东江特委旧址及红四师师部旧址等皆深具浓厚的历史底蕴,是孕育海丰文化名人的天然摇篮。
海丰红色政权标志物红宫红场,原为明清时期学宫,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在这里召开海陆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革命政府。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粉刷成红色,会场用红布覆盖墙壁,代表红色政权,此后就将学宫改称为“红宫”。“红宫红场”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广东海陆丰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以彭湃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海陆丰人民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活动场所;“红宫红场”以及里面所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物,犹如一章波澜壮阔的乐曲,向人们奏响革命先烈们头可抛、血可洒、为革命、献身躯的光辉史迹,激励子孙后代们踏着先烈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此外,“红宫红场”更是教育后人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精神的力量之源。丘东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好男儿,他以海丰人为傲,更以广东人为傲,他说:“广东人,尤其是广东军人,就等于男子汉。”[1]聂绀弩的话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念:“他很骄傲自己是广东人。”
(二)高尔基等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
三十年代高尔基文学理论和创作在中国大量传播,影响了一批中国文人,丘东平也不例外,可以说,高尔基是真正意义上对丘东平的创作及其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外国文学作家。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丘东平被迫远离故乡海丰,流亡香港,这期间,他为了生存,饱经沧桑和历练,他凭着对知识一腔热血的渴求,在无意中接触到了高尔基,丘东平像是在黑暗的世界里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特别是高尔基作品里涌动的从贫困与屈辱里摸打滚爬出来的人生经验以及他身上的那种顽强不屈的生命热情,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丘东平,这成为了丘东平人生低谷期的精神粮食。正如他向吴奚如先生说的:“高尔基的作品,给我显示了多么美丽的远景啊!它唤起了我的理想和力量,使我们那几个逃亡者傲慢地生活在脏污的渔夫宿舍里,忘却了蚊虫的吮吸、疾病的传染、饥饿的煎熬……”。[2]也正如罗飞先生所说:“苦难的生活,却使他和高尔基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显而易见,高尔基关注底层、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的写实精神影响了当时七月派的创作,作为七月派核心作家的丘东平更成为了受其影响之下的那支会思考的芦苇。高尔基摒除对浮世的冷漠描写,注重挖掘底层人们的苦难生活,并表达对受压迫和屈辱者的深刻同情,进而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了丘东平毕生的创作,成为丘东平全部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人的创作思想,也在丘东平创作思想中得到印证。丘东平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完善情怀、荒诞意味、寓言式叙事、俄罗斯异域情调、存在主义格调等特色,正是丘东平思想多元化的体现。在托尔斯泰的道德完善情怀这一点上,丘东平受其影响颇深,有甚之更是生成了“不全则无”的道德完美主义的人生信念,他说:“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个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杀。”[4]“不全则无”(All or Nothing)作为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剧本《布兰德》(1866年)中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青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一个口号般铺天盖地,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为了表达不妥协的精神,往往借用这句台词,丘东平也不例外。
(三)新思潮、新理念与新的创作技法的影响
作为七月派中坚作家的丘东平,首先是忠于现实的生活、斗争,继承“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他也自觉坚持文学的现代化走向。1935年春天,丘东平抱着学习军事的信念只身漂洋过海到日本去,他说:“我要到日本学军事去,进士官学校,我要在那将要到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成为真正的军人。”日本是打开世界的窗口,在日本,丘东平受到了新的思潮、新的理念的影响,在创作上也形成了新的技法,特别是日本新感觉派创作,其特色和丘东平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创作风格基本吻合。《沉郁的梅冷城》一文得到了郭沫若“技巧到了纯熟的地步,大有日本新感觉派倾向”的赞誉。
“文学是人学”。新思潮影响下的丘东平,其思想在创作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积极接受了法国波特莱尔、德国尼采、日本新感觉派等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在创作的思想、题材及艺术力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形态。石怀池在《东平小论》中说:“东平作为一个从‘底层’来的东方作家,贯穿在他作品里面的是‘一种新的英雄主义的号召’。”[5]杨淑贤等人则在军事文学发展上指出了他思想及其创作的特色:“给温文尔雅的文学圈带来一个粗犷的灵魂,一股逼人的锐气。”[6]其他如“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7],“常常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抗争以来最伟丽的诗篇”,“充满了悲壮的真实”[8],“苏联战壕小说的真实气息,以及美国反法西斯文学的荒诞意味”[9],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面影”[10]等赞誉,皆来自丘东平思想中新思潮新理念及其创作新技法的展现。丘东平的创作思想指导是多元的兼容并蓄,正如他在1935年11月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论述到小说所表明的:“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11]郭沫若赞誉丘东平:“我在其作品发现了一个新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12]
二、丘东平文艺美学思想的艺术特色
丘东平作为“七月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其创作特色在“七月派”风格的基础上,努力开掘自我个性化的风格,彰显自己的格调。聂绀弩说:“他最讨厌庸俗的大众化论者……要求的语言是猴子的语言,要求的作品是一张白纸。”[13]胡风对他的《第七连》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是英雄的诗篇,那艺术力所开辟的方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加进了一笔财富;那宏大的思想力所提出的深刻的问题,值得人们反复地沉思。”
(一)寓浪漫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格调
胡风说:“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他是把他的要求他的努力用‘格调’这个说法来表现的。”[14]而这种“格调”,首先体现在寓浪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代表作《第七连》中,当战斗进行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死去的团长突然用电话对“我”发问:“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我仿佛觉得,我的团长是在和我的灵魂说话,他的话本应该写在纸上,焚化……”,在现实的灾难中,浪漫主义的笔调在这里别具特色。现实残酷战争中,作者作了大胆的想象“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可当下的现状却是“我们,零丁地剩下了能够动员的二十五个,像发疯了似的晕蒙、懵懂……”,这就是作者浪漫主义手法的浪漫体现。堪称历史抒情诗篇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作者用热情和闲适密切结合,艺术也发展到更大的高度,圣门说:“对比着市上流行的虚伪做作的东西,差不多像汪洋的海洋和日照的露珠,绵亘百里的峰峦和路边碰脚的石子。”这抗日民族战争高亢的旋律正激荡着读者的心灵。
《暴风雨的一天》、《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叶挺印象记》等作品,多数是以真人实事为素材,采用直描、曲叙,想象、歌颂等笔法,在现实的基础上融进了他个人的浓厚炽热的感情色彩,以及独特浪漫而又大胆的想象和剖析,其作品在很强的新闻性、纪实性的同时,也揉进了小说的典型性与文学性,洋溢着抗战初期的时代气息,基调激昂,风格浪漫。
俄罗斯异域情调也是丘东平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丘东平的很多作品中,无论是对建筑物的命名还是给小说人物的取名,都带有俄罗斯风格,特别是以家乡海丰为题材的小说,往往地名和人名都充满了俄罗斯特色。比如有一篇写家乡海丰的土改革命战争的作品,作品中把男人的名字取为什么 “斯基”,女人的名字取为什么“诺娃”,深具俄罗斯情调。
(二)另类的叙事模式建构
丘东平的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自觉地坚持文学的现代走向,接受了日本、法国、俄罗斯等现代派作家的影响。现代派文学所强调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诸如变形、荒诞、象征、寓言式、幽默讽刺等均在丘东平的创作中得到体现。首先,丘东平善于用寓言和象征手法,赋作品于原始蛮性意味的同时有象征诗化了的美学意味。《一个小孩的教养》中这个小孩取名“永真”,正是象征着小孩的诚实和有教养,而恰恰是这种敢说真话的宝贵的优良品质使他的父亲被杀,而永真说真话的结局却是痛不欲生的灵魂拷打与折磨。作品表面上写永真的“没教养”,而作者的创作意图里,恰恰是这种“没教养”才是真正的教养,文章寓言性和象征性艺术意味浓厚。其他如《多嘴的赛娥》、《给予者》、《通讯员》、《火灾》、《长夏城之战》、《慈善家》等作品,皆有寓言式叙事的因素。《火灾》通过南方梅冷镇一个土豪地主陈浩然一家的活动,剥落了地主士绅阶级伪善的外衣,控诉了其残害农民的暴行。小说用寓言的笔法,对陈浩然“慈善心”的反动阶级实质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一切掩盖自己吃人的本质而愚弄劳动者的欺骗,都是应该受到毫不手软地鞭挞。而丘东平善于用寓言和象征手法进行本质的揭示。夏征农在主编的《每月文艺丛刊》中指出:“东平先生的作品,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他常常以寓言的形式,描写当前动乱的社会,在青年作家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凡爱好文艺者,均宜手此一编。”
其次是变形、荒诞的超现代风格。丘东平的作品里充满着悖论和荒诞悲剧,现实与结局之间的不可理喻,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按常理,等等,丘东平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引起民众对战争中人的荒诞命运的哲学反思。《一个小孩的教养》永真说真话却被告知“你错了”,而说真话的结果经过印证也确实是错了,而且错得不轻;《多嘴的赛娥》中赛娥并不多嘴,却死于“多嘴”;《慈善家》中因为慈善家慈善的行为,更多的小鸟被捕杀;《火灾》中“凡是有慈善家的世界,就不能没有灾难”;等等,是为荒诞。丘东平创作中所建构的荒诞一系列现代和后现代方式叙事,其意图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告诉读者,“世界是荒谬的”,而“现实比小说更荒诞”。[15]
最后,辛辣幽默讽刺手法的运用。丘东平十分推崇果戈里辛辣幽默的讽刺手法,面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惨烈的阶级矛盾等严酷事实,丘东平无情地撕去那些伪善者的假面,愤怒地揭露并鞭笞那些草菅人命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用犀利的的笔端勾勒了他们墨黑的“良心”和丑恶的“灵魂”。[16]丘东平的这类辛辣幽默的犀利讽刺手法不但射向农村,也涵盖了文化界以及军旅生活中的非人道的现象。《教授和富人》写一名教授和一位“知名的富人”互相利用、互为表彰的丑陋的交易行为;《诗人》讽刺了那些“比最薄的灵魂灵感还要薄,比最飘忽的灵感还要飘忽”的唯美派诗人,把他们自作多情、百无聊赖、模仿抄袭的颓废生活用讽刺调侃的笔调勾勒得栩栩如生;《寂寞的兵站》通过一个普通士兵黄伯祥的厄运反映了军队中的黑暗现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与残忍;《中国朋友在东京》讽刺了中国留学生中有些人荒废学业,忙于交际应酬的风气;等等。丘东平的很多作品中,或调侃、或庄重,或喜剧性地幽默风趣、或“含泪”的黑色幽默,均讽刺了特殊时代的特殊人与事。聂绀弩说:“他(东平)的文章有幽默、讽刺、调皮的特长”,胡从经说;丘东平认为自己是一名“讽刺作家”,首先是撕去伪善者的假面,其次是要拂拭伙伴脸上的污垢。
(三)战争美学的文体选择
作为革命文学家的丘东平,叙写战争文学是其必然选择。他的作品不时地被冠以“纪实小说”“战争文学”“红色经典”“战地报告”等名称,具有了战争美学的一般特征。而丘东平对战争文学的选择受到法国著名战争小说家巴比塞的影响至深,他在自己的独白里强调的巴比塞的格调是 “最重要”的,“又正确、又英勇”的,这就是对战争美学文体类型的选择与肯定。正如彭燕郊说:“对于东平,战争只是生活,即使是被扭曲了的生活,也还是生活”,“战争当然是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充满希望并被希望所照亮”。他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取材于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时的斗争事件,于1932年10月发表于《文学月报》,该小说为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为革命文学注进新泉,引起文坛的关注和反响,东平也从此选择了一条书写革命文学的道路,从此踏上征程。
丘东平对战争小说的书写,有几个特点,首先,采用纪实方式,表现了鲜明的现场性。他的文字往往力图回到战斗的现场,不停留于战争时间的新闻式报导。其次,以人为本的叙事方式。丘东平的战争美学,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战争所带来的人的内在精神状况的描写,通过对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刻画,来反映战争本身的残酷野蛮,进而通过反思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来揭露时代的黑暗,人性的扭曲。第三,是战争叙事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无论是对修辞手法的选择,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他都极力避免“单一性”和“单纯化”,显示其军旅作家的本色,彰显其独一无二的战争美学特色。最后,在苦难和抗争中构建战争美学文本。傅修海说:“在开掘现代中国战争的‘蛮’性方面,在同代的中国作家中,丘东平实在是少见,甚至是仅见的一个。”[17]丘东平独特的叙事模式给属于那个年代的文坛增添了清新独特的创作新意。正如胡风先生所说的:“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到我们的思想要求最终要归结到内容的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他是把他的要求努力用‘格调’这个要求来表现的。”
三、结语
庞瑞垠说:“东平啊东平,一把有残缺的剑,总还是剑!一块有瑕疵的玉,毕竟是玉!”丘东平作为“七月派”的中坚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左翼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看作是革命活动,其一生虽不尽完美,但却丝毫不影响其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及其当代意义。他是现代战争文学的杰出代表,是用生命和鲜血谱写诗篇的革命作家,他的创作不但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堪称“中国左翼文学的新血液”;而且,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也有重要的贡献,而其文艺美学思想也为现代人文精神添光加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为数不多的“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革命文学家。正如于逢同志所说:“作为一个作家,东平对于艺术的奥秘一直在进行艰苦的探求;而作为一个革命家,东平则至始至终是坚强英勇的战士。”作为人民战士的丘东平,他是“我以我血荐轩辕”英雄形象的最好写照,是民族解放战场上的英雄,他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不妥协的战斗的意志和灵魂,是中华民族光辉的无价的民族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