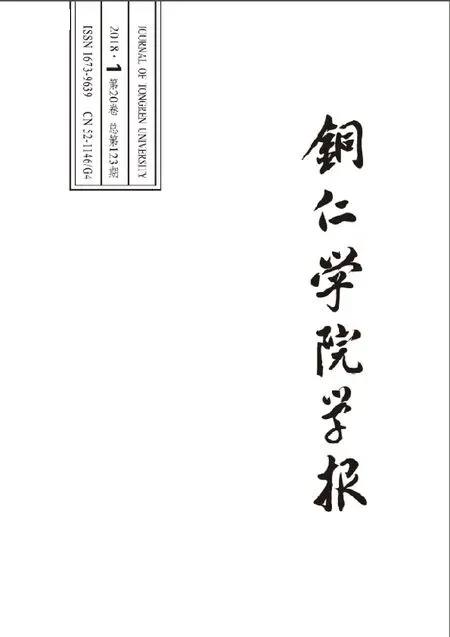解构主义翻译观照下的唐诗英译及文化传播
——以五种中国传统花卉为例
粟向军,谭占海
( 遵义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
翻译是文化沟通与交流的纽带,更是民族文化活力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之崛起离不开“西学东渐”,中华民族的强大也不能没有“中学西传”。无论何时,翻译都是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潜在因素,其作用不可低估。
近年来,中国文化自信与自觉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在不断增强,但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状况尚未根本好转,中国文化出口还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 34%,亚太地区占 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 5%,其余 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1]。可见,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势在必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值得与世界分享的优秀传统文化数不胜数,唐诗就是其中一例。本文结合解构主义翻译观,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唐诗英译中文化载体桃花、梅花、菊花、梨花和芙蓉花五种传统花卉的翻译策略及其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与意义。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翻译观源于语言哲学家对语言和意义本质的思索,是解构主义思想在翻译中的一种体现。解构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治和社会动乱的背景下产生,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其核心观点与西方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左。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以二元论和等级制为基础,强调文学优于非文学、思想的纯粹性胜过表层结构等二元对立,这种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思想恰好是反二元对抗、反中心理论的解构主义者们批评和攻击的对象。解构主义思想主要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著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保尔·德曼和德国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语言、意义和翻译现象全新的深入思考逐渐演变和发展成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一般认为,沃尔特·本雅明的著作《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奠基之作,而德里达则是最杰出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此外,福柯、罗兰巴特、海德格尔等人也都对翻译的概念、语言和意义的本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翻译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意义是不确定的和流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及意义的认识与众不同。首先,从解构主义者的立场看,言外无物,即语言除了自身并不指任何事物。福柯说,语言脱离了它所代表的事物,但又指出语言是了解事物的唯一媒介。其次,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不同的语义链具有无限递归性,即译文是上一个译文的译文(Gentzler, 2004)。换句话,原作与译作之间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symbiosis)。翻译中原文与译文都是意义链,两者共同作用提取“纯净的语言”,即众所周知的共同语,它类似于巴比伦塔被摧毁前上帝和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再次,在解构主义者眼中,译作并非原作重现而是原作的重生和改写,按照德里达的说法“翻译”最好表达成“调节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此外,传统的语言观念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有某种固定的联系,而解构主义者则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固定,且原文背后没有译文必须代表和忠实的核心意义。
(2)译文是原文的来世。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完成之后这部作品也就死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要靠它的译作来维持和延续。所有的文本,无论原文还是译文都被看作是意义的碎片。每一次对原文的翻译和解读事实上都向“纯净的语言”或者说“上帝的语言”迈进了一步。从解构主义角度看,沃尔特·本雅明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源语言就像一颗洋葱,当人们剥完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之后才发现里面没有确定的意义,因此原文的存活取决于译文,即译文的各种特性在延长原文的生命周期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解构主义者认为好的译文是原文能够存活的原因。
(3)差异是解构主义翻译家深入探索语言本质时特别强调的方面。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是解构主义者最关注的地方,而翻译正好为此提供了最佳场所。为了更好地表现和解释这种差异,德里达创造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erance),这是一个非常难于理解却十分重要的解构主义概念。同样,沃尔特·本雅明采用概念“纯净的语言”(pure language)阐发了这一观点。
解构主义翻译观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因此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郭建中[2]、王宁[3]等学者开始评介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其中有人在肯定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创新力的同时也批评了它的极端与虚无(nihilism)。尽管该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对语言和意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及对差异价值的强调都十分契合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需要。此外,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异化翻译策略在理论精神上不谋而合,二者都强调语言文化差异的价值及重要性,对文化译介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唐诗传统花卉翻译的策略分析
花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有悠久的赏花、爱花传统,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具有深刻中华文化内涵的花文化,不仅把花看作赏心悦目之物,也常常是以花喻人、托花言志,借花来表达一种人生领悟和追求。中国文学中,花往往与诗有着不解之缘,例如唐诗中有大量的词语描写各种花卉。现将唐诗不同英译本中五种中国传统花卉的翻译策略分析如下:
(一)桃花英译
桃花在中国文化中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喻意,常被用来喻指女性或是表达对人生的精神追求。试考察下列唐诗中桃花的不同译文:
唐诗原文(崔护《题都城南庄》):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许渊冲[4]译文:
I do not know where the pink face has gone;
In vernal breeze still smile pink peach blossoms full blown.
唐一鹤[5]译文:
Where has the girl’s face gone?
In the spring breeze
The peach blossoms remain smiling dear.
很明显,以上两种译文都将“桃花”直译成“peach blossom”,用桃花忠实地表达了诗人对所邂逅女子的爱慕之心,但二者的区别在于:许的译文在“peach blossom”之前添加了“pink”一词,很自然激发出读者对桃花的联想,从而将桃花的比喻对象(女孩的美貌)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同时与前一句译文中的“the pink face” 形成照应,前后关联有利于读者理解作者以花喻人的涵义。比较而言,唐的译文则需要读者在理解上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才能在“the girl’s face”和“peach blossom”之间建立起认知关联。因此,从译诗的角度讲,译者如果一味忠实于原文而缺乏一定的创造性,那么不但译文的诗意难以体现,而且唐诗中“桃花美女”的文化蕴含往往也难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而许的译文从韵律节奏和词句修辞上都保留了中国古诗的韵味特点,并传达出了诗中“人面桃花”的文化形象。在翻译策略上,二人都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即同时选择了“将读者送出国去”,但许的译文似乎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有利于传递“桃花”所负载的中国文化信息。
(二)梅花英译
梅花是人们以花喻人的首选,因为梅花代表着坚贞不屈、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梅花是中国文学诗词乐于歌咏的对象,如“一树寒梅白玉条”、“梅花香自苦寒来”、“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等诗句都是对它的由衷赞美。此外,人们还常用梅花来表达思乡怀亲之情,即传递对家乡和亲朋好友的思念。因此,如何恰当体现梅花的文化内涵是英译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试分析如下诗句:
唐诗原文(王维《杂诗三首·其二》):
来日依窗前,寒梅著花未?
威特·宾纳[6]译文:
Was the plum, when you passed my silken window,opening its first cold blossom?
许渊冲[4]译文:
Did mume blossoms in face
of my gauze window blow?
曾培慈[7]译文:
On the day of your departure, by your ornate window, Did you notice any budding flowers on those plum trees?
以上译文中“寒梅”有五种不同的译法,美国汉学家威特·宾纳将“寒梅”直译为“cold (plum)blossom”,在文化信息传递上充分还原了寒梅的意象,引发了西方读者对梅花的文化认知与好奇,译文自然流畅,尤其是“my”和“first”突出了诗人渴望从交谈者那里得知故乡消息的思乡之情,较好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曾佩慈将梅花译成“flowers on plum trees”,似乎多了一些通俗,但因为“cold”的缺席诗句并没有将梅花不惧寒冬、傲雪独立的文化形象呈现给读者,此外译文中第二人称“you”和“your”的反复使用也增大了读者阅读时和作者在思乡之情上产生共鸣的距离感。比较而言,曾的译文显得有些平淡无味。
和宾纳与曾的译文比较,许的译文将“寒梅”译作“mume blossom”好像没有“cold plum blossom”和“flowers on plum trees”通俗易懂,但事实上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却更准确到位。在植物学中,梅花的学名为“prunus mume(拉丁语)”。然而西方人常常分不清“梅”、“李”和“杏”,将“梅”译成“plum”(实际上“plum”指“李”)。另外,许在译文中选用了文学词汇“blow”,从文体上体现了诗歌的特点和要求,但美中不足的是“mume blossom”同样没有传达出寒梅的文化意象。总体上看,威特·宾纳和曾佩慈的翻译策略意在靠近读者,采用的是归化法,但对诗歌翻译的文体风格表现不足,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和风格上有一定的差距,而许渊冲主要采取的是异化翻译策略,他的译文较注重从思想和风格整体上与原文保持一致,但在表现梅花的文化负载上却有所缺失。
(三)菊花英译
菊花早植晚登,素有君子之德。另外,菊花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中国人有饮菊花酒与喝菊花茶的传统和习惯。因此,菊花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其含义深远并象征广泛。试分析如下诗句:
唐诗原文(孟浩然《过故人庄》):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威特·宾纳[6]译文:
wait till the Mountain Holiday
I am coming again in chrysanthemum time
许渊冲[4]译文:
On Double Ninth Day I’ll come round
For the chrysanthemum again.
唐一鹤[5]译文:
I’ll be back again to see his chrysanthemum whe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on is coming.
王玉书[8]译文:
When comes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of the year,Surely I’ll come again for chrysanthemums dear.
曾佩慈[7]译文: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we are, To again gather here and chrysanthemum admire.
比较以上五种译文,虽然都把“菊花”一致译成“chrysanthemum”,但很明显五种译法表现菊花意象的方式不尽相同。首先,翻译“就菊花”(指与朋友重阳时节相聚饮酒赏菊)时只有宾纳采取归化译法将其译为“in chrysanthemum time”(菊花时节,即重阳节),而其余的译者将其分别译为“for chrysanthemums”“see his chrysanthemum”和“chrysanthemum admire”以表达诗人重阳时节与朋友一道饮酒赏菊的愿望。其次,从句序上看,宾纳、许、王和曾的译文与原文一致,某种程度上是异化的体现,而唐的译文选择的是典型的英语复合句句式,则是他归化处理的结果。另外,宾纳通过归化把“重阳节”翻译成“the Mountain Holiday”更容易被英语本族语人接受,但这种译法却不利于读者将重阳节与菊花关联起来,从而理解诗人借菊花表达思亲怀远的文化内涵。就文化信息传递而言,总体上许、唐、王、曾的译文因受异化处理而略占优势。
(四)梨花英译
梨花体态娇小、颜色洁白,在暮春时节盛开。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梨花通常具有两层文化含义:一是代表洁白娇美,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描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用梨花象征雪的洁白美丽,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风雪突至而形成的美丽壮景。梨花和雪的观感比较也使洁白如雪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诠释;二是预示别离惆怅,如刘方平的《春怨》:“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梨花开在晚春时节,暗含伤春之意,且“梨”的谐音为“离”,所以人们习惯借梨花来抒发离愁别绪或者怨春悲己的惆怅心情。试比较分析以下译文对梨花文化喻意的传达:
唐诗原文(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威特·宾纳[6]译文:
Is like a spring gale, come up in the night,
Blowing open the petals of ten thousand pear trees.
许渊冲[4]译文:
As if the vernal breeze had come back overnight,
Adorning thousand of pear trees with blossom white.
王玉书[8]译文:
As if the spring breeze suddenly came back o’ernight,To turn thousands of pear trees here in full bloom white.
曾培慈[7]译文:
It is all as sudden as the arrival of spring breezes overnight,At once snow falls like whe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pear trees blossom and thrive.
通过比较以上译文,我们发现宾纳的译文将梨花译成“petals of pear trees”却未作相应关联与解读,貌似还原了原文诗句,但实际上并未忠实体现原文的真正含义,原文对“梨花如雪”的比喻义在译文中荡然无存,这种曲解作者本意的做法更遑论梨花文化内涵的传递。许、王和曾的译文都把梨花译成“pear trees blossom”而且都强调了梨花的“white”,即用梨花的洁白来描写壮丽的雪景,许和王的译文在诗句的语气上也惊人的相似,都使用了虚拟语气来比喻和形容寒风入夜形成白雪皑皑的雪景犹如一夜春风起带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观景象,同时两位译者都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作押韵的特色,“overnight与white”及“o’ernight与night”分别巧妙地展现了原诗句中“来”和“开”的相同韵律,而曾的译文在体现梨花的文化喻意和反映原诗韵律上都不及许和唐的译文。在笔者看来,许唐二人的译文既传递了原作的“真”也保留了原作的“美”,都是译者善用异化和归化法的结果。由此可见,单纯的异化策略于文化信息传递而言也是不可取的。
(五)芙蓉花英译
芙蓉花姿态艳丽,气质高贵,并且“芙蓉”与“富”和“荣”谐音双关,意喻富贵荣华。芙蓉花有木芙蓉与水芙蓉两种,在古代芙蓉花通常指水芙蓉(即荷花)。因此,芙蓉花的文化含义除了谐音指代“富贵荣华”以外,还可以表示“清新自然”之意。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杨贵妃貌美如花且气质高贵的美人形象通过“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生动描写跃然纸上。如何表现诗中芙蓉花代表的文化喻意,各译家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试分析如下:
唐诗原文(白居易《长恨歌》):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威特·宾纳[6]译文:
But the petal was like her face and willow-leaf her eyebrow, And what could he do but cry whenever he looked at them?
许渊冲[4]译文:
Willow leaves like her brows and lotus like her face, At the sight of all these, how could his tears not fall.
唐一鹤[5]译文:
Facing lotus flowers like Queen’s face
And like queen’s brows willow leaves,
How could the emperor refrain
From shedding tears!
王玉书[8]译文:
The lotus and her face were alike;
The willows her eyebrows were like.
How could the Emperor hold back his tears
When he saw all these of past years!
曾培慈[7]译文:
The hibiscus was like the late Lady’s face and the willows her eyebrows,
With such scenery, how could the Emperor not be reminded of the Lady’s countenance?
从宾纳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到芙蓉花被翻译成了“petal”,笼统地代指杨贵妃的容貌,这种归化的处理方法只能向读者传递出杨贵妃貌美如花的笼统意象,译者主要是从读者理解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译文用词俗白,达意的效果较好。许的译文将芙蓉花译为“lotus”,给读者呈现出杨贵妃貌如出水芙蓉(即荷花)的清新美艳形象,既能准确无误地表现作者思想,也容易引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求知欲。通过对比我们还发现,为了保留原作的韵律,译者将译文诗句的词序“芙蓉如面柳如眉”故意作了调整,使“face”与“fall”呼应从而体现原作“眉”与“垂”的押韵,可见译者在追求唐诗英译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唐的译文虽将芙蓉花也译成了“lotus flower”,似乎紧扣原文,但实则有冗余之嫌,而诗句中“the emperor”一词的增补更表现出以读者为主体的归化翻译思想。王的译文将芙蓉花译成“lotus”明确了作者的思想,更突出的是他的译文采用异化法,句子对仗工整,韵律整齐,从译文形式特点上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唐诗韵味。曾的译文和其他译文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将芙蓉花译成了“hibiscus”。由于“hibiscus”与“lotus”实际上分别指“木芙蓉”和“水芙蓉”(即荷花)两种不同的花,因此产生的结果是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意象和联想。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朝时芙蓉多指水芙蓉,即今天的荷花。所以,译者对该诗句中芙蓉花一词的翻译恰当与否值得商榷。此外,译者通过增补“the late Lady”和“the emperor”等词语表明其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译法。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唐诗英译中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兼而有之,但在以上五种花卉英译上主要还是以异化策略为主,这很大程度上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和异化翻译策略强调差异性或异质性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同则不继”的翻译理论观无疑能为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启发与帮助。实际上,文化对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由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世界文化彼此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唐诗英译的解构主义观与异化策略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
总之,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不断深入发展,“西学东渐”仍在持续,但“中学西传”的热情正在高涨。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进程中,解构主义翻译观与异化翻译策略的基本思想观念必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注入新的活力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具体而言,如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在解构主义和异化翻译理论的指引下找到一条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万季飞.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10.29,第1版.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王宁.德里达与解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J].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3-28.
[4] 许渊冲.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5] 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6] Bynner, Witter.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7] ZENG Peici/曾佩慈. English Translation of 300 Tang Poems.From URL: http//scribd.com/28utsc/info.
[8] 王玉书.王译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