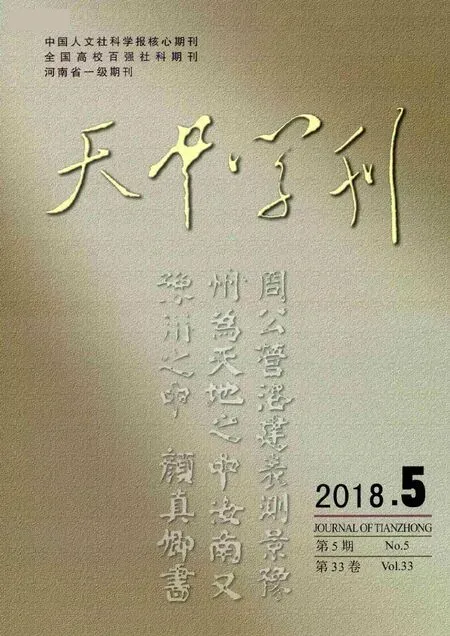毒药与良方:寒食散的两面
章原
毒药与良方:寒食散的两面
章原
(上海中医药大学 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服散是魏晋风度的标志之一,然而关于寒食散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数人视其为毒药,但文献中也有其为治病良方的记载。梳理相关文献并探究这种分歧的成因可以发现,不能武断地全盘否定寒食散的药性。事实上,寒食散是一类方剂的总称,其本为疗疾而创设,如果药物对症,服食得宜,确能奏效;反之,“平人无病”,却妄加服食,又不知节度,则会疾患丛生而后患无穷,堪称“毒药”。
服散;寒食散;魏晋风度
服散是魏晋社会的一种社会风尚,亦是魏晋风度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正如王瑶所言:“整个魏晋名士的生活都和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172自1927年鲁迅在广州进行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之后,关于魏晋风度与寒食散的研究工作一直络绎不绝。特别是余嘉锡《寒食散考》与王瑶《文人与药》两篇文章颇具代表性:余嘉锡对历代关于寒食散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考证精详,条分缕析;王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魏晋士人服散的情况。此后,学界相关探讨仍在持续地进行。应该说,经过深入的探讨,学界已经摸清了魏晋文人服食寒食散的大体情况。
但是,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来看,围绕着服食寒食散的诸多细节仍然迷雾层层,而且随着研讨的深入,部分曾被视为定论的结论实际上也存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寒食散曾经一度被视为类似鸦片的“毒药”,但近年对它的评价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注意到它也具有一定的疗疾效果,甚至有称其为良方者。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医学、文学、史学等角度探究寒食散被称为“良方”与“毒药”的两面。
一、符号化的“毒药”
一提到魏晋时期的寒食散,许多人会下意识地在脑海中涌现“毒药”“祸害无穷”之类的字眼,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
(一)魏晋至唐时人们服散后的种种惨状
历史上记载服散后种种惨烈情形的文献资料颇多,其中尤以皇甫谧描述最为剀切:“每委顿不伦,常悲忿,叩刃欲自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晋书 · 皇甫谧传》)类似记载在余嘉锡《寒食散考》中收录甚详,兹不多述。
由于服散风气太盛,所导致的疾患极多,甚至影响到了魏晋以后的医学发展。汉唐之间的医书有不少专门列治疗服散相关疾病的篇章,多将服散引起疾病的原因视为服食不当所引发的副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医书本质上仍视寒食散为治疗疾病的方药,如《诸病源候论》中单列“解散诸病”。皇甫谧虽然遭受了服食后的种种痛苦,但并不因此而反对服食散。他认为寒食散尽管是“至难之药”,但有特殊的疗效,“心加开朗,所患即瘥,虽羸困着床,皆不终日而愈”[2]34。因此,对于服散大可不必废弃不用,只须小心谨慎,正确节度,严格掌握适应症。但也有人认为服食过多会导致中毒现象,如《晋书 · 哀帝纪》言帝“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孙思邈《千金要方》《解毒并杂治方》卷中专列《解五石毒》,提及:“寒石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此,汉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3]438按照现代学界一般的观点,人们多认为何晏所服的是孙思邈所称的“五石更生散方”,其方主治“男子五劳七伤,虚羸著床”,包括十五味药。身为医药大家的孙思邈明言此方“有大大猛毒”,不啻从医药学的角度对寒食散的“毒性”进行了权威确认。
隋唐以后,虽然服散之风渐息,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时代风潮,其所引发的讨论与思考并未就此偃旗息鼓。后人每每面对魏晋的服散之风而大发感慨,如苏轼所云:“世有食钟乳、鸟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4]108到了清末,许多人目睹鸦片祸国殃民的情况后往往会联想到魏晋时的服散,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将服散与鸦片类比。
(二)近代以来学界的态度趋于统一,多将寒食散视为有毒、有害之物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干脆将其称之为毒药:“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可知吃这种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5]528–529此后,学界的研究多延续这种思路,比如余嘉锡在《寒食散考》中说:“夫人莫不乐生而恶死,而服毒药者独以自戕其生为乐,此不可解也……呜呼,庸讵知后人乃以毒药为嗜好,其祸人家国,有千百于酒者乎?”[6]182又如王瑶在《文人与药》中也明确谈及:“‘散’是一种毒性很重的药,服的时候如果措置失当,是非常危险的。”[1]144应该说,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占据了主流,寒食散已经被符号化,成了“毒药”的代名词,学界常将其与唐宋丹药和明清鸦片相提并论。
(三)当代以来,有化学、医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从现代科学实验的角度讨论寒食散的毒性
20世纪80年代,化学史家王奎克认为,通常人们将五石散中的五石理解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但“白石英是二氧化硅,紫石英是含锰的二氧化硅,石钟乳是钛酸钙,赤石脂是含铁的陶土(硅酸铝),石硫磺是天然产的硫磺”[7]80,并非属于有毒矿物质,更达不到孙思邈所说的“大大猛毒”的程度。另外,何晏所服散方是合张仲景的草、石二方而得,但是由于古籍医方记载混用之故,草方中的礬石实为礜石之误,礜石是无机砷化合物,含有剧毒,“小量服用,可以起促进消化机能、改善血象、强健神经等有益的作用。超过一定的剂量,则会引起轻重不等的砷中毒”[7]80。雷志华、高策则认为寒食散中所使用的紫石英并非过去一直认为的无毒的水晶,而是萤石,过量服食会引起氟中毒[8]104。
需要说明的是,古今对于“毒”的理解不同。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而在中国古代,毒的含义要宽泛许多。李零曾进行过考证,他认为“毒”字与“笃”字有关,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比如,马王堆帛书《十问》中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9]21。在许多场合,甚至“毒”与“药”都是高度重叠的概念,如《周礼 · 天官 · 冢宰》中有“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鹖冠子 · 环流》亦云“积毒为药,工以为医”,明代医家张景岳《本草正》中云“药以治病,以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有偏也……大凡可以辟邪安正者,均可以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故邪也”。直到今天,民间仍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正是这一观念的通俗化表达。但是不论如何,在后世对于寒食散的认识过程中,寒食散逐渐符号化,成了“毒药”的代名词,而它本来创设的目的与功用反而逐渐模糊。
二、“建殊功”的良药
令人诧异的是,在无数人笔下寒食散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它也被诸多人视为令人向往的疗疾良方。嵇含专门写《寒食散赋》称颂它的奇效。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甚至称:“五石、三石,大寒食丸散等药……斯诚可以起死人耳。”[3]748评价之高,令人又啧啧称奇。
事实上,按照主流的观点,早期寒食散相传就是出自汉末两位名医华佗或张仲景之手。皇甫谧考证认为它出自张仲景之手,“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在流传至今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有“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前者明确注明要“宜冷食”,后者则以“寒食散”而命名。众所周知,《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经典著作,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收录于其中的药方当然是治疗疾病所用的,如“紫石寒食散”方“治伤寒令愈不复”(《金匮要略 · 杂疗方》),而“侯氏黑散”则“治大风,四肢繁重,心中恶寒不足者”(《金匮要略 · 中风历节脉证并治》)。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有张仲景用五石汤治疗疾病之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10]2
根据医界学者的研究,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出,王粲所患疾病为麻风[11]29。麻风病古称为“疠”“疠风”“癞”等,其典型症状包括眉落、鼻柱损、肢指脱等。“四十当眉落”正是其重要症状之一。这段记载本意在于称颂张仲景医术诊断的高超,但其明确提到以“五石汤”可以治疗王粲之疾。所谓“五石汤”是否是五石散,不可轻下结论,但是从情理推断,其成分较为接近,它也是由五种石药组成的。再结合《伤寒杂病论》“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来看,可以推断在汉末时五石已常用在防病治病上。
关于寒食散服食后的疗效,最著名的当然是何晏服食之后效果的记载。《世说新语》注引秦承祖《寒食散论》云:“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以“获神效”来形容何晏服食寒食散的效果,可见其验如神。何晏虽然少年富贵,容貌俊美,但由于酒色过度,身体状况极差。《三国志 · 魏书 · 方技传》记载:“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因体质极差,何晏遂服用寒食散以治病。《诸病源候论 · 寒食散发候篇》记载:“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世说新语 · 言语》亦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关于寒食散的盛行,后人多以何晏为首倡者,正是由于其服食之后疗效极佳,不但能治病,而且神清气爽,所以引得众人竞相效仿,遂沿袭成风。关于何晏服食寒食散的效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何晏服食寒食散之后,实际上也散发中毒,呈现“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的样子,所以当时人称其为“鬼幽”。关于这两种说法,区别主要在于何晏“鬼幽”的情状是服散之因,还是服散之果。笔者以为,虽然文献资料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介绍,但是依常理度之,将何晏“鬼幽”之状作为服散之因较为合理。首先,正是由于何晏的提倡,寒食散才盛行,倘若何晏服食后产生了这样的恶果,寒食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盛行开来。其次,虽然何晏寒食散的具体配方不详,但是按照今天对于寒食散主要配方的了解,其中所含石药的成份的确在短期内对“鬼幽”的情形有一定的疗效。
寒食散具有治疗效果的另一典型例子则是嵇康的侄子嵇含所留下的资料。嵇含之子体弱多病,有一次接连呕吐数日,命悬一线,嵇含“决意与寒食散,未至三旬,几于平复”。嵇含为此作《寒食散赋》,在《序》中交代原委“余晚有男儿,既生十朔,得吐下积日,羸困危殆,决意与寒食散,未至三旬,几于平复……”云:
矜孺子之坎坷,在孩抱而婴疾。既正方之备陈,亦旁求于众术。穷万道以弗损,渐丁宁而积日。尔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进不访旧,旁无顾问。伟斯药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还精爽于既继。(《艺文类聚》卷七十五)
从引文可知,嵇含之子年方“十朔”,只是一个十个月的婴儿,患有疾病,十分危险,甚至到了“羸困危殆”的程度,但在服食寒食散之后,很快便“几于平复”。由于亲眼看见了寒食散的效力,所以嵇含在赋中称寒食散“伟斯药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还精爽于既继”。
众所周知,在医学诸科之中,妇科与儿科向来被认为是难中之难,特别是襁褓之中的幼儿,不得已要用药,也要慎之又慎,稍有闪失,便会有性命之虞。但是嵇含在幼子“羸困危殆”之际,却以寒食散来喂服,并且取得了“几于平复”的效果。对于视寒食散为虎狼之药的后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此外,关于晋时名医靳邵的记载虽然很简略,但也能管中窥豹。《医说》记载:“靳邵,不知何许人也。性明敏有才,术本草经方,诵览无不通究。裁方治疗,意出众见。创置五石散、矾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获异效焉。”关于靳邵医术的记载简略,只在《外台秘要》《千金翼方》等方书中保存有其数种方剂,他创置的“五石散”“矾石散”均未流传下来,但是从“士大夫无不服饵,获异效”来看,其方剂效果还是不错的。
与服散所导致的种种痛苦的记载相比,关于寒食散疗疾的资料要少得多,但毕竟是存在的,且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这是讨论寒食散的功用时不可忽视与回避的一面。
三、良方还是毒药
为何同样是服食寒食散,却会有如此不同的效果,更导致后世如此天壤之别的评价,这一问题常令人疑惑不已。综合史料来看,笔者以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有几点值得格外注意。
(一)寒食散与五石散不可混为一谈
寒食散与五石散并不等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讨论魏晋的服散之风时,不少人均会将寒食散与五石散等同,这其实不妥。六朝时期的服食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即凡服食指后须采取寒饮、寒食、寒衣、寒卧等将息措施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种特殊方剂,而应当是某一类方剂的泛称。当时属于寒食散的方子很多,在张仲景方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五石散是寒食散中的某些类别,而且也有所谓“草方”与“石方”之分。由于其主要配方由五种石药组成,故此被称为“五石散”,其中“五石”的具体组成也不同。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服用,但最著名的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由于各种方剂的组成配伍不同,寒食散所追求的功效当然不同,正如《诸病源候论》所云“诸方互有不同:皇甫惟欲将冷,廪丘公欲得将暖之意”[2]34。相应地,寒食散副作用的情况也截然不同。因此,同样是服食寒食散,但实际上服食的具体药方并不相同,服食之后有些获奇效,有些遭大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药物对症因个体差异而不同
即便是药物对症,但由于个人体质不一,即便是同一种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作为一类方剂,寒食散虽然具体配伍有差异,但是其主要的组分是石药。比如,“五石散”即是由五种石药组成,但究竟是具体的哪些五石在后世存在分歧呢?葛洪认为是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隋代名医巢元方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孙思邈认为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这些药按照中医的药性理论,均属于燥热峻烈的药物。比如石钟乳,李时珍认为“其气慓疾,令阳气暴充,饮食倍进而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泆,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阳愈炽”(《本草纲目 · 石部》),易发为淋浊、痈疽等病。
正常人服食热性的药物后会出现全身发热,面色润红等现象,而如果体质偏热的人服食之后,无异于火上浇油,出现种种热毒现象自在意料之中。但是,如果是体质偏寒凉的人,适度服食热性的药物,不但不会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反而会调和体内的平衡,能治疗某些疾病,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三)服散后需要诸多注意事项和措施
事实上,服用石类药物起源颇早,即便是以“五石”治寒,也早已有之。《史记 · 扁鹊仓公列传》有“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的记载,并引扁鹊之言认为“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据考证,此盖出自《扁鹊医经》,可见服石一法当出现在战国,最迟亦不晚于西汉初年。仲景之方似即脱胎于《扁鹊医经》[9]265。但是为何后来却在何晏倡导后变成为祸人间的“鸦片”呢?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医药学的角度来考虑,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在于是否对症以及服散后是否有诸多注意事项和相关措施作为辅助。皇甫谧认为这些措施有“六反”“七急”“八不可”“三五疑”等,如果稍有不慎,举措失当,则祸害无穷,反之运用得当,或有疗效。孙思邈说:“凡石皆熟炼用之。凡石之发,当必恶寒头痛心闷,发作有时,状如温疟,但有此兆,无过取冷水淋之,得寒乃止。一切冷食唯酒须温……凡服石人,慎不得杂食口味,虽百品具陈,终不用重食其肉,诸杂既重,必有相贼,积聚不消,遂动诸石,如法持心,将摄得所。石药为益,善不可加……然其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致杀人。甚于鸩毒、紫石、白石极须外内映澈,光净皎然,非尔亦不可服。”[3]438
基于此,孙思邈又强调并非所有的人、所有的年纪都适合服食五石,认为“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3]438在这里他基于石药性热和随着年纪增长人体内的阳气盛衰变化做出判断:三十岁之前,不适合服石,因为阳气太盛;三十到四十之间要根据体质判断,如果身体过于肥充,也不适合服石;四十以上,阳气渐衰,则“必须服之”,但是在服食的量上要有所控制;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服一剂,七十以上则一年一剂。他还认为:“人年五十以上,精华消歇,服石犹得其力。六十以上转恶,服石难得力。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着诸病。是以大须服。”[3]438
孙思邈作为医药学家、养生学家,其言当然有其道理,而且这也应当是他自己的亲身实践总结。《千金要方》虽未有孙思邈服食寒食散的记载,但却证明他在中年时服食过包括钟乳在内的石药:“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至于将息节度,颇识其性,养生之士宜留意详焉。”[3]438显然,对于石药的认可,是他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
要之,寒食散本是用以治病的方剂,如果对症,又辅助措施得力的话,完全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正如余嘉锡《寒食散考》中所言:“寒食散本以治病,药当期病,未必不可奏功。”但问题在于,汉唐之间的服散之风中,热衷于服食者多是健康的常人,其服散的目的并非仅用以治病,因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多种原因综合导致的。孙思邈在《千金翼方》明言“平人无病,不可造次著手,深宜慎忌”[3]748,正是血与泪教训的总结。
[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4.
[3] 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4]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8.
[5] 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8–529.
[6]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2.
[7] 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0–87.
[8] 雷志华,高策.毒药还是良药?:中国古代寒食散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4):104–105.
[9]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
[11] 王树芬.论张仲景诊王仲宣一案的真实性及其价值[J].中华医史杂志,1997,27(1):29–31.
〔责任编辑 赵贺〕
2018-04-2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办事经费项目(GZY-BGS-2017-40);上海市科技史学科科研项目(P313030414)
章原(1973―),男,山西太原人,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K235,R289
A
1006–5261(2018)05–01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