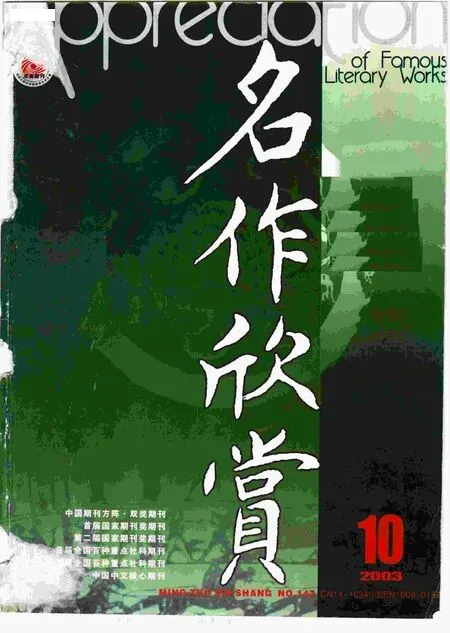曹操《蒿里行》发覆
山西 张德付
作 者: 张德付,现从事国学教育工作,授学于山西太原北辰学堂。
曹操《薤露》《蒿里行》两首诗,用乐府旧题,叙述汉末时事。方东树以真朴许之,谓《薤露》“雄恣真朴”①、《蒿里行》“真朴雄阔”②云云。窃以为以雄许之可,以真许之则不可。《蒿里行》一诗尚有颇多待发之覆,为诗家所昧,兹先征引其诗如次,然后加以分析讨论: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方东树谓:“此言袁绍初意本在王室,至军合不齐,始与孙坚等相争,而绍弟亦别自异心。铠甲四句,极言乱伤之惨。”③方氏认为此诗主要是为袁绍而发,极有见地。所谓义士,余冠英注云:“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领。初平元年春,关东州郡起兵讨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④余氏此说本诸王金绶《古诗评点》,而有误解。王氏注云:“《通鉴》:初平元年春,关东州郡皆起兵讨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⑤王金绶是吴汝纶的弟子,此书评语录自方东树《昭昧詹言》(为夹注于诗句下,时有省改),圈点本诸姚鼐,实为桐城师说。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其实也是以《昭昧詹言》为据,其注释也多沿袭王氏《古诗评点》,而每每故意加以损益,遂使学者昧其所本。王氏注“义士”,其主意在 “推袁绍为盟主”,而非“关东州郡诸将”,也就是说,“义士”就是确指袁绍,而不是泛言关东诸将。因为曹诗后文云“淮南弟”,则曹操所指目自在袁绍,而非其将领,否则“淮南弟”从何说起呢?余氏不解此注,遂致诗旨晦塞。《后汉书·袁绍传》云:
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⑥
此即“义”之本事。初平元年,袁绍以渤海起兵,而关东州郡同时俱起,约盟,鉴于袁氏四世三公,社会影响力大,遂遥推袁绍为盟主。董卓闻袁绍起兵山东,遂诛袁氏宗族在京师者。故袁绍自谓“出身为国,破家立事”,洵为不诬。“乃心在咸阳”,余氏注说义军“初心在直捣洛阳,象刘邦、项籍之攻入咸阳”⑦。此说也本诸王金绶。王氏注引《通鉴》云:“董卓在洛阳,袁绍等军君皆畏其强,莫敢先进。曹操曰:‘举义军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军何疑?’”⑧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迁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⑨
曹操孤兵独进,以致惨败,退至酸枣,而此时“诸军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因此,曹操心中愤愤不平,厉声指责诸将:“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⑩由此看来,《蒿里行》此数句,不可泛泛读过,因为曹操于此可谓心有余痛。而其以兵败的主要责任,归到盟主袁绍头上,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句也不可泛泛解释。《后汉书·袁绍传》载: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⑪
曹操实力渐强,其北方之最强劲的对手就是袁绍。因此,曹操既已挟持天子,马上下诏指责袁绍擅相讨伐。《蒿里行》此句与建安元年诏书正相吻合。
“淮南弟称号”,是指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之事。则此诗必作于建安二年之后,而其下限当在官渡之战前,否则曹操在诗中必然会写到袁绍之败。既然诗句中没有透露任何袁绍兵败的消息,则此诗作于官渡之战前,大概是可以推定的。“刻玺于北方”句,王金绶谓:“《后汉书》术有僭逆之谋,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子,夺之。”⑫然而,袁术时在淮南,不可谓之北方。且既以弟立文,则此句必指其兄袁绍无疑。故余冠英未采纳王氏之说,而另外推求诗句本事,注云:“初平二年,袁绍谋立刘虞为天子,刻作金印。”⑬袁绍谋立刘虞,其事不果。袁绍刻金印,据卜文柏考证,确有其事。⑭然而,我们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说袁绍刻金印的,都是他的对头(公孙瓒、曹操),其可信性不免要大打折扣。因此,不能不令人怀疑此句别有本事,而刻玺也当另有隐情。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
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⑮
原来,袁绍曾经得到一枚玉印,且向众人炫耀,时曹操恰好在座。曹操遂嫉恨于心,多年后形诸诗文,不云得玺,乃云刻玺,盖曹操意谓此印并非得之天,乃是袁氏私刻,因此,玉印一事非天命攸归的象征,只能贻人笑柄罢了。至于袁绍的玉印究竟是无意中得来,还是有意私刻,已经不重要了,其举措已经给对手留下了攻击的口实。
此诗前十句为一层,写袁绍有始无终,为争势利而更酿祸乱,句句皆指目袁绍,就连与之不和的袁术称帝,也冠以淮南弟之名而归咎于他。曹操之心可谓深刻!次四句为一层,写乱伤之惨,其实也是对袁绍的指责。此四句,诗家多未能得其确解。“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指生人之祸。“白骨露于野”,余氏无注,而诗家往往想当然地以为即死尸抛却于荒野,无人掩埋之意。其实不然。《三国志·崔琰传》:
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崔琰谏曰:“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掩骼埋胔,示憯怛之爱,追文王之仁。”绍以为骑都尉。⑯
道路暴骨,即白骨露野,其原因乃在于士卒“掘发丘陇”。此袁绍部下所为,曹操此句诗正指此而言。有趣的是,《后汉书·袁绍传》载袁绍宣檄,指擿曹操的罪恶,其辞有云: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⑰
袁氏檄文“无骸不露”之语恰好可以为曹操“白骨露于野”句做注脚,而“毒施人鬼”也可以说是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数句的绝佳概括(前两句是毒施人,后两句是毒施鬼)。明白了这一点,则此数句读来实令人心惊魄动。《蒿里行》一诗及建安元年责袁绍诏书与袁氏之檄文,实可视为曹操、袁绍之间隔空过招,其相互指斥的内容大略相同,可谓针锋相对。且袁绍、曹操之相互指控,皆属事实,并非污蔑。(《文心雕龙·檄移篇》认为陈琳此檄“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过其虐”⑱,恐未曾考核史实)由此看来,《蒿里行》一诗的写作年代即当在袁氏发表檄文前后。其中诗句,几乎全是对袁绍的批评指控。另外,曹操《董逃歌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学者已指出此诗是曹操宣泄对郑玄趋就袁绍而不依附自己的怨恨。⑲《蒿里行》一诗与《董逃歌词》,同样可以见出曹操对袁绍的嫉恨,也同样反映出其心胸狭窄,为人刻薄的性格。这样看来,《蒿里行》末二句收束(“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以仁自处,实不免于奸欺、诈伪。学者不达《蒿里行》之旨,不知此诗实为曹、袁一段公案,遂使老瞒得以行其奸于百世。呜呼,焉得不谓之雄耶!
①②③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第68页,第68页。
④⑦⑬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4页,第94页,第94页。
⑤⑧⑫王金绶:《古诗评点》,民国戊午刊本。
⑥⑪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74页,第2384页,第2396页。
⑨⑩⑮〔南朝·宋〕陈寿:《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⑭卜文柏:《曹操〈蒿里行〉“刻玺于北方”补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28页。
⑯〔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7页。
⑱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2页。
⑲徐克谦:《曹操为什么写诗讽刺郑玄之死》,《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2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