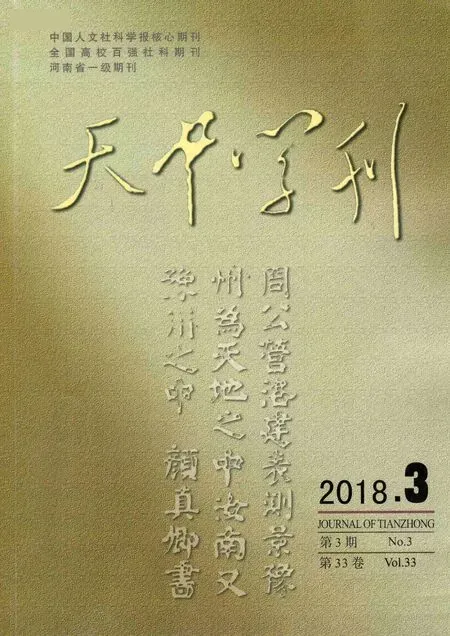萧统评陶渊明三十年研究述评
张梦珂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其诗歌风格因与时流迥异而诗名不显。陶渊明死后,挚友颜延之为之作《陶征士诔》,对其诗文评价仅“文取指达”四字;沈约《宋书 · 谢灵运传论》历数先秦至刘宋文坛之英,独缺渊明;刘勰《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①;钟嵘《诗品》仅将其列为中品。梁昭明太子萧统独具慧眼,将陶渊明的诗文收入《文选》,编《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立传,对其德文并重推崇备至。萧统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为确立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随着“陶学”第三次高潮②的到来以及“文选学”热潮的持续升温,作为两大研究领域的交叉点,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正如穆克宏所说:“萧统对陶渊明作了高度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评论资料,不但对于我们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研究萧统的文学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近30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了初步成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述评。
一、萧统发掘陶渊明的贡献
萧统以储君和文坛领袖的身份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和立传,将其诗文选入《文选》,高度评价其人其文,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萧统发掘陶渊明的贡献,虽说法稍异,但基本达成共识。
钱钟书从文学批评角度关注了这一问题,其在《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中历数六朝文学家对陶渊明作品视之等闲,突出萧统对其独超众类的“解推”[2]。在《管锥编》中,钱钟书进一步强调萧统在陶渊明批评中的敏锐性:“昭明《文选序》大都当时常谈,而其《陶渊明集序》首推陶潜‘文章不群超类’,则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3]1446盛赞萧统对陶渊明批评的眼力超群与真知灼见。于浴贤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的《萧统评价陶渊明探微》一文认为,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远出流俗,他为扩大陶诗的传播和影响、确立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于浴贤同时也指出萧统仅片面维护其心目中的隐逸形象,对陶渊明人格、思想的认识不足。钟优民《陶学发展史》[4]则认为萧统对陶诗的教育作用评估过高,难免招来文学万能之讥,但从总体上考察,萧统仍不失为陶学史上最早且多层次评价的批评家。上述两位学者对萧统评陶局限性的认识颇为难得。
一些学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萧统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所做的贡献。李剑锋于《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发表《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一文,认为萧统在陶渊明中古时期接受史上“写下了最有价值的一页”,因为萧统看到了陶渊明文如其人的特点,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具有“理想化、完美化的倾向”。刘中文于《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发表的《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一文,则强调萧统是真正在灵魂上沟通、融化陶潜的第一人,认为萧统开创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新纪元,使陶学进入自觉时代。
萧统发现陶渊明的首创之功得到普遍认可。刘文忠《萧统与陶渊明》指出萧统是陶渊明第一个真正的知己,是研究陶渊明的第一功臣[5]460–470。张亚新《论萧统的陶渊明研究》认为萧统为后世陶渊明研究开出一种规范,开辟陶学的新时代[5]557–578。边利丰于《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 2期发表的《萧统——陶渊明经典的“第一读者”》一文,更是从多个方面肯定了萧统解读陶渊明的开创意义。钟涛、包琳于《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发表的《论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述了萧统为陶渊明所做的贡献:《陶渊明集》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具有开山之功;《陶渊明集序》是宣传陶渊明其人其文的有效广告;《文选》为陶作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而萧统作为传播主体具有重大影响力,为后世陶渊明的传播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思路。这一研究视角虽已不算新颖,但在萧统评价陶渊明的问题上还是首次,也引发我们不断从新的角度看问题。
总之,相关研究者一致认为,萧统是高度评价、深度挖掘、全面开发陶渊明文学成就的第一人。在陶渊明遭到冷落时,萧统以伯乐相马般的慧眼发现其价值,尤为难能可贵。
二、萧统推崇陶渊明的原因
萧统有着深厚的“陶渊明情结”,《陶渊明集序》云:“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6]200地位悬殊、毫无交集的两人,往往被称为隔世知音。萧统为何如此推崇不合时宜的陶渊明呢?学界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外在因素
一是复杂的政治背景。俞绍初注《陶渊明集序》曰:“此文为陶渊明文集之序,而全篇重点却在申说韬光晦迹,遁世隐居可以全身避祸。此种思想之产生,盖与昭明晚年因埋蜡鹅事发,遭梁武帝猜忌有关。”[6]201汪习波、张春晓于《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发表的《颂陶藏心曲 谦抑避雄猜——论萧统〈陶渊明集序〉的另一面》一文,也认为萧统尊陶“有相当明显的避嫌自明意味”。梁武帝阴狠猜忌,萧统后期身处的环境恶化,迫使他借助陶渊明以自保,自表谦心,暗示廉退,明扬风教,实为避嫌。萧梁重隐风尚的大背景,则为其避嫌自明“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林其锬《略论萧统为何特别钟爱陶渊明》从时代思潮、萧统的地位处境、心境变化详细考察,认为复杂险恶的宫廷政治环境使萧统向往身心自由的理想社会,这与陶渊明的诗作思想是一致的,故向陶渊明寻求心灵解脱[7]579–590。这一说法显然不如“避嫌自保说”深刻。
二是重文的社会环境。郭晓春于《求索》2013年第9期发表《论南朝三大家对东晋陶潜之评价》一文,文章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析,认为陶渊明受到萧统关注有其“必然性”。梁武帝对文化非常重视,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萧统作为文坛领袖,爱好文学,且较为开明,对风格不同的陶渊明持包容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从萧统对身边文人的赏爱程度来看,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文化环境,仅为萧统发现陶渊明提供了可能性,并非所谓“必然性”,毕竟陶渊明不是当时公认的文坛代表。当然,萧统也可能是受到身边文人的熏陶。曹旭《品语发微之二——钟嵘、二萧与陶诗显晦》认为萧统嗜陶,很可能是受钟嵘品陶的影响。他将《诗品》与《文选》《陶渊明集序》进行对比考察,发现二人对陶诗的审美趣味、品评标准是一致的[8]199–201。
(二)内在因素
刘中文于《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发表《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一文,认为萧统推崇陶渊明,应从萧统自身寻找原因,二人在人格深处相契合,并从三方面进行探讨:其一,惺惺相惜,敬仰陶渊明的高尚品格。其二,志趣相投,都对山水情有独钟。其三,思想相通,都认同隐逸的生存方式。时人多推崇陶渊明的隐逸人格,沈约将其归入《隐逸传》,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开篇即用大量笔墨论述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也是其隐逸思想的表达,这应是他推崇陶渊明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李娜的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陶渊明接受史研究》认为与萧统推崇陶渊明,与其豁达的胸怀、超越世俗的眼界及其文学观不无关系。萧统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崇尚“典而不野,丽而不浮,文质彬彬”的中和美,而陶渊明的作品符合这一审美标准。结合当时浮靡华丽的文风来看,萧统或许是将陶渊明作为典范来宣传自己典雅的文学思想,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流,以矫正时弊。
上述研究均是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进行的合理推测。萧统推崇陶渊明应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些答案综合起来考察,才更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当然,无论从哪方面入手,我们都不能脱离史料与时代背景。
三、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
《文选》选陶诗8首,分隶于“行旅”“挽歌”“杂诗”“杂拟”四类,文仅《归去来兮辞》一篇。苏轼曾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认为陶渊明诗歌“可喜者甚多”,而萧统“独取数首”[9]30。萧统既如此推崇陶潜,却为何在《文选》中选录陶作仅寥寥9篇?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选陶诗者另有其人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在《文选编辑的周围》一文中根据《文选》收录陶渊明的作品比谢灵运等人少得多等矛盾,对《文选》的编者是萧统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认为萧统仅是挂名,并未参与实际编辑工作[10]31–46。之后,刘文忠也提出大胆猜测:“选录陶作入《文选》之人,未必就是萧统。”[5]469认为陶诗的选录殆假手于人,并非出自萧统本意。但这一观点显然证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陈复兴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的《陆机与萧统的文学批评》一文,也认为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在《陶渊明集序》中凸显无误。而《文选》所录未全面体现出萧统的文学思想与编辑意图,恐怕是参与编选的文人难以摆脱文学时代风潮所致。
这涉及《文选》的编者问题,目前学界仍在探讨之中。即使《文选》成于众手,但萧统的核心地位和组织工作,是无法轻易否定的。再假使陶作的选录为刘孝绰等人实际操作,而萧统作为太子及总编辑,其意愿未被尊重也不甚合理。
(二)二者非在同一时期
张虎升《知音异代论萧陶——兼驳萧统弱冠为陶潜结集说》认为《文选》的取舍标准与《陶渊明集序》存在较大差距原因是《文选》的编定和陶作的结集不在同一时期[11]101–108。胡耀震《〈陶渊明集序〉的写作时间和萧统评陶的独异众说、自相矛盾》也提出“不同时间”说,认为与萧统不同时期的境遇、心态有关:其早年编纂《文选》为“娱玩文华”,而《陶渊明集序》作于“中大通二年(530年)春之后”的晚年,因忧失太子之位而“突然强调起风教”[12]469–480。此说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且不说《文选》的编纂年代尚无定论,关于《陶渊明集序》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是大通元年(527年)③,而此文得出的时间结论及“突然强调起风教”等说法,恐经不起推敲。
(三)文学价值取向不同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教育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功能,二者相辅相成。丁永忠发现在萧统的时代里,文学的这种双重价值功能被人为割裂,他于《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发表的《论萧统〈陶渊明集〉与〈文选〉的不同文学价值取向》一文,认为形成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萧统编纂二书的目的不同,体现着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一为娱乐、审美;一为“鉴诫”“风教”,《文选》和《陶渊明集序》就是这两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分别体现。高思莉于《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发表的《从〈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探析萧统的文学观》一文沿袭丁永忠的观点,认为《文选序》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而《陶渊明集序》在肯定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教化功用,萧统超越时代的局限,以不同的价值标准编纂《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体现了他成熟全面的文学观。
(四)主观与客观之差异
曹旭以为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在主观与客观、不同场合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方面”[8]198–199,即出于个人爱好,萧统私下可对陶渊明爱慕有加,而《文选》作为总集,选篇则需依据当时公认的审美标准。持论相同者颇多,如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认为《陶渊明集序》所言仅为萧统一己私见,而《文选》中选诗的多寡则更多地反映一时的公论[13]。王运熙于《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发表的《陆机、陶潜评价的历史变迁》一文,也认为“《陶渊明集序》表现的是萧统个人的爱好,而《文选》的选篇数量,则体现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共识”。《文选》作为总集,具有官书性质,不能纯粹以萧统的个人喜好作为选录标准,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结合当时的文学风尚与审美趣味来看,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五)二者之间并无矛盾
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认为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之间其实并无矛盾。贺忠顺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发表的《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评萧统的〈陶渊明集序〉》一文,指出萧统奉献了一部《陶渊明集》,这是陶渊明独有的殊荣。鉴于既有专集,《文选》中少录当合情合理。齐益寿《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认为萧统对陶作本身的评价并不高,仅是对陶渊明人格敬仰的自然延伸,而《文选》所选陶作与萧统的风格特色是一致的,也与《文选》的选文标准是相符的,因此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之间并无落差[7]526–556。马朝阳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的《从〈文选〉选陶渊明作品见萧统的文学观》一文认为,从整体上看,《文选》所选陶作大致涵盖了陶渊明的风格与思想,萧统选文定篇具有宽容性、进步性,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提倡对萧统要“以古识古”,设身处地,同情理解,方能做出客观评价。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无论如何,萧统总算让陶渊明诗文在《文选》中占得一席之地,并以其平淡自然的意境特立于绮靡华丽的主流文学中间。这不只彰显出文学批评家萧统的预见性,也显示出他超越时代局限、突破思想囿见的勇气。
四、《闲情赋》之“白璧微瑕”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渊明诗文评价很高,唯独对《闲情赋》颇有微词,以为是“白璧微瑕”,由此引发了一场聚讼不休的千古公案。苏轼率先发难:“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9]30此后附和者甚众。责难派的阐释则是建立在对《闲情赋》的歪曲之上。元李治力驳东坡之说:“《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东坡以昭明为强解事,予以东坡为强生事。”[14]清王闿运亦以为《闲情赋》“有伤大雅,不止‘微瑕’”[15]。钱钟书则直接为萧统辩护,十分精辟:“其谓‘卒无讽谏’,正对陶潜自称‘有助讽谏’而发;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萧统所批评的,是陶渊明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截然相反,即“事愿相违,志功相悖”,犹“悬羊头而卖马脯”,妙语解颐,一针见血。因此钱钟书认为萧统对陶渊明“品评甚允”[3]1220–1221,无可指责。
袁行霈承袭了钱钟书的观点,他于《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发表的《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一文,从《闲情赋》的题目、承传关系、赋中的自白,断定陶渊明写作的主观动机确实是防闲爱情流宕,但也认为铺陈太过难免失其主旨,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相悖,因而给萧统等人留下话柄。萧统的批评本无可厚非,但致使原可顺利发展的情类赋从此受挫,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这一见解十分独到。
今人批评萧统者亦不在少数。丁浩然于《江海学刊》1987年第6期发表的《〈闲情赋〉新探》一文认为萧统批评陶渊明之论不全面,是因为他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缺乏深刻理解,并从四个方面批判萧统思想的狭隘性。范子烨指出萧统对《闲情赋》的责难,无疑是“用道德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以宗教情结绑架了文学创作,以个人趣味充当了批评标准”[16]。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萧统的违心之论:“只能看作是处在梁武帝尊儒以及宣扬佛教的‘断房室’的风气之下,萧统不得不作的一种说教,并不代表他的主要倾向。”[17]当然,这一说法过于牵强。顾农曾于《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风教与翰藻——萧统的文学趣味和〈文选〉的选文趋向》一文批驳了此说,并认为萧统的文学趣味近于儒家正统,而《陶渊明集序》中重视“风教”以及批评《闲情赋》,儒家气味尤为浓厚。学者多站在顾农这一边,认为萧统之所以否定《闲情赋》,在于它不符合萧统所继承的儒家正统的文学思想。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认为萧统是通过对《闲情赋》的否定来宣扬自己“防闲私欲之情”“合符礼节”的文学思想[18]。吴晓峰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发表的《也谈萧统的文学观》一文认为儒家正统观念是萧统的思想主流,无论他如何推崇陶渊明,但终归还在于其“有助风教”,表达爱情太过直露的《闲情赋》自然在排斥之列。
出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观和太子以德为师的身份意识,萧统认为《闲情赋》有伤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萧统特别强调陶潜诗文的社会教育作用,而这篇赋明显与此背道而驰,因此《文选》中不予选录。然而这又引发了另一问题:萧统既责《闲情赋》,为何却在《文选》立“情类”赋并收入与之相似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明张溥云:“(萧统)擿讥《闲情》,示戒丽淫,用申绳墨,游于方内,不得不然。然《洛神》放荡,未尝删之,而偏訾此赋,于孔子存郑卫,岂有当焉?”[19]今人周振甫于《名作欣赏》1984年第2期发表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读陶渊明〈闲情赋〉》一文也认为萧统用“劝百讽一”来批评《闲情赋》,是“违背他选文的标准的,是自相矛盾的”。如郭子章所言:“昭明责备之意,望陶以圣贤。”[9]154袁行霈指出萧统对《闲情赋》苛求,而对其他爱情赋态度宽容,实际上是用两种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评论的。他对陶渊明期望太高,要求完美,于别人无妨的作品,在陶渊明这里便被贬为瑕疵。刘琦、杨秀云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的《〈文选〉情类赋与萧统的伦理观》一文,将《闲情赋》与《文选》“情类”赋进行对比,归因于萧统的伦理观,指出《文选》“情类”赋的选篇符合人伦道德与儒家伦理规范,《闲情赋》则与此不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陶渊明集序》高度赞美渊明诗文而《文选》仅选陶作9篇的原因相似。力之系列文章: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的《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和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的《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认为是《陶渊明集序》与《文选》中“道德(功用)与审美之价值取向分殊所致”,并进行细致考辨,反复论证,有较强的说服力。正如钱钟书所言:“瑕抑为瑜,不妨异见。”[3]1221《闲情赋》是瑕是瑜,见仁见智。后人根据《闲情赋》“有无讽谏”形成“言情”与“寄托”两派主旨之争,而《闲情赋》也在不断地争论中愈发彰显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萧统对陶渊明是发自内心的仰慕与爱重,还是带有政治功利与道德伦理色彩的指瑕,客观上都促进了陶渊明的传播。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呈现良好态势,总体评价较为公允。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这一论题,涉及《文选》编者、编辑时间、选录标准以及编者的文学思想等“选学”重大课题,更涉及陶学发展史、陶渊明接受史、《闲情赋》主旨之争这些“陶学”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缺乏系统性,一些问题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新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发掘。笔者认为,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是将两大领域相结合,仅从一方面入手难免会陷入僵局,只有把握全局才能开阔眼界,才能有所突破。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的深入探索,必然要建立在对萧统、《文选》、陶渊明及其诗的充分认识之上。而以此作为链条,可将两大领域紧密串联,彼此之间相互借鉴,转换视角,融会贯通,相互促进,这将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
注释:
① 《隐秀》篇的补文虽有“彭泽之□□”,但关键两字是缺文,且学界一般认为此补文系明人伪托。
②“继宋代和清代曾出现的两次研究陶渊明的高潮之后,20世纪末更出现了空前繁盛的第三次高潮”,参见李华《钟优民〈陶学史话〉述评》(《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③ 俞绍初注释此序时说:“日人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云,他所见之《陶渊明集》旧抄本,在此序言之后有‘梁大通丁未年昭明太子萧统撰’十三字,若此说可信,则此序撰于公元527年。”学界多赞同此说。
[1] 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8.
[2]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88–92.
[3] 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钟优民.陶学发展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9–11.
[5]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文选学新论[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6]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7] 中国文选研究会.《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8] 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G].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M].韩基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1] 张国光,等.古典文学新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12] 赵敏俐,佐藤利行.中国中古文学研究[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13]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4.
[14] 李治.敬斋古今黈[M].北京:中华书局,1995:4.
[15]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3086.
[16] 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07.
[17]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 2卷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564–565.
[18] 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6.
[19]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