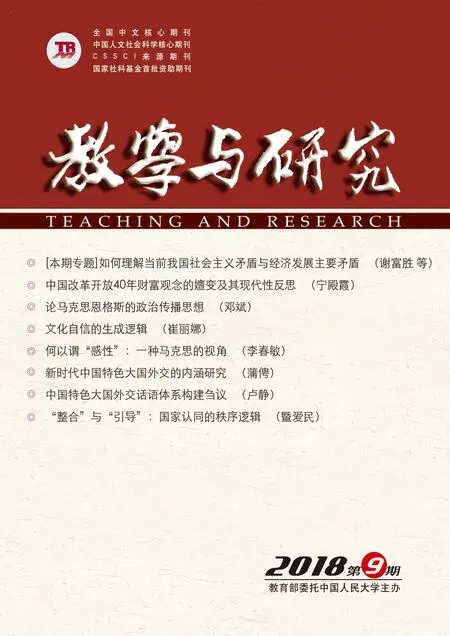机动性与固定性的辩证法
——大卫·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及其局限
国内学界有关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内在矛盾的指认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须知,哈维正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space economy)危机的必然性。那么,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何以必然包含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是什么?它为何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危机?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又将遭遇何种危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构成了哈维整个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核。为突出其重要性,本文将这一内核称为“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国内学界更倾向于考察哈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是什么,而很少追问其根源是什么。即使有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之具体根源(如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矛盾)的分析,但却未能进一步追问在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对立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加深层的矛盾。更为可惜的是,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这一深层根源,但却未能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予以系统考察和揭示[注]参见赫曦滢,赵海月:《大卫·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第83-106页,人民出版社, 2014年。。鉴此,本文拟详细探讨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阐释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之深层根源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相关理论之局限性。
一、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视角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地理学上的矛盾之处”。[1](P50)这一矛盾即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mobility)与为实现这种机动性而采取的空间形式的固定性(fixity)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根本要求:资本和劳动只有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实现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依赖于一系列空间机制的建造,但这些空间机制却具有固定性,必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成为“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2](P83)因此,在哈维看来,“固定性与机动性之间的根本矛盾内含于有关资本在时空中积累的理论之中”。[3](P77)
那么,何谓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何谓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二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我们首先来考察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哈维的理论目光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实现过程。在他看来,价值实现就是价值普遍化的问题,而价值的普遍化与空间整合(spatial integration)密切相关,因为“倘若未能建立空间整合,价值形式的普遍性就会受到干扰”。[4](P578)所谓空间整合即指在不同位置开展的不同劳动如何通过交换行为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在不同位置生产的产品如何通过交换顺利地到达购买者手中以实现其价值,而这个“到达购买者手中”的过程就是一个空间整合的过程。它意味着打破一切物理空间障碍,重塑整个空间关系(即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关系)和空间格局,建立以价值为核心的关系空间[注]哈维认为,空间不是某种单一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内涵。因此,他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概念与哲学史上的不同空间观念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三重空间观:使用价值—绝对空间;交换价值—相对空间;价值—关系空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由这三种空间共同构成,而资本积累的逻辑就在于通过空间生产不断将绝对空间转化为相对空间,打破绝对空间障碍,进而建构一个以价值为核心的关系空间。参见David Harvey: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Stuttgart(Germany):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PP93-118.。
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整合呢?哈维指出,虽然空间整合的必要条件是“商品交换”,但其充分条件却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所给定的”。[4](P579)所谓“机动性”,是指不同形式的资本(劳动力属于可变资本)在地理空间中自由迁移的特性。哈维认为,机动性并非各个生产要素的迁移,而是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迁移。资本既可以作为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又可以作为劳动过程来迁移,不同形式的资本具有不同的机动性。正是不同形式的资本在地理空间中的不同运动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塑造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和空间格局。哈维详细考察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
第一,商品形式的资本的机动性。哈维指出,“使货物到处迁移的能力界定了商品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4](P580)“商品”是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有它顺利地从生产者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商品才能实现其价值。商品能否“顺利地从生产者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就是商品的机动性。在哈维看来,这种机动性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程度。对资本主义而言,“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5](P532)所以,交通运输业不仅是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生产价值,它出售的产品是空间或位置的变动。这种产品的价值会成为其他商品价格成本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这种产品的价值,“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5](P538)在哈维看来,正是通过革新交通工具和运输联络,资本主义不断地重塑着全球的空间格局。
第二,可变资本和劳动力的机动性。哈维指出,存在两种关于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不仅是劳动力商品的承载者,更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移动受到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影响和控制。劳动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迁移、反抗、再生产等活动主动地塑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然而,哈维显然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劳动者倘若被看作一个在本质上由资本统治的对象,就无非是可变资本,即资本本身的一个方面。在可变资本的运动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律是内嵌在对一般资本的机动性和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律当中的。”[4](P586)这样,劳动者在迁移时的自由恰好转变为它的反面,为了寻求基本的生存条件,劳动者不得不跟随资本流动。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力单纯的自由迁移。劳动者越具有机动性,资本就越可以轻易地采用新的劳动过程,并凭借更加有利的位置来获利。在哈维看来,正是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在地理上的自由迁移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
第三,货币资本尤其是信用货币的机动性。在哈维看来,信用货币与其他货币形式(如金条、铸币、钞票等)不同,它是现代社会一切货币中最具机动性的货币。它通过传输技术在全世界自由而快速地迁移,完全打破了一切物理空间壁垒。“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电传、电子转账等等——它们都能帮助信用货币在‘转瞬之间’穿越空间。这种货币明显可以在基本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游荡;它可以整合并协调生产与交换,却几乎不用理会物质性的空间壁垒。”[4](P593)信用货币的机动性除了依靠一系列通讯设施的建立外,还必须在“尘世”中找到它的代理人或执行人,并通过这些主体建构出一整套执行相应任务的组织、制度、机构和方案,如金融中介、股份公司和虚拟资本市场、银行体系以及国家制度等。在哈维看来,正是通讯设施和社会机制的建立为货币资本创造了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流动的虚拟空间。
可见,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从而促进了价值的普遍化。但是,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并不是靠自身实现的,它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空间机制的生产。没有运输和通讯网络的建造、交通工具的革命,以及一系列社会机制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建立,资本和劳动就不可能在地理上自由迁移,从而也就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
二、空间形式的固定性
为实现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资本主义必须生产出一系列空间机制,进而重塑整个空间格局和空间关系。然而,哈维发现,在大规模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仿佛越来越倾向于在空间中固定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进一步积累,还是向全球的扩张,资本必须首先在空间中“就位”,即固定下来,才能进行流通以实现积累。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在“为其他形式的资本争取更强的地理机动性的斗争中,地理上的固定性也越来越强”。[3](P78)
在这里,哈维所谓的“固定性”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就物理属性而言,空间产品必须被固定于空间之中,不容易移动;另一层则是就价值实现形式而言,任何空间产品都是一种资本,如果它无法快速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抑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自身价值,那么这种资本就具有相对固定性。为实现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而采取的空间形式,大都具有这种固定性的特征。根据哈维对每种空间形式不同功能的不同描述,可以将其主要划分为三类: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消费基金(consumption fund)和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
首先,作为空间形式的固定资本。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固定性与运动之间这种深刻的、易引发危机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固定资本是这个矛盾的核心”。[6](P112)那么,固定资本为何会成为这个矛盾的核心呢?因为固定资本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它完整地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体现出来。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固定资本的不动性与可动性的矛盾。从物理属性来看,固定资本可以分为不动的和可动的两类。哈维指出,这两种固定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景观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业中,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在地理上的移动模式,受限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的增殖需求,而“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价值的收回,取决于运动中的资本对特定地点的不可移动资本的使用”。[6](P112)其二,固定资本的物理属性与价值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固定资本价值的实现程度不仅与自身的物质属性相关,还受制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如市场的竞争环境、公司的利润实现能力、技术变革的速度等。因此,在哈维看来,固定资本的价值从表面上看仿佛具有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但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存在。其三,固定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矛盾。从生产的立场来看,固定资本表现为“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4](P378)但从资本流通的立场来看,固定资本却只是“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所面临的障碍”。[4](P379)固定资本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凸显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
其次,作为空间形式的消费基金。哈维认为,“某些商品在消费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些商品没有被直接消费掉,而是被用作消费工具”。[4](P367)这些商品就是消费基金,如住房、餐具、厨具等。哈维指出,如果从卖方的立场出发,消费基金对资本流通没有太多影响;但就买方而言,消费基金的固定性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消费基金,尤其是住房,不仅具有物理上的固定性,而且同样具有价值实现形式的固定性。购买者必须储存一定量的货币或者以借贷、利息等形式对其进行支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消费基金的使用被整合到了生息资本的流通当中。借出货币的依据是消费基金项目的使用者的未来收益”。[4](P369)消费基金所承载的对未来收益的债权,可能远远超过其使用者在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导致货币资本脱离其劳动基础,引发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
最后,作为空间形式的建成环境。建成环境是“许多景观的大杂烩,而这些景观是按照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规定、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塑造出来的”。[4](P372)其独特性在于“空间方位或空间位置对于建成环境的要素是一个根本的非附带的属性”。[4](P373)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建成环境的所有要素都采取了商品形式。一方面,空间、方位、位置对于建成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建成环境又是由各个经济要素聚合而成。因此,建成环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地理秩序、空间关系、复杂的、复合的商品。在哈维看来,“建成环境的创造使我们不得不把关于地点和空间的安排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属性。我们现在必须认为,积累过程运行在一种按照资本主义特有的逻辑来界定的时空框架中。”[4](P376)建成环境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属性和空间形式的固定性[注]需要指出的是,在哈维那里,除了以上三种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以外,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固定性的影响。这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技能、习俗以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劳动力和信用货币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参见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580-596页,张寅译,中信出版社, 2017年。。
资本和劳动在地理空间中的自由迁移,主要依赖于以上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商品形式的资本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依赖于交通网络、运输工具等固定资本的生产;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依赖于一些经久耐用的、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立,这些设施实际上就是建成环境;货币资本的机动性同样依赖于一系列通讯设施等固定资本的生产。但是,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却使得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固定在土地上,无法满足资本无限度积累的需要,而将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必须打破的空间壁垒。在哈维看来,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与为实现这种机动性而采取的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法,构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既是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重要途径,又会带来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全新危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正是在这种不断建立固定性,又不断打破固定性,一步一步转移危机,又不断生发新危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向前发展。
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对资本积累而言,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是绝对的,只有资本和劳动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建构空间整合,实现价值普遍化,从而实现资本积累。相反,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则是相对的,任何空间形式的生产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一旦它无法再继续满足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它就必须被摧毁,被重建。因此,哈维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斗争,那就是资本在特定时刻按照自己的条件创造了一个自然景观,但又不得不摧毁它,通常在危机产生时、在随后的时间点将它摧毁。”[7](P23)那么,资本主义为何“通常是在危机产生时”将这些景观摧毁呢?这就关涉到哈维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与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哈维指出,“资本的剩余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就会散失价值、遭到毁灭,这些阶段就叫作‘危机’”。[4](P26)而危机的总体根源则在于马克思曾试图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得危机在生产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哈维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三块”危机理论。
“第一块”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即指“资本与运用它的机会相比是过剩的”,[4](P315)哈维将这种生产过剩的状况叫作“资本的过度积累”。[4](P315)其根源是资本家追逐生产力无限度革命的倾向与整个资产阶级追求积累的持续平稳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哈维指出,为了解决生产领域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采取了“时间—空间修复”(spatio-temporal fix)策略,即以固定资本、消费基金和建成环境等空间形式的生产为前提的“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两种化解或转移危机的方法。
所谓时间延迟,是指资本主义通过固定资本、消费基金和建成环境的投资和生产,使资本剩余得到盈利性的吸收,进而推迟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资本流通领域的时间。然而,对这些空间形式的投资和生产,需要信用体系作为保障。在此,信用体系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资产阶级不仅可以通过信用体系对固定资本等实体经济进行投资,还可以对货币本身进行投资,用货币赚取货币(利息)。最终,信用体系变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虚拟资本‘颠倒错乱的形式’走上了前台,让‘颠倒现象’得以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4](P425)当虚拟资本的无限增殖彻底脱离了它的货币基础,就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第二块”危机,即金融危机。
哈维指出,“第二块”危机主要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本主义”,[4](P503)而一旦我们将视域扩展到全球,“考察危机形成过程中的国际性方面”,[4](P509)危机的地理特性就凸显出来。在这里,资本主义利用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资本的空间转移,为本国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寻求新的盈利性空间,从而实现危机的空间修复。但是,地理扩张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空间竞争,这将导致全球空间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第三块”危机。在哈维看来,这种危机的最极端表现形式是以帝国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大战。
可见,“第二块”危机和“第三块”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危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解决“第一块”危机的过程中。那么,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为何必然遭遇全新的危机呢?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在“时空修复”过程中遭遇的“第二块”和“第三块”危机都有其具体根源:第二块”危机根源于信用体系造成的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对立;“第三块”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空间竞争。实际上,在这些所谓的“根源”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的根源,那就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早就内含于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过程中。
在哈维那里,“修复”(fix[注]“fix”一词本就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固定”,另一层含义是指“修复”。哈维用这个词来表达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化解自身危机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将空间生产的“固定性”与“机动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包含于其中,凸显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具有两层含义:就物质意义而言,它是指“整个资本的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取决于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2](P94)就比喻意义而言,它是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2](P94)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危机实质上就源于这两种意义间的矛盾,即“机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是为了实现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使过剩资本得到盈利性吸收,从而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另一方面,“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又不能脱离它的物质基础,必须以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为前提。在这里,空间形式固定性的建构不仅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机制。只要对空间产品的投资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资本就会不断地生产出这种固定性。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这种由空间形式固定性的建造而形成的“地理惯性”,而一旦这些空间形式丧失了吸收剩余资本的能力,无法满足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由这些空间产品造成的价值丧失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不得不摧毁由自己建立起来的地理景观。
由此可见,“机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矛盾才是引发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就“第二块”危机而言,正是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使得“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物质形式中的流通”不得不“通过诉诸纯粹货币形式的资本来调节”。[4](P378)这里凸显出来的实际上是货币资本的机动性与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货币资本的持续流动(无限增殖)以固定资本等空间形式的价值实现为前提,而这些空间形式的价值却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4](P378无法满足货币资本持续增殖的需要。当货币资本的持续增殖脱离了产业资本(主要指固定资本、消费基金和建成环境)的物质基础,金融危机就将来临。因此,资本主义不得不摧毁由自己建立起来的固定资本等物理景观,重新创造新的物理景观来满足货币资本持续流动的需要。就“第三块”危机而言,帝国主义的空间竞争同样以空间生产为前提,无论是将本国的过剩资本投资于其他区域的空间生产活动,还是将本国的过剩资本借贷给其他国家,都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机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矛盾扩展到其他空间。在通过另一区域的机动性来打破本地区的固定性的同时,另一区域的固定性将越来越强。这不仅无法彻底消除危机,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四、“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的局限性
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核,它在一定程度深化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内在矛盾的认识是全面的,相反,这一认识有其根本的局限性,即它仅仅揭示了空间关系的机动性与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指认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将成为空间关系的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却没有考察空间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内化于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
对哈维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资本如何建构自身的历史—地理景观,以及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如何成为空间关系的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他更加强调社会过程中各个空间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真正创造了这些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空间形式表征出来的社会关系。哈维实际上是站在资本逻辑的客观立场,过度强调资本逻辑对劳动主体的制约性,进而弱化了劳动主体自身的创造性力量。正如他在考察两种有关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的观点时,更倾向于将劳动力当作单纯的可变资本,从而将劳动力的机动性作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即使他也强调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的塑造作用,但他是从劳动者作为资本逻辑的附属物这一层面出发去考察劳动者的主体性力量,而不是将劳动者作为资本逻辑的建构者去考察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劳动产品的生产,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生产。“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5](P450)
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生产为前提的。只有劳动者在各个地方、场所和区域中不断地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空间形式的生产才成为可能。用于空间生产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积累起来的,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才成为了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因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研究,不仅要考察空间形式与空间关系之间的矛盾,更要考察内化于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和空间关系本身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实质。由于哈维是将空间生产置于资本流通的环节中予以考察的,他实际上将劳动主体排除在外了。相比于哈维对劳动主体自我建构历程的忽视,同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的哈特和奈格里,则专门探讨了劳动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影响。笔者以为,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哈维“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在这方面的不足。
哈特和奈格里更加强调从主体维度去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于劳动形式的转变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劳动形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兴起。所谓“非物质劳动”即指“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一种情感反应”。[8](P108)非物质劳动并不意味着物质形式的消失,相反,大多数非物质劳动的生产都依赖于物质形式的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的存在。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强调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是就其产品而言的”。[8](P109)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这不是说非物质劳动已经在世界生产体系中普遍化;相反,非物质劳动在全球劳动中只占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却支配着当今社会的其他劳动形式。因此,非物质劳动的主导性“是就质的维度而言的,它对其他劳动形式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倾向性的影响”。[8](P109)所以,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生命政治劳动’这样一种新的霸权形式,它是指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关系,并在最终意义上生产社会生活本身”。[8](P109)正如工业劳动在马克思的时代虽然只占有全球生产中的一小部分,却对其他劳动形式和社会生活具有霸权作用一样,非物质劳动是当今资本主义的霸权性劳动形式。
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探寻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根源。在他们看来,由于非物质劳动的兴起,资本越来越无法控制劳动本身了。知性劳动或情感劳动完全可以在传统的劳动过程之外进行,资本只能占有非物质劳动的结果,却无法占有非物质劳动的过程。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在空间中的分散化,资本越来越多地开始对非物质产品——信息、专利、技术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商品化。“资本与生产性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有机的了,因为资本日益外在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生命政治的劳动力不再是资本主义机体内一个起作用的器官,而变得更具自主性,而资本通过其规训性政权占有装置以及剥夺机制等,寄生在劳动力之上。有机关系的断裂与劳动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处于资本生产和管控危机新形式的核心”。[9](P114)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实际上与劳动形式的转变而带来的劳资关系的改变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由于越来越无法掌控直接的劳动生产过程,而只能“寄生在劳动力之上”。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而且内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只有理解了内化于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和空间关系本身的矛盾,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总之,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仅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空间形式与空间关系之间的“客体矛盾”,却没有揭示空间生产中的“主体矛盾”,这构成了哈维“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的根本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