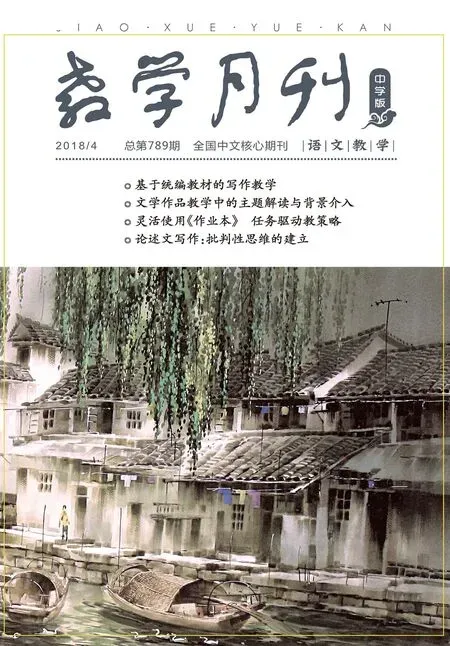文学作品教学中的主题解读与背景介入
杨雁怡 王斌杰
(浙江省富阳中学,浙江杭州 311400)
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主题读解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创作背景介入作为解读作品主题的一种手段,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似乎成为文学作品教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凡面对一篇文学作品,大部分教师会习惯性地将作品的相关背景置于教学的初始阶段,其用意就是通过背景介入更准确地把握作品主题。可与此同时,许多教师又会习惯性地在另一个教学环节中撇开作品的创作背景,带领学生重新走入作品主题的探寻之旅。但是,撇开创作背景的主题探寻往往带来“过度解读”的问题,而教师往往又不能清晰地界定或判断哪些是误读、哪些是合理解读。
读解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理论繁杂,流派众多,尤其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在中学的文学作品教学中,对主题的解读需要有一些关于解读的基本立场,否则将陷入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一、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
M.H.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动有四大要素,即世界、作品、作家、读者。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不同的批评家往往会特别强调其中的某一个要素,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1]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批评家基于不同的批评立场来解读作品,从另一个角度讲,对某一个要素的强调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批评观,最终形成了以作者创作为依据的“作者中心”范式、以文本的语言结构为依据的“文本中心”范式和以读者接受为依据的“读者中心”范式。
这三种文学批评范式的历史沿革是一个互相否定又前后接续的过程,体现了文学批评者对文学理解的变化,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同时也有各自的不足。
“作者中心”批评范式强调作者至上,文本与作者之间关系紧密,文本是作者的影子,而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通过梳理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凡与作者相关的一切元素诸如生平、经历、时代、人际、事件等都会进入文本理解的视野,并被视为与文本有着某种因果关系的重要支撑。这一批评理论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知人论世”的批评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习惯将与作者相关的一切元素称之为“写作背景”,写作背景与一篇作品的主题之间必定有很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于一个作品不可能是在真空写作状态下形成的,它一定和作者创作时的境遇、心情相关,也和作者的创作风格相关,当然也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小说《药》的主题就与鲁迅小说一贯来的创作风格、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国民性等诸多背景紧密相关,如果缺失这些背景,对该文的读解将遇到极大的阻碍。
“作者中心”批评范式在历史上曾和实证主义结合,把文学批评变成发掘和研究作家及文学史的考据学,其结果很有可能“会使诗本身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2]228,而在语文教学领域,往往表现为不顾作品本身的特质而将之与作者的性格、气质以及其作品主体风格一一对应起来,形成僵化的阅读路径。
“文本中心”批评范式从“作者中心”范式中跳出来,将阅读与解读的焦点从作者转移到文本,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文本本身、在于它的审美特性,文学的意义应该从文本中找寻,因为文本就是一个独立的语意系统,无论是作者想体现创作意图,还是读者要理解作者的意图,借助文本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背景资料。“文本中心”批评范式将文学批评聚焦到文本本身,把作品独立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原了文学作品独立的审美特性。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进步,但其完全割裂与作者、历史、现实等背景,甚至割裂与读者的联系,把它从背景参照系中孤立出来,将其视为一个完全自足的意义体系,专注其本身的形式、技巧、符号等内容,抛弃其社会功能及教化意义,显然又使文学批评走向了一个极端。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抽离作者创作的主题指向,或者可能性的主题解读,将教学内容定位于单一的言语表达形式,忽视这种表达背后的意义,以及作品所具有的历史、现实、未来价值。这样的“文本细读”显然是一种买椟还珠式阅读教学。
“读者中心”批评范式是对之前的批评范式的拨乱反正,它关注了之前批评观中很少或没有关注的读者问题,把读者的阅读活动、审美经验、阅读能力等纳入了批评的范畴。它以关注文学阅读的过程以及文学效果为重心,摈弃之前批评范式的单一注视,把读者的阅读与作者、文本作为一个双向交流的体系,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于读者的相互交流之中,突出了读者对作品意义建构的重要性。但是,“读者中心”批评范式在张扬读者在作品意义构建方面的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本读解的混乱,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把“读者中心”批评范式称为“感受谬见”,并批评说“感受谬见则在于将诗和诗的效果相混淆,也就是诗是什么和它产生的效果”,其“结果都会使诗本身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2]228那也就是说,在“读者中心”批评范式中,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很有可能被读者感知消解甚至取代,既然文本的意义可以被读者任意感知,那么读者对文本的读解的合理性又如何来界定和评价呢?在语文教学中,这样的情况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个性化解读与创造性解读不断被人无限拔高的时候,似乎学生所有的解读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成立。如此,文学作品教学势必陷入标准缺失的混乱和虚无之中。
由此看来,若文学批评的视域仅限于文学活动的某一要素而忽视其他要素,必然带来文学批评的缺陷,只有融合各个要素,实现各个要素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文学批评才可能从偏执走向完善。接受美学大师、“读者中心”批评范式的代表人物姚斯就这样反思:“接受美学并不是独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它并不足以解答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不如说,它是对方法的片面反映,它不拒绝任何补充,而且还有赖和其他原则配合。”[3]
二、背景介入的路径与意义
上述三种文学批评范式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作品教学,尤其是关于作品主题读解。在背景介入与否以及何时介入的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的状况,这和教师是否自觉地有选择性地将这三种文学批评范式融入教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自觉和有选择性的表征就是能根据不同的文本样式以及阅读能力培养指向来决定采用何种范式。
(一)基于作者意图的主题解读与背景介入
有的文学作品主题单一,而且主题指向的现实性非常强。这就需要有对应的写作背景材料的支撑,否则主题读解会非常困难。如果学生缺失背景材料,阅读就会失去意义。比如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那首著名诗歌《近试上张籍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整首诗表面上写新婚女子婚后第二天要去拜见公公婆婆时的忐忑心情,如果不提供相应的创作背景,学生很难明白朱庆馀创作此诗的意图,虽然诗题已经提供了部分并不充分的背景。笔者在课堂上是这样来进行背景介入的:
(1)当时唐代应进士科举的士子有向名人行卷的风气,以希求称扬和介绍于主考。
(2)张籍当时是水部郎中,以擅长文学而又乐于提拔后进与韩愈齐名。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生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故写下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
如果缺失了这个写作背景的支撑,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无法准确理解的。对于这样的作品而言,也只有把握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学生才可能进入对作品创作技巧层面的研习,也才有可能对主题理解有进一步深化。可见,写作背景的介入对解读这样的作品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二)基于作者意图消隐的作品主题解读与背景介入
有的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但随着时间流逝,作品的原初主题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广的主题。这个时候背景介入就要非常慎重,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破坏作品文学上的审美意义。这样的文本,其审美价值的研究要比原初的主题指向探寻有意义得多。
同样以诗歌教学为例,唐代宋之问那首流传甚广的《渡江汉》,多少读者为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所表达的游子的思乡情怀感染,无须任何背景材料的介入,读者能感受到久离家乡的归乡者的惴惴不安:“这惴惴不安里有对家乡故人生死存亡的惦念,有对故乡是否拥抱游子的忧虑,还有若惊若喜的回乡之情,这是一种人人心中都有的普遍情感,读到它就勾起人对故乡的一分眷念。”[4]16而事实上,这首诗却是神龙二年(706)宋之问从流放地逃往洛阳时途径汉江所作。如果介入这样的背景,那份美好的情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近乡情更怯’成了被通缉的逃犯潜逃时的心理报告,‘不敢问来人’则成了逃犯昼伏夜行鬼鬼祟祟的自我坦白。”[4]16所以葛兆光先生指出:“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历久弥新、传诵不绝的抒情诗歌,它并不传达某一历史事件、某一时代风尚,而只是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像自由、像生存、像自然、像爱情等等,它的语言文本只需涉及种种情感与故事便可为人领会,一旦背景羼入,它的共通情感被个人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坏了意义理解的可能。”[4]23
(三)基于开放文本的主题解读与背景介入
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得以流传并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除了作品具有文学史上独特地位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审美结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经验背景下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这样的作品进入教学领域,阅读教学的价值取向就有了多种可能性。特别是对主题的读解,无论是基于作者意图的读解,还是基于读者理解的解读,都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内容。
在教学中,许多教师往往会双管齐下:或先解读作者意图,再进行个性化解读;或先进行个性化解读,再回到作者意图的解读。
笔者认为,如果教学取向定位在作品原初主题的探寻,从某种程度上有益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思考力,因为阅读需要撇开纷繁的阅读“干扰”,回到创作的原点来审视作品,把自身放在作者的背景立场上来观照作品。这样的解读恰如德国诠释学的鼻祖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5]他认为,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就是一种由读者理解作品时心态向作者创作时心态的心理转移。事实上,这种主题的探寻不失为一种有趣而有意义的教学行为。如莫泊桑的名篇《项链》的教学,许多教师和学生从多个角度解读作品的主题,或诚信,或担当,或虚荣,甚至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但是揭示“人生的无常与尴尬”这个原初主题的读解未必会显得封闭与肤浅,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原初的主题远比后来的花样解读要深刻得多。
如果教学取向定位在作品主题的多元解读,首先决定于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与读者没有任何关系的自足自给的封闭结构,它是一个“半成品”,一个有待读者不断填充的意义结构。这为作品主题的多元解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其次是学生具备多元解读的能力,这个能力取决于学生积累阅读经验的多少,这种经验会以“先见”的方式或者形成一定的阅读图式影响后来的阅读。正如海德格尔说的:“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6]伽达默尔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绝不可能存在摆脱一切先见的理解,尽管我们的认识意愿必然总是力图避开我们先见的轨迹。”[7]
笔者在进行《清兵卫与葫芦》一课的教学时作过这样的处理:先不提供任何写作背景,甚至连作者都隐去,让学生自主探寻作品的主题,通过合作学习,学生基本上能将作品与现实意义联系起来,梳理出作品的隐喻结构特征。显然,这样的解读正是基于对文本本身的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延展性而实现的。而当笔者提供了有关志贺直哉的丰富的背景资料的时候,学生对主题的解读很快发生了变化,主题指向由时空上的宽度变成了特定背景中的深度。
:
[1]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6.
[2]维姆萨特威,比尔兹利罗.感受谬见[G]//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5.
[4]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G]//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23.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8.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