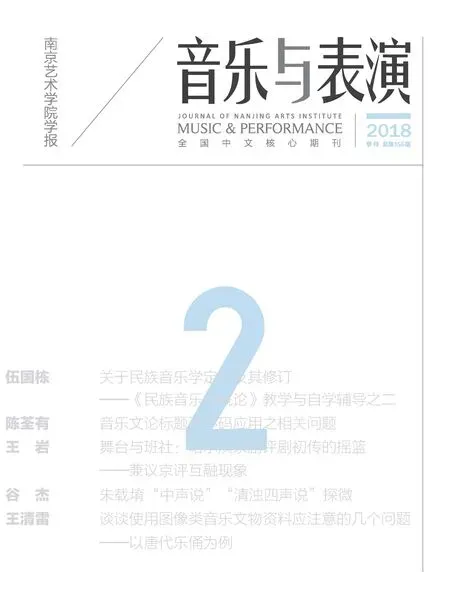河南曲剧形成的历史动因新探
河南曲剧又被称为“曲子戏”“文明曲子”“洛阳曲子”或“高台曲”,它是在民间曲艺“河南鼓子曲”的基础上,借鉴了民间歌舞“踩高跷”的艺术元素而形成,并吸收了俗曲小令和其他戏曲的优秀成果而逐渐成长起来,表演风格质朴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在河南及周边省份影响广泛。河南曲剧形成于清末民初洛阳关林兴起的“高跷曲”,随后在豫西地区迅速兴起,至20世纪20年代转变为“高台曲”后,在艺术风格上完全成熟。清末民初是我国地方小戏迅速兴起的重要时期,从河南曲剧的形成与发展看,很多戏曲并非于一时一地形成,而是有更为丰富的源流。本文通过对河南曲剧形成的历史动因分析,意图揭示民间戏曲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为地方戏曲的当代转型和发展提供历史视角和借鉴。
一、因俗而生:民俗需求促进了高跷曲的出生
河南曲剧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洛阳南郊的王屯村(今属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其首创者是晚清秀才王凤桐(1822—1898)。
王凤桐的最大功绩是将流行于南阳、洛阳两地的鼓子曲融合,并结合民间歌舞“踩高跷”,创制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让化妆之后的高跷艺人边踩高跷、边演唱鼓子曲,时人称之为“高跷曲”。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在一年一度的关林庙会上吸引更多的群众观看,击败对手拔得头筹。1875年开始,王凤桐组织本村踩高跷的村民和鼓子曲玩友开始训练这一新的表演形式。果然,这一年的关林庙会上,王屯村高跷队凭借新颖的演出形式一炮打响,在与“哑巴高跷”的竞赛中毫无悬念地胜出。此后,在每年的关林庙会上,王屯村高跷队大受欢迎,受邀往各村献演。王凤桐大受鼓舞,“挑选其易学易唱、音乐价值高的曲牌在王屯附近的范滩、矬李、李屯等村教唱,四乡,尤其七里河玩友争往拜访求教,因而这些曲牌便很快得以推广”[1]65,“高跷曲”这一新的戏曲雏形很快传遍河南府(洛阳)、汝州、陕州等豫西各地。
初期的“高跷曲”分为相公、姑娘、丫鬟与和尚4个角色,采取轮流演唱的方式:一人演唱鼓子曲,其他三人配合以舞蹈,演唱时到一定节口时,跷下众人齐声应和。演唱曲目主要来自鼓子曲,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如《三国》《水浒》《红楼梦》《蓝桥会》《小姑贤》《戒洋烟》《劝赌》等。此时的高跷曲已经初具“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的戏曲特征,这可以从当时人们将“高跷曲”称为“唱故事”“玩故事”和“高跷故事”得到印证。只是由于表演方式仍然采取独唱和一唱众和的方式,唱段具有明显的曲艺特征。舞蹈与唱腔、故事情节的结合尚不紧密。因此,初期的“高跷曲”既具有民间曲艺的特点,也兼具民间歌舞的特征。
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民俗活动、更离不开参与其中的底层百姓。除了参加庙会,“高跷曲”也在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闲暇之余,人们往往凑在一起,在庭院或麦场拉起场子,边踩高跷边演唱“高跷曲”,给单调贫乏的生活添加了些许颜色和欢乐气氛。与鼓子曲的坐堂弹唱相比,高跷曲的演唱形式更加灵活,克服了因空间狭小而无法满足更多观众需求的局限,将原来封闭性的厅堂表演改为广场式的群众性表演,无形之中扩大了它的受众面。
其后不久,王凤桐开始编写剧本,这是“高跷曲”转变为戏曲的转折性事件。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现有角色的简单分工和曲艺式的叙述方式之间产生矛盾,难以生动流畅叙述故事和展开情节,也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二是坐堂弹唱的鼓子曲字少腔繁,冗长易拖沓,无法与明快活泼的高跷节拍节奏相配合,从而走腔掉板。“高跷曲”的上述弊端导致了人们贬称其为“哼曲子”“哼高跷”,认为它是“憨唱憨扭”,不上档次。于是,尽快向戏曲转变,由厅堂个体性欣赏方式转向广场群众性欣赏方式,便成为王凤桐面临的紧迫问题。
他的这次改革以确立新的表演方式并革新唱腔为核心,改编的第一个剧目是《蓝桥会》。《蓝桥会》变独唱为对唱,一人饰一角,变曲艺式的故事叙述为剧中人物的道白与表演,并根据剧情需要将原有唱词进行增删改修,增强了唱腔的戏剧化表现。
李振山在《洛阳曲剧史话》中收录了2段王凤桐传授的早期曲牌,其中的[背弓]调唱腔还保留着鼓子曲舒缓悠长的唱法特征,旋律在中低音区进行,节奏缓慢,唱词优雅。但同时,唱词已改为第一人称,唱腔在旋律、节奏、力度、音色等方面具有更为鲜明的起伏对比,戏剧化效果明显,更能深入表现人物性格和抒发情感。
以《蓝桥会》的排演为标志,这时的“高跷曲”已经具备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这是河南曲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此后,王凤桐又改编或移植了《王三姐拜寿》《小姑贤》《卖瓦盆》《翻车》《小两口关灯》《梅绛雪》《拾玉镯》等剧目,终因积劳成疾,于1898年溘然长逝。《蓝桥会》的编写时间距离1898年应该不会太远,笔者将它推定在1888至1898年之间,那么,河南曲剧的雏形也大致在此时间段内。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以上剧目作为高跷曲的代表作,传遍了豫西地区。
二、因时而动:时代风尚促进了高台曲的确立
许多人将高跷曲艺人登台演出、“高跷曲”变为“高台曲”,看作河南曲剧形成的重要依据,这是时代风尚主导下的一次重要变革。1926年5月18日(民国15年农历四月初七),以临汝县(今汝州市)艺人朱万明和关遇龙为首的会社“同乐社”,在登封市颖阳镇李洼村演出①李振山《洛阳曲剧史话》中提供了另一种大同小异的说法,同乐社首先在颖阳镇的宝林寺登上牛车搭的临时舞台,后转至李洼村戏楼演出3天。见:李振山.洛阳曲剧史话[M].//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工文史资料,第十七辑[C].洛阳:西工区政协,2002:31-32。期间,因天下大雨地面泥泞,艺人无法踩高跷演出,但是围观群众迟迟不愿离去,纷纷要求继续唱下去,于是有人找来牛车,把门板搭上去,搭成临时戏台,让艺人登台演唱。在旧社会,人们常把登台演出和收取酬金看作戏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玩友一旦登上舞台演唱,就会被人们当成下九流的“戏子”,以“玩友”自称、视收取报酬为耻的高跷曲艺人们死活不愿意,怕老家人知道了今后抬不起头。然而,他们终于拗不过热情的现场观众,“经他们反复商量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发了誓,赌了咒(意思是任何人回临汝都不准说),毅然甩掉了跷腿登上了(牛车)戏楼,演出了《周老汉送女》《蓝桥会》等戏。”[3]演出结束后,高跷曲艺人对此讳莫如深,忌讳别人说自己是戏子,于是相互赌咒发誓不许外泄。
从现实情况看,20世纪初,在豫西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高跷曲艺人登台演出的事件,如各地文献所记载:“1919年元宵节期间,洛阳市西工区邙山镇东陡沟村(今中沟村)的高跷曲艺人登上了“白衣台”(灯棚),进行演出。”[4]“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河南南阳一带,有几位鼓子曲友异想天开,把地摊鼓子曲搬在高台上扮演。”[5]据《河南文化史》统计,“从1910到1926年的17年中,至少有过5次登台活动”[6]:有邓县大堂的盛长娃(宣统二年)、南阳独山的王旭东(民国9年)、洛阳大屯的张新乐(民国14年)、洛阳东陡沟的刘洛(民国15年)、临汝的朱万明(民国15年,登封市李洼村)等。
但是,以上这些登台演出,都没有临汝县同乐社的这一次登台演出造成的轰动大,朱万明、关遇龙他们的这一做法很快传遍四乡八地,各地的高跷曲艺人纷纷效仿,于是,“高跷曲”演变为“高台曲”,河南曲剧正式形成。因临汝县同乐社的主要成员来自汝州市,因此,一般认为,河南曲剧发源于汝州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戏曲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历时性、动态性地考察这一形成过程,不必拘泥于一时一地。依据前述事实,笔者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河南曲剧的形成时间应该是清末民初,形成地点是以洛阳、汝州和南阳为核心的豫西地区。
不可否认,地处洛、宛必经之地的汝州是河南曲剧的重要发源地,汝州籍艺人在当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纷纷受邀到各地指导高台曲的演出,大多数还担当主角,对河南曲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贡献。首先,朱万明对于初创时期的河南曲剧贡献甚大,除了将唱腔加以革新并推广以外,他还改进了乐队编制和乐队伴奏。以他和关遇龙为首的同乐社最早闯进了城市戏院,立足了脚跟,为河南曲剧的商业化演出和艺人的职业化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同时,他还培养出了一大批河南曲剧名家,如许雷、刘保才、樊大立、王俊卿(王秀玲养父)、“三朱”(朱六来、朱天水、朱双奇)、陈万顺、李金波(王秀玲之师)、李玉林(张新芳之师)、钟国顺(琴师,宋喜元之师)等。其次,汝州籍的剧作家大量涌现,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剧本,极大地丰富了河南曲剧的剧目。例如,夏店乡毛寨村的私塾先生郭成章(1901—1981),改编和创作了《风雪配》《六月雪》《陈三两爬堂》《陈妙常》《风雪配》等剧本;朱万明改编和创作了《求灵芝》《活捉三郎》《杨八姐闹店》《苏三爬堂》等剧目;纸坊镇的韩宗皋改编和创作了《巧中巧》《错中错》《朱买臣休妻》等剧本。许多剧本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对于河南曲剧由三小戏转变为舞台大戏,影响深远。第三,以朱万明和关遇龙为首的同乐社1926年5月18日的登台演出,虽然它不是“高跷曲”的首次登台,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极为广泛,“高台曲”的称呼由此流传开来。第四,由于汝州是洛阳通向豫南、豫东南的必经之地,加之本地人们的特殊喜爱,汝州出现了大量的曲子班和高水平艺人,也吸引了洛阳、南阳等地的许多艺人前来搭班演出,有力地促进了河南曲剧的传播与辐射。如1927年春,关遇龙曾邀集龙门镇南北的曲剧名角如朱天水、刘保才、李久长、朱天水、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等,前往汝州市临汝镇,与另外两台梆子戏和一台越调戏“对戏”,结果连战连赢。接着又获邀至汝州城连演18天,轰动大街小巷,“三朱”的美名由此叫响,打开了汝州、洛阳、南阳、许昌、郑州、漯河等地的演出市场。
从演出实际和现实需要来看,高跷曲艺人卸掉高跷、登台演出的最大贡献,是将艺人的双腿解放出来,直接促成了肢体的解放和表演动作的发展,促使河南曲剧成为一个成熟剧种,这是河南曲剧形成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高台曲的形成,无疑与民国初年的时代风尚息息相关,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内乱、外患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乱世,但却形成了地方戏遍地开花的特殊现象。究其原因,与人们历经苦难却坚韧乐观的民族性格有莫大关系。尤其是豫西地区,由于地处伏牛山脉东部相对封闭地区,虽然军阀争斗不止,赋税兵役沉重,土豪劣绅仗势欺压,但是社会局势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当地居民以农业耕种和山林资源为凭,尚可勉为维持生计。社火是当地百姓精神寄托、娱乐享受的重要途径,数不胜数的各类节日庙会则是其繁衍不息的重要载体。王凤桐之所以创制“高跷曲”,初衷就是为了参加正月十三的关林庙会,与其他社火一决高下,其后的“高跷曲”玩友基本上都是借助于神社而开展活动。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不免对戏曲有着更为狂热的精神需求,但“高跷曲”受限于高跷的动作和节奏拘束,放不开手脚,与豫西人民追求大开大合、热烈奔放的审美追求存在很大差距,于是,由“高跷曲”演变为“高台曲”也就顺其自然了,使表演空间得以大大扩展。
三、因情而变:审美情趣促进了艺术风格的成熟
“高跷曲”已经具有戏曲的特征,成为分角色(生、旦、丑)演唱、以第一人称展开剧情、唱腔戏剧化的“三小戏”。但是,王凤桐的改革还存在不足,主要是唱腔音乐仍采用鼓子曲的大曲牌,“存在着唱词字少哼哼多,妨碍对唱表演,唱腔音低声粗,离远听不清的问题”[2]18,抒情和叙事能力受到很大制约,不利于深入揭示人物的情感变化和戏剧性冲突的展开。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重要人物,是关林镇大屯村艺人谢新富(1887—1950)和汝州市杨楼乡郑铁炉村艺人朱万明(1891—1962)。
谢新富的贡献在于摒弃了[背弓][铺地锦][码头]等低沉舒缓的大曲牌子,代之以明快爽朗的杂牌小调,如[阳调][满舟][银扭丝][剪剪花][汉江][渭调][呀呀哟]等,并参照陕西眉户调高音区的音乐旋法,升高这些曲牌的音区和坠胡的定弦。改革后的“高跷曲”唱腔高昂清脆,极大开发了演员的高音区音色,较好解决了唱词与旋律的配合问题,使艺人能够轻松适应嘈杂喧闹的广场式演出。谢新富还指导朱六来、张五魁等艺人对曲牌表现进行了规范,如叙事观景时就用[阳调],惊奇兴奋时用[剪剪花],愉快高兴时用[银纽丝],悲痛哭诉时用[汉江]等。“民国初,洛阳大屯‘高跷社’郑云升、宁文定、谢振乾、张孟林等率先使用新调演唱,颇受观众的欢迎,一举击败了洛阳七里河、谷水、白碛、王屯、范滩等洛河南北岸所有的曲子班社,名声大振,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洛阳新调曲子,后叫洛阳小调曲。”[1]365此外,朱六来参照谢新富的曲牌革新方法,创制了《蓝桥会》中的相公唱法;朱双奇创制了具有眉户调风味的丑角唱腔。
朱万明长年来往于洛阳、汝州之间,学习谢新富所创的小调曲子的同时进行了润色改进。同时,他还创制了[小汉江][书韵][慢舵]等曲牌,丰富了“高跷曲”的唱腔音乐。此外,朱万明还对主奏乐器大弦进行了改造,即后来的曲胡;他还在乐队中增加了锣、鼓、镲等打击乐器,吸收了京剧等的锣鼓点,丰富了河南曲剧的打击乐。
这种艺术风格的戏剧化转变还体现在演员们对河南梆子、京剧、扬高戏等大戏的唱腔、表演、舞美、乐队、锣鼓经等的借鉴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艺人开始进入城市演出,如许昌、开封、周口、南阳、洛阳等,这就为他们接触其他戏曲创造了良好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曲剧的班社遍及全省各地,周边省份也有演员们的演出活动,一些艺人沿着陇海铁路流亡到了陕西西安、宝鸡、甘肃天水、兰州等地。因此,艺人们开阔了艺术视野,与其他戏班子有了更多交流,戏曲表演程式逐渐正规化,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培养了一大批城市观众。同时,曲子戏的艺人们还保持着质朴生动、风趣幽默的生活化艺术取向,剧目以民间生活题材居多,如《李豁子离婚》《小姑贤》《小姑恶》《蓝桥会》《闹书馆》《安安送米》等,这是河南曲剧能够在激烈的城市演出市场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
河南曲剧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并迅速发展,关键在于“高台曲”阶段,艺人开始进入城市戏院演出,并扎根落户,在其他戏曲、说唱、歌曲、歌舞等艺术的影响下,高台曲的艺人们加快了河南曲剧向大戏发展的步伐,为科班训练创造了条件,这是艺人为适应市民阶层审美口味、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审美情趣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四、因戎而播:军事活动促进了曲子戏的广泛传播
军队养班、随军演出,是推动河南曲剧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期间,中原是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驻豫旧式部队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一些军事长官出于个人家庭爱好、丰富官兵文化生活等目的,往往大量招募曲子戏演员入伍当兵,组成戏班子随军演出。例如,20世纪20、30年代任国民党第20路军总指挥兼河南代理主席的张钫便非常喜欢听曲子戏,文明河南的四朱(朱万明、朱六来、朱天水、朱双奇)不仅为他和家眷唱过戏,他们所在的曲子班1934—1935年间曾随二十路军到江西的九江、南昌、南城,福建的光泽、邵武、崇安、建阳等地长期演出,有力促进了河南曲剧的传播交流。其他如驻扎唐河的228旅旅长范龙章、驻扎方城的226旅旅长李万如、45师师长戴民权等军官,也都十分嗜好曲子戏,频繁也请各地曲子班到驻军演出。
驻豫旧式军队对河南曲剧演出有着极大的需求,曾经招收了大量的汝州籍艺人随军演出,按照兵饷标准发放,这对战乱年代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仅能解决温饱,还能养活一家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促发了更多汝州籍人士从艺,其他地方的艺人也争相投身从戎,凭借一技之长满足官兵的文化娱乐需要。例如,曾任国民党39军副军长的戴民权,曾多次派人回家乡(临汝县)招收曲子艺人,1933年秋,找到临汝县艺人卢天德,召集了宗银聚、张金元等7人组成戏班随45师巡回演出,每月饷银不含伙食费8块银元。朱万明、朱六来、关遇龙等人曾多次回到老家,招募家乡的艺人到军营唱军戏,因待遇优厚,曲子艺人争相投军,如张钫1936年麦罢,在临汝县一次性招收了70多人到南方为士兵演出[7]。借着到各地演出的机会,艺人们还移植了京剧、梆子戏等传统剧目,如《宋江杀院》《苏三爬堂》等,丰富了曲剧的题材内容表现。
这种随军演出形式,是一种面向特定人群、循着特定路线的点状传播方式,在中原文化区域内,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在当地生根开花;而到了江西、福建等异质文化区域,主要在城镇和兵营等封闭区域演出,一方面固然可以被当地的客家人和河南人所接纳,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难以生根发芽、落地开花等现象,更主要起到的是展演、宣传、展示等作用,也在无形中扩大了河南曲剧的影响力。
五、余 论
以上所述四种要素,是促使河南曲剧形成的决定性成因。而河南曲剧能够在众多地方小众脱颖而出,与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有着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积极吸收和借鉴戏曲、说唱、歌舞、民歌等音乐形式的有益成分,这是河南曲剧由小到大、迅速成为一个成熟剧种的基本前提。例如,朱万明创制[慢舵]的灵感便是直接来源于黄河船夫的号子声调,成为河南曲剧的重要声腔。早期河南曲剧的身段表演、角色划分、道白吐字、演员服装、乐队编制、锣鼓经和剧目等,几乎都是艺人从当时流行的秦腔、京剧、河南梆子、越调等剧种借鉴、吸收而来,使艺人基本具备同其他戏曲相抗衡的实力。
第二,艺人执着进取的精神和职业化转变,使河南曲剧迅速适应民众阶层的审美趣味,成为促成河南曲剧的内在动力。在当时封建思想浓厚的环境中,许多艺人冒着被斥为“戏子”的风险而投身河南曲剧的创建事业当中。汝阳县艺人李久长(1906—1990),17岁开始踩跷演唱,父亲一怒之下差点将他活埋,被禁家中长达3年不得出门。但李久长仍想方设法坚持,1927年元旦在许昌市戏院演出后一炮走红,被誉为“仙家娃”。在河南曲剧的创始时期,像这种积极投身其中而忘我奉献的艺人比比皆是,为河南曲剧的壮大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后备人才。同时,众多戏社进入城市剧场后,收入分红制就取代了以前的接红贴、送红包和均分制,激发了演员的积极性。可以说,城市剧场演出、收入分红制和科班的出现,是艺人职业化的必要保证,保证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第三,普通百姓对于河南曲剧具有强烈的文化需求,这是形成河南曲剧朴实风趣的民俗风格的社会基础,更是维持艺人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艺人长期依附于乡间的庙会、社火、婚礼、丧葬等民俗活动之中,以普通民众阶层为演出对象,所以演出风格大多朴实风趣,深受人们欢迎,听曲子成为民众娱乐活动中的重头戏。每逢河南曲剧演出,周围村庄必定蜂拥而至,看戏误事有之、误工误活有之、争抢位置有之、挤塌墙壁有之……例如,以关遇龙和朱万明为首的同乐社曾在1928年秋收后,受嵩县德亭乡的大户梁素的邀请演出,但由于路途遥远,时有土匪出没,梁于是托亲靠友,派人持枪分段护送,将“三朱”安全请到了家中,使演出顺利进行。可以说,正是由于当地广大民众对河南曲剧的如痴如醉,才使艺人的表演风格得以形成,才使艺人生存的物质基础得到保障和巩固。
第四,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是河南曲剧迅速壮大的经济基础,为河南曲剧赢得了提升艺术品位的雄厚实力。随着艺人的职业化发展和专业戏班的兴起,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便应运而生,以便适应城市的演出市场和演出对象。例如,汝州市骑岭乡艺人关遇龙,被誉为河南曲剧史上功勋卓著的首位组班人,之所以能够将洛阳、汝州等地最优秀的艺人凝聚在他的班社中,就在于他具有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在演出班规、经济收支、市场宣传、后勤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班社迅速发展壮大,影响迅速扩散至中原各地,甚至远播湖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份。这种运作方式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扩大了演出市场,演员的报酬得到大幅提高,形成了提高艺术水准的激励措施和淘汰机制,引发马太效应,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从经济层面保证了河南曲剧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