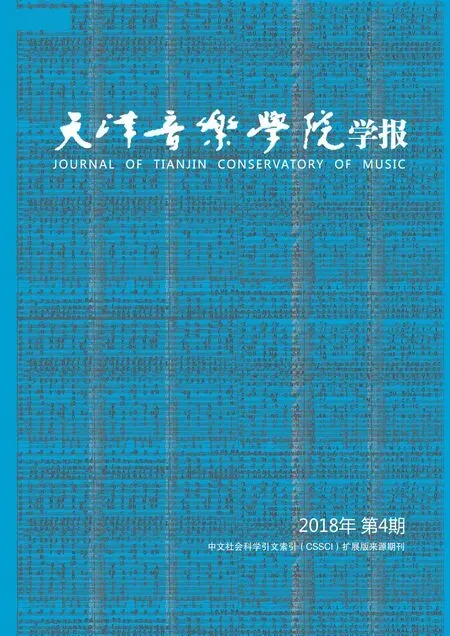第九届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会年会纪实
马国伟
2017年11月23日至25日,第九届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学会年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本届会议由东北亚音乐研究所、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会、韩国釜山国乐院主办,韩国釜山大学、韩国音乐文化学会承办,并由韩国釜山大学产学协力团和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协办。来自中国、韩国、蒙古、泰国等国家共5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近40位学者分别参与了学术谈论。会议为期三天,首日在国立釜山国乐院举行,后二日在韩国釜山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厅进行学术研讨。
11月23日上午九时,会议开幕式在国立釜山国乐院艺池堂举行,东北亚音乐研究所权五圣先生致开幕词,他代表会议主办方欢迎各国专家学者到来,并希望东亚音乐考古学术研讨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并发扬光大。王子初先生代表中方致开幕辞,首先感谢本届会议主办方韩国釜山大学,随后他在致辞中强调了音乐考古学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古代音乐史研究需要构筑传统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等多学科史料系统研究。王先生还介绍了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为音乐考古研究作出的努力,希望郑州大学能与各国学者进一步交流,建设一个音乐考古研究者的学术基地,最后他代表中国音乐史学会、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感谢韩国国立釜山大学为举办这次学会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国立釜山国乐院徐仁华院长代表此次承办单位介绍了韩国国立釜山国乐院的历史和现状,并简要介绍了釜山岩刻画、墓葬等相关资料,她对这次音乐考古学会在釜山举办并为各国学者提供认识和了解釜山的学术交流机会感到荣幸。
开幕式结束后,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会议由权五圣先生主持,来自郑州大学王子初、釜山大学崔昍、华南师范大学孔义龙三位教授分别发言。王子初先生为此次会议撰文《音乐考古学在中国》,专文介绍音乐考古学学科沿革、性质以及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从197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会议将音乐学与考古学学科合二为一开始,梳理了美洲与欧亚系统中考古学的学科旨向。他认为,尽管亚洲、欧洲及美洲等地区都有考古学,但分属历史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音乐考古学在国际上兼收并蓄两种学科思维,欧亚音乐考古学更注重对物质遗存的研究而非社会生活习俗的解读。中国音乐考古学延续宋人金石研究的思路,对古代人类社会音乐生活中间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20世纪70、80年代发掘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和贾湖骨笛,不仅推翻了以往对先秦音乐史的认识,更为揭示中华民族音乐文明起源提供了参考和依据。迄今为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共出版了19卷,它是在中国音乐考古研究蓬勃发展中编撰的一套丛书,和音乐考古人才培养共同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发展。籍中国音乐考古学历史渊源,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丰硕成果及学者们共同努力,中国音乐考古学和国际音乐考古学学科研究必将走向新的高度,迈上新台阶。釜山大学崔昍《骨笛研究》从韩国新仓洞、唐岭洞等地出土的弦乐器残片介绍开始,他援引朝鲜学者的考古结论:朝鲜一处遗迹发掘了一支骨笛,时间可以推算到公元前2000—1000年左右。骨笛有13个孔,与《乐学轨范》里大笒孔数一致,认为可以推定韩国乐器在公元前已经出现。对于发掘的13孔“骨笛”是否适宜演奏,是否是乐器,他和宋方松、宋慧珍、李金元等学者都持怀疑态度。崔昍教授对照中国裴李岗、河姆渡文化出土资料,认为尽管贾湖骨笛已经有了五声或七声音阶,但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是骨哨,因此对贾湖出现骨笛是否是乐器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提出“五声七声系统,是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慢慢到汉代正式的确立?”华南师范大学孔义龙《回归本源——从羁縻制看岭南铜鼓乐的兴衰》一文,关注羁縻政策下岭南铜鼓文化的发展。文章从四个方面讲述制度和铜鼓文化的关系。该文介绍了铜鼓形制发展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即周代铜鼓、汉唐铜鼓、宋元铜鼓和明后铜鼓,这些铜鼓大致反映出形制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伴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变,也伴随着审美功用的演化。该文指出,周代时期早期铜鼓从云南西南传播过来,铜鼓兼有炊具和乐器功用,鼓面通常装饰太阳纹及水鸟,反映出当时民族的文化信仰,也体现出铜鼓祭器的作用。汉唐时期在羁縻政策的进一步影响下,铜鼓文化高度繁荣,铜鼓体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代表强势文化的硕形铜鼓虽然继承了早期铜鼓特征,但太阳对应的万物生衍更代表着阶级教条与社会执法,硕形铜鼓在当时只属于上层阶级,铜鼓不仅作为乐器更作为礼器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宋代产生土司制度以后,两种强势文化碰撞导致豪权削弱,文化下移,铜鼓应用范围更广,功能更丰富,逐渐普及融入人们的生活,这个时期铜鼓纹饰与审美融入了更多的汉文化,铜鼓甚至运用丧葬礼仪等民俗活动中。明代“改土归流”以后,闽南铜鼓文化属性脱落,铜鼓土著文化外在形式不仅发生改变,其民俗信仰和审美等内在结构也发生了汉化。“改土归流”过程中宗族制度同步推行,铜鼓的政治功能被削弱,土著文化也越来越弱化,铜鼓乐也逐渐蜕化到土著民族中,经过千年制度变化,铜鼓又回归到本来的乐器功能。上午会议研讨结束后,釜山国乐院演奏团还为嘉宾进行了一场传统的器乐表演。
23日下午,研讨会分三个单元进行,分别由王子初、张翼善、李庸植主持,研讨内容主要涉及部分地区的音乐考古发现以及乐器研究。韩国岭南大学朴昭铉《蒙古弓弦乐器轧筝(Yatgalig)再考》一文提出雅托噶的演奏方式也可能为拨弦。她对蒙古国和中国蒙古族的雅托噶类乐器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直到20世纪初才发现其足迹,并通过了解蒙古学者著述,认为雅托噶既可以擦弦也可以弹奏,她还去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寻找乐器资料,发现图片资料显示雅托噶是用二指、中指、食指来弹奏的乐器,并查询字典工具书,认为“蒙古的弓弦乐器轧筝、中国的牙筝以及韩国的牙筝是同一类乐器”。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秦巴特·巴相胡也对雅托噶进行研究,他在《复原和改良的蒙古宫廷乐器“国家雅托噶”(箜篌)》一文主要探讨13世纪蒙古宫中音乐使用的7弦、9弦、11弦国家雅托噶的复原和改良。文章从文献中寻找雅踏的“踪迹”,认为在14世纪波斯语和15世纪的诗里可见到这个名字,指的是横弹的乐器。雅踏这个名称到后期在古代蒙古口碑文学中多次出现,是一种来自天上的乐器,代表了勇猛和信赖。她通过研究13世纪的历史文化资料和口述资料,以及外国游客游记等文献,得出当时不是雅托噶起步阶段,而是发展阶段。13世纪的文献资料显示,雅托噶分为大雅托噶、雅托噶、国家雅托噶和非常雅托噶,而13世纪既有横弹雅托噶也有竖弹雅托噶,到了14世纪弦数增加,竖弹雅托噶逐渐变成了波斯雅托噶,所以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形态,雅托噶可以分为五种。
郑州大学陈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金仁淑及泰国玛哈沙拉堪音乐学院阿塞尼奥·尼古拉斯三位学者分别介绍了音乐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陈艳《近年中国重要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对近十年来发现的重要音乐考古资料进行了介绍,文中尤其对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墓和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三处音乐考古资料情况进行详细介绍。2009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盱眙大云山发掘了一座墓葬,墓主为汉代江都王刘非。墓中不仅出土编钟一套,而且首次见到文献中所说的“玉编磬”。王子初带领团队经过5年研究,成功复原并复制了这套编磬,这在国际上也是难得的音乐考古成果。2015年发现的海昏侯墓是近年来汉墓发掘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墓葬,出土器物数量多,并且同时出土编钟24件及编磬一套。汉代音乐考古资料比较少,这次海昏侯墓音乐考古资料出土,为汉代礼乐制度补充了重要资料。汉代以后,编钟的发现非常少,2013年江苏扬州发掘了隋炀帝与萧皇后墓,墓中出土了一套编钟,虽然16件编钟形制简陋,锈蚀重,无法测音,但这套编钟的发现对了解隋朝礼乐制度,以及研究隋唐礼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些考古资料的发掘,不仅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发展的日新月异。金仁淑《韩国考古学的考察》一文对目前韩国音乐学和考古学的沟通与交流提出看法。她从考古学调查发掘后的研究质疑开始,认为“韩国的音乐考古缺少沟通”,她援引韩国2014年发掘的腰鼓一例,认为研究者推断的“或许是东亚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个腰鼓资料”的结论缺乏推理依据,并且认为这些研究应该有音乐专业的学者介入。除了实物资料须考古学和音乐学学者共同参与研究之外,音乐学者对出土乐器的名称也应该有比较准确的解释。她希望韩国学界能够多学科共同参与考古发掘,协同研究,并呼吁韩国音乐考古学科要有一个新的起点。阿塞尼奥·尼古拉斯《10—17世纪东南亚锣的考古记录》一文对散见于中国南海海域及周边的锣、钹、钟等乐器进行整理,并对乐器进行测量和比较研究,尤其对平面锣和凸锣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并对所见锣进行分型分式。
除了对乐器及考古发现的研究外,有的学者对乐器上的纹样或图像、图鉴上的相关音乐考古内容进行研究。韩国全南大学李庸植《乐器文物中动物纹样的象征性》一文主要针对伽倻琴上的动物纹样进行探讨。他首先对伽倻琴代表性特征羊耳头进行考察,认为羊在高丽时期(金朝)才正式流入朝鲜半岛,所以羊耳头与羊进入朝鲜半岛的历史不太符合。他推测伽倻是受到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影响,伽倻琴的这个羊耳头不应该叫做羊耳头,而是受到南边佛教的双鱼纹的影响,并呼吁当代学者研究乐器的时候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檀国大学林美善《描绘1702年济州牧使李衡祥巡视的<耽罗巡历图>——济州官衙活动中的演奏和表演》对《耽罗巡礼图》中有关音乐表演的场景进行研究,探索18世纪初济州的音乐文化,并进一步对比朝鲜王朝后期的宫廷和地方表演文化的异同。在《耽罗巡礼图》中“船游乐”场景展现了1702年济州地区表演情景,由此可确认18世纪初济州地区的表演种类和形式同朝鲜中央地区的表演种类和形式没有差别,这也是推测朝鲜后期表演文化具有普遍性特点的主要依据。另外,从图中也可发现,直到18世纪初济州表演活动中才有唐琵琶使用实践,而呈才表演中伴奏使用的“三弦六角”还没有在济州出现。济州牧和县由于活动举办地不同,出现音乐等级的差别,组合乐器也有一定差异,但是大笒、筚篥、琵琶及教坊鼓等乐器是呈才表演的基本组合形式,在一些大规模呈才表演中会增加玄琴、伽倻琴等乐器。延边大学张翼善《朝鲜遗址遗物图鉴中的乐器探究》一文对朝鲜平壤出版的《朝鲜遗址遗物图鉴》进行研究。《朝鲜遗址遗物图鉴》是一本按时代顺序由多篇构成的考古学资料合集,近20卷。这部文献资料中有一支出土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骨笛图像,笛长17.2厘米,开13孔,距今约2000年。他通过对骨笛的观察和研究认为,骨笛开孔的地方宽窄不一,但音孔位置一样。为了弄清楚骨笛的发声和演奏方式,他用竹子仿制了骨笛,发现第十二孔和最上面的孔音高为八度,认为这可能是不均匀的十二律。
24日研讨会在韩国釜山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厅进行,研讨会分五个单元,分别由林美善、金宝姬、金仁淑、马国伟和郑花顺主持,研讨内容主要涉及出土乐器、乐舞、音乐考古图像的研究以及相关音乐考古文献资料的整理。韩国湖西大学朴恩玉《万波息笛与三竹》一文通过对文献资料记载的新罗管乐器进行检索,对新罗统一前后的管乐器相关文物进行了调查研究。韩国的传统乐器包括“三弦”(玄琴、伽倻琴、琵琶)和“三竹”(大笒、中笒、小笒),而大笒作为与中国和日本管乐器不同的独特的韩国乐器,对韩国音乐具有重要意义。最早记载“三竹”的《三国史记》对“三竹”有文献说明,说明中一起收录了“万波息笛”的神话故事,因此她提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层面的关系。为了解开“三竹”历史来源的问题,她对新罗管乐器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根据文献,新罗统一之前是没有管乐器记载的。新罗统一以前的文物可以见到7件土偶,时间约在4世纪到6世纪之间,乐器虽然不好辨认,但都是使用纵吹的演奏姿势,这可能是新罗统一以前唯一的演奏姿势。新罗统一时代横吹管乐器可以从感恩寺、石像寺中找到。从万波息笛的起源来看,在三国统一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三国统一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唐朝的帮助和影响,笛子出现了不同的演奏方法,而万波息笛强调新罗本土文化,与以往纵吹的笛和唐笛相区别,这种新出现的乐器很可能就是三竹之中的大笒。她又通过感恩寺和月池东宫的金铜版佛对比,可知当时新罗已经出现了大笒一类的乐器,不仅如此,三国时期当中首次出现了三竹的记录,为万波息笛是大笒类乐器的假设也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据。华南师范大学向娟慧《从出土器物看汉代岭南乐舞的发展状况》一文选取乐舞文化为研究内容,通过对汉代岭南地区历史变革的梳理,岭南出土器物的文化成分,观察该地区乐舞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汉代音乐文化对岭南乐舞的影响。她认为,汉代乐舞随着宫廷礼乐文化向岭南发展,在南越宫廷生根发芽,并与越族文化交流融合。南越国覆灭后,宫廷乐舞文化流向民间,在岭南贵族阶层以及民间乐舞文化中延续。汉乐文化传入,提升了南越音乐文化高度,也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丰富面貌。沈阳音乐学院贺志凌《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一文对2010年艾斯克霞尔墓地南发现的11件箜篌进行研究。文中不仅详细介绍了箜篌形制与数据,并且将出土箜篌做对比研究。她发现,出土较为完整的几件箜篌在材质、结构、比例、发音原理、具体形态及制作工艺等方面体现出较为一致的共性特征。她进一步通过对乐器形制和构造研究认为,这些角形结构箜篌体现出的特征更符合横置的演奏方法,这对且末、鄯善两地出土箜篌资料“横置”或“竖置”的争论也是一个有益补充。艾斯克霞尔南箜篌的出土,绝不仅是箜篌资料数量上的补充,它不仅丰富了以往对中国出土箜篌材质、结构、审美、功用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而且对其持奏方式、文化来源也有了更为肯定的判断,对于研究中国箜篌发展过程乃至中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韩国釜山大学金志玧《通过史料看笙簧》一文对图像、造型、器物等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以了解乐器笙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历史踪迹。他梳理了相关笙簧资料,包括庆北大学博物馆所藏石造浮屠、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碑像、崛山寺址僧塔、凤岩寺智证大师寂照塔身、实相寺百丈庵石塔、华严寺石塔以及上院寺、宝相寺和日本寺庙收藏的铜钟和梵钟。通过不同时期的资料,可以发现传入韩国的笙簧最早出现在有关佛教的石造物中,后在佛教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等都有使用。韩国清州大学郑花顺《韩国音乐史中琵琶类乐器的轨迹》一文对《三国史记》《高丽史·乐志》《世宗实录·五礼》《国朝五礼义序例》《乐学轨范》等相关音乐文献进行梳理,对文献中关于琵琶类乐器的内容进行研究,以了解唐琵琶、乡琵琶、和月琴三类乐器源流。文章通过对壁画及造型等相关音乐考古文物的考索进一步参证琵琶类乐器,试图在二重证据的考察中进一步考订琵琶类乐器的发展轨迹,并提出对韩国音乐史中琵琶类乐器变迁过程的旧识的商榷。延边大学郝娟娟《中国锣类探究》一文通过图像资料和文献史料,对锣的名称、尺寸、分类、用途、音响效果及比例等方面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她认为,锣在中国南方分布较多,在音乐实践上南方比北方更偏好锣。从统计情况看,在蒙古族、壮族、藏族等民族中,壮族使用锣较多,壮族人民非常喜欢在活动或音乐中使用锣。郑州大学孙晓彤《<抛球乐>向高丽的传播与发展》一文梳理了与抛球乐相关的文献,并对文献中描述的“抛球乐”表演形式进行考证。她认为,从目前可见的最早记录《抛球乐》的文献来看,抛球乐产生于唐代。唐代音乐传入高丽后成为“唐乐”,宋清时期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高丽有《抛球乐》的表演,并且基本沿袭了文献记载的演出形式,或根据表演场合进行简化。釜山大学姜惠贞《朝鲜王朝后期雅会图中琴的音乐图像解释学探讨》一文试图从音乐图像解说学的视角,探讨朝鲜王朝后期的雅会图中出现的琴。雅会图是一副描绘文人聚集在一起写诗唱和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画,与中国10世纪的“文会图”类似。雅会图系列在盛唐之后创作的原因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有关,尤其在明代流行的文人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王朝后期雅会图中衍生的花木是弹琴像上使用的主要素材。通过探讨朝鲜王朝后期的雅会图,可以了解宴会图中的琴是代表文人的象征主体。韩国国立国乐院陈允景《对平调和界面调的演奏学考察——以唐筚篥指法为中心》一文基于演奏学视角对《乐学轨范》和《梁琴新谱》中平调和界面调的分类提出新的看法。她认为,不仅平调(徵音阶)和界面调(羽音阶)的分类方式,不适合分析传统音乐多种调式调性乐曲,而且从演奏学的角度来看,平调和界面调讨论现今器乐曲也是不合适的。她通过对比中国、日本、亚美尼亚以及朝鲜半岛演奏方式与记谱,希望藉此探讨平调和界面调是如何具体运用在唐筚篥的散形和指法中。
王清雷(中国艺术研究院)、徐长青(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文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玲玲(中国艺术研究院)、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著的文章《谈谈对海昏侯墓音乐文物的几点初步认识》对2015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海昏侯墓出土音乐文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海昏侯音乐文物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文中认为,海昏侯编纽钟14件,最小一件没有鎏金纹饰,非本套纽钟。他们对部分纽钟进行了测音,发现其音色优美,音高准确,均为实用器。有的甬钟器身刻有音名,其中刻有“宫”音的甬钟音高恰为小字一组c。墓中同时出土一套铁编磬,也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一例铁编磬。另外,他们对乐车库出土的铙进行质疑,认为这是久已失传的镯,而非铙。对海昏侯音乐文物的整理中,他们获得了许多新的发展和认识,对汉代音乐考古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看法,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也将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得到检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曹葳蕤《<文物>(1990—2016年)所载打击乐器类音乐文物资料的梳理与研究》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伟岸《<考古>(1990—2016年)所载打击乐器类音乐文物资料的梳理与研究》二文分别对近十几年《文物》《考古》刊载的音乐文物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文中对乐器种类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尤其对其中的打击乐器音乐文物资料做了全面详细的梳理,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与研究。作者认为,《文物》《考古》近十几年记载的打击乐器包括陶响器、铃、编钟、磬、鼓等分别有18种1331件和12种1246件,其中许多乐器名称的厘定出现专业性错误,如扁钟与甬钟,纽钟与镈,“振铎”与镈,铜铃与铎等,这些名称错误有时引起对乐器种类和性能的误读,因而乐器的命名需要专业性指导。除了名称问题之外,文中还对部分音乐文物资料的断代问题以及乐器时空分布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音乐学院王军《匈、汉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神木大保当汉墓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研究》一文对陕西神木县大保当镇的汉墓群里的音乐图像进行考察,发现尽管26座墓葬多数被盗扰,但音乐图像资料保存较好,造型完美,内容涉及古代百戏、说唱及舞蹈等场面。作者认为,墓葬群中有关音乐画像所呈现出的文化信息表明,墓葬的主人为匈奴人,“精美画像石是汉化了的匈奴人,沐浴汉族文化的历史再现”,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匈奴和睦友好的见证。这种匈、汉民族友好相处的描绘在历史文献、或者类似石刻、壁画的考古发掘中,都很少见,弥足珍贵。韩国延世大学金宝姬《佛教仪式乐器小考》一文对三国时期、高丽王朝、朝鲜王朝的法器如梵钟、鼓等进行了介绍,并且梳理文献资料中佛教使用的乐器,并对这些乐器进行了分类,对乐器的功能和用途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日本真言宗寺院密宗仪式中使用的金刚铃和金刚杵的用法进行了探讨。华南师范大学马宁《从汉代画像石看两汉时期的乐器发展》一文通过汉画像石这一材料,对两汉时期的乐器发展进行了梳理,着重对汉画像石上出现的乐器的种类及特征以及乐器的组合方式进行了考证。她认为乐器种类主要包括打击类、吹奏类、弹拨类三类乐器,鼓类乐器基本贯穿了两汉时期,在汉代乐器组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汉代非常重要的乐器,乐器种类趋于便于携带,音乐艺术功能从呆板无趣的礼乐音乐向娱乐化世俗化音乐的转变与过渡。汉代礼乐制度重要性逐渐在下降,俗乐艺术的地位上升,加上大量的外来文化,两汉时期的音乐艺术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风貌,而这种变化通过汉画像这种墓葬的形式镌刻保存了下来。全南大学诸晓星《<园幸乙卯整理仪轨>的音乐史意义》一文对1795年正祖李祘时期整理仪轨中的华城行宫班次图进行解读。华城行宫班次图以正祖母亲惠庆宫洪氏轿子为中心,随行人员组成多个乐队,乐队主要使用打击乐器和管乐器,可以看到鼓吹乐的表演。作者以华城行宫班次图探讨正祖时期用乐风格,整理并总结了图中出现的乐队的行列顺序、乐器的编排和名称,通过图像及相关音乐文献,对18世纪朝鲜行进乐队音乐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釜山大学朴正莲《中国古代“佾舞”的象征和内容在朝鲜的传承——以 <乐书孤存 >之“舞义”为中心》一文从中国古代“乐”和“舞”的角度来考察“佾舞”的观点,以及宗庙祭祀当中的“佾舞”。她认为,朝鲜“佾舞”虽在服饰和动作上有传统的象征和表现,但在内容和娱乐性方面与传统偏离,其原因是因为朝鲜文人对此理解不够深刻,过分依赖过去跳舞方式,应该根据丁若镛提出的这种现象,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宗教“佾舞”的状态。除此以外,她通过查找宗庙“佾舞”的相关文献,认为之所以发生改变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韩国的“佾舞”当中还是一直传承了原本的特征。
25日上午研讨会在韩国釜山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厅继续进行,共有来自中韩两国的7位学者进行了发言。郑州大学乔军《汉代区域乐舞画像艺术之比较研究——河南、山东地区汉乐舞画像比较研究》一文关注豫鲁地区汉代画像石乐舞题材,对两地发现的画像石进行了梳理,用对比的方法观察两地乐舞画像石的风格特征,总结二地的风格分别为庄严肃穆和浪漫灵动。她认为,齐鲁地区画像石多反映儒家礼乐教化、宴饮享乐和仪仗出行的题材和内容,出现了大量的礼乐、祭祀、游猎、车马出行的场景,“呈现出一种质朴厚重、刚健秀丽之美,渗透出深沉凝重和朴实严谨的儒家气息。”河南南阳地区汉乐舞画像渗透着浓厚的楚文化,音乐风格浪漫迤逦,艺术形式新颖多变,内容富于创造与想象。郑州大学贾琳《唐代乐舞文化特征探微》一文探讨了唐代乐舞兴盛的原因:唐代乐舞兴盛除了与统治阶级爱好与提倡有关,国力强盛和开放的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全面繁荣。她分析了唐代三个历史阶段的舞蹈文化特征,认为初唐时期舞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展现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盛唐时期乐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乐舞的功能专项娱乐性质,而到了中晚唐时期文化风格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舞蹈作品风格更加多样化,作品及表演从宫廷向民间普及。华南师范大学陈君《从南戏<琵琶记>版本岭南本土化看岭南的戏曲发展》一文通过分析潮剧《蔡伯喈》和粤剧《琵琶记》改编的形式与内容,观察二者与南戏《琵琶记》的关系,她认为“潮剧的直接来源是南戏,但也受到了弋阳腔、民间歌谣等的影响”,潮剧《蔡伯喈》对南戏《琵琶记》的改动是小部分的,而粤剧《琵琶记》从唱腔、唱段、台词、舞台动作等方面都是自创,可以观察到南戏《琵琶记》进入岭南地区的本土化改造过程。东北亚音乐研究所权娜《欧洲联盟音乐考古学相关学术活动现状》是一篇记述欧洲音乐考古学项目(European Music Archaeology Prpject)和近东音乐学在线(Near-Eastern Musicology Online)活动的文章。通过EMAP和NEMO的活动情况的整理,探讨这些活动的现状和积极性作用。郑州大学马国伟《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音乐考古发现》一文对长江下游跨湖桥、青莲岗、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吹奏、击奏类乐器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认为从距今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开始,长江下游地区主要发掘了骨哨、陶埙、摇响器、陶铃和陶鼓,这些乐器发现主要体现了三种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这三种文化也是先吴越地区音乐文化的主要构成。郑州大学王芳《中国古筝与朝鲜半岛伽倻琴的对比研究》从形制、演奏技法、演奏方式以及文化属性等方面做对比研究,她认为“古筝和伽倻琴之间在古时候便渊源颇深,伽倻琴是朝鲜人民依据中国古筝再融入本民族的文化所创造的,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郝永光《韩国上院寺梵钟上出现的乐器性格考察》对韩国江原道五台山上院寺梵钟上铸刻的飞天奏乐图像进行考察,意图通过对梵钟乐器的考察了解哪些乐器是朝鲜半岛的本土乐器,哪些是随着佛教音乐一起传入朝鲜半岛或先于佛教音乐传入。
此次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年会继承了以往年会的学术传统,不仅介绍了东亚地区近年音乐考古新发现,而且在相关研究课题中有新的认识与收获,取得一定的进展。与会学者在一些研究课题中相互交流,交换意见,促进东亚地区音乐考古学科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特别是各地音乐考古新生力量的加入也为音乐考古学科带来了活力。会议于11月25日中午举行了闭幕仪式,并同时宣布第十届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年会将于2018年10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孔义龙代表下届承办方真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