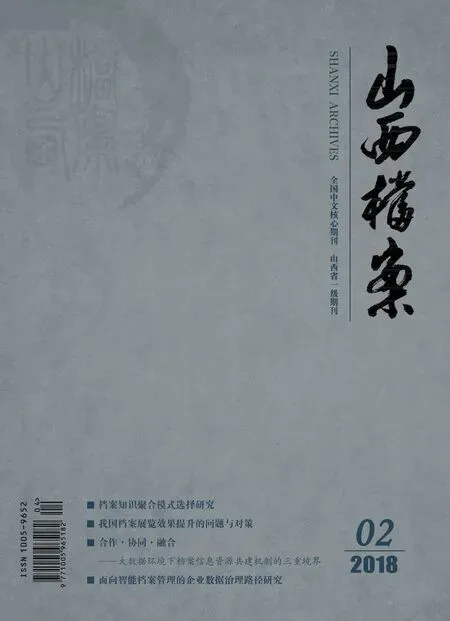设计的“本土化”问题: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
文 / 武敏 夏志丽
曾几何时,“西域”几乎凝聚着所有中国人的全部想象,因为那里有中国人梦想死后去的极乐世界——“西天佛土”。而如今在“西天佛土”呆腻了的所有西方人,以及终于见识了“西天佛土”的中国人,都转而来我们“东土”寻找“灵魂的家园”,仿佛一踏上这片“净土”就能羽化而登仙。艺术家们再也不会将毕加索、弗洛伊德挂在嘴边,而是纷纷祭出了“本土化”的法器。尤其是在今天,追求中华文化的再次复兴与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成为国内各领域的文化选择与诉求。对于设计的从业者而言,无论是在文化立场上还是在专业的思路上,中国当代设计如果不在“本土化”的方向迈进的话,似乎也没有太多别的出路。但无论是建筑设计、平面设计还是服装设计,整个中国设计领域的“本土化”实践,似乎更多的是一些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的堆砌,更多的是在迎合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情调”,当然这种对“东方情调”的追求不仅仅是设计界的现象,在别的文化领域如艺术圈中,这样的风尚可能还风头更盛一些。事实上这种“东方情调”是一种后殖民的产物。萨义德认为,东方是在西方中心论下凭空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念,东方主义反射出西方人的“权力象征”,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57也就是说,这样的设计最后只会变成西方文化的一种快餐,是一种假的“本土化”。实践上的“东方情调”与理论上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本应该是相悖的东西,却很有意思地成为中国当代设计的一体两面。这与我们对设计在当下所面临的历史契机的认识不足有关。关于对设计的反思,似乎多集中在特定专业的技术问题与思路上,而设计应该是与普罗大众最为息息相关的艺术门类。本文拟对时兴的“汉服运动”作一些剖析,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试图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设计现象与设计文化作一些理论上的反思。
一、“本土化”与意识形态
事实上,在中国不只是设计界,许多文化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建筑,都出现了追求“本土化”的思潮。这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断裂有关。在这些“本土化”的实践中,有些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和方式,如中国现代文学中,莫言和马原的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实践,虽然也有争议,但它体现了中国文学和现实的延续性,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当代建筑领域,王澍积极践行的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以及马岩松效法自然的“山水城市”等,作为一种对现代建筑的批判和反思,在当代显得尤为可贵,同时有着很强的创造性。在某些领域,“本土化”的实践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例如,近来学术界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所推行“汉服运动”,以及一系列恢复传统生活行为准则的活动,其本意也许是好的,说明整个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现代都市生活对人的“异化”,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归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但它在实践上却走到了一种极端的境地,从一开始的“汉服运动”到后来的“祭孔”,以至于“女德班”,甚至还出现了重新推行裹脚的习俗,这样的“本土化”实践就显得尤为可怕、可笑。事实上这种行为不是在重新发现一种文化,而是在推行一种意识形态,即全面恢复封建礼教和行为规范。这不仅无法使当代人脱离“异化”的困境,更会使人重新沦为旧道德和陋习的奴仆,更是对近代革命的反动。
二、“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汉服运动”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因为其中的“汉服”是以汉代和明代的服装为蓝本,力图消除“异族”印迹,将汉族的统治作为正统,舆服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中从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在中国,衣服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但传统服饰的消亡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国服的建立也是被政治所裹胁,每次改朝换代都会影响服饰制度的变迁。不同的服饰代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阶级。关于舆服,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大量的典章制度,例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引起朝野的轩然大波。清代满人入关又是一场“辫服风云”,引发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惨剧。直到民国,辛亥革命中重要的一环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首要的又是剪发易服,由是将中山装定为国服。如果说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的规训,那么中国历代的服饰制度则是这种规训在人的身体上的延伸。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和多元性都是一种事实。而且,在现代广泛被视为中华之“正统”的朝代,如汉代和唐代,恰恰是多元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而之后由汉族统治的宋代被广泛认为进入中国的“近世”,中国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开始出现衰落。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史学家傅乐成曾经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2]343在这样的情境下强调“汉服”的正统性,被诟病为“皇汉主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日本设计界的镜鉴
我们从上述的“汉服运动”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到,在“本土化”当中,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尊重现实,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跟社会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文化革命同时进行的,所以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裂,因而恢复相对统一而全面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可能。当代“新儒家”推行的“汉服运动”,包括与之配套的各种祭孔仪式,只是试图简单地全套照搬封建的礼仪和行为规范。这种汉服的设计从来不考虑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也不考虑穿衣人的合适性,即这种设计从来不是注重功能性的、以人为本的。更何况“汉服运动”中的汉服,是一种山寨的汉服,工艺很差,配色也很俗,布织得也很差,并没有领略古代师傅们的匠心,只是抄袭了传统符号。这种行为本身就只是一种符号。事实上,“本土化”应该是一种创新性的实践,而不应该是将一种逝去的文化遗产照搬出来。其实,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模仿传统,都是一种模仿,甚至可以说都是一种抄袭,本质上都是对设计的背叛。在当下的处境中,我们更应该学习我们的近邻日本,作为同为东亚文化圈并且同样经历了历史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日本在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同样是对待传统服饰,日本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设计师,如20世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设计师三宅一生、山本耀司、高田贤三等。他们既非常了解日本传统服饰的精髓,又都有在西方的留学经历,能把握住西方最前卫的服装设计理念,甚至打破了西方对服装的认识,将东方关于服装的理念纳入到设计当中,完美地实现了传统审美趣味与现代设计语言的融合。
在这方面,日本的平面设计中也有许多非常经典的案例。像原研哉的设计,能够做到禅宗与极简主义的结合,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杉浦康平在《传真言院两界曼茶罗》的装帧设计,采用中国和日本传统的古书装订和画轴形式,并附有照片和图画,是西欧装帧形式不能比拟的,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些日本的经典设计案例,即便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很现代的,是有现代生命的,适合现代生活的,同时又体现着日本传统的审美原则与文化。这才是一种成功的设计。当然,这些案例的背后,是有着与中国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因为日本政府也在鼓励传统文化的复兴,日本人更是一直以日本文化为荣,所以日本传统文化没有断裂过。日本的设计师们对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比较成功的。在文化上,日本注重保护国家的传统文化,有一大批文人致力于保护日本的优良传统。由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以至于现在中国人甚至要去京都寻找唐风。我们要去遥远的异乡去寻找自己的传统是一件憾事,日本对传统的重视也令我们汗颜。而中国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与多年的闭关锁国,在四十年前才真正接纳西方现代文化。所以,中国的设计师在这方面显得先天不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不了解,可以说我们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技术上都有明显的不足,才导致了现在设计界所展现出来的面貌有特别多的模仿和抄袭痕迹。
四、设计师的天职
包豪斯固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设计的理念与思潮,且意在反对机器大生产时代产品设计的粗糙与不亲民,但它的国际主义风格也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产物。那种冷冰冰的设计,在今天是可以通过设计的“本土化”来使其变得有温度的。[3]但这种冷冰冰并不完全是包豪斯造成的,因为真正可教的其实只有技术,包豪斯只是在将设计技术系统化,变得可以传授,而文化和审美以及创新,则应该只能靠设计师个人的专业素养。设计师在面对传统资源时更应该探索的是一种方法论,而不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堆砌各种东方的符号和语言。今天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只有立足于当下东西碰撞的现实处境,找到真正的自己,才能实现真正“本土化”的设计。事实上,设计的“本土化”问题,是一个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要去恢复一种死的遗产,还是要去尊重和传承一种活的文化?这才是今后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1]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傅乐成.汉唐史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3]武敏.风景与构成[J].美术观察,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