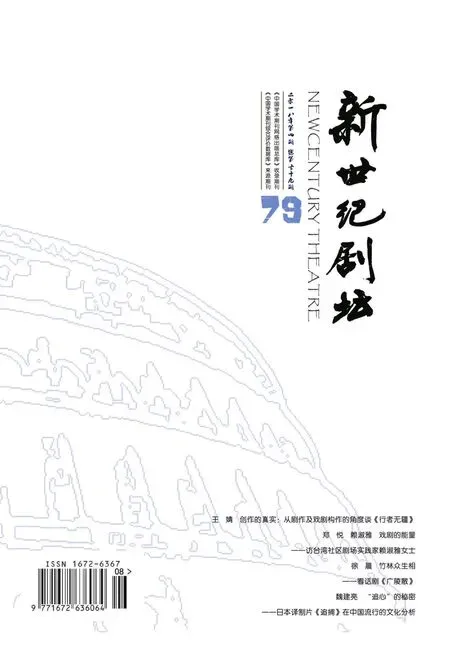走不出去的房间
——看NT live《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耶尔玛》
王 甦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 Live)伴着枝头第一抹新绿,开始在中间剧场放映,这一季的主题是“无处逃离”。上个周末,看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以下简称《谁害怕》)和《耶尔玛》后,当真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压抑,令人窒息。两部戏同样是家庭、婚姻题材,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没有孩子的家庭一步步分崩离析,走向瓦解。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作品。曾创作过《动物园的故事》《微妙的平衡》《三个高个子女人》的阿尔比一贯关注现实和幻想,剧作充满了喜剧包裹下的绝望。故事发生在历史系教授乔治和妻子玛莎的客厅,深夜,数学系年轻有为的教授尼克带着青梅竹马的妻子哈尼来做客。原本畅谈政治、人生、哲学、历史的愉快夜晚,随着酒精和游戏逐渐失控。
《耶尔玛》改编自西班牙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1934年的同名作品,改编者西蒙·斯通把故事背景由西班牙乡村转移到英国伦敦。33岁的女记者耶尔玛和经商的丈夫约翰原本很幸福,二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住大房子,喝昂贵的香槟,生活舒适而精致。一切的不幸起源于耶尔玛想要孩子的念头。
两部戏的舞美一繁一简。《谁害怕》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布景,一个精致的房间,沙发、壁炉、书籍、相片、酒,一个家该有的东西,台上都有。《耶尔玛》的舞美更加现代,高高的四堵透明玻璃围墙,通过更换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地面来区分场景,这是一个广义上只属于耶尔玛的房间。观众看她如同观察实验器皿里的小白鼠。
这是两间走不出去的房间。女主人都被困住了。玛莎和乔治结婚23年,婚后没多久玛莎就通过幻想孕育出一个儿子,通过大段的描述可以看出玛莎非常相信和依赖自己的幻想,几乎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她有过一段有爱情的婚姻,但被父亲拆散了,她也顺从地嫁给了父亲认可的配偶乔治。乔治看似绅士、温柔,但平庸、懦弱,就是个凤凰男,他没能成为系主任,更不可能接过岳父校长的职务。他不敢得罪玛莎,忍受妻子的酗酒、咒骂,陪着玛莎一起编造谎言,但他很清醒,要求玛莎不要对外人提到“儿子”,还声称这是“游戏规则”。他恨岳父,也恨妻子,这从他开玩笑似地用玩具枪对玛莎开枪就看得出来,他应该幻想过无数次枪膛里冒出的不是恶作剧雨伞,而是真枪实弹。但他不敢,他不能没有校长女婿的头衔。当玛莎用出轨来报复冷漠的乔治,乔治男人的自尊爆发了,他离开了房间,退出了“游戏”。当他再回到客厅,用宣告“儿子”死亡彻底击溃了玛莎。玛莎对幻想的笃信,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但她没有行动力,只能逃进幻想,编造幻境保护自己,维持生活下去的勇气。
阿尔比的作品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也不喜欢被概括。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充满恐惧和伤痛,沟通的欲望和自救意识很强烈,看似在沟通,实则封闭自我,拒绝交流,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玛莎看似强悍霸道,她受过教育,衣食无忧,但她根本不知道如何独立思考,也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她只能是校长的女儿,乔治的妻子。她反抗过,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幻想中的儿子身上,在幻想中,她让儿子离家出走,远离囚禁,获得自由。但乔治一句话就轻易地把“儿子”杀死了。
耶尔玛的房间看似开阔,实际更加闭塞。玻璃房间内的世界一览无遗,但里面的人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相比玛莎,耶尔玛的故事更有现代性和普世性,她像所有大城市的职场女性一样,阳光、自信、知性。她可以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可以在博客里自由发表评论,质疑丈夫的生育能力,吐槽姐姐的软弱和盲目生育。似乎,她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可一切都是假象。她想要个孩子。为什么想要呢?因为年纪大了,因为别人都有孩子,因为婚姻生活的平淡,因为世人认为,生育让女人变得完整。耶尔玛一直在不自觉地履行女人的义务,且行动非常积极。起先,耶尔玛只想孕育爱的产物,总不见消息,便积极自查,让丈夫检查,两个人的身体都没问题,但上天就是不肯给她一个孩子。而姐姐的婚姻生活一团糟,却接二连三怀孕、生产。出于亲情和礼貌,耶尔玛压制心底的嫉妒,当姐姐流产时,耶尔玛竟感到窃喜和庆幸,认为“上帝终于公平了一次”。求之不得的欲望,让耶尔玛的心逐渐被恶占据。为了生育,她无心工作,花掉了6万英镑,前后进行12次人工授精,结果依旧是失败。有着自由心灵的耶尔玛不断地自我催眠,要和别人一样,要履行生育义务,要忠于丈夫,欲望和不甘驱使她不断打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她开始沉沦,绝望地想和前男友发生关系,她要达到目的,即使不择手段。最终,耶尔玛失去了工作、丈夫和理智,她彻底疯癫了。耶尔玛最终用死亡实现了自我成全和求子之路的圆满,但她的死亡体现了创作者深层次的无奈。
物质的富足无法改变玛莎和耶尔玛精神的空虚。她们和无数男性剧作家创作的女性角色一样,美丽、智慧,但都不自觉沦为了婚姻生活中的弱者。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盛行时,《谁害怕》恰巧反映出女性的保守和循规蹈矩,精神和现实生活都受到父亲、丈夫的控制和压抑。而改编自当下的《耶尔玛》进一步撕开了现代婚姻制度的假面。新石器时代中期,孤独的人类终于开始了对偶婚姻制。一男一女为了生存结合在一起。而婚姻发展到今天,女性依旧没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人类的孤独的灵魂也没有得到慰藉,女人还是男人获得权力、地位的垫脚石,生育的工具。真可怕。
两部戏里的男性角色都极其理智,乔治清楚地知道幻想和现实的壁垒,他在戳破玛莎的幻想前,走出了房间;尼克也心安理得在人前享受着妻子的富有、恭顺、乖巧,连妻子假孕这样的伤心事也拿出来炫耀。约翰看起来对耶尔玛忍让、关怀,但他在丈夫岗位上的缺席和漫不经心,是逼迫耶尔玛走向偏执和疯狂的催化剂。当女人们伤心、流泪、绝望、求助时,男人们忙着喝酒、应酬、赚钱。
玛莎和耶尔玛都不愿接受人生和婚姻的不圆满,她们寻找出路,积极地争取,但抗争最终都会失败,幻想都会破灭,很残忍。这是剧作者下意识透露出的态度,即使有悲悯,依旧没有为玛莎和耶尔玛打开封闭房间的大门。
诚然,“茶花女”“包法利夫人”“莎乐美”等经典女性文学形象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但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一种转换。玛莎和耶尔玛的故事都是悲剧结尾,一个没有了幻想的救生衣,早晚溺亡;一个到死都没能摆脱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劣势。
两部作品的演员都很出色,尤其《谁害怕》的女主演艾美达·斯丹顿,第三幕几乎成为她的个人演技秀,喃喃自语的独白、绝望失控的嘶喊和最后呆滞的破碎的只言片语,她把看似坚强,实则脆弱无助的玛莎塑造得张力十足,我们对她的挣扎和绝望感同身受。其他三位演员也贡献了教科书似的表演,唯一的瑕疵就是斯丹顿的表演比较用力,尼克的扮演者卢克·崔德威显得自然许多。这位曾在《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中带来精彩表演的青年男演员,在此剧中依旧演技精湛,眉梢嘴角总带着戏谑的微笑,将衣着光鲜,满腹私欲的教授塑造得活灵活现。
《耶尔玛》的女主演比莉·派佩8岁开始当演员,在英国也是家喻户晓的女星。她的表演风格很细腻,把耶尔玛由自信明朗、心有不甘、自我怀疑、挣扎抗拒、沉沦放纵层层递进地呈现出来,疯癫后,她也没有表现得过于歇斯底里,用收敛的方式表达痛苦和绝望。
玛莎和耶尔玛的痛苦极具现实意义,优秀的戏剧作品总能和当下产生共鸣。在女权主义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多文艺作品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近期的《海达·高布乐》《简·爱》都从不同角度探讨着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女性才能迎来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戏剧完成这样的使命,但这些作品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而国内影视界流行的“大女主”风行,恰恰也反应了观众对女性题材的偏好。只是女权绝不仅仅是所有人都爱“我”的玛丽苏,也不是随意改变游戏规则,碾压他人。
热心公益、独立自信的美国女演员艾玛·沃森曾拍摄过一组尺度很大的性感照片。有人批评她自诩女权主义者,却拍这种“讨好男性”的性感照。她的回应非常得体,“女性主义是给予女性选择权,女性主义不是用来攻击其他女性的工具。这是关于自由、关于解放以及平等。”
借用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作为结束,“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希望女性,在文学作品和现实中,都能有自己的房间,大门永远敞开,门外春花烂漫。